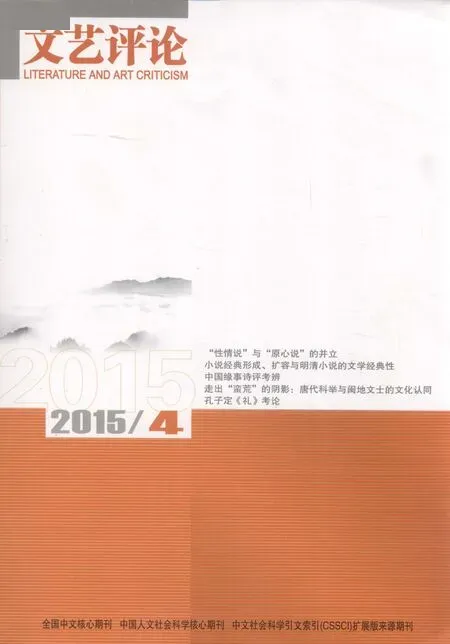小说经典形成、扩容与明清小说的文学经典性
李建武
小说研究
小说经典形成、扩容与明清小说的文学经典性
李建武
明清小说的文学经典性体现在哪些方面?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可操作办法?笔者近年来一直在探讨这些问题。
随着深入研究,笔者发现这涉及“文学经典”课题的最基本的两大问题:文学经典形成需具备哪些条件?文学经典是不是永恒的?
一、小说经典形成
小说经典形成所需条件很复杂,众说纷纭。这里引述一些著名学者的看法。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化有两极:一极是著作的艺术品质,另一极是文本的接受。只有艺术品质高、意义空间辽阔的作品,具有权威地位参与阅读和评论的作品,实现了两极连接的作品,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①童文以《红楼梦》为例讨论“文学经典”,突出了文学作品内在的意义和艺术品质,强调了意蕴内涵和艺术成就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性的内在因素,而文本的接受、读者的(持续不断的)评论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性的外部因素。这当然很有道理,笔者也基本认同,但童文也带来一些疑问:艺术成就要达到多高程度才算具备经典的条件?有没有可操作的标准和尺度?其所举之例是《红楼梦》,而它一般被认作中国古典小说成就最高的作品,明清其它小说名著的成就就要逊色于它。
平心而论,童文以《红楼梦》为例来论述经典形成的条件,确实是拔高了经典的标准,提高了“经典性”的“门槛”,让更多学者对经典的尺度无所适从。事实上,中国明清经典小说不是唯一的,除了《红楼梦》,还有其它经典小说,如四大奇书。而后者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如《三国演义》有“特征化”的人物塑造,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②的弊病;《水浒传》时不时对嗜杀成性行为不分好歹的宣扬,成为它不可忽视的弱点;《西游记》“八十一难”收伏妖魔的办法和结局大都有些类似;《金瓶梅》描写两性家庭生活有情色之弊。但这些缺陷的普遍存在并没有影响它们成为小说经典。所以,笔者认为,经典小说的缺陷应该成为经典问题讨论的内容之一,不解析经典小说的缺陷问题就无法全面理解经典的涵义,也会影响我们对经典标准的把握,并因此漏掉一些“经典”作品。只有理解了经典小说的缺陷问题,才便于我们确定“经典”的衡量尺度。
再看一些见解。刘象愚认为经典形成既有外在原因,又有内在原因。“经典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须经过上百年的时间考验,须经过反复不断地被阅读、被解释、被评价,须在众多教育机构不断被传承,这涉及到文学经典的“可复读性”。内在原因是文学经典的本质性特征,即“经典性”。具体而言,内在原因指经典需具有的丰富的内涵、实质的原创性,还有跨时空性和无限的可复读性等。③
这一类见解倾向于认为文学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伦理的文学名著,具有“超时空性”和“永恒性”。这种经典观被称为“本质主义”的经典观④,它把经典的构成更多地限定在文学作品的内部。
王宁则认为,成为经典的“最主要的因素不外乎这样三个:文学市场、文学批评和大学的文学教科书,并认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典的名单会发生相应变化。”而“任何经典文化和经典文学在一开始都是非经典的,有些一开始属于流行的通俗文化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的调整,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精英文化产品”。⑤
美国学者保罗·劳特(PaulLauter)认为文学经典具有变化不居的特征,经典背后所体现的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变化决定了经典也是变化动态的。⑥张立群则以《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为例说明经典是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并不是一经确立就是永恒的。⑦
这一类见解倾向于认为经典有时代性、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而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在经典的界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关注的是“谁的经典”,而不是抽象普遍意义的“经典”。这种经典观被称为“建构主义”的经典观。⑧其认为“经典是由于外部的因素所发明出来或至少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其自身先天的美学条件”,拒绝承认“文学经典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美学原则”,强调文学经典是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等外在因素建构出来的。
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釆取了折衷的态度。如童庆炳后来既指出经典具有永恒性,又强调经典的变动性、建构性。他认为经典形成涉及六个要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并对其关系进行阐述。⑨
笔者也认为经典的形成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即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是它成为经典的基础和前提,是经典作为必然性的存在。而外部原因,即人为的、文化的、政治的因素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不可或缺的中介或“桥梁”。任何文学经典作品都必须借助外在的因素被发现、被推介、被阐释出来,方能成为经典;否则终将是埋没于深山绿林中默默无名的“奇花异草”“寂寞伟木”。有时对作品的模拟仿效,如续书等衍生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走向经典的途径之一。因而,小说经典应是既具有高峰性、典范性的作品,又往往是某个时代或某些群体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的标志和反映。如:中国小说在上古阶段是“小道”,写的是“残丛小语”,被学人看不起;即使到了明清,出现了章回小说代表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但其地位并不高,故在那时中国小说是不可能取得经典地位的,没人谈中国小说的“经典问题”。后来,大量的西方小说理论被引入,尤其是人物性格论认为塑造生动的“圆形”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魅力。在这种审美标准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小说便在世界文学史上得不到“文学经典”的荣誉。现今,学术界又开始反思,思考文艺的民族特征,探索民族化的文艺之路;觉得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既应倡导小说理论的国际化,又应尊重小说理论的民族性。这时我国古代以情节为主的章回小说代表作又将开始得到高度评价,以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很多出版社开始奉之为“经典”。
所以,小说理论和评价标准的变迁带来经典小说名单相应的增加,即小说经典扩容。那么,是不是可以原创性、独特性和民族性来讨论小说的经典性呢?笔者以为,是可以的。通过考察文学作品的原创性、独特性和民族性来判断是否经典,也许是去掉民族虚无主义情绪的合适途径,也是小说经典扩容的基本手段。
二、小说经典扩容
“文学经典是不是永恒的”则属于经典扩容探讨的问题。为何要扩容经典?因为经典修正和经典扩容实质上就是经典形成的外部原因,是一种人为的、文化的因素在改变着经典作品的名单。笔者发现,西方人看待文学经典的标准比我们国内低。如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多是扁平人物,按国内一些学者对“经典”的高标准,狄更斯无论如何,是进不了经典作家之列的。但我们知道,杰出的小说理论家佛斯特就认为狄更斯足以“跻身于”世界“大作家之林”。⑩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按中国目前学界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进入经典小说的,因为它缺乏完整生动的性格塑造,但西方人却把它看成冒险家题材的经典小说。再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它的小说叙述与“性格人物是小说之魂”的小说观念是相左的,它以叙事和分析案情见长,没有性格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但故事新奇,“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⑪,西方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尤其是近年来英国女作家J.K.罗琳所著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尽管被认为“表现了虚幻和邪恶,这样的图书应该远离孩子,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罗琳的写作风格平庸,故事内容重复拖沓”,但还是被评为“深谙文学经典成功之道”。⑫尤其是这个系列小说因为畅销盛行,所以被认为是欧美新玄幻小说的经典。我们还可联想到欧洲杰出作家歌德曾高度评价过中国古代的二三流作品《好逑传》。⑬由此可见,西方人的“经典”观念和标准并没有我们国内某些人想象的那么苛刻。
当我们考察西方学术界的“经典修正”思潮时也会发现,他们也存在“使那样被埋没的作品重见天日的实际问题”⑭,“经典修正工程也进一步延伸到那些长期以来被普遍忽视了的、与经典文学作品不相吻合的文学体裁,例如哥特式作品、自传、日记、游记、浪漫史、儿童文学等等。而当人们把所熟悉的作品与其他一些来自同一块历史土壤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对于文学体裁等级的质疑与挑战”,需要“适当将经典书目的范围扩大”。⑮也就是说,经典修正需要打破传统经典文学观“一”统天下的单一制模式。
而当前已有了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想作为前沿性思想,我们更需要善于质疑前面已有的所谓的思想成果,我们更需要解构现有的等级制书写的文学史,修正以前等级制的文学史书写原则,力图以多元化方式扩大文学经典的范围,让经典增容。这样,呈现给我们的经典作品就不再是以往那种凤毛麟角的阳春白雪,不再是单一制逻辑思维主导下的经典名单。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过分降低经典的标准,仍坚持经典应是经常进入该类前两三名的作品。
笔者认为,一个让小说经典扩容的简便办法是将小说经典进行分类,即按文体、题材、性别、时代、载体、风格、口味等将类别分得更细一点。
如按文体分,可分为章回体、非章回体、韵文体、散文体(自由体)、文言体、白话体等小说经典;按题材分,可分为言情、武侠、革命斗争、改革等题材小说经典;按性别分,可分为男性、女性作家小说经典;按时代分,可分为古代、现代、当代小说经典。如说到中国当代小说,琼瑶小说是言情婚恋经典,金庸小说是武侠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是红色革命小说经典。也可按载体形式分,分为实体(如纸质)、虚体(如网络)小说经典。纸质小说经典还可按国别继续分。
还可按风格、口味分。如词以风格简单分,就是豪放与婉约词经典。小说的风格则有很多,如脂粉柔情的、平淡素净的、金戈铁马的,可按此给经典分类。口味方面,就像食物有麻味、辣味、酸甜味、咸酱味、蕃酱味、咖喱味、烟熏味等一样,小说经典也可按口味进行分类,如分为儿童、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或学者、医生等口味经典。⑯
为何要这样给小说经典分类呢?这本质上就是经典修正与经典扩容。小说经典只有按题材、文体和时代等来分,指某一类作品中有突出代表性、有重大影响力的小说作品。这种观念下的“小说经典”标准才既非太高,也非太低:才能正确地实现经典修正与经典扩容。
三、明清小说的文学经典性
通过以上讨论小说经典形成与扩容,不难发现:文学作品的“文学经典性”(liter-arycanonicity)就是指文学经典具有的本质性特征和丰富的内涵⑰;经典既有典范性,又有原创性、独特性和民族性,它往往是某个时代或某些群体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的标志和反映;经典也有变动性、建构性、时代性、历史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而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在经典的界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典形成是“合力”的结果,这些“合力”至少包含了文本、读者的接受、批评家的阐释、政治体制、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等。
正是带着这些基本思想观念,笔者来探讨明清小说的文学经典性。而为了节省篇幅,笔者选取七个方面:优质性和高峰性、陌生化和原创性、品牌性和名牌性、民族性、易传播性与易接受性、经典化过程的曲折性、丰富的可争议性和可阐释性来作为评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文学经典性”的依据。
为何要这么选?或者说,为何与当前学术界一些提法要有所不同呢?这其中原因首先是为了不人云亦云,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其次是为了弥补他人见解之不足,推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评判标准;再次是为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明清小说的文学经典现象与规律:明清小说经典与广泛意义下的文学经典肯定存在不同特征,明代四大奇书也肯定存在与清代《红楼梦》相异又相同的经典特征。
“优质性与高峰性”近似于学界的“权威性”。然而,刘象愚提到的经典的“权威性”⑱一词有较强的等级制嫌疑,童庆炳只以《红楼梦》为例论述经典具备的条件⑲,又容易导致大家对文学经典的门槛要求过高。而“优质性与高峰性”则只针对品质而言,这样,文学经典的门槛就会稍低一点(这就涉及经典扩容)。此外,采用“优质性与高峰性”诠释“经典性”的方法,有利于消融将文学经典成因分内部与外部因素的“简单切”做法的弊端,有利于改变以往将内容与形式艺术完全剥离开来的做法。因为很多时候,小说经典性既包含作品的内在品质的魅力,也包含外部特征因素(如易传播性、易接受性、经典过程的曲折性)所散发的一种气质。“优质性与高峰性”也是如此,它既包括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又包括其思想魅力。故用它替代学界使用的有等级制嫌疑的“权威性”这个概念,或许就更合适。
《三国演义》的优质性和高峰性表现在全景式展现中国古代战争的方方面面,最善于叙事,巧设悬念,相当多的事件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等。《水浒传》的优质性和高峰性表现在个性化人物塑造、多层次刻画人物、结构上连环勾锁与层层推进等。《西游记》的优质性和高峰性表现在有极强的幽默笔法、创造了奇妙绝伦的神幻世界、做到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等。《金瓶梅》的优质性和高峰性体现在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性格,有网状的艺术结构,具有中国小说向近代小说转变的轨迹,创造了人性问题上多个二律背反的典型文本等。《红楼梦》的优质性和高峰性则是以上小说名著优点的集大成,又扬弃了以上小说经典的诸多弊端,其成就是全方位的,艺术化和诗化色彩以及唯美倾向更强,浓重突显全方位大悲剧的审美趣味,彻底完成小说向近代的转型等。当然,优质性还包括小说的思想内容方面,笔者认为:受众人拥护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是明清小说成为文学经典的又一重要因素。
“陌生化和原创性”是前辈学者,如布鲁姆⑳、刘象愚㉑、童庆炳㉒等在评价文学经典时的共同提法,笔者也肯定这一提法,故直接采纳。
但笔者舍弃了学术界传统的“经典性包含不可复制性”㉓、“文学经典的不可改写性”㉔的看法。㉕为何要舍弃?主要是发现:这一提法经不起质疑与深入推敲,尤其考察明清长篇小说名著的文学经典性时。因为流传于世的明清长篇小说名著往往存有几个版本,这些版本之间有的是有较大文字差别的。如《三国演义》有《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本和《三国志传》系统本等,其版本相当复杂,如有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等;《水浒传》有百回本、百廿回本、一百零二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七十一回本等;《西游记》有世德堂本、杨闽斋本等;《金瓶梅》有万历本、崇祯本,即“词话本”、“说散本”等;《红楼梦》也有多种脂砚斋评本等版本。显然,它们不是续作、仿作,却分别都是四大奇书和《红楼梦》的正本。虽然它们之间有一些文字上的差异,但这并不根本影响它们的传播以及人们对它们文学经典地位的肯定。读者均认为自己读到的作品就是这小说正宗作品。各版本间文字的差异存在,说明明清小说经典的文字可以被修改,改后的文本并不会根本影响对其经典地位的评价。而且,各版本之间内容与文字的大同小异,又说明明清小说经典是可以复制的。再有,说明清小说经典是不可复制的,可能也失去了意义。因为每部文学经典作品,以及它们的续作、仿作,都可以说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其文字一旦较大改变,就不再是原作本身了。这样,就会推导出“任何一部小说作品都是不可复制或不可改写的”观点。故对于明清小说名著来说,最好不套用“不可复制性”。
“品牌性与名牌性”的提法,则可形象地让人明白小说经典的巨大魅力。笔者以为,完全可用“品牌性与名牌性”形容明清长篇小说经典的文学经典性概貌。因为明清时代诞生了针对这些小说名著的续作、仿作、戏剧等衍生作品;而在现代社会,则产生了针对这些小说名著的许多电影、电视剧、卡通、flash动画、绘画、邮票、火柴画、电子游戏、改编本等衍生作品。因而,在当下语境下,用当前流行词汇“品牌性”、“名牌性”或许能更全面、更妥帖地描述与阐释其文学经典性的特点。如《水浒传》的品牌设计是关于官逼民反和关于忠君与招安;核心宗旨是“官逼民反”和“忠心报主”;核心价值主要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杀尽贪官污吏”、“忠心报主”。《西游记》的品牌设计是诠释唐僧西天取经,渲染斗智斗勇,以孙悟空和猪八戒贫嘴表现出超级浓重的幽默诙谐感;核心宗旨是诙谐幽默、游戏,调节生活,增加人生情趣;核心价值一是休闲娱乐,二是鼓舞人们要持之以恒,勇于向“妖魔鬼怪”世界作斗争,并斗争到底,取得圆满成功。《金瓶梅》的品牌设计是以热冷转换的氛围叙事的形式,诠释情色和妻妾成群的家庭,渲染人性是复杂、丰富、立体的;核心宗旨是告诫纵欲、贪财必然导致自我灭亡;核心价值是戒淫戒贪的情感取向。小说消费者对明清小说经典都有品牌偏好与品牌忠诚,明清小说经典都有品牌的影响效应,在中国内外都有强大的产业链,尤其是根据它们改编的电视剧、电影、戏剧等。
“民族性”特性也是学术界目前的共识,很多学者都已注意到文学经典往往会反映民族特征。故笔者直接吸收。
易传播性与易接受性是学术界探讨文学经典时已关注到的特点,笔者也加以采纳。
而本来,经典化过程的曲折性未必是所有文学经典都具有的特征,因为有的作品一面世,就传播很顺利,评价也一直很高。但对于明代四大奇书而言,经典化过程的曲折性绝对是符合它们的共同实际的。所以,曲折性成了它们经典性的共同之处。
“丰富的可阐释性”是前辈学者所提到过的,只是他们常将其表述为文学经典一定有较大的可阐释空间。如童庆炳提到了“经典必备六要素”㉖,其中两要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是可以吸收和借鉴的。韦勒克也说过:“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决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㉗的确,一部长篇小说经典应该有很强的可阐释空间。只是笔者结合“经典性”,将之更改为“丰富的可阐释性”,或许更符合特性的用语要求。
但“丰富的可争议性”是目前学界还未确立的一条标准。或许这条对有的文学经典作品不适用,但具体到四大奇书和《红楼梦》身上,却非常适合。故笔者将其上升到明清长篇小说成为经典的必备条件。通览这五部著作,“丰富的可争议性”成了它们作为某一类文学经典现象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没有丰富的可争议性,明清长篇小说就无法成为文学经典。这一点,也是笔者具体研究明清小说经典时发现的一个规律。
综上所述,笔者尝试以优质性和高峰性等七个特性来论述明清长篇小说经典性的相同点。这七个特性既简单通俗,又好记、易理解,有广泛的适用性和通用性。它们体现了由文学本体的内部品质向外部因素延伸的研究顺序,也体现了观照领域由重到轻的逐渐转变。同时,它们是讨论小说经典性时最值得优先考虑的方面,可看作明清长篇小说经典性的七要素。也就是说,看一部明清小说到底是不是文学经典,可从这七方面去研判。其中,优质性和高峰性、品牌性和名牌性主要涉及经典形成条件和扩容的问题,陌生化和原创性主要涉及经典形成条件的问题,而民族性、易传播性与易接受性、经典化过程的曲折性、丰富的可阐释性和可争议性主要涉及经典扩容的问题。故这七个经典性的归纳和提炼,是对明清小说的经典形成条件与扩容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
【作者单位: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510830),中山大学中文系(510275)】
①⑲㉖童庆炳《〈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7页。
③⑰⑱㉑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④⑧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⑤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⑥和磊《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⑦张立群《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⑨㉒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⑩[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9页。
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1页。
⑫谭华《如何看待“哈利·波特”现象》,《光明日报》,2008年1月7日,第5版。
⑬[德]爱克曼辑《歌德谈话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⑭⑮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299、301页。
⑯李建武《赛珍珠等欧美人的看法对文学经典观的启示》,《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6期。
⑳[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㉓魏萍《不可复制的经典》,《电影评介》,2006年第5期。
㉔阮直《经典的不可续写性》,《四川文学》,2011年第8期。
㉕肖四新《文学经典必备的品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0年第1期。
㉗[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版,第36页。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3CZW054)、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GD14HZW02)、广东省学科建设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013WYXM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