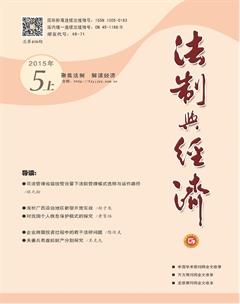无可争议的判决
李翔宇
[摘 要]“洞穴奇案”作为历史名案,其不同的判决结果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持久和深远的,但从法律和道德价值的统一性,法之价值的层次性,正义价值的不可倒退性以及生命权的内在实质要求上看,本案的判决当是无争议的,即四被告应当被判处死刑。
[关键词]法律价值;正义价值;生命权
洞穴奇案,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教授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洞穴奇案的“奇”在于,它将我们置于特殊客观环境下法律与伦理的困境之中,将原本清晰明了的法律适用问题,扩张至人类道德关照的模糊地带,令人左右为难。然而,“令人为难”素来是历史名案的共同特点,1842年美国诉霍尔姆斯案有之,1884年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亦然,但法律人却不可因此放弃判断的权力。
本案将法律与道德置于“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特殊境地下进行比较,设置了一个法律价值上的冲突。笔者认为,本案中的四被告(杰克、丹尼尔、凯特、露西)之行为,已构成纽卡斯王国法律中规定的杀人罪,应当被判处死刑。
洞穴奇案中,洞穴中五名探险人受困于封闭的独特环境,在形式上,构成了一个“封闭且资源贫乏的王国”,而外界的纽卡斯王国,则代表了一个“开放且正常的王国”,本案中,关于法律伦理价值争议的焦点,是在极端特殊的条件下,法律的价值是否与道德价值相冲突,法律价值是否应当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正义的价值性是否可以发生倒退,契约神圣是否可以在特殊环境下将生命权作为标的。
一、法律价值与道德的统一性决定法律的伦理价值不应当发生改变
洞穴奇案道德上的争议是“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可以以个体的牺牲,换取众人的存活”,这是法律所未规定的,出于此行为环境下的行为人,其行为是否可以得到道德上的宽恕,影响法律价值的判断,从而影响判决结果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道德范畴,对于生命权的保障,是最低底线,也是最高标准,个人的生命权与众人的生命权具有同质性,即,为了拯救众人的生命,牺牲个体的生命是不道德的。本案中,被困的五人来自于开放世界(纽卡斯王国)、其道德价值应当与开放世界的道德价值保持一致,且被牺牲的人是无过错的,将一个无过错人置于个人生死与众人生死的天平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这个天平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同时,生命权神圣是针对个体而言的,在生命权上,不存在一加一大于或等于二的说法,极端的推崇生命权,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生命权是可以被称量,甚至是可计算的。这不仅不符合道德,更不符合法律。本书的作者富勒就坚信法律和道德是不可分离的,他说,法律单纯作为秩序而言、包含了它自己固有的道德性,如果我们要建立可称为法律的任何秩序,就必须尊重这种秩序的道德性,即法律和道德是相统一的,法律的价值取向应当同道德的价值取向相同,而不应当因外在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异化。法律是道德的高度统一与内化,其追求的价值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在法律中,人身权尚且不可被称量,遑论生命权了,因此,本案中,道德和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是相对统一的。
二、法之价值的位阶性要求法律伦理不应当发生改变
在洞穴奇案中,关于法之价值的争论在于,法应当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应当推崇其固有的自然价值取向?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派强调法的制定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本案中,五名被困者在“封闭且资源贫乏的王国”中的投票行为,实质上,就是法的运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种法律价值始终贯穿其中。被困人员的投票行为,可视为法的制定,且这部法律秉承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法学派的价值取向,法律制定的结果也贯穿了这一价值。法律的实施结果是对个体实施了屠杀、换取了资源,使大部分人取得了存活,并且这部法律的监督,也是被大多数人掌握的。这样的法律运行过程,与希特勒为屠杀犹太人而修改《魏玛宪法》何其相似?恶法非法,秉承不正当的价值取向的法律,最终会由民主演变成大多数人的暴政,会演变为法律程序上的正义,实体上的非正义。法律的价值是有位阶性、层次性以及上位、下位之分的,当法的下位价值与上位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选择上位价值。毋庸置疑,对于个体生命权、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私有权等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的保护,应当是法之价值的最高体现,应当被贯穿于法运行的全过程中,否则,法律将会发生畸变的危险。本案中,无论是洞穴中的封闭王国,或者是纽卡斯的开放王国,在法的运行过程中,均应贯穿法律的上位价值,否则,法律将不能谓之以法。
三、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决定正义的价值性不能发生倒退
本案中,对于四被告的定罪量刑,一个影响我们判断的问题是,在洞穴奇案特殊的封闭环境下,谋杀个体以换取整体生存的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价值判断。正义,意味着公平与遵守某种公认的社会秩序(包括法律),本案中,由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公认的社会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即投票决定谁应当被杀而换来其他人的存活,但是,这种变换了的社会秩序(法律),本身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今阶段所确立的社会秩序的。剥夺人类生命的行为,在某些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如为了在灾荒条件下节约粮食而处死老人或婴儿,或按宗教仪式将社会成员进行献祭,或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进行陪葬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并不影响这一事实的真相,即一般来讲,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社会都认为,故意杀害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是应当受到严惩和谴责的。”本案中,通过卢卡斯王国对被困人员的救助行为,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纽卡斯王国应当是,或近似一个现代社会,因此,关于杀害或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应当是被认为不正义的。虽然本案中,环境较为特殊,但不能以个案的特殊性,来否定社会发展关于社会价值取向的进步,来断定在特殊悄况下,为达到某种目的正义的价值可以发生倒退,故,不能以特殊的社会秩序为理由,来赋予“洞中社会”一个畸形的正义观,也不能以个案,来断言正义的价值可以发生倒退。并且,我们对于某种行为“不正义”的判断,是基于“这些行动是否剥夺了人们应当得到的某种东西,或这些行动是否拒绝给予人们应当得到的某种东西”依照此标准进行判断,本案中投票决定谁被杀死的行为本身,就触犯到了潜在个体应当拥有的生命权,投票行为本身就是不正义的、遑论正义的价值是否倒退这个问题了。
四、生命权的内在實质否认其契约上的标的性质
本案中另一个可能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的,应当是契约神圣这一原则的对抗性。即,在“封闭且资源贫乏的王国”之中,五名被困者以生命权为标的,订立了一个契约,因此,应当本着契约神圣精神对抗死刑判决。这种观点存在一个根本上的问题,即五个人以投色子的方式,以生命权为标的达成的共识,能否作为契约?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构成契约,因为生命权是不能作为契约标的。生命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具有排他性和对世性,其本身也是不可转移、不可出让的。诚然,在国家契约论中,人们是会以出让一部分权力给国家的方式,以获取个人与他人更大利益,但这一部分权利中不可能存在生命权。并且,契约的签订,也应当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其形式和实质上都应当符合某种法定条件,而对于几乎所有的法律来说,对于生命权的保护,是最基本的标准,上文已经论述过,即使在洞穴奇案的特殊环境下,生命权也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以生命权为标的的契约,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具有法律上的基础,因此,契约标的不成立,此契约是无效的,也就不存在与死刑判决的对杭。
综上所述,由于法律价值与道德的统一性、法之价值的层次性、正义价值的不可倒退性以及生命权的内在实质要求,决定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是由自然人构成的社会,法的伦理价值就不应当发生改变。
因此,洞穴奇案中,对于四被告的判决应当是无可争议的,即,他们应当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