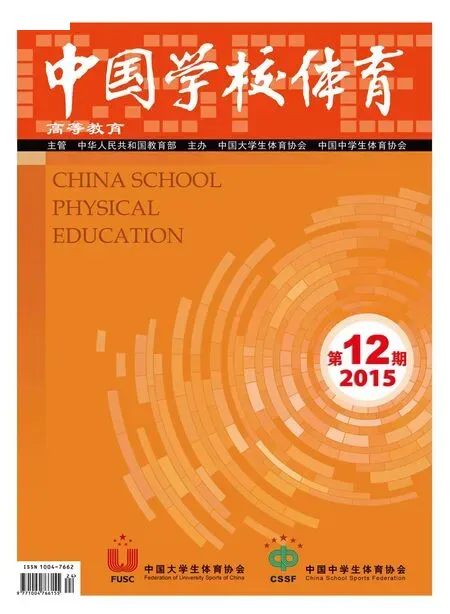作为游戏的冰雪运动文化主题沿革的哲学解读
关景媛,隋 力,韩文娜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作为游戏的冰雪运动文化主题沿革的哲学解读
关景媛,隋 力,韩文娜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以历史学、哲学、体育学跨学科视域,以游戏论作为理论工具,对我国冰雪运动文化主题演进进行阐释和解读,认为冰雪运动发展演进阶段主旋律与体育游戏思想主题转化的时代特征耦合。作为游戏的冰雪运动在从游戏感到形式感,从生产性到文化性,从应对自然到融合自然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冰雪器具的开发、冰雪运动游戏品性的形成以及社会功能和人文价值的延展。
冰雪运动;游戏理论;文化主题;游戏品性;哲学解读
从冰雪运动在我国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来看,其在古早时期是一种从生产生活中逐渐演生为祭祀、军事、娱乐等文化形态的人类活动。现代之前,冰雪运动并不是当今体育竞技意义上的人类活动形式,而是一种作为游戏存在的运动。从抵御冰雪,到逐渐适应—认识—驾驭—享受冰雪运动,形成了具有本土性、地域性、民族性、创生性的冰雪运动历史和文化,在政治上维系民族情感,军事上振奋民族精神,文化上增强民族团聚力,在不同层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功用。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以“中国冰雪文化”、“冰雪运动历史”为主题词索引文献149篇,内容涉及隋唐时期至今的多样化文本素材(文献、风俗、祭礼、庆典、狩猎、传说、绘画、地方志等);以“游戏理论”为关键词并依据“体育哲学”研究方向作为拣选条件选取相关文献87篇,内容涉及有关西方游戏理论评介及其与体育的关系问题。本研究基于以上研究基础,试图建立冰雪运动文化史与游戏理论发展史之间的联系。
1 “骑木而行”—识御“自然”的游戏感[1]与古代冰雪器具开发
1.1 原始的生产劳动是冰雪体育文化产生的基础 冰雪威胁与侵袭,对远古人类而言无疑是自然界最暴决、严峻、残酷的致命大敌。冰雪中的交通成为古代寒冷地带著民生产生活中最大的困难,在雪情难卜的情况下如果盲目驱赶车马冒进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以鹿群为挽力又难以引渡过深雪沟壑。生存在广袤寒域的先民在火的助力下努力认识、适应、驾驭作为自然力的“冰雪”,并积累了如何识雪、御雪、用雪的技能、经验和习俗,积淀了关于冰雪的体验、思考和文化,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相对安全神速的交通运输工具——滑板、雪橇和爬犁,进而成为主宰域北大地的主人[2]。
此外,“爬犁”,也是一种受“犁杖”形式的启发改制而成的北方先民主要运输交通工具,亦称“扒犁”“、扒杆”,满语称为“法喇”,“制如冰床而不施铁条,屈木为辕似露车,坐低,旁轮前有扼而高,驾以牛或马走冰雪上疾如飞,亦可施帷蟆袭绸以御寒”[2]。
优势是可以不分道路,只要有冰、有雪便可通行,因而是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实用有效的运载工具,其中,狗拉雪橇是北方最具特色的爬犁形式,“冰走耙犁使犬部(注:赫哲人曾史称‘使犬部’,世代喜用雪橇。雪橇,又称‘拖床’、‘柁床’、‘冰床’,是小巧灵便的雪上运输工具),雪施踏板贡貂人”,该诗句讲述了赫哲人在寒冷多雪的地方求生存特别依赖狗拉雪橇进行交通和生活,一般每个雪橇少则套两条狗,多者套十几条狗,可日行百余里。女真人也常驾驭“狗拉雪橇”赴黑龙江出海口北上捕鹰貂,头狗开道,安全神速,因而雪橇犬也成为北方猎人们最珍爱的朋友和伙伴。
1.3 对工具的练习和使用形成多种冰雪游戏的雏形 为了更好地适应和驾驭滑板、爬犁、雪橇等交通运载工具,在生产生活中增强效能性和稳定性,练习和训练就成为人们生产劳动闲暇时的必要内容,由此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冬季活动,如满族的滑冰、雪地竞走、跑冰车,鄂伦春族的滑雪等。可以说,滑冰滑雪工具的使用,为北方特色的体育活动的形成奠定了物质与实践基础。
这一时期的冰雪游戏是以识御自然、驾驭工具为目的指向的,因而其意识核心是对自然世界的应对,思考的主题是作为物的世界。这是由人类生产发展阶段特征决定的,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尚处于朴素唯物主义阶段,对世界本原的把握往往借助自然界中的物质,如水、火、气等,因而对脱胎于生产劳动的日常身体活动也具有较明显的器物依赖,获得游戏感(指人类游戏活动的非理性状态,即人类那些未经审慎反思的对游戏的官感与经验)的焦点也在于现实需求层面对物的驾驭感、协调感,并没有更高层级的精神追求、主体意识、道德感的参与,这与人类游戏活动的早期发展特征相吻合。
2 “祭雪驱邪”—神祗与祭礼助推冰雪游戏形式感的生成
2.1 对自然力的敬畏感与神化 原始宗教中的一大部分,是关于人类生活上重要危机的神圣化。愚昧而弱力的原始人类对神秘而强大的自然力由恐惧而生敬畏,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同化自然力,构想了许多神的形象,这些形象从外形到性格,无不与人们对于不同自然力的感受性相联系。冰雪神话与传说和神秘的冰雪祭礼为域北冰雪文化增添了一层神圣而绚丽的艺术光环[2]。
北天寰宇的冰雪姊妹神的善与恶。北方早年传讲“白灾”即暴雪连绵,“黑灾”指冬日少雪、大地干旱缺水。如果说畏来自对生存的未卜,那么敬就源于生存的恩赐。在萨满教原始自然崇拜的诸神中,冰雪神是主宰北天寰宇的姊妹大神,她们同是天母神阿布卡赫赫或称腾格里天神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叱咤万里,神威无敌[2]。区别在于雪神本善,冰神本恶,雪神温柔纯洁,总是赶着鹿雪橇,背着桦皮兜,扬雪驱邪逐瘟魔,让大地在白雪保护下安然无恙,但偶尔也受到大风蛊惑而酿成雪灾;而冰神或是被形象化为张着巨齿的黑鲸,或是张着巨口的白虎、白熊、白鳖,乌尔奇人为求捕鱼、捕海兽吉顺平安而祭拜冰神,那乃人为祈求冰河中渔业和猎业丰收则虔诚祭奉冰神的化身—雪豹形凶神焦格德尔·亚尔哈。
从中可见,在原始的冰雪姐妹神神话传说中,蕴含着一定的游戏精神和辩证法,善非常善,恶非恒恶,规则是有所变化的,影响其自身的作为。
我国北方诸民族萨满祭祀中的冰雪神话。在满族先世黑水女真人著名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中讲,宇宙初开时,恶魔耶鲁里偷走地母巴那吉额姆的桦皮篓里那能使大地变黑、冰雪交加的黑发全都撒向大地。阿布卡赫赫为使光明和温暖永驻人间,驱赶耶鲁里,但是终因地母失去不少黑发,留下许多白发,所以,世间总是雪天多过暖天[2],为北方地区冬长夏短、雪季漫长提供了形象的解说。
此外,鄂伦春族的传说也以拟人化的修辞解释了北方暴雪为何总伴有呼呼的风声,即是风婆婆赶着风车游逛,误把冰雪当成云朵拉来了[3]。无独有偶,先人总是愿意把白雪与女神相联系,萨哈连人把穆林穆林山称为“奇莫尼(注:为满语,意为乳房)妈妈”,传说这位雪山女神拥有雪白的肌肤,常赤裸着向着黑龙江侧卧而眠。她睡的香甜的时候,天空就晴朗静谧,大地就草沃花香,雪水消融沿山而下,滋育大地哺育牲畜。可当她苏醒后,就会风雪大作,冰雹成灾,人畜死亡。因而萨哈连人为祈求畜牧业得到女神的庇护,敬她为畜牧女神[2]。相似的传说也有讲,有座神山住着曼君女神,又称曼君额云,“曼君”实为“尼莽吉”,即为“雪”,所以曼君女神就是雪神,雪神所住的这座山是卧勒多女神布星阵中之巨星,称雪星(或寒星)。阿布卡赫赫在同耶鲁里拚搏时将 “雪星”踏裂,掉在地上这一半就成为曼君乌延哈达。此后,雪神分两地居住,居住在天上时,北方无雪,春暖花开;居住在地上时北方沃雪连年。因而人们尊奉曼君女神为季节神,亦是北方雪神,年年致祭不衰[4]。早期的神话传说都是基于对自然力的形象化解释,因而在信奉与祭祀中,也往往带有鲜明而质朴的形式感,昭示着先民们最为直白而切实的祈求。
2.2 雪祭大典复演先人原始渔猎生活影迹 满族先世黑水女真人流传下来了关于神圣的大雪在祖先生逢绝境之时降落,挽救了满族先人的事迹:“相传,/祖先起根的遥远年代,/我们先人们,/狩猎于黑龙江北宁涉里山,/山西住着仇家大部落,/人称‘巴柱’魔怪。/先人受其伤害,/被欺赶逃遁……/猎肉没有了,/皮裘没有了,/火种没有了,/先人尸横遍野……/巴柱部落追踪赶来,/先人啊全藏在雪被里,/大雪弥漫如毛裘,/像天鹅舒展的翅膀。/行人藏在翎毛腹肚下,/恩佑脱险。/吉祥啊,吉祥,/后嗣由此接续,留存。/祖先感激天赐神雪,/代代诚祭雪神……/”[5]此为满族很多姓氏都还保存着每年的雪祭大典的最初缘由。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的雪祭遗留下来的是对于雪之恩佑的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并且雪祭的目的和形式也逐渐丰富,逐渐形成具有一定娱乐性、游戏性的雪祭活动。
近世雪祭有两种动因:1)为祈雪、请雪、求雪。在北方,有瑞雪兆丰年的习俗,若逢雪枯时节,则人们会视之为灾祸的先兆,为求雪阖族或几个噶珊(村落)联合举行雪祭典礼;2)为庆雪、娱雪。若逢喜降瑞雪,则预示着狩猎丰盈,无病无灾,农事丰捻,族人感恩而行雪祭盛典。雪祭时间、神坛地址,均由氏族德高望重的老萨满卜定。老萨满通过旋转起舞后静立缓睁双眼,卜出雪坛新址,族中男女老少齐捕捉鲜活的野兽飞禽,修筑雪祭神坛。雪祭是先民生产生活状况的形式化表达,是与自然斗争融合真实的历程在宗教仪式中的缅怀和复演,再现往昔原始渔猎生活的影迹。“雪祭时神坛两侧砌起两座圆顶雪屋,冰做柱,雪坯打墙,外披野猪皮、驼鹿皮,屋内尽量铺上熊皮、黑獭皮、貉皮、灌皮等,点鱼油和兽油灯取暖照明。雪祭雪屋供男女主祭萨满占卜、祭神,为族人治病,也使族人们牢牢记忆祖先创业之艰辛”[5]。
2.3 冰雪民俗游戏为教民化性提供精神土壤 人们对冰雪的感情在宗教的仪式中得以升华,冰雪已由人类的异己之力变为恩佑之力,雪祭以其独有的仪式感,再现了北方先民们识雪、御雪、用雪、娱雪的经验,是人类长期同作为自然之力的冰雪相斗相容中所积淀的生存智慧和民俗文化。祭礼中,族众和萨满模拟、歌颂、复演昨天的英雄故事,激励后人在冰雪生存中发挥“识雪路”、“辨方向”、“识兽迹”、“缚禽兽”以及“驾驭雪板”的高超技能、熟识冰雪规律的“应对诀窍”等。萨满教古祭情节活泼生动,形成了诸多需要融合勇气、智慧和体力的民俗游戏活动,如多林莽尼是位善跳跃行走的英雄神,他能连续跳过9个山头,可单腿跳跃,可脚踏滑板飞跑,更能上到树的高枝上,这些也都成为了民俗游戏的原始情境和模仿素材;嘎哈山妈妈是位能看透冰层雪阵的智神,启迪族众辨识凶险、临危藏匿等奥秘。族人还玩“走迷宫”游戏,即用冰雪坯砌成迷宫,智者闭目进诸洞,遵时走出者视为吉祥,目的是锻炼冰雪中识方向的技能,模拟古人在林海雪原中沉着应对、摆脱灾难、转危为安的非凡勇气和心境。还有流传至今并且被广泛推广于北方众多城市与多民族人民中的大众性游戏—堆雪人、打雪仗、冰雕、雪雕、雪中迷藏等竞技游戏活动。族众在信仰崇拜与赏玩游戏中,认识同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气候现象,在与自然的博弈、协调中发展天性,是古代先民对冰雪文化的重要贡献。
人类的游戏起于对自然的仿拟与崇敬,因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趋赴神性的。柏拉图认为“人是作为上帝的玩具而创造出来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应该演好这个角色,并相应地安排他们的一生,这就是他可能从事的最好的娱乐……怎样的生活才是正确的呢?一个人应该在‘游玩’中度过他的一生——祭献、唱歌、跳舞。这样,他才能赢得众神的恩宠,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侵犯,并在战斗中征服他们”[6]。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著民,他们的保护神将向他们提出关于祭献和舞蹈的启示,显现给他们各种各样神的福祉与恩佑,并且指示人们在纪念这些神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游戏,以赢得众神的好感,据此,他们才能过他们自己天性要求的生活。
对于北方先民而言,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离不开冰雪的恩赐与警示的,这里的人民天性就趋附冰雪神力,他们信奉冰雪对他们的赐予,也畏惧冰雪之神动怒带来的灾难,这也是地域为人们烙下的文化基底,按柏拉图的说法,他们需要对冰雪祭献、讴歌和欢庆,这应是他们日常活动的重要主题。此外具有形式感的游戏活动也将成为教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儿童的游戏被用作教育儿童的工具和手段,柏拉图认为孩子必须参加那些符合律法的正当游戏,对北方先民而言,为他们定下这些律法的就是自然神、冰神雪神,他们的孩童从小就要被长辈教导做一些规则之内的游戏,通过游戏,使孩子们熟悉捕猎、捕鱼、滑行、建造房屋的规则,对于具有形式感的神祭游戏而言,“人们也以为它不会起什么作用,而实际上它慢慢地向人的心灵渗透,悄悄地改变人的性格和习惯,再以逐渐增强的力量改变人们的处世方式”[7]。
3 “冬猎、冰嬉”——近代冰雪民俗奠基冰雪运动游戏品性
3.1 作为官民共同的冬季生产娱乐活动的冬猎 在古代,冬季是官民捕猎的黄金季。依据动物冬天觅食的条件和习性,猎人们布下陷阱,围猎动物,往往收获颇丰,这也是为何北方各族先民将冰雪奉为恩惠之神[2]。《辽史·营卫志》记载了契丹皇帝每年凿冰取鱼、纵鹰鹊捕鹅雁的游猎活动[8],反映古代契丹人的冬猎景象。这种习俗现在已成为北方人民每年的大型公众性的表演游戏—冬捕,渔民在破冰开江撒网捕鱼之时,会有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民众,一睹冬捕的壮观景象,起网之后最大的一头鱼也将被视为最具有吉祥意义的鱼王,竞相争拍。《龙沙纪略》记载了“将军猎野猪于通铿河”的冬猎事件。在东北,有一道地方名菜就是杀猪菜,成为人们欢度新年祈求来年丰衣足食、阖家幸福的吉祥菜。鄂伦春族猎人有生动的冬猎谣谚:“冬天顶风走上山崖寻鹿,走进草甸子寻抱子,走进高山柞树林见野猪,走下高山看黑熊,登上高山土洞见紫貂,山林雪地看白兔,都柿甸子找树鸡,河边暖流看水獭”[2]。清康熙九年(1670年)流放宁古塔(宁安)文人张贲《白云集》诗云:“射猎冲寒雪,冬狩极北溟。驰镰昏日月,鸣摘乱流星。鹿尾连车载,雕翎带血腥。今年膺上赏,生获海东青”[9]。冬狩诗生动描述清代雪猎的景况,气势壮阔。
3.2 《冰嬉图》反映清代冰雪游戏走向成熟 “冰嬉”名称始自乾隆的《冰嬉赋》[10],乾隆皇帝对冰嬉极为倡导和重视,特把冰嬉定为国俗盛典,是满清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包括冰上竞技表演和游戏娱乐,是一种有很强表演性的群体活动,在冰雪运动的发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11]。可以说,冰雪运动在清代以军事、政治等功能,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情感、增强民族团聚力的重要作用[12],也凸显冰雪运动已然成长为具有游戏特征的社会性文化活动。
清朝,冰上运动已成为检阅军队冬季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满清政府将滑冰、滑冰射箭、冰上足球和冰上摔跤等作为京城卫戍部队的重要军事训练项目,创立“技勇冰鞋营”滑冰兵种,专职兵丁称为“冰鞋”,教练称为“冰鞋教习”,建立专门的训练和管理机构。因此,冰嬉的推展促成了我国古代滑冰活动的“黄金时代”。从宫廷到民间,成为大众健身运动的代表,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的冰上运动。清代有3幅代表性的描绘冰嬉场景的《冰嬉图》,分别是宫廷画家金昆、程至道、福隆安的《冰嬉图》,张为邦、姚文翰的《冰嬉图》,金廷标的《冰嬉图》,均通过绘画的形式再现了冰嬉运动在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流行,是举国上下喜欢的运动之一,绘画作品中还体现了当时滑冰水平是较高的,人物可以根据号令编列队形,可以做出旋转动作、逆向滑行动作和燕式平衡动作。据《满洲老档录·冰戏》记载,1623年正月初二,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太子河冰面上举行了我国古代第1次冰上运动会,共2项内容:1)男子冰球比赛,参加者穿皮革制的内垫乌拉草的鞋子在冰上抢踢,参赛者为王子及其随从;2)女子冰上赛跑,按照官职、爵位分组进行比赛;赛后在冰面上大摆筵席庆贺[13]。可见这是一次宫廷高规格的冰上游戏盛典,从规则上、组织上已经标志着有显著的游戏特征,表明当时我国的冰雪运动已经具备较为全面的、成熟的游戏品性。
3.3 节庆风俗形成多彩的民族冰雪游戏 不同民族的节庆活动反映了各民族民俗冰雪体育文化。满族冰雪娱乐活动较多,有“雪打灯、走百病”的风俗,由此,形成了规则有一定变通性的雪地竞走游戏[3]。正月十五元宵节,东北地区也叫灯节,在这一天家家都要做冰灯,北方很多小学的劳动课都会教给小学生们如何制作冰花。夜晚来临,就会有社团组织闹冰灯、扭秧歌,各色的冰灯、火红的绸子、艳丽的头饰和服装,映衬着白雪,甚是喜庆,也成为不少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民风素材。传统冰雪习俗的传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冰灯、冰雕和雪雕艺术,以供民众欣赏娱乐,打冰滑梯、钻雪城堡等成为北方人对童年游戏的集体回忆。
游戏研究先驱胡伊青加(John Huizinga)在《游戏的人》中阐明:人是游戏者,人类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4],“游戏就将自己从自然进程的行列中标识出来,此外附加和扩展的东西就好比花开、装饰和外衣”[1]。他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类文化的社会表现称作游戏的高级形式,涉及竞争与竞赛、表演与展示、舞蹈与音乐、露天表演、化装舞会与比武。北方冰雪民俗游戏正是这种人类文化的社会表现形式。
游戏具有自愿性、佯信性、封闭性和形式的可审美性特征。1)游戏是主体出于自愿而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是超乎外力或自然必然性的;作为因自愿而自由的活动,游戏是与受强制因而不自由的活动相对的,近代时期,冰雪活动经历了对物的世界的应对和对神化的自然力的献祭之后,复归人性的追求,彰显人在冰雪运动中的主体自由,因而具有了形式感,具有审美指向;2)游戏与日常生活的“不同”,游戏的诡秘性质,最为生动地体现在“乔装打扮”中。但对游戏“只是一种假装”的意识,决不妨碍游戏者以最大的严肃来从事游戏,即带着一种入迷。通过《冰嬉图》中人物的不同滑行姿态,可以感受到士兵们对于滑冰和射箭的组合游戏充满兴趣,沉浸其中,以最大的热忱再现先民滑雪涉猎的生活样态;3)作为现实生活的插曲,游戏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游戏是在某一时空限制内“演完(play out)”的,自有其终止,且一切游戏都是在一块从物质上或观念上、或有意地或理所当然地预先划出的游戏场地中进行并保持其存在的。游戏的封闭性不仅表现在时空特征上也表现在活动规则上,这在野蛮人团体的宏大的仪典游戏中同样显著。在隆重节日期间一切报复和仇杀都被悬置起来,即因神圣游戏期而对正常社会生活暂时悬置;4)规则使活动有序。游戏所创造的秩序是最高的,游戏的高度有序性使得游戏具有运动形式上的可审美性。正如雪祭仪式中复杂繁琐的环节,以及诸多民俗游戏中流传下来的约定成俗的规则,进入游戏的游戏者就会自觉遵守,即使是娱乐游戏,大家也都在公认的、传统的规矩之下进行。“仪式的参与者们都相信,它带来一种较他们日常生活更高的事物的秩序,这个世界的影响并不随游戏的结束而消失;相反,它持续不断地把它的光芒放射到外面的日常世界,对整个团体的安全、秩序和繁荣起着有益的影响”[1]。
4 “冬奥会”—现代竞技赛会推动冰雪运动功能与价值延展
4.1 冬奥会奖牌设计变化昭示冰雪运动的审美化发展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自1924年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22届。历届冬奥会奖牌的设计代表了一个国家、民族、群体的特有文化,每一块奖牌的设计都在寻求最具新意、最有特点、最能代表本国特色的视觉焦点,让世界了解举办城市,让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15]。表1为对历届冬奥会奖牌设计元素的统计。
根据表2可知,伴随冬奥会逐渐走向成熟,其奖牌的设计总体趋势呈现由素朴到个性化的转变,从早期的突出“物象”(赛道、山峰、雪花、器材、火炬)逐渐转变为突出“人”(运动员、民族人物),契合游戏理论发展早期特征,即由关注物的世界、关注自然世界转而关注作为主体的人。并且在图案元素的应用上可以看出由具象到抽象的过程,从呈现具体的人转而凸显“意象”,强调精神内涵,在呈现手法上具有后现代美学意味,在图腾、规制、形态、材质、工艺等方面试图打破传统,彰显差异,突出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特性。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唯一具有恒常性、传承性的要素就是五环,意味着人们对于作为游戏的冰雪运动本质有共识性的认知,这种设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冰雪运动进入自为的发展状态,自为即意味着既不是自然世界在游戏,也不是神在游戏,也不是人在游戏,而是游戏本身在游戏,即游戏具有自足的本质[17],游戏在创造着文化,并在文化创生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游戏自身,实则是一种复归天性、彰显心性的游戏精神在推进冰雪运动的发展和创造冰雪文化的价值。
4.2 冬奥会口号彰显冰雪文化精神的传承性 口号的提出不仅是基于现实社会制度及政治氛围的需求,也是基于文化传统提供的精神追求和信念基础。冬奥会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响应并反映世界对冬奥会的价值认同。从口号的统计中可以看到,“火”成为一种意象反复出现。赫拉克利特是西方第一个讨论游戏的哲学家,他认为世界是火的自我游戏,火是指变动的活火,最大特点是变动不居,处于永恒的生成变化状态。火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个运动过程,而非现成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对立的战争与和谐,推动万物变化的原则是作为始基的“火”,它就按照内在秩序合乎规律地进行编结、连接和塑造。冬奥会所推崇和致力于传承的恰是这种精神和价值追求,激情永恒、不断创造、协调融合。

表1 冬奥会奖牌图案中元素与出现次数及届次统计[15-16]

表2 近5届冬奥会口号统计
4.3 冰雪之用促进大众身心健康、彰显人文价值 人文体育是近年来重大赛事和盛会的人类共识,因其具有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人文特征,是与体育的本质相适应的重要认识。现代体育随着冬奥会的推展,发生了2大重要转变:1)从群体的政治需要转向人类的根本需要;2)从社会的强制性需要转向个体幸福生活的主动需要[18]。人们对冰雪游戏的认知从自然主题转化为神化主题,经由对冰雪竞技项目拓展、成绩提升和人的自我突破的追求之后,复归到关注冰雪本身的价值、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命价值,倡导更具有人文关怀感和生态主义的人文体育精神。
以冰雪本身的价值为例,中医讲冰雪具有保健功能、健身功能和医病功能。传说生活在漠北诸民族婴儿以雪擦身,可敌百病。冬日以雪搓身,体壮祛寒。冬泳持之以恒,少患杂症,延年益寿。《黑龙江述略》、《蒙医妙论》均记载了酒醉冻僵者,需以雪搓身,以冰水温之,令寒邪大出,才能使之得救。《本草纲目》称雪为药,《千金方》记载了雪治热烦的方子,萨满许多以冰雪与土药相配治热邪昏厥、狂语、血痢等验方,其他如《医林纂要》、《本草拾遗》、《日用本草》等,均概述了冰雪治病问题,丰富了祖国医药学宝库。此外还传承下来一些以冰雪窖藏、腌莽菜肉等制做佳肴的良方[2]。冰雪在健身、医药、饮食、丧葬等方面都有独特的功能,此时的冰雪运动已然不是拘泥于竞技赛场,更多的是走进凡常人的生活,在日常游戏中扮演恰当的角色,兼具实用价值和精神价值。
可见,人是一种价值的存在,人的活动是基于理性考量而进行的有价值的活动,作为社会性、文化性的冰雪游戏,其发展理路反映了人们体育价值观。体育价值观是体育实践主体的人以自身需要为尺度对体育客体意义的认识[19]。在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中,人类只有不断地反思和追问自己的需要,才能对体育客体形成一个真切的认识,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是以人为本的体育价值观确立的必要条件。
5 结 语
冰雪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人类游戏,其发展演进文化主题大体经历了“自然—神化—人性—自为”的沿革过程,而哲学中游戏理论的产生发展也大体经历了“世界—神—人性—存在”的思想主题,因而可以说冰雪文化是一种游戏文化,二者发展的阶段轨迹共轭。作为游戏的冰雪运动在从游戏感到形式感,从生产性到文化性,从应对自然到融合自然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冰雪器具的开发、冰雪运动游戏品性的形成以及社会功能和人文价值的延展。
[1]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著.游戏的人[M].多人,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10.
[2] 富育光.北方冰雪文化述考[J].民间文化,2001(2):72-78.
[3] 王诚民,倪莎莎,郭晗,等.冰雪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高师理科学刊,2014(5):75-78.
[4] 富育光,荆文礼.满族神话史诗《天宫大战》[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b08c2890102vp5d. html,2015-07-07.
[5] 郭淑云.满族萨满教雪祭探析——兼论原始萨满教的社会功能[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2(5):65-70.
[6] (希腊)柏拉图,著.法律篇[M].张智仁,何琴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4-225.
[7] (希腊)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96.
[8] 王飞.简述辽代的四时捺钵[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2):13-14.
[9] 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M].沈阳:辽沈书社,1988,10:383.
[10] 韩丹.论我国古代滑冰的鼎盛时代:说清代的“冰嬉”(下)[J].冰雪运动,1998(1):70-72.
[11] 张华,张大春.从《冰嬉图》探窥清代滑冰运动[J].冰雪运动,2015(5):32-34.
[12] 齐震.《冰嬉图》中满族传统体育文化意蕴的解读[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28(4):118-121.
[13] 韩丹.论我国古代滑冰的鼎盛时代:说清代的“冰嬉”(上)[J].冰雪运动,1997(4):69-71.
[14] 张萌萌.赫伊津哈游戏论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3:34.
[15] 董宇,李小兰,王沂,等.从视觉角度诠释第21届冬奥会奖牌设计的新思路[J].冰雪运动,2010(4):47-49.
[16] 历届冬奥会奖牌设计欣赏[EB/OL].http://www.sj33.cn/ article/sssj/201402/37179.html,2014-02-15.
[17] 春水.论游戏的自足本质[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33-38.
[18] 胡小明.新世纪新体育[J].体育学刊,2000,7(5):1-7.
[19] 唐宝盛.冰雪体育教育的人文价值[J].冰雪运动,2010(3):71-73.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Theme Evolution about Winter Sports as the Game
GUAN Jing-yuan, SUI Li, HAN Wen-na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China)
This study explains and interprets the problems of China’s winter sports culture theme evolution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history, philosophy and sports science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through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them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ce snow sports evolution stag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hanges of the theme about sports games. As a winter game, the winter sports change from a game to a form, from production to culture and from respond to natural to integrate with natural, which obj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ice and snow appliances,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winter sports game and facilitates the extension of social function and the humanistic value.
winter sports; game theory; cultural theme; game character;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G86
A
1004 - 7662(2015 )12- 0020- 07
2015 - 11 - 25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吉林省高校女生体育观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541);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2015年度高教科研项目重点课题“身体哲学的视阈下吉林省高校女生体育观问题研究”(项目编号:JGJX2015B3)。
关景媛,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体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