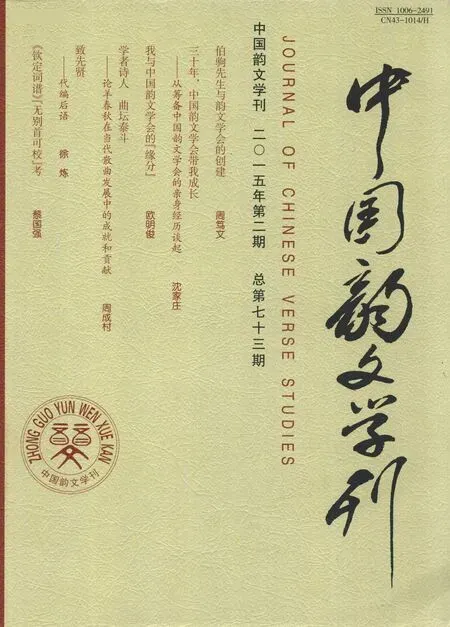赋体与东方思想
——论越南《玉井莲赋》与中国《子虚》、《上林》赋
[越南]潘秋云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 语言文学系,越南)
赋体与东方思想——论越南《玉井莲赋》与中国《子虚》、《上林》赋
[越南]潘秋云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 语言文学系,越南)
越南莫挺之的《玉井莲赋》与中国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在本国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其文学意义不仅在于文学艺术上的成就,而更多的是体现了该体裁在特定的时间内的重要性与文化内涵。本文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研究这两篇作品,以探讨越南汉文赋和汉赋之间的关系与其异同的同时,也探讨了通过赋体表现出来的东方思想特色。
越南汉文赋;汉赋;东方思想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玉井莲赋》与《子虚》、《上林》二赋都南辕北辙,相差甚远。两者的搭配好比拿小大卫跟巨人歌利亚来作比较,也就是说,毫无可比性。那么,本文为什么要把这两篇赋作为第一对比较作品?其原因如下:
一、《玉井莲赋》历来被认为是越南独立文学史上现存的第一篇汉文赋,也是最富名气的赋之一。《子虚》、《上林》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点的大赋,也是汉赋中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在越南赋学史上《玉井莲赋》的地位跟《上林赋》在中国赋学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同等的,所以笔者将两者比较而论。
二、《玉井莲赋》和《子虚》、《上林》都是体现“献赋”风气的最佳例子。莫挺之跟司马相如都因作赋而受到了王者的欣赏。这两篇赋的创作背景都比较特殊,从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时代的文学风气以及文人及其作品在所处时代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在《越赋纵横》中,钟逢义曾经写道:“《玉井莲赋》,系陈朝莫挺智(之)所作,可以说是一篇汉赋的复制品。”作者把《玉井莲赋》比作汉赋,但没进一步说明是哪一篇。本文试把它跟汉赋的代表作《子虚》、《上林》进行比较,同时也参考其他汉赋作品的例子,以探讨越南汉文赋和汉赋之间的关系与异同。
本文将通过对作者和作品创作背景的介绍与对作品本身的艺术特征的分析来进行探讨。
一
莫挺之(1280-1350),字节夫,原为谅江南策州平河县兰溪人,后移居海阳省南策县南新社陇洞村。他是黎朝莫显绩的后代。莫挺之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名人。他一生经历了陈朝的四代:陈英宗( 1293-1314)、陈明宗( 1314-1329)、陈宪宗( 1329-1341) 和陈裕宗( 1341-1369)。莫朝的开国皇帝莫登庸是他的第七代子孙。有关莫挺之的生平没有更多记载。我们现在只能通过其留下的寥寥几篇作品来了解作者的情怀与其创作宗旨。
莫挺之凭其才华在越南文学史上脱颖而出,同时,凭其机智在越南文化史上留下不少佳话。其中,广为流传的两部作品都缘于王者因他长相欠佳而给他不公平的对待时的当庭献赋,至今传为美谈。
第一次是陈朝英宗朝(公元1304年)时,莫挺之应试获状元。相传当英宗接见状元时,看他个子矮小,其貌不扬,有不悦之意,甚至想把他降为榜眼,让第二人选来作状元。莫挺之便当场写了《玉井莲赋》。
客有:隐几高斋,夏日正午。临碧水之清池,芙蓉之乐府。忽有人焉。野其服,黄其冠。迥出尘之仙骨,凛辟榖之癯颜。问之何来,曰从华山。乃授之几,乃使之座。破东陵之瓜,荐瑶池之果。载言之琅,载笑之瑳。既而目客曰:非爱莲之君子耶。我有异种,藏之袖间。非桃李之粗俗,非梅竹之孤寒。非僧房之枸杞,非洛土之牡丹。非陶令东篱之菊,非灵均九畹之兰。乃泰华峰头玉井之莲。客曰:异哉。岂所谓藕如船兮花十丈,冷比霜兮甘比蜜者耶。昔闻其名,今得其实。道士欣然,乃袖中出。客一见之,心中郁郁。乃拂十样之笺,泚五色之笔。以为歌曰:架水晶兮为宫,金凿琉璃兮为户。碎玻璃兮为泥,洒明珠兮为露。香馥郁兮层霄,帝闻风兮女慕。桂子冷兮无香,素娥纷兮女妒。采瑶草兮芳洲,望美人兮湘浦。蹇何为兮中流,盍相返兮故宇。岂濩落兮无容,叹婵娟兮多误。苟予柄之不阿,果何伤乎风雨。恐芳红兮摇落,美人来兮岁暮。道士闻而叹曰:子何为哀且怨也。独不见凤凰池上紫薇,白玉堂前之红药。敻地位之清高,蔼声明之昭灼。彼皆见贵于圣明之朝。子独何之乎骚人之国。於是有感斯言起敬起慕。哦诚斋亭上之诗,赓昌黎峰头之句。叫阊阖以披心,敬献玉井莲之赋。
《玉井莲赋》作为应制之作,引用了大量的中国诗歌入诗,从《诗经》、《离骚》中的词语至陶渊明、韩愈、刘禹锡、杨诚斋等诗歌中的意境和韵味。其中心意思在“叹婵娟兮多误。苟予柄之不阿,果何伤乎风雨。恐芳红兮摇落,美人来兮岁暮。”作者在“客”的角色中叹息婵娟之坎坷多误,芳红谢落,倘得“美人”青睐,恐已年岁迟暮了。这里用隐喻手法道出作者渴望圣上垂恩的心愿。而更巧妙的是下文接着用“道士”的角色来缓解气氛并转向曾赞君主:“彼皆见贵於圣明之朝。子独何之乎骚人之国”。其含义也是英明的统治者不该让贤臣怀才不遇,终身遗憾。
此赋让陈英宗马上对他另眼相看,并赐官位。莫挺之在朝廷中可说是如鱼得水,平步青云。
第二次是当莫挺之奉君命出使元朝时(年月尚未详),元朝内外文武官员一看到他就有藐视的表情。此时正逢外国有使者进奉扇子,元帝命莫挺之作铭,他马上写了这首《扇子铭》。
大火流金,天地为炉。汝于是时,伊、周大儒。北风其凉,风雪载途。汝于是时,夷、齐饿夫。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汝有是夫!
此铭一出,马上受到元朝君臣的赞美,把他视为才子。传说元朝皇帝还给他“两国状元”的美称。后来有人把这首铭当做被永乐皇帝“夷十族”的方孝孺的作品,因在方孝孺(1357-1402)著作《逊志斋集》当中,有一首《扇子铭》。而这首铭在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六有记载,而且莫挺之比方孝孺(1357-1402)大75岁。莫挺之出使中国时,方孝孺还没有生。认为此铭为方所作的说法是以讹传讹的。
莫挺之的《玉井莲赋》和《扇子铭》在相似的背景和动机之下创作出来。虽然两篇作品属于不同的体裁和题材,但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就是做人做事要学古人不以大才而傲,不以貌丑而悲,是金子总会发亮的,是奇花异草总会有人发现和欣赏的,看人不能以貌取人,君主更应该任人唯贤。然而,《玉井莲赋》因是为本国君主写的而少几分讽谏多几分赞美,同时灌注更多的个人情怀;《扇子铭》则因是为外国统治者写的,既要证明实力、维护尊严又要营造和气,而多几分气势少几分情感。
二
司马相如(约前179年—前117年)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就此可看出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班固《汉书》中的《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照录,但从其记载中也可以看到班固对司马相如的肯定。从《史记》和《汉书》当中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虽然才华洋溢,也热爱文学,但人生追求却非以文学家为终。据《史记》、《汉书》所记载,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少年时喜欢读书,也学习剑术,他父母给他取名犬子,后来因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而自己改名为相如。
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司马迁为他与廉颇所写《廉颇蔺相如列传》,表彰了他的大智大勇和高尚品德,并始终认为“其处智勇,可谓兼之”。我们现在读《司马相如传》可推测出他仰慕蔺相如的原因有三:
其一,蔺相如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战胜了强秦的威逼凌辱,维护了赵国尊严。他的机智与果敢,很值得任何渴望攻出声名的大丈夫景仰与学习。其二,蔺相如与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尚品格,跟廉颇在“负荆请罪”的故事中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品德与胸襟,对司马相如有着显明的教育激励作用。其三,蔺相如凭三寸舌取得赵国君臣的信任,又说服秦王,“完璧归赵”而垂名青史,而司马相如却“口吃”。由于自身缺陷而仰慕别人身上的优点,并渴望拥有同样的能力正是人之常情。《司马相如传》里面有一段记载: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创作《子虚赋》的过程反映了司马相如不得不回到现实生活的一面。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汉文帝、景帝、武帝三代,正是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代。战国时群雄割据的现象已经逝去,蔺相如的辉煌业绩难以重演,而司马相如本身能力也难以往这方面发展。因此,司马相如的聪明才智渐渐地转向了文学。《司马相如传》中收录了司马相如的三篇赋和四篇散文。其赋有《天子游猎赋》(一般称之为《子虚赋》或《子虚·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其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这些文章体现了司马相如丰富多彩的文学造诣,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创新。不过,无论其赋还是散文,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汉武帝而写。连最后一篇文章《封禅》也是他去世之前准备好,以供使者给皇帝献上的,且仍然是一篇颂扬国家的兴盛强大,体现中央王朝的尊严声威的作品。《汉书》载其事:
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 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这样,说他是个勇于创新、锐意开拓的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雄心勃勃、不断想办设法把自己推荐给最高权力者的在大统一文化中还带着游士精神的文人。汉武帝接纳他富赡的才华,但并不接纳他雄放的气魄。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因此,后来“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
在司马相如的心目中,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为皇帝进言、为封建制度服务,而并不是文学。他并没有刻意追求创建如何伟大的文学事业。文学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展示自我的工具,一种毛遂自荐的手段而已。他没有那种后来文学界中常见的用文学来表达自己内心,以求解脱的创作冲动,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写作。这跟我们现代心目中的文学家着实相差太远。
总之,司马相如的个人抱负跟其文学事业并不一致。他一生并未达到自己的政治愿望,但却在无意中为自己建立了如此伟大的文学事业。笔者认为如果文坛上和政坛上有的可相比较之处,那么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完全可以跟蔺相如在中国历史上所建立的功绩与名声相媲美。
关于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上林》二赋,《汉书·司马相如传》的篇幅里有一半用来记录这篇天子游猎之赋。这篇赋是司马相如作品当中最重要之一,也是《司马相如传》中的亮点。
我们先看看其内容。赋的前半部分记叙楚使子虚出使齐国,应邀参与齐王的出猎,不服齐王的“矜而自功”,从而向齐国之君臣——代表者是乌有先生——夸耀楚国的云梦泽和楚王在此游猎的情况;接着轮到乌有先生不服,便夸称齐国的宏大以压倒之,然后说出一番道德教训,作为这部分的收结。赋的后半部分记叙当时亡是公——天子的发言人——也在场,在齐楚面前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举,表明诸侯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最后又说出一番提倡节俭的道德教训。这一作品前一半被称为《子虚赋》,后一半被称为《上林赋》。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子虚赋》视为一篇独立、完整的作品,那么“亡是公”这个人物从开头到结束没有任何言行,只是“存焉”。这显然是文章中不该有的多余。然而司马相如为何被称为“赋圣”?《子虚赋》与《上林赋》为何被称为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应该有其道理。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记载,这两篇赋,或者可以说这篇天子游猎赋的前后部分,其创作时间不同。《子虚》是司马相如早年从枚乘游历时的创作,而《上林》则是后来司马相如被汉武帝接见时,趁机献上的。这件事情在《汉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通过高温制曲的菌群演化规律分析,一方面可通过分析菌群演化特征,为监测曲块品质差异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优化制曲工艺,如缩短曲块储藏时间、改变储藏条件、调节曲房条件(如温度、通风)等,奠定基础。最终为提升与稳定酒品质、降低制曲生产成本提供科学依据。
当武帝读《子虚赋》时,认为写得好并感叹:“我偏偏不能与这个作者同时”,而杨得意乘机推荐其同乡人司马相如的时候,说的是“自言为此赋”,表示不敢肯定相如即是作者,并为相如展示才华留个机会。武帝当然很惊喜,就召来相如询问。相如承认了,但怎能让汉武帝完全相信他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汉武帝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挥手成章的话,也不能让皇帝等得太久。然而《上林》大赋不是一篇好写的文章,应该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来完成。司马相如在创作《子虚赋》时,应该对下一篇已经有所准备。而且在写《子虚赋》的过程中,也有其意图在里面。具体的表现就是先把一个“亡是公”摆在那里,等着展示作者的才华与思想的机会。
在这里有个问题:该不该把《子虚赋》与《上林赋》视为一篇完整的作品?
在《史记》和《汉书》中,对这两篇赋的划分好像也不太明显。一开始所记载的是司马相如“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后来,到上面所引用“上读《子虚赋》而善之”的那一段,作者对司马相如赋作了一些介绍,然后把全文照录下来。全文是《子虚》与《上林》的结合。《司马相如传》最后提到这篇赋的时候在作品的名字和内容上也不分《子虚》与《上林》。
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
这样,司马迁和班固都有意无意地把《子虚》与《上林》这两篇赋视为一篇完整的作品。因而后来有不少文学家和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者把这两篇赋合起来,命名为《子虚上林赋》。
但是笔者认为《上林赋》并不能跟《子虚赋》融为一体。其原因有二:
其一,《上林赋》虽然跟《子虚赋》有关,但事实是,《子虚赋》早已经完成并成为一篇独立作品,而《上林赋》的创作是一种续写。而跟几乎所有的续写作品一样,它会给作者带来一时的名声,但在文学价值上是一种失败。《上林赋》显然重复了《子虚赋》的题材,结构与思想。我们现在读这篇赋时会感到很乏味,因为从中看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也看不到它跟前面作品比起来有什么进步,除非词语更加繁冗会被视为一种进步。虽然,《上林赋》的出现与其立即被赞赏的现象还引起了新的潮流:一方面是以赋取宠,另一方面则是堆砌辞藻的习惯,深深地影响到后来的历代文学家。但在文学上并没有特出价值。
其二,《上林赋》与《子虚赋》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但其精神气脉却已大不同。如上面所说,《子虚赋》极富游说色彩,由双方来不断地辩论、反驳,以自己夸张宏肆的语言来压倒对方。而《上林赋》则表现了作者已经深深地体会大统一文化的滋味,里面完全看不到战国时代精神的余澜了。如果把作品放回其时代另一眼看,《上林赋》会体现出其价值的另一面。汉代是一个文学开始被重视的时代。但是这一时代所重视的文学跟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文学根本不同。汉武帝对辞赋文学特别喜好,即位后,便大力收罗这一类文人到中央宫廷来。这些人的主要任务是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议、批评。这样,赋以其特殊形式和表现手法,一边赞颂帝国的强盛,一边为王者加以讽谏,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用这些标准来评价,《上林赋》还的确值得处于汉赋的最高峰,因为它彻底地体现了汉代与汉代文学的所谓“大统一时代”的文化精神。
司马相如的文学事业与其对后代文人重大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在《史记·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主要是把贾谊当作和屈原一样关心国事而不遇其君的进步作家来尊敬和同情的,而对贾谊的文学作品,只收录了《吊屈原赋》和《鹏鸟赋》,著名的《过秦论》则附于《秦始皇本纪》之后。而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贾生列传》的六倍。可见司马迁对司马相如文章的欣赏与重视高于贾谊。而班固在其《汉书》里面全部把它照录下来,同样表达了他的肯定。
笔者认为司马相如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身上拥有代表一代文学的绝技与才华的同时,也具备这一代文人最典型的光荣与悲哀,正如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所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三
汉赋多用主客对话的方式构成赋文。一般分首中尾三部分。首部相当于引子,道出写赋原由。中部高谈阔论。尾部点题,抒发个人情怀。《玉井莲赋》的主客问答体跟汉大赋较为相似,都主要以一方的高谈阔论展开赋的主要内容;但同时也具有宋代文赋主客问答体的韵味,即主客之间不仅有逻辑性或哲理性的语言表达,而且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启发的情感互动。
汉赋在创作手法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描写事物面面俱到,以求穷形尽相。其二是通过大力夸张、对比,铺叙所描绘的事物。其三是大量用排比、对偶技巧来组织夸丽的文辞,层层铺垫。
《子虚赋》在描写云梦泽时已把赋面面俱到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瓑玄厉,碝石碔砆。其乐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藭菖浦,江蓠蘼芜,诸柘巴苴。其南侧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似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茛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色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芬;其上则有鹓鶵孔弯,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蜓貙犴。
这段例子可称为汉赋描写手法的经典之一。作者不仅用尽词语描写了云梦泽本身和其构成元素(山、石、土等等),而且还顾及其上下东西南北等有关事物。其夸张程度简直口若悬河,正如篇中人物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到了《上林赋》,夸张罗列手法更上一层楼,足以让人对着那“字林”而目瞪口呆。
《玉井莲赋》全面体现了这三特点。首先,他的确把玉井莲描写得穷形尽相,只是莫挺之改换一种手法,连续用了六个排比否定“非……”,用否定以收肯定之效。“非桃李之粗俗,非梅竹之孤寒。非僧房之枸杞,非洛土之牡丹。非陶令东篱之菊,非灵均九畹之兰。”玉井莲其形其相,美不胜收,妙不可言。桃李梅竹,牡丹菊兰,均为人们所欣赏的名花贵卉,然均不可以以之比拟,于是最后只能得出“A就是A”的断言判断:“乃泰华峰头玉井之莲。”
这一段“非……”排比否定正好也体现了《玉井莲赋》身上汉赋的第二特点。其铺叙了玉井莲一切名花贵卉都不是,又远胜这一切。这正是大力夸张类比所展现的效果。
上面这一段“非……”既是排比又是对偶。这种排比对偶技巧之运用,往往可以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充沛的气势,又如:
架水晶兮为宫,金凿琉璃兮为户。碎玻璃兮为泥,洒明珠兮为露。香馥郁兮层霄,帝闻风兮女慕。桂子冷兮无香,素娥纷兮女妒。采瑶草兮芳洲,望美人兮湘浦。蹇何为兮中流,盍相返兮故宇。岂濩落兮无容,叹婵娟兮多误。苟予柄之不阿,果何伤乎风雨。恐芳红兮摇落,美人来兮岁暮。
这种层层铺垫的对比、对偶主要是为了组织更多夸丽的文辞,呈现出更好的夸张、铺陈效果,跟汉赋相同。然而,他那种较为工整的文字和对声色和谐的追求就是后来的俳赋,比汉大赋的艺术手法要雕琢精细得多。
总体来说,《玉井莲赋》的“外貌”给人的第一印象仿佛像汉赋的“小样品”,不过在细节上,它体现出很大的不同。他其实也是越南“综合体”的产物之一,集各种赋体的特点于一身,写得极为漂亮,穷极越南汉语文学之美,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韵味。
四
越南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刚取得独立时,由于与中国文化传统暂时割裂,以及长期战争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统治者尚无暇顾及文化建设,所以这个时期越南的文化面貌比较贫乏。直到李朝(1009-1225)时期,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日益繁荣,越南文化与思想才得以兴起。
从前,只有僧侣才是知识阶层,他们不但在朝廷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也为越南文学史创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随着李朝正统的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制定于发展,越南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按照儒教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儒士阶层。儒士成为越南封建阶级中新的知识阶层,其产生是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需要。从李朝起,儒教在社会上开始居于重要地位,它成为服务中央集权政体、巩固等级制度和培养忠于皇帝思想的得力工具。
然而,在李朝时期,按照儒教思想意识进行教育和推行科举制度仅仅是个开始,培养出来的儒生人数相对较少。在社会文化层面上,佛教仍占优势,僧侣们仍对文化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到了陈朝(1225-1400),儒士阶层的人数日益众多,他们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逐渐取代了僧侣势力。在政权机构中,儒士出身的官吏日益取得优势并担当了朝廷重要职务。此时文学创作也完全由儒士阶层承担起来。
在李朝的基础上,陈朝的学习制度和科举制度越来越有条理和趋于正规化。据史书记载,陈朝的考试内容开始有赋。具体时间为公元1304年,陈英宗设定考试形式为四期:第一次考暗写,第二次考经义、诗、赋,第三次考诏、制、表,第四次考文策。后来考试内容在每一代都有所改变,但考赋这一项目一直留存。
儒教大力发展,并且有逐渐压倒佛教的趋势。陈初,佛教还盛行,但僧侣正逐渐失去在国家生活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到了陈朝末年,儒教和佛教发生了冲突。黎文休、黎括、张汉超等当时有名的儒士对佛教进行了批判和排斥。佛教的优势逐渐减弱,随后让位给儒教。
在加强中央集权政体的同时,统治阶级一方面想依靠儒教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培养人才的制度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但另一方面,由于陈朝历史伴随着抵抗元、明侵略军的抗战并连续取得巨大胜利这一过程,生活在生气勃勃地抗击外来侵略的时代,使统治阶级也不得不服从于民族精神和国家自强意识的强大威力。越南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不断地培养民族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和英雄气魄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意识渗透到各阶层人民中,并广泛地反映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
越南儒学由中国传入,与越南本土传统思想相结合,产生了某些变异。越南儒、释、道三教合一或三教融合的色彩比中国浓厚得多。越南人称之为“三教同源”。从丁朝到陈朝,越南社会思想基本上是三教同尊而以佛教为主。儒学发展到陈朝取得主导地位,到后黎朝形成独尊之势。在阮朝,儒学仍然处于正统地位。可以说,儒家学说与越南封建社会相伴始终。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文化与越南的民族文化相辅相成,构成了越南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民族心理,成为越南传统文化的主流。
赋是封建集权社会的文艺产品。儒家在越南的兴起和兴盛同样给越南汉文赋提供了思想基础。在越南汉文赋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带有越南特色的儒家、道家及“三教同源”等思想在越南汉文赋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在《玉井莲赋》中,这种东方特殊的思想内涵同样有所表现。
五
可以说西汉时期是文学为王者服务的时代,而汉武帝时期是最典型的体现。汉武帝喜欢辞赋,司马相如便不断地献赋。因为汉武帝喜欢游猎,所以才有了《上林赋》。因为汉武帝好仙,所以才有了《大人赋》。因为有这样的汉武帝,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西汉文学面貌。
然而,当文学为某些少数的人服务的时候,哪怕这些人多么喜爱文学,文学也不会如看起来得那么有前途,她的发展的空间反而会更狭小。因为个人爱好不管怎么广泛也是有限的,个人眼光不管怎么透彻也会有偏见的。再加上至高的权力因素,文学的发展其实是限制多过生机。因此,虽然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比起来,汉赋的文学价值显得有所不及。在文学思想与意义上,是逊于其他朝代的文学。
陈朝也是一个文学开始走向为王者服务的时代,越南士大夫也可以通过献赋以自荐。不同的是,陈朝的君主不是喜欢辞赋,而是喜欢能够创作好作品的贤才。赋凭其容量和艺术特点,是一种能充分体现作者学力和笔力的文学工具,因此在科举制度及荐举制度上有用武之地。
虽然都是献赋,但司马相如赋是以帝王及其霸业为中心,赞美的是一统天下的时代,而莫挺之赋是以自己为中心,赞美的是自己,或在更大程度上,是国家栋梁之才。这两种创作思想的不同导致两篇作品在其自己国家的文学史上有不同的命运。至今《玉井莲赋》仍然耐人寻味并照样有多人问津,而《子虚》、《上林》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其存在价值只是文学博物馆中一个时代的展品。
《玉井莲赋》的确在艺术手法方面受到了汉赋很大的影响,但其并不是一种复制品,而更像一种越南“综合体”赋的表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在于“量”,而“质”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子虚》、《上林》华丽宏大,《玉井莲赋》清晰娇小。《子虚》、《上林》的腔调是浑厚而充满理性的,《玉井莲赋》则是优柔而富有感情的。《子虚》、《上林》的效果是震撼人心的,《玉井莲赋》则是耐人寻味的。这些是《子虚》、《上林》和《玉井莲赋》的区别,同时也是越南汉文赋跟中国汉赋的基本不同。
[1]钟逢义.越赋纵横[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5).
[2]班固.汉书(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
徐 炼潘秋云(1981- ),女,越南人,越南胡志明市师范大学讲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东亚文学。
I207.2
A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2-0026-06
1006-2491(2015)02-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