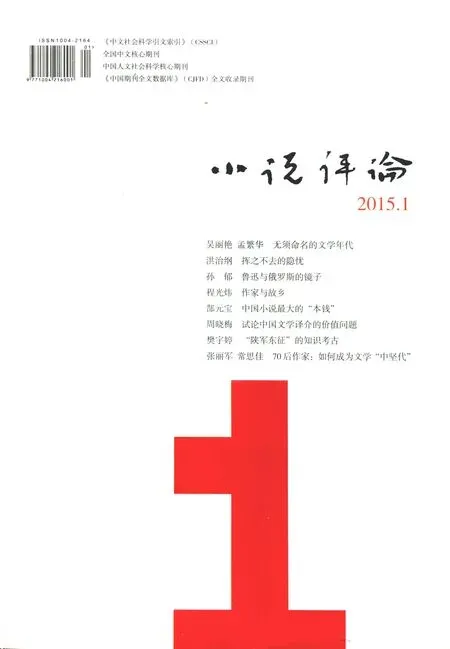艺术形式的实践与探求
——2014年长篇小说侧面
崔昕平 王春林
艺术形式的实践与探求——2014年长篇小说侧面
崔昕平 王春林
又是岁末年初,又到了从文体意义上对于一年来的长篇小说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即将成为过去的2014年,长篇小说文体的重要地位依然得到了很好的持续,依然有很多中国作家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之中。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这一年当中,值得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长篇小说,主要包括贾平凹的《老生》、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刘醒龙的《蟠虺》、雪漠的《野狐岭》、叶兆言的《很久以来》、关仁山的《日头》、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李骏虎的《共赴国难》、薛忆沩的《空巢》、张翎的《阵痛》、张好好的《布尔津光谱》、孙惠芬的《后上塘书》、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范稳的《吾血吾土》、叶弥的《风流图卷》、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张大春的《大唐李白》、阎真的《活着之上》、刘心武的《飘窗》、庞贝的《无尽藏》、郭严隶的《野沙》、王妹英的《山川记》、王蒙的《闷与狂》、周嘉宁的《密林中》、许大雷的《夏》、李伯勇的《抵达昨日之河》、季栋梁的《上庄记》、席星荃的《风马牛》等。细察这些长篇小说,思想艺术上自然各有追求各具特色,但其中有一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有不少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艺术形式上一种主动积极的实践与探求态势。本文之主旨,即在于对于2014年长篇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进行相对全面的检点与剖析。
大凡艺术形式的实验与探索,就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依我所见,年届八旬的老作家王蒙《闷与狂》的形式探索,就属于虽然精神可嘉但实际上却不怎么理想的状况。首先,是艺术形式实验探索层面上的令人失望。应该承认,王蒙在《闷与狂》的酝酿写作过程中,的确憋足了一股劲,的确有着一种彻底打破传统小说艺术规定性的强烈愿望。从这种愿望出发,王蒙差不多已经放逐了几乎所有的小说艺术元素。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甚至于小说细节,所有这些,在《闷与狂》中全都销声匿迹了无踪影。如果放大我们的视野至整个世界文坛,就应该知道,类似的极端艺术实验,曾经一度在法国的“新小说派”那里变成过现实。这一方面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就是萨洛特的长篇小说《金果》。“《金果》的问世在萨洛特发表《向性》二十四年之后,其写作手法已浑然天成,完美地体现了萨氏的创作美学和理念。与萨洛特的其他十二部小说相比较,这是一部分水岭式的作品,它进一步瓦解了传统文学中的人物、情节、叙述的概念,将声音和话语充斥到文字的每个角落。此后,萨洛特的每部小说创作,就都只是话语的堆积和发散。萨洛特认为,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言语具备一切捕捉内在心理活动的必要素质。它们表达起来灵活自由,语义微妙丰富,既可透明,又可隐晦,可以将那种既急促焦躁又忐忑不安的情绪加以保护或外露。《金果》则将对话推向了极致,发展成一部多声部的交响曲。”“萨洛特认为:‘小说的本质就是描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存在的那种心理状态,而不再是去纠结复杂的情节和人物,也不再是去描绘风俗习尚。如何将那种莫名其妙的,存在于每个人和每个社团的心理因素昭之于众才是小说的根本意义所在。’”虽然说所有的先锋都难免会遭遇寂寞孤独的命运,都难免会显得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但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说,萨洛特的极端艺术实验,应该说取得了相当程度上的成功。这一点,从她初期被视为“新小说派”的一员骁将,就可一窥其端倪。其实,只要认真端详一下萨洛特的小说文本,尤其是《金果》,我们就不难发现,作家不过是放逐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而已。人物虽然还在,但人物的外部动作与外貌描写什么的,却统统都不见了,读者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些人物带有明显潜意识意味的心理世界。但请一定注意,细节还在。只不过,萨洛特的笔端的细节,已非寻常意义上的细节,而是一种高度主观化的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话语洪流中的细节。读者稍不留意,这些难以捕捉的细节,就极有可能稍纵即逝。然而,尽管萨洛特小说细节的辨识难度极高,但细节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说过了萨洛特,再来说王蒙的《闷与狂》。单就小说写作实践的先锋性追求来说,王蒙较之于萨氏只能说是更加激进更加彻底。萨洛特小说中的人物与细节处理方式,尽管与读者所惯见的传统小说大为不同,但这些关键性因素毕竟还都在。然而,到了王蒙这里,不只是情节消失了,而且连同人物,甚至细节,也都不见了。从头到尾,我们读到的不过是“我”关于自己漫长人生极具主观化色彩的感觉描述而已。全书共计十六章,只有在细究文本,并且对王蒙生平有相当了解的前提下,才能够约略辨析出这十六章内容其实可以被切割为四大块加以理解。第一块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记述自己对于童年生活的印象。第二块是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叙写着少年布尔什维克王蒙的青年生活。第三块是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王蒙被打成右派打入另册后自我流放新疆的那段生活记忆。第四块就是剩余的部分,记述着新时期王蒙再度复出后的生活境况。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我们以上的分析与切割带有相当勉强的成分,实际的阅读感觉只可能是,读者自始至终都面对着一片可谓是漫无边际的话语洪流,似乎有一位话痨症者面对着你无休无止地开合着自己多少有些失控的嘴巴。很大程度上,王蒙的这部《闷与狂》可以被看做是通篇皆是内心独白的现代心理小说。读过之后,能够给读者留下印象者,大概也就是那通篇如同印象画一般随意弥漫的主观感觉,情绪化色彩极其鲜明的情绪表达。类乎于萨洛特那样的人物与细节,在《闷与狂》中几乎可以说是踪迹全无,更遑论对于人类潜意识领域的尖锐穿透与表达了。在我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可以被放弃,甚至于人物,也就可以不要,但一部被标明为小说的文学作品,又怎么可能没有细节呢?!从根本上说,小说是细节的艺术,细节是小说的生命。连细节都被弃之不顾了的小说作品无论如何都难言成功。而这,正是导致王蒙《闷与狂》艺术失败的关键症结所在。
但与王蒙的《闷与狂》相比较,在2014年的长篇小说领域,更多留下的,恐怕却是作家们艺术形式探索的成功纪录。其中给人印象深刻者,比如雪漠在《野狐岭》中对于幽魂叙事手段的有效征用。《野狐岭》的思想艺术成功,首先体现在对于一种叙述形式别出心裁的营造上。虽然小说所要表现的核心事件是齐飞卿的哥老会反清的故事,但雪漠所可以选择的叙事切入点,却是对于百年前两支驼队神秘失踪原因的深入探究。关键问题在于,既然那两支驼队早在百年前就已经神秘失踪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他们的失踪之谜弄明白呢?这样,自然也就有了招魂术的“用武之地”。“进入预期的目的地后,我开始招魂,用一种秘密流传了千年的仪式……我总能招来那些幽魂,进行供养或是超度,这是断空行母传下来的一种方式。”凉州一带,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民谣:“野狐岭下木鱼谷,阴魂九沟八涝池,胡家磨坊下取钥匙。”很大程度上,这个广泛流传的民谣,正是雪漠写作这部《野狐岭》的基本出发点。“那所有的沙粒,都有着无数涛声的经历,在跟我相遇的那一瞬间,它们忽然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记忆。在那个神秘的所在,我组织了二十七次采访会。对这个‘会’字,你可以理解为会议的‘会’,也可以理解为相会的‘会’。每一会的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劲头大,就多聊一聊;有时兴味索然,就少聊一点。于是,我就以‘会’作为这本书的单元。”
实际上,也正是凭借着如此一种招魂行为的艺术设定,雪漠非常成功地为《野狐岭》设计了双层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招魂者“我”(也即雪漠),是第一层的叙述者。而包括木鱼妹、马在波、齐飞卿、陆富基、巴特尔、沙眉虎、豁子、大嘴哥、大烟客、杀手(联系杀手所叙述的内容认真地追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个无名的杀手其实是木鱼妹。又或者,杀手与木鱼妹本就是同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结果),甚至连同那只公驼黄煞神在内,所有这些被招魂者用法术召唤来的百年前跟那驼队有关的所有幽魂,就构成了众多以“我”的口吻出现的第二个层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招魂者“我”正是通过这许多个作为幽魂的“我”从各不相同的叙事立场出发所作出的叙述,最大程度地逼近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
然后,就是那些一直在进行着交叉叙事的第二个层次的幽魂叙述者。从根本上说,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迥然不同于他者的精神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类个体从不同的精神立场与观察视角出发,所看到的自然是差异明显的景观。比如,关于木鱼妹那样一种可谓是差异极大的理解与判断:“在对木鱼妹的解读中,就有着境界的高下:在木鱼妹自己的叙述中,她是以复仇者形象出现的;大嘴哥眼中的木鱼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而马在波眼中,木鱼妹却成了空行母。”不同叙述者眼中木鱼妹形象的差异之大,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叙述者的话语权问题。关于小说中叙述者所拥有的话语权,曾经有论者写到:“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的史料,讲到某王朝灭亡时,往往会碰到女人是祸水这类叙述和评论。其中评论一看就知道是史学家的个人意见。但他的叙述有时则显得很客观,特别是那些没有夹杂评论的叙述。没有批判性的阅读,你可能会简单地接受这些为既定事实。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全是男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希望推脱责任的男人的叙述时,你就必须警惕。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叙述的权利,她们的声音被压制了,没有留下来。那么,你就必须细读现有叙述的字里行间,发现其中的破绽。”在这里,论者颇具说服力地论述了叙述者所拥有的话语权问题。雪漠之所以要在《野狐岭》中设置如此之多的叙述者,正与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关系密切。那么,对于雪漠在叙述者设定方面的积极努力,我们究竟应该予以怎样的衡估呢?必须注意到,如同《野狐岭》这样在一部作品中设置众多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情形,在现代以来的小说作品中其实屡见不鲜。究其实质,可以说是小说艺术形式现代性的一种具体体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把众多的人物设定为叙述者,就意味着赋予了他们足够充分的话语权,是对于他们各自主体性的尊重与张扬。在充分尊重人物主体性的同时,因为把阐释判断事物的权利最终交付给了广大的读者,所以,如此一种分层多位叙述者的特别设定,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于读者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正因为这种艺术设定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于人物与读者的双重尊重,所以自然也就成为了小说所具现代性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毫无疑问,对于雪漠《野狐岭》中分层多位叙述者的艺术设置方式,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
然而,同样是对于幽魂叙事手段的艺术征用,孙惠芬的表现又与雪漠有着明显的不同。与雪漠征用多位幽魂叙述者的那样一种罗生门式的叙事方式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在《后上塘书》中,孙惠芬只是设定了一位幽魂叙述者。这位幽魂叙述者,不是别人,正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之一,那位小说一开篇就被杀害了的刘杰夫的妻子徐兰。说起来,《后上塘书》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通篇的中心事件就是徐兰的意外被杀。徐兰的被杀之所以能够引起各方的高度注意,与她的丈夫刘杰夫在上塘村位置的重要存在着直接关联。上塘人刘杰夫,可以说是当下时代一位特别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一位颇具几分传奇色彩的传奇人物。作为上塘村的一位普通村民,本名刘立功的刘杰夫创业发迹的历史,可以说是与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而行的。又或者,也正是凭借着改革开放时代背景的强劲支撑,刘杰夫的创业发迹方才成为了可能。先是和一位名叫方永和的铁哥们合伙干工程,紧接着,“他在翁古城开起了夜总会;他和一个叫大下巴的黑社会合伙打人蹲了拘留;他改掉原来的名字,不叫刘立功叫了刘杰夫;他到福建和南蛮子合伙开矿,当了矿老板;他不但在福建有公司,在翁古城还有一个豪华大酒店;他在好几个城市里都有房子,家里保姆佣人三四个,来回出行,身边还有保镖……”刘杰夫的创业与发迹,本来与上塘也不存在什么关系。关键在于,很多年之后,发迹后的刘杰夫居然回到了上塘村来发展他的事业。因为刘杰夫已经由叫来叫去的传说变成了直逼眼下的现实存在,所以,他的成为上塘人心目中的显赫人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此一位上塘的显赫人物,他的妻子意外被杀身亡,自然会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事件。
事实上,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正是围绕着徐兰之死建立起来的。徐兰意外被杀,那么,她究竟因何被杀?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小说第一节,除了概略地介绍刘杰夫的创业发迹历史之外,集中记述徐庆中杀妻一案及其具体告破经过:“他杀死老婆的原因非常简单,大半年没回家,想回家和老婆亲热亲热,老婆却护着身体坚决不让动,怀疑老婆生了外心骂了几句难听话,结果,从不会发火的老婆居然扇了他响亮耳光,结果,他一个狠劲儿,就把老婆掐死在炕上”,并且,由徐庆中杀妻而引出了徐兰被杀事件。如果第一节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小说的序幕,那么,从第二节开始,就进入了故事的主体部分。贯穿于文本始终的双线结构,也正是从这一节才正式开始的。从这一节开始,尽管多数的章节都在以第三人称的全知方式讲述着警方积极介入之后的破案过程,但幽魂叙事的适度穿插,一方面可以以第一人称从死者徐兰的角度追述往事,观察家人亲戚对于自己猝死的种种反应,另一方面却也与第三人称的全知方式构成了互补的另一条结构线索。但不管是那一条结构线索,其最终都指向了对于真正杀人凶手的确定与寻找。就此点而言,孙惠芬的这部《后上塘书》在艺术设计上确实带有几分突出的悬疑色彩。
但同样是悬疑色彩的制造,刘醒龙的《蟠虺》又与孙惠芬有所区别。具体来说,刘醒龙《蟠虺》所采用的悬疑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关于那两封神异的甲骨文来信。这两封信的神异,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写信人郝嘉,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夏天,就已经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其次,这不是一封简体信,而是一封用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认识的甲骨文书写的信件。第三,是一种特别的寄信地址和方式:“省博物馆背后,进东湖公园大门,过小梅岭、可竹轩,道路尽头俗称老鼠尾的半岛最前端先月亭前,周一下午四点十分独坐于此的曾本之先生亲启”。当然,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先后寄来的两封信的具体内容分别是“拯之承启”与“天问二五”。一位明明确确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多年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给曾本之写信的。那么,这两封信的写作者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如此煞费苦心地给曾本之写这样一种特别的信件?所有这些,自然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悬念,牵引着读者以一种欲罢不能的心态去最终弄明白隐于神异信件之后的真相。
其二,是郝嘉与郝文章父子二人不无离奇色彩的人生遭际。作为曾本之楚学院曾经的同事,郝嘉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多年,但在小说中他却凭借着马跃之煞费苦心炮制出的甲骨文来信而强势浮出水面。马跃之之所以要冒用郝嘉的名义写信,正是因为他一直对郝嘉的自杀原因心存疑问。实际上,马跃之的疑问,也同样是曾本之无法释怀的一种疑问。尽管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但郝嘉的真正死因却构成了推动小说情节演进的一个悬念,而且也只有到了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读者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郝嘉之死却也与郑雄对他的出卖有关。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导致郝嘉之死的诸多原因才得到了充分的揭示。然后,是郝文章的离奇入狱。作为一位前程无量的楚学研究天才,作为楚学泰斗曾本之的得意门生,郝文章最令人费解的行为,就是因为试图把曾侯乙尊盘据为己有而锒铛入狱长达八年之久。也只有到郝文章后来出狱之后,我们方才弄明白他的入狱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愿的意思。唯其因为知道青铜器大盗老三口也被关在狱中,一心想着要彻底澄清曾侯乙尊盘真相的郝文章才不惜以身入狱一探究竟。曾本之在当时之所以未加阻拦,也是因为对郝文章多有了解的他,实际上已经隐隐约约意会到了郝文章的本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郝文章这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入狱行为,就真正称得上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了。此种行为所充分凸显出的,很显然正是郝文章那样一种为了学术真理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献身精神。
其三,是关于老三口与华姐传奇故事的讲述。除了曾经与曾本之在狱中会面之外,老三口一直以幕后的形式活动在小说文本之中。所谓幕后的形式,就是指我们所有关于老三口的信息,包括他与华姐的夫妻关系,他的盗墓行动,他的入狱出狱,乃至于他最后的惨死于密谋的车祸,都是叙述者借助于其他人物之口告诉读者的。正所谓盗亦有道,虽然身为青铜大盗,但老三口的言行举止却并没有完全逾越考古学界的规范。倘若机缘凑巧,在青铜重器方面拥有某种绝世才能的老三口或许能够成为如同曾本之一样的学术泰斗也未可知。事实上,最早发现曾侯乙大墓的,不是别人,正是老三口。在一般读者的理解中,老三口携带娇妻华姐那样一种充满冒险色彩的盗墓与亡命生涯,本就充满着突出的悬疑意味,有着足够的吸引力。当然,同样具有强烈悬疑色彩的,也还有老三口唱给曾本之听的那一首来自于岷县的民歌花儿:“高高的山上有一窝鸡,不知道公鸡么母鸡;清朝时我俩亲了个嘴,到民国嘴里还香着,好像老鼠偷油吃哩!”只要略作查对,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流行的民歌只有前四句,根本不存在最后一句。老三口刻意地添加上这一句,其实就是要暗示曾侯乙尊盘的埋藏处所在。
难能可贵的是,年轻的70后作家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也进行着非常引人注目的艺术形式探索。对于徐则臣《耶路撒冷》这样一种具有格式塔意味的艺术结构,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一个层面,是文本中已经由两种不同的字体明确标示而出的两条小说结构线索。一条是以初平阳、舒袖、杨杰、易长安、秦福小、景天赐这几位主要人物的名字标出的主体故事部分。另一条则是写作者初平阳应邀在《京华晚报》开设的“我们这一代”专栏部分文章的选辑。尽管初平阳实际完成的专栏文章数目很大,但最后被选辑进入小说叙事流程的却只有十篇专栏文章。这十篇文章,或叙事,或议论,或演讲,或调查报告,总归有一点,都是在围绕70后一代人说事。就设定主旨而言,徐则臣之所以要把这些专栏文章穿插编织到小说文本之中,显然是要进一步扩大主体叙事部分的外延。外延之一,就是把关注视野由主体叙事部分那个有限的人物群体拓宽到更为广大的70后人群。外延之二,假若说小说的主体叙事部分带有感性描写的特质,那么,初平阳的这些专栏文章则更多地带有一种理性提升的意味。能够把理性的思考有机地融入到小说叙事进程之中,正是现代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必然要求之一。而徐则臣,则很好地借助于专栏文章的设定做到了这一点。
外延的两种内涵之外,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徐则臣那样一种把专栏文章巧妙链接到小说文本之中的文本处置方式。因为是自己开设的专栏,所以通过初平阳而进行链接,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一种方式。初平阳之外,徐则臣的另外一种链接方式,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境中阅读这个专栏。比如秦福小,在北京,她一边开电梯一边阅读初平阳的专栏文章。再比如易长安,居然在仓皇的逃亡途中也能够发现有人在阅读这个专栏。当然,更值得注意的,则是舒袖对于《京华晚报》的刻意收藏。尤其不能忽略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徐则臣不仅巧妙地把专栏文章链接到了文本之中,而且也还赋予了专栏文章以相应的叙事功能。其一,舒袖之所以要坚持订阅收藏《京华晚报》,当然是源于她内心中对于初平阳的无法释怀。而这样的事实却又由她的丈夫叙述出来,一种妒恨心理的潜隐存在自然也就凸显无疑了。但更为关键的,却是初平阳此处所特别提及的,与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密切相关的“广场意识”。尽管徐则臣由于受制于现实文化语境的缘故,没有进一步展开,只是点到为止,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正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那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批正当年的70年代生人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烙印。一代人曾经的精神迷茫与困惑,一代人精神的最终走向成熟,显然与那一历史事件存在着无法剥离的内在联系。
其次,在第一条结构线索之中,细致地做更深一个层次的剖析,又明显地存在着四条次一级的结构线索。虽然小说中主体叙事部分陆续出场的70后人大约有十多位之多,但严格地说,这些70后人的故事实际上都是被其中四位主要人物形象的人生轨迹连缀在一起的。这四位主要人物形象的人生经历,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为了横贯于文本始终的四条彼此缠绕纠结在一起的次一级结构线索。具体来说,这四位人物都曾经游走于花街和北京之间。首先是初平阳。初平阳大学毕业后曾经有过一段在淮海师范大学教授美学的短暂经历,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师范大学平庸烦琐的教学生活而“决定辞去教职到北大去考博士”。尽管由于学术兴趣转移,中文系毕业的初平阳改考社会学专业后一度受挫,但最后却还是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北大的社会学博士。为了筹措博士毕业后继续前往耶路撒冷进行深造的费用,初平阳回到了自己久别的故乡花街。其次是杨杰。曾经有过一段行伍经历的杨杰,转业后进入一家濒临倒闭的碎石厂工作。很快地,碎石厂由于经营效益不佳而迅速倒闭,杨杰被迫无奈下岗。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之后,杨杰最终在北京站住脚,成为业界有一定影响的水晶石老板。接下来是易长安。天资特别聪颖的易长安,虽然也如同其他几位一样游走于花街与北京之间,但他所走上的,却是一条制假贩假的歧路。最后是四位中唯一的女性秦福小。由于弟弟景天赐自杀身亡的缘故,秦福小“从十七岁离家出走,在中国的版图上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在北京停下来,她还是秦福小。”尽管停留在北京的秦福小,也只不过是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电梯工,但她却出人意料地不仅以未婚之身领养了一个孤儿,而且给这个孤儿命名为景天送。最终,在外漂泊多年的秦福小,决定携带景天送彻底返回故乡花街。从以上的分析即不难看出,这四位在花街一起长大的70后人尽管其各自的人生故事有异,但一个共同点却是,都曾经有过在花街与北京之间漂移的经历。
作家宁肯,一贯以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性探索引人注目,这一点在《三个三重奏》中也有着突出的体现。宁肯《三个三重奏》的先锋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元小说形式的熟练运用上。熟悉宁肯的读者都知道,早在他那部先锋实验色彩鲜明的《天·藏》中,他就曾经运用过使注释成为小说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小说“半壁江山”的写作形式。这一次,在《三个三重奏》中,注释的形式再次获得“粉墨登场”的机会。假若说《天·藏》中的注释部分,更多地是在展开某种哲学或者宗教意义上的思辨,那么,到了《三个三重奏》中,宁肯在充分展开故事的同时,也在注释部分干脆直截了当地谈论起了小说写作本身。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小说中旁逸斜出的注释部分?宁肯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把它看作了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某种区别所在。传统小说是单一式封闭型的,是“单体的影院或者剧院”,而现代小说则是复合式开放型的,是包括有“回廊,花园,草坪,喷泉,LED屏”等众多因素在内的“一个复合型建筑”。质而言之,传统小说特别注重于某种审美幻觉的制造,尽可能地让读者产生一种并非是在阅读小说的感觉,企图迫使读者从始至终专心致志地沉浸于文本世界中。而现代小说,则是要以一种在小说中谈论小说写作的方式,彻底打破读者的审美幻觉,不断地提醒读者你正在阅读一部以虚构为其本质的小说作品。如此一种写作形式,很显然应该被看做是宁肯对于“元小说”叙事策略的一种有效征用。
其次,《三个三重奏》先锋性,突出地表现在艺术结构的特别设定上。作为一位有着自觉结构意识的长篇小说作家,宁肯无论如何都不会满足于讲述一个单线条的故事。营造一种带有突出复调意味的立体结构,对宁肯而言,几乎就是命定的事情。正如同标题所强烈暗示出的,“三个三重奏”之所以能够成为“三个”“三重奏”,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三条相互交叉缠绕的结构线索。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三条不同的结构线索。
一种可能的理解方式是,杜远方、李敏芬、黄子夫在杜远方亡命期间的故事为一条,杜远方、居延泽、李离八九十年代的故事为另一条,“我”、杨修、李南八十年代初期的故事为第三条。其中,前两条因为有杜远方的存在而关系密切,第三条则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平行关系。具体来说,除了主题上的遥相呼应之外,第三条与前两条之间关系的建立,更多地依赖于“我”的存在。“我”既是小说主体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小说中行动的一个人物。这里,需要展开一说的,是《三个三重奏》中叙事人称的特别设定。小说所实际采用的,是第一和第三两种叙事人称。前两条结构线索的故事,作家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这一部分,构成了小说中非注释的主体部分。第三条结构线索的故事,作家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落实到文本中,也就是小说中的注释部分。
但根据自己一种直观的阅读感受,笔者却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的理解方式。那就是,亡命期间的杜远方、李敏芬、黄子夫为一条,审讯期间的居延泽、谭一爻、巽为另一条,东窗事发前的杜远方、居延泽、李离为第三条。需要加以特别说明的一点是,这样的一种理解方式,并不意味着文本中的注释部分不重要。我们此前之所以要不惜篇幅探讨分析《三个三重奏》中元小说叙事方式的有效征用以及“我”、杨修、李南之间故事的深层内涵,本身就已经鞭辟有力地说明着注释部分的重要性。在承认注释部分重要性的同时,我觉得,把小说主体部分的叙事过程理解为“三个三重奏”,可能更有助于作家对权力主题做集中深入的思考与表达。假若我们把以上三条结构线索分别看作是A、B、C三部分,那么,在阅读《三个三重奏》的过程中,你就不难发现,宁肯的第三人称叙事实际上正此起彼伏地不断游走于以上三个部分之间。客观上,每条线索自身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艺术世界。把这样的三条结构线索再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自然就是内部构成成分复杂有序的所谓“三个三重奏”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宁肯的这部长篇小说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典型不过的复调小说。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贾平凹《老生》在艺术形式上所作出的可贵努力。到了《老生》,面对着长达百多十年的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继续采用这种作家自己在此前的《秦腔》和《古炉》中操作特别熟练的密实流年式的叙事方式,显然已经不再现实。到底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才能够更有效地进入自己的表现对象,自然构成了贾平凹所无法回避的艺术挑战。对于《山海经》的持续阅读和悉心揣摩,给《老生》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启发。贾平凹在后记中坦承:“《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一个“神话”,一个“人话”,道出的却是贾平凹阅读《山海经》的所悟所得。具而言之,《山海经》之对于贾平凹,首先就影响到了《老生》的艺术结构设定:“《老生》是由四个故事组成的,故事全都是往事,其中加进了《山海经》的许多篇章,《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由贾平凹自己的言论,再结合《老生》的文本实际,即不难看出,《山海经》所启发于贾平凹的,首先就是一种小说的“方法论”。作为一部古老的地理之书,《山海经》以极其素朴的方式记录了人类初民对于大自然的认知和理解。比如《南山经》:“……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蝮虫,多怪蛇,不可以上。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杻阳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金。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鱼,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作者就这样,一座山一座山地渐次写来。首先沿着方位写出山名,然后将这座山的矿产、动植物等等一一罗列而出,言辞简洁至极,直指事物本身,绝无任何旁逸斜出的附着与雕饰。这种写作方式对于贾平凹的启发,显然就是,当自己面对着一部堪称纷繁芜杂的几乎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切入表达的中国现代历史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如同《山海经》一样,以切片分割的方式加以表现。这也就是贾平凹自己所谓“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正因为采取了如此一种小说的“方法论”,所以《老生》也就成了一部没有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如此一种文本的生成,显然是《山海经》的影响所导致的结果。正如同《山海经》虽然写了五千三百多处山,二百五十余处水,你却很难指认其中的那座山或者那条水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一样,贾平凹的《老生》写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四个不同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写了一群人,但我们却无法指认其中的那一位就是居于小说核心地带的主人公。假若说“山”与“水”可以被看做是《山海经》的中心物象的话,那么,《老生》的主人公就可以被理解断定为是中国现代历史。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一部长篇小说,既没有贯穿性的整一故事情节,也没有贯穿性的主人公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我们一般并不把贾平凹看作是注重于小说形式实验创新的先锋作家,但由以上具有突出原创性色彩的艺术处理来看,贾平凹小说写作一种鲜明先锋性特质的具备,不管怎么说都是难以被否认的。
以上,我们结合具体的文本细读,对于2014年间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这一特定文体艺术形式上的积极努力探索状况,进行了一番相对细致深入的扫描与分析。通过以上分析,的确应该承认,我们在长篇小说的形式实践上已然取得了不容忽略的突出成果,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艺术经验。行将结束本文之际,我们真诚希望,未来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能够在艺术形式的实践与探求方面取得越来越丰硕的成就。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崔昕平 太原学院
王春林 山西大学
注释:
①王晓侠《从〈金果〉的多声部看新现实主义中的真实》,载《世界文学》杂志2014年第5期。
②陈心想《追问大学学什么》,载《读书》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