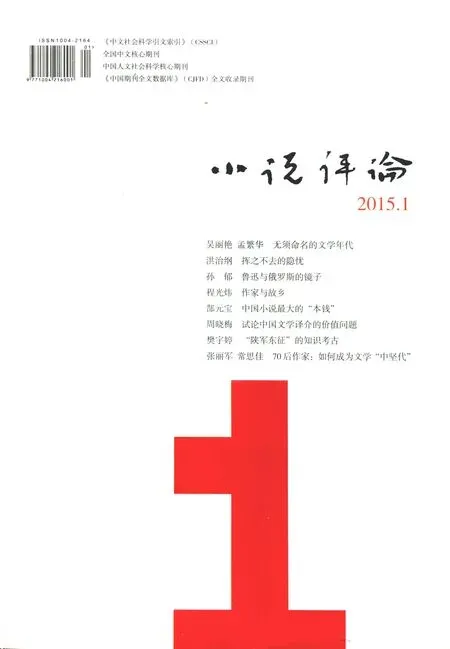书写三秦异闻:以杨争光为例
邱华栋
书写三秦异闻:以杨争光为例
邱华栋
1985年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界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文学方面发生了向内转和对文化和文学的根进行追问的变化,出现了寻根文学热潮。而艺术界,则出现了著名的“85美术新潮”,一大批深受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潮影响的中国艺术家涌现,并以举办各类展览的方式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和争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考察杨争光的小说,就很容易理解了。陕西作家杨争光是十分重要的一位小说家,他多年来都是一边从事影视剧写作,一边进行小说创作,他和主流文坛有所疏离,获得的评价,远不如他作品达到的水准高。而我认为他是一个被低估的小说家,对杨争光的研究将持续地进行。他在描绘三秦大地的奇闻异事和对历史的批判,以及结构小说的形式,都受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这样的拉美小说家的影响。
1957年,杨争光出生于陕西乾县,1978年幸运地考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之后,先是被分配到了天津工作,1984年调入老家陕西,后长期在陕西西安工作。进入21世纪之后,调入到深圳市文联,从事专业的文学创作。到目前为止,他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部:《越活越明白》、《从两个蛋开始》、《少年张冲六章》,中篇小说13部,短篇小说近50篇。此外,他还出版有诗集一部,收录了他从1979年到1988年之间写下的140多首诗歌。他介入影视界,写有《双旗镇刀客》等多部电影作品,参与电视剧《水浒传》的剧本写作,担任《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总策划。影视作品的创作是他赖以为生、改变了他的生存环境的营生,而他内心里最喜爱的,还是小说创作。
考察杨争光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需要将其定位在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他的写作与1985年之后勃兴的寻根文学、地域文化小说和先锋派文学都有关系,但他与这样的写作又都保持了某种疏离感。他阅读面很广,也深受当时的拉美文学热潮的影响,比如,他就谈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
没有空间存在的时间,只是一个理论的存在。没有时间存在的空间,也是一个理论的存在。《百年孤独》开篇的第一句,从时间来说,是一个线性的回旋。它的‘魅力’在于,一句叙述,不仅‘叙’出了时间的质感——有空间存在的时间;也‘叙’出了空间的轮廓,有时间存在的空间。有质感的线性时间必然和空间有关。
‘缠绕着的时间’与‘毛线团’:在小说一书中,时间是可以依叙事的需要缠绕成团块和圆球的——我称为是‘毛线团’——这正是人类历史记忆中的时间的性状。也许只有在小说中,作为记忆和过程的时间才可以得到如此真实的呈现。《百年孤独》中的时间,就是‘缠绕着的毛线团’。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抽拉‘还原’成一条直线。但要小心一点,否则,会把它扯断,使它变成无数个小线段。然而,也不要紧,事实上,记忆中的时间经常是不完整、甚至是不连贯的——时间不能在事件(现实、实在)中脱离空间而独自存在。这些不完整,不连贯的线段就成为‘片段’。
但《百年孤独》的魅力不仅在此。《百年孤独》具有小说艺术经典的几乎所有的元素和要件:它塑造的艺术现实是成熟的,也是童稚的;它有经典的人物,经典的人物关系;它有非凡的想象力,它的想象力不仅是感性的,也理性的;它具有人物(生命)面对事件的极富个性的应对。而整部小说,则是马尔克斯面对《百年孤独》这一艺术事件的个性化应对。它显示了拉美文学爆炸的高度。
那么,在他的作品里,有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的痕迹呢?我仔细阅读了他的多部作品,显然,在小说的结构和时间因素的运用,在本土的荒诞和魔幻手法的运用,在对地域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在小说的结构形式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对叙述艺术的精妙把握,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主义,在杨争光的笔下,处处都可以看到其回响。
我在阅读杨争光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时,常常会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的潜在影响。他巧妙地化用了拉美文学的精神和魂魄,将之与中国独特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具体说来,在杨争光的笔下,体现在陕西的地域文化、历史记忆和叙述艺术上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的运用上。
具体说来,地域文化的部分,在于杨争光所写的,大都是和陕西的地域文化有关,语言、民俗,人的社群结构,都是陕西特别是关中一带的农村的面貌。历史记忆的部分,杨争光的小说时代背景隐约地涵盖了从20世纪初期中国军阀混战到匪盗横行鱼肉乡里,再到日寇入侵和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延伸到了198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长达百年的历史记忆,都是杨争光从中汲取写作灵感的创作资源。空间结构和时间的运用,在于杨争光小说叙事艺术的独特呈现,这一点我在下面分析他的作品的时候,会进一步地阐发。
长篇小说《越活越明白》发表于1999年,是杨争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篇幅也最大,有42万字,但艺术水准比《从两个蛋开始》还是逊色一些。这部小说是杨争光的知青生活的回忆性书写,带有着某种自传性。但小说内部的时间跨度依旧很大,从1970年代写到了20世纪的末期。
杨争光喜欢用小标题来结构作品的章节,小说共分24章,每一章有4到8个小节。小说中的几个主人公,他们作为知识青年来到了乡村,在严酷的环境里“战天斗地”,最后体验到了人生的悲苦。改革开放使他们的命运得到了转变,小说的地理背景和空间叙述,也由陕西农村到了沿海的开放城市。人物的命运在金钱和欲望的漩涡里得到了新发展,小说中的人物越活越明白了,而他们也老了。这部小说探讨的,还是人物的命运,但这部小说让我觉得它是一部根据杨争光创作的某部电视剧的脚本改编而成的长篇小说。
完成于2002年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是杨争光的代表作,小说的题目就带有黑色幽默的成分,让人很有兴趣,从两个蛋开始?这两个蛋,是什么蛋?接下来,我们明白了,原来,这两个蛋是两个人,一个叫雷震春,一个叫白云霞,他们是在1949年共产党军队在推进过程中,留在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来的奉天县的两个工作组成员。后来的故事,就由这两个“蛋”的命运展开了叙事,小说的地域背景,是奉天县一个叫符驮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雷震春和白云霞这两个革命下的“蛋”来到之后,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的时间跨度达到了50年,一直到2000年,是一个中国乡村的独特的当代史。
我认为,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极大地展现了杨争光的文学特质:狡黠的中国乡村才有的黑色幽默、历史批判与人道主义、人性的永恒性与历史的无情和荒诞。这部小说也体现了他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的一些文学性的塑造,共分4个部分,36节,基本是沿着线性时间来叙述的,讲述了1949年之后一个中国乡村的独特故事。
这部小说是那样的真实,但是在触及到诸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悲剧性历史事件的时候,充满了荒诞感,尽管小说中很多事情都是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真实发生的,可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读起来,却带有着荒诞和魔幻的色彩。这部小说简直是另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某个乡村的野史,别史。特别是小说中关于“大跃进”时期乡村的大量真实情节的描写,在我这样的没有经过那个历史时期的作家看来,带有着别有意味的荒诞和魔幻感。比如,为了亩产过万斤,农民会造假到将所有的稻麦密实地堆积起来,在稻麦田里,孩子可以坐在成熟的麦秆之上而不会掉下来。为了种植麦子,农民给麦子施肥的时候,竟然用煮透的狗肉汁来浇灌。读来不禁嗟叹,原来,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在小说的最后还有两个简短的附记,附记一,是对符驮村的考证和一些方言的解释;附记二,则是符驮村1950年到2000年大事记,成为了小说很好的注解。
2009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杨这部《少年张冲六章》,我觉得,是他继《从两个蛋开始》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本来,杨争光的写作姿态,是一直保持着对历史和现实的尖锐批判,同时,对写作手艺的琢磨和讲究,对结构的精心把握,也一直是他的优长之处。
《少年张冲六章》是一部教育小说,也是一部结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的结构很有特点,让我想起来巴尔加斯·略萨的一些作品。全书分为六章,小说的叙述是时间平行的,分别写了张冲的爸妈,老师,同学,姨夫一家,其中第五章,是张冲的作文的引文和点评。到了第六章就是张冲自己,他从小时候长到了17岁,在一家娱乐城当保安,他在与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发生冲突之后,挖掉了那个局长的眼睛。
这部小说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史。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小说以一个叫张冲的少年,在具体的学校和家庭的小环境中的扭曲性的成长,侧面书写了这个变革的时代之痛和时代之伤。最后,酿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张冲挖掉了公安局吃喝嫖赌的副局长的眼睛,然后因为只有17岁,最终进了少年管教所。
这部直逼现实的小说,读来让人震惊。少年张冲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就是我们孩子的故事,每一个当代人都有可能是张冲,而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张冲这样的儿子。小说由此引发了我们对当代文化、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和世道人心的无尽的思考,并使小说文本充满了不断被延伸解读的可能性。小说在处理内部人物和时间的方法,采取了各个章节平行的手法,六章,仿佛是六条线索在平行发展,与巴尔加斯·略萨的那些结构现实主义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杨争光的三部长篇小说相比,他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似乎艺术成就要更高。而他引起广泛瞩目的,也是这样一些中篇小说:《黑风景》《赌徒》《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流放》《杂嘴子》《对一个符驮村人的部分追忆》《驴队来到奉先畤》,以及独具特色的大量短篇小说,比如《光滑的和粗糙的木橛子》《公羊串门》《上吊的苍蝇和下棋的王八蛋》《他好像听到了一声狗叫》《代表》《高潮》等等。这些小说独具陕西特色,在于杨争光对陕西方言的运用和陕西民俗的书写。对此,他曾经在谈话中说到:
陕北的民间艺术包括剪纸、腰鼓、唢呐、民歌等,都是一体的。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复杂。就说剪纸,剪得那么笨拙,那么单纯,就像是小孩子的作品,但你能感到一种浑厚、沉重的东西。我之所以喜欢它,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那种返璞归真的复归心理。它确实具有艺术的魅力,它和好多现代派艺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确实令人震惊。比如延长有个刘兰英,50多岁了,她就绝对不能剪出两幅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两次剪不出同样的作品。她在剪纸之前,也不知道能剪个什么样子,剪着剪着就出来了。我想这就是一种最佳的创作状态,在剪纸之前她不清楚的只是表现形式,她有思想、感情、人生经验的积淀,她有强大的基础,问题只是怎样一刀一刀把它表现出来。她需要寻找的只是一种形式。这些民间艺术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用一种简单、笨拙的形式反映了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杨争光是如何看待民俗的,是如何从民间文化资源里吸取创作的养分的。剪纸艺术家创作一幅剪纸的过程,被杨争光看成了和自己的创作过程一个样的艺术发生过程,于是,他接着说:
所以,我不认为后来的艺术就比以前的艺术高级,艺术和科学不一样,不掌握科学的人能创造人类最高的艺术。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背景,它与生存环境又必然联系,在这种环境里只能或必然产生这样的文化,比如拉美产生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国的‘寻根文学’,最本质的弱点就是缺乏对生存的体验,对洋玩意儿的移植(很生硬)。有人说,形式就是内容,我不同意。福克纳,马尔克斯对我的启发是,他们的东西恰恰是立足于本土,表现了他们那个地域中人的生存状态。
在上述这段话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杨争光自己的文学观念。他的作品土得掉渣,让我想起来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但是他又很洋气。一方面,他对“寻根文学”的弱点进行了自己的批评,显示了他拉开了与寻根文学流派的距离。寻根文学的对文化的根的寻找,在杨争光这里,就是对本真的、当下的、历史想象的本土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吸取。我在阅读他的短篇小说《光滑的和粗糙的木橛子》《公羊串门》《上吊的苍蝇和下棋的王八蛋》《他好像听到了一声狗叫》等作品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些作品和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短篇小说集《平原烈火》是多么的亲近。一个写的是陕西高原上干坼、贫瘠的土地上的中国农民那悲剧性的挣扎和渴望,一个人写的是墨西哥失去土地、卷入战乱的农民的境地,两者之间,却有着同样的人生景象。杨争光笔下的中国农民,为了一口粮食,为了一个木橛子,为了一句话都能到拼命的地步,而胡安鲁尔福,则将墨西哥农民被大历史所席卷的无奈命运写得让人心酸,发人深省。
而且,在小说的叙述艺术上,杨争光和胡安·鲁尔福都是采取了对话、白描和简单的叙述,留白很多,增加了读者的想象力,但是却增强了阅读的冲击力。在杨争光的中篇小说代表作《黑风景》《赌徒》《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流放》《杂嘴子》《对一个符驮村人的部分追忆》《驴队来到奉先畤》中,我们看到了历史背景的虚化,根据作品人物的命运,隐约可以看出有的写的是晚清时期,有的是民国时期,有的则是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时期的中国大陆农村。
这些中篇小说,无不聚焦于小人物和某些特定人物的命运,将人物放到绝境中,然后看这些人是如何迸发出善恶来。有趣的是,他的这些颇具中国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地域文化民俗小说,却有着一定的世界和人性的共通性,比如,他的《老旦是一棵树》被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英国翻译家特别地把他的这部小说翻译成苏格兰某个偏僻乡村地区的那种乡土英语,使英语读者很好地理解了他的这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又被一个保加利亚导演看中,将中国农民老旦的故事,拍成了一个保加利亚的农民老旦的故事。在这部小说如此离奇的流传过程中,可以看到杨争光作品所深具的人性、命运的人类普遍性。
综合说起来,纵观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我可以隐约分析出拉美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对小说内部时间的运用、对魔幻情节的使用上,对杨争光发生了影响,而杨争光在多次的谈话中也说到了一些。但巴尔加斯·略萨在小说结构和叙述技巧上对他的影响、胡安.鲁尔福的短篇小说在主题、对话、故事、人物等方面,和杨争光也有着某种联系,不过这都是杨争光从未提到的。这有时候就是优秀作家之间的某种呼应,谈不上他们真的影响了杨争光,因为,杨争光就像所有的陕西本土杰出小说家那样,从来都是把自我的发现和创作放在了首位,而从来都不想去模仿什么。于是,最终成就了独具特点的他自己。
邱华栋 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②③杨争光:《杨争光文集》之卷九《交谈卷》,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99—300页,第351-356页,第351-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