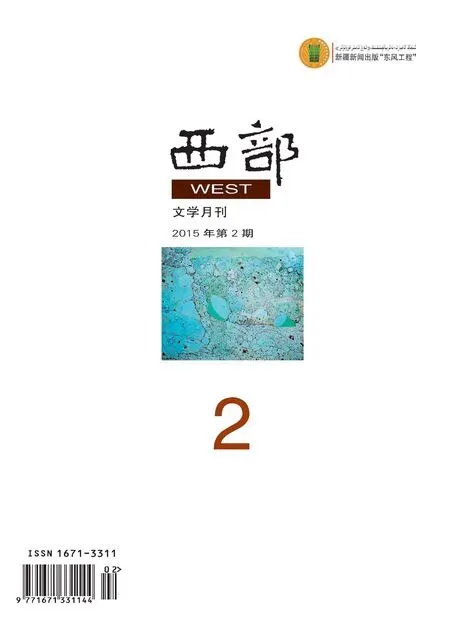春节心情(外二篇)
高兴
1
独自坐着。大多数时间都独自坐着。独自,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宿命。一个人的世界。本质上,我们都只有一个人的世界。
过年,仿佛是遥远的事,是小辰光的事。小辰光,喜欢热闹,喜欢家庭大团聚。岁月流逝,心理也在变化。越来越偏爱静了,越来越沉湎于独自了。独自,无边的自由,无边的想……是那样的远,又是那么的近。消息,抵达内心。
Margaret 发来薰衣草的照片,给除夕的早晨增添了几许色泽。受松风的影响,我也喜欢上薰衣草了。这些天,薰衣草成了牵挂。松风在埃及,那里,局势动荡。昨天,松风乘坐祖国的包机,平安归来。于是,薰衣草又成为最好的祝福。
在读法国作家高兹的《致D》,一封长长的情书。我停留于这样的句子:“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一遍又一遍地读……
2
家在哪里?或者哪里是家?
除夕之夜,我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似乎与过年的气氛格格不入。但换个角度,恰恰是过年气氛让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这和“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究竟来自何处?”等问题一样,同样属于人类的基本问题。
当赵本山们正在春晚舞台表演的时刻,我却被一个基本问题困扰着。这其实涉及到归属和归属感,又进一步关系到幸福和幸福感。不能深究的问题,又不得不深究的问题。昆德拉、马尼亚、米沃什、温茨洛瓦、奈保尔、萨义德、萧红、三毛等作家都反复深究过这一问题。归属和归属感,因而成为理解他们众多作品的关键词之一。多少人一生都在漂泊,苦苦地在文字、在内心、在爱中寻找归属。不管能否找到,起码你得努力去寻找吧。
窗外,爆竹声不断响起。全世界数十亿华人都在过年,多么气势磅礴的节日。不仅仅是欢喜吧,肯定也有隐痛,不合时宜的隐痛。隐痛,自然需要隐藏,否则,你就太自私了。在内心,我祝福所有的人平安、健康和快乐!
接到松风短信。从开罗平安回到祖国的松风特录《出埃及记》以表感恩之心:“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领出埃及……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云柱和火柱,保佑众生。云柱和火柱,保佑你走向远方。
感恩,这个散发着宗教光辉的词,有拯救的力量。人心,面对现实问题时,错综而脆弱。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世界和生活的复杂性常常让人不知所措。痛,油然而生。文学的最大使命之一就是要发掘和呈现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而人呢,则需要超越和升华。你爱一个人,就要接受他或她的一切。你爱他或她,他或她也爱你,这就够了。相信爱,也就是相信时间,相信未来。在此意义上,爱,是一种信仰,当然也是感恩。为什么偏偏是你?为什么偏偏是他或她?这就是恩赐,就值得感恩。
空茫,渐渐被填满。是感恩?是一则短信?一次聊天?一个电话?该出去走走了。是的,早该出去走走了。有了祝福和感恩之心,你发现,世界原来完全可以变得单纯而美丽。
薰衣草和紫苏,我一直分辨不清。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索性就这么想吧:薰衣草就是紫苏,紫苏就是薰衣草。呵呵,简单,而快乐。
3
总在做梦。一做梦,就会抵达远方。远方,本身就是梦,时刻都在诱惑人的心灵,抗衡着此处的苍白。法国天才诗人兰波说:生活在别处。于是,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一首行走的诗歌,走向远方,不管前景如何。
我不想讲话,也不愿思想:
但无限之爱涌向我的灵魂,
我要走向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像个流浪儿,
和大自然一起幸福得如同和一个女人为伴。
——兰波《感觉》(葛雷译)
在梦中醒来,仿佛还闻着隐约的芬芳。梦有气味儿,有时,还能听到声音。芬芳来自何处?隐秘的源头,兴许同远方有关。内心在呼唤,呼唤着暖,呼唤着春,呼唤着远方。昨天,立春。立春,在北方,要吃春卷的。美丽的民俗,欢呼春的来临。春节,就是春的节日。
温习着一些词,细小却温暖的词,比如粥,比如米香。想喝粥,突然的,像一种呼应。自己动手,淘米,量水,点火。不一会儿,竟然就有米香,在屋里弥漫开来。早晨,喝碗粥,暖暖的。这种感觉,真好。
天,一直阴沉着。九点半左右,听到一个消息。那一刻,天就放晴了,真是巧了。“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卞之琳的诗在脑海中响起。多么有意味的诗。光照到我的书桌上了,照亮了我写下的每个字。
光与水,水与光,石头城,西域,湖,船,家乡的黄酒,雨中的石子路,童年的伙伴……潜意识中,这些词,叩击着我的心扉,轻轻的,柔柔的,同光,同水,融合在一道了。我知道,又在想了……想家。
4
被爆竹声惊醒。睁开眼,懒洋洋的,想:哦,今天是初五。初五,民俗中,也有讲究的,叫破五。
停留于一本书,或者停留于一个念想。时间变得精致,显出它的肌理。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散漫地阅读,而且越来越喜欢散漫地阅读。散漫地阅读,随兴,惬意,也轻松,真正是幸福的阅读,是十八世纪的阅读。而如今,实用阅读和功利阅读,简直泛滥成灾。这是生存的需要,倒是能理解的。
依据心境,拿起一本书,读上几页,基本就能判断,是否情愿跟着书走。常常,阅读还与气候有关,而气候绝对影响心境。二十岁时,回到家乡,逢上雨天,就会带上一本诗集,多半是爱情诗集,到公园,找一个亭子,坐下,在雨声中读诗。浪漫,诗意,却有点做作。呵呵,可爱的二十岁。人到中年,再逢如此情形,就会泡壶茶,坐在亭子里,听雨。还读什么诗啊。听雨,其实也是在读雨,你能读出各种味道的。
阅读的边界,日渐开阔。你走在路上,也是在阅读。你关注一个人,也是在阅读。倘若善于阅读日常细节,会其乐无穷的。那些优秀的作家,都首先是优秀的阅读者,广阔意义上的阅读者。我听见赫拉巴尔在感言:“生活!生活!生活!”我听见纳博科夫在强调:“伟大的细节!”我还听见索雷斯库在低语:“诗意并非物品的属性,而是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中观察事物时内心情感的流露。”
画面也值得阅读。我要向莫非和益明致敬。摄影家,用画面说话。他们也在阅读,阅读并捕捉。益明发来不少照片,都是家乡的场景,深得我心。细微,更有韵味。这几天,我天天都在阅读益明的照片,仿佛是一种温习。就是一种温习。仿佛她在走来:我梦中的爱人。无数美好的感觉,渐渐的,溢满了我的心头。于是,阅读,又有了甜蜜的滋味。而想象中的甜蜜,纯粹得如同刚刚出生的婴儿。
5
时间影响心绪,至少于我而言。凌晨四点,醒着,胡思乱想,心绪紊乱。那是个容易忧郁的钟点。我特别害怕的钟点。若能用睡眠绕过它,就好了。并不羡慕吃得香的人,却绝对羡慕睡得香的人。睡眠养人的。那些睡得香的人有福了。
看着天渐渐亮起来,没有期待的晴朗。天阴,似乎要下雪,但终于还是没有雪的影子。今冬,北京几乎就没下过雪。而雪的消息,却不断从南方传来,也从西域和中原传来。气候整个儿颠倒了,世界也整个儿颠倒了吗?心里在隐隐盼着雪。是呼应一种心绪?还是希望冬天就得像冬天的样子?
庙会就在附近,红红火火的样子。最后一天了,想去看看,感受一下过年气氛。购得票,进入公园,顿时陷入人的漩涡,密密麻麻的面孔朝你逼来,恐怖的感觉袭上心头。天哪,赶紧出逃。不到十分钟,就又站在了园外。这时,忽然觉得,静,多么的贴心。最好就我,和她。
刘恪兄要来,真好。又有几个月不见了。这世道,人们活得好像都不容易,刘恪兄亦然,遇到了不少烦心事。即便这样,还完成了六十万字的书稿,不得不让人佩服。六十万字,不是闹着玩的。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真正的血汗啊。写作,是件熬人的事。望着坐在沙发上的刘恪,觉得他又苍老了许多,真有点心疼。可他倒情绪不错,说着自己的种种计划,说着读书的快乐:“每天,躺着读一本书时,心,那么的静,有说不出的舒服。”我们可不敢躺着读,眼睛吃不消的。刘恪却神了,怎么读,视力都照样好。天生的。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想写点什么,却感到了表达的艰难。那个英国女人伍尔芙说:“我们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少得何等可怜。思想的幻影,往往不等我们把它抓住,一从心头出现,就又从窗口溜掉,要不然它那一线游移不定的光芒倏然一闪,就又慢慢沉落,复归于黑暗的深渊。”说得极是。索性沉默着,沉默着,任心随意漫游,再慢慢地合拢……
窗外,依然有礼花点亮夜空。
6
雪,还是飘临了,出乎意料,仿佛夜间发生的奇迹,又仿佛某种救援。刚开始还没注意,在投入地读信。待读完信后,走到窗前,不由得一声惊喜:啊,雪!
这竟然是北京今冬的第一场雪,也是新春的第一场雪。人们几乎停止期盼的时刻,雪,还是飘临了。难得的雪,带来的是远方的消息,是天空的祝福吧。我情愿这么想。
望着雪,陷入沉默。内心饱满,或空茫到一定程度时,沉默,便是最好的表达。雪,是天空的词语,洁白、透明、舞动的词语。天空的词语,写满大地,衬出薰衣草的影子,我们只能慢慢领会。于是,唯有沉默。
光,落到雪上,一闪,变成梦了。沉入水。雪,其实,也是水的变奏。光,与雪,与水,一道演绎的梦。飞翔的梦,向着天空,朝着那个方向。可以直接抵达的,偏偏绕了个大圈子。兴许,是为了尽量延长飞翔的过程。过程,美,缠绵,而忧伤,呼唤声声,穿越漫长的路途。抵达,却是瞬间的事。兴许,要用一生一世,完成梦中的抵达。一生一世,就有了盼头。
毕竟已人到中年,否则,倒回二十年,会冲向雪地的。那时,根本没在意,踏上雪地的时刻,雪已受到了压迫。那时,还根本不懂得雪的感受。如今,我会站在雪地的旁边,看雪怎样在光线中变幻,闪烁,呈现微妙的表情。雪,是一个名词,又迅即成为动词。雪,也在做梦呢,是天空布置的功课。
此刻,究竟是深夜,还是凌晨,我已分辨不清……
7
“和你在一起我才明白,欢愉不是得到或是给予。只有在相互给予,并且能够唤起另一方赠与的愿望时,欢愉才能存在。那一天,我们彻底把自己交付给了对方。”法国哲学家高兹在《致D》中如此写道。情人节,再次捧起这本书,似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是封深情的情书。当今时代,深情,已成为一种奢侈。可真正的爱,又怎能没有深情。否则,它就值得怀疑。深情,从心底升起,将世界缩小,又把世界放大。无限大。
缓慢地读,有些书,就得缓慢地读,就像这本《致D》,也就百十来页,完全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读完,可你却舍不得一口气将它读完,你更愿一句一句细细地品读,将它当做陪伴,当做深情的酒,读读停停,抬起头,想,仿佛被句子牵引着,甘愿被句子牵引着,沉入内心,或走向远方。窗外,玫瑰的呼唤隐隐传来。是情人节,爱人,爱人,爱人,你在哪里?
一束光
垂落
天幕的缝隙
照亮头一朵春花
伊朗电影导演基阿鲁斯达米的诗。他说的头一朵春花,究竟是什么花,又有着怎样的颜色?是紫色的吧。下意识中在问,也并不见得非要答案。世上很多事,没有答案,反倒更能保持某种魅力。这也是艺术的秘诀。
已是子夜,我静静地躺着,不愿思想,只愿沉醉。被一股力推动着,迷失在半睡半醒中。即便闭着眼,你也能感觉到那束光。那束光,垂落,我却听到了水的声音……
8
一晚上都坐在窗前,看礼花不断地点亮夜空,绚丽得让人目眩。正是元宵节,又一股欢庆的浪潮,将春天的节日推向最后的巅峰。
此刻,这喧闹反而令我静,异常的静。在礼花的衬托下,享受静,享受孤独。其实,也曾想走出门去,点几支礼花,感受那简单的快乐,可心里,总有更大的声音在回响。那声音令我更静,仿佛水果的芬芳,已将水果提升到了诗意的高度。仿佛旋律的余韵,已将旋律转化为梦幻的影子。想,同礼花一道升起,却比礼花升得更高。它刺破天空,又融入天空。
还是忍不住吃了两个元宵。正好两个。出于期待。都说吃了元宵,一切都会圆圆满满的,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这自然只是种说法。可人在期待的时刻,愿意相信所有美好的说法。期待本身,就是对美好的向往。期待,让爱的人走近爱,让梦的人去实现梦,让生命成为生命。期待,就是六年,十年,你都愿意等,你都相信,那一天定会来临。期待,是水和光的动力,最终变成了水和光。期待,也就是狄金森所说的“希望”,长着羽毛,栖息在灵魂深处,唱着没有歌词的歌曲,无休无止……
远方的远方,雪还在飘吗?谁又在雪花飘中行走?想象,也是想的一种形式吧。沉默,同样是。沉默中,雨,热烈地叩击着心扉。雨同雪会合时,天空撒下了水晶。我想说的,我没有说,天空在说,用最高的言语。
节日即将过去。春天已经来临。回味的时刻,心,又不禁在问:怎样的梦,怎样的美和好,在等着我们呢?
瞧,你又在期待了……
豆豆
1
整整一天,没有停歇的劳作。筋疲力尽。
这时,豆豆走来,望着我,在静谧的光中。我不睡,她也不睡。从来如此,一种天然的默契。
真想为她写点什么,随便写点什么。几句话,几行诗纯净的表达。为她,更为我自己。可是望着她,在静谧的光中,我竟然感到了言语的窘迫,言语的空洞和无望。望着她,我干脆失去了言语。没有言语,没有诗歌,只有豆豆,只有豆豆在初冬的子夜望着我,而我也望着她。这可爱的小东西,我全部的字典和笔,我最最温暖的专制和剥削。
2
连续两天了,闷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有豆豆陪伴着。累了,困了,就抬起头,歇息歇息,喝口水,抬起头,就能看到豆豆。总在我的视线里的豆豆。
想起黑海边。那时,豆豆真像个豆豆,那么小,小篮子都能装得下。每天,都带她到海边溜达。她喜欢溜达,喜欢海边。一出门就开始小跑,不管不顾,像只小鹿,直冲着海边跑去。是某种辽阔的蓝吸引着她?是海面吹来的风吸引着她?不晓得。这都是人的猜想。豆豆没这么多情,她只晓得游戏,海边就是最好的游乐场。常常,海鸥见到豆豆,会故意俯冲下来,撩拨她一下,逗弄她一下,然后又鸣叫着向天空飞去。海鸥原来也如此淘气。豆豆急得原地打转,对着天空汪汪叫,可又无可奈何,恨自己没有翅膀,不会飞翔,只记住了海鸥的鸣叫。后来,离开海边多年,哪怕电视里传出海鸥的鸣叫,她依然会从里屋或阳台冲出来,竖起耳朵,对着电视汪汪叫。那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海边。
3
睁开眼,铺天盖地的光,灿烂得有点奢侈。来自天空的惊喜。光让人精神,也让人慵懒,多么惬意的慵懒。
多么惬意的豆豆,她最会享受慵懒的快乐了。此刻,她就卧在光中,眯缝着眼,静静的,乖巧又满足的样子。有时,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光让她沉醉。
光让她闪烁,让她也变成了一团金黄的光,仿佛光被光照亮。任何时候,她都愿融入光中,哪怕是在酷夏。酷夏,气温达到四十度,人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汗如雨下。只好紧闭门窗,打开空调,躲在家里。可豆豆忽然不见了。床上,桌下,到处寻找,连个影子都没有。末了,在阳台上发现了她,正在晒太阳哩。在四十度的热浪中晒太阳,那么怡然自得。刚刚从梦中醒来,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也难以理解。这个傻孩子,把阳光当作了氧气。兴许,对于她,阳光就是氧气。
4
起风了,但我没注意,是门窗紧闭的缘故。门窗紧闭,便有了一片安宁。我就在安宁中读了一天书。
合上书,已是深夜。看到豆豆走过来,跃跃欲试,想要游戏。我一空闲,她就要游戏,总是这样的。玩打仗,她先进攻,摆出凶猛的样子,低吼着,用手撩拨我。不时,假装咬我一口。她懂得游戏的规则,并不真咬,只是轻轻含一下,象征性的,算是打败了我。然后,嘹亮地叫,不停地原地打转,以示助威,或算作庆功。末了,还得夸她:“豆豆厉害!豆豆真厉害!”听到我的夸奖后,她会摇晃起尾巴,满屋子跑,那么得意,那么骄傲,像个公主。
其实,她也就“窝里横”,一出门,就变了态度,从不让任何同类接近,也从不接近任何同类。一点不合群,只顾独自行走和奔跑。谁都不理不睬,甚至拒斥他人友好的表示。古怪的小东西,是孤傲?还是胆怯?兴许,两者都有。
5
豆豆,有一定的理解力。一些关键的词,她懂。比如吃饭,比如穿衣服,比如遛弯。每天都要带她出去遛弯。一到时间,她就开始期盼,开始观察,用她那双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你,只等着你说出那声:“咱们出去遛弯喽!”
这句话是她的节日。这句话让她激动。每每听到这句话,她会一下子扑到你面前,用小手拍打着你,欢快地摇动着尾巴,让你给她穿衣裳,系链子,再紧紧跟着你,看你穿衣裳,关电视,锁门。你动作稍稍慢点,她还会着急,汪汪叫,迫不及待的样子。这个小东西,一点耐心也没有。
她最喜欢河边了。那里干净,安静,通常没什么人,一块自由的天地。可以撒开腿疯跑,小鹿似地疯跑。豆豆昂起头,支棱着耳朵,奔跑的时刻,就是一只小鹿,风中的小鹿。跑到三十来米,便会及时转身,及时回到我的身边。有时,还会邀我一道跑,和我比赛,使出浑身的劲儿,非得跑到我的前头才肯罢休。这个小东西!
6
每次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时,准能听到豆豆的动静,她早就迎侯在门旁了。打开门,豆豆在摇曳,在舞动,在欢叫,真心欢迎我的归来。这是她的仪式,迎接仪式。这仪式每次都让我温暖。
然后,她就会引我来到她的小屋,在床上躺下,展开身子,也不怕走光,让我抚摩她,一遍又一遍,适宜地眯缝着眼,不时地舔舔我的手,以示友好和感激。我一停下,她就立即撩一下我的手,提醒我继续,总也没够。这个小东西,倒是挺会撒娇,也挺会享受的。
我要出门,她通常都会出来,同我告别,抓住我,不让我走,舍不得的样子,得反复和她讲道理,她才肯放手。“宝贝,乖乖待在家里,回来给你买好吃的。”我只会这么说。有时,她也会使使性子,就躺在沙发上,漠然地望着我,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搭理。又把她独自留在家里,显然她是生气了。
7
子夜,静的中央。想起昨夜的情形,禁不住笑。又聚在一道了,松风,山水,文颖,小唐,张遇,还有好几位新朋友。从南京,从苏州,从连云港,来到北京会聚。是惊喜引发的惊喜,又像约定带出的约定,让人欣悦。
喝了太多的酒,浑身的酒气,连豆豆都在用目光责怪我。对酒,她分外敏感和警惕,因为她也有过醉酒的经历。那是在海边,豆豆还像豆子般娇小,享受着我们的宠爱。好吃的东西几乎不断,酱牛肉,红烧排骨,滑溜鸡片,葱爆鸭丝,我们吃什么,她吃什么。完全平等的待遇,外交官的待遇。在喝的方面,也一模一样。我们喝可乐,也给她喝可乐。我们喝茶,也给她喝茶。我们喝橙汁,也给她喝橙汁。居然来者不拒,还喝得有滋有味,一个劲地摇晃着尾巴。
她会有什么不喝呢?我们纳闷。一回,在她的水盆里倒了点啤酒,纯粹是试探。豆豆照样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喝得一滴不剩,仿佛同自己干了一杯又一杯。抬起头,她先四下打量了一番,随后,忽然在地上打起了滚,耍赖似地打起了滚,拦都拦不住。嘴里还发出哼哼叽叽的响声,也不知想表达什么,或者仅仅是宣泄,满屋子都是她的动静。如此折腾了大概半个小时,显然是醉了。
好在她不贪杯。从此以后,一闻到酒,就会远远地躲避,晓得它的厉害。而且连可乐、橙汁、绿茶之类的饮品也顺带戒了,只喝水,清清爽爽的水。豆豆,起码比我自觉,呵呵。
8
豆豆乐了。我终于有空带她出去溜达溜达了。说是我遛她,其实,更多时候,是她在遛我。她不断变换着速度和方向,想停就停,想跑就跑,完全没有规律,完全随心所欲。她停,我也得停。她跑,我也得跑。仿佛停是为了跑,跑是为了停。不过,豆豆不自私。跑到前面时,她会回过头来,等我。我们常常来到河边。豆豆在黑海边长大,我来自南方,我们都喜欢水。有一回,在沙滩,前方有片白色在闪烁,在诱惑,她抵挡不住,冲了过去。我们赶紧把她拉了上来,湿漉漉的豆豆不知道那是海。
厨房:母亲的身影
厨房,总是让我想起母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母亲:“母亲属于那样一种类型的女人:总在不停地劳作,总得做点什么,一旦手中没活了,反而会感到别扭,会感到难受。忙碌成了她的一种天职,一种习惯,一种生存方式,甚至忙碌本身于她就是休息。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劳碌命吧。”
记忆中,母亲似乎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待着,忙忙碌碌,没完没了。那是她的岗位,是她的空间。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有母亲的身影,那片空间才能叫厨房,否则,它就不完整,就名不副实,就空荡荡的。
那片空间独立,但不大,也简陋,在天井的那一头,带屋檐的瓦房,砖砌灶台,水缸,煤炉,一张小桌子和两三个小凳子,就是它的全部了。那时还没有冰箱、微波炉之类的现代电器。灶台有两个灶眼,放着两个大铁锅。一个专门用来煮饭,另一个用来炖汤、做菜和炒菜。灶台里侧堆着高高的柴火,相对隐蔽。我们几个玩小把戏玩捉迷藏的时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躲进厨房,躲到柴火的后面。做饭时,架柴火极讲究,架得好,就能控制火候,并延长燃烧时间。母亲先要到里侧,蹲下身子,架柴火,点柴火,等火势稳定,锅热得差不多时,再站到灶台旁,做饭,炒菜,或热饭,热菜。然后,过几分钟,再到里侧侍弄柴火,如此反反复复好多回。真是里里外外忙个不停。
夏天闷热,待在厨房里,实在不是滋味,尤其在七八月份,简直可以说是煎熬。冬天,厨房却是个温暖的地方。我们都争抢着要为母亲侍弄柴火。望着炉膛里燃烧的火焰,闻着渐渐冒出的香味,冬天,于我们,甚至有了童话的色彩。捷克诗人霍朗在其诗作《雪》中这样写道:
子夜,下起了雪。此刻
厨房无疑是最好的去处,
哪怕是无眠者的厨房。
那里温暖,你可以做点吃的,喝点葡萄酒,
还可以透过窗口凝望你的朋友:永恒。
前几年,当我读到此诗时,心中涌起了一阵的亲切和温暖。厨房记忆,让我一下子贴近了霍朗的内心,也让我再次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物质贫困的年代。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好几个孩子,就是好几张嘴。吃饭,成了父母的头等大事和最高目标。那时,能吃饱,就不错了,我们压根儿不敢奢望吃好。
可母亲还是发挥出了她的全部才能,不但要让我们吃饱,还要让我们吃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物质有限,就得运用智慧和想象力了。母亲只要走进厨房,待上一两个钟头,就能魔术般,变出几道像模像样的菜来,真是神了。这让我对母亲佩服极了。每每闻到饭菜的香味,我都会坐不住,立马停止写作业,或玩游戏,悄悄溜进厨房,站到母亲的身边,看母亲做饭,很乖很专注的样子,带着小小的私心。母亲明白我的心事,不多一会儿,便会夹上一口菜,塞进我的嘴里。有时,看到母亲在厨房拾掇带鱼或鹅肠,我还会小声地建议:能红烧吗?母亲望望我,笑笑说:“那好吧。”不知怎的,儿时,我喜欢所有红烧的饭菜:红烧鸡块,红烧带鱼,红烧萝卜……只要红烧,就一准好吃,一准下饭。
都说,对于孩子,邻居家的饭菜总是更香,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我从小就喜欢母亲做的饭菜,坚定不移地喜欢。其实,母亲做的都是些地地道道的家常菜,用料都极普通的,可经过她的搭配和调制,味道就不一般了,就是好吃。用朋友荔红富有韵味的江南普通话叫“好吃得不得了”。
母亲注重实践,又善于琢磨,久而久之,在厨房研究出了自己的菜谱,饭店绝对没有的。比如,菠菜炒大肠,谁会想到用菠菜炒大肠呢?看似简单的菜,却要费上好几天的工夫。菠菜,用新鲜的,而大肠则要反复清洗,再放上各种佐料,加以煨制,然后还得风干一段时间。烹炒时,必须巧妙掌握油、盐、酱、醋和糖的比例。每回,母亲端上这道菜时,我们几个孩子总要欢呼的。
还有韭菜炒螺蛳肉,同样费工夫。这是家乡的特色菜,饭店里一般都有,可饭店里做的绝对比不上母亲做的。母亲先要搬上一只小凳子,坐在弄堂里,用针一颗一颗地挑出螺蛳肉,韭菜也要一遍又一遍地清洗。几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炒时特别讲究火候。末了,一定要放点胡椒粉,也许这就是诀窍。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下饭的菜了。
由于家境并不富裕,我们往往要等到过年,才能集中领略到母亲的最高手艺。红烧狮子头、蛋饺、慈姑烧鹅、油豆腐塞肉、百叶结烧肉、猪头糕,还有酱肉和酱鱼。那时,过年前,我们家乡,家家户户厨房的屋檐下都挂着无数的酱肉和酱鱼,真正鼓舞人心的旗帜。这些永远的家常菜啊!我们期盼着过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期盼母亲的饭菜。然而,过年也是母亲最最辛苦的时刻,一连五六天,母亲基本上都在灶台旁度过。别人在吃在喝在聊在玩,母亲却在忙碌。过年对于孩子是欢乐,对于母亲实在是重轭。但年还得过,而且还得快快乐乐地过,这是母亲朴素的念头。现在想想,真是内疚,我们当时怎么就不懂得心疼母亲呢!
也忘不了母亲做的野菜馄饨。用野菜、鸡蛋、豆腐干丁和鲜肉作馅,包得满满的,大大的。那么实实在在的馄饨,只有母亲才做得出来的。吃的时候,不能不放点白酱油和猪油。在南方,吃菜饭时,也得放猪油的。猪油,有一种说不出的香。记得我考上大学时,母亲把我的小朋友们都请到了家里,吃馄饨。邱悦,慧良,志刚,姜勇,益民,都来了。那天,母亲特别开心,一大早就进厨房,包了那么多馄饨,保证我们放开肚子吃。吃得我的小朋友们个个赞不绝口。母亲看着我们吃,禁不住笑。
常常,想到厨房,想到母亲做的饭菜,童年的所有美好感觉便溢满心头了。
如今,父亲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家乡的老房子还在,空着。只要回到家乡,我都要到老房子里,对着父母的遗像,磕上几个头,然后四处看看,摸摸,仿佛在寻觅着什么。那里有我的童年和少年。站在厨房里,总会恍惚看到母亲的身影,怎么也抹不去,母亲在望着我呢。我知道,那只是幻觉,厨房里再也没有母亲的身影了。那片空间,永远地空了,谁也无法将它填充,什么也无法将它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