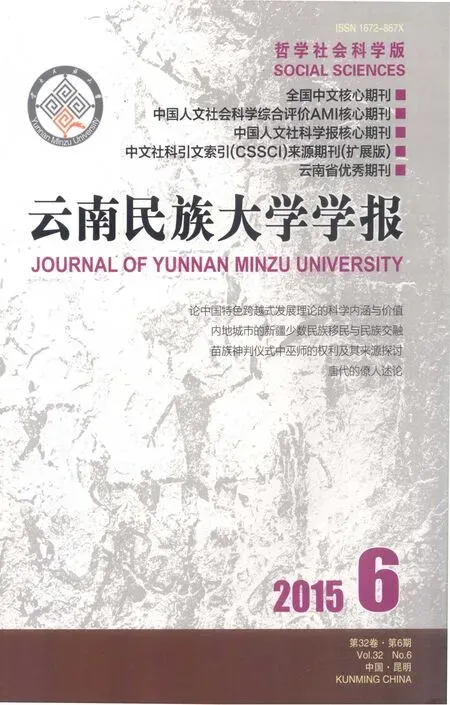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互助行为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影响研究
起建凌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201)
互助行为指的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帮助的行为,这些行为受人们的意识支配,不以明显的追逐利益为前提,行为的发生是自发性的,行为的结果是以满足他人利益或减少风险为目的,行为的发生在社区内是受正面评价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的传统和现代社会观念发生碰撞,村民的观念呈现裂变、融合的趋势,村民的市场意识越来越强,经济人的特点在村民身上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现代村民的行为和传统村民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传统的人口较少民族互助行为
人口较少民族村民间的互助行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怒族。居住在怒江大峡谷的怒族村民由于受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村民之间保留了较多的传统行为。
怒族是云南省特有的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贡山、福贡三县,第六次人口普查总人口为28759人,其中,男性14857人,女性13902人。此外怒江州的兰坪县和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维西县也有少数怒族居住。怒族自称“怒苏”、“阿怒”、“怒”、“阿龙”等。①《怒族简史》编写组:《怒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他们大多居住在怒江两岸海拔1500米至2000米的山腰台地,传统怒族居住的村落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大多数都是由家族血缘近亲所组成,这是传统怒族村落组成的特点,这种居住形式一般人口规模较少,多则50多户,少则10多户。另一种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 (主要是傈僳族),人口较多。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社会流动人口加大,也有少量其他民族人口到怒族村寨居住,所以,目前的怒族居住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由于怒族族源形成历史差别较大,且居住地怒江两岸尽皆高山深谷,交通极为不便,山川阻隔,怒族各支系之间语言差别较大,没有本民族文字,不但词语不同,语法结构也不一样,彼此之间不能通话。1950年以前,除少数居住于兰坪、维西等地的怒族进入封建社会以外,大多数怒族还保持着原始社会的一些特征。
(一)怒族的共耕制度。
怒族传统生产力水平较低,且受交通、语言、婚姻制度影响,其内部生产、生活关系较为密切,新中国成立前还保持有原始土地公有制度,主要包括村寨公有、氏族公有和家族公有。这三种土地公有方式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土地公有管理的松散及人口规模的扩大,土地逐步变为私有。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土地逐步私有化后,又形成了伙有共耕制度,伙有共耕制度包括氏族公有土地共耕、家族伙有土地共耕、开荒伙有土地共耕、共同买到伙有土地共耕、姻亲伙有土地共耕等,这些共耕形式采用的是村民共同所有,共同耕作、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一种生产形式。共耕产生的原因,一方面受到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村民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个体村民很难胜任农业生产活动,通过集体活动就较好地解决个体村民无法完成的一些工作。
(二)怒族的互助制度。
随着私有化的发展,怒族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为更好的适应社会,应对复杂的生产、生活环境逐步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互助行为。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传统互助形式:
1.借地。①《怒族简史》编写组:《怒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缺地或少地的村民可以向有地的村民请求借给少量耕地耕种。借地规模在一亩以上的可通过送礼的方式来代替租金,礼物一般是一头小猪或者2只簸箕。如果是一亩以下的,可以不用送礼,与土地所有者共耕。送礼一般是在秋收以后,且一般是在村寨内部进行。
2.助耕。村寨中富裕村民根据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数,事先通知亲友或者本村寨成员参加帮助进行春耕或者秋收,一般人数不超过20人,时间1~2天,不付劳动报酬,只是提供助耕者每天一顿酒饭。
3.换工。贫穷的村民无力招待酒饭,就采取换工的形式,相互以等量劳动日来抵消。
4.共养家畜。贫穷村民由于无力单独饲养牛、羊、猪等牲畜,就采取几户共养的形式,饲料由大家共同承担,由其中一户饲养,宰杀时饲养户可以多分一个头,剩下的肉平均分配。如果是销售,获得的收益,饲养户可以多分一份,其余的均分。
5.租养家畜。没有能力购买幼畜的农户从其他的农户家租借小家畜进行饲养,等到家畜长大后,不管是宰杀还是出售,双方对半分配。
6.借牲畜。村民家庭因为疾病、丧葬缺乏祭品时,可以向亲友借猪或鸡作为祭品,一般半年到一年归还,归还时不需附加任何报酬。
7.要粮。贫穷农户在缺乏粮食、种子的时候,可以向本家族成员“要粮”。要粮者只需送给对方一只小鸡或者一碗水酒,就可以得到数量不少于一个人10天的粮食,而且不需要归还。
8.协作建房。房主把建房材料准备好,约定时间邀请本村寨男子前来帮忙,凡被邀请者都要携带一捆茅草或木料赠送房主,房屋修建完毕,由主人招待酒饭,不需要付报酬。
在生产力不发达背景下的传统社会,怒族的互助行为更多的是以血缘或氏族为纽带而进行的一种合作行为,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村民有三种作用:一是通过共同劳动,以利益分配的形式加深亲缘之间的连结;二是通过合作的关系,对稀缺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进行统一调配,提高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是通过协作或者合作关系比单干劳动具有较为明显的生产优势,解决在生产力水平低背景下,个体或者单个家庭无法解决的生产问题或降低生产、生活风险。
二、现代人口较少民族的互助特点及模式
(一)现代人口较少民族互助行为特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怒族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实施以后,怒族的生产、生活互助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受传统互助思想的影响,怒族互助行为与其他民族相比还保留一些特色鲜明的互助行为。
据2011~2012年间对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兰坪县,德宏州芒市、陇川县,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海县进行了实地调研,以入户访谈和问卷的形式重点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程度比较高的乡镇如匹河怒族乡、独龙江乡、三台山德昂族乡、布朗山乡、户撒阿昌族乡等乡镇进行入户调查,发放问卷650份,回收有效问卷581份,有效问卷中男性421人,女性160人,年龄最大83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44岁。通过调查发现,人口较少民族现有的互助行为有如下特点:
1.通过物资互助来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遇到人生礼仪中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重大事项时,乡邻和亲友都会主动送来钱财和食物,利用全村的力量来帮助操办由某一家单独难以完成的事情;怒族婚礼前,全村寨的各家各户壮年男子或女子,都主动到男方家帮助料理结婚的有关事务。结婚当天,男、女双方亲戚、朋友以及同一个村寨村民都会主动来帮忙,有的村民会送上现金作为贺礼,有的村民会采用传统方式背上一块猪肉、一些米、蔬菜和一捆柴火作为贺礼。怒族的婚礼是歌舞的盛会,青年人弹奏起琵琶调,吹起口弦曲,跳起琵琶舞和锅庄舞,尽情欢歌。老年人边向新婚夫妇祝福,边唱《婚礼歌》,一派喜悦之情溢满庭院。
2.通过劳动互助来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其他的互助行为还包括修缮旧居或新建住屋时,怒族全村的人和其他村寨的亲朋好友都要来协助修建,出工出力,壮劳力一起到山上砍伐木材等建筑材料来帮忙建设。
3.互助行为与交际行为相交织。怒族群众之间对于村寨及亲朋好友发生的情况都关注度较高,参与的积极性与自觉性都比较强。一方面是因为怒族群众生存条件恶劣、物资匮乏,需要相互支持,共同抵御生活、生产风险。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是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匮乏,怒族群众可以通过聚在一起,共同劳动,载歌载舞、喝酒吃肉、交流谈心,以这样的形式形成紧密的人际网络,村民利用这个网络获得各种信息和感情交流,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
(二)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现有社会互助模式。
1.大家庭互助保障模式。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在面对生产、生活困难的时,有着相似的互助行为,这种互助模式在云南部分普米族、景颇族、德昂族、布朗族、基诺族皆存在。如,由一对夫妇的几代后裔共同居住在一个大家庭内,以家庭为纽带,由家庭人数优势来应对生活、生产风险,传统的大家庭互助模式成员一般包括一对夫妇的三代或者四代后裔,包括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媳妇,女儿、女婿、外孙女、外孙女婿等家庭成员。在这种家庭中已婚子女又组成多个小家庭。大家庭的公共财产由大家庭的家长统一管理,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共同享有。这样的传统大家庭规模达40人,规模大的甚至超过100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大家庭的模式在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依然保有痕迹。在怒江州独龙江乡、匹河乡调查期间,其中一户独龙族家庭规模达到15人,三代同堂,儿子均已经成家,三个儿子娶了三姊妹,全家所有人居住在一个大家庭里,共同劳动、共同生活、集体分工,所有的土地、林地、家禽、牲畜共同管理,所有财产共同分享。通过这种大家庭生活模式既降低了生产、生活成本,又提高了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尤其重要的是在面对生产、生活风险时,这样的大家庭也比小家庭模式更能抵御风险。
2.村寨互助模式。人口较少民族多居住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山区,形成了封闭而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这种封闭的环境导致居住在一起的群众相互凝聚力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共济互助关系友好。这种互助行为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有一定的差别,但内容基本一致。一般来说,越是边远封闭、交通不便的村寨其凝聚力也就越强,传统的互助行为就越多。当村寨中或周边村寨与自己沾亲带故的人、家庭出现重大事项或者出现重大变故时,如生病住院、结婚、死亡、盖房子等时,全村寨的人以及周边的亲戚朋友都会出钱、出物、出力来给予帮助,不去的人会受到村里人的排挤与歧视。并且这些帮助会约定俗成形成一定标准,这个互助标准会根据帮助人的经济实力、与被帮助人的关系有所不同,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变化。2011年6月,在怒江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调查发现,村子里有人生病住院,村里人都会去探望,在国家没有发放低保前,由于手里没有现金,一般是准备一块肉和一些蔬菜前去探望。农村低保制度实施后,村民一般准备20元左右的现金前去慰问。在访谈中村民认为带食物去的话,看望的人多,被看望的家庭不好处理这么多食物,而现金的话可以帮助生病住院家庭适当减轻经济负担。如果遇到婚丧、嫁娶或是盖房子这类大事,村民还是会带着食物或者现金去帮忙。
这种互助行为虽然可以帮助村民集群体的力量抵御个人生活风险,但是对于农村低保户来说无形当中增加人情往来的次数,加大了经济负担。
3.宗教组织互助模式。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地处边远,受汉文化影响相对较少,由于历史原因,十九世纪国外的宗教势力开始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进行宗教活动,所以基督教、佛教以及一些本土宗教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有较强的影响力。在当地出现灾害或者群众出现重大困难时,这些宗教组织都会通过宗教活动帮助他们。这是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适应社会变化的一种表象,也是宗教势力扩大影响的一种手段。
4.互助形式以劳动、实物与现金帮助为主。在调查问卷中,当问到别人有困难你一般采用什么形式帮助时 (多选),46.99%的调查者通过劳动力进行帮助,占34.08%的采用实物形式进行帮助,占32.36%的通过现金进行帮助。这些数据说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受互助传统的影响,通过村民间实物帮助所占的比例与内地汉族地区相比还是比较高的。
三、人口较少民族互助行为与对农村低保制度的影响
(一)村民互助行为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救助作用明显。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是典型乡土社会,人们通过紧密的人际关系形成一些约定俗成、自觉互助行为,这些行为帮助大家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遇到生活风险的时候,由周围的人来共同分担,以最大程度减小风险造成的伤害。在问卷调查中,当被问及没有农村低保前,生活遇到困难怎么办时,由亲戚朋友帮助占63.86%,村里 (村集体)机构组织帮助占8.6%,政府救济占3.79%,其他形式的占23.75%,由此可见,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对于贫困人口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二)互助行为与农村低保制度相辅相成。人口较少民族的互助行为可以整合村民中有限的资源,积少成多,发挥整合放大的作用。正如麦克奈特的观点“专业人士和国家机构提供服务,社区解决实际问题。”农村低保制度为贫困村民提供稳定的生活保障。而互助行为能够发挥近距离的优势,及时的解决村民的贫困问题,为贫困人口提供低保制度不能提供的精神慰藉。
(三)互助行为能丰富社会救助的形式与层次,减少贫困人口对低保制度的依赖性。现有的农村低保制度强调的是事后补偿,对于村民的贫困现象难以进行提前防范,重在指标而难以治本。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统的互助行为能够提供国家实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所不能提供的精神慰籍,有利于贫困人口生存技能的学习和致富能力的提高。通过互助行为形成了紧密互助性高的人际关系网,在进行互助行为的同时,往往还能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交换打工的信息;提供在当地有效的致富信息;通过共同劳动交流生产技能;一起从事农村经营活动,共同应对农村经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这些互助形式,是典型的“授之以渔”的模式,较好的解决了贫困人口“造血”能力不足的问题。
(四)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保障水平,降低宗教对贫困人口的影响。人口较少民族的互助行为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的限制,可供支配的资源有限,保障水平不高,无法应对整体风险和较大的灾害。由于村民的流动性加大,以紧密互动的人均关系网形成的传统社区功能逐渐弱化,分摊模式的互助行为逐渐被淡化,现有的农村低保制度由于有国家的相关制度和资金作为保障,可以充分弥补传统互助行为的不足。另外,农村低保制度有着覆盖面广,保障水平相对较高,涉及面大,影响力深的特点,有利于通过低保制度的实施来降低宗教团体对贫困人口的影响,体现党中央、各级政府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关心和重视,强化党和政府在人口较少民族心中的影响力,号召力。
四、弘扬人口较少民族互助行为促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完善的建议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经济发展了,政府才有经济实力提供给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高水平的生活保障,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才是有源之水,才能在解决自身困难的同时去帮助别人。无论从国内外的经验,还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传统来看,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众多,家庭数量庞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决定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家庭和社区作为民族地区的基本单元,对其成员的利益和责任的承担负有最直接的保障作用。因此,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村民之间的互助传统行为决不能在现有的农村低保制度体系中被忽视。应充分发挥传统互助行为的作用,对于贫困人口而言,这种救助行为不仅成本低、效率高、服务快捷和全面,最重要的是更加常态化和人性化,对具体的困难提供的解决方案更加具有针对性。弥补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法覆盖的各种生活领域中的不足,特别是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缺失。
(一)大力弘扬与鼓励传统互助行为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我国有着悠久的尊老爱幼、互助互帮的优良传统,我国的部分法律法规也对社区、邻里、街坊互助的义务提出了要求,在现有条件下,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难以满足村民对社会保障需求。传统的互助行为在一定时期内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农村互助行为依然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级政府应合理引导和扶持互助行为,让其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家庭和社区互助为辅助。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家庭和社区的生活保障功能依然是农村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可靠基础,农村家庭和社区是建立在一夫一妻制度之上的社会单元和利益体,对于村民所面临的生活风险应该首先考虑由家庭和社区来帮助应对,当家庭和社区无力应对风险时,政府及时介入,由政府最后承担责任,帮助贫困人口解决困难。
(三)农村低保制度的完善与村民互助行为的发展息息相关。农村低保制度是由地方政府制定的用于解决贫困人口生存困难的救助制度,在现有的救助制度中,只能基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其他问题无法解决也无力解决。而村民的互助行为能够发挥社区中生活护理、文化娱乐、应急服务等功能,弥补农村低保制度对于贫困农民精神慰藉不足的问题,能够使救助对象在心里上获得心里认同,增加归属感、参与感。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人际关系紧密的社区逐渐开始衰落,由亲缘、血缘关系形成邻里关系将会逐渐淡化的背景下,要以构建和谐社会和团结稳定的边疆地区为契机,通过弘扬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村民互助行为,充分发挥农村能人的影响力、号召力,依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形成具有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有特色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农村保障体系,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制度效果。不仅有利于强化边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同时还可把边疆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建成社会和谐、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