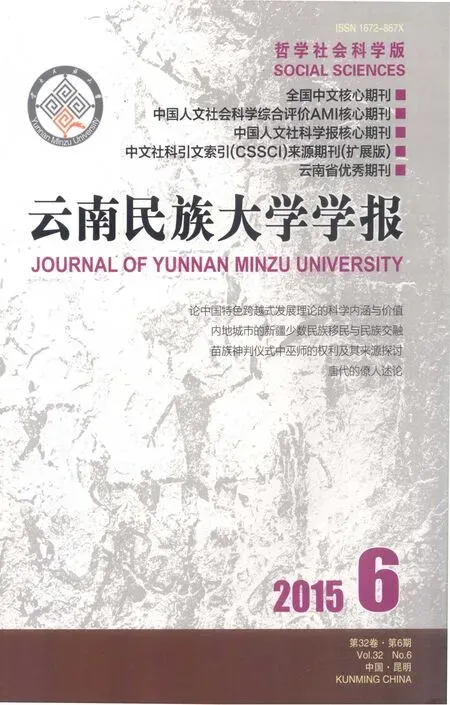近20年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杨永福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关于“西南边疆”一词,在不同的论著中,其空间界定并不一致。本文中的西南边疆,主要指涉今天的云南、广西、贵州和川西南地区。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明清之际是贵州民族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①李耀申:《试论明清之际的贵州民族社会变革》,《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事实上,明清之际同样是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从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清代无疑要超过明代,是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变革最为明显的时期。导致发生剧烈变革的原因除改土归流与国家权力的强力渗透、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持续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及其影响外,还有清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的文教政策及其作用与影响。因此,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关于清朝的文教政策及其教育活动,近年来研究较多。但关于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的研究,似还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本文尝试对20年来国内学界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要梳理,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设想,并求教于方家批评指正。
一、研究状况的回顾
对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及相关的研究,据笔者所知,已有很多学者关注,并进行研究。②如长江师范学院李良品教授主持的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史研究”(批准文号05XMZ046),云南民族大学顾霞博士主持的云南省社科基金一般规划项目“明代书院与边疆文化传播研究”,文山学院田景春副教授主持的云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明清时期云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等。至于具体的研究成果,下面分别论述。
(一)整体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研究逐渐发展为中国边疆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对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研究亦有很大进展,从历代民族政策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重要者如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均从通史的视角对历代封建皇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的政策作了宏观研究,教育政策被视为治理举措之一,但限于篇幅,论述不多。具体到清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等著作有较深入的考察。其中部分内容在论及清代治理开发西南边疆时,指出教育政策的运用及其效果,然限于体例、篇幅,上述成果难以深入研究。③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龚荫:《中国民族政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何耀华总主编《云南通史》(第四卷)、《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三卷)、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一卷)、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第五卷)等分省区通史,也有涉及清代教育的内容,但篇幅均较有限。①何耀华总主编:《云南通史》(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贵州通史》编委会编:《贵州通史》(第三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第五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分省对古代教育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如: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第四章“清代前中期贵州教育的全面发展”,简要介绍了清代前中期贵州学校教育、民族教育以及书院、私学、科举制度等各类教育形态和教育现象发展的基本情形。局限于体例,清代贵州教育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不多。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第三章对清代贵州各种教育活动作了简要的叙述。刘光智著《云南教育简史》对两汉至民国时期云南教育发展的历史作了简要的叙述,其中第二章“元明清三代的云南教育”对清代云南的学校教育有叙述,但极为简略。蔡寿福、陶天麟主编《云南教育史》关于清代云南教育发展的内容同样较为简略。杨益新、梁精华、赵纯心编著《广西教育史》亦大致同上。②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刘光智:《云南教育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蔡寿福、陶天麟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杨益新、梁精华、赵纯心编著:《广西教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在专题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
余梓东的《论清朝少数民族教育政策》③余梓东:《论清朝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清朝政府突破了“华夷之辨”的局限,制订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在实施中予以倾斜,使之在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清朝统治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清朝的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涉及不多。
胡绍华《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④胡绍华:《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一文,首先简要考察了清朝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文教为先”政策的由来,其次重点阐述了该政策的具体措施,即提倡强制土司子弟及土民入学学习,广设义学、社学和新学,设立儒学、府州县学和书院,开科举之门、培养人才。在此基础上,对清朝“文教为先”政策进行了评价,认为客观上对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王美芳的硕士论文《文教遐宣—清朝西南地区文教措施研究》⑤王美芳:《文教遐宣—清朝西南地区文教措施研究》,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对清朝在西南地区实施的文化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使用的文献资料多为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但该文主要偏重于对清代西南地区的义学教育及其影响的考察研究。
徐彩霞《清代文教政策述评》⑥徐彩霞:《清代文教政策述评》,《文学艺术》2012年第10期。认为清代文教政策包括崇儒重道、提倡程朱理学、严格制定学规、笼络利用汉族文人、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以科举调控学校、提高官学地位,调控非官办学校等内容。但篇幅、内容较为简略。
针对清朝在某一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的论著较少,如程印学的《清王朝对傣族地区的文教政策评析》⑦程印学:《清王朝对傣族地区的文教政策评析》,《商丘师院学报》2006年第12期。分两个阶段对清代傣族地区实行的文教政策进行了简要的考察,认为清前期傣族地区的文教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入学习礼作为土司承袭的必要条件、积极设立和倡建义学,清末新政后,清廷继续加强在傣族地区的文教政策,如设立土民学塾。这些措施,对于发展傣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促进傣族社会进步和巩固国防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官学教育研究
这里说的官学教育是相对的。因为在清代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除了府州县学以外,书院、义学、社学也得到官府的大力支持。从办学指导思想上看,它们都要服从于清廷的统治要求和治边方略。从这个意义而言,上述学校均视为官学亦无不可;但为了区别或是突出义学、书院研究的情形,这里的官学主要指府、州、县学,习惯上也称儒学。
古永继《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⑧古永继:《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分两个阶段对清代云南官学教育 (前期的儒学、书院、义学,后期的新式学校)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梳理,肯定了其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并总结出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三个特点:一是与内地相比迟缓落后,与自己过去相比则发展迅速;二是社学不复存在,义学取代社学;三是重视民族教育,促进民族地区人才培养。
顾霞、顾胜华的《清代滇东北地区的学校教育》①顾霞、顾胜华:《清代滇东北地区的学校教育》,《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2期。对清代滇东北地区的学校教育,主要是书院、义学的开办情况作了简要的考察,并梳理了这一地区人才培养的政策和模式,认为学校教育的兴办,减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异质性,提高了地区民族的文化认同度,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赵美仙的《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儒学教育及其影响》②赵美仙:《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儒学教育及其影响》,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对明清时期大理地区官学、书院等构成的儒学教育,兴办、发展的历史背景,儒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发展概况,以及对大理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的的推动作用等问题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
张羽琼的《论清代前期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③张羽琼:《论清代前期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认为,贵州民族教育在清代前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体现在各级学校数量的增多,在学生员和科考录取名额的逐步增加,特别是新辟苗疆地区义学的陆续兴办,反映了贵州民族教育的成绩。之所以得到较大发展,原因有朝廷和地方官员的重视,改土归流的善后需要,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等方面。
(三)义学与社学研究
近年来,关于清代在西南民族地区大规模开办义学,一些学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首先,是一批学位论文专门针对清代西南地区义学而展开研究。于晓燕硕士论文《清代边疆民族地区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云南义学研究》④于晓燕:《清代边疆民族地区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云南义学研究》,云南大学,2005年。对清代云南义学创设的历史背景、时空分布特点、管理运行制度、义学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后来,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研究》⑤于晓燕:《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该书立足于清朝档案和地方志书,视野宽广,以明清时期国家对南方民族地区治理进一步深入、控制不断强化为背景,考察了清代南方七省民族地区开办义学的基本情况,认为大量开办义学是清朝治理南方民族地区政策的重大调整,适应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并形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该书是近年来研究清代南方民族教育尤其是义学教育较重要的著作。
蒲晓的《清代云南义学研究》⑥蒲晓:《清代云南义学研究》,云南大学,2011年。在研究梳理清代云南义学发展概况、特点的基础上,考察了义学与书院的联系与区别,从资金筹集、教学管理两个方面对云南与山东两地的义学进行比较,最后考察清代云南义学的影响。
许庆如《清代贵州义学的时空分布研究》⑦许庆:《清代贵州义学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在考察清代贵州义学设立的历史背景之后,对贵州各地义学建置沿革逐一列表明示,并对贵州义学时空分布特点作了简要分析。认为贵州是清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义学的典型省份,和其它省份一样,其义学的大量设立体现了清廷注重边疆民族教化,力图通过文教上的宣扬王化来达到政治上的有效管理与控制。毛信元《清代贵州榕江地区义学政策实施情况研究》⑧毛信元:《清代贵州榕江地区义学政策实施情况研究》,西南大学,2008年。从教育史学科视野对清代榕江地区义学政策进行研究,内容包括清代贵州榕江地区义学政策的实施背景、义学政策的实施情况、官府的义学政策在榕江产生的影响,并以榕江为个案对清代义学政策进行反思。
在所见公开发表的专题论文中,对清代贵州义学的研究较多。顾龙先《“苗疆义学”历史考察》⑨顾龙先:《“苗疆义学”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对包括贵州苗族地区在内的“苗疆义学”的设置情况、发展迅速的原因和发展阶段以及苗疆义学的历史作用等问题作了简要考察,认为贵州的民族教育就是滥觞于清代的苗疆义学,苗疆义学开创了贵州民族教育的先河。
蒋立松《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学、义学发展述略》⑩蒋立松:《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学、义学发展述略》,《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在对贵州社学、义学创办、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考察后,认为清政府在贵州设立社学、倡办义学,有着特定历史背景,并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社学、义学在贵州民族地区的兴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羽琼《论清代贵州义学的发展》①张羽琼:《论清代贵州义学的发展》,《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认为清代贵州义学最早创办于康熙二年,此后经历了创立、进一步发展到蓬勃发展、陷入低谷又走向发展这样四个阶段,并呈现出发展缓慢、起伏较大,以教化少数民族子弟为主,创办容易、坚持困难等特点,因此作为初级官学教育组织的义学,在提高贵州各族人民整体文化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
宋荣凯《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义学试探》②宋荣凯:《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义学试探》,《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论清代贵州义学教育的创建、办学性质及功效》③宋荣凯:《论清代贵州义学教育的创建、办学性质及功效》,《怀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两文,前者简要探讨了清代贵州民族地区义学兴办、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后者主要考察贵州义学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官员的作用,并对义学的办学性质、教育功效进行了讨论,认为清代贵州义学教育属于官办,是清代官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在民族地区开办的基础教育,在教育普及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其效果远胜过前代。
许庆如《清代贵州义学经费来源探析》④许庆如:《清代贵州义学经费来源探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认为义学的生存状况与经费来源直接相关。作者主要考察了清代贵州义学的经费来源情形,指出贵州义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官方出资和民间捐资,并具有多样化、从官方到民间的演变趋势、民族性特色鲜明的特点。
黄廷安《清代黔东民族地区义学教育发展简论》⑤黄廷安:《清代黔东民族地区义学教育发展简论》,《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黄亦君《清代贵州思南府义学研究》⑥黄亦君:《清代贵州思南府义学研究》,《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两文,分别对清代黔东民族地区和思南府的义学教育发展的原因背景、义学教育特点、义学办学经费、教学管理以及义学的作用等进行了简要研究。
李良品《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义学教育研究》⑦李良品:《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义学教育研究》,《教育评论》2008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义学发展的原因,其次总结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义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义学的管理、义学教育的作用进行了考察。
可以看出,对清代贵州义学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几个取向:一是立足于全省地域空间的宏观探讨,二是对具体地区义学办学情况的研究有扩大之势,且主要集中于乌江流域、黔东苗疆等有特点的地区。
对清代云南义学的研究亦有较大进展。李可《清代云南“义学”初探》⑧李可:《清代云南“义学”初探》,《昆明师专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是较早的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初探》⑨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初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7年第3期。、《试论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⑩于晓燕:《试论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 《清代滇黔义学比较》⑪于晓燕:《清代滇黔义学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8年第1期。,陆韧、于晓燕《试论清代官办义学的性质与地域特点》⑫陆韧、于晓燕:《试论清代官办义学的性质与地域特点》,《历史地理》(第22辑),第277~287页。等文,主要关注的是清代云南、南方民族地区义学的发展背景、经费来源、教学管理以及义学的性质特点,并对清代云南、贵州两省义学进行了较深入的比较。
清中前期,社学在西南边疆地区曾较为广泛存在。张羽琼《论清代贵州社学的发展与衰亡》⑬张羽琼:《论清代贵州社学的发展与衰亡》,《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对清代贵州社学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之后指出,顺康雍时期是贵州社学初步发展阶段,乾隆初年贵州社学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在乾隆十六年后,清政府便采取种种措施限制贵州社学的发展,社学在贵州走向衰亡。
(四)书院教育研究
西南边疆书院教育至明清之际始进入一个较为兴盛的时期,故不论是发展的速度,还是发展的水平,整体均落后于内地发达地区。从全国范围来看,关于明清书院教育及其社会功能,学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内地文化教育发达省份书院教育的研究。对西南边疆书院教育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是分区域的研究成果。
关于清代云南书院教育的研究,可见郑升等《近三十年云南书院、文学综述与展望》①郑升等:《近三十年云南书院、文学综述与展望》,《长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李天凤《明清云南书院发展述略》②李天凤:《明清云南书院发展述略》,《教育评论》2003年第2期。两文。专题论文较少,如李庭辉《思茅明清书院研究》③李庭辉:《思茅明清书院研究》,《思茅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张黎明《明清建水书院及其文化价值》④张黎明:《明清建水书院及文化价值》,《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则对今普洱、建水两地区明清书院教育进行了研究。
关于清代贵州书院教育的成果甚少。或许是因为王阳明于明中后期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在这里授徒讲学,对明代贵州书院教育影响很大的缘故,因此关于明代的书院教育有部分研究成果,如张羽琼的《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⑤张羽琼:《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等。
(五)其他相关研究
清代的教育与科举选拔密切相关,因此,一般将科举制度视为国家文教政策的一部分。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主要是宏观的视角。这是因为清朝的科举制度 (如考试内容、考场要求、录取程序等),在全国范围内是统一要求的,并没有因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而有变通;但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执行,还是有所区别的,比如实行分省取士的做法,就对西南边疆各省有所照顾或优惠。夏卫东的《论清代分省取士制》⑥夏卫东:《论清代分省取士制》,《史林》2002年第3期。、李润强的《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⑦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均对此有论述。
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士人群体的扩大即是表现之一。杨斌《清代贵州人才的地域分布》⑧杨斌:《清代贵州人才的地域分布》,《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2期。、古永继《明清时期云南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思考》⑨古永继:《明清时期云南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思考》,《云南学术探索》1993年第2期。、侯峰、罗朝新《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⑩侯峰、罗朝新:《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学术探索》2002年第1期。等文对这一时期贵州、云南士人群体的地理分布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清代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兴办教育,促进了中原内地儒学文化的传播。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滇川黔彝区儒学的传播和影响》⑪潘先林、潘先银:《“改土归流”以来滇川黔彝区儒学的传播和影响》,《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一文,对明清时期滇川黔交界彝族地区办学情形、儒学对彝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生活的普遍变化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认为儒学的传播,不仅影响了彝族上层的思想行为,而且深入地影响着彝族下层民众的生活方式,从改汉姓、说汉语,到岁时节日的变迁。
唐建荣《儒学在贵州民族地区古代社会的传播与影响》⑫唐建荣:《儒学在贵州民族地区古代社会的传播与影响》,《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简要考察了两汉至清代儒学在多民族的贵州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历程,指出儒学的传播对贵州各民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王红光《清代贵州民族文化变迁的思考》⑬王红光:《清代贵州民族文化变迁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认为贵州民族文化在物质生活方式、生活情况、生活礼俗、精神生活、节日生活、社会组织、集市与交换、学校与教育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迁。导致变迁的三个基本因素是自然选择、政策影响、文化互动。
二、既往研究的不足
由前述可知,迄今为止,关于清朝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及其相关的研究,存在着以下不足。
第一,整体性研究不足。在前面涉及的课题以及论著成果中,很少将清朝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据笔者粗略查新,仅有胡绍华《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⑭胡绍华:《清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王美芳的《文教遐宣—清朝西南地区文教措施研究》①王美芳:《文教遐宣—清朝西南地区文教措施研究》,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徐彩霞《清代文教政策述评》②徐彩霞:《清代文教政策述评》,《文学艺术》2012年第10期。等数篇论著,从整体观的视角来考察清代西南或南方民族地区的文教政策;于晓燕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相关专题论文,对清代在云南、南方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有相当的考察和梳理,而更多的成果是专门对某一类学校展开研究,如官学教育、书院教育,或者义学教育。换句话说,对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及其相关内容的整体性研究是不够的。
第二,从研究的地理空间看。除了部分成果如于晓燕、王美芳的著作以及少数专题论文立足于西南地区的视野外,《贵州古代教育史》《云南教育史》《广西教育史》等著作是分省性的研究,大部分专题论文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省份或下属区域,比如云南滇东北、贵州苗疆、乌江流域等教育活动的考察,而且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两省,而对川西南、广西等地的研究似不多见。
第三,研究不平衡。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研究空间地域不平衡。在前举研究成果中,对清代贵州教育活动的研究较为丰富,而且体现出全省性和区域性两个指向。在区域性研究中,又以考察苗疆地区的义学教育的成果为最。其次,对清代云南地区的教育活动的研究亦较为可观,但对次区域的教育活动的研究较少。对川西南和广西地区教育政策及其活动,研究就很少了。二是对各类学校的研究不平衡。清代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大力实施教育政策,开办了官学、书院、义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涵盖了启蒙教育、初等教育、科举应试教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但从研究状况看,主要集中在关于义学的研究方面,而对其他学校教育的研究还较少。
第四,对具体教育活动如义学的原因背景、内容性质、作用影响等关注较多,而延伸性研究,即将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置于全国性的大背景下,将其与清廷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其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措施等联系起来,从文化治边的战略高度去研究,并深刻揭示民族教育政策与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显然做得还很不够。
第五,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上,主要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教育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多学科交叉的趋势,且个案研究较多,但比较研究不足。
三、对今后研究之思考
清代200余年 (主要是在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发生了显著变革。清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举措,清廷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中原儒家文化在西南边疆得到更加深入的传播,边疆与内地一体格局发展的历史趋势愈加明显。可以说,清朝统治时期,是近现代西南边疆民族关系、民族地理分布格局逐渐确定下来,近代中国西南部疆域最终形成的时期。这些,与清朝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因此,对之深入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针对以往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笔者以为,今后的研究应重视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加强整体性的研究。由于西南边疆地区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民族众多,历史上滇、黔、桂及川西南地区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因此在清代,这里是土司制度最为集中的地区。从部分研究成果得出的初步结论来看,清廷对西南边疆的各项政策基本具有同一性。因此,将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是可行的。运用边疆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教育史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清朝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或许能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揭示在当时全国社会大背景下,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的特点 (边疆性、民族性),分析探究这一政策与边疆民族社会互动促进的基本内涵,较为清晰地把握清初期、中期到晚期西南边疆民族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其次,注重区域研究的平衡性。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在加强整体性研究的同时,亦需要开展区域性研究。一是加强省一级空间范围内清代民族教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形的研究。因为在当时,很多教育措施,包括各类教育机构的设置、在学生员和科考名额的规定、教育管理和经费来源等,都是在某一行省范围内确定实施的。因此,以省级行政区为研究空间,考察清朝民族教育政策的落地情形、运行状况、影响作用,应是比较确定可信的。而从当时的情形看,各省民族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形并不平衡,如云南与贵州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各省民族教育政策及实施情况的研究。二是需要重视对当时省级以下区域或者某一民族聚居区域教育政策及其作用的研究。从清代西南边疆各地区民族教育政策实施的情况看,国家层面的政策要求是统一的,但具体到西南各地,由于自然环境、人文社会背景不同,因此在政策的执行上存在局部的差别或不平衡;各地的民族亦不相同,各民族聚居地区的教育实施情形亦有较大差异,因此,开展对彝族地区、壮族地区、傣族地区、贵州苗疆等此类地区教育政策、活动、影响等研究,一方面体现当前学界空间区域化、内容精细化之研究趋势,同时亦有利于对西南边疆民族在明清大变革之际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入考察。
复次,在研究内容方面,注重系统性研究,更加重视民族教育的影响与作用的考察。仔细审察既往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基本涉及了当时西南边疆的所有教育政策及教育活动,而学者关注的重点亦非常突出,一是对义学的关注较为集中。前面所述及的论著相当部分是对义学的研究,涉及开办义学的背景、性质、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经费来源、影响和作用等问题。二是国家层面在西南边疆的政策措施。除此而外,关注点就比较分散了。鉴于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似应重视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如清代西南边疆官学教育、清代西南边疆义学教育、清代西南边疆书院教育、清代西南边疆士人群体、清代西南边疆科考优惠与防弊等,同时应前后延伸、左右拓展,进一步深入探究国家教育政策、边疆教育活动对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变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变化、西南边疆稳定等的影响。
第四,在继续加强个案研究的同时,注意比较研究。以往的研究成果,采用个案历时性研究方法较多,如于晓燕的《清代滇黔义学比较》①于晓燕:《清代滇黔义学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8年第1期。等采用比较研究的成果就极少。今后要进一步推进清朝西南边疆民族教育政策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似应更多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原因有二:一是西南边疆各地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民族众多、人文社会背景差距甚大,这就难免影响到政策的实施及效果、作用,因此对不同区域尤其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教育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更能揭示其时序发展曲线和空间分布差异的特点;二是当个案研究进行到一定时候,必须进行比较研究,方能发现在国家层面政策同一性要求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应对的局部差异,从而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总之,清朝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的研究,在西南边疆治理史、西南边疆民族史等领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迄今为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信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有更多高质量的成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