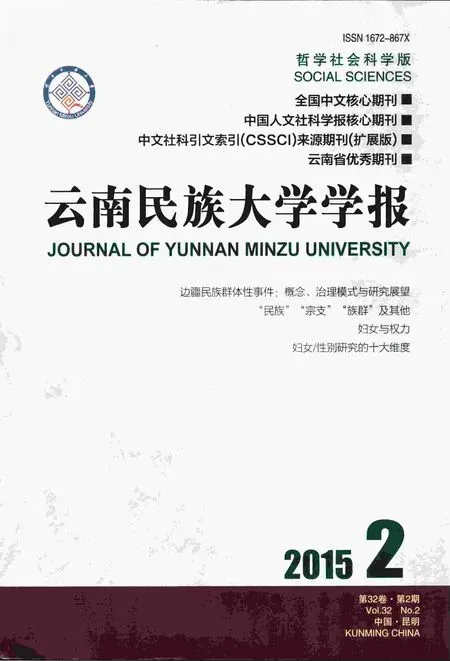智残人士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相关性研究——以南京市分析为例
李春凯,欧 颖
(1. 香港中文大学 社会工作学系,香港;2. 香港大学 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香港)
智残人士作为残疾人中的一类特殊群体,由于智力受限,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残疾人更难表达自身需求,其社会融合与康复难度较大,一直是社会中极少受到关注的弱势群体,甚至受到社会歧视。
前人研究发现,智残人士的生活质量可能与其相处的人提供的自然支持系统密切相关。本次调研采集了100 名智残人士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与实际需求信息,并从家庭、机构和政府支持三方面着手,对322 个研究对象和8 家机构进行调查,全面了解智残人士的社会支持情况,旨在全面掌握南京市智力残疾人士的生存现状,并进一步探究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并就提升智残人士的生活质量提出针对性措施。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智力残疾在国内外研究不同的语境里也被称为“智力障碍”、“智力落后”,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研究整体较多,国内学界目前多是从医学和心理学角度切入研究,但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的研究较少,总体上实地调查资料较少,资料与研究成果不够丰富且较为陈旧。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简称QOL),也有学者译为“生存质量”,生活质量的研究最早出现于20 世纪30 年代的美国,当时侧重社会指标研究。现在,生活质量已运用到社会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卫生管理学等多个领域,虽然生活质量的定义很多,但基本可以归纳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及综合型生活质量三类。①黄笑笑,韦小满:《智力落后成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综述》,《中国特殊教育》2009 年第10 期。本文中的生活质量概念选取第三类,将智残人士生活状况的客观条件和智残人士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结合起来,以更加准确客观地衡量智残人士的生活质量。
美国学者M. A. Verdugo 等人于2011 年底根据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设计出智残人士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情绪状态、人际关系、个人发展、物质条件、健康状况、自我决定、社会融合、权利8 项。②Robert L Schalock . Three decades of quality of life . ProQuest Psychology Journals,2002,15 (2):116 -127.曹凡林③曹凡林:《上海市成年智障人士家庭需求调查》,《中国特殊教育》2006 年第6 期。采用自编的智障人士家庭调查表,调查了上海市1412 个成年智障人士家庭需求,他的问卷是由智障人士的家长或监护人填写,虽然规模较大,但是只能从家庭一个侧面反映智残人士的生活质量。许加成和金萍等人都是以M. A. Verdugo 提出的8 个核心指标所覆盖的领域为基准制定问卷。前者针对来自多地的智障者、智障者家长与教师及康复人员设计了三个版本的智力残疾人生活质量问卷调查表,这是较早且系统的专门针对智残人士生活质量所做的调查,但是样本代表性有待提高,题目偏难不利于回答。①许家成,王勉,向友余:《关于中国智障者生活质量的分析研究》,《中国特殊教育》2004 年第8 期。后者于2005 年在北京市进行系统抽样,以北京市成年智力残疾人、家长和亲友、基层康复工作者等三百多人为研究对象完成的生活质量调查,许家成也参与其中,这次调查从对生活质量各领域的主观期望、感受到的支持程度和实际现状三个角度反映成年智力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整体调查较为严谨全面,但是未曾考虑政府支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②金萍:《成年智力残疾人生活质量调查》,《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7 年13 期。综上所述,国内针对智残人士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并没有全面反映智残人士的社会支持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且缺乏实证分析。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研究为横向调查研究,2013 年3 月到8 月,本研究课题组以南京市鼓楼区、玄武区、建邺区和白下区为重点调查区域进行抽样调查,由于智残人群的分散性与隐蔽性,考虑到调查的可操作性和有限的人力物力,未登记在册的智残人员不在调查范围内,本研究重点调查日间托养型机构、寄宿制机构和特殊教育学校内的智残人士生存现状,调查对象包括四类人群:机构登记在册的智残人士及其家属,智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残联相关管理人员、所在社区群众。其中智残人士的抽样重点以18 ~65 岁在机构内接受服务的智残人士为主,智残服务机构按照服务类型与机构性质选取了华侨路街道慈恩托养中心、红山街道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凤凰街道安养中心、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方舟启智中心、宁馨阳光家园、火凤凰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博爱残疾人服务发展中心八个机构进行调研。
(二)调查方案设计
本次调查针对四类人群,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制订了两份问卷和两份访谈提纲,整体设计如下:
(1)针对智残人士及其家属采用一对一的问卷访谈与个别深度访谈相结合,问卷访谈实际分为两部分,即智残人士回答部分及其家属回答部分,智残人士部分问卷以客观题为主,主观题为辅,主要收集其基本信息以及对其生存质量的主观感受;家属部分主客观题各一半,对个别智残人士或其家属做了深度访谈,作为调查的深入挖掘的补充部分。
问卷填写的基本原则是智残人士回答部分的问卷因人而异,具有一定思考能力的三、四级智残人士回答所有智残人士反馈信息部分的问卷,主观题根据其理解情况自由选择回答,在其言语表达受限的情况下尽可能鼓励调查对象通过手势、点头、摇头等多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愿;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其他智残人士的基本情况问卷的客观题由其家属代填,主观题不填写。家属回答部分必须由其家属本人完成。
(2)针对相关的社区群众分层抽样后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社区群众对智残人士的了解情况与态度倾向,这部分问卷结构较为简单,共发放200 份。
(3)针对十五名残疾人托养机构工作人员进行结构访谈法,侧重了解工作人员对智残人士的认知情况与评估机构服务质量,同时收集机构的信息与服务资料。
(4)对5 名残联管理人员进行结构式访谈,侧重了解其对智残人士的了解程度与态度,并收集南京市智残人士统计资料。
两份问卷均经过三次修订,并且进行了小规模试测,在第一次试测后根据实际再次调整问卷内容并确定问卷终稿。访谈提纲作为访谈的框架,除了提纲内容外,实际访谈内容根据被访谈者实际经验可以有所侧重。通过结构式访谈法向残疾人托养机构的工作人员、残联管理人员收集资料,了解其对智残人士权利与福祉的认知和态度。通过调查问卷法,掌握智残人士基本生存现状以及社会大众对智残人士的看法。
(三)样本概况
本调查的四个部分收集到的资料分别为:智残人士及其家属,实际发放问卷106 份,有效回收100 份,回收率94. 3%,深度访谈对象为3 人;访问智残人员服务机构7 家,一线工作人员15 人,政府管理人员5 人;对社会大众发放问卷200 份,有效回收197 份,回收率98.5%。调查机构包括公办和民办两种类型;并涵盖日托、特殊教育、庇护工厂、生态农场、家庭服务等目前南京市智残机构所有的服务的类型,具备一定代表性。
本次调研回收的有效样本中,智残男性56 人,女性44 人,全部为汉族,其中94% 持有残疾人证,另外6%则没有残疾证,仅1 人没有定级,残疾等级1 ~4 级的都有,其中二级最多,占到57%,重度的一级、二级智残人士占到总调查人数的62%,这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反映了中国智残服务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轻中度的三级、四级智残仅占27%。
三、研究发现
本研究重点从为智残人士提供社会支持的三类主体家庭、机构与政府出发,并考察宏观社会文化对智残人士的支持度。总体看来,智残人士生活质量虽然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仍然不容乐观。
在整个智残人士的外部支持网络中,家庭支持对智残人士的生活质量有着最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家属对智残康复与科学照顾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智残服务机构对于引导学会自理与自我决定、提高智残人士的情绪控制能力、拓宽个人发展渠道和社会融合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支持就业达成稳定物质条件的重要中介,但目前智残服务机构服务水平良莠不齐,且发展受制;政府政策在提高智残人士生活质量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国家的政策倾斜对智残人士的物质水平与接受康复治疗的条件有着直接的影响,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国家政策抱有较大期望,但是政府支持有两点缺陷:一是政策优惠以少量的财政补贴为主,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智残人士的生活质量;二是制定政策的人对智残人士需求认识不深,国外研究显示,与残疾人接触有助于提高对残疾人的积极态度,有残疾儿童的父母比没有残疾儿童的父母对残疾人有更加积极的态度,而许多制定政策的人与智残人士接触很少,这必然导致政策制定时的疏漏与不足。①Kelly EJ . Attitudes of parents of non -disabled students regarding inclusion of disabled students in Nevada's public schools .Psychology Rep,2001,88 (1):309 -312.以下从M. A. Verdugo 提出的8 个生活质量指标出发简述智残人士的生活质量,并分析其与所得到的
不同的社会支持之间的关联性。1、情绪状态与健康状况。
智残人士的情绪状态和健康状态受家庭成员与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影响最大,因为家庭是其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家庭所能提供的生活条件与受家庭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习惯对智残人士影响深远。智残服务机构的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合理地引导智残人士思考,帮助其疏导其心理问题,促进其身心康复。
访谈发现,由于家庭宠溺、社交圈窄、终日无所事事等原因,相当一部分智残人士在前往智残服务机构接受服务前,脾气并不好;进入智残服务机构之后,在机构老师的引导与帮助下,很多智残人士逐渐学会控制情绪,生活更加和谐。而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目前南京大多数智残机构师资薄弱,员工数目都在十人以下,从事这一行业的男性尤其少,全职员工人数很少,日托机构一般是一个人照顾好几个学员,有时甚至一人照看当天机构内所有学员,很多机构将期望寄托在志愿者身上,志愿者工作不专业的现象司空见惯。
大多数智残人士对现有生活并不满意,表示很满意与比较满意的智残人士仅占样本总人数的7%和10%,很不满意与不太满意则占到了54%,说明有相当多的智残人群的生活质量有待进一步调整与提高。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智残人士和家属在面对未来打算时,都充满了疑虑与迷茫,尤其是家长们对自己离世后孩子的生存问题非常担心。
澳大利亚1998 年的残疾调查结果显示,有智力残疾的人比健全人患精神残疾的概率更大,且更容易患多种残疾,精神障碍是智残人士最普遍的伴生残疾,其次是感官/言语残疾和身体/多种残疾。②宋铭,王娜,张俊婷,田宝,邱卓英:《澳大利亚智力残疾的调查方法和流行病学统计分析》,《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4 年第10 期。我们这次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结论。面向智残人士的调查中,约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既有智力障碍也有精神障碍,除去回答问题时思考时间较长外,能够清晰表达自己意见和想法的智残人士占被访人数比例很低。智残人士的自理能力普遍较差,拥有完全自理能力的仅占样本总数的13%,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智残人士无法独立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我们调查的对象基本上属于南京市智残人士中相对比较健康的群体,而现场所见到的重度及极重度的脑瘫患者连活动身体都很困难,很多重度智残人士都被安置在家中照看,得不到专业护理。而南京的智残服务机构主要面向轻中度智残人士,很少提供针对重度智残人士的外展服务,个别机构提供外展服务,但其对象主要是家境较好的重度智残人士,家境不好的重度智残人士是目前亟需关心的群体。
2、人际关系与社会融合。
人际关系与社会融合对于健全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获取资源与信息交换的途径,但是智残人士却很难实现正常的人际关系与社会融合。一方面,他们缺乏与正常人交往的渠道,既渴望与外界沟通与交往,又担心被外界歧视与欺骗。由于多数智残人士的交际圈在家庭内部,所以智残人士最依赖的对象为父母,对于家属(包括父母和其他亲人)依赖度高达90%,家庭支持对智残人士生活质量有着非常直接且重要的影响。
智力因素被家属们认为是智残人士融入社会最重要的障碍,有78%的家属如此认为,在目前有限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这是难以扭转的既成现实;另有67%的家属赞同歧视因素,通过对访谈资料整理可发现,家属认为受到社会的歧视与排斥是智残人士无法融入社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在对智残人士所在社区普通群众所做的调查中,作为个体的受访者大多表示自己对智残人士没有歧视,但他们同时认为整个社会对智残人士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智残人士及其家属与社会对歧视感受度的差异对其社会融合有一定影响,具体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探究。
3、物质条件与个人发展。
智残人士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富足,政府资助是其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绝大多数被访者家庭属于社会中下层,年总收入偏低,大多数被访家庭属于低保户或低保边缘户,社会支持来源单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076.93 元,不到2012 年江苏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在有些智残服务机构中,低保对象占接受服务总人数的一半甚至更多。
调查显示,91%的家庭表示接受过政府相关部门、残疾人联合会与社区居委会的帮助,形式有重残补贴、助学券、低保补助、节假日慰问品、实物帮助(免费取药)、接受服务(托养服务,与政府推动的志愿者服务)等,但是总体上受资助金额较少,实际资金额度从每年每人2400 ~6480 元人民币不等。
对于智残人士而言,个人发展是一种奢侈的愿望,他们的社会融合度很低,自我保护与自理能力差,没有足够的劳动收入,甚至无法劳动,绝大多数智残人士终其一生都和其家人生活在一起,或者在机构被托养,极少有人可以自力更生。成年智残人士大多赋闲在家,只有少数接受过职业训练和康复训练,而且只能习得简单的机械性操作。智残人士接受职业培训与康复训练的最重要的场所与中介是智残服务机构,事实上所有被调查的智残人士都是在智残服务机构里接受职业培训的。南京市目前有几个大的智残服务机构都提供绘画、编织、房间清理等简单的工作培训,可是产品的需求市场不大。在促进智残人士的个人发展方面,政府支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目前的政策规定主要是满足智残人士最基本的生存与照顾问题,没有考虑到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就业与“助其自助”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政府可以通过购买专业的智残服务机构就业支持项目、残疾人小额资金贷款、发展相关的社会企业等方式促进智残人士就业。
4、自我决定与权利。
智力因素是智残人士的致命弱点,智力较低使得他们很难如健全人一般思考,因而很难自我决定。残疾等级越高的智残人士越难以做出自我决定,三级、四级的轻中度智残人士只能做出一些简单的判断与决定。这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他们难以有效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也几乎没有能力去捍卫自身权利。
存在某种需求往往意味着存在相对应的权利诉求,智残人士自身由于智力因素受限,所以他们的家属作为最关心他们的监护人,成为他们事实上的权利诉求代言人。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家属普遍认同经济需求(85%)、住房需求(75%)、就业需求(63%)、交往需求(54%)、健康需求(59%)、和教育需求(44%)、护理需求(35%)、婚姻需求(31%),而性需求认同率较低(19%)。虽然家长认同智残人士的这些需求,但同样认为受家庭经济条件制约,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
此次抽查的智残人士中,94%的被访对象未结婚。在智残人士的婚姻问题方面,只有14%的家属明确表示支持。实际生活中智残人士婚姻权利容易被忽视既有客观原因也有父母的主观因素。中国现行《婚姻法》第6 条规定:“患麻疯病不能治愈者或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禁止结婚。现实中禁止他们结婚,一是基于优生学原理,这两种人结婚可能将疾病遗传给后代。二是不能充分控制、辨认结婚这一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①张競芳:《关于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建议和设想》,《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1 期。很多智残人士的父母对子女的异性交往和婚姻持反对态度:一是智残子女跟正常人成婚后受欺负,跟同样生理条件的(智残人士)结婚,有了孩子会加重智残人士自身以及家庭负担;二是认为智残子女没有性的需要;三是认为他们缺少为人父母的能力。
四、智残人士生活质量方面存在的不足
1. 国内智残人士安置方式较为落后,仍处于摸索阶段。
目前,南京市智力残疾人士照顾方面属于发展步伐较快总体质量较高的城市,以公办凤凰托养中心为全国智残人士托养中心成为全国优秀日托智残服务机构的典范,而整体而言,南京市的智残服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早在20 世纪40 年代,美国就已逐渐形成了以机构化安置、家庭安置、日间活动中心和庇护工场的日间工作、尽量在社区正常的工作环境中进行日间工作为主的五种安置模式,我国当前面向智残群体的安置途径只有前四种,当前的日托中心与其中的日间活动中心类似,而庇护工场近几年才在国内兴起。目前国内普遍认为智残人士不能适应竞争性岗位,极少思考如何拓展智残人士社会融合与自力更生的渠道。
2. 国内智残人士分散度高,且隐蔽性高,大部分智残人士接受的社会支持比预期更少。
学界目前对于智力残疾的发生率尚未达成一致观点,通常观点认为应占一般人口的1% ~3% ,在美国,智力残疾的流行率估计一般认为人口的1% ~1.5%。20 世纪80 年代澳大利亚统计局调查发现,当去除人口变化的年龄影响后,智力残疾流行率在0.56% ~0.67%之间变化。根据南京市统计年鉴,当前南京市户籍人口超过636 万,而由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提供的资料可知,目前全市智力残疾人口为13465 人,持证的智力残疾人士约占总人口的0.21%,如果我们保守估计南京市的智力残疾率为0.5%,那么有近2 万的智力残疾人未曾登记在册,这部分智残人士大部分被其家属隐匿在家中,难以享受相应的福利补贴与正常的康复性照顾,由于这部分群体较为分散,其需求也较难被关注。
五、增进智残人士生活质量的策略
当前南京市智残人士生活质量比以前有所提升,但在经济保障、婚姻需要、教育就业等方面现状堪忧,智残人士服务机构发展遇阻,社会对智残人士接纳度较低。加强政府投入与政策支持、改善民办智残托养机构的环境、提升残疾人事业宣传力度是当前促进智残人士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
1、加大政府投入,切实加强政策制度支持。
政府在对智残人士的经济补贴方面,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和智残人士现状,不断提高经济补贴的标准与水平。特别是做好智残人士家庭扶贫工作,不断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可能性。在教育方面,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待遇,充实教师队伍,保证为智残人士接受教育与培训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与环境。在就业方面,支持智残人士服务机构建设与发展,加强智残人士就业培训,动员社会力量搭建智残人士就业服务平台,加强就业信息平台建设,为智残人士提供诸如勤杂工、手工制作等力所能及的工种,保证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得收入来源;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强智残人士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完善医疗、养老、康复等社会保障制度。
2、加强民办智残托养机构建设,强化扶残助残作用。
加强对民办智残托养机构的培育和扶持。政府可以调动企业、社会各界的力量,建立专项基金,为民办智残托养机构建设与改造、基础设施配备、人才队伍配备提供经济支持;建立行业交流协会,促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智残托养机构之间的业务交流、不断提高行业内专业化水平;加强智残托养机构人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薪资待遇,强化业务培训;充分发挥社区康复模式的作用,努力尝试通过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探索居家助残新模式,将社区服务组织与社会工作服务纳入智残人士服务领域,利用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方式使智残人士在社区内就能接受良好的培训与发展。
3. 提升残疾人事业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社会环境对于智残人士的康复与发展影响深远,理解、包容、尊重的社会环境将会对智残人士的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应充分承担社会责任,利用公益广告、新闻倡导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关心智障人士的发展,大力支持残疾人事业。同时以典型引路,积极宣传智残人士自强不息的模范事迹和扶残助残的先进典型,努力营造理解、尊重、关照、帮扶智残人士的良好氛围。鼓励智残人士克服自卑心理,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动员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一切力量积极开展针对智残人士的扶助工作。大力将志愿者服务引入残疾人领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现代文明的残疾人观,形成关爱、帮助智残人士及其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