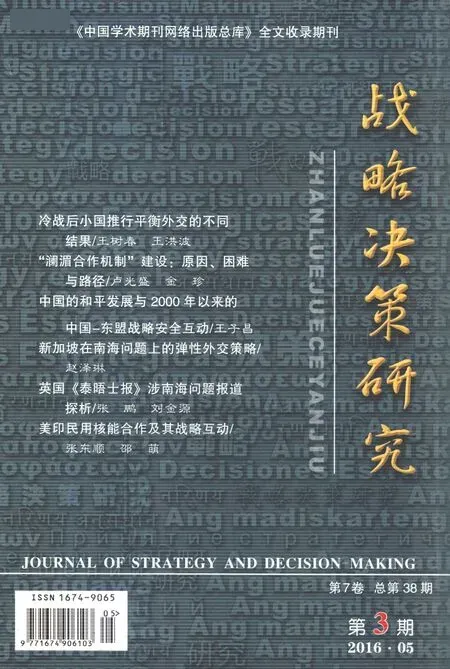“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原因、困难与路径?
卢光盛 金 珍
“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原因、困难与路径?
卢光盛 金 珍
作为我国推进区域合作和周边外交的一项重要举措,“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于2015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2016年3月,我国主办首次澜湄合作机制领导人会议,澜湄机制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作为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次区域合作平台,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三方面的突出困难:澜湄合作机制与老机制的协调问题;下游湄公河国家对于澜湄合作机制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中国对澜湄合作机制的支持力度。在当前环境下,我国应从战略高度上将澜湄机制建设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在策略上重点经营与中路的老挝、泰国和柬埔寨三国的合作;广泛开展功能性领域合作,实现次区域经济合作向政治互信、安全合作扩展;加大开放,放宽粮食进口、地方外事权限等;加强布点考虑,争取澜湄合作中心落户昆明或南宁。通过切实推动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实现我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倡议权、引领能力和规则制定权,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和周边外交中的试验、示范和“早期收获”的作用,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繁荣与稳定。
澜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周边外交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主轴的次区域合作兴起。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在不同范围内展开了多层次、机制化、实质性的次区域合作。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的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为促进东盟次区域发展,中方愿积极响应泰方倡议,在10+1框架下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①《李克强在第18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15年 1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2/c_1117218197.htm此后,各方分别于2015年4月和8月,在北京和清迈举行了两次高官会,就合作目标、原则、重点合作领域、机制建设等达成一致。11月12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议在中国云南景洪召开,标志“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在中国倡议“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澜湄次区域有望成为率先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先行区和试验田,建设和完善澜湄合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澜湄合作的国内外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及次区域发展的现实情况,剖析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原因,分析深化澜湄合作机制面临的主要困难,并思考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如何切实推进澜湄合作机制建设,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一体化进程。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关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内外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根据研究领域、研究议题以及成果数量,可以将国内外对澜湄合作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国内一些机构开展了关于澜湄经济合作的相关政策规划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最终成为国家与地方政府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专著主要集中于对次区域国别政治经济、资源概况等问题的研究。相关论文的数量不多,主要对次区域的合作模式、主要困难及合作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传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如关税同盟理论、区域(地区)主义等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增长三角、增长多边形等方面的理论思考,并结合东南亚的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个阶段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开创性和战略性的特点,起到了良好的决策参考作用,但也存在研究领域较为狭窄、分析对象不具体的局限。
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初至2011年。这一时期澜湄合作逐渐成为我国东南亚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尤其是2002年,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简称GMS)领导人会议召开之后,澜湄合作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议题也不断细化和深入。国内学者主要从两大视角展开研究,一是国别参与澜湄合作的视角。由于我国是澜湄合作中的主要参与方,也是次区域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国家,国内不少学者对我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进展、困难、前景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张锡镇提出我国与湄公河国家合作的深化,面临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水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领域”,必须找到突破障碍的有效途径。②张锡镇:《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进展、障碍与出路》,载《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3期,第5页.付瑞红在分析了次区域合作的特征、中国参与合作的角色特征等问题之后,提出“中国政府进一步利用自身的经济、政治优势更好的发挥政策协调者的角色是必要的,也是值得期待的。”③付瑞红:《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阶段演进与中国的角色》,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5期,第69页.二是专题研究的视角。国内学者主要围绕次区域合作中的产业、贸易、金融等专题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议题。水资源开发是次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内容,国内对此也展开了专题研究,但是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在这个阶段,随着众多域外大国参与湄公河流域的开发,围绕澜湄合作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研究路径呈现出由单一的经济路径向国际政治(关系)路径扩展的特点。
相比之下,国外研究对于澜湄合作或是GMS的总体研究、区域研究比较有限,主要采取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路径,集中于大湄公河“水政治”(Hydro-Politics)所引发的生态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议题。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为主,专著的数量较少。具体而言,国外研究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澜沧江-湄公河这一跨界河流的管理。如,佩奇·索科姆的《跨界河流管理:以湄公河为例》,常·万纳瑞斯的《湄公河地区的环境和经济合作》等;④Pech Sokhem,Kengo Sunada&Satoru Oishi,“Managing transboundary rivers:The case of the Mekong river basin”,Water International,Vol.32,No.4,December 2007,pp.503-523;Vannarith Chheang,“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Mekong River”,Asia Europe Journal,Vol.8,November 2010,pp.359-368.二是中国参与次区域合作的动机、措施及影响。如,提莫·门尼肯的《中国在国际资源政治中的表现:湄公河的教训》,吉姆·格拉斯曼的《角逐湄公河-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与泰国》等。⑤Timo Menniken,“China’s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Lessons from the Mekong”,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9,No.1,April 2007,pp.97-120; Jim Glassman,Bounding the Mekong: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China,and Thailand,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0.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不少学者和机构往往带有“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与湄公河下游国家的合作,不乏“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如,亚历克斯·利伯曼在《霸权渗透: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湄公河大坝建设》中,就以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表现为例,否定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认为中国自身过度强大而湄公河国家严重示弱,中国对于这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绝对不会做出让步,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不可能实现双赢。⑥Alex Liebman,“Trickle-down Hegemony:China’s‘Peaceful Rise’and Dam Building on the Mekong”,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7,No.2,August 2005,pp.281-283.关于中国参与的湄公河水资源开发的研究,国外一些研究有失客观和公允,给中国与次区域国家的合作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第三个阶段:从2012年至今。GMS合作进入第三个十年阶段以来,即第四次GMS领导人会议发表《GMS经济合作新十年战略框架(2012-2022)》之后,国内关于澜湄合作的研究出现两种趋向。一种是延承原有轨道,依据继续深化经济合作的研究思路,围绕该战略框架确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关注自然与社会因素三大战略目标开展研究,国内不少学者仍认为应坚持“突出GMS合作的主导地位”。⑦黄征学、肖金成、申兵:《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思路及对策》,载《区域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第19页。
第二种是国内开始出现一种研究重心转向的趋势。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在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关税降低及道路联通的边际效应降低的情况下,特别是在GMS合作几乎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看重的政治互信、安全合作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方面问题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深化澜湄合作的问题。沈铭辉分析了GMS机制的不足之后,指出中国如果在今后的合作中,将“过多的原本不属于GMS的东西纳入目标范畴,则会导致中国反受其害”。⑧沈铭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与中国角色》,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3期,第18页。任娜和郭延军提出“探讨建立全流域水资源合作机制的可能性”。⑨任娜、郭延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问题与对策》,载《战略决策研究》2012年第2期,第65页。毕世鸿提出在安全合作方面,“中国可考虑重构既有的合作框架,择机与湄公河国家联手筹组类似上海合作组织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加强顶层设计。”⑩毕世鸿:《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2期,第71页。卢光盛则明确提出了推动GMS合作升级,提出拓展次区域合作的政治-安全以及社会维度方面的思路,针对湄公河航道安全与联合护航、跨境犯罪防控与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了专题研究。⑪卢光盛、金珍:《“一带一路”框架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5期,第67~81页。从 2014年年末开始,特别是到2015年年中开始,国内学界开始出现了“在GMS机制之外,由中国主导另外创设一个新的合作机制”的意见和声音。⑫卢光盛:《“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几点思考》,载《东亚要报》2015年7月,第1-6页。这说明,本阶段国内的一些前沿性研究,呈现出了与外交决策部门形成某种呼应和配合的趋势,实现了学术研究与外交战略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一阶段国外研究的主要议题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对合作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域治理等问题继续给予重点关注。⑬Sebastian Biba,“China’s Continuous Dam:Building on the Mekong River”,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42,NO.4,November 2012,pp.603-628; Andrea Haefner,“Regional Environmental Security:Cooperation and Challenges in the Mekong Subregion”,Global Change,Peace&Security,Vol.25,No.1.2013,pp.27-41.
综上,国内外研究旨趣差异明显,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可能。现有成果主要取得了三大方面的进展:一是从国际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等方面对澜湄次区域合作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解读。二是应用性、对策性和经验的研究,较好地服务了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的现实需要。三是初步提出了GMS合作升级和澜湄合作机制的初步构想,并在总体思路和基本框架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不过针对“澜湄合作机制”这个研究问题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和外交部门总体上还缺乏系统、深入和针对性的研究。虽然提出了澜湄机制的设想并初步变成了现实,但至少还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并没有充分得到解决。一是,澜湄合作机制提出的原因。新机制成立有何必然性和重要性?澜湄机制与中国当前倡议的“一带一路”有何关联?二是,澜湄合作机制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澜湄合作机制本身是一个多边合作形式,其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湄公河下游5国的理解和支持,获得域外大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接受也非常重要。这些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态度如何,其主要顾虑、利益关切、参与(或应对)策略、优先领域是什么?三是,我国推进澜湄机制建设的路径和对策研究亟需加强。国内学界及有关部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和框架阶段,远不能满足现实的紧迫需要,这些正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二、提出澜湄合作机制的原因分析
在过去合作中,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表现出了较强的活力,极大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次区域经济合作增长乏力,安全与战略环境日趋复杂化,以及中国与湄公河下游国家经济和总体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面临发展的瓶颈。无论是从次区域合作的相关理论,还是澜湄次区域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澜湄合作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合作方式。
(一)从理论层面来看,澜湄合作机制的提出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
新功能主义认为,区域内国家在经济、技术等功能性领域的合作深化,会产生“外溢”(spillover)效应,最终能够促进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逐步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厄恩斯特·哈斯提出,合作之初各行为方主要在一些技术性或非争议性的领域开展合作,但各方会逐渐发现,只有将更多的权威让渡给集体决策机构,或者扩大其它相关的功能性领域合作范围,才可能达到合作目标。随着合作范围日益扩大,各方的合作会逐渐向有争议的领域进行。最终使得原来只是经济一体化,提升到政治一体化。⑭Ernst Haas,Beyond the Nation-state: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48-50.“外溢”效应不会自动产生,而是一个自觉、能动的过程,依赖于一系列基本变量和条件的成熟,否则就会产生“环溢”(spillaround)、或者是“溢回”(spill-back)等现象。哈斯和菲利浦·施密特共同研究后提出,政治溢出取决于背景、经济联盟、过程等变量,每一项的分值越高,经济合作溢出到政治领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多元化、民主化、工业化等更有助于实现政治溢出。⑮Ernst Haas and Philippe Schmitter,“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18,No.3,1964,pp.705-738.在新功能主义看来,不同领域的合作都具有潜在的关联性,任何领域合作的成功都会增强合作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的愿望和信心。经济合作逐步推进并溢出到越来越多的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此后核心机构将加速扩展,共同体建设也将由此真正起步。尽管新功能主义的相关理论是针对欧洲一体化而发展起来的,也存在较多的局限性,不过就一体化进程及区域治理研究而言,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及逻辑对于当下澜湄次区域合作仍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实主义则强调权力、国家间的竞争、相对收益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认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必须由一个或几个政治实体,愿意发挥自身的权力和影响来领导和推动一体化的实现。关于经济一体化是否有助于安全合作以及解决区域性冲突,不少现实主义者提出否定的看法,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而会受到地区冲突的制约和反作用。肯尼思·华尔兹提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增加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不会带来和平,而且会因此导致更多的冲突。⑯肯尼思·华尔兹,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142页。约瑟夫·格里克提出相对收益的概念,认为在区域合作中,相对收益较少的国家在政治军事安全方面会受到相对收益较高国家的制约,但各国不会自愿地为了经济利益而在国家安全方面做出让步。从长远来看,相对获益会阻碍区域一体化的努力。⑰Joseph Grieco,“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85-507.还有学者提出,相比贸易制度的安排,军事安全同盟对区域合作的影响更大。一个国家更可能与政治军事盟友实现一体化,而不是其敌对者。⑱Joanne Gowa and Edward D.Mansfield,“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2,1993,pp.408-420.这就意味着,成员国家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会深刻影响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和深度。如果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得不到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就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益。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看上去与欧洲相似,但实质上不论是合作动机、机制还是进程,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通常而言,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为了实现贸易的扩大,以及摆脱对外经济依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很多学者持悲观态度。主要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区域一体化水平的起点往往很低,除非伴随一定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否则经济一体化很容易走向解体。我国学者郎平在分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案例之后,提出“大国推动”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政治和安全合作的重要动力。如果想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到更多的“政治衍生品”,需要尽可能地增加参与方对从合作中获益的政治预期,为潜在的政治合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⑲郎平:《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政治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129-148页。
总体而言,区域一体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与独特性等特点,任何单一的理论范式难以解释权力、安全、以及利益间复杂的关系。但是以上相关研究至少可以给澜湄次区域合作提供以下两点有益的启示。第一,从经济和技术等功能性领域着手加强次区域合作,会产生积极的政治作用,地区层面的治理也会随之扩展,包括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合作是“高阶的”(advanced)次区域一体化的一种自然趋势。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中应尽可能增加安全、政治等多议题合作。这不仅能增加成员国的收益,克服利益不平衡分配的问题,还将提高冲突的机会成本。在某个议题处于绝对或相对劣势的国家,可以从区域合作中的其他议题寻求利益的补偿。对于难以分割的利益冲突,建立多议题的制度框架可以为调解冲突提供更多选择,以及更大的谈判空间。
(二)从现实层面来看,澜湄合作机制的提出具有紧迫性和创新性
一是澜沧江-湄公河地区经济合作深度不够形成掣肘。自1992年成立GMS合作机制以来,次区域国家重点在经济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次区域经济合作到达了一个较高层次,如何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和层次的问题日益突出。在2015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零关税”在与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这四个新东盟国家的实现,次区域内的关税水平已经降低到非常低的层次。可以说,次区域内关税(一般商品)几无可降之地,降关税促进贸易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大下降。同时,继续施行通关便利化等优惠措施将很难产生明显的刺激效果,次区域一体化需要新空间。此外,次区域国家全部为发展中国家,各国的国内资源和产业结构比较相似,主要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普遍依赖外部资金和技术,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直接的竞争对手。除中国之外,老挝、柬埔寨等国普遍国内市场狭小,消费水平和层次较低,难以吸纳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在次区域内无法形成有效的分工。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对接加快的背景之下,次区域各国间竞争有余而互补不足成为阻碍合作深化的不利因素,次区域迫切需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
二是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原有合作广度不够的天然劣势。澜湄次区域合作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安全和社会领域的合作一直进展不大,导致次区域合作虽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但存在政治互信不足、安全合作水平低下的总体状况。在社会领域上,次区域内不断涌现的跨国贩毒、走私、偷渡、赌博和贩卖人口等问题,各国对此一直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渠道,而在跨境水资源合理分配和科学利用,跨区域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上的合作程度更低。这些功能性领域合作的低水平,是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一大特点,也是其重要不足。特别是合作中的水电开发、航运安全、环境保护、农业、旅游等诸多领域都涉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本身,而次区域现有合作机制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如GMS在次区域合作中最具影响力,但是GMS以经济为主要合作领域,水资源管理目前并不在GMS合作机制框架内。湄公河委员会(MRC)关注了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该组织只是区域间政府组织,属于咨询机构,无强制执行权。⑳MRC Annual Report 2014. http://www.mrcmekong.org/assets/Publications/governance/MRC-Annual-Report-2014.pdf并且,MRC的成员国为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四国都是湄公河的下游国家,一些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更倾向于维护下游国家的利益。中国若加入湄委会,作为其中唯一的一个上游国家,在涉及到中国相关问题的处理时可能会受到来自下游国家、区域外国家甚至是国际组织的影响,有受到针对和排挤的危险,进而导致一些水资源开发项目无法及时有效的实施。澜湄合作的深化迫切需要上下游国家加强利益协调,探寻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平台。
三是中国希望在次区域合作中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尝试体现中国的倡导权甚至规则制定权。长期以来,次区域外大国不断积极参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GMS、MRC等机制就主要受美国、日本的主导或影响。近年各国还通过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共建多种合作机制,深化合作关系。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加大对湄公河国家的战略投入力度,还试图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重塑亚太经济秩序,2016年2月4日越南与相关成员正式签署TPP协议。日本自2009年起建立“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2015年日湄首脑会议上发表的《新东京战略2015》宣言中,日本表示在今后3年内,将向湄公河国家提供7500亿日元(约61亿美元)援助,主要协助各国建设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如打造港湾、发电厂,及开通越南到缅甸的东西走廊道路,并在人力资源培训、产业提升等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㉑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New Tokyo Strategy 2015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MJC2015),July 4,2015,http://www.mofa.go.jp/s_sa/sea1/page1e_000044.html印度和湄公河国家建立“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主要在旅游、教育、文化及交通领域开展合作。欧盟、澳大利亚和韩国主要在民主、人权、水资源管理、环保、医疗服务等方面有较多投入,对湄公河流域国家有较大影响。
域外国家在多个方面与湄公河国家推进合作,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湄公河下游5国对中国合作的需求,增加了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复杂性和竞争性。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湄公河下游国家既期待搭“中国便车”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推动地区繁荣和稳定,又对中国怀有不同程度的担忧和戒备。中国作为次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和提供最多发展机遇的国家,在过去的合作中,无论是在区域合作的主导权方面,还是规则的制定权、话语权等方面,都存有明显的不足。中国需要平衡好次区域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安全诉求,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在中国倡议“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澜湄合作机制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望成为率先取得突破的方向,在周边外交中发挥出试验、示范和“早期收获”的作用。
三、推进澜湄合作机制面临的困难
澜湄合作机制建立之后,各国展开了切实合作。2016年各方会举行澜湄合作首脑会议和其他层级的系列会议,并将推出一批具体的合作项目。作为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次区域合作平台,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三方面的突出困难。
(一)澜湄合作机制与老机制的协调问题
澜沧江-湄公河次地区内,由多方参与的多种区域合作机制长期并存。除了前述的GMS、MRC、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发起或主导的机制之外,还有次区域内国家自主建立的其他机制。如,东盟主导的“东盟-湄公河利于开发合作”、中老缅泰四国毗邻地区的“黄金四角经济合作”,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等。这些合作机制发挥了不同的功能,满足了多层次的需求和各方利益。相比原有合作机制而言,澜湄合作机制颇具特色。特别是在合作领域方面,明确将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列为三大重点领域,将在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合作、农业和减贫合作等5个优先方向集中推进合作。㉒《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全文)》,新华网,2015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12/c_1117126335.htm#0-tsina-1-43291-397232819ff9 a47a7b7e80a40613cfe1但是不可否认,澜湄合作机制在合作目标、领域、项目等方面与其他机制存在交叉和重叠。如何与GMS、MRC等其他相对成熟、各具特色的合作机制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及如何与次区域内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有效合作等,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澜湄机制需要不断加强与上述多重合作机制的沟通与协调,建立健全与各种合作机制之间的联动和协调体系,建立和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以增进合作倡议的活力。
(二)下游湄公河国家对于澜湄合作机制的认可和接受程度
对于中泰推出的澜湄合作机制,湄公河流域国家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担心中国主导而使小国利益受损。一方面,在过去的合作中,湄公河流域国家已经表现出既不希望全面倒向中国,也对西方国家在本地区的活动保持警惕。湄公河地区国家一直通过推行“大国平衡”策略获取利益并提高自身地位,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机制来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今后,必然不会放弃这一策略而全力支持澜湄合作机制的建设。另一方面,次区域国家之间存在着多重矛盾以及利益之争。尤其是次区域各国的市场主要是外向的,内部国家的市场并不占据重要地位。这决定了各参与方不可能同意让渡主权,更不愿意建立强制性的制度安排。㉓毕世鸿:《机制拥堵还是大国协调——区域外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2期,第69页。如何增强澜湄合作机制对于下游湄公河国家的吸引力,切实让湄公河国家从合作中得到实惠,这是推进澜湄合作机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澜湄次区域的开发合作一直以开放灵活而著称,澜湄合作机制需要通过开发合作的良性竞争,以公平公正的姿态,真正赢得下游湄公河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三)中国对澜湄合作机制的支持力度
在次区域合作中,对于小国或者经济薄弱的国家而言,参与合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在非经济方面,如贩毒、走私、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等问题上,则因实力不允许而导致较少关注;而对于大国或者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而言,参与合作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利益,更多是一种维护国家安全的策略,应更多考虑非经济方面的利益。㉔胡志丁:《次区域合作与边境安全及边界效应调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82页。为此,中国可充分发挥地缘优势,适时提供符合本地区的公共产品,如贸易、金融、援助、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促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不断完善澜湄合作机制建设。在公共产品受惠面上,要与湄公河国家的需求相符合,不仅使各国政府受惠,同时还应惠及普通民众,不断促进次区域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分享。但是,次区域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国共同参与。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但也无法承担其他国家免费搭车的全部成本,只能量力而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旦澜湄合作项目全面铺开,由于项目往往投入大,回收期长,中国也难以单方面承受。因此,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为深化澜湄合作提供资金和市场支持,也是澜湄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推进澜湄合作机制建设的路径
(一)战略层面,将澜湄合作机制建设提到“一带一路”早期收获的高度
2015年3月,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在中国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㉕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体现出中国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推进澜湄次区域合作。
相比于我国周边其他区域,澜湄次区域具有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和市场需求,更少的区域风险(如领土争端、恐怖袭击的担忧等),“一带一路”所倡议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该区域有着良好基础。中国可以考虑通过澜湄合作机制,尽快确立一批“早期收获”项目,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挥出地区经济资助国的重要作用,推动湄公河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澜湄合作机制还可以与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新设立的丝路基金、新近推动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沟通与合作。争取国际金融机制和发展基金的参与,为澜湄次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等提供有力的投融资支持。
(二)实施策略,重点经营与中路的老挝、泰国和柬埔寨三国的合作
当前,越南因南海问题对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有所顾虑,缅甸新一轮大选、政治经济转型的推进,可能导致中缅合作短期内出现不确定性。中国与东路的越南、西路的缅甸,在深化合作方面近期较难以有大的作为。而中国与中路的老挝、泰国、柬埔寨三国一直有着较好的政治基础、战略需求,“中路突破、撬动两翼”应该是目前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开展合作的一个明智策略。可以考虑在澜湄合作机制下,重点推进对老挝的各方面工作。支持老挝做好201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相关工作。在与老方充分沟通和老方接纳的基础上,大幅度加强对老挝的投资和援助力度,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中方企业在老设立经贸合作园区,推进铁路、电站、经济开发区等对老挝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项目。依托中老两国签署的《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方案》,加快“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推动两国边境地区发展。㉖《中老签署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方案》,《人民日报 》,2015年9月1日03版。广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扶贫、人力资源开发和职业技术培训等发方面内容,向老挝更多开放市场,让老挝享受更多的出口中国的优惠待遇,促进两国经济优势互补,便利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将老挝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加以经营,推进“中老友好合作条约”的商谈和签署等。以此来逐步增加对次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模式向柬埔寨和泰国扩展。
(三)合作领域,广泛开展功能性领域合作
一是推进以跨境铁路建设为主的互联互通建设。目前中老、中泰铁路正在稳步推进。201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项目在万象举行了奠基仪式。项目北起老中边境口岸磨丁,向南延伸至万象,全长418公里。㉗《中老铁路奠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2月3日 01版。这条铁路北端与中国境内的玉溪至磨憨铁路对接,南端与泰国的廊开至曼谷铁路相连,预计于2020年建成通车。12月19日,中泰铁路举行奠基仪式,两国务实合作的典范工程正式启动。路线从泰国东北部重要口岸廊开府,到首都曼谷及东部工业重镇罗勇府,全长867公里。㉘《中泰铁路启动 李克强“高铁外交”再落一棋》,人民网,2015年12月1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5/1219/c1001-27950565.html除跨境铁路之外,当前还应围绕边境线、湄公河流域线、公路线、通讯线等,与湄公河国家共同制定次区域互联互通整体规划,推进中缅陆水联运大通道建设,充分发挥昆曼公路的效益,全面加快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的规划与建设。探讨签署次区域运输便利化协定,加强规制和联通,提升“软件”建设。倡导并探索推进“中-老-柬经济走廊”建设的可行性,争取先期修通昆明—万象和金边—西哈努克港两个区段,率先建设并在老柬两国形成示范。
二是提升次区域产能合作。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都处于工业化初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中国在基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钢铁、水泥、电力、交通、造船等方面拥有先进的工业装备和富余的成熟产能,性价比高。中国可根据各国发展规划,兼顾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经济转型的双重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产能合作,帮助相关国家实现自身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把加强中国与次区域国家产能合作作为推动和扩大双方相互投资规模,完善澜湄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与次区国家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资金和企业将大规模进入周边国家的重大项目建设,中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特别是对次区域国家的矿产、水电资源开发等直接投资,在合作中要更加注重规范方式,遵守严格的环境和质量标准,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扩大合作的社会效益,更多地顾及当地就业、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是探索开展次区域金融合作。应加强次区域金融合作和交流,探索政府间和国际间、民间的合作机制,探讨制定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未来发展路线图。争取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以降低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同时,中国应推动金融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推动国际金融开放合作,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探寻适合次区域发展的国际金融区域合作模式,探讨项目融资和鼓励投资机制,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市场化的人民币投融资,为金融市场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与次区域国家共同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应对国际和地区金融风险。
四是推进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目前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并非全程安全、适航,沿线的跨国犯罪猖獗,2011年10月“湄公河惨案”的阴影至今仍未完全散去,航船货物与人员安全仍存在隐患。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自2011年12月建立后,有效维护了湄公河流域安全与稳定。但是,因为合作涉及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和主权国家授权问题,彼此还心存芥蒂,下游一些国家很难主动接受中国武装力量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面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复杂的安全形势,需要澜湄合作机制投入更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新的合作平台下,次区域各国进一步深化执法机制合作,扩大合作范围,推动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向综合执法合作升级转型。
五是加强文化交流与人文合作。中国应与湄公河国家推进广泛的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志愿者服务等一系列的合作。加强与次区域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合作。共同建立农业合作中心,建设优良农作物品种示范站、优质高产示范田等,帮助次区域国家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落实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在缅、老、柬等国建立减贫合作示范点。加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促进次区域内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帮助湄公河国家培养更多农业、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的专业人才。
(四)加大开放,放宽粮食进口、地方外事权限等
在粮食进口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的市场容量和购买力,放宽对来自次区域国家农产品进口的配额限制。从近年来,我国与次区域国家的交流来看,老挝等国多次郑重提出希望我方放宽稻米、玉米等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配额、技术壁垒等限制。事实上,我国在开放农产品市场方面仍有较大的空间,这是我国不可替代的一种优势,与次区域国家开展合作时应加以积极利用。通过签署农产品贸易协定,使其享受更多的出口中国的优惠待遇。可优先考虑对老挝进行试点,在条件成熟时可向其他国家扩展。当然,放宽粮食进口管制涉及我国粮食安全、粮价补贴等问题,需要从战略高度去统筹考虑,稳步实施和推进。类似地,在管理机制、地方外事权限、境外劳动力利用等方面,我国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些领域都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
(五)布点考虑,争取澜湄合作中心(办公室、办事处)落户昆明或南宁
到目前为止,澜湄次区域的区域性机构主要集中在泰国曼谷,不利于中方在次区域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应争取将相关的平台、机制的办事机构落户昆明或南宁。例如,可以探讨在昆明设立湄公学院(Mekong Institute,MI)分院或第二学院,甚至考虑将 MI从泰国孔敬整体迁至昆明,重点开展管理、金融、学位教育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弥补MI目前的短板。考虑在昆明创建澜湄合作中心,重点开展政策沟通和与项目规划工作,为澜湄合作提供政治支持和政策指导。考虑创建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加强经验技术交流,帮助相关国家制定水资源利用和防洪减灾规划,加强水资源开发管理能力建设。对综合利用水资源进行总体规划和科学设计,避免各自为政带来相互猜疑。可以依据2015年10月24日通过的《关于加强湄公河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㉙《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新华网,2015年10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0/24/c_1116928240.htm争取在昆明建立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等。类似地,我国可以结合云南和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方面的政策,在昆明或南宁设立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代表处或办公室,增强对次区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卢光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博士,教授,博导。金 珍,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14级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升级版的对策研究”(15CGJ025)阶段性成果;(2)云南省社科规划基地项目“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升级版路径研究”;(3)“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