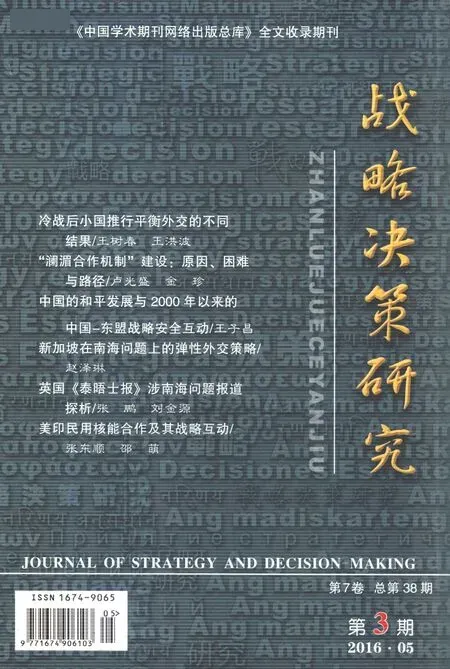英国《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探析
张 鹏 刘金源
英国《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探析
张 鹏 刘金源
随着21世纪初南海问题在亚太地区的升温,作为英国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泰晤士报》对于南海问题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泰晤士报》相关报道议题主要集中于南海问题升温缘由、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的海上冲突以及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展吹填工程等方面。特定的素材选择、鲜明的政治倾向、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是《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的主要特征,由此对英国的主流舆论以及政府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力。为此,中国政府应通过大众传媒构建良好国家形象,主动及时地公布新闻信息,加强中英经济合作,管控双方外交分歧,以防止英国势力涉入南海争端。
英国;《泰晤士报》;南海问题;新闻媒体
近年来,南海问题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影响下不断升温,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各国主流媒体亦给予该问题充分报道,对南海岛屿争端、石油开采及军事演习等话题表现出极大兴趣。新闻媒体涉南海问题报道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其关注点多为中、美及东盟国家媒体对南海问题的报道,鲜有学者从英国主流媒体舆论角度来加以探讨。作为公认的英国第一大主流媒体,自21世纪初南海问题升温以来,《泰晤士报》对南海问题进行了详尽报道,在引导国内舆论以及政府政策方面发挥出重要影响力。
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后,两国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①《习近平访英侧记:“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中国新闻网,2015年 10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10-24/7587290.shtml这为中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如何进一步深化中英两国双边关系和推动中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继续深入发展是当前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的重要考验。有鉴于此,笔者以英国《泰晤士报》为切入点,对2010~2015年《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进行整理,剖析英国主流媒体对南海问题的聚焦点与舆情态势,分析其对国际舆论以及英国政府南海问题外交立场所产生的影响,并探究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
一、《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概况
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于1785年元旦由约翰·沃尔特创办,初名为《每日环球纪录报》(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改名为《泰晤士报》,是一份在全英国发行的综合性日报。由于消息来源可靠,报道内容详尽,加之悠久的创办历史,《泰晤士报》在英国社会,尤其是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和知识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泰晤士报》涉中国南海的首篇报道出现在20世纪初,②该报道为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在新加坡海域的相关活动。参见:“Japanese Squadron off Singapore”,The Times,Dec.22,1904.其后一直断断续续偶有涉及。2010年前后,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影响下,南海问题不断升温,《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开始集中出现。近五年来,《泰晤士报》关于南海问题报道的深度及广度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加以梳理:
(一)报道数量分析
数量多少是评判新闻事件受媒体关注程度的基础指标。对报道数量作分析,可以管窥媒体对新闻事件的重视程度。经统计,自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干涉南海问题言论至2015年12月31日的五年多时间内,《泰晤士报》涉中国南海报道数量约为201篇,平均每年约为40.2篇,每月约为3.1篇,即英国读者几乎每周都可以从《泰晤士报》获取一篇有关中国南海的新闻报道。③数据通过在ProQuest、EBSCO数据库及《泰晤士报》官网中检索“South China Sea”等关键词得出。相关报道中虽有“South China Sea”字样,但与南海问题关联不大;部分报道虽未出现关键词,但其主题却围绕中国与南海主权声索国展开。经过筛选,共获得有效文本173篇。通过分析可知,《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数量分布与南海地区重大事件的发生紧密相连。在南海局势刚开始发酵的2010年,《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数量并不多,仅为11篇。2011年5月和6月,因中越之间发生严重海上冲突,《泰晤士报》相关报道数量增至34篇。受2012年4月中菲之间爆发海军长期对峙的“黄岩岛事件”影响,《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数量在该年度增至41篇。2013年南海地区形势较为和缓,《泰晤士报》相关报道数量减为17篇。2014年5月发生中越“981”石油钻井平台事件,引发越南国内持续数周的反华游行示威活动,南海地区局势势顿时剑拔弩张,《泰晤士报》相关报道数量随之上升,达36篇。2015年上半年《泰晤士报》相关报道紧紧围绕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吹填工程”展开,数量为35篇。由此可见,南海局势的间歇性升温决定了《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数量波动性发展。
(二)消息来源分析
消息来源是衡量新闻报道真实性与客观性的重要尺度,从消息来源可考察新闻的可信程度,《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的消息来源主要有三类:
第一是该报派驻各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这是《泰晤士报》相关报道的主要来源。泰晤士报》信息来源地较广泛,其中来自中国的消息数量最多,占总数的29.4%。其次是南海主权声索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比例约占18.4%。每当南海问题升温时,在新闻事件发生地及舆论中心,《泰晤士报》会通过派驻记者在第一时间给予报道,其较强的时效性引人关注。第三为美国,比例约为11.6%。美国是南海问题升温的主要幕后推手,对美国政府南海论调及行动的密切跟踪有助于提高其新闻可信度。
第二是该报引自各国的官方表述。《泰晤士报》在报道中多次引述中、美、越、菲等国官员或官方发言人的声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道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华春莹的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答记者问,共计11次;从美国发回的报道中,来自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的言论数量达21次之多;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讲话也是被引述次数较多的对象;对越南则多采自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言论。官方表述作为信息的权威来源,不仅对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起到极大作用,同时对受众对于事件性质的理解发挥重要影响。
第三是援引其他媒体的报道。《泰晤士报》援引其他媒体的消息来源同样较广泛,其中大多数取自中国媒体,主要有《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但在介绍这些媒体时,《泰晤士报》往往会对这些媒体的性质加上解释。如给《环球时报》的3次解释分别为“政府支持的小报”(state-backed tabloid newspaper)、④Anne Barrowclough,“China Denies Preparing for War Against the Philippines,”The Times,April 12,2012.“政府控制的民族主义小报”(state-controlled nationalist tabloid)⑤Richard Lloyd Parry,“Vietnam Mobs Burn and Loot Foreign Factories in Anti-China Protest,”The Times,May 14,2014.以及“民族主义小报”(nationalist tabloid)⑥Leo Lewis,“Chinese Workers under Siege from Vietnam Mobs”,The Times,May 16,2014.;对《人民日报》的性质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官方报纸”(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⑦Anne Barrowclough,“China Threatens‘Counter-Strike’Against Philippines,”The Times,June 29,2013.对《解放军报》的解释则为“人民解放军主要喉舌”(chief mouthpiece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⑧Adam Thorn,“China Threatens US With Military Action,”The Times,April 22,2012.《泰晤士报》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解释中国媒体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会让读者质疑中国媒体的客观性。
(三)新闻体裁分析
新闻体裁类型是探究媒体传播新闻形式的重要参数。对体裁类型作分析,可以把握媒体对新闻事件的认知与特点。《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的体材类型主要有四类:第一类为消息体裁,报道总数98篇,主要内容为南海地区局势发展进程的一般性报道,这是《泰晤士报》最经常、最大量使用的体裁,其特点是报道直接,文字简洁,时效性强。第二类为特稿体裁,报道总数40篇,主要聚焦于南海问题中专门性与具体性话题。特点是以形象化为主要手法,对重要的新闻事件或人物进行具体、生动地再现,是富有表现力与感染力的体裁。⑨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206页。如在报道2014年越南国内的反华游行时,《泰晤士报》配有11张图片,主要是越南民众在中国使馆前集会示威与中国工厂被越南民众打砸抢烧这两种内容。第三类为评论体裁,报道总数28篇,多围绕中美两国因争夺地区主导权所展开的战略博弈进行分析。特点是就人们普遍关注的实际问题发表针对性评论的议说性文体,最能反映媒体对报道内容所持观点与立场。如“不要让我们因为中国的威胁而变得偏执”一文,即围绕西方国家应如何应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展吹填工程而评。⑩Roger Boyes,“Let's not get Paranoid about a Chinese Threat,”The Times,April 29,2015.第四类为少量有别于上述三种的介绍类体裁,其特点是涉及与新闻事件有密切关联的生活、历史、自然、人文等题材,是融知识、趣味与新闻为一炉的表现形式。⑪胡立德:《新闻体裁类别研究》,载《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07页。如分析中国新护照上将南海争议海域划归中国领土的地图将引起南海主权声索国抗议的报道。⑫Roger Boyes,“China's Dash for Growth is a Passport to Contention,”The Times,November 24,2012.可见,《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在新闻体裁的使用上进行了精心安排,以文叙事,借图佐文以及凭论析闻成为其报道南海问题的重要方式。
总体而言,《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数量众多,消息来源广泛,新闻体裁丰富。这一方面表明《泰晤士报》对南海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和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泰晤士报》信息来源的广泛性、客观性提高其了新闻可信度,其新闻内容的多样性、丰富性则向受众传递了较为清晰准确的信息,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
二、《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的文本分析
受社会主流价值观、权势阶层及商业利益影响,媒体在面对浩瀚的新闻材料时,并不能够对其进行全部以及完全客观公正的报道,而必须对题材进行筛选,留下符合自身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素材。这也表明,“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抽取的过程。”⑬范士明:《美国新闻媒体的国际报道及其舆论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第36页。这种选择、抽取的过程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对未知事物的理解,对其脑海中认知世界的构建产生关键性影响。《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偏爱的主题,仅仅当他们有话要说的时候才去写点什么。”⑭G.N.Clark,“British Newspapers and Information-Servic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International Affairs(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Vol.22,No.3(Jul.,1946),p.328.《泰晤士报》在涉南海问题报道的议题设置,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而展开:
(一)对南海问题升温原因分析的报道
2010年南海问题逐渐升温后,《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相关报道的内容也随即丰富。表面上看,南海问题是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因部分岛礁归属与海域划界不明而导致的主权纷争,背后隐藏的却是大国全球战略博弈下区域影响力发挥的实质。“美国试图利用南海问题推进自己的地缘战略部署。从国家基本战略的角度看,美国的目的在于通过保持其对南海的军事控制能力以及这种控制的政治合法性来维护其在西太平洋的霸权。”⑮时永明:《美国的南海政策:目标与战略》,载《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1页。但《泰晤士报》却罔顾事实,在分析南海局势趋于紧张的原因之时,将矛头直指中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军事力量的增强及控制整个南海地区的野心,是引发该问题的首要原因。为说明其立场,《泰晤士报》先后发表多篇报道,关注中国对南海问题采取的咄咄逼人态势。尽管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着墨也较多,但其解读为应对中国之举。
首先,“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南海地区的不断控制,成为南海问题升温的主要因素。”这是《泰晤士报》所持的主要立场。早在2011年6月14日,《泰晤士报》就声称:“中国将南海视为自己的‘后院’,其在南海一连串的行动,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即将其东南亚邻居推向自己的战略对手,即美国的怀抱。”⑯Richard Lloyd Parry,“South China Gambit May Push Beijing's Neighbours toward US,”The Times,June 14,2011.在8月25日的报道中,《泰晤士报》列举了中国不断增强军事实力的举措,包括研制反舰弹道导弹、打造新的潜艇和军舰、增强网络战争技术以及已经完成的机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中国除拥有已成功试水的‘瓦良格’号航母外,还计划到2015年建造国产的航母。”⑰Leo Lewis,Michael Evans,“China Strikes Back at Pentagon Fear of its Burgeoning Naval Power,”The Times,August 25,2011.11月17号,《泰晤士报》又以《美国通过部署海军陆战队支持太平洋盟友》为题称:“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给美国的太平洋盟友造成巨大压力,但美国必须确保其与该地区盟友的牢固关系。因此,除了在日本、菲律宾拥有军事基地外,美国还和越南签署了防务协定,计划向新加坡部署巡逻舰,以及向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等。”⑱Anne Barrowclough,“President Bolsters Pacific Allies by Deploying Marines,”The Times,November 17,2011.
其次,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以及在南海周边地区军事部署的增强,也是南海局势趋于紧张的重要原因。2012年,《泰晤士报》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报道有增无减,并更多地关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具体军事部署。3月28日,该报载文《美国以增援澳大利亚盟友打开反对中国新战线》称:“美国正考虑在澳大利亚和斯里兰卡之间的科科斯群岛建立基地,并将于2015年在该基地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这些岛屿将为设置间谍飞机侦查南海提供绝佳之所。”⑲Anne Barrowclough,“Obama Opens New Front against China with Reinforcements for Australian Ally,”The Times,March 28,2012.6月2日,《泰晤士报》以《美国将海军力量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为题报道称:“美国海军力量的60%将会部署在太平洋地区,而只留下40%在大西洋地区,并将向亚洲盟友与军事伙伴介绍雷达规避喷气式飞机、新型轰炸机、反潜飞机等新技术……这是华盛顿从欧洲和中东向亚洲转变策略最引人瞩目的实际行动。”⑳Richard Lloyd Parry,“US to Move Naval Power from Atlantic to Pacific,”The Times,June 2,2012.在8月6号题为《内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应带头应对中国的军事实力》报道中,《泰晤士报》称:“中国弹道导弹和潜水艇等军事装备的获得,已经在澳大利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造成一种不安全感。美国总统奥巴马之所以计划到2017年在澳大利亚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正是出于打消地区盟友不安和焦虑的心理。”㉑Sophie Tedmanson,“US Marines in Outback Spearhead Response to China's Military Might,”The Times,August 6,2012.
最后,越南与菲律宾等南海主权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推行的不合作与对抗性政策,也是南海问题升温的又一因素。在报道2011年越南国内的反华示威游行活动时,《泰晤士报》称:“越南的反华示威游行活动在越南官方媒体中被报道,说明其背后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允许和支持。”㉒Richard Lloyd Parry,“Vietnam Fury over Chinese Oil Rig,”The Times,May 14,2014.“中国主张一对一处理领土争端,但越南却坚持欢迎外国介入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㉓Victoria Richards,“More Anti-China Protests in Vietnam as Row Escalates,” The Times,June 19,2011.在报道2012年中菲“黄岩岛事件”时,《泰晤士报》认为:“菲律宾在这次冲突中的表现较中国更咄咄逼人,尤其是菲律宾决定派遣军舰去黄岩岛海域抓捕中国渔民,而中国则只派出了海监船。”㉔Anne Barrowclough,“China Denies Preparing for War Against the Philippines,”The Times,April 12,2012.在2011年6月19日的报道中,《泰晤士报》称:“中国和其他五个国家之间争夺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导致南海局势升温。越南已经宣布征兵并举行海上实弹演习;菲律宾派遣军用飞机飞越其所宣称拥有的主权区域……对手们部署海军舰艇、勘探船只、钻井平台和渔船船队以争夺南海丰富的渔场和潜在的能源储备……对中国来说,和其他亚洲声索国就资源问题达成和解并不容易,因为南海资源价值高,其他声索国已经下定决心去开采。”㉕Michael Sheridan,“China Sails in Search of Oil,”The Times,June 19,2011.
尽管《泰晤士报》认为南海问题的升温是多种因素所致,但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首要因素,而美国的干预以及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对抗被认为是应对中国崛起之举。在《泰晤士报》看来,中国的崛起及军事力量的增强引起了南海周边国家的担忧,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为了保护盟友,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而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则是在美国的介入下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由此看来,尽管《泰晤士报》标榜“新闻自由、客观报道”,但它在叙述事件发展时,总是带有一定的选择性和倾向性,以突出某些细节和省略部分事实而导向鲜明地暗示自己的立场。经过精心剪裁后的关于南海问题的新闻素材经过长年累月、连篇累牍的报道,给受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南海问题再度升温的责任主要在于中国。
(二)对中越、中菲海上重大冲突的报道
随着美国的不断介入,越南和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愈加频繁。《泰晤士报》对中越和中菲之间的海上冲突作了较为详尽的报道,但观察冲突的视角与切入点存在差别,对于冲突原因的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导向性。
1.对中越海上冲突的报道
自1988年南沙海战以来,中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总体保持缓和关系。但这一维持了20多年的稳定局面到21世纪初被打破。2011年5~6月相继发生非法侵入中国管辖海域开展油气作业活动的越南石油勘探船只与中国海监船发生碰撞事件以及越南动用武装军舰非法驱赶在中国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民事件。事后双方除外交抗议外,还都在各自海域举行了实战演习。越南国内甚至爆发了持续数周、蔓延全国的反中游行集会。一时间,形势迅速恶化,使得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陡增。但《泰晤士报》并未就两起冲突进行全程及后续报道,只于6月12日的一篇题为《越南以实战演习来回击与中国的冲突》的报道中,在介绍越南决定于13日举行军事实战演习的时候,简略提及了二者。而对于越南国内爆发的反华示威游行,《泰晤士报》则在12日、14日和19日给与了专门报道。在12日的报道中,《泰晤士报》对其进行了一般性介绍:“反华示威游行似乎要波及全越南,上周数百名反华示威者在河内中国大使馆外进行了抗议活动。”㉖Rebecca Seale,“Vietnam Stokes China Row with Live-Fire Drill,”The Times,June 12,2011.14日的报道继续对抗议活动内容展开详细描述:“周日,在首都河内和胡志明市,数百名越南人游行示威谴责中国,有消息显示这至少被当局默认批准的。几百名示威者高举写有标语‘打倒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属于越南’的横幅在河内中国大使馆前高声和平游行,之后又前往市区的还剑湖。”㉗Richard Lloyd Parry,“South China Gambit May Push Beijing's Neighbours Toward Us,”The Times,June 14,2011.19日的报道则通过民众的口吻表达越南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越南反华抗议已经持续三周,加剧了争议海域紧张局势。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离河内中国大使馆不远处街区游行示威,高喊‘打到中国’、‘抵制中国货’的口号……20岁的学生阮孟河说:‘如果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将会为之战斗。不仅仅是我,所有的越南人都会誓死保卫我们的领土……参加过1979年越中短暂边境战的82岁老兵阮龙说:‘今天我来参加游行示威的目的是为了保卫我的祖国不受中国侵略。我相信中国大使馆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听我们‘打倒中国’的口号。”㉘Victoria Richards,“More Anti-China Protests in Vietnam as Row Escalates,” The Times,June 19,2011.《泰晤士报》由表到里,由浅入深,逐步渲染了越南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华情绪。
2014年5月2号,中国企业所属“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开展石油钻探活动,但遭到越南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大批船只强力干扰,并冲撞现场执行护航安全保卫任务的中国政府公务船只。《泰晤士报》并没有对这一事件进行全程报道,而对这一事件所引发的越南国内反华示威游行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从14~17日连续四天,《泰晤士报》对其进行了密集报道,其中14日3篇、15日2篇、16日3篇、17日1篇。在这些报道中,《泰晤士报》一方面记录了越南反华示威游行活动的内容,同时将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如在17日的报道中,《泰晤士报》称:“中国仍不愿接受在南海主权争议海域设置油井行为而导致暴力的批评。”㉙Leo Lewis,“Chinese Workers Hide from Vietnam's Rampaging Mobs,”The Times,May 17,2014.在27日报道中,《泰晤士报》称:“在过去的几年中,北京在宣称拥有整个南海主权方面越来越咄咄逼人——对于被日本控制的东海岛屿也是如此。”㉚Richard Lloyd Parry,“Tensions Worsen as Vietnam Blames China for Sinking Fishing Boat,”The Times,May 27,2014.
《泰晤士报》关于中越海上冲突的报道回避事件本质,过分渲染越南国内盛行的民族主义情绪,既营造了越南民众对中国不满之情的氛围,又塑造了越南政府维护海洋利益坚定决心的形象,同时向读者传递了中国在冲突问题上应负主要责任的信号。《泰晤士报》仅从越南视角窥探中越南海冲突,忽视中国政府和平处理冲突的呼吁,对冲突原因的产生原因缺乏性理性分析。实际上,无论是2011年还是2014年的中越海上冲突,越南国内外政治外交形势的变化才是冲突发生的根源。㉛具体分析参加赵卫华:《越南的南海政策及中越关系走向——基于国际法与区域外大国的分析》,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46-55页。因此,《泰晤士报》在该问题上的报道不利于受众对中越南海冲突事件实质的合理认识。
2.对中菲海上冲突的报道
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在21世纪初爆发的海上冲突,莫过于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冷战终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拥有黄岩岛主权未表示异议。1992年,菲律宾前国家安全顾问哥勒斯妄称菲律宾拥有黄岩岛主权,挑起两国争端。其后,菲律宾依仗与美国稳固的军事政治联盟关系,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不断寻衅滋事,多次抓捕中国渔民。《泰晤士报》关于中菲海上冲突的报道,侧重于菲律宾在黄岩岛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的原因分析。
一方面,《泰晤士报》认为美国对菲律宾的外交支持对于中菲冲突起到推波助澜作用。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欲在南海中沙群岛黄岩岛附近抓扣中国渔民,被及时赶到的中国海监船制止,双方随后发生对峙。第二天,《泰晤士报》就以《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对峙》为题对此进行报道。报道认为:“由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不久前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缓和中国在东南亚地区侵略所造成的紧张态势,要求东南亚的新兴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有‘建设性’的角色”,㉜Anne Barrowclough,“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in Stand-Off in South China Sea,” The Times,April 11,2012.菲律宾因此才敢在黄岩岛事件上与中国对抗。17日,《泰晤士报》发表题为《随着中国展示军事肌肉,太平洋地区形势紧张》的报道认为:“虽然美菲以打击穆斯林和共产主义叛乱及得到基地组织支持的激进分子威胁”㉝Dvika Bhat,“Nervousness as China Flexes Military Muscles in Pacific,”The Times,April 17,2012.为名举行联合军演,并且极力否认针对中国,但本质却在于回应中国对黄岩岛问题的行动,“这加剧了紧张局势”。㉞Dvika Bhat,“Nervousness as China Flexes Military Muscles in Pacific,”The Times,April 17,2012.另一方面,《泰晤士报》指责中国国内吁战舆论是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因素。4月12日,《泰晤士报》发表《中国否认对菲律宾准备战争》的报道,除了渲染黄岩岛事件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形势外,报道称:“(中国)政府支持的小报两周前要求中国通过一场‘小战争’来对抗菲律宾……《环球时报》社论宣称南海地区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一旦冲突爆发,中国必将采取坚定的行动。”㉟Anne Barrowclough,“China Denies Preparing for War Against the Philippines,”The Times,April 12,2012.22日,《泰晤士报》再次以《中国以军事行动威胁美国》的报道称:“中国因为美菲两国16日于黄岩岛海域举行的军事演习而被激怒,解放军的喉舌——《解放军报》称,美菲联合军演将会导致南海问题走上军事对抗和通过武力解决的岔路。”㊱Adam Thorn,“China Threatens US with Military Action,”The Times,April 22,2012.
《泰晤士报》对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措施激进化的原因分析,虽然认识到了美国于其中的刺激因素,但也忽略了菲国内政治派别斗争与能源利益需求在其中的推动作用,尤其是未能就菲律宾所提出的南海权益主张依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泰晤士报》未能跳出西方政见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窠臼,渲染中国国内非主流战争舆论对冲突的催化作用,忽略中国政府克制自我行动和言辞以避免局势升级的努力,以及通过开展对话和平解决分歧的呼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为菲律宾的无理行为开脱。
总体来看,无论是报道中越海上冲突还是中菲海上冲突,《泰晤士报》都缺乏将越、菲两国实际国情与当今大国全球战略博弈背景相结合的分析,由此造成未能对冲突的根源展开实质性梳理。《泰晤士报》无视有关方面的对话与呼吁,这无益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三)对中国吹填工程的报道
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展吹填工程早非新鲜事,但这一事件在2015年开始引起各方关注,《泰晤士报》也不例外,相关报道数量达15篇。最惹人注目的是,报道附有多幅卫星拍摄到的不同岛礁吹填工程进展画面。《泰晤士报》将填造的岛礁称为“沙洲长城”(great wall of sand)㊲Leo Lewis,“Us Attacks China's‘Great Wall of Sand'as Threat to Neighbours,”The Times,April 11,2015.或“沙城”(sand city),㊳Leo Lewis,“China's Sand City Emerges from Sea,”The Times,April 21,2015.并对这些岛礁上中国方面的建设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泰晤士报》对南海岛礁吹填工程的关注点集中于岛礁应用目的、各国关注原因及这一活动产生的影响。
《泰晤士报》认为,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实行大规模吹填工程的目的主要出于军事考虑。2月20日,《泰晤士报》以《中国在争议岛礁建立要塞》为题,援引一位专家分析称:“这些要塞距离中国大陆有600英里,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只能局限于军事战略。”㊴Jamie Fullerton,“China Builds Fortress on Disputed Reef,”The Times,February 20,2015.报道同时指出:“南海岛礁要塞网的建立增强了中国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将会对飞越南海上空的飞机进行身份识别。”㊵Jamie Fullerton,“China Builds Fortress on Disputed Reef,”The Times,February 20,2015.4月11日,一篇题为《美国攻击中国的“沙洲长城”是邻居的威胁》的报道同样认为:“中国大规模的吹填工程已经将一系列热带小岛屿变成潜在的军事前哨。”㊶Leo Lewis,“Us Attacks China's‘Great Wall of Sand'as Threat to Neighbours,”The Times,April 11,2015.
关于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开展吹填工程引起各国关注的原因,可以从《泰晤士报》在2月份报道中引述一名西方外交家的评论中一窥究竟:“这些吹填工程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规模更大、更野心勃勃。随着这项工程的进展,以后我们在许多不同方面对抗中国将变得异常困难”。㊷Jamie Fullerton,“China Builds Fortress on Disputed Reef,”The Times,February 20,2015.显然,西方国家将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展吹填工程视为未来在南海地区进一步扩张的准备,其关注原因是为密切掌握该项工程活动进展的最新状况,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对抗中国。这不单是西方国家看待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写实,在本质上也符合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衡中国目标。
对于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开展吹填工程所造成的影响,《泰晤士报》认为这引起了担忧中国“侵略”行为的南海周边国家恐慌,菲律宾尤其如此。“有个在填的岛礁离中国南部有1000英里,而离菲律宾只有300英里。”㊸TomCoghlan,“SatelliteImagesShowChina'sSecretIslandAirstrip,”TheTimes,April18,2015.“菲律宾怀疑中国正在将这些岛礁变为可以容纳军舰、而且有适合军用飞机跑道的军事基地。”㊹Leo Lewis,“China's Sand City Emerges from Sea,”The Times,April 21,2015.“菲总统阿基诺三世称中国的行为增加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将引起全世界的担忧。”㊺Tom Coghlan,“Satellite Images Show China's Secret Island Airstrip,”The Times,April 18,2015.不仅如此,作为菲律宾长久稳固的盟友,美国并没有坐视不理菲律宾的诉求,“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中国正在凭借块头和肌肉强迫其他国家处于从属地位。”㊻Leo Lewis,“Us Attacks China's‘Great Wall of Sand'as Threat to Neighbours,”The Times,April 11,2015.除了口头要求中国停止开展吹填工程外,“美国还拟定派遣军舰和飞机挑战中国在南海争议岛礁建设的飞机跑道,这增加了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㊼Michael Evan,“US Navy Set to Confront China over Island Bases,”The Times,May 14,2015.
《泰晤士报》对中国在南海部分岛礁开展吹填工程的报道偏重于其军事能力的发挥,过分渲染中国在南沙群岛修建设施对南海周边国家造成的威胁。实际上,开展人工岛礁及设施的建设主要是为各类民事需求服务,以更好地履行中国在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海洋科研、气象观察、生态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包括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此外,《泰晤士报》对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侵占中国的部分岛礁开展建设工程活动绝口不提,无视两国在岛礁进行建设军事基地的行为,表明其在该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与偏见毫无根据,同时也是基于对越南和菲律宾两国行为的默认与袒护。
总体而言,《泰晤士报》在就南海问题升温原因、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上冲突、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展吹填工程等事件进行报道之时,秉持“中国威胁论”的立场,倾向于将南海问题产生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强调中国在应对南海问题上的举措是南海局势趋于紧张的首要原因,辩解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合理性,忽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克制与维护南海地区稳定的努力。从报道产生的影响来说,《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不仅无助于有关国家和平解决南海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为美国等域外国家进一步插手南海问题制造舆论,大开方便之门。
三、《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的特征
自2010年以来,《泰晤士报》就南海问题做了大量报道,从这些报道的议题及内容等方面看,其报道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是报道素材的选择性。“新闻具有选择性是媒介可以影响公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媒介权力的一个来源。”㊽郭永虎:《近代泰晤士报涉藏报道初探》,载《西藏研究》2010年第6期,第98页。新闻素材的选择依赖于媒体的自我取决,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公众对事件的认知。《泰晤士报》在涉南海问题报道的素材选择上进行了精心安排,以期凭借自身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通过特定的报道素材,在传递自身对南海争端上观点的同时,又左右受众对南海问题的看法。从《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的报道类型来看,绝大多数报道都是有关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造成南海局势日益严峻、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外交干预、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的不满与抗议等等。在报道的内容上,《泰晤士报》避重就轻,很少涉及中越、中菲海上冲突根源及过程,而是更多地集中于越南和菲律宾对冲突的反应,同时忽略中国政府对和平处理争端的呼吁。在报道对象的选取上,对越南在南海争端中的报道所占比例远多于菲律宾。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新闻媒体为国家政治服务的特点。自卡梅伦政府上台以来,英国对越南的关系取得了长足进步。2010年,英越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 2011年到2015年,英国和越南共举行了四次战略对话等等。英越友好关系的发展通过《泰晤士报》的报道得到了明显的表达。
二是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过程中,受制于时代以及身份框架的制约,并不能摆脱思维意识的局限,总是会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沦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机器”。《泰晤士报》虽然标榜“客观、独立”,但实际上不可能客观到脱离当时的政治经济关系,成为超越国家、民族、价值观认同的国际性报纸。“当重大国家问题产生之时,《泰晤士报》就必须采取鲜明的立场,并且有可能的话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推广。”㊾Stephen Koss,The Rise and Fall of Political Press in Britai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360.《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并未从第三方视角出发,以一种客观的观点看待南海局势,反而不断宣传“中国威胁论”,紧紧围绕着中美之间的政治军事博弈展开报道,始终强调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是引发地区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故意塑造美国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形象。实际上,《泰晤士报》的这一报道方式正是迎合了英国政府的政治诉求。自卡梅伦政府上台以来,英国为了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逐渐加强和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东南亚诸多国家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必然会引起了卡梅伦政府的兴趣。仅2011年7月至11月,时任外交大臣黑格就四次发表外交声明,除了表示“美国仍然是英国实现国际目标的最强大伙伴和牢不可破之盟友”外,还希望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㊿William Hague,“Britain's Foreign Policy in a Networked World”,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britain-s-foreign-policy-in-a-networked-world--2.(上网时间:2015年5月23日。)虽然与中国有紧密的贸易联系以及巨大的合作潜力,但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怀疑与忧虑,其“对华政策基调很难超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争夺权力与利益的窠臼,将会始终包含遏制中国的因素。”马晓云:《卡梅伦政府对华政策评述》,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9期,第31页。因此,这也就解释了《泰晤士报》为何不遗余力地刻画中国“恃强凌弱”的面孔以及美国对南海地区介入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正如《泰晤士报》所言:“当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崛起问题是通用的。当新兴大国崛起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期待和需要更大的区域或全球角色,并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空间。这样的过程发生在19世纪晚期,当时的德国和日本变得更强大和野心勃勃。至少,我们从中国的例子中可以获得经验。”Bill Emmott,“If the US Plays by the Rules,China Might Too,”The Times,September 24,2012.
三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萨义德指出:“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指东方学)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5页。长久以来,西方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中有关东方的许多理解与行为仅仅是凭借西方人脑海中早已形成的固化思维模式进行处理。这种思维模式即“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8页。因此,在欧美国家政治中,西方社会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应居全球主导体系的思想长期盛行不衰。而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中又起着重要作用。“大众媒介提升、延展了一些意识形态观念,通过它们,这些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合法,传播起来很有说服力,甚至是富有魔力的。”[美]詹姆斯·罗尔,董洪川译:《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页。
《泰晤士报》以西方视角身份审视南海争端,忽视南海问题所牵涉各方的战略复杂性,在南海主权归属问题上既不做历史分析又缺乏法理依据,宣称为维护南海地区航行自由与安全,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应当就南海问题发挥应有的责任与作用。《泰晤士报》的论点与行为反映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即西方国家作为全球经济秩序与战略格局的建立者和主导者,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区域安全上的责任是名正言顺且不可推卸的。然而,西方国家仅凭自我理性思维与行事风格加以想象和实践,忽视区域行为体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舆情,不顾有关国家多次拒绝与严斥,执意对相关形势发表不合适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西方霸权主义行为。
四、《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的影响及对策
不可否认的是,《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误读和扭曲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外部世界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主流媒体的描述与传播。南海问题是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因划界不明而产生的主权纷争,其争端由来已久,并非一蹴而就。《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缺乏对争端缘由的追溯,视中国之崛起为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未能意识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本质及其对越南等南海主权声索国在处理南海争端方面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分析有关报道的时候,作者倾向于引述中国的国防建设,如中国第一艘航母试水成功、试图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沙岛礁开展吹填工程等。《泰晤士报》过分渲染中国的国防建设,臆测中国的军事战略,将中国塑造成超强大的“军事机器”,视越南和菲律宾为受欺负的“弱小”国家,扭曲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作为在西方世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泰晤士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读和扭曲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西方社会大众在心理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其消极作用不可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对英国政府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思(Allan Nevins)在论述《泰晤士报》对英国政治发挥的作用时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泰晤士报》一直都是英国政治结构中完整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该报存在一些琐碎的新闻,但其整体一直强调重要的公共事务,着眼于英国最大利益。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泰晤士报》的编辑们长期以来一直和唐宁街10号保持密切联系。”Allan Nevins,“American Journalism and Its Historical Treatment,” 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36,No.4(Dec.,1959),p.414.《泰晤士报》对英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决定了她必然会影响到英国政府于南海问题的决策。
英国政府于南海问题立场的转变深刻地反映出这一实际。近期以来,英国政府就南海问题频频发声。2015年1月,外交大臣哈蒙德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时则称,“英国支持亚洲基于规则,而不是基于权力的秩序……地区争端应该通过谈判和国际法,而不是通过武力或威压解决……如果该地区(指南海地区)政治和军事紧张导致安全局势恶化的话,我们随时准备向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Philip Hammond,“Foreign Secretary's Speech on the UK in Asia Pacific”,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foreign-secretarys-speech-on-the-uk-in-asia-pacific.2016年1月7日,哈蒙德访问菲律宾,并就中国在南海岛屿新建机场进行试飞时表示:“任何企图对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上的航行和飞越进行限制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危险信号’。”《美英越菲结伙非议中国南海试飞》,参考消息网,2016年 1月 8,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60108/1048031.shtml1月8日,英日两国在东京举行“2+2”会谈,双方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表示:“反对大规模填海等威吓性、单方面行动,要求采取克制”。《外媒:日英2+2会谈高调插足南海》,参考消息网,2016年 1月10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60110/1049308.shtml可见,经过《泰晤士报》连篇累牍式的涉南海问题报道,南海问题的进展不断地社会公众中传播,媒体舆论的集中“轰炸”“使没有列入政府议程的问题列入议程,使排在后面的议程排在前面”,范士明:《“CNN”现象与美国外交》,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第37页。政府的外交决策因之发生了变化。此外,媒体信息的广泛传播也促使政府的决策更加公开、透明,“国家更容易被渗透,越来越不暗箱了。维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级秩序越来越困难。”[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因此,《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的广泛传播也使英国政府在对南海问题上的决策不再遮遮掩掩,对其抛出相关立场的时间起到了加速作用。
针对《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对国际舆论及英国政府外交决策产生的影响,中国政府应当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首先通过大众传媒在国际社会上构建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体现国家内涵与精神的直接“名片”,其正负与否,直接影响国家间政治实践、外交联系与文化交流等。西方社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即使在现今社会也并非完全清晰,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凭借自身丰富的传媒资源,通过传媒舆论长期丑化中国形象,同时也与中国传播资源基础薄弱,缺乏国际性大媒体有关。针对《泰晤士报》扭曲和误读中国国家形象的现实,为扭转其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就《泰晤士报》所频繁援引《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以及《解放军报》等中国媒体话语来看,这些在中国有着较强社会公信力的媒体应当肩负起构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重任,积极加入中国所参与的全球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建立公开、独立、透明、迅速报道和分析信息机制,刘康:《如何打造丰富多彩的中国国家形象》,载《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第4页。避免因信息滞后而引起谣言造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读。(2)在现有媒体态势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增强实力,打造可读性强、可信度高的权威型国际性媒体,提升对国际舆论的掌控力。同时利用这种强大的舆论影响力,“迫使”其它西方媒体对新闻内容进行转载和传播,进一步扩大舆论范围。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第9页。(3)要避免空、大、虚的宣传方式,提高传播技巧,增强信息活力,敢于创新,乐于尝试在对外传播中使用国外受众习惯接受的风格与表达方式。在内容相同的前提下,通过不一样的方式而受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刘继南、何辉:《当前国家形象构建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第36页。(4)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重大活动,积极承担应有责任,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开展民间互动,推动文化教育交流,改善青少年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总之,完善对外信息传播体系,建设高效宣传机制,增强与世界各国进行良性互动与理性沟通,将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眼光融合为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门洪华,周厚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及其传播途径》,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第14-15页。才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打消因中国崛起而造成的西方社会忧虑心理。
其次是中国政府应主动公开及时更新新闻信息。从《泰晤士报》对《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性质的定义可以看出,西方媒体对中国带有官方色彩的信息传播媒介表现出质疑的态度。因此,它们总是寻求第三方较权威渠道获取信息源,严怡宁:《中国民族问题在西方媒体中的冲突框架及应对》,载《对外传播》2011年第4期,第8页。而此类信息的来源与性质往往因功能属性等原因无法完全用以佐证。如《泰晤士报》所展示的中国在南海岛礁开展吹填工程的部分卫星图片来源于《简式防务周刊》,虽然其信息分析在西方媒体和政府中被视为权威,但其关注焦点侧重于军事与安全防务。如果仅依据《简式防务周刊》拍摄的南海岛礁吹填工程介绍,就会陷入断定岛礁上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为中国发展强大军事行动能力的误判。实际上,这与中国政府信息未能及时公开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采取过于保守的态度,就很容易造成渴望信息的外国媒体与有备而来的肇事者达成议程一致的结果。”严怡宁:《媒介事件化的中国民族问题——对<纽约时报>2000年以来中国民族问题报道的研究》,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63页。外交部有关南海岛礁建设活动的信息,往往是在例行记者会上采取“记者提问——发言人回答”的被动模式进行对外公开。而许多信息在此之前已经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被炒的沸沸扬扬,各种猜想和谣言因中国政府信息的迟滞公布而甚嚣尘上,影响到西方民众对事件本来面目的认识。因此,中国政府在应对重大事件以及突发事件之时,可以采取主动提供信息,及时更新信息,多次扩散信息,以及允许自由采访等方式向西方媒体及民众展示事件本原,避免引起无端猜测,有损国家形象。
第三是加强中英双方经济合作。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利益的大小决定国家行为的程度。英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虽然不时语出惊人,但南海问题并非英国国家核心利益。从中英两国关系大局来看,南海问题不过是英国政府对华关系的一个抓手而已,经济合作才是英国对华关系中的核心部分。卡梅伦政府上台后,立即表示出迫切希望扩大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意愿。2010年11月,上任半年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即率领“最豪华代表团”访华,其中包括商界领袖50余人,商业大臣、财政大臣等4名内阁大臣。中英双方签署了数十亿英镑订单,包括一系列经济和文化教育协议、金融领域改革与发展研究合作协议。卡梅伦在北大演讲时表示:“我们需要和中国在贸易、投资和对话领域有强大的联系……只要可以,我们就希望尽可能多的和中国开展贸易。”David Cameron,“PM's Speech at Beida University,China”,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pms-speech-at-beida-university-china.(上网时间:2015年7月12日。)2013年12月,卡梅伦再度访华,这次更是率领7名内阁大臣和150多名工商界领袖的史上最大访华团,规模是10年首次访华的3倍。中英双方在贸易、文化等领域签署了40多项协议,金额高达56亿英镑。卡梅伦表示:“中国的崛起不仅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机会,而且对英国和全世界来说也是如此”,“开放的英国对开放的中国来说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比英国对中国的投资更开放。”David Cameron,“UK and China's Long-term Relationship:Prime Minister's Speech”,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uk-and-chinas-long-term-relationship-prime-ministersspeech.(上网时间:2015年7月12日。)因此,中国政府应牢牢把握住英国对华关系中的核心部分,不断扩大深化中英双方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明确掌握主动权,使英国在关乎其整体外交格局中的关键领域对中国产生依赖性,进而促使英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有所顾忌,不敢轻易插手。
第四是管控中英双方外交分歧。中英双方在外交层面交往的最大阻力为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香港问题。尽管两国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前景比较乐观,但这三者仍然是横亘在中英关系中的巨大障碍。2010年5月,英国联合政府上台后即发布5年规划纲要称:“将会和中国寻求更紧密的合作,但在所有的双边关系中都坚定地支持人权。”“The Coalition:Our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p.20,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3820/coalition_programmefor_government.pdf.(上网时间:2015年7月10日。)此后英国外交部多次发布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说三道四;2012年5月,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执意接见达赖喇嘛,引起中国政府强烈不满,双方关系一度陷入僵局。12月,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施维尔(Hugo Swire)称,对西藏地区的人权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确保外交使团、国际媒体和有关各方能够无限制地进入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其他藏区。”“UK Has Serious Concerns about Human Rights in Tibet”,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has-serious-concerns-about-human-rights-in-tibet.(上网时间:2015年7月10日。)在香港问题上,自1997年香港回归至2015年2月,英国政府以每年两份的数量,共向议会提交了36份《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内容涉及香港该年度发展状况及英国政府的态度。在香港普选问题上,英国政府同样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2014年7月10日,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称:“世上没有完美的普选模式。重点在于任何方案都应给予香港人民以真正的选择,让他们感觉到能够真正主导自己的未来。”“The Six-monthly Reports on Hong Kong:1 January to 30 June 2014”,p.3,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28978/HONG_KONG_Six_Monthly _Report_Final_Version2.pdf.(上网时间:2015年7月10日。)可见,这三个问题并不会因为中英经济密切合作而在短期内得到化解,稍微处理不慎,不排除英国政府会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施压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政府应抓住卡梅伦政府积极寻求与中国扩大经济合作的契机,深化双边交流,增进相互信赖,加强务实合作,建立事务磋商和工作协调机制,敦促英国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合理管控双方外交分歧,最大限度减小英国政府打南海牌的可能性。
总之,《泰晤士报》涉南海问题报道既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舆论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政府的对华决策。中国政府在向国际社会加大良好国家形象宣传、主动公开及时更新新闻信息的同时,又要牢牢把握好中英双方关系的核心部分,审慎处理可能引起双方关系僵化的外交分歧,以尽量避免南海问题由于西方媒体的渲染而走向国际化。
张 鹏,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硕士生。刘金源,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