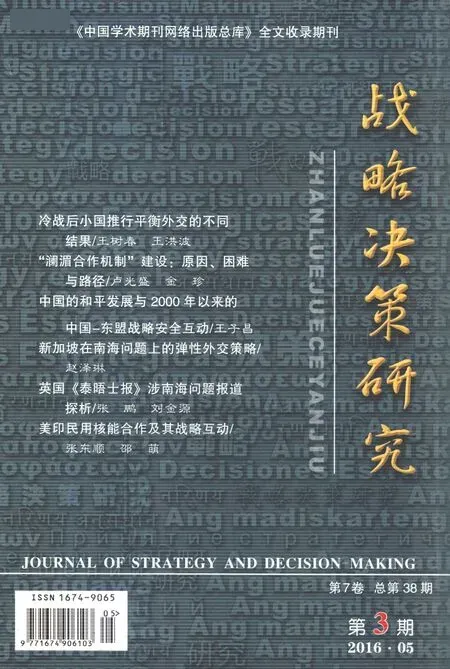中国的和平发展与2000年以来的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
王子昌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2000年以来的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
王子昌
2000年以来中国和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主要背景因素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为了表示自身和平发展的决心,在东盟的要求下,与东盟联合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主动倡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与东盟达成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合作协议,与东盟一起发起促成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机制。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方式在分析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时遇到的难题启示我们,跳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分野,运用新的安全分析范式,可以对200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给出一个一致的、合理的解释。
安全互动;和平发展;安全方式
本文将对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背景进行研究。这里所说的东盟,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这里所说的战略,是就一些问题的重要性、整体性和长远性而言的,也即这些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从长远和整体性讲,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所说的安全,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定义的军事安全,而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安全,与此相对应的,不安全包括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或脆弱性。也许一些问题本身不是安全问题,而是一种经济贸易问题,如长期的贸易赤字,抑或仅仅是因为贸易上过于依赖一个国家,可能导致的对一个国家的过度依赖,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就可能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因此中国东盟围绕这些问题的互动也成为本文的考察对象。
本文认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对双方来讲,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与经济发展,具体到安全事务而言,互动的目的在于,找出或建构出双方在一系列安全事务上的最大公约数,或说最大的共同利益,并通过相应的机制,将其固定下来。依据这样一种理解,笔者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构成了推动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最主要的背景因素。
如果以2000年至2015年间的16年作为一个观察时段,那么可以认为,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变化当属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要展现自己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路径,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了解自己和理解自己,支持自己,就必须要与其他国家进行一系列的互动。对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安全互动的背景,国际关系的几种理论都进行了解释尝试,以图找出双方互动的主要推力。
在中国-东盟的战略安全互动研究中,自由主义范式用的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中国-东盟的经济互动研究中。这种研究范式通常使用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完成之后可能对双方经济活动效率的影响,以论证中国倡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双方签署相关协议的合理性。这一研究范式潜在假定具体的经济利益是推动双方战略互动的主要动力。如果是这样,就很难解释,在签署自贸区协议时,中国为什么愿意主动做出让步,规定“早期收获条款”,让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农产品在自贸区建成之前率先以低关税或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
阿米托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试图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把中国东盟之间的安全互动作为“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影响力的具体个案,分析日渐崛起的中国如何通过互动最终认同了东盟的行为规范,按照这一理解和推论,中国-东盟安全互动的主要推力是“东盟方式”(ASEAN Way)的吸引力和中国的学习热情。如果像阿米托夫所言,经过多年的互动,中国已经认同了“东盟方式”,那么近年来中国用武力捍卫南海权益的系列举动就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中国的学者张哲馨博士则试图从安全观念入手,认为正是由于东盟安全观念的变化,使200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2010年以前为相对和谐的一段,以后为相对不和谐的阶段。张哲馨博士认为在2010年之前东盟奉行的是合作安全观,在2010年之后,东盟奉行的是均势安全观,具体体现为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正是东盟安全观念的变化使得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态势发生变化。因此,张博士认为必须“以‘升级版’新安全观引领中国-东盟安全合作”。①张哲馨:《新安全观与中国—东盟安全合作》,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5年4月,第210页。安全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范式所假定的国家的最主要的目标,张哲馨博士把安全观念作为影响国家行为选择的最主要的变量,因此可以将其研究归为现实主义的研究谱系。
笔者不认同张哲馨博士的看法。笔者认为,东盟奉行的合作安全观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有的只是东盟安全战略依据一些具体问题和安全形势的变化而作的具体调整。东盟建立伊始就明确自己奉行积极的“中立”外交政策,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在大国关系中搞平衡。依据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很难依据东盟的安全观念变化作为将中国-东盟安全互动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笔者认为,2010年战略安全合作中的不和谐也只不过是双方战略安全互动中的一个正常表现,即通过互动,修正自己对地区安全问题的理解。笔者在对背景的分析中也不遵从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做法,依据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分析方式,对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背景因素进行归类,而是试图依据巴里·布赞(Barry Buzan)提出的安全分析范式,对这一背景因素进行分析和梳理。
本文的分析和论证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分析中国和平发展的提出及其对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影响。和平发展是中国的大战略,一切国家的行为选择,包括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互动必须从这一战略出发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二是分析近两三年以来日渐清晰和明确的“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与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影响。三是对既有的研究范式和相关推论进行分析,提出一个超越的分析范式。最后,依据以上的分析,对全文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决定中国东盟战略互动的主要背景因素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可以追溯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和平发展战略的一种具体体现,即通过对国内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这一思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和路径。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中国在1991年—冷战格局解体不久—就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②1991年7月,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代表东盟邀请钱其琛以东盟主席国外长嘉宾身份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开幕式,并与6国外长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议,以此拉开了中国—东盟对话的序幕。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上开始了对话与合作。1994年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可以看作双方战略安全互动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广泛的关于安全问题的对话,化解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于中国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的疑虑,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外资进入中国和中国贸易对外扩展的有利的环境,东盟也需要这样一个机制,扩展“东盟方式”的影响,通过对话,理解其他国家的战略和政策意图,化解可能的冲突,维护对自己有利的和平与安全环境。总的来说,中国由于自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参与多边机构的经验也不多,因此在1998年之前中国在与东盟战略安全互动中,主动性不是很强。1997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点。
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在危机之时,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不通过贬值刺激自己的出口提振中国经济,不使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这一举动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好感和信任,也让中国有了一种大国的意识,中国政府意识到,作为大国,中国应该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与东盟的安全互动中,中国也呈现出更多的主动性。
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可能会影响到东盟国家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为了打消东盟国家的顾虑,中国政府总理朱镕基率先倡议,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经过研究、论证和谈判,2002年中国和东盟在柬埔寨首都金边(Phnom Penh)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这也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为了打消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顾虑,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世界贸易大厦的恐怖袭击、2003年的萨斯病毒的传染、2004年海啸对东南亚的袭击使中国意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形势的影响,因此又与东盟签订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合作宣言和协议。③如2002年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中国-东盟非传统合作宣言》(Declaration of ASEAN and China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2004年在泰国曼谷签署的《中国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等。2003年中国作为域外大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2005年中国又与东盟一起参与发起了东亚峰会,一个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综合性论坛。
中国和东盟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一系列互动,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在外交上的具体要求和体现。2005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根据白皮书,中国采取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今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不仅如此,中国还以自身的努力和成就促进了世界和地区和平,首先中国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是对周边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一大贡献,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其次,在其他国家遇到危机时,中国自身的稳定和中国对遭受危机国家的援助和救助也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主张“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通过合作尽可能消除或降低恐怖主义活动、金融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应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略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应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④中国新华社网站: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22/content_3954937.
2011年9月,中国政府又发表了《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做了更为完善的表述。⑤人民日报网站: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19.html关于与周边的合作,白皮书提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友好的方针,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从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一个必然要求。
在该白皮书中,中国政府重申,“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通过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和东盟倡导的综合安全理念以及通过合作与对话寻求和平与安全的具体做法也是一致的。⑥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在战略安全互动中的主要难题是南海问题。造成这一难题的不是双方的安全观存在差异,而在于东盟一些成员国企图绑架东盟,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一贯坚持:南海问题是中国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的问题,应该通过双方的直接对话和谈判解决问题。笔者认为,东盟在《2013年东盟安全展望》中加入“南海争议已成为地区安全重大威胁”的表述也没有什么不妥。从其具有的外溢影响来看,南海争端确实已经成为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和东盟在这一问题上或许有不同的立场,但这不会严重影响中国与东盟在其他安全问题上的合作。
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影响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会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从其提出的背景来看,中国提出这一倡议的目的就是期望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文件形成的一个重要文献就是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讲话:《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在该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阐释了预期可以提升中国东盟战略互动水平几个重要因素:同东盟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有共同追求;在维护地区繁荣稳定上有共同利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有共同语言;对丝绸之路原则和精神的解读也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相关预期。
对丝绸之路原则和精神的进一步解读,可以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和平发展路径的更为具体的阐释。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倡议书,虽然对“一带一路”进行了某些设想作了详细阐释,但对“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和平与发展意义仍然阐释的不够清楚。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只是点到为止。
例如,张蕴岭教授曾提出,“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认识,‘一带一路’是我国作为上升大国坚持不走传统大国争霸、称霸的老路,而走开放、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新的和平发展道路的体现。为何要借用丝绸之路这个词?因为,古丝绸之路所代表的精神,也可以称之为‘丝绸之路精神’,可以最好地体现这些理念和原则”。⑦张蕴岭:《聚焦“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7月 31日。http://www.cssn.cn/jjx/jjx_gd/201407/t20140731_1274694.shtml但这“一带一路”战略怎样如何具体地体现这一点,张教授却并没有予以展开分析,笔者将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分析。
首先,是对历史上丝绸之路本质与精神的解读与分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关国家的和平交往之路、共同致富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之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是帝国靠坚船利炮打出来的侵略与征服之路,它是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生命危险,船载马驮探索开辟出来的;商人的财富不是靠强取豪夺,而是通过互通有无,满足人们的众多需要;在这条路上,也有官员和军队,但军队和官员不是为了侵略和征服,而是为了传播信息和文化;在互通有无的过程中,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表现在语言、服饰、建筑、制度、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吸收和融合。
今天我们提倡“一带一路”,不是因为怀旧,而是历史上的“一带一路”跟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恰好契合:中国要走和平发展之路。
其次,是对和平发展之路进一步展开的具体要求。中国政府多次通过政府文件表明,中国将走一条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靠武力侵略和征服崛起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学者也纷纷著文对这一立场和表态进行演绎和分析,从逻辑上论证其可能性。但可能逻辑上是一回事,实际上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计划。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可以说很好地弥补了中国和平崛起言说中缺失的一环:中国将通过参与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换取资源和市场。
在这一计划和倡议的实施中,资源不再是拿回中国,而是就地转化为产品用于当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也不是拿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品去挤占,而是销售本地生产的产品。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它可能无法再用GDP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可能需要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标准。这样的一种思路既可以减少中国自然资源的损耗,减少污染,也可以减少商品输入和输出可能导致的国际经济冲突。由于当地国家需要,也可以减少竞争可能带来的其他冲突,在此过程中,不仅可以为当地政府带来税收,也可以为当地社会创造就业,为当地社区创造便利,真正地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和平发展。笔者认为,这样理解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它可能会影响东盟之间的凝聚力,即中国可能会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使用分化瓦解东盟。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如何分配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基金?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的主要设想是希望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贷款投资,带动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优先在哪些国家、投资哪些基础设施建设,这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即它可能成为中国政府通过投资诱使其他国家政府服从中国意志的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很可能就会影响东盟作为一个外交共同体在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上立场的一致性,或者说,让东盟在一些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上无法形成一致的外交立场,用一个声音讲话。在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上,站在一致的立场,用一个声音讲话,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对当事方施压,让当事方采取克制,这是东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主要影响力所在,如果中国利用其主导的亚投行和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基金,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东盟一些成员国施加压力,对东盟来说,无疑是关乎东盟生命力的战略安全难题。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对东盟成员国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也有利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有利于缩小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有利于减少成员国内部的贫富差异,有利于经济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建设。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作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其提出的目的也在于提升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水平,但究竟会对东盟的共同体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双方在这一问题进行深入互动。
三、超越传统研究分野,以安全范式解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背景
在中国与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过程中,中国有时相当主动,如主动倡议与东盟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有时又会表现得相当被动,如迟迟未能与东盟在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方面取得进步。如何理解这种迥异的表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试图从相对独立的变量出发,对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安全互动行为进行解释。
现实主义主要依据权力变量对国家行为进行解释,认为一个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权力,在无政府社会中以自己的力量生存与安全。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行为主要取决于该国在各国综合实力排行榜中的地位。一个国家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增加自己的权力,一是增强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二是与他国结盟。增强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既可以通过侵略、兼并他国的办法,也可以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与他国结盟,既可以通过与主要的大国和强国结盟,以阻遏可能的入侵,也可以与弱国结盟,通过数量上的优势对大国挑起局部争端进行外交上的限制。从实力、性质上讲,东盟是一个弱国之间的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协调组织(虽然根据其规划,它已经宣布建成东盟共同体),其主要的力量在于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投票权数和协调统一的大市场的潜力。依据这样的解释,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安全互动的目的主要是建立于自己有利的外交盟友,以争取可能的资源和市场。依据这样的逻辑: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会在与东盟的战略安全互动中可能表现得越来越任性:当中国需要时,中国就会努力推进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当中国不需要时,中国就会将其晾在一边。这样的一种解释,存在逻辑上的混乱不清和结论上的多重性,即什么样的结论都是可以的。
逻辑上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实力的界定不一。专家曾经努力试图界定实力,从最初单纯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硬实力、到现在包括文化软实力、领导人决策力等在内的综合实力,到现在也没有达成共识,学者们在谈论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概念时,仍然是用GDP、军事开支作为主要指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使用简单明了的概念,仍然会存在问题,这里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实力和行为之间的简单对应。国家的实力和决策、具体的外交行为并不存在一个机械的、简单的对应关系,中间存在一个大大的黑箱有待开解。具体到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安全互动,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简单对应关系:随着中国的日趋强大,GDP从2000年的1.2万亿美元,到2015年的11.4万亿美元,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2/weodata/weorept.aspx?sy=2000&ey=2015&scsm=1&ssd=1&sort=country&ds=.&br=1&pr1.x=58&pr1.y=3&c=924&s=NGDPD&grp=0&a=#download军费开支从2000年的146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1294亿美元,⑨凤凰网数据:http://news.ifeng.com/mil/special/2015zgjf/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安全互动越来越淡化。不仅没有如此,随着中国的日趋强大,中国反而更公开地向东盟示好:强调与东盟的共同利益,要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根据现实主义的分析范式,这是难以理解的。
如果说现实主义未能对中国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那么自由主义也未能对这一战略安全互动提供有力的解说。自由主义主要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一个国家的行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会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但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会考虑其所面临的各种制度约束,在各种制度约束中,一个国家会选择一种最优的策略。该理论还认为,制度本身也是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国家行为体讨价还价的结果,制度的达成就代表着一种国家间利益的暂时均衡,国家的互动就意味着国家间就制度不停地讨价还价,因此制度也呈现为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
把自由主义运用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分析,可以推论出如下结论:中国之所以积极与东盟就战略安全问题与东南亚进行互动,是因为中国是东盟主导的一系列多边合作制度的受益者。同时中国也想通过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改革和创新制度增加自己的收益。自由主义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与东盟战略安全互动中的一些现象,如积极推动“东盟加三”会议论坛、与东盟一起创立东亚峰会等。但有些现象则难以解释:为什么会主动倡议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而且在后来签署的协议中,规定了“早期收获”条款,在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前,让老挝、柬埔寨,缅甸等落后国家的农产品率先以低关税或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从以上的分析看以看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安全互动问题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作为一种分析理论,自由主义还假定国家的偏好是既定的,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国家没有大小、文化、历史的差异,而事实是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性,即使都同样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其对何为最大利益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追求这种最大利益的政策选择也可能不同,这也是自由主义在解释国家的行为选择时经常会碰壁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中,建构主义理论是运用的比较多的,阿米托夫·阿查亚对东盟方式的研究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建构主义主要是从身份和认同的角度研究一个国家的行为,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会有某种行为,是因为其自觉认同某种身份或制度。对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分析认为,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地区一系列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就是其他国家通过与东盟的互动逐渐认同了东盟方式的结果,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表现,为了能够成为东亚峰会的成员国,每一个国家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与合作条约》。依据这样的一种理解,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的背景主要应该是中国通过观察和学习逐渐认同了东盟的基本制度和东盟的行为方式。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区分一个国家对某种身份和制度的认同是真正的认同还是对制度的投机性利用,具体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如果是中国真的认同了“东盟方式”,中国为什么经常企图用强力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笔者以为,以上三种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方式在解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问题时都会在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因此笔者这里尝试借鉴巴里·布赞提出的安全分析范式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对其他各种分析范式遇到的问题给出一个统一合理的解释。
在《人、国家与恐惧》一书中,巴里·布赞企图提出一个与现实主义权力研究平起平坐的安全研究议程,更具体地说,巴里·布赞企图为国家的安全行为选择提供一个通用的解释公式。总结巴里·布赞在该书中分析和论述,其安全分析范式的主要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坚持以国家安全为分析的核心
坚持把国家安全放在国际体系中加以考察,注重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对国家安全选择的影响。
(二)巴里·布赞认为,依据国家间互动的密度、国家间共识的多少、互动规则的多少及其被遵守的程度,可以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划分为不同的成熟状态。处于不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的主要着力点不同。
在没有多少共识和行为准则、互动密度不大的极不成熟的无状态,国家边疆安全的主要任务是军事安全,即国家名下的政权、领土、人口不被他国的军事力量征服或消灭。在互动密度比较大、有着较多的共识和行为规则的相对成熟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的重心可能更多地要向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倾斜。即使是同样的领土安全问题,不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的任务也有所不同。
在不成熟的无政府状态,领土安全的主要威胁是他国的军事入侵。而在相对成熟的无政府状态,领土安全的主要威胁可能是敌对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民族主义宣传及其造成的领土分裂。
(三)坚持国家安全的相对性
国家安全是国家间互动关系中一种相对的状态。它不仅取决于自己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而且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变化。即使一个国家在发展变化,但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发展的快,他也可能会感受到威胁。即使其他国家没有发展变化,自己的相对衰落也会让一个国家感受到威胁。
(四)对国家的强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在巴里·布赞的安全分析框架中,国家不再是一个除了权力大小而没有其他区别的行为主体,而是由具体的领土、人口和某种国家观念聚合而成的一个个具体的行为主体。依据其聚合的程度,可以将国家分为强国家和弱国家,国家的强弱不同,对同一问题的安全感知也不同。依据这样一种这样的安全分析范式,可以2000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战略安全互动的背景表述如下:
由于西部地区的落后、台湾一直未能得到统一、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因此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国把自己在很多的时候定位于一个弱国家,这和东盟成员国对自身的定位基本是一致的,对自身的安全问题十分敏感。在两极格局解体后,中国坚定地把自己融入国际社会,同东盟展开了密切的战略安全互动,以期构建一种相对成熟的无政府状态,改变自己面临的安全问题的形态;中国意识到国家安全的相对性和弱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敏感性,因此通过一系列政府文件,表明自己和平发展的决心,并主动提倡议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也正是由于对安全相对性的清醒的认知,中国在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以后,不但没有抛弃东盟,淡化与东盟的往来,反而提出,要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帮助亚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同时也认识到,和东盟的密切互动,只是改变了一些争端问题存在的环境,但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其他国家并没有予以理会,因此中国不得不在某些时候,以强力显示中国维护南海岛屿和海域的相关权利和利益。
基于以上分析为基础,笔者尝试总结如下:2000年以来中国和东盟战略安全互动的主要背景因素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为了表示自己的和平发展的决心和满足自己和平发展的需要,在东盟的要求下,与东盟联合发表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主动倡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与东盟达成了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合作协议,与东盟一起发起促成了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机制。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方式在分析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互动时遇到的难题,并启示我们跳出传统的研究范式,运用新的安全分析范式,可以对200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安全给出一个一致的、合理的解释。
王子昌,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东南亚安全格局对我国家安全战略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