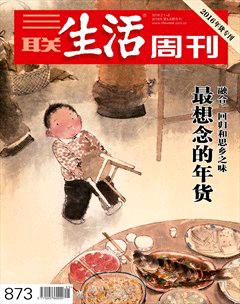一别经年难再见
张峿脩

对于旅居北美的人来说,头年10月到次年2月这段日子,既短且长。10月的万圣节,11月的感恩节,12月的圣诞节,1月的元旦,2月的春节、元宵、情人节,有人欢天喜地生怕浪费了一个调剂饕餮的由头,有人百爪挠心过鬼门关一样难挨。
年前,朋友携出差兼探亲的太太来小住,这位先生厨艺颇精,到了见家里只备了牛排青笋,便小试身手,添了道海鲜意大利面——虽然不是西餐拥趸,但那十字花刀切的鱿鱼我也是很久没见了。接下来几天是烤肉、褐菇香肠焖饭、鲔鱼饭、培根青口,龙虾刺身、清蒸、煮粥三吃收尾,天南海北,都算是“美漂”党摸索出来就地取材又方便可口的吃法。沾了这位太太的光,我过节总算不用绞尽脑汁就饱了口福,撑着闲着就想起从前。
新年,还是应该有雪的。
我和这对朋友,是在纽约读书的时候相熟的。这位先生跟我同校,但是家远在布鲁克林深处,当初他还没碰到他后来的太太时,四个小伙子住在一起,他们家是一群大学校友过年聚会的地方。这边年轻人聚会,如果不买外卖,往往就是火锅、烤肉、包饺子这几样,方便量足,宜调众口,况且谁都能来搭把手,至于烤鸡烧鸭炖鱼做席面这种事,看心情看体力三两年来个一次就不错了。后来我一路向北,发现也大同小异。这位先生是成都人,火锅自然是讲究的,有两年,白汤要现烧,红汤底料要现炒,至于后来发展到意大利面要现擀,已经是后话了。有一位朋友是天津人,某一年做的油爆板栗让人念念不忘,他平时话很少,有一年醉了第一次听到他骂娘。另两位是我的老乡,一位常常泡实验室跑长岛,然后买菜回来,任凭大家打趣他漫长的感情纠葛,另一位经常通宵打游戏,白天睡觉,有时候晚上会爬起来打牌,是个中高手。那些年常来常往的朋友,随着毕业散落各地,一别经年难再见。
菜不够的时候,会去附近的Di Fara Pizza买一张比萨。这是纽约一家传奇老店,1959年开业,长年被各种杂志评为纽约最好吃的比萨。门脸有些平民区的落魄,镶在门楣上的空调总是滴水,下面拿个脏乎乎的塑料桶接着,里面破破旧旧三五张桌子,十几个座位,然而初榨的橄榄油满手留香,新鲜从窗口菜圃里揪下来的罗勒(Basil)叶味道凛冽醒脑,五六种意大利奶酪混成一种朴素传统浑然一体的味道,一种形容不出的魔力。店主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来的老大爷,当年就已经七十几岁了,说是每张比萨都要亲手做,孩子们只许打下手。其实每次去布鲁克林都想吃一块,并不常能如愿,也总在想不知道是他先不做,还是我先离开。结果自然是我先走了,辗转各地一些年,不后悔,常遗憾。多少事,也不知道自己是执念太多还是太少。
有一种说法,在一个城市生活五年,对它会有家乡的感情,我在纽约和北京都恰巧待了五年,没到七年之痒就离开了,所以总是抱着一种温和善良的怀念。比如我没有经历北京这几年的雾霾、沙尘暴、地铁发水、三环堵车,所以连想起来首都机场出来空气里亲切的烟火味,夜里树杈苍苍凉凉地伸向天空,打车路过长安街,两边楼顶上的乌鸦都是好的,到了三里屯想的是如今再找不到的那些小饭店,不是朝阳群众。比如我一过圣诞节,总能想起刚到纽约那两年,过节去洛克菲勒中心逛街,花坛里的灯饰是吹号角的天使,第一次听着电音版《卡罗尔的钟声》看Saks Fifth Avenue灯光秀的震撼,还有冰场里刀划冰面的声音,让我想起大学的湖,想起家乡的运动场。至于鞋踩在泥泞的残雪里湿透,回家时鞋跟又卡在地铁通风口拔不出来的事情如果飘到脑子里,我就自动切换到老家干净的积雪,穿着棉鞋走路,咯吱咯吱总像是有人陪着,鼻毛还是会冻起来,但走着走着,胸口就有一团热气。
我很小的时候,每到过年就要赶火车去爷爷家。冬天里匆忙归家的人潮如蚁,外加菜市场里称斤要两的此起彼伏,算是最有年味的,纵然不见得美好。偶尔站台上路灯下飘着雪花,不用打光构图,就是电影镜头。那时候上火车像是打仗一样,我记得不止一次我被举到窗口,不认识的叔叔伸手把我拽进去。有时候没有座位,妈妈就搜寻瘦子,然后央求人家,说让孩子搭个边儿。有时车上太挤,远途站了太久的人撑不住了,在过道、门口,甚至洗漱间坐了一地。爷爷家在一个山城,记得要爬好一阵子台阶才到。靠钢厂吃饭的城市,在没有雾霾的当年,似乎星星也很少,夜里黑漆漆的,仰起头就看到一幢楼的灯光叠着另一幢楼的灯火,连着天上偶尔蹿起来的烟花。万家灯火听起来温馨,其实从小我就知道,幸福是很难的。
年饭我没什么印象,倒是有一次火车上,我见到对面的人吃枇杷,第一次见,直勾勾地盯着,最后人家没奈何地给了我一个。那时候南方的水果在东北很少见,我自然不知道金黄色的枇杷也算是应了新年的景,有的只是尝了新鲜的心满意足,记了20年。家乡最有特色的应景“甜点”大概就是冻秋梨和冻柿子,从屋外拿进来,硬实实结着一层冰,扔在水盆里解冻,拿出来吃的时候,还是冰得牙齿一阵刺痛。搁到《舌尖上的中国》里面,估计也要说,一口下去,酸甜冰爽的汁水溢满口腔,解酒解腻,这是自然的馈赠与中国人勤劳经验的结晶。在这方面,我的胃并没有那么怀念家乡,所有跟牙齿作对的美食我都不太热衷,比如过年前后才有的黏豆包,热气腾腾,金黄色,带着苏子叶的香气,只是太黏牙了。其实,那年头的平民百姓不过是想尽了办法,在天寒地冻的地方,找到些让日子稍微不那么清苦的办法。怀念总是带点幻想,我记得更小的时候,姥姥家还有院子,院子里码着酸菜缸、酱缸、咸鸭蛋缸,还腌着几坛子的黄瓜、茄子、豇豆、胡萝卜丝,酸得爽快,咸得干脆,定义了我对这两种味道的概念。然而,冬天去缸里面捞菜真是件苦差事,女人的手,因此变得红肿粗糙。
后来年夜饭就是三口人了,父亲会叫我去帮忙贴对联,然后定了中午的菜单和晚上的饺子馅,就开始和面剁馅儿、卸肉洗鱼、准备炒菜。妈妈负责炖菜和打下手,总归会有个小鸡炖蘑菇,有个炖马哈鱼,似乎缺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就不叫年菜了。其实我记事以后,也并不见多少人对这两道菜怎样热爱,既然过年总是要吃的,只好在材料上下功夫,榛蘑和白蘑要问朋友找山里野生的,鱼最好是松花江得莫利打的,鸡就得是乡下亲戚送来货真价实的走地鸡,有时也换换野鸡,早年还有飞龙。家乡的菜,若论做法讲究,其实乏善可陈,可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总比我待过的其他地方要淳厚彻底很多,不知为什么,黄瓜、蘑菇、豆腐、油豆角、蒜苗、韭菜、羊肉、田鸡、鲫鱼,离开家了,味道总似乎不够鲜、不够香、不够正,于是总有些怅然若失,不如吃当地的东西。总是下午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做新年总结,晚上要拜年,吃饺子前要去放鞭炮,吃完了要去放烟花,换新衣服,看看电视,年俗随着年纪渐长也懒得麻烦了。年初二去姥姥家总是高兴的,可以跟弟弟妹妹玩儿,替大人去买酒,剩下点零钱,可以收压岁钱,可以肆无忌惮地看电视,地方台那几天会一天七集播电视剧,看得昏天黑地,我还记得万人空巷的张无忌版《倚天屠龙记》和老版《还珠格格》,大人们忙忙碌碌聊着天做饭,七手八脚地抬出大桌面,摆座位,按辈分长幼敬酒拜年,面红耳热,然后再急忙凑上麻将桌痛快过把瘾,一转眼,年就这么过去了。一年又一年,有时平静有时糟心,匆匆忙忙,居然就这样过去了这么多年。
如今住在西岸,雪是没有的,天气凉凉的,超市里应有尽有,只多不少,逢年过节就摆着兰花和富贵竹,也人头攒动,然而似乎总透着一点匆忙和憔悴,不像记忆里国内那么鲜活而有生气。想来总归是人跟人,挨得不够近,牵绊得不够紧,散落在异乡,抱团取暖,却总还要警觉着,如何能暖和呢?办年货,放鞭炮,祭祖烧纸逛庙会,皆不得行,种种情绪,似乎只有食物可以寄托,“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