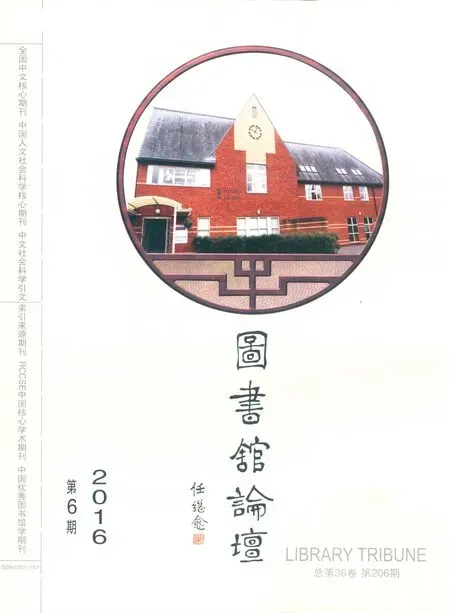ILAS三十年(1985-2015):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
陈定权
ILAS三十年(1985-2015):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
陈定权
摘要文章利用历史研究法系统梳理ILAS近30年的发展脉络,总结和分析ILAS的成功因素、历史影响、目前的市场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为研究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绝佳案例,对ILAS的全方位研究可以为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参考。
关键词ILAS 自动化系统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集成系统
引用本文格式陈定权. ILAS三十年(1985-2015):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J]. 图书馆论坛,2016(6):34-42,26.
1985年10月,在深圳市委指示下,深圳图书馆(以下简称“深图”)起草了《深圳图书馆电脑应用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设想方案》)[1]。《总体设想方案》是专门针对当时正在建设的深图新馆(红荔路)而提出的,指明了深图计算机应用的发展方向——建立图书馆集成系统。鉴于此,本文将该方案视为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ntegrated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ILAS)的早期理论探索,而1986年开始研制的流通管理系统则是早期实践探索。这样,从1985年算起,到目前ILAS正好30年。ILAS曾“引领全国图书馆步入自动化”[2],见证了我国信息化早期发展历程,在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疑是研究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史的绝佳案例。在ILAS而立之年对其作全方位和历史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历史研究法,系统梳理ILAS从1985年至2015年的发展脉络,试图从多元视角来客观评价ILAS,分析其成功经验和失误之处,展望ILAS的未来,期望为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参考。为论述方便,本文提及的“ILAS”特指具体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项目”则是指为研发ILAS而推出的工程项目或科研项目。所谓项目(Project),是指那些临时性、一次性的活动[3]。所以,ILAS项目有明确的目标,在时间、费用和资源等约束条件下实现预期的目标,跟深圳市科图自动化新技术应用公司(以下简称“深科图”)日常对ILAS系统升级维护等运作是不同的。
1 ILAS立项初期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市场
集成性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并非一蹴而就,它由早期的单功能系统演化而来。所谓单功能系统,是指实现图书馆某一个业务功能的系统,如编目系统、流通系统,各系统之间的信息无法共享。因为MARC标准研制早,国外是“以联机编目带动图书馆自动化”[4],而我国大体上是以流通系统带动图书馆自动化,这与我国当时缺乏书目数据标准有关,解决流通业务问题更有着现实紧迫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实现集成化、实用化和商业化,出现了专门为图书馆研制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商业公司[5]。商业化系统的出现使图书馆能专注于资源建设和服务质量的提高。经过多年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基本上不再独立研制软件,更多的是作为功能需求方来深度参与系统开发过程,引入商品化系统。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研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大约是1978年[6]),也起步于单功能系统。因为当时的中文处理技术尚未成熟,这些系统只能处理西文文献,但为后来的自动化系统研制奠定了基础。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发明了中文字符处理技术(1980年颁布的GB 2312- 80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是基础性工作),在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流通业务难题后,图书馆的自动化需求集中迸发。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研制进入蓬勃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图书馆先后引入中型机、小型机和PC机(当时也称为单用户微型计算机)。当时系统研制有两个技术方案:一是基于中(小)型机的“主机-终端”(host-terminal)模式,二是基于PC机的单机模式。前者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采用HP 3000/39小型机开发流通系统,后者如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采用IBM PC/XT开发流通系统[7]。20世纪80年代我国制订了一些基础性标准,如《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GB 2312-80)、《书目信息交换用磁带格式》(GB/T 2901-82)、《文献著录总则》(GB/T 3792.1-83)、《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GB/T 3792.3-85),也有了UNIMARC中译本(1986面世,1992以此为基础推出CNMARC)。这些标准有力地推动了自动化、标准化、网络化、集成化的进程[8]。至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国外尚未成功研发汉字处理技术,客观上为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研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孕育期,保护了我国尚处于襁褓之中的自动化系统。在“主机-终端”时代,国外系统业已实现商业化,但价格昂贵且不支持中文字符,而处理中文字符是我国研制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关键,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尽快研制出支持中文字符的系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研制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与国外同期的系统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当时的学者评价说,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应用水平低,软件研制未走向商品化,标准化程度不高,书目数据库建设未形成规模,配套设备与技术跟不上,更重要的是没有统一规划,低水平重复研制现象较严重[9];各地图书馆及相关单位闭关自守、各行其是,重复开发研制低水平低效率产品的现象比比皆是[10-11];我国实现集成系统的集成度是有限的[12]。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大环境下,面对图书馆迫切的需求与缺乏统一标准规范的现实,由国家主导研制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成为图书馆界最普遍的诉求。
2 ILAS发展历程回顾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研制进入了积极探索阶段。1988年前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正在或已经研制出自动化系统[13],ILAS则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需要说明的是,深图1987年是以“图书馆集成系统”名称立项,后来改为“集成图书馆自动化系统”(Integrated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ILAS),最后在正式立项时,根据中文行文习惯,改为“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英文则不变。ILAS中的字符“i”就是为突出与早期单功能系统的不同,强调“集成”特征。ILAS本来是一类系统的泛称,最后演化成一个具体系统的专有名称,ILAS在我国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1986年12月深图(红荔路)正式开馆。1985年深圳市委领导作出了“深圳图书馆开馆时,一定要让读者使用计算机查找书目和借还图书”的指示,这间接印证了我国“以流通系统带动图书馆自动化”的技术发展路线。《总体设想方案》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中央书目数据库”。1986年深图优先启动(光笔)流通管理系统的研制工作。1987年6月由文化部主持举办鉴定会,鉴定委员们建议在流通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研制具有先进水平的图书馆集成系统。鉴定会结束后,深图邀请部分鉴定委员咨询和探讨“图书馆集成系统”立项与研制等问题,与会专家呼吁文化部支持“图书馆集成系统”的立项和研制工作。由此,ILAS正式进入深图的视野。
经过多轮咨询论证,1988年1月文化部决定把“图书馆集成系统”项目列为文化部重点科技项目,研制期限为1988年1月至1990年12月。深图时任馆长刘楚才于1988年1月13日签订《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重点科技项目任务书》[14]。至此,由国家倡导、深图牵头研制的ILAS项目被正式提上计划日程,深图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研制工作。
1988年12月文化部主持召开总体方案论证会,确定《总体方案》。1990年4月ILAS研制成功(ILAS 1.0)。经过17个不同类型的用户馆使用,深图自身全面采用(转型期为1991年4月到11月),待其达到实用程度之后(ILAS 2.0),才在1991年11月召开产品鉴定会。鉴定会认为,系统的各项技术指标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久ILAS项目被列为文化部重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产品鉴定会的召开标志着ILAS正式定型。那时的ILAS,后来更多地称为“多用户版”(主机-终端模式),一直发展到5.0版。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客户机/服务器(Client/Server,C/S)技术的成熟和成功应用,“主机-终端”模式逐渐让位于C/S模式。技术环境和用户需求的变化让ILAS有了升级换代的压力和动力。1996年ILAS项目组提出研制ILAS第二代网络版产品的计划。1998年深科图在ILAS 5.0的基础上推出ILAS II。1998年5月文化部相关单位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ILAS II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从“多用户版”发展到C/S模式的“网络版”,ILAS II顺应了时代发展和技术潮流,到达了历史巅峰。
1997年开始,我国兴起了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热潮。2001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将国家重点科研课题——“数字图书馆应用平台及网络架构研究与开发”(简称dILAS,也就是后来产品化的ILAS III)下达给深图。dILAS是我国“十五”期间数字图书馆攻关计划项目,希望开发出在网络环境下运行的,既包括传统业务与管理,又体现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与读者服务特色的集成化通用数字图书馆应用平台及其产品。1998年深图新馆(莲花山前)正式立项。dILAS项目能够落户深图,跟深图新馆立项与建设大背景密不可分,可以说dILAS是为深图新馆保驾护航的,后来它也是赶在深图新馆正式开放(2006年)之前通过鉴定。2003年深圳提出的“图书馆之城”建设进一步修正了ILAS III的需求设计。
2005年,dILAS通过文化部鉴定。深科图以dILAS为基础,推出了产品化的ILAS III。ILAS III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图书馆解决方案和实用系统,图书馆用户可以通过它提供的功能和技术进行资源整合与服务整合;ILAS III也可以作为一个构件,通过统一的协议加入数字图书馆体系[15]。ILAS III最大的变化是:彻底放弃后来饱受争议的专用数据库LDBMS(在C-Tree基础上开发出图书馆专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采用通用数据库管理系统Oracle。目前除ILAS III外,深科图还推出了针对总分馆制的基于B/S系统和云平台的面向小型图书馆的系统。
ILAS III推出的时代是群雄并起的时代。1999年就在全国投入使用的江苏汇文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汇文”)的图书馆管理系统LibSys;2005年通过鉴定的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图创”)图书馆集群管理系统InterLib;一直瞄准高端市场的国外先进的图书馆集成系统,如艾利贝斯公司的Aleph 500,都在挤压ILAS的市场空间。群雄并起的现实决定了ILAS III的推广应用不会一帆风顺。
纵观ILAS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如下特点:(1)体系架构基本跟上了技术发展的节奏,从最初的“主机-终端”模式到C/S模式,再到B/S与C/S并存以及云平台;(2)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放弃了专用的LDBMS,改为流行的Oracle,全面支持ISO 10646字符集,采用了XML、元数据,提供开放性访问接口等;(3)以图书馆传统业务为中心,不断重构技术体系和功能体系,尽可能满足图书馆和读者的需求,如联合编目UACN-UC、个人书架、读者推送、微信服务平台。
3 ILAS成功因素分析
ILAS一经推出,很快就在我国掀起第一轮的系统迁移浪潮[16],很多图书馆从自行开发的系统迁移到ILAS。毫无疑问,ILAS是成功的,取得了预期效果。ILAS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对ILAS成功因素的分析零星散见于深图人的回忆录、领导讲话和其他文章。笔者通过梳理辨析,从第三方的角度来分析ILAS的成功因素,并依次论述。
(1)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深图人的锐意进取。深圳特区为ILAS项目的研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科技创新环境和政治生态。ILAS项目的早期立项、资金安排、人才配备等,以及后来的鉴定会和发布会都得到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文化厅、深圳特区政府等鼎力支持。ILAS III的研制也是以“十五”规划期间数字图书馆攻关计划项目的名义而得以顺利开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作为一个软件研制项目,来自政府的支持力度和广度是罕见的。深圳特区特有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让深图人有着一种胸怀天下、舍我其谁的历史责任感,在改革浪潮中锐意进取。时任馆长刘楚才在其1984年出版的《在新浪潮中》有一段激情澎湃的文字:“只有那在浪潮中勇于追求和探索的人们,才可能有所创新和开拓。”[17]在他的领导下,深图在新技术浪潮下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
(2)科学决策是ILAS成功研制和推广应用的关键。ILAS的近30年历史中有四次重大决策左右其方向。第一次是ILAS的技术举措,即采用UNIX操作系统、LDBMS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C语言,这决定ILAS开发的成败,确保了ILAS的快速产品化并推向市场。第二次是延迟召开产品鉴定会,而不是举行成果鉴定会,也就是在17家用户馆和深图全面采用后召开产品鉴定会。这是“有关ILAS命运的一次重大而正确的决策”[18],为初生的ILAS的茁壮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赢得了成长的时间。第三次是深科图的成立,尽管当时是采取权宜之计的内部承包,但为后来的ILAS市场化和市场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ILAS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商业平台。第四次是彻底放弃LDBMS,全面拥抱业界通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Oracle,使得深科图可以更关注于发展着的业务和专用技术,也使ILAS具备了对外全面开放的数据基础。
(3)项目组成员知识结构科学合理。项目组成员既有来自高校图书情报学院(系)的专家,也有多年从事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技术的馆员,前者有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王大可、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的王林与赵洗尘等,后者包括原深图馆长刘楚才、原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数据库研究室主任沈迪飞、原深图技术部主任余光镇、原湖南图书馆软件组长朱光华、原湖北省图书馆计算机部副主任马瑞、原湖南图书馆采编部主任甘琳,以及当时20多位成员中唯一没有图书馆专业背景的技术专家刘明晶[19]等。简而言之,项目成员中既有具有丰富的图书情报理论背景的学界专家,也有奋斗在图书馆业务一线的馆员和IT技术专家,确保了技术与业务的完美融合。这一点完全契合信息系统界的“业务与技术融合”(Business-IT Alignment)的思想。
(4)独具特色的汉字处理技术为项目研制和推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汉字是象形文字,跟西方主导设计的西文字符处理技术截然不同。国外系统商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汉字处理技术问题,汉字处理技术成为当时国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进入我国市场的“拦路虎”。自1980年推出《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解决了汉字处理的关键技术[20],80年代末结束万“码”奔腾的汉字编码战国时代,宣告汉字输入技术问题成功得到解决[21]。汉字处理技术的成熟客观上催生出图书馆处理中文书刊的现实需求,支持汉字信息处理成为系统选型时的必备选项。
(5)商业化的运作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深图时任馆长刘楚才借改革开放春风,克服各种困难,1987年前瞻性地在全国率先成立深圳市科图自动化新技术应用公司,为后来的ILAS市场化和市场推广奠定了基础。在实施与推广中,项目组考虑到在商品竞争的时代必须尊重“市场的选择”,故将深科图作为推广ILAS的实体。而之后的事实证明深科图在从软件研制转换为产品推广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2]。
(6)对MARC的研究与支持是ILAS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无论是1985年的《总体设想方案》,还是1988年12月确定的ILAS《总体方案》,都一致认为“实现图书馆自动化最基本的条件”是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在当时还未制定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深图集5个图书馆的力量,用两年半时间完成当时全国最大的符合行业标准的6.5万条书目数据库,为之后ILAS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遵循MARC相关规范是ILAS成功的关键。自1986年UNIMARC中译本面世后,国内业界对UNIMARC的认识和接受度都逐步提升,开始讨论编制《中国机读目录通讯格式》,并积极实践。对国内外MARC相关标准的研究与采用,为ILAS的标准化、国际化从数据结构方面提供了保障。1992年正式推出的CN-MARC 给ILAS数据结构的选型吃了一颗“定心丸”。
4 ILAS的历史意义
ILAS不只是一个系统,更像是我国图书馆信息化的“图腾”。有着近30年发展历程的ILAS在我国图书馆信息化发展历史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原深图馆长吴晞在ILAS 20周年技术研讨会上评价ILAS是“一面旗帜”“一座里程碑”“中国图书馆的骄傲”“一所大学校”[23],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具体而言,笔者认为ILAS具有如下历史意义:
(1)填补了我国商业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空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信息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的生存尚且存在危机,不少图书馆以“有偿服务”来缓解财务压力,更别说采购动辄几十万美元的国外图书馆自动化软件系统。当时国外通行的图书馆自动化软件INNOPAC售价超过30万美元,每年维护费2万美元,而ILAS的售价仅5,000元人民币起[24],自然受到国内市场的热捧。尽管有不少高校图书馆尝试自行开发,但其适应性不够,持续发展乏力,无法满足图书馆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求。商业化的ILAS一经推出,图书馆就可以从市场上寻求技术解决方案,把关注焦点转向资源和服务。可以说是ILAS的研制推广才使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真正开始走向独立发展[25]。ILAS也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1998年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展出期间,ILAS被誉为“中国图书馆自动化的骄傲”。
(2)凝聚和培养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代图书馆技术人才。当时项目组由深图计算机部、外单位借调和从8个省市图书馆派来的技术人员共10人组成,包括深图的余光镇、吴晞,从其他单位借调或其他单位外派的有沈迪飞(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朱光华(湖南图书馆)、马瑞(湖北图书馆)、甘琳(湖南图书馆)、王林(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赵洗尘(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大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刘明晶(铁五局科研所)。这些图书馆技术人才是既精通IT技术也熟悉图书馆业务的两栖人才。同时,ILAS的推广使用和培训为全国数千家图书馆培养了多支高水平的专业技术队伍,现在他们已是各馆的技术骨干力量[26]。1992年沈迪飞编写的《图书馆自动化应用基础》在配合推广ILAS和培养人才方面颇有建树。可以说ILAS既是图书馆技术人才的汇集地,也是人才培养和人才输出的高地,将其誉为“一所大学校”是名副其实的。即便是现在,它也是图书馆界储备技术人才最多的地方。
(3)为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树立了成功的典范。第一代ILAS开发策略相当明确,经过多家用户馆成功采用后,才以产品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宣告ILAS项目的巨大成功,这是对当时全国“软件鉴定会就是软件追悼会”现象的强力扭转,为我国之后软件的开发与应用起到了典范作用,为我国研制更多更优秀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树立了标杆,也是向外界宣告:中国图书馆界也能够开发自己的软件产品!
(4)彰显图书馆人的事业责任感。ILAS的使命是“迅速提高全国图书馆自动化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它的研制并不是为了实现个别图书馆的自动化,而是为了推动全国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图书馆的现代化,故ILAS的研制是一项关系全国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人的事业,是图书馆人的共同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图书馆人在业务上本着“一切为用户馆”着想,精益求精;在工作中表现出忘我的干劲和感人的献身精神;在应用上同用户馆不仅是市场经济下的买卖关系,更多是为图书馆现代化事业而共同奋斗的战友式的合作关系[27]。
(5)以创新者的姿态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沉寂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八馆联合”的研制模式是文化科技方面的创新;从需求出发确定方案,从成功试用到产品定型是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研制流程的创新;在全国建立了几十个推广站,同用户共同推广是科技产品销售经营领域的新举措;在ILAS应用的同时,举办了从操作员到技术员再到管理人员、馆长的培训班,ILAS的推广应用推动了我国图书馆的自动化进程。这种全面创新既得益于深圳特区改革开放之新风,更来自深图人的锐意进取和拓荒牛的精神。
5 ILAS当前的市场困境及其成因
ILAS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巨大成功,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但在数字图书馆时代,ILAS受到国内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双重夹击,市场有所萎缩,面临着发展困境甚至生存危机。
随着电子资源在馆藏资源中的比重扩大,电子资源的管理已成为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与电子资源相关的系统,如2000年兴起的联邦搜索和链接技术(SFX/OpenURL、DOI/CrossRef),2002年前后出现、2005年开始在国外流行的电子资源管理(ERM),2006年前后兴起的资源发现等陆续登台。可以说第一代ILAS是为了快速响应国内市场需求,短期内推出自己的产品,有其时代迫切性,重点解决了市场上“有和无”的问题;ILAS II跟上了技术环境(C/S模式的采用)的变化(功能结构变化不大),以优化产品为中心,解决了“好和坏”的问题;ILAS III依然以图书馆传统业务为中心,并在传统业务基础上兼顾数字图书馆(侧重于网络化服务、电子资源服务),迟迟未推出链接解析、ERM、资源发现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则是战略失误,当然也可能是技术储备不足。国外三大系统开发商(艾利贝斯公司、Innovative公司、SirsiDynix公司)在链接解析、ERM、资源发现等方面将国内系统开发商远远抛在后面,这使ILAS III的核心竞争力在新形势下有所下降,流失了足以引领图书馆发展浪潮的高端优质客户,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等“985工程”高校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都是国外系统的座上宾。
随着“技术复制周期”的缩短,国内后起竞争者可以在短期内推出更契合市场的自动化系统。因为是后起之秀,没有历史遗留系统的包袱,可以借鉴先行者的经验和汲取他人的教训,快速响应需求,短期之内就可以推出产品。这些新出现的市场竞争者,如江苏汇文、广州图创,在总分馆制、图书馆之城、因高校合并而催生出的多分馆等项目推动下,拿下了不少市场份额。因为这些项目首先是在发达地区或重点高校发起,还具有市场风向标作用,在系统选型上,容易成为后行者的标杆,并逐渐形成抱团效应。例如,1999年推出LibSys的江苏汇文(江苏省教育厅控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参股组成)在高等院校中攻城略地,蚕食着高校图书馆市场;借东莞图书馆新馆建设(2005年9月正式开放)之机而顺势推出InterLib的广州图创在公共图书馆界也享有盛誉。尽管深科图位于珠三角地区,但珠三角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却没有为ILAS带来“红利”,东莞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等最终相继选择了InterLib。尽管这些后起之秀在链接解析、ERM和资源发现上没有更多作为,但因为契合用户的需求,稳步地蚕食ILAS的传统市场。
再者,我国已不存在类似于当年汉字处理的技术壁垒,国外系统很容易进入中国市场,横亘其中的唯有价格和服务水平。目前国外系统开发商中只有艾利贝斯在中国设有办事处并支持本地化开发,已经拥有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优质高端客户。
占据高端市场的国外系统(主要是Aleph 500)、在高校图书馆影响日盛的LibSys、崛起于城市图书馆(尤其是总分馆制)的InterLib,以及其他一些各具特色的系统(如重庆大学的AdLib)构成了ILAS系统的挑战。虽然开源系统搅动了国外图书馆市场,但在国内影响甚微,目前还不足为虑。
国内系统开发商在链接解析、ERM、资源发现上着力不多,这类系统大多由我国数据库商研制,这个姑且不谈。仔细梳理众多时间节点,我们会发现ILAS与后起之秀相比,对市场反应总是落后一两个节拍。例如,江苏汇文是在1999年正式推出LibSys(南京大学是在1998年底采用),而ILAS II则是在1998年5月推向市场。考虑到系统的研制周期,南京大学图书馆在系统市场调研和系统选型时,ILAS II正处在研发测试阶段。再如,东莞图书馆(新馆)的系统市场调研和系统选型从2002年开始,因为市场上没有适合的可供选择系统,就深度参与广州图创,共同研制InterLib,2005年开始使用,而ILAS III直到2005年4月才对外发布。也就是说,东莞图书馆在系统选型时,ILAS III的研发才刚刚起步。ILAS II之于LibSys、ILAS III之于InterLib,缓慢的研发节奏无意之中培养出两个最具竞争力的对手,为后来的ILAS困境埋下了伏笔。
另外,在市场经济下,ILAS推广应用逐渐失去文化部等政府部门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宏观上分析,这是我国行政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市场化日趋完善的必然结果。来自政府的支持是ILAS早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深图业务发展的需求是第一代ILAS和ILAS II的关键需求,而这些关键需求在当时代表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普遍需求,但ILAS III的需求则未能很好契合公共图书馆的普遍需求,遑论高校图书馆。ILAS III当时的研发重点是全面采用RFID,深科图更像是深图的技术部,是为深圳“图书馆之城”项目服务,确保深图“全面采用RFID,如期开馆”,ILAS III深深烙上了深图的印记更像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深图与深科图之间的深度捆绑早年成就了ILAS,后期则成为深科图的羁绊。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微观上分析,与“ILAS母体——深圳图书馆面临体制方面的改革和转型,人心浮动,前景不明”[28]有着极大的关系。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深图与深科图的深度捆绑、过分依赖政府的支持,以及深图体制改革与转型,让深科图弱化了当初“弄潮儿”的锐气和“执牛耳”的豪情,最早市场化的深科图如今却难以快速响应市场用户的需求。
6 ILAS的未来走向
曾经辉煌的ILAS现在依然是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但在国内外系统的双重夹击之下,ILAS的市场逐渐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分析ILAS近30年的历史和国内应用的现状,笔者试图探析ILAS的未来走向,也许会对其“王者归来”有所启示。2009年6月13日,深图主办ILAS 20周年技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对ILAS未来提出四点期望[29]:重点关注不断发展着的业务、服务平台的建设、多层次的产品体系和全球竞争。结合这四点期望以及当前市场和技术环境,笔者就ILAS的未来走向给出以下判断:
(1)在市场化环境下,改革深科图与深图之间的关系。未来的ILAS应该是属于图书馆界,而不仅仅是深图。近30年的ILAS发展历程中,第一代ILAS的立项和推广离不开权力的影子,ILAS III依然如此。图书馆界主导、政府支持、企业化运作,这种ILAS曾经成功的模式发展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ILAS发展的桎梏。ILAS III严重桎梏于深图的功能需求,几乎是为深圳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之城”定制的系统,尽管它也满足了大多数图书馆的需求。对政府的依赖以及对深图的依附,无法适应市场,饱受批评的售后服务、无法快速响应需求等,深科图与ILAS的影响力下降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赞助只能是“锦上添花”,而不应该是“雪中送炭”。唯有跳出现有的桎梏和依赖,未来的ILAS才能再次赢得市场的尊重。
(2)准确把握图书馆和读者需求并快速响应是ILAS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因为有多家大型图书馆深度参与,第一代ILAS对需求的把握和分析十分准确。ILAS II功能需求变化不大。2001年开始的ILAS III,以RFID为创新点和关键功能需求,则是严重偏离了绝大多数图书馆的需求,如RFID的超前设计、未能把握总分馆、多校区图书馆等迫切需求,消耗了有限的技术资源。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艾利贝斯公司提出URM框架以及2010年产品化的图书馆服务平台(Library Service Platform,LSP),宣称是新一代图书馆集成系统,值得深科图借鉴。未来的ILAS应该向平台化方向发展,推出服务平台,以期快速响应更多的个性化需求。深科图未来应聚焦于自己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与第三方内容供应商(如超星等拥有海量数字资源的公司)基于开放标准的深度合作可能是不得不采取的策略。2015年10月6日,信息解决方案供应商ProQuest收购系统供应商艾利贝斯集团[30],则是“内容为王”[31]的最直接证明,“内容”战胜了“技术”。艾利贝斯集团被收购的结局值得深科图深思和警惕。对图书馆而言,技术回归到工具属性,资源无疑是图书馆优先考虑的因素,剩下的则是服务。未来的ILAS能否在新一轮的浪潮中得以生存,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和快速响应目标用户的需求,尤其是“那些发展着的需求”[32],帮助图书馆重构新的服务体系。
(3)未来的ILAS的研制应全方位遵循相关标准规范。王雅丽在1998指出:“评价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此系统是否在标准化方面有所考虑。”[33]ILAS的成功得益于手工编制的遵循MARC标准的书目数据库。发展到现在,应从MARC标准拓展至全方位的标准规范。无论是在程序代码级、体系架构上,还是在系统的资源层以及服务层,未来ILAS都应尽可能支持或兼容相关标准规范。事实上,ILAS III对标准的支持力度还有待提升[34]。作为系统开发商,跟踪与研究相关标准规范应该是一项常规性工作,甚至应参与标准规范的制定或修订工作。
(4)在软件日趋同质化的今天,未来的ILAS应力求打造自己产品的竞争优势。所谓竞争优势,就是别人难以取代或短期内无法取代的优势。图书馆自动化产品体系有多个层次,未来的ILAS不可能在所有层次上参与竞争,深科图应尽快确定自己的竞争层次,突出自己的竞争优势。保证高质量的系统只能保持企业的竞争均势,如何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才是关键。早期ILAS的竞争优势是价格优势和本地化服务。在通用目的信息技术不断成熟的技术环境中,在全球化涌动的今天,竞争早已超出国家的界限,ILAS早就登上了全球化竞争的舞台。2009年于平指出:“我们应该从全球的背景下思考ILAS的优势,找准ILAS在国际同类产品中的位置。”[35]未来的ILAS要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思索自己的研发重点和目标图书馆,利用自己的竞争优势,在我国图书馆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环境下找到突破口,在我国自动化市场上占据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鉴于目前情况,放弃诸如“985工程”高校图书馆等高端客户,巩固和拓展数量更为庞大的中低端市场,可能是无奈之下的现实选择。
7 结语
客观来说,ILAS经过近30年历史,依然屹立在图书馆自动化市场,不能不说是图书馆技术界的一大奇迹。将ILAS置于历史视野下,笔者试图真实还原其发展轨迹,以一个独立学者的身份来客观总结其经验教训,科学探析其未来走向,期望为ILAS的强势回归提供现实参考,抑或为ILAS敲响警钟,防止出现深科图被内容供应商兼并的结局。同时,希望以史为鉴,为我国图书馆集成系统或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参考。作为中国图书馆界曾经的骄傲,ILAS的历史荣耀不只关乎深图和深科图,它未来的一举一动依然是中国图书馆业界和学界的关注焦点。
注释
①dILAS既是“数字图书馆应用平台及网络架构研究与开发”课题的简称,也是课题成果“数字图书馆应用软件平台”的简称。以数字图书馆应用软件平台dILAS为基础,深科图推出了产品化的ILAS III,两者关系非常紧密,甚至等同使用。这点可以从dILAS主要研制成员、深圳图书馆副馆长王林对dILAS的介绍和深科图对ILAS III的介绍上可以看出。请参考(a)王林. 数字图书馆应用软件平台——dILAS[J/OL]. 公共图书馆,2006(3)http://www.publiclib.org.cn/library/periodical_ show/1063.html.(b)深圳市科图自动化新技术应用公司. iLAS III数字图书馆系统[EB/OL].[2015-10-07]. http:// www.ilas.com.cn/?p=201.
②深圳图书馆以ILAS成功研制的日期1990年作为“ILAS元年”。
参考文献
[1] 余光镇. 忆ILAS立项前后[M]//吴晞. 时代的链接——深圳图书馆十五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45-51.
[2] 沈迪飞. 深图引领全国图书馆步入自动化[N]. 深圳晚报,2014-09-12(B06).
[3] 毛基业,郭迅华,朱岩,等. 管理信息系统:基础、应用与方法[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46. [4][13][33] 王雅丽.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的发展历程及今后的策略[C]//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新技术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选.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230-234.
[5] 李广建,张智雄,黄永文. 国外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现状与趋势[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3(3):33-36.
[6]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高校图书馆计算机应用交流会暨成果展示会纪要[C]//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高校图书馆计算机应用经验交流会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
[7]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新技术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选[C].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169-192.
[8] 肖红梅,钟贞山. 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综述[J]. 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7(6):80-86.
[9] ILAS项目组. ILAS的研制开发、推广应用及发展思路[M]//吴晞. 时代的链接——深圳图书馆十五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43-15.
[10] 余光镇. ILAS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发展进步的十年[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1999(S1):128-130.
[11] 谭祥金,危由军. 广东省图书馆自动化[M]//谭祥金,赵燕群. 谭祥金赵燕群文集.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262-284.
[12] 张忠友. 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系统的发展历程[J]. 大学图书馆学报,1990(6):17-20.
[14][17] 刘楚材. 深图创业史上弥足珍贵的篇章——ILAS系统诞生始末[M]//吴晞. 时代的链接——深圳图书馆十五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34-44.
[15] 深圳市科图自动化新技术应用公司. ilasIII数字图书馆系统[EB/OL]. [2014-12-22]. http://www. ilas. com. cn/p=201.
[16] 陈定权,张雪成. 我国图书馆集成系统迁移浪潮研究——以“211”高校图书馆为例[EB/OL]. [2014-06 -10]. http://www.dlf.net.cn/manager/manage/photo/ admin201205008.pdf.
[18] [22][35]沈迪飞. 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与ILAS[M]//吴晞. 时代的链接——深圳图书馆十五年.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16-33.
[19] 刘明晶:用智慧敲开命运之门[EB/OL]. [2015-09-10]. http://campus.chinaren.com/20050909/n240366273. shtml.
[20] 龚滨良. 建国以来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大事记[J].中国科技史料,1985,6(2):6-11,15.
[21] 张华平.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发展简史[EB/OL].[2015-10-09]. http://www.nlpir.org/?action-viewnewsitemid-11.
[23][29][32] 吴晞,于平. 回顾与展望ILAS二十周年技术研讨会[EB/OL].[2014-01-03]. http://www.publiclib. org.cn/library/periodical_show/1193.html.
[24] 顾晓光. 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12):1-18.
[25][26]吴晞. ILAS是什么?——在纪念ILAS二十周年技术研讨会上的讲话[EB/OL].[2014-01-07]. http:// www. publiclib.org.cn/library/periodical_show/1193.html.
[27] 沈迪飞. 我为能做ILAS人而永远骄傲[J]. 公共图书馆,2010(2):55-58.
[28][34]kevenlw. 说说dILAS [EB/OL].(2005-05-14)[2014-01-03]. http://meta.bokee.com/1516447.html. [30] ProQuest. ProQuest与艾利贝斯合并,加速全世界图书馆的创新步伐[EB/OL].[2015-10-07] http://internationalnews.proquest.com/blog/allnews.
[31] 程焕文. 资源为王,服务为妃,技术为婢[EB/OL]. [2015-01-0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 19f0100hjob.html.
Brief History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ILAS in 30 Years(1985-2015)in China
CHEN Ding-quan
AbstractThis paper outlines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ILAS in China since 1985 using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analyses its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historical influences,the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Because ILAS is a typical system and a best case study of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historical research on ILAS can offer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integrated library automation system;automation system;library automation;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作者简介陈定权,博士,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6-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