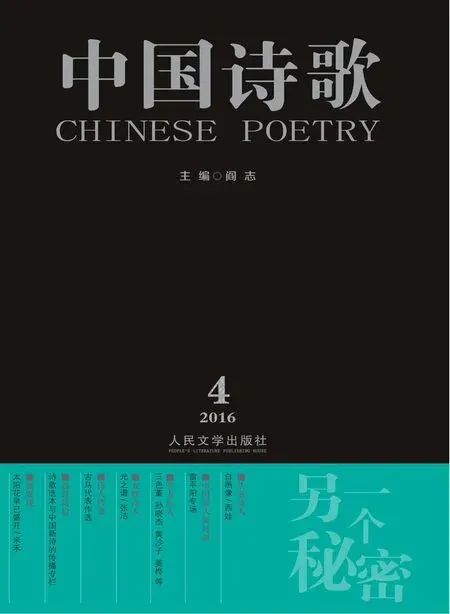颓废的“欣快症”与“新生”
——邵洵美新诗导读
□刘玉杰
颓废的“欣快症”与“新生”
——邵洵美新诗导读
□刘玉杰
邵洵美的显赫身世向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我们可从其家族谱系中管窥一二:祖父为清末重臣邵友濂,祖母为李鸿章之女,母亲为盛宣怀之女,妻子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五岁识字、六岁入私塾读书,后进圣约翰中学接受西式教育,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又到法国巴黎学习过绘画,可以说是中西教育熏陶下的现代知识分子。似乎很难还原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邵洵美,因为他一生的身份实在太多:作为诗人,他创作出版了三部诗集,《天堂与五月》 (1927) 、《花一般的罪恶》 (1928)、《诗二十五首》(1936),另有二十余首未收入诗集的散篇;作为小说家,他创作出版了《贵族区》等;作为翻译家,“译笔华美而熨帖,才气纵横”,与查良铮齐名,有“南邵北查”之誉(赵毅衡:《邵洵美:中国最后一位唯美主义者》,《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34页),除了收有十位诗人诗作的译诗集《一朵朵玫瑰》、比亚兹莱的《琵亚词侣诗画集》和其他短篇译作外,还翻译有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麦布女王》,拜伦的《青铜时代》,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和《四章书》,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等长篇译作;作为出版家,主编过《狮吼》、《金屋》、《新月》、《时代画报》、《论语》、《人言》、《自由谭》、《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等十余种中英文杂志,创办过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上海时代书局等,“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丛书也均出自其手;作为文学活动家,被誉为“文坛孟尝君”,由他我们可以织构起一个包括徐志摩、沈从文、徐悲鸿、郁达夫、施蛰存、项美丽(Emily Hahn)等在内的中西文化名流群像图。
在进入邵洵美诗歌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与其诗歌密切相关的思想特质。在邵洵美长文《一个人的谈话》中,他先是这样自问自答:“我常问自己,究竟女人更适宜于写诗呢,还是男子更适宜?我的答话,总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具有两性的灵魂,太男了不好,太女了也不好。”接着又说:“我也觉得人总是人,而人又总是半神半兽的;他一方面被美来沉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艺文闲话》,上海书店出版社,第8页、第32页)在诗作《女人》中他也写道:“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不论是在他的诗学观念、人生哲学还是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二元包容。这恐怕不是邵洵美的独创,因为在他所崇敬的诗人波德莱尔那里,我们也可以寻觅得到类似的人生体悟:“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同时都会有两种乞求,一是向上帝,一是向撒旦,祈求上帝或灵性,是一种晋升的欲望;祈求撒旦或兽性,是一种堕落的乐趣。”(波德莱尔:《赤裸的心》,胡小跃译,《波德莱尔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这正是解读邵洵美诗歌的钥匙。他的诗歌既是美的又是丑的,既是现代的又不乏古典元素,既是颓废的又蕴含着新生……
颓废的欣快症
颓废欣快症(the decadent euphoria)是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提出的但未做具体解释的术语,总体而言它是颓废的审美化,是主体盲目地享受颓废所带来的快感的一种病症,与提倡及时享乐的刹那主义具有基本一致的内涵。邵洵美也在诗中写道:“跑得/比时光更快的,还有/刹那间的欢乐。”(《Undisputed Faith》)表现颓废欣快症的诗作占邵洵美全部诗作的半壁江山,其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其时间意象是静止的、停滞不前的。邵洵美在《贼窟与圣庙之间的信徒》一文中曾说:“人生不过是极短时间的寄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决不使你有一秒钟的逗留,那么,眼前的快乐自当尽量去享受。”(邵洵美:《火与肉》,金屋书店,1928年,第59页)人类的颓废感本来就源自对时间的一维性感悟,具体到人类自身就是生命的有死性,因而在死这一终极寂静的前夜,有人会选择与之相反的喧嚣来享受、挥霍、耗尽生命。《序曲》中写到的正是这种人生体验:“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原是和死一同睡着的;但这须臾的醒,/莫非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在诗人看来,天地万物结束前那短暂的醒来,恐怕惟有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了。在《Madonna Mia》一诗中有如下诗句:“怕甚,像锋针般尖利的欲情?/刺着快乐的心儿,流血涔涔?/我有了你,我便要一吻而再吻,/我将忘却天夜之后,复有天明。”这里表达出一种主观意志选择下的时间停滞,人们因感官享乐而不愿去思考明天。《上海的灵魂》同样描摹了这样的时间观念:“在此地不必怕天雨,天晴;/不必怕死的秋冬,生的春:/火的夏岂热得过唇的心!”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代表着生死轮回,隐喻着时间的圆形结构,时间在这一隐喻中不再是线性的、一去不复返的,而成为可以往复的。但诗人并不在乎这样的隐喻,雨也罢晴也罢,生也好死也好,时间是冰冷的虚空,而惟有现世的情欲之火可以给人带来暖热的餍足。
第二,其诗置于都市空间背景之中。这与诗人的都市体验密切相关。他在《诗二十五首·自序》中谈到现代诗题材时说:“到了现在,都市的热闹诱惑了一切田野的心灵,物质文明的势力也窜进了每一家门户,一两个小时中从茅草屋可以来到二十层的钢骨水门汀的高厦门前,官能的感受已经更求尖锐,脉搏的跳动已经更来得猛烈:在这种时代里再写和往昔一样的诗句,人家不笑他做作,也要说他是在懦怯地逃避现实了。”(邵洵美:《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12-13页)诗人既体验到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又深刻领悟到人在都市经验中官能感受的极端化。诗人摹写最多的是巴黎和上海一西一中两个现代化都市。在诗末明确标明写在“巴黎”的诗有《天堂》、《情诗》、《恐怖》、《莎》、《我只得也像一只知足的小虫》等多首,可以说诗人对于巴黎这一都市有着很深厚的体验,这可透过写巴黎的诗《病痊》来得知一二:“几天不见巴黎,/巴黎的风也已老了。”“巴黎我底巴黎,/我几时曾忘却了你?”“这样可爱的你,/我怎愿人人来恋顾?”巴黎所带来的现代性体验,并未因诗人留学回国而中断,上海这一现代化城市继续了这种体验。《日升楼下》是诗人在电车中看到的“十点零十分”这一瞬间的上海景观,“车声笛声吐痰声,/倏忽的烟形,/女人的衣裙。//似风动云地人涌,/有肉腥血腥/汗腥的阵阵。”听觉、视觉、嗅觉的都市体验后,在“星中杂电灯”这一自然景象与人工景象并置的意象中,“我在十字的路口,/战颤着欲情;/偷想着一吻”。《上海的灵魂》则更换为“我站在这七层的楼顶”向下俯视的视角来摹写上海,“舞台的前门,娼妓的后形;/啊,这些便是都会的精神;/啊,这些便是上海的灵魂”。舞台、娼妓只能算作都会精神的表征,真正的都会精神恐怕是虚幻和死亡:“此地有真的幻想,假的情;/此地有醒的黄昏,笑的灯;/来吧,此地是你们的坟茔。”
第三,充溢着诸多的女性意象。一方面,“女人是我底灵魂之主”,“你快给我个美人绝世” (《Légende de Paris》),对女性身体的刻画不仅是全面的,比如“月儿样的眉星般的牙齿”(《Madonna Mia》)、“石榴色的嘴唇”(《Madonna Mia》)、“乳壕”(《五月》)、“蛇腰”(《Z的笑》)、“蝌蚪般的眼睛”(《月和云》)、“樱唇”(《月和云》)、“燃烧着爱的肚脐”(《Légende de Paris》)、“蜜泪”(《花一般的罪恶》)、“沸汗”(《花一般的罪恶》)等等,甚至突破了常人的意料,在《我们的皇后》、《花一般的罪恶》两诗中均以“下体”词汇入诗,在《我不敢上天》中则更是具象地加以摹写:“但是可怕那最嫩的两瓣,/尽叫我一世在里面荡漾。”不难发现,诗人对女性形象的形容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往往不惜使用俗语,第二是无不浸淫着强烈、浓厚的带有极端化的情感。
另一方面,也在对女性身体的消费之中体悟到罪恶,因而对女性有着贬抑的称谓,如“淫娃”、“淫妇”、“妖异”等。然而这些贬抑的称谓又往往与颂扬的语汇紧密夹杂在一起,比如“鼻里不绝你那龌龊的香气,/眼前总有你那血般的罪肌”(《恐怖》)、“正像新婚夜处女的蜜泪;/又如淫妇上下体的沸汗” (《花一般的罪恶》)、“你是西施,你是浣纱的处女;/你是毒蟒,你是杀人的妖异”(《Madonna Mia》)……使得女性同时处于褒贬之两端,悬殊之间生成了巨大的审美张力。
第四,自然的情欲化。在对人为性的凸显中,颓废主义发展出反自然的倾向,这在邵洵美这里依然有效。在中外文学传统中,自古都有将女人喻作花卉的传统,诗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绝佳的情欲载体。除了《花》一诗外,在《堕落的花瓣》、《牡丹》、《水仙吓》、《情赃》等诗中花卉都被情欲化了,正如诗人最广为人知的诗篇题名一样,真真正正是“花一般的罪恶”了。比如《牡丹》一诗写道:“她那童贞般的红,/淫妇般的摇动,/尽够你我白日里去发疯,/黑夜里去做梦”,“我总忘不了那潮润的肉,/那透红的皮,/那紧挤出来醉意。”唐宋时代所奠定的牡丹以高贵之美为主的审美范式,在颓废审美主义这里消失殆尽,牡丹成为了让人醉生梦死的荡妇的象征。尽管与花卉一样,蛇在中外文化传统中也经常作为女人的喻体存在,但不同的是花卉通常是正面意义,而蛇往往是负面意义的。邵洵美的《蛇》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你垂下你最柔软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我不懂你血红的叉分的舌尖/要刺痛我哪一边的嘴唇?”如果说《牡丹》中的牡丹还是静态的诱惑物的话,那么这里的蛇的形象则显得更具动态,是具有主动性的诱惑主体。值得一提的是,此诗经常与冯至的十四行诗《蛇》作比,有学者认为:“与冯至同题诗比较,冯诗更雅,邵诗则俗,但都不失为诗美中的一个品种。”(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二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除此之外,海水(《漂浮在海上的第三天》)、城市(《病痊》)等都被女性化、情欲化,就连月亮、白云这些纯洁的象征物,在邵洵美那里也沾染了情欲的色彩。《月和云》写道:“一个,有像蝌蚪般的眼睛,/一个,有未曾刺伤的樱唇。”并称月和云是“两件仙神羡慕的妖珍”。尽管《月和云》写“月中有爱,云中什么没有”,但《颓加荡的爱》一诗写的却是云之爱:“睡在天床的白云,/伴着他的并不是他的恋人”,“啊和这朵交合了,/又去和那一朵缠绵地厮混”。云的飘无定形成为男女之间颓废之爱的自然映射。
第五,反宗教精神。邵洵美诗歌中的宗教涉及基督教、佛教等,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基督教意象。诗人多次写到上帝、圣母、亚当、夏娃、天堂、天使等,比如在《歌》、《五月》、《Madonna Mia》、《我们的皇后》、《昨日的园子》、《天堂》、《我也只得像一只知足的小虫》、《诗人与耶稣》、《童男的处女》、《自己》、《天地的命令》、《声音》、《洵美的梦》、《在紫金山》、《神光》等诗中。诗人在诗中思索了宗教的悖论,目的在于论证颓废的合法性。《天堂》开篇就发问:“啊这枯燥的天堂,/何异美丽的坟墓?”在诗人看来,天堂之所以枯燥乏味,而自己宁愿入地狱而不愿上天堂(《五月》:“天堂正开好了两扇大门,/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就在于上帝“将一切引诱来囚在里面,/复将一切的需要关在外面”。也就是说,在诗人看来,上帝禁锢了人类最基本的欲望,而这与颓废的享乐是截然相反的。诗人认为上帝这样做是没有合理性理由的,“原来上帝也有说不出/理由的时候:当他要禁止有翅膀的/飞;有情感的爱;有痴望的唱出/他自己都不曾预备着的歌声”(《声音》)。
可以看到,邵洵美自己或许并未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颓废美学,但我们可以从其诗作中提炼出一个关于颓废美学的架构来:从最基本的时、空观念,到具象的选用(女人意象、自然意象),以及经由宗教经验介入的对于形而上的终极思考。
反思中的新生
然而,颓废的欣快症只是颓废的一个最为人们熟知的维度,它并不构成颓废的全部。颓废的另一维度是反思与新生。陈梦家认为,《洵美的梦》“是他对于那香艳的梦在滑稽的庄严下发出一个疑惑的笑”(陈梦家:《序言》,《新月诗选》,新月书店, 1931年,第27页)。其实,这种对于颓废欣快症的疑惑早在《洵美的梦》发表的1931年之前就已存在。颓废的欣快症与对颓废的反思并不是先后出现的,而是共时地并行存在于邵洵美的诗作之中。
首先,是对人生颓废的反思。即便是邵洵美早期典型的摹写颓废欣快症的诗篇,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到反思的尾巴。比如在《Légende de Paris》中,就有对于时光流逝的反思,“美人是我底灵魂之主,/啊却也是时光底奴隶”。《堕落的花瓣》中有对自身生命的反思,“美人是魔鬼;/爱了你,/她总玷污你,/一定的”。《月和云》中有对欲望的反思:“我已有桃红的罪恶,千千;/灰色的欲求吓,无厌无厌。/啊,为甚这有了我的世界,/有了她,有了她又有了她?”在《还我我的诗》一诗中,诗人抒发出“淫娃”与“诗”之间的取舍矛盾:“还我我的诗,淫娃,/啊得了你的吻,失了我的魂。”“啊我的晨星,淫娃,/为了你,我写不出一字半句。”诗人的诗是属灵的,是诗人灵魂的象征;淫娃的吻是属肉体的,折射出诗人的欲望。尽管诗歌以如此的反问作结:“要是你不爱我时,/我将怎样来寄托我的忧虑?”似乎对于欲望仍旧割舍不下,但整诗终究反映出一种对于颓废的反思精神。《诗二十五首》中尽管仍有摹写颓废的诗作,但仅有《牡丹》、《蛇》两首,已经跟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颓废已然不再全然是诗歌的描摹对象,而成为一种被诗人反思的对象。比如《出门人的眼中》:“也有绻绵的手圈住我的项颈,/我也尽把金钱去换他们的恩情,/镜子里也有过两对两样的眼睛;/我怕异香的玫瑰虽让小蜂吸吮,/遭殃的是那尝到甜味的灵魂。”这里以小蜂喻人,以玫瑰喻欲望,用回溯式的冷静眼光反思狂热享乐的后果——灵魂的遭殃。再看《绿逃去了芭蕉》:“绿逃去了芭蕉,红逃去了蔷薇,/我再不能在色彩中找到醉迷。”这里的色彩既指欲望享乐,又指生命的色度,而色彩的消褪就既指享乐的消失也指生命的流逝。“只是可怜的白鸽已上了年纪,/他不再想去逗引霞云的欢喜。”诗末这两句以白鸽喻指年迈之人,以色彩饱满、风姿迷幻的霞云喻指欲望享乐,表示出对于颓废享乐的拒绝。
其次,拒斥死亡的到来。邵洵美诗歌中体现出的对于死亡的态度,与颓废主义赞美死亡的审美态度是大不相同的。他写死亡是为了表达出对于生的渴念,体现出“生的执着”(苏雪林:《颓加荡派的邵洵美》,载苏雪林《浮生十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76页)。诗人笔下的死亡描写并不少见,比如《歌》和《昨日的园子》写到了花儿树叶的凋零、枯黄以及鸟儿的死亡,甚至《死了的琵琶》一诗写一只死了的琵琶,“他已不想把才子去配娇娃”。但真正能见出对于死亡的态度的,恐怕还是《死了有甚安逸》一诗:“死了有甚安逸死了有甚安逸!/睡在地底香闻不到色看不出;/也听不到琴声与情人的低吟,/啊还要被兽来践踏虫来噬啮。”这里,死亡遭到了拒斥,活着的生命成为最可宝贵的。“因为死究竟是一片容许/延宕的账单,你可以借了/神的力或是人的力去关说,/要他宽限些时日再索取”(《Undisputed Faith》),死本是无法预定的偶然降临之事、不容凡人商议的绝对之事,在这里死成了可以赊账、拖延的世俗账单,成了人与死神之间经由商议而确定的未定之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颓废主义者对于死亡的态度,是趋向,是向往,是想象,却不是立即的实行,在放弃生命的过程中,却发现了生命的潜在的创造性的展示和某种程度上的对于生命的敬畏。”(薛雯:《颓废主义文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
最后,渴望新生。表现颓废欣快症的诗歌与《花》、《十四行诗》、《到乡下来》、《二百年的老树》等几首诗歌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如果说前者是感官的,那么后者多是反思的;前者是现时的,后者则是历史的;前者带有浓厚的异域风格,后者则浸染着民族风姿;前者是城市的,后者则是乡土的……新生的主题基本上都是在自然、乡村等题材的诗歌之中。《花》是邵洵美诗歌中以花为题材的诗歌中的特例,表达出花是天地孕生的具有着广博胸襟的自然精灵,它爱溪流“向着无障碍出笑着流”、爱白云“有超脱和高尚的精神”、爱风“自由地逍遥东西南北”,也知道了太阳的本能和月亮的洁净,更不愿听到鸣鸟的哀嚎。它从自然中汲取的高洁精神,使得它无法忍受世界的污浊,因而“他希望忍耐的雨珠,/把这污渍一一洗去”。最终,它以芬芳的花香“将地狱染成了天堂,/一切烦恼消灭沦亡”。象征着生命休止以及罪恶的地狱变成了美好的天堂,可以说在这首诗里新生的主题是一种完成式。《二百年的老树》则是一首渴盼新生的诗,以一棵拟人化的树的视角,描摹一个乡村的平静生活:“他看着他们的脸儿透红,/他看着他们弯了腰过冬;/没多时他们也有了儿女,/重复地扮演他们的祖宗。”或许在诗人看来,这是太过平静、太过古老、也太过波澜不惊的生活,因而,诗的最后写道:“他已看厌了,一件件旧套,/山上的老柏,河上的新桥;/他希望有一天不同平常,/有不同平常的一天来到。”尽管诗人并未指明这不同平常是什么,但可以推知是他所熟知的现代文明。诗人在期待中华古老文明中进步性力量的出现。
我们不能忽视颓废与进步、发展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是现代性和进步的概念,另一方面是颓废的概念,两者只有在最粗浅的理解中才会相互排斥。”(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6页)也就是说,新生其实与诗人浓烈的颓废感是分不开的,从最为朴素的生命衍生关系中就不难得出颓废之中孕生着新生的结论。
形式美的追求
在诗歌艺术追求上,邵洵美将法国唯美主义诗人戈蒂耶的名言——“形式的完美是最大的德行”——奉为圭臬,提出:“形式的完美便是我的诗所追求的目的。但是我这里所谓的形式,并不只指整齐;单独的形式的整齐有时是绝端丑恶的。只有能与诗的本身的‘品性’谐和的方是完美的形式。”(邵洵美:《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10页)具体而言,其形式美的诗学主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诗歌的格律化。邵洵美在诗歌流派上被视作是新月派诗人,陈梦家1930年代编选的《新月诗选》以及蓝棣之1980年代编选的《新月派诗选》等有影响的选本都将邵洵美的诗作选入其中。而新月派在诗歌艺术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诗歌的格律化。闻一多在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中讲,诗歌的格律可以分为视觉方面的和听觉方面的两类,“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闻一多:《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三联书店,1999年,第167页)。邵洵美显然受到闻一多的影响,在1936年所写的《诗二十五首·自序》一文里曾坦言:“我五年前的诗,大都是雕琢得最精致的东西;除了给人眼睛及耳朵的满足以外,便只有字面上所露示的意义。”并将《洵美的梦》一诗之前的诗作称作是“少壮的炫耀”(邵洵美:《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8页)。属于眼睛的视觉方面的是诗行的规律性,具体可分两种:一种是每一诗节行数相同、每一诗行字数相同的整齐,如《五月》、《月和云》、《春》、《一滴香涎》、《恐怖》、《To Swinburne》、《假使我也和神仙一样》、《一首小诗》、《季候》等。一种是有规律的变化,比如《Madonna Mia》每段后两句均比前两句多一字,每句都会使用一次逗号;《日升楼下》四节,每节三行,首行皆七字,二三行皆五字,使得整诗短促有力,与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十分契合;《洵美的梦》整诗共50行,中间没有诗节划分,且隔行押韵,尽管每行字数相同,但因很多诗句有标点的插入,看起来并不十分呆板,具有一种错落有致的灵动,这样的形式与梦境的无意识流动是比较贴切的。属于耳朵的听觉方面的主要是诗的韵律。比如《季候》一诗,每行均十字,两行一节,共有四节,节内用韵,一节一换韵,听起来很有节奏美感,另外韵脚的更迭所带来的多变的节奏感,也与爱情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暗相契合。
其次,诗人善于尝试不同的中外诗体。中国诗体如民歌体(如《新嫁娘》、《游击歌》、《〈论语〉征兵歌》)等,外国诗体如“莎格”(即萨福体,如《莎》、《我们的皇后》)、五步无韵诗(如《声音》、《自然地命令》)、四步无韵诗(如《Undisputed Faith》)、十四行诗(如《天和地》、《一个疑问》)等等。诗人对于各种诗体适合于什么样的诗歌有着明晰的认识,他认为“‘五步无韵诗’的特点是在能使情境的力量延长……用这种格律,长诗会觉不到长”,四步无韵诗“情致更来得亲切,更来得素朴,适宜于更天真的意境”,而十四行诗最适宜于“去记录一个最纯粹的情感的意境”(邵洵美:《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9页)等等。萨福体诗节(Sapphic stanza)是诗人尝试较早的一种外国诗体,它由四个诗行组成,前三行每行含十一个音节分为五个音步,第四个诗行有五个音节。《莎》一诗就是诗人用萨福体诗节写成的致敬他所崇拜的萨福的诗。一般说来,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因此,对应到汉语语境中的萨福体诗节,从表面上看就是前三行每行十一个字,第四行五个字。由于汉语轻重音并不明显,所以英语由轻重音所构成的关于扬、抑格的音步在汉语现代诗里无法体现出来,但汉语诗歌有音组节奏论、顿节奏论等,依旧可以在每个诗行中大致分出五个音组或顿。
莲叶的|香气|散着|青的|颜色,
太阳的|玫瑰|画在|天的|纸上;
罪恶|之炉的|炭火的|五月|吓,
热吻着情苗。
最后,诗贵曲折。邵洵美认为:“诗是根本不会明白清楚的。”这是他从谛里雅的《诗的明显与曲折》那里继承来的诗贵曲折的诗论。而“一到字眼发生了‘象征的作用’时,诗便曲折了”。至于什么是象征的作用,他认为“大概形容和譬喻是暂时的象征,象征则是永久的形容和譬喻”(邵洵美:《诗二十五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11页)。诗人没有强调形容、譬喻与象征之间的区别,而是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总的来讲,其早期诗歌多形容、譬喻,后期诗歌多象征。《季候》、《声音》、《自然的命令》、《蛇》等都是表现象征艺术的佳作。比如说《声音》中的声音就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象征,与其说它是上帝的声音、诗的声音,倒不如说是来自诗人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自然的命令》与《声音》一样具有哲理思辨的特点,有人指出,诗中的“她”就是“诗人所爱恋、所追求的真、善、美”,“‘自然的命令’就是真善美的命令”(季广德:《试论邵洵美的诗与诗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4期)。
在《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于自我身份的思考与认同:“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作为诗人的邵洵美,其审美品位、思想境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自己对于人生、社会万象的思索、体悟不断变化发展的。从颓废的“欣快症”到“新生”,从抒写唯美到发出抗日的激昂之声,在某种程度上讲,邵洵美可以被看作是一位一生中都在自我完成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