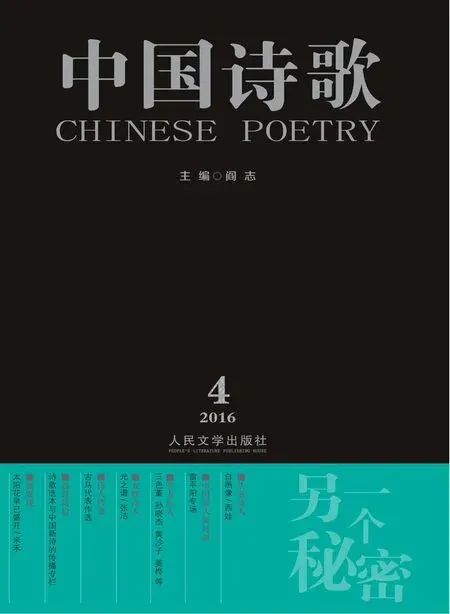诗歌选本与新诗经典的产生
——关于伊沙编《中国口语诗选》
□程继龙
诗歌选本与新诗经典的产生
——关于伊沙编《中国口语诗选》
□程继龙
为“口语诗”说话是要冒风险的,似乎越来越多的行内人以贬损口语诗为能事,身处口语诗墙垣之内的人,又不能完全有力地解释和反思他们的价值和观念。我想借不久前伊沙编选的《中国口语诗选》说点话,这是一部具有鲜明流派色彩的诗选。
当代诗坛上严格来说称得上流派的诗歌群落为数不多,比如“中间代”是借助其他代际称谓的划分,《中间代诗全集》虽然标识出了成员构成及其代表作,但是其可共享的诗学观念还相当模糊;“70后”、“80后”、“90后”正在生长形成中,本身还够不上流派称谓,只是一个权宜的叫法;“下半身”、“垃圾派”、“打工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运动、浪潮,且本身已经或正在化入其他群落力量中。“流派”是一个相对稳定而成熟的概念,构成流派的群落,必须具有较为稳定的理念或观念的基点,具有骨干的和正在壮大的成员,发展演变中具备纵深的历史感等等。
口语诗有相对较为成熟的诗学理念。新诗的“口语”问题,从第三代诗歌那里已经开始思索了,“他们”、“莽汉”等的一些核心成员的论说至今不断被提及,还有九十年代作为泛流派存在的“民间派”的隐性实践。伊沙为这部诗选所写的代序《口语诗论语》对口语诗的整体观念,有总结性的意味。他认为1980年代第三代诗歌中的某些口语诗行为是口语诗的“发轫期”,他也将这一时期看作“自发”而非“自觉”的“前口语”时代;1990年代是“发展期”,理论界的“后现代热”刺激了它的发展;新世纪以来属于“繁荣期”,是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它的繁荣;“后口语”,包括它的“发展期”和“繁荣期”。伊沙像于坚等人那样将口语诗的谱系一直上溯到胡适“白话诗”、晚清“我手写我口”,乃至唐诗宋词的某些口语传统,且暗含了一种经由接通后现代思潮而继续促进新诗“现代性”变革的愿望。这篇“论语”接下来点染式地描绘出涵盖口语诗观念、态度、技法、诗美标准等因素的草图。伊沙使人强烈地意识到,“口语诗”之“口语”,不单纯是一个语体问题,“口语”还关乎诗人立场、诗歌观念以及文体特征。“口语诗”的“口语”的反面是什么?是“非口语”,“非口语”又指什么?在论述中,伊沙分别指“书面语”,就是落实于书面的、经典的死文字;指“普通话”,最好的口语也许是方言,然而方言进入诗歌必须除以普通话这个公分母,伊沙在此有一种隐而不发的矛盾态度,前面这两点都是在努力思索解决“口语诗”的语体问题;指“叙事”,而不是叙述,叙述是口语诗文本推进过程中的结构性的精彩自呈,而叙事是抒情诗人在抒情诗走到穷途末路后的紧急输血;指“抒情”,口语诗也认可“诗缘情”,但是指向一切非传统的新型的抒情,不惮于冷硬、粗俗,因为必须直面和处理当代现实的粗粝、残酷一面;指“意象”,经典的现代主义带来的意象过度化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口语诗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反意象”的要求,是“裸诗”,须重新发挥“赋”的功用,扔掉道具,直指人心。另外还关涉一些不可或缺的意识:“从舌头到身体到生命到人性到心灵到灵魂”,借助“口语”的切身性,重新激活现代主义诗歌以来的以生命意识为基的优良传统,且将其深化到一内一外两个向度,向内进入灵魂,叩击当代人日渐虚弱的灵魂,向外进入现实的各种场域和细节,恢复唐诗一直以来的“人间性”,并且恢复诗歌介入当代现实的能力,调整诗性主体的位置,既不犬儒,也不精英,而是采取可以接通现代公民社会的“平民主义”态度,做一个俗人在世的诗人,在人间的低处随处发挥诗的力量,而不像白衣诗人波西米亚式地在“诗意的,太诗意的”地方寻找诗。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语诗充满了平民主义的伦理感,它也回到了汉语最基本的层面。
这个选本展现了口语诗的风貌和可能性。开篇诗人韩东的《山中剧场》使口语诗真正步入了神秘之境,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山中剧场”既是意念中的梦境存在,又是语言叙述带来的奇观,韩东总是那么平稳而深刻,如今他已超越了“有关大雁塔”时期的浅白和调侃。隐秘的祖师王小龙的《坠落》:“醒来,你听见谁在和太阳厮打/打得风不成形水不能饮鸟不敢鸣”,是雾霾,略带幽默的俗化叙述把对当下现实的感觉带入超现实领域,他使人们意识到,在当代现实比超现实还要超现实。唐欣一贯是中年男性诗人的闲扯姿态,“把肖邦放来听听”,“抱一本白皮的《世界史》乱翻”,他注入的是一种针刺式的滑稽效果。赵原《看牙的颜色就知道是哪个村的》,以绝妙的方式介入对化工污染的控诉。沈浩波《饮酒诗》再次伸张了“俗人在世”的本真人生观。南人《鸟的自由》以愤激的诙谐说出了对自由的理解。双子《性感妈妈》是对人性隐秘的突然洞见。口语诗崇尚语言的切身感,重视叙述的现场感,追求技艺的简捷感,坚持介入现实的批判性,这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
当然,这部诗选也存在一些重要的缺憾,如漏选于坚、李亚伟、杨黎等前辈口语诗人的重要文本,不管诗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恩怨如何,如果有志于与历史对话、进入文化史的话,应当适当选入他们的作品。另外一些后起之秀的入选作品,还不是他们最好的。这本选集一再让人们想到伊沙前几年编选的《现代诗经》,《现代诗经》中选出的某些口语诗的品质,真当得起“诗经”的称呼。最后,仍然没能看到对口语诗一些重要观念、技术问题的反思,例如如何保证“口语一经书写还是口语”这一难题,某些口语诗题材过度琐屑,尽管都认同开新是第一要务,但是必须意识到并非所有见闻和情绪都能成为诗,必须正视艾略特的眼光的审查。再比如具体如何在口语的肌体中纳入意象元素,如何克服对“现场感”诗学的无节制迷恋,避免段子式的线性思维模式等,这些深层问题尚待后续实践来给出答案。

——关于戏曲流派传承的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