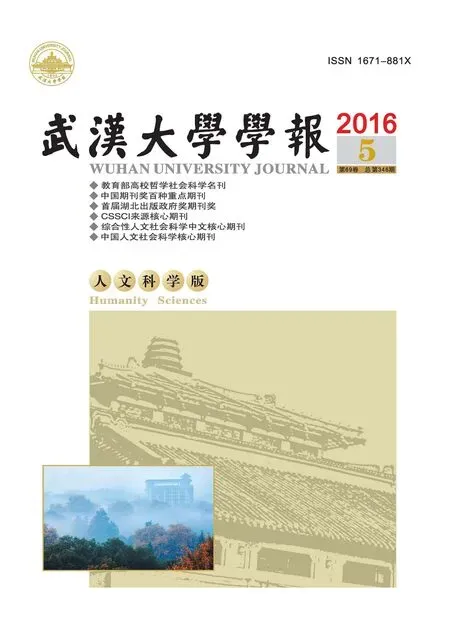阶级与市场歧视
——对弗里德曼的批判
李风华 梁家琪

阶级与市场歧视
——对弗里德曼的批判
李风华梁家琪
市场神话——米尔顿·弗里德曼无疑是它的重要推手——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市场消灭歧视”,其实质就在于对市场歧视的否定。以平等就业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弗里德曼有关市场歧视问题的三个论证理由为:市场歧视的本质是一种个人偏好;市场歧视引发的结果是一种被动伤害;干涉市场歧视等同限制思想自由。分析表明,弗里德曼的辩护逻辑不成立,市场歧视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在影响市场歧视的因素中,阶级因素具有结构性的影响,并且基于阶级的市场歧视内生于市场。
资本主义; 市场歧视; 阶级; 米尔顿·弗里德曼
流行的观念认为,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它是特权、等级、专制等等那些让我们厌恶的政治手段的反面,因此市场不存在歧视行为。追溯起来,这种市场神话论源远流长,我们可以列出一连串名单。但是,毫无疑问,神化市场方面最重要的鼓吹手之一,就是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将市场经济——弗氏把它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原则充类至尽,应用到社会政治生活,反对政府干预,并得出资本主义是保卫自由的最好制度这一判断。
以往的弗里德曼批判者,比如阿马蒂亚·森,更多的是从自由的角度批判这一市场神话论*参见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中“市场与自由”一章(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但对于其中的一个重要论据——市场消灭歧视——则关注不多。笔者尚未见有中文文献讨论这个问题,相反,流行的论述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一观念。这也侧面证明了检视这一论据、探讨市场与歧视的关系的学理必要。基于这一考量,本文将致力于与弗里德曼的内部逻辑对话,指出市场自身无法避免市场歧视,而阶级正是正确认识市场歧视的重要视角。
一、 弗里德曼:市场消灭歧视
弗里德曼首先从一个历史事实出发,认为:“特殊的宗教、种族或社会的集体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殊不利的条件,正像俗语所说,他们是受到了歧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歧视已经大为减少,这是一件突出的史实。”*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8页。弗里德曼通过举出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发展在不仅“为被歧视的少数派们提供了存在的空间”,而且“为歧视现象的历史性减少提供了条件”这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为此,弗里德曼给出了几个历史证据:“其一,尽管有官方的迫害,犹太人还是能够工作并维持他们自己。原因可能是有市场部门的存在。其二,尽管清教徒和公谊会教徒的某些生活方面受到限制,但他们还能够移民到新世界,因为他们能在市场里累积足够的资金去这样做。其三,在南北战争后,南方各州采取许多措施来对黑人施加法律限制。在任何规模上从未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对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权设立障碍。没有设置这些障碍显然并不反映对黑人免除限制的任何特殊关怀,而却反映了对私有财产的基本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能超越了对黑人歧视的愿望。在任何社会中,保存歧视是性质上最垄断的领域,而在具有最大竞争自由的那些领域,对于特殊肤色和宗教团体的歧视却是最少。”*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18页。.
必须承认,弗里德曼的历史表述是有说服力的。相比较之前封建社会或奴隶制度,资本主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传统的依据等级或身份而产生的歧视。正是基于这个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这个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守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但是,一个在历史上消灭了封建歧视和奴隶歧视的制度,并不能保证它能够消灭一切歧视现象。要证明市场消灭一切歧视现象,还必须给予理论的证明。
为了论证在自由市场中可以消灭歧视,弗里德曼提供了如此说法:“面包购买者不知道面包是由白人还是黑人、是由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种植的小麦所做成。结果,小麦生产者处于最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地位,而不管社会可能对他雇佣的人员的肤色、宗教或其他特征的态度。”*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19页。也就是说,在弗里德曼看来,自由市场具有把个人的经济效率和其他特征相分开的经济动机。在强烈的经济动机导向下,很少会有人为了坚持自己的歧视倾向而提高自己的成本。因此,在自由市场当中,本着经济效率至上的原则,歧视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看上去,弗里德曼的论述有点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又说:“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57页,意思相似。不过,马克思从未否认在简单商品交换领域中的形式平等,他更重要的工作是证明,一旦离开商品交换领域,资本家和工人“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05页。。马克思对于市场的形式平等的认可与弗里德曼对市场的极度吹嘘是完全性质不同的论述,两者的重要差别在于对市场歧视的认定问题。
所谓市场歧视,它不同于传统的依据个人政治与法律身份而导致的歧视,相反,它是在自由交换过程中,交易者基于自身所处的相对优势而对于另一方交易者所实施的歧视。比如,用人单位往往设置明确或潜在的限制性条款,拒绝女性、有色人种、乙肝病毒携带者等求职者。弗里德曼认为这种现象不构成真正的歧视,对它的干涉事实上是对自由的侵害,因此,市场——或者弗里德曼眼里的资本主义——已经彻底消灭了歧视。
本文不打算对弗里德曼进行社会历史或阶级立场的批判,而将本文的任务限制在内部对话。为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弗里德曼有关“市场消灭歧视”的证明。正如前述分析表明,这个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历史功绩,而在于对市场歧视的认定上。如果我们所谓的市场歧视其实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经济自由,那么,我们当然要为市场欢呼,它已经实现了人类最高的平等。但是,如果这种市场歧视其实只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其资本主义的辩护事业的正当性就相当可疑。在这个问题上,弗里德曼的逻辑本身非常简单,他无意构建一整套严密的理论来证明这一点,主要是用几个事例来进行解释,它们分别是平等就业立法、劳动权利法、学校教育的种族隔离——这些是当时美国社会所关注的几个重要社会政治问题。由于批判对象的理论形式比较简单,本文的任务也相对轻松,我们接下来检视这些案例,最主要的就是平等就业问题*Equal Employment,中译本作“公正就业”,不确,本文改译为“平等就业”。。从他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市场消灭歧视的三个彼此紧密相关的理由。
二、 弗里德曼的逻辑错误:以平等就业为例
平等就业是平权行动的一种,指每个人都不得依其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族裔、残障和年龄等因素而受到歧视,人们应该享有相等的就业机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平权运动的进展,平等就业机会原则获得了广泛的认可。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中的第二条第一部分就是对于该原则的表述。弗里德曼对此予以强烈否定,他的依据是:市场歧视的本质是个人偏好;市场歧视的后果是被动伤害;干涉市场歧视等同限制思想自由。
(一) 市场歧视的本质是个人偏好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确立了“任何人不得以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一个人的工作申请”的准则。在弗里德曼的眼中,这却是一条难以容忍的触犯自由的恶法。他认为,“歧视他人并使之失去工作”不是对个人基本法定权利的伤害,而只是与“由于不喜欢某个歌手的风格而拒绝去看他的演唱会”类似的个人偏好。既然是个人偏好,那么,对所谓的市场歧视行为最多只能讨论和说服,而如果运用法律来干预,那就是干涉公民的自由。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弗里德曼将个人偏好等同于市场歧视,事实上是一种偷换概念。毫无疑问,歧视必然源于个人偏好,但个人偏好并不必然产生歧视。一般来说,歧视的外延要小于个人偏好。歧视是一种政治学的术语,它指人们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人的缺陷、缺点、能力、出身并由此导致后者在工作机会方面的不平等。一个人可能有带偏见的个人偏好,但并不意味着他因此就有权将这种偏见付诸实践。弗里德曼的错误在于将法律对于歧视行为的干预引申为对于个人偏好的干预,这一做法不知不觉间混淆本来泾渭分明的领域之间的边界,为神话市场作出了铺垫。
从个人偏好到歧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阶级。首先,个人偏好本身往往受到阶级的影响。“例如,某些美丽的花卉在习俗上被视为惹人厌的莠草;也有些比较容易栽培的花卉,受到那些买不起更奢华品种的下层中产阶级的认同和喜爱,但是这些品种却被某些人斥之为庸俗,这些人有能力负担昂贵的花卉,并且对花匠产品所呈现的财力之美,受过高等的、有计划的熏陶。”*凡勃伦:《有闲阶级论》,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这种由于社会阶级的不同而决定的品味或偏好的不同,表现在诸如家具、房舍、公园和庭院等消费品上也莫不如此。其次,个人偏好能够构成歧视,也往往经历阶级这个结构性变量。单个人的偏好本身无法构成一种影响经济社会的力量,但是众多类似的偏好由于与经济社会结构相关,从而与某个特定的阶级,尤其是优势阶级相联系起来,就产生了显著的歧视后果,亦即对于弱势阶级的社会伤害。
还要看到,在论证不可以采取法律手段来干涉市场这一观点时,弗里德曼又犯了明显的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弗里德曼认为,由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推行的平等就业立法是对人们自由的干预,并认为这样的法律是极其危险的。其逻辑是:如果一条法律可以给政府以禁止某种歧视行为的权力,那么另一条法律也可以反过来给政府以指定歧视某些人群的权力,因此,这条平等就业立法是绝对不能施行的。依其逻辑类推,我们可以设想,由于人们害怕会给政府以指定杀害某些人的权力,那么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可以赋予政府处置杀人犯的权力?更进一步说,弗里德曼一方面认为用棍棒打人是政府必须管的“主动伤害”,但是按照他的上述逻辑,他又认为不应该给予政府保护他人不被打的权力,因为这有可能反过来给政府以指定用棍子打他人的权力。弗里德曼将潜在的政府暴政看得如此可怖,以至于他要连政府一起端掉。
(二) 市场歧视是一种被动伤害
说到伤害,弗里德曼倒是并不否认市场歧视的这一后果。面对市场经济中的就业机会不平等的现象,主流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市场歧视,并且其中蕴含了对于弱势一方的伤害。基于这一理解,针对“在就业问题上对人与人之间订立契约的自由进行干预是应该的”这一观点,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人提出了一种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解释,即当两个人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具有均等条件时,拒绝雇佣黑人而不拒绝白人的个人就是伤害别人。因此,对这种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歧视,由政府来干涉是必须且合理的。
弗里德曼承认伤害的现象,但却否定其歧视的本质。在他看来,伤害分为积极的伤害和消极的伤害,也就是所谓的主动伤害和被动伤害。他认为用棍棒打人是主动伤害,法律必须管理,而因为偏好爵士乐的歌手却使得歌剧歌手受到经济损失是被动伤害,法律不能管,因为这种伤害并不涉及任何不自愿的交换,也不会带来第三方的负担或者得利。
对于弗里德曼的如此言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确实没有必要对被动伤害进行干预。比如,一个人与其情敌竞争失败,政府并不存在充分的理由去补偿失败者。但是,弗里德曼将这一逻辑充类至极,禁止干预一切被动伤害,却是过于自信的推导。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反驳:那些因为种族、性别等因素而受到的被动伤害是结构性的,它蕴藏于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就业机会如此重要,使得政府有理由对此问题进行干预。用G.A.柯亨(即G.A.科恩——编者注)的话来类比,“尽管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脱离无产阶级的自由,而且事实上即使每个无产者拥有这种自由,但无产阶级却存在脱离无产阶级的集体不自由,是一个被囚禁的阶级”*《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G·A·柯亨文选》,吕增奎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7页。。换句话说,当这一被动伤害不仅仅局限单个白人和黑人之间,而是普遍而反复地出现在大多数白人和大多数黑人之间,我们有充分理由质疑这一“被动伤害”,从而予以干预。
我们可以拿中国的高考招生为例来讨论这一被动伤害问题。一般来说,相比较其他标准,仅仅依靠分数来的大学招生制度要更倾向于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农村居民。但即使如此,农村生源的大学生比例仍然远低于城市生源*参见梁晨、李中清:《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可见,农村居民在大学入学,尤其是精英类大学的入学中相对弱势,这就是弗里德曼意义上的被动伤害。但是,这种被动伤害绝非偶然,它受到了阶级结构的深刻影响。不过,当这种被动伤害已经呈现出结构性的倾向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就构成一种歧视,并试图在政策上予以纠正。近年来,一些大学在农村生源上的自觉优惠可以视为对该歧视的部分纠偏。
(三) 干涉市场歧视等同于干涉思想自由
讨论完市场歧视的本质与后果,现在来探讨针对市场歧视的措施的合理性问题。
在《资本与歧视》一文的最后部分,弗里德曼断定,支持平等就业立法的人同时也支持言论自由是自相矛盾的行为。他说道:“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将为保护种族主义者在街头宣传种族隔离主义的权力而战斗到底。但是,假使他为了实现他的原则而拒绝雇佣黑人来从事某一具体工作,该协会却赞成把他投入监狱。”*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24~125页。这些人居然既认为有歧视思想的人拥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力,又认为一旦他们把歧视从思想付诸实践就应该被关进监狱,似乎陷入了自相矛盾。看上去,这真是致命一击,让对手吃进去自己的拳击套而倒地。但细细查看,并非如此。我们认为,这里弗里德曼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他将人们的思想自由等同于人们的行动自由。思想自由,又称观念自由,作为一种基本人权,是个人持有不同于他人,包括不同于家长、宗教组织、执政党等任何权威的独立思想之权利;与之相对应,行动自由则是将思想自由付诸实践并造成对他人影响的自由,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法律的一般规定是原则上不干涉个人的思想自由,而对行动自由则会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因为行动自由的产生,不仅是个人自由权利得到践行的过程,同时也可能会造成对他人行使自由的某种程度的不利影响。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通常所公认的“在不干涉或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行动自由”这一观点符合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在弗里德曼的逻辑里,他基于赞同干涉个人的思想自由是不合理的这一观点,将需要法律干预的行动自由等同于个人的思想自由,也就是将本来合理的管理行为即对行动自由的管制等同于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即对人们思想自由的干预。对于他再次出现的混淆语义的错误,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来有力地反驳他,即“是否有人愿意维护我们把想用木鱼砸他愚蠢脑袋”的思想变成行动的自由?在平等就业问题上,我们当然无法禁止有些人心里对于人种、性别、族裔、出身等方面的歧视,但是那种将这种歧视心理付诸实践的做法却是不允许的。
这里我们补充一种弗里德曼可能的辩护:“人的思想和行动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只要行动不构成对他人的主动伤害,则应该被看作是思想自由的一种延伸,一起受到保护。这就像我们履行某种宗教仪式就是宗教信仰的延伸一样,只要不构成对他人的主动伤害,即便不被别人喜欢,也应该受到保护。”*这一意见源自本文匿名评审者的诠释,他认为弗里德曼应当不至于犯如此明显的愚蠢错误,即把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混为一谈。这种诠释也许比较真切地把握了弗里德曼的原意,即弗里德曼的着眼点在于被动伤害,而非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的区别。但是,对于此处的批判而言,弗里德曼的本意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样推导其逻辑时事实上混淆了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并从而将对后者的干涉视同对于思想自由的干涉。这种辩护意见试图将论证的义据拉回到主动伤害与被动伤害的问题上。不过,即使是回到被动伤害问题上,思想自由还是行动自由的问题仍然无法摆脱。让我们设想一种典型的见死不救的情景:A与B有不共戴天之仇,B的婴儿正爬向井中,此时只有A一个人在旁边。由于对其父亲的仇恨,思想上,A恨不得希望这个孩子死去。对于A的这种思想,虽然道德上并不可取,但法律却无能为力。然而,A若将该思想付诸行动,真的见死不救,法律自然有理由干涉。在这里,就A的思想和行动来说,孩子的死亡是一种被动伤害。但是法律在此处的干涉(行动)与不干涉(思想),其依据仍然在于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的本质性区别。
从阶级的视角来观察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问题,我们会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使假定优势阶级与弱势阶级的思想自由能力一样*这个假定当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被统治阶级不但在行动自由能力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缺陷,思想自由方面也受到了统治阶级思想的桎梏。这里的退一步只是说明,自由(不管是思想自由还是行动自由)受到了阶级结构的深刻影响,一旦充分自由,被统治阶级往往更居于弱势,不平等更加深化。,两者的行动自由能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为优势统治阶级拥有丰厚的物质资源和权力能够践行其思想,相反,弱势阶级由于缺乏权力与财富从而使得其思想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从平权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限制优势阶级思想上的自由,在行动上予以限制也或多或少有利于平等。
总之,基于平等就业的分析表明,弗里德曼逻辑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把蕴含着阶级差别的市场歧视混同于个人偏好,认为其结果是被动伤害而无需干涉,并断言对它的干涉事实上是对于思想自由的干涉。这一逻辑错误的发生归根结底源于他神话市场,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以此为资本主义辩护。这种市场神话断言,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就能自动地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它实质上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理论,它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敲门砖,其理论具有强烈的阶级偏见。
三、 阶级视野中的市场歧视:必然性与出路
对弗里德曼的批评同时也是对市场歧视存在的证明。一旦在理论上澄清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市场歧视非常普遍,比如受教育机会、健康条件的差距、高尚文化产品的生存困境、正外部性道德行为的缺乏回报等等。此处,我们尝试从阶级分析的视角探讨市场歧视的内在阶级属性及其市场经济中应对市场歧视的出路。
(一) 基于阶级的市场歧视内生于市场
很多人抱怨自己在市场中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但并不是所有抱怨是合理的。只有那些抱怨具有了普遍性,说明某一类人所面临的相似处境,才有可能表明市场歧视的存在。比如当黑人或者农民家庭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普遍要少于白人或者市民,我们有理由说,这里存在着教育市场的歧视。与传统的等级歧视不同,市场歧视行为在表面上都能够遵从一种形式的平等,尤其是交易过程中所体现的自由意愿,往往被市场主义者所推崇。但是,一旦撇开这种形式上的自由意愿,而从交易的潜在对象比较角度来看,市场歧视所蕴含的不平等非常突出。不管是就业机会不平等、受教育机会、健康条件的差距抑或其他,这种市场歧视都普遍存在,它内生于市场,是“商品拜物教”这一逻辑充类至极的必然结果。
影响市场歧视的因素很多,比如种族、地域、城乡、性别等等。本文仅仅从阶级的角度来审视市场歧视,指出它的市场歧视与阶级差别的内在联系,并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探讨克服市场歧视的出路。这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而是因为阶级的产生与市场内在相关,同时它对于所有的交易有着深层结构性的影响。比如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政治哲学界对于市场歧视的讨论往往关注于种族或者性别,这与美国的政治传统有关。我们的看法是,虽然种族和性别确实是构成市场歧视的一个重要变量,但也要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及其相应的阶级日益分化,阶级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事实上,许多市场交易中表面上的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根源是阶级歧视。比如美国就业市场中歧视黑人的现象,多数与其说是因为种族,毋宁可以归咎于阶级。美国各行各业的精英中都有黑人,黑人甚至能够当选总统。可见,黑人中的上层阶级所受的种族困惑会显著减弱,而白人中的贫民所面临的就业困难也普遍存在。这说明,在市场歧视的缓慢演进中,阶级的结构性影响要远大于种族、性别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基于阶级的市场歧视更具有结构性,它内生于市场。
所以如此,这与阶级的属性有关。阶级差距源于所有制上的对立,这种对立直接影响不同阶级的个人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存在着人们坚持要求的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即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合法权利获得各种有利的社会地位。具体而言,如法国的《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人人生而平等,都具有平等地履行义务和平等地享受诸如生存、就业、选举等方面的权利”,这是法律规定的人们所具有的形式上的一种机会平等。但是在自由主义市场当中,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却只能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没有做出努力来保证一种平等的或相似的社会条件,即不保证面向前途的相同的利用这些机会的手段、资源或能力上的平等,也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实质机会平等的实现在市场中受到了歧视,并且这种限制是自发形成的且一以贯之。无论什么时候市场上交易的决定都受到买者和卖者个人特征的影响,而不是受他们想要买卖的产品质量及特征的影响。如此,市场便产生了机会的不均等和经济缺陷。这种机会的不均等在人们的就业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即市场倾向于将各种职务的机会给予拥有高收入者和高收入家庭。“种族或性别歧视可以使确定的工作报酬更少——剥削,或被排除在好的职业之外。一个妇女以同等的技术获得一份与一个男人同样的好职业时,她只能得到更少的报酬,这种剥削产生了不公正的不平等。”*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王奔洲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90~91页。这个经验主义的例证表明,排斥是劳动力市场上歧视的主要形式,它产生了不平等的机会和不平等的收入,限制了实质机会平等,并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社会的不稳定。
实质机会平等在市场中得到限制的情况在获得资本方面的歧视状况下也比较突出。以获得资本方面的歧视为例,按照理想市场的客观标准,每个人都期望同样的投资工程面对同样的利息成本,但事实却证明这是一厢情愿。实际上,干得好的工程总能得到优惠待遇。富有的投资者经常可以拧开自己资金的龙头,而不是为他们的工程去借贷。当他们去借贷时,债主会对偿还有更大的信心,而并不操心工程的进展。对富人偏爱的反面就是对穷人的歧视。作为结果产生的非效率和机会不均等,阻碍了常人在开办企业、购买住宅、教育以及所有形式的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这些情况在职业决定和职业选择与获取方面比比皆是。以银行工作机会为例,由于富人本身就是银行的潜在利益对象,出于对订单利益的需求和再生产,银行在挑选工作人员时显然倾向于向富人阶级的子弟打开方便之门,而平常百姓的子弟由于缺乏这根利益链条从而被拒之门外也是常有之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需求凌驾于道德的公平正义之上。从更深一层次来看,市场对于实质机会平等限制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而主要的后果则是人们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倡导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美国为例,研究者指出,“美国最富的前五分之一人口(以及最富的前5%人口)所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是自1947年以来最高的,而最穷的前五分之一人口所占的相应份额,是自1954年以来最低的”*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0~181页。。
这种巨大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的存在事实,根源于市场对实质机会平等的限制。它表明,基于阶级的市场歧视内生于市场,并且进一步拉大阶级差距。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歧视将长期存在。在缺乏政治力量介入的前提下,基于阶级的市场歧视将构成影响经济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力量。
(二) 市场条件下限制市场歧视的出路
由于市场歧视内生于市场,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消除或者克服市场歧视是一种过高的期望。基于市场经济在全球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普遍现实,我们不讨论市场经济之外克服市场歧视的可能,而尝试给出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限制市场歧视的出路。基于阶级在市场歧视中的结构性作用,我们再度回到阶级分析。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涉及的广泛性,本文无法深入展开这个论题,而仅仅提出一种初步的设想。
第一,基于劳动阶级的立场来对待市场歧视。站在右翼的角度,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机制,不存在市场歧视。要克服这种粉饰现实的神话,我们虽然也可以诉诸基于种族、性别、地域的不平等从而证明市场歧视的存在,但归根结底,只有阶级具有结构性和内生于市场的特征,由此也决定,要真正能够长期应对市场歧视,就只能依靠阶级分析,并最终立足于劳动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说过:“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页。。通过自觉地对于歧视后果的阶级利益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种种繁杂错乱的歧视现象。而对于歧视与否的判断,其正义性一般地应当诉诸劳动阶级的立场。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非中性的*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它或多或少会有利于某个群体,而不那么有利于另外一些群体。因此在同一制度中受损的利益群体往往声称受到了歧视。但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声称而认定歧视。一种行为是否构成歧视,是否具有正当性,应当从该行为所倾向的阶级利益来判断。以所得税率为例,比例所得税貌似更公平,但相较累进税制而言,对低收入者的相对负担要重,因此它事实上构成了对劳动者的歧视。相反,遗产税看上去对于资产所有者构成了一种歧视,但由于它的理由是每个人进入社会的相对平等,因此有充足的理由来支持这一税制。在上述两种税制的评判中,由于劳动阶级的立场的坚持,我们可以得出大多数人认可的结论。
第二,现实的平等要求应该限制市场歧视。理想的社会不存在市场歧视,但是如果无法实现理想,我们就只能追求限制市场歧视。由于我们仍然处于阶级社会中这个事实未发生改变,也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歧视即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并且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消灭,除非达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歧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对于歧视即不平等现象,目前我们只能限制市场,尽力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逐渐地向理想的平等这一终极目标靠近。
比如人们进入市场之初就往往存在着先于市场的不平等及其由此导致的市场歧视。富人阶级的子弟拥有富裕的父母和幸福稳定的家庭生活;从具有挑战性和有效的教育中受益,上名牌学校;结交有才能和有影响力的朋友;获得健康和平衡的营养等等。用沃尔夫的话来说:“由于把不同境遇的人们带入市场的非人格的淘汰过程的非常不同的起点和天赋条件,以及他们所遭遇的程度非常不同的好运或坏运,因而产生了不公平。”*查尔斯·沃尔夫:《市场,还是政府——不完善的可选事物间的抉择》,陆俊、谢旭译,重庆出版集团2007年,第117页。对于这种无法改变的不平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也无法彻底消除,更何况消除的结果有可能导致其他方面更大的不公平或者无效率*此处涉及运气及其相关正义问题。右翼立场视运气为自然正义的分配,而左翼的运气均等主义则试图抹平运气的不平等后果。尽管笔者对运气均等主义抱有理论上的同情,但在现实政策上,应当区分不同类型的运气:对财产的初始分配要给予更多的重视,而基于智慧、美貌等天赋因素的运气不平等则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合理的做法就是对于市场歧视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壮大公有制,提高奢侈品税率,补助低收入家族,实施社会福利等等。
第三,社会团结应构成反对市场歧视的限度。基于实质的平等而限制市场歧视,这是劳动阶级立场歧视观的应有之义。但是,不能把这种歧视观理解为一种忌妒,其目的是把有产阶级的财富拉平到劳动者的水平。相反,对于市场歧视的正确观念还应当依归于社会的团结,即团结构成了这一反市场歧视的制度与行为的限制性价值*Lawrence Crocker指出,平等的动机应当是团结而不是妒忌。参见Lawrence Crocker.“Equality Solidarity,and Rawls’ Maximin”,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77,6,(3),pp.262~266。通常而言,团结蕴含着牺牲优势阶级部分利益的要求,本文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基于团结的考虑,弱势阶级的诉求不应过度。正如抗日战争时期,采用减租减息而不是土改更有利于推动抗战。。社会团结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通常而言,人们在歧视、平等、阶级等问题上的讨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蕴含着一种将社会割裂的倾向。一些判断标准即使是正义的,但由于实施时的倾向,总有一部分人经受了过多的损失,从而为社会割裂和仇恨埋下了根源。
提出这一团结限制的意义在于,反市场歧视——或者任何反歧视行为——虽然本身具备了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但其实施却应当考虑到人们的心理承受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以古代王莽的均田制改革为例,不可否认,这一改革具备正义性,可以说触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问题。但是,由于它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分裂,使相当一部分地主官僚背叛了王莽政权,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规模的起义和社会动荡。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正义的事业,由于违背了社会团结,最终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社会团结的要求并不是放弃正义的标准,而是提出如何更好地实施正义标准的问题。在反对市场歧视问题上,提出符合劳动者阶级利益的实质平等标准的制度和政策,本身并不是难事。困难的是在推行反对市场歧视的过程中满足社会团结的要求,这需要对于社会团结的深刻理解和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
四、 结 语
笔者尝试对阶级与市场歧视问题给出一个初步的探讨。说是初步,不仅仅是因为本文的论文容量有限以及更多深入的问题尚有待于将来,更重要的是,相对于目前中文政治哲学对于市场歧视的忽略,本文试图照射这一令人惋惜的盲点,以引起人们关注。
对弗里德曼的市场神话进行批判只是有关广泛存在的市场歧视获得哲学关注的一个起步。笔者期待中文政治哲学界能够将自己的哲学理论投射到这个每日广泛发生,却往往为人习之不觉的领域。通过对就业、生活、交际、社团、消费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的审视,政治哲学不但能够揭示出现存制度中的不合理并推动变革,同时也将大大丰富政治哲学的内涵。
●作者地址:李风华,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Email:acton.lee@163.com。
梁家琪,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涂文迁
◆
Class and the Market Discrimination:A Critique to Milton Friedman
LiFenghuaLiangJiaq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One of the important justifications for the market myth,of which Milton Friedman is a major advocator,is that market can eliminate the discrimination.Actually,the real meaning of this statement is to deny that there is market discriminations.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 of equal employment,this essay reviews three reasons for the market discrimination proposed by Milton Friedman: the essence of market discriminations is the individual preference; the outcome of market discrimination is a passive harm; to intervene the market discriminations will lead to restrictions to freedom of thoughts.The analysis shows that Friedman’s justifications are wrong and the market discriminations have their own logic,which could be found in the fact of unequal class.
capitalism; market discriminations; class; Milton Friedman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BZZ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