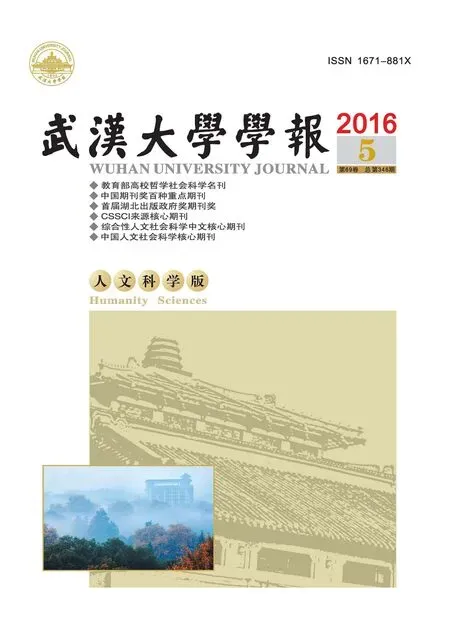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
刘丹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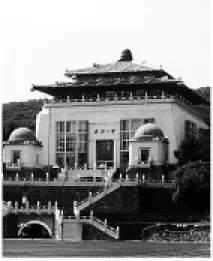
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
刘丹忱
“天下观”形成于先秦,它是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其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这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向心力。中国传统对外思想表达了一种“一”与“和”的原则化理念。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关系。这一秩序在近代以前数千年中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之特征的民族国家分立的标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由列强主导又建立了各种体系,在这一系列世界秩序建立之前都是一场场堪称人类浩劫的大规模战争。西方先行世界其他文明一步,实现了其文化的现代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而后挟工业文明之威,完成了世界性传播,并据此构建了世界秩序。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其文化当然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前提下贡献于世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天下观;天朝封贡体系;主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世界秩序观
一、问题的提出
“天下”是传统的中国概念,如今人们转换使用“世界”这一称谓,但“世界”一词源于印度佛教,其实,“世界”只是中国古代“天下”概念中的一部分。“天下”在古代中国内涵极其丰富,它是中国思想家建构出的最大的空间单位,既可指中国与四方合一的世界,也可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更是与“家”、“国”一起构成谱系的价值体,是“国”之合法性的最后依据。“天下观”是古代中国人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观。
面对近代以来之变局,中国传统的观念包括据此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涉外制度体系都遭遇到来自西方全方位的冲击,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这种遭遇是不是一种野蛮与文明的对抗,抑或是落后封建意识与先进资本主义意识的碰撞,还是一种分别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观念的遭遇,而各有千秋、互有长短呢?
当代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重视思想观念对一个国家涉外制度的影响①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传统观念对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作用,一般来说主要体现于涉外制度、政策以及中外关系形态,也就是王朝根据观念所提供的原则化理念去确定世界秩序的目标,并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因此,就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历史中观念的作用展开研究,不仅关系到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也关系到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度,而且可以直接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提供必要的资源。
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话题。从近代史上看,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并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迅速崛起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对于未来的东亚乃至世界意味着什么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大国的兴起必将对地区乃至世界格局带来重大的冲击,国家间力量对比失衡往往导致原有的国际秩序出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从反面印证了研究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能否成为一个有效的对外战略,其核心在于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否促使国家的发展与外部环境之间尽可能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因此,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研究国际秩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关系到我们能否从历史中寻找到资源为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启迪的问题。
二、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据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等人的观点,就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观①参见Benjamin I.Schwartz.“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66~288.。东亚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天下秩序观更是多有研究②中国大陆学者如李云泉的《万国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年;陈尚胜的《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等。日本学者如安部健夫的《中國人の天下覌》,载安部健夫《元代史の研究》附录一,東京創文社1972年;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韩国学者有全海宗的《汉代朝贡制度考》、《韩中朝贡关系概览》等论文,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等。港台学者如黄枝连的《天朝礼治秩序研究》(上、中、下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邢义田的《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载《永恒的巨流——中国文化新论﹒根基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
自商朝始,天下秩序的概念以《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最为系统。然而我们无法确定太史公所说的有多少是实况的反映,又有多少是利用后来的概念去描述的。例如,在他的笔下,五帝俱曾为“天下”诸侯推尊的“天子”。《五帝本纪》提到舜分天下为十二州,《夏本纪》有九州、五服之说。此外,在“中国”的四周,已经整齐地分布着戎夷蛮狄。天下、中国、四方、四海、九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似乎在夏代以前都有了,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无法证明。
充满疑古精神的古史辨派代表顾颉刚先生曾在《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一文中批评了以为中国从来就是统一的误解,他说:“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他们争战并吞的结果,从小国变成了大国,才激起统一的意志;在这个意志之下,才有秦始皇的建立四十郡的事业。”③顾颉刚:《古史辨》第2册上编,载[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民国丛书》65,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1页。但是近几十年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人眼界大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指出,“综观各地发现的殷商时期的方国遗存,它们的文化面貌尽管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在很多主要的方面和殷商文化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表明殷商文化的分布已经远远超过原先的想象,它不仅存在于黄河中下游,而且发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充分证实了殷商文化对于各个方国的强大影响。这些方国中,有的是殷商帝国的重要盟国,有的长期与殷商帝国处于敌对状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物质文化上都接受了殷商的文明。”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4页。这便说明文化统一的进程正为政治的统一奠定着坚实的基础。
也许可以说,中国人的天下观在夏商之时孕育出朴素的原型,到两周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周人对天下观的贡献并不在于延续了商殷以来较为机械的方位、层次观念,而是产生出一种文化上的天下观。“中国”和“天下”这两词在周初时正式出现在传世文献中。“天下”首见于《周书·召诰》中的“用于天下,越王显”,意思是说用此道于天下,王乃光显也。可见“天下”是一个由“王”来执政行道的世界。“中国”首见于《周书·梓材》中的“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此处的“中国”仅是“中原”之义。
“天下观”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形成于先秦时期。在《易经》、《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中,“天下”既指中国与四方的总合,也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中国与四方的“四夷”,共同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同时,“中国”的文明至高无上,天子受“天命”而执政于“天下”。
周天子对于王畿以外的地区不直接施政,而是视层次的不同,以不同形式的“礼”与他们互动。祭公谋父在劝周穆王不要征犬戎时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国语·周语上》)这甸、侯、宾、要、荒就是我们习称的五服。以往顾颉刚等学者曾认为文献记载多有漏洞而不甚可信。其实,罗志田先生的观点倒更令人信服,“此一叙述的不那么严整,恐怕反提示着其更接近变动时代制度的原状。”①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载《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对于不守职贡的各服,甸、侯、宾三服同属华夏,所以要刑、伐、征;而对要、荒二服则主要是德化感召。畿服理论中“无勤民于远”、“德流四方”的传统于此奠定。关于五服或九服的理论还见诸于《尚书·禹贡》、《周礼·秋官》、《周礼·夏官》等文献中。
中国历史上天下观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要向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来过渡。这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状态是暂时的,而人们追求的统一状态是常态,是主流。葛兆光先生分析宋代的“中国”意识,认为当时由于辽、西夏、金的兴起,宋朝士大夫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②参见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载《文史哲》2004年第1期。。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时常受到挑战甚至被异族所取代,但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却根深蒂固。入主的异族政权往往以华夏正统自居,沿用封贡制度,在与周边民族和邻国交往中确立自己的宗主地位。这便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具体到中国传统对外思想的原则化理念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清晰的问题。古代儒家的“天下观”,虽然认为“华夷有别”,但却又更主张“天下一家”、“王者无外”、“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由此可见,“一”与“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一种原则化信念,所谓“王者无外”、“定于一”、“一统华夷”、“和而不同”、“和为贵”,都表达了这种“一”与“和”的原则化理念。
在具有大同理想的天下观的统摄之下,涉及到“华夷观”、“王霸观”等几个从属观念,虽然大一统是儒家高扬的旗帜,但对“夷狄”,他们却倡导不干预主义的原则。东汉人何休在注疏《公羊传》时这样说:“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鲁隐公二年”条)把能够“守在四夷”视为中国安全的象征。《左传》中载:“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境。”(《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又逐渐形成了“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王者不治夷狄”等治边思想。在提倡王道的“亲仁善邻”政策的同时,天下观还一直保有“以力辅仁”的外交理念。《左传》在分析军事与道德关系时,这样总结:“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荀子·王制》中说得更加清楚:一个国家对外要做到“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是知王道也”。对于实施王道而言,广布仁义与保持强大的军力缺一不可,只有常备强大的军力足以抚顺诛逆,王朝的广布仁义才能真正收到效果。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天下观在观念层面的华夷之辨与制度层面的天朝封贡体系。
目前学术界有些学者片面强调中原汉族政权的华夷观对当时民族关系的恶劣影响,而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学生更是被灌输“华夷之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封闭僵化、盲目排外的思想,因此要加以严厉的批判。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因果倒置的凭空指责。历史真的如此吗?为什么长时段的史实和这样的说法不尽相同呢?事实上汉、唐,甚至包括宋、明,这些以汉人为主导民族建立的国家几乎都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对外来文明中优秀的东西一般是抱着学习、吸收的态度,这些时代的人民也好,知识分子的主流也好,较普遍地具有开放豁达的心态。
《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孔子最早也是最系统地提出了以“夷夏之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思想。在孔子看来,诸夏代表着文明和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应当以诸夏的文明改造夷狄的野蛮,使原本落后的夷狄向先进过渡,最终达到诸夏的文明水平,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但孔子并不排斥夷狄,甚至也没有歧视夷,《论语·子罕》中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认为有教无类,夷是可居之处,君子居于夷狄之地肩负着文化传播与改造的责任,因此夷狄可以教化不以为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孟子·离娄》)可见,具有夷狄血统的大舜和周文王却能被奉为华夏族的著名先王。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蛮族就是天生的奴隶”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高书文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39页。古希腊人把非希腊人都称为“蛮族”(Barbarian)。的种族优劣论有着天壤之别。
孔子以文化的野蛮与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最高标准。这一文化概念,不仅包括语言、风俗、经济等基本要素,而且更包括了周礼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孔子还认为夷夏可变,如果夷用夏礼,夷则进而为夏,如果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楚庄王问鼎中原,被视为“非礼”,而至鲁宣公十二年的晋楚之战,孔子在《春秋》中却礼楚而夷晋②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4~225页。。春秋诸家中,夷夏观最为明确的当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但儒家在明“夏夷之辨”的同时,并不排斥异族。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孔子相信夷狄可以教化的思想显然与希腊先哲柏拉图视“异族为异类”的种族观大相径庭。
中国人自己很早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政治疆域,更非一个种族疆域。中国所涵盖的民族和疆域不断以内聚的形式扩大的历史进程,印证了中华天下观中的华夷之辨所独具的包容性和向心力。春秋时代,秦、楚都不被目为中国,秦因为受“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直到秦孝公(前361-前337年)变法之前,仍不得参加中国诸侯的盟会,中国以“夷翟遇之”(《史记》卷五《秦本纪》)。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孟子·滕文公》)。可见直到战国中期,孟子还认为不行周公仲尼之道的楚国不属于中国。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被异族取代的现象并不鲜见,但华夷观念难以撼动。南北朝时的五胡、后来的蒙元、满清其绝大部分都融入到中国的此观念之中。正如雍正《大义觉迷录》所云:“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华夷互转的含义,概括起来就是“夷狄入华夏则华夏,华夏入夷狄则夷狄”!翻译成白话也就是说:“文明人如果接受了野蛮愚昧的观点和行为方式,那么,他就已经脱离了文明变成野蛮人;而如果一个曾经野蛮愚昧环境的人,进入了文明开化进步的体系,接受了文明,那么,他就可以变成一个文明人了。”
其实华夷之辨的原意是文明和野蛮之辨。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其本质是歌颂追求文明,反对倒退野蛮愚昧!不但是对中国,放到全世界,都是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至理箴言。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文化来区别,这比两千年后持着民族优越论来殖民世界、贩运黑奴的欧洲殖民者在道义上高多了。后来中国个别统治者出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目的据“华夷之辨”抗拒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绝非该思想的原意和主流。至于个别持有类似狭隘思想的人物其他文明的历史中都有,并非中华文明所独具。
关于天朝封贡体系③由于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有时人们把古代中国与周边邻国结成的关系称为“宗藩关系”,其实很欠妥当。因为它们之间并无像西方殖民宗主国对殖民地藩属国那样拥有支配和统治的宗主权。而中国封建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由于“册封”和“朝贡”两种活动的关联,才结成一种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因此成为“封贡关系”更为恰当。,是一种以儒学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在东亚建立的一种秩序,以天朝为核心,覆盖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封贡体系,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殖民体系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充满了掠夺和压迫的殖民关系。晚清外交家曾纪泽曾指出:“盖中国之于属国,不问其境外之交,本与西洋各国之待属国迥然不同。”④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第208页。对于这一点,一些国外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这里所涉及说的朝贡体制是一个内涵更为复杂的多元体系。它作为亚洲世界和国际秩序中的外交、交易原理发挥其作用,使各个国家和民族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又能够承认彼此的存在,它是一个共存的体制……近代的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经济关系是不能和它相提并论的”⑤加藤陽子:《戰爭の日本近代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02年,第66~77页。。封贡体系的不平等性主要体现在封贡礼仪与封贡表文当中,象征意义更为突出。这与近代条约体系的不平等性有本质的不同。
封贡体系中的等级性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天下观与华夏中心意识有关。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存在是由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而产生的。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缺少与其它发达文明之间的对等交流,华夏族日益增强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所以,在天下观的影响下,中国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把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其它国家都纳入封贡体系的范畴,以和平互利为目的,维护自身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发展,并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促进其臣属国的发展。“在华夷秩序中,各国的最高权力即使难免受到来自王朝内部政变的威胁,却一般不会因来自外部侵略而遭罹亡国的命运;国家之间一般也不需要借用国际条约来确认自己在领地内的最高主权;此外,在文化多元化和多神诸教并存的宽松氛围中,没有一种宗教力量可以形成对中华帝国最高统治权威的挑战。”①肖佳灵:《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这一秩序把东亚各国人民引导到了文明社会,促进了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制度和事业的发展,使这一地区的思想、道德、知识、社会管理、行政效率、经济和生活水准,在近代以前数千年中总体处于世界前列且较为和平稳定。该秩序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性质的。
外交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国家利益。中国古代对外思想中的“守在四夷”,便体现了维护天朝安全的一种方法——缓冲国(Buffer-States),物质上的“厚往薄来”所换来的不仅仅是属国对天朝地位的承认,更重要的是国防意义上安定的周边环境。“协和万邦”也是旨在形成一种对万邦进行协和的国际关系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儒学与东亚各民族的文化水乳交融,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逐渐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东亚各国虽然民族构成、历史发展、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但由于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因而信奉了包括天下观在内的一些共同价值观念,并共同巩固据此构建的封贡体系。
天朝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不平等国家关系。比如1644年,明末代皇帝朱由检殉国,“崇祯”年号却被朝鲜李氏王朝一直在内部公文中延用,加上朱由检在位的17年,前后一共使用了265年。堪称中国皇帝年号使用年限之最。中国的朝贡国这种远超现代国家利益考虑的做法,充分说明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的王道政治理念的效用,使朝贡国并非力之不逮,实心悦诚服也。
再比如,越南人接受儒家的夷夏之辨观念,越南人经常自命为“中国”、“中夏”,而以中国以外的其他民族为“夷狄”。越南人潘叔直编辑的《国史遗编》记载,1842年,阮朝遣使往中国,到北京后清朝官员让他们住进“越夷会馆”,越使大怒,令行人裂碎“夷”字,方肯入内。又作《辨夷论》以示之,其义略谓:“越南原圣帝神农氏之后,华也,非夷也。道学则师孔孟程朱,法度则遵周汉唐宋,未始编发左衽为夷行者。且舜生于诸冯,文王生于岐周,世人不敢以夷视舜、文也,况敢以夷视我乎!”
毫无疑问,天下观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使用了政治、军事资源,正所谓“以力辅仁”,但是更多的则是依靠思想和道德自身的力量。《贞观政要》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广;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强。封域之外,声教所不及者,不以烦中国也。”②吴兢:《贞观政要》,岳麓书社2000年,第300页。天下观中蕴含的儒家德教思想改变世界常常是以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通过心灵的感化而显示出来。它超越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界限,甚至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克服宗教和种族的顽固偏见,为自己开辟广阔的传播空间。可见,天朝封贡体系主要不是依靠武力维系,更有效的则是依靠华夏一整套的德教礼治。因此,该秩序具有一定的非强制性。
到19世纪60年代为止,中国与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琉球等,一直保持着朝贡册封的关系。根据1818年《嘉庆会典》记载,朝鲜对中国是一年四贡,琉球是两年一贡,越南也是两年一贡(贡使是两次一起派遣,所以也可以说是四年一贡),泰国是三年一贡,老挝则是十年一贡。19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的封贡体系崩溃,1875年日本占领琉球(1879年日本将琉球废藩置县),1885年丧失越南,1886年丧失缅甸,1895年丧失朝鲜。1901年,清朝被迫放弃了传统的朝贡礼仪而接纳了西方的外交礼仪,则标志着传统天朝上国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当然,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文明无一例外地败给了以欧洲为代表的工业文明。
三、《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的西方世界秩序观
回顾欧洲的历史,我们发现分裂的状态是欧洲古代、中世纪时代的主旋律。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ies of Westphalia)的签署,似乎战乱频仍的欧洲才变得有序了一些。但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特别是罗马文明)那种以战争作为生产方式的文明特征并未改变,地理大发现、贩运黑奴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海外殖民无一不是以强大军事力量来实现的。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们为近代西方的世界秩序观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法国的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在《论共和国六书》①Jean Bodin.The Six Books of a Commonwealth.K.D.McRae(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法文本1576年出版,拉丁文本1586年出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主权是共同体所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②让·博丹:《主权论》,李卫海、钱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此中译本是从博丹的《论共和国六书》中摘译的有关主权理论的四章)。。“他们把君权同罗马法中的治权和封建时代的领主权融合到一起,确立了近代法律制度的主权地位。”③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4页。另一位则是荷兰的著名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他在1625年发表的《战争与和平法》发展了博丹的主权学说,认为“凡行为不从属于其他人的法律控制,从而不致因其他人意志的行使而使之无效的权力,称之为主权”④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3页。。格劳秀斯从主权对外独立的方面补充了博丹的理论,他的国际法思想是建立在罗马法体系的基础上,以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理论为基石,把罗马私法理论涉入国家关系中⑤刘丹忱:《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政治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324页。。简言之,主权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巨人是在继承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做出了现代性的转化,从而建构了近代西方世界秩序观的理论。当然,这些内容不仅成为欧洲国家间战争与和平时期需要遵守的惯例,而且也成为欧洲国家征服其它文明地区的理论依据。其中包含着一些扩张、劫掠有理的所谓“法律依据”,是与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历史走向背道而驰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是近代国际法的实际源头,又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美国学者莱恩·米勒(Lynn Miller)在《全球秩序》一书中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至少奠定了一种欧洲体系的基础,而在当代,这一体系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⑥Lynn Miller.Global Order:Values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4,p.20.。《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它建立了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之特征的民族国家分立的标准,还在实践上为古典罗马法权威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主权。主权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并不承认任何国家内部其他政治实体,也不承认任何来自外部的更高实体。事实上,现代国际关系秩序是基于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法之上的。
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欧洲仍然战乱不断,他们似乎更愿意接受刀光剑影后达成的平衡,但此后欧洲国家间的战争都是以捍卫民族国家利益的名义而战,不再似中世纪那样打着某一神圣的旗号而战。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为利而战,不再为所谓的义而战了。国家之上不再有一统天下的权威,哪怕是神权。无论战争如何血腥残酷,战胜国从战争中攫取到多么巨大的利益,在表面上它们都信誓旦旦地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为了解决各国在势力范围方面的争端,建立能达到某种平衡的世界秩序,由列强主导又签订了许多和约,建立了各种体系,包括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等。是堪称人类浩劫的大规模战争达成了某种平衡的世界秩序。
西方有民族国家观念、无天下观念,因此难以走向一体化。即使建立了像马其顿、罗马帝国这样的大帝国也不会长久。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体系足够庞大,但最后还是要瓦解,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天下观去统摄,早晚要分崩离析。那么他们有民族国家观念,是不是就会尊重民族自决了呢?也未必。他们容易以此为依据挑动其它国家搞分裂、闹独立,但不适用于他们自己。举个反例就清楚了。北爱尔兰闹了那么多年的独立,大英帝国还是不许可。
尊重主权和民族国家概念的深化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也不可过分夸大。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作为世界两大外交体系是不可割裂而言的,它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外扩张性和侵略性,这与它们形成的历史时期和背景有关。条约体系是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威斯特法利亚会议的召开而产生的,是一种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也是欧洲人进行殖民扩张的重要工具。特别是殖民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帝国主义国家同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附属国之间形成的一方压迫另一方的不平等的国际外交体系,很难与尊重主权和民族国家的理念结合起来。
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西方关于世界秩序观研究的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更多地关注于文明、文化,出现了三个最突出的学说,即“文明冲突论”、“软力量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承认民族国家现在仍将是国际事务中最重要因素的同时,强调文化和文明对国家间的冲突与联合所产生的影响,并预言文明的冲突将取代超级大国的竞争①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约瑟夫·奈的“软力量论”认为,同化性力量是一种能力,它需要一个国家的思想具有吸引力,同时某种程度上又具有体现别国政治意愿的导向。他还谈道,类似于经济、文化这样的软实力需要同军事力量这样的硬实力相结合而互补,软力量更能使他国心悦诚服地仿效,其对世界的影响效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硬力量②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5页。。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亚历山大·温特则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指出,社会的共同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使结构具有动力,以往的理论强调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动力,观念则无足轻重。但温特认为,观念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建构作用。共同观念的改变不会轻易完成,因为有体系的文化很难改变,而有底蕴的大国凭借其实力更具有创新文化的能力③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43页。。
可以说,西方传统的世界秩序理论以实力和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强大实力背后更深刻的文化价值观,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是该国外交行为的力量源泉,是国家外交行为信心的基础。亨廷顿指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④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29页。
四、结 语
当今的国际秩序再次面临着重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无疑是硬力量对比之争,但也是理念之争。指导、引领体系之间转变的外交理念是一种看不到的力量,这种外交理念是体系之间碰撞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体系的转变。如果一种文化价值观得到更多国际集体的认同,它就会对整个国际秩序体系产生作用。假若一个国家明确国际体系未来发展的方向,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力量就会由弱变强,反之,力量就会由强变弱。
以世界秩序观为视角,研究中国与欧洲长时段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天下观、华夷之辨理论等具有一定凝聚、向心、尚和的力量,而欧洲民族国家观念、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理论具有一定分裂、离心、尚争的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必定会存在着平衡中的失衡或动态中的相对平衡等状态。如果说20世纪的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话,可以说21世纪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稳定、和平、安全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我们判断世界是否处于有序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尺。
近百余年,西潮东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人或抱残守缺、妄自尊大,或尽失自信、以夷变夏,于是对西学做无根之嫁接。我们知道文化的兴衰是与能否纳新、能否迎战相呼应的。犹如江河之于细流,拒之则成死水,纳之则诸流并进,永葆活力。文化之活力在兼容并包,同时须纠正自断脐带、漠视传统的错误,应使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衔接。对于一个伟大民族而言,传统与现代应该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分割断绝。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潮流是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又是对国家主权理论的严峻挑战。各国在更高层次上做出理性的选择,可能会回归国家利益本位,对主权做一定的制约、限制乃至有限的让渡。21世纪的另一个焦点是亚洲的持续快速发展。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8月在《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一文中预测,2050年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0%上升至50%。各大国都在这一地区寻求推动多边合作,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其文化当然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西方先行世界其它文明一步,实现了文化的现代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而后挟工业文明之威,完成了世界性传播,并据此构建了世界秩序。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扩大、民族融合是文化与民族内聚而形成的,并未伴随着以轴心向外辐射的大规模军事扩张,这一点同西方的大国崛起恰恰相反。此一特质既动摇了各版本“中国威胁论”的文化根基,也会增强我们推广自己外交道德的自信。目前首要的任务是着手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逻辑上,完成一个从“世界的中国”到“中国的中国”的升级与转型,这种转型也应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桂 莉
◆
The Tianxia(天下)Worldview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View of World Order in Occident
Liu Danche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he Tianxia(天下)worldview was origined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presents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orderofworld.Itssupreme idea is universal harmony.All these made Chinese culture have the meaning to embrace non-Chinese,and formed the unique centripetal force of the Chinese.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howed principles of “one”and“unity”.We have to discriminate 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n the tributary system.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argument between Chinese and barbarians,which was not merely nationalism.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ributary states was neither equal to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ributary system,nor to colonial powers and colonies.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his kind of order is peace and mutual benefit.The Peace Treaties of Westphalia established the criteria to identify nation state according to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specting for sovereignty and deepening the conception of nation had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but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The powers dominated a set of systems after The Peace Treaties of Westphalia.The world order was founded after great wars even catastrophes.The Occident took the lead in modernizing the culture,extracted preeminent values and then expanded world-widely with the power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to found the world order.As the only continuous civilization on the earth,the Chinese culture has the great values that could be conductive to the whole world.The key question is how the Chinese culture modernizes itself,meanwhile benefits others.
the Tianxia(天下)worldview;tributary system;The Peace Treaties of Westphalia;sovereignty;the view of world order in occident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BSS021)
●作者地址:刘丹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8。Email:liudanchen2001@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