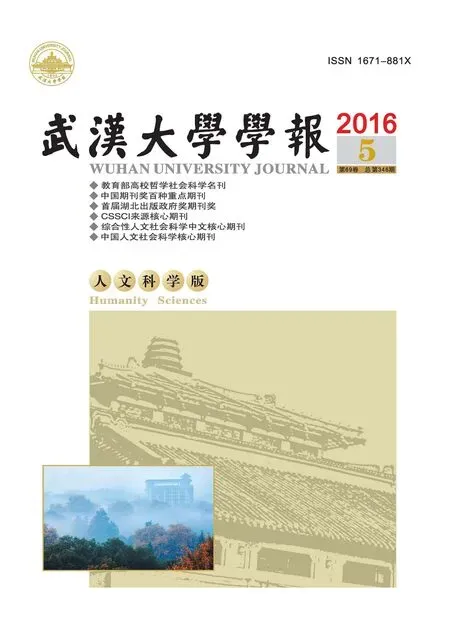“反公众”何以为“反”
——一种多元视角下的公共领域思考
周 翔 程晓璇

“反公众”何以为“反”
——一种多元视角下的公共领域思考
周翔程晓璇
新派公共领域理论学者提出的反公众和反公共性以一种多元的视角批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基于霸权建构的排他性,揭示公共话语的权力关系。我们需要从三方面阐释理解反公众之反的本质内涵:一是反公众所隐含的对立性,也即成员对自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地位的充分意识;二是作为社会空间的反公众,具有从主流公共领域的传播流中退出和再进入的二元功能;三是反公众向外追求公开性。而反公共性代表了反公众的言说方式,是与主流话语积极竞争的传播行动。反公众和反公共性概念对中国本土研究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揭示国内舆论场多元话语竞争的状态,并关注中国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少处于从属地位的边缘话语实体,从而以一个多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为主流媒体所忽视的话语问题。
反公众; 反公共性; 公共领域; 公共话语
反公众(counterpublic)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中提出来的,与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neo-Habermasian public sphere theory)的兴起难解难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自问世以来即在学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哈贝马斯原理论几个难以回避的缺陷上:对资产阶级理性讨论的过分理想化、对公共领域多元性的忽视、对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默许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一如既往地对大众媒介的过分悲观等*C.Calhoun.“Introduction: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in C.Calhoun(ed.).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2,pp.1~51.。原始意涵中的公共领域虽然是一个从未实现过的乌托邦式的存在,但在讨论民主协商和公民社会时自有其重要意义,因而不少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值得被重构而不是被舍弃的概念*参见如下学者的研究:K.M.DeLuca & J.Peeples.“From Public Sphere to Public Screen:Democracy,Activism,and the ‘Violence’ of Seattle”,i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02,19(2),pp.125~151;N.Fras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Public Opinion in a Post-Westphalian World”,in Social Text,2007,25(26),pp.56~80;K.Phillips.“The Spaces of Public Dissention:Reconsidering the Public Sphere”,in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1996,(63),pp.231~248.。哈贝马斯之后,大量学者的批判和延伸重新建构了公共领域的内涵,旧瓶已然换上了新酒。为区别于原理论,由批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发展而来的新理论被笼统地称为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这些来自于多学科领域的批判和反思将公共领域概念模式向多样性这一方向推进和发展。与原理论相比,它们更关注于社会权力结构、差异和排他性的议题,不再将公共领域视为哈贝马斯的那个单一全面式的布尔乔亚的公共领域。
在诸多新理论中,反公众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关键概念。它的提出标志着某部分群体的公众不但是作为话语实体星群之一分子而发展,也同时是作为一种对排除了潜在
参与者的较为广泛的公众的替代而得以明确表达*R.Asen.“Seeking the ‘Counter’ in Counterpublics”,in Communication Theory,2000,10(4),pp.424~446.。反公众一词的使用最先始于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R.Felski.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Feminist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9.。其背景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维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层出不穷,社会研究的命题和范式也随之悄然发生改变。研究者从历史记录中发现,诸如女性、工人、有色人群以及同性恋者这样的从属社会群体有利于形成替代性公众,也即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所提出的次反公众(subaltern counterpublic)*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in Social Text,1990,25/26,pp.56~80.。比如19世纪的美国女性次反公众,她们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藉由刊物、电影、讲座、会议、节庆和聚会等等这样一些公共领域,催生和传播了许多描述社会现实的新词语,包括“性别歧视”(sexism)、“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和“婚内强奸”(marital rape)等,通过这些词语表达投射出被主流公共领域忽视的、女性自身的需求和认同。这个时期来自不同阶级和种族的北美女性在实际生活中建构了通往公共政治生活的通道(比如仅有女性参加的志愿者协会包括慈善和道德改革的社团等),尽管她们被排除在正式的公共领域之外。也正是南希·弗雷泽在对哈贝马斯的四大预设进行批驳、以此重新思考公共领域时,将反公众一词由女性主义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引入社会科学。
一、 从公共领域四大预设的消解到次反公众的提出
在反思原公共领域理论中,不少新派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哈贝马斯的布尔乔亚式理念,在这种布尔乔亚式的理念下,公共领域是单一全面、无所不包的,所有公民作为个体的私人进入到此领域讨论国家相关事务和活动。受到对社会复杂性和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认识的激发,新派学者开始从单一模式转向寻求更为多元化的模式,比如塞拉·本纳比(Benhabib)的交往多元模式(plurality of modes of association)*S.Benhabib.“Toward a Deliberative Model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in S.Benhabib (ed.).Democracy and Difference: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67~94.、查尔斯·泰勒(Taylor)的嵌套式公共领域(nested public spheres)*C.Taylor.Philosophical Argument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以及杰勒德·豪泽(Hauser)的网状结构(reticulate structure)式公共领域*G.Hauser.“Civil Society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ublic Sphere”,i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1998,31(1),pp.19~40.等,这些公共领域的概念化阐释无一不强调多元公众的连接关系和网络。在众多的新概念模式中,最常被引用的文献之一当属南希·弗雷泽的《公共领域再思考:对现实既有民主的批判》一文,她在文中指出并批驳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所隐含的四个预设,以此奠定了反公众的讨论框架。
弗雷泽首先从另一种历史眼光来分析,认为对公共领域的布尔乔亚式的概念理解是以一种社会秩序为前提,在这种秩序中国家界限分明地与私有化市场经济相分离,社会与国家也是清清楚楚互为分离的,而这种分离被假定是排除私人兴趣的公共讨论形式的基础。然而,这些条件最终随着非布尔乔亚阶层获得了公共领域的控制而销蚀瓦解。社会因阶级斗争而极化,公众也因碎片化而分解为利益竞争群体的大众(mass)。而且,随着福利国家大众民主的兴起,社会与国家开始相互勾连缠绕,原本是对国家的一种批判性监督意义上的公共性让渡于公共关系、大众媒介化的舞台表演以及对民意的制造和操纵*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59.。
在概念体系建构上弗雷泽指出,公共领域这个布尔乔亚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概念隐含着四个核心预设:1.公共领域的对话者有可能将各自的地位差异悬置起来,“好似”他们是基于社会平等来协商,也就是说,社会平等并不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2.竞争公众的多样性必然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向更大民主的前进,一个单一而全面的公共领域总是要比一组多元公众更为可取;3.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严格限定在对公共福祉(public good)的审议上,私人利益和私人议题的出现总是不受欢迎的;4.有效运转的公共领域要求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截然分离*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p.62~63.。这四个预设恰恰是弗雷泽重点批判的靶子。
对于预设一,弗雷泽从对悬置地位差异的功效的错位理解入手,来破解同等参与(participatory parity)的可能性。她认为,在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下,人们不可能实现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同等参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既是未实现的乌托邦理想,也是一种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进行霸权统治的工具。哈贝马斯单一全面的公共领域实际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白人男性的公共领域,边缘、从属群体(妇女、同性恋、少数族裔等)难有藉此发声的余地,反而会被强制纳入主流强势阶层的“我们”意识中,被迫接受强势者虚假的共识。女性被排除在这种公共领域之外,正是基于社会赋予她们的性别地位。以往女性主义研究已揭示了诸多同等参与的非正式障碍,比如在混合性别的审议场合,男性打断女性的时候远多于相反情境,男性发言也多于女性。社会不平等的实际存在却被当做好似不存在,这种悬置并不能促进同等参与。相反,这种悬置往往有利于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使协商成为其支配的面具,从根本上并不利于从属社会群体,而这些群体通常缺乏平等的近用渠道和平等参与的手段。而且,布尔乔亚式的公共领域其实是假设一个“零度文化的空间”,但这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因为在分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ies)里,赋权不平等的社会群体容易发展出受到不平等重视的文化风格,其结果就是发展出强大的非正式压力,将从属群体在日常生活和正式的公共领域中的贡献边缘化。
因此,针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里单一的综合公众,弗雷泽提出了多元的公众(multiple publics)这样的理念,并认为实现真正平等参与的途径是竞争公众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她进而评估了在分层社会和平等主义多元文化社会(egalitaria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这两种社会中多元公众的相对价值,以此来批驳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预设之二。弗雷泽通过历史记录(即前文所提到的北美实例)的考察指出,在分层社会中,作为“与公共领域平行的话语竞技场”的非正统的次反公众(sub-counterpublic)发挥着论争功能,也即他们通过创造和传播对抗性话语而扩大了话语论争,并形成对自身认同、兴趣和需要的对抗性解读。弗雷泽认为,这些被哈贝马斯视为公共领域碎片化迹象的次反公众,虽然不一定都是道德的、良性的,但实际上拓宽了话语空间而有利于民主政治*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67.。
而在平等主义多元文化社会里,在没有结构性不平等的文化多样性条件下,一种单一的公共领域是不是更合乎多元公众的心意呢?弗雷泽自设的这个问题从三个方面得到了否定的回答:首先,公共领域不单是形成话语意见的竞技场,同时也是形构和确立社会认同的竞技场。这就意味着参与不单是陈述中立的命题内容,更意味着参与者能够在道出自己心声的同时,通过习语和风格来建构和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零度文化的空间。其次,在平等主义多元文化社会中,公共生活不可能构成一种单一全面的公共领域,那等于是通过一个单一顶板式的透镜过滤掉多种多样的修辞和风格标准,而且这种透镜并非真正的文化中立,它实则是有效地使某一文化群体的表达标准优越于另一群体。再者,跨文化差异的交流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个人说要求将差异悬置起来,那么这样的交流必然是不可能的。毕竟,所谓公众的概念是预先假定其内部参与者的观点具有多元性,因此允许内部差异和对抗性的存在*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p.68~69.。总而言之,在弗雷泽看来,无论是哪种社会,多元公众比单一公众会更好地实现同等参与。
这种多元性理念同样也体现在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话语议题限制的批判上。她认为,批判理论需要对私人和公共这些词语采取一种更为严厉、更加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词语不是简单的社会空间指称,它们是文化归类和修辞标签*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73.。在政治话语中,它们是经常被用来使某些利益、观点和话题丧失合法性的霸权词语。比如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有关家庭私生活的修辞试图将某些议题和利益个人化和家庭化而将它们排除在公共辩论之外。即使一个妻子在家受到重创,也可能因其受虐之事被打上了私人标签而无法出现在公共话语中;当涉及工作场所的民主问题讨论时,也可能因为个人经济利益的标签而遭到排斥。也就是说,在布尔乔亚式的公共领域中,即使消除了分层限制,议题类型也阻碍了妇女和工人参与到公共讨论中来。
至于建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预设之四,弗雷泽的解构策略是,首先指出该预设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取决于如何理解公民社会。如果认为这一词语所表达的是一种私人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就会坚持让它与国家分离,也即捍卫古典自由主义,其必要前提条件是受限制的政府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然而,这样的资本主义是不能促进作为同等参与前提条件的社会经济平等的,而同等参与又恰恰是民主的公共领域所必不可缺的。如果按照另外一种理解,也即公民社会这一表达意味着既非经济亦非行政的非政府或亚级(secondary)社团的联结,那么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界限就应该泾渭分明,如此才能保证一个有效运作的公共领域,确保更大范围的检验*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74.。这里强调的是私人的个体,他们不以任何官方身份参与公共领域,因为公共领域是作为国家的对应物、提供非官方话语意见的讨论空间而存在的。公共领域的这种超政府特征赋予在此空间所产生的公共舆论以独立、自主与合法性的光环。在此意义下,公民社会与国家的明显分离是可取的,它促进了弗雷泽所指的弱公众,其话语实践仅限于意见形成,而不包括决策制定。而这也恰恰是公共领域将公民社会与国家绝然分离这种预设可能导致的一个悖论;也就是说,如果要绝然分离,那么在逻辑上,这种弱公众的话语实践就不能向决策制定扩展,否则就会威胁到公共舆论的自主,公众也就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而失去对国家的批判话语监督的可能性。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意见形成的层面上而无法延伸至决策制定的话,这种批判话语监督也就必然失去其实质意义。对此,弗雷泽提出了以自治议会为代表的强公众一说,其话语实践包含了意见形成和决策制定这两个层面。随着议会自治的实现,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也就模糊了,但这种模糊在理论上却代表了一种民主进步,因为公众意见的力量因意见转化为权威决定而得到了强化,并由此获得了权力。因此弗雷泽认为,任何要求(联合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绝然分离的公共领域概念都无法想象自我管理、内部公众协调和政治问责等这样一些民主平等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形式*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p.75~76.。
简言之,弗雷泽及其后来者的批判要旨在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所谓的普遍性实际上是将某一特殊精英群体的主观性表现为客观的常态范畴,是基于霸权建构的排他性领域。正是在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以一种多元视角进行批判时,弗雷泽针对单一而宽泛意义上的公众提出了次反公众这一概念,其意义在于建构“一种关于公共生活形式的批判政治社会学,这种公共生活有多元但不平等的公众参与其中。这意味着将不同公众之间的竞争性互动理论化,并识别出致使其中的一些公众居于从属地位的机制”*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70.。后来学者*比如罗伯特·阿森和迈克尔·沃纳两位学者,参见其相关论述:R.Asen.“Seeking the ‘Counter’ in Counterpublics”,pp.424~446;M.Warner.“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Public Culture,2002,14(1),pp.49~90.将弗雷泽带有亚群体意味的次反公众进一步扩展为反公众,认为反公众的概念模型能够揭示公共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凸显出不同公众之间的竞争、话语实践中的排他性和某些公众克服排他性的尝试。
二、 “反公众”之“反”:对立性及其功能的辩证性
反公众也是公众,拥有和公众类似的一般性特征:通过话语自发组织;以陌生人为目标方向;其公共言说兼备个人与非个人成分;注意力是形成其成员的最低门槛等*M.Warner.“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pp.49~90.。但弗雷泽之后的学者并不是将反公众限定为某类人群,而是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社会话语实体和话语自反性流通的社会空间,不能化约为人群、地点或者话题,而将此作为反公众地位的必要标签*参见阿森和沃纳的相关论述:R.Asen.“Seeking the ‘Counter’ in Countepublics”,pp.424~446;M.Warner.“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pp.49~90.。除了所有公众都具备的特征外,要真正理解反公众的内涵本质,则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做进一步的阐释:
首先,反公众隐含了对立性(oppositionality),这意味着反公众成员对自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地位有着充分的意识。弗雷泽最早对亚反公众的描述指向社会中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这部分群体,以此指代对其身份、利益和需求的对立性诠释。因此在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看来,这听起来像是在哈贝马斯对理性公众的经典描述之前插入了“对立的”这一限定语。沃纳认为,反公众之所以为反(counter),是因为其成员意识到自身居于从属地位,这一特定术语所要划清文化界限的不单是较为广泛的一般公众,同时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公众。“冲突不仅扩展至思想观念和政策问题,而且延及到构建公众的话语类型和表达方式,以及媒体间的层级。构成它的话语不仅是另一种不同的习语,而且是在其他背景下被视为敌意或不得体的语言。”*M.Warner.“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p.86.
不同于效仿家庭亲属关系、以友爱忠诚为导向的社区,反公众的团结和互惠扎根于受排挤和被剥夺的集体经验;不同于强调自身独立性的自治公共领域,反公众着重寻求对主流公众的挑战和抗争*J.Downey & N.Fenton.“New media,Counter Public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in New Media & Society,2003,5(2),pp.185~202.。比如在一个同性恋反公众内,无人隐匿在“柜”中,因为寻常言说中构成藏匿个人的“柜体”这一异性恋预设在这样一个公众群内被搁置起来,个人对污名的抗争被转移为公众模式之间的冲突。
反公众的对立性表现在何处?在罗伯特·阿森(Robert Asen)看来,对立性可以表现在人群的身份认同,这个角度对解释某类人群被排除和支配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历史行之有效,但容易忽视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和个体归属的多重性,从而将对立性简化为基于同质性、有严格内外之别的群体认同,否认基于异质性的联合作为反公众的参与来源,而过于强调群体认同会掩盖政治经济分层对反公众的重要影响。对立性也可以表现在产生反公众话语的论坛,这个角度突出的是情境因素和机构布局对参与反公众的影响,但包容更多差异言论的论坛未必是生成反话语的理想场所。对立性还可以表现在由反公众进入更广泛公众视野的议题上,这个角度可以揭示出话语竞争和变革的过程,但它一般只关注议题从边缘到中心的单向路径,而且免不了陷入同公共、私人两分法一样的困境——如何预设议题的反与非反?*R.Asen.“Seeking the ‘Counter’ in Counterpublics”,pp.424~446.阿森的论述提醒了研究者论及反公众时容易陷入的二元对立的简化论误区。
其次,作为社会空间的反公众具有从主流公共领域的传播流中退出(withdrawal)和再进入(reentry)的二元功能。早先在费尔斯基的女性主义反公共领域模型中,反公众对内指向“女性在共同体和团结意识之下的性别认同”,对外寻求女性主义诉求的合法性,通过政治活动和理论批判挑战现存的权威结构*R.Asen.“Seeking the ‘Counter’ in Counterpublics”,p.429.。弗雷泽同样强调了反公众的两种功能:“一方面,它们为撤退和重新组合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它们也为针对更广大公众的动员活动提供基地和训练营。”*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p.68.也正是这种辩证性使得反公众部分抵消了层级社会中支配群体的参与特权,拥有解放性的潜力:在精英霸权无法监视和压制的空间内形成联合、构建认同和自身的话语,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对抗的话语散播到更广泛的公众,以求克服被排除的地位。
第三,反公众向外追求公开性的这一面值得注意。反公众不同于有意自我隔绝的飞地,“长远来看,它是反分离主义的,因为其选择的是‘公开’的取向——将从属群体的话语传播到更广阔可见的场所”*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p67.。成员们知道他们是某个潜在的、更大的公众的一部分。沃纳也认为,反公众和其他公众一样,通过面向不确定的陌生人述说而形成。虽然包含了风险和斗争,话语流通的边界会逐渐向外扩散,且对变革有所诉求*J.Downey & N.Fenton.“New media,Counter Public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pp.185~202.。多克斯塔德(Doxtader)则指出,“‘反公众’的‘公开取向’看上去标记了一个对达成理解的程序上的承诺”*E.Doxtader.“In the Name of Reconciliation:the Faith and Works of Counterpubilicity”,in R.Asen,D.C.Brouwer (eds.).Counterpublic and the State.Albany,NY:SUNY Press,2001,pp.59~86.,它本身包含了两个目的:将对立性的争论引入公共领域,以一种保留协商民主共识性本质的方式。
三、 “反公共性”与“反公众”话语传播行动
不同于哈贝马斯对理性协商达成统一共识的推崇,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采用了多元主义的视野,对议题的公共性有更多拷问。在弗雷泽看来,公共议题和私人兴趣之间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分别。历史上,家庭暴力曾被囿于私事范畴,经过女权主义者长期的话语论争才被纳入公共意识当中。话语论争决定了什么能够算作公共事务,民主公开应该保证少数团体享有说服其他人的机会,使从前非公共的事物成为共同关切的事物。
弗雷泽积极赞同话语的竞争,认为“亚反公众的扩散意味着话语论争的扩大,在层级社会是好事儿”*N.Fraser.“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p.67.。反公众话语与更大范围受众的接触构成了反公共性(counterpublicity)——类似于“公开上市”的活动*R.Asen.“Seeking the ‘Counter’ in Counterpublics”,p.441.。但是不像反公众,对于反公共性,学者们在研究中始终没有使用过一个严谨而统一的定义。芬顿和唐尼(Fenton & Downey)直接把反公共性与符号论争(symbolic contestation)等而视之*N.Fenton & J.Downey.“Counter Public Spheres and Global Modernity”,in The Public, 2003,10(1),pp.15~32.;而在多克斯塔德的解释中,反公共性是“异议表达内共识基础赖以培养的修辞过程”*E.Doxtader.“In the Name of Reconciliation:the Faith and Works of Counterpubilicity”, pp.61~62.;布劳威尔(Brouwer)则认为它命名了“为‘反公众’服务进行的具象性、政治性干涉的行动”*D.C.Brouwer.“Counterpublicity and Corporeality in HIV/AIDSZines”,i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05,22(5),p.345.。总而言之,反公共性指涉的是一种与“公共性(publicity*“Publicity”一词在英文文献里具有多重涵义,有时指的是“公开性”,有时则指“公共性”。)”相对的传播行动,目的在于动摇占主流公众的意识形态霸权,它揭示的是反公众外向扩张寻求更广大公众的一面,回答的是反公众如何言说的问题。
对于反公众向外进行话语论争的一面,学者们的关注点多在于:带有亚文化色彩的利益团体、社会组织或社会运动等主体独特的传播实践*参见如下学者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M.Stephenson.“Forging an Indigenous Counterpublic Sphere:The Taller de Historia Oral Andina in Bolivia”,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2002,37(2),pp.99~118;B.Dobler.“From Socialismto ‘Sentiment’: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ties,Counterpublics,and Their Media through Jew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in Communication Theory,2011,21(1),pp.90~109; K.DeLuca,S.Lawson & Y.Sun.“Occupy Wall Street on the Public Screens of Social Media:The Many Framings of the Birthof a Protest Movement”,in 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2012,5(4),pp.483~509.,以及它们与媒介系统的关系——被排除的话语实体如何通过大众传媒把冲突由边缘带至公共生活的中心,激起更广泛的公众讨论?抑或建立起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的渠道进行传播活动?唐尼和芬顿认为,主流公共领域是动态而非静止的,会有周期性震荡和结构变化,这为反公共性提供了进入的机会,虽然其议题常按大众媒体的要求来被框架化。欧文斯和帕尔默(Owens & Palmer)分析了1999年西雅图抗议活动中,黑色方阵(Black Bloc)的无政府主义者如何采用暴力手段来“制造新闻”*L.Owens & L.K.Palmer.“Making the News:Anarchist Counter-Public Relations on the World Wide Web”,i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03,20(4),pp.335~361.,利用主流媒体对其的负面报道来扩大受众关注,再利用线上的另类媒体进行反向的公关宣传。德鲁卡等人将这种暴力视为“符号性暴力”,因为它针对的对象是财产而不是人,为的是吸引媒体注意力。他认为“暴力是烦扰的,但对于被政府机构和公司权力排除的人们而言,符号性的抗议暴力是登上公共荧幕并和权力对话的有效途径”*K.M.DeLuca & J.Peeples.“From Public Sphere to Public Screen:Democracy,Activism,and the ‘Violence’ of Seattle”,in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2002,19(2),p.144.,否则运动中的其他元素也会继续被边缘化。而在博伊考夫(Boykoff)看来,大众传媒既有新闻规范和新闻价值的约束,使得异见人士为博取关注而不得不使用更为偏激的策略和修辞。反公众极尽所能曝光议题的重要性在于,“只有通过它们在媒体上富有争议的呈现,这些话题才能到达更广大的公众并在‘公共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J.Boykoff.“Framing Dissent:Mass-Media Coverage of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in New Political Science,2006,28(2),pp.201~228.。除了把边缘的议题引入主流媒体,反公众还“创造另一个媒体系统,并通过水平的通讯网络传达给人们,摆脱公司媒体的控制”*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虽然对网络的态度略显保守,但唐尼和芬顿承认在新媒体的语境下,另类媒体的研究更值得认真对待。正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关于互联网传播与政治抗议关系的著述正越来越多。卡斯特描述了1994年萨帕塔主义者们的“信息化游击运动”,这是从属人群利用互联网绕开官方媒体封锁、成功对抗权威最富标志意义的案例。他们通过互联网传递自身要求和讯息,“发动一场国际公共舆论运动,从而从舆论上防止墨西哥政府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86~87页。,获得谈判筹码。萨帕塔主义者的反公共性不仅影响了墨西哥国内的公共领域,还影响了跨国界的公共领域,其“线下抗议+线上‘反公共性’”的策略为世界各地行动者们提供了学习的范本*J.Downey & N.Fenton.“New media,Counter Public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p.196.。
米利欧尼(Milioni)考察了反全球化运动中独立媒体(Indymedia)所构建的线上反公众及其反公共性,发现有别于主流新闻模式,独立媒体使用了更多的草根信息源,以便更直接地再现生活世界,重设那些被主流公共领域忽视的议程;独立媒体也未完全与主流媒体隔绝,相反它们常常引用主流报道,并附上自己的补充资料和解读,重设理解事件和议题的框架*D.L.Milioni.“Probing the Online Counterpublic Sphere:The Case of Indymedia Athens”,in Media,Culture & Society,2009,31(3),pp.409~431.。
德鲁卡等人对比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传统媒体系统和社交媒体系统对事件的不同呈现。在美国的各大权威报刊上,占领华尔街运动先是被沉默,再是被奚落。相对的,在美国的社交网站上,对于占领华尔街的讨论多元而热烈,“推特、Facebook和YouTube为行动主义提供了旧媒体中所没有的新语境”*K.DeLuca,S.Lawson & Y.Sun.“Occupy Wall Street on the Public Screens of Social Media:The Many Framings of the Birth of a Protest Movement”,in 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2012,5(4),pp.483~509.,集体行动和参与的土壤得以转型和增殖。他们认为,或毁或誉,占领华尔街首先需要的是存在于被媒介所形塑的社会现实中。
而在互联网原生性的集体行动方面,豪顿(Houghton)把黑客行动主义视为一种线上反公共性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探索。她将黑客行动主义分类为政治编码(political coding)、表演性黑客行动(performativehacktivism)、政治骇客(political cracking)并辅以三个对应的案例,展示它们如何作为反公众运作,激起公众对政治偏好的反思,动摇支配者的话语霸权*T.J.Houghton.“Hacktivism and Habermas:Online Protest as Neo-Habermasian Counterpublicity”,in (Doctoral Dissertation),2010,Retrieved from UC Research Repository,http://hdl.handle.net/10092/5377.。例如hacktivismo利用软件帮助部分地区的网民突破当局网络审查和封锁,扩大异见人士的话语范围;创作自由基金会(Creative Freedom Foundation)发起的互联网黑屏抗议活动中,参与者将自己的社交网络头像换成黑色方块,并放置导向活动主页的链接,主页上解释了黑屏抗议的目的——反对新西兰著作权法的某条修正案,这种病毒营销式的反公共性成功冲击了推动该修正案的精英话语;而著名黑客组织“匿名者”则是直接用DDoS攻击或网站涂鸦的方式,破坏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他们连自己的网站都控制不了,遑论网络审查过滤器。
四、 结语及讨论
哈贝马斯布尔乔亚式理念下的公共领域是单一全面、无所不包的。然而新派学者拒绝这种大一统视野,而是从社会复杂性和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出发,寻求公共领域更为多元化的模式。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新版序言中,哈贝马斯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自己对多元公众的误读以及其他学者予以批判反思的努力。从弗雷泽到沃纳再到阿森等学者,以对原理论的批判为基石,提出反公众和反公开性的概念,并将其不断延伸、发展。它们延续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对公民社会、民主政治的关怀,同时更注重差异和排他性的解读。反公众之反,乃是对自身被排除地位的确认,由此构筑边缘认同的堡垒,在内部形成自身的成熟话语,然后向外挑战主流话语霸权。反公共性代表了反公众的言说方式,是与主流话语积极竞争的传播行动。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交织建构社会现实的背景下,行动者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把原本边缘化的议题带到更大范围公众的视野里,另一方面要巧妙地组织自身的框架和话语以获得理解和支持。互联网无疑丰富了集体行动中话语、符号竞争的形式和可能性。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引入中国后,与本土情境结合,亦催生了大量学术论著。针对公共领域这一理论框架是否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基于哈贝马斯提出该理论的西方历史语境及其对公域和私域、国家和社会的严格划分,认为中国不具备产生公共领域的文化和社会条件;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对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商会、学社和报刊的研究,挖掘和分析了中国构建公共领域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土壤,指出在中国构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两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分别是曹卫东和许纪霖。另参见传媒领域中部分代表性论述,如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邵春霞、彭勃:《谁的“公共领域”?——概念运用的困惑与修正》,载《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孙藜:《从媒介与“私人性”的关系看公共领域之可能——当代中国语境下对哈贝马斯历史分析的再认识》,载《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特别是网络的兴起,激发了不少传媒研究者探讨网络公共领域的特征、运行机制、作用和前景等问题,甚至开始勾画依托新媒体如博客等来“收复公共失地”的美好愿景*参见部分相关论述,如许英:《论信息时代与公共领域的重构》,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李蕉:《博客:收复公共失地——兼论公共领域的实现》,载《学术界》2007年第3期;宋石男:《互联网与公共领域构建——以Web2.0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为例》,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尹连根:《结构·再现·互动:微博的公共领域表征》,载《新闻大学》2013年第2期。。然而,无论哪种观点,其讨论多是建立在原理论的理想模型之上,少有引入或吸收新派公共领域学说的概念和思想来反思和解析当下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引入在承认社会复杂性和社会结构多样性基础上提出的反公众和反公共性的概念,对中国本土的相关研究具有反思意义。
首先,从中国的现实状况而引发的学理解析需要来看,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全面转型的阶段,社会结构经历着一个震荡、变化甚至变革的过程,加之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化进程,各种社会文化和思潮涌动,利益主体和社会认同也日趋多元化。从原本大一统的公共领域视角出发,恐难有效理解当下中国参差多态的话语生态。以这样一种大一统的视角来看待传媒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时,在涉及公共领域关键要素的具体分析中或多或少体现出几种倾向:一是将公共议题先验性地预设为某类或某些既定议题,强调政治性,忽略文化性,并且忽略了私人议题经由公众讨论而成为公共议题的动态可能性;二是在认识到我国媒体在建构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局限的同时,时常透露出传媒中心倾向和精英特征,尤其重在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对公共领域的建构作用,对非主流媒体和/或另类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空间在此方面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还疏于探讨;三是在探讨新媒体构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问题上,大多基于创建交往空间的介质(比如互联网)的技术特征来论述,相反,公共话语实体或公众的复杂性和主体性却并未得到应有的等量重视。对此,将公共领域概念模式引向多样性方向发展的新派理论视角或许可以给研究者带来更多的启示。
其次,从新派理论概念的现实应用来讲,反公众能够揭示中国公共话语空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少处于从属地位的边缘话语实体,比如中国本土也存在着劳工、女权、LGBT等与欧美社会类似的反公众。已有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主流公共领域的排他性和边缘话语挑战排他性的努力。例如,有学者通过案例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和自有知识分子促成了一个亲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党媒在劳资冲突的个案处理上也往往显得乏力,而工人们用自发的传播实践所构建的反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则“运转在中国政治、经济、知识及媒体精英组成的合法化机构的惯常标准之外”*G.Xing.“Online Activism and Counter-Public Sphere:A Case Study of Migrant Labour Resistance”,in Javnost-The Public,2012,19(2),p.79.;也有学人通过对我国传统媒体的文本分析,阐述了女权主义在主流媒体上被误读、被污名化的过程*杨雨柯:《激进的女权标签——女权主义如何在媒介平台被污名化》,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S1期,第94~109页。;还有学者考察“同志”群体创办杂志,建构另类公共领域,构建“同志”群体的媒体再现,通过媒体为“同志”群体赋权*章玉萍:《另类媒体的双重角色:以中国大陆“拉拉”杂志〈les+〉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S1期,第138~152页。。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着其他更为本土特色的边缘话语,如由中国特殊的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下岗工人群体(见红歌会网),如由年轻一辈挑战家长专制和传统孝道带来的代际冲突(见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这些反公众是如何被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条件所形塑的?其内部如何构建自身话语和认同?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话题。
另外,反公共性强调了主流公共领域的动态性,有助于揭示国内舆论场多元话语竞争的状态。近年来,新媒体崛起,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层出不穷,国内媒介生态系统正经历大变革。微博、知乎、微信等公共平台降低了普通人参与表达的门槛,传统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被打破,原有的媒介层级变得更扁平。在网络平台上,再边缘、小众的话语都可以找到回声,也更容易拓展话语的流通边界。反公众以反公共性来争取达到更为主流的公众,例如家庭暴力一开始只被视为夫妻纠纷的家务事,近年来在微博上得到不停地推动和讨论,渐渐成为公众议题,并影响了司法和立法*范红霞:《女性问题、大众媒介与公共议程的互动——以家庭暴力立法为例》,载《现代传播》2012年第5期,第145~147页。。前述的反公众与主流公众的话语竞争经历着怎样的动态过程?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独特的传播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从反公众和反公共性出发,从强调共识迈入关注竞争,以一个多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为主流媒体所忽视的话语问题。
总之,对哈贝马斯框架的理论反思将我们对公共领域的认识扩展,超越理性主义者对认知和体制的关注,而转向其他社会性维度,比如情感、文化和道德等。从另一种视角对公共领域进行重新思考,不但能使我们认识到经典公共领域的排他性和阶级统治性,以及它与次属公众的对抗关系,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想象反布尔乔亚公共领域的潜能。
●作者地址:周翔,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juliewuhan@163.com。
程晓璇,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涂文迁
◆
What’s “Counter” in “Counterpublic”: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from a Pluralistic Perspective
ZhouXiangChengXiaoxua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Counterpublic” and “counterpublicity” proposed by neo-Harbermasian theorists criticize the exclusion in a hegemonic Habermasian public sphere and reveal the power relation in public discourse from a perspective of pluralism.The “counter” in “counterpublic” needs to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1) the oppositionality,which means the awareness of an excluded status on which marginalized identities are built and autonomous discourses are framed; 2) the binary functions of withdrawing from and reentering into the communication flow of mainstream public sphere; 3) reaching out to a wider publicity.“Counterpublicity” reveals how the “counterpublic” speaks out,and represents communication acts to challenge mainstream discourses.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lications of “counterpublic” and “counterpublicity” for the China-based research exist in their helping to reveal the current state of discourse 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and thus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mariginalized discourse entities in the Chinese public discourse space ignored by mainstream media from a pluralistic perspective.
counterpublic; counterpublicity; public sphere; public discourse
10.14086/j.cnki.wujhs.2016.05.00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86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