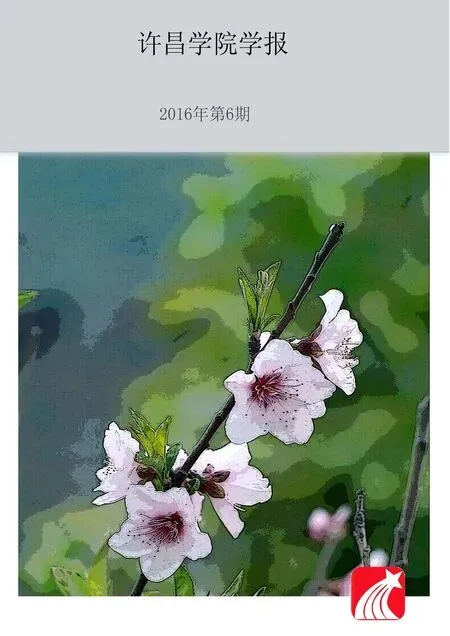论孟浩然之背疽及其死亡
卫 佳,杨和为
(六盘水师范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贵州 六盘水 553001)
论孟浩然之背疽及其死亡
卫 佳,杨和为
(六盘水师范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系,贵州 六盘水 553001)
孟浩然晚年身患背疽,卧于襄阳,因为诗友王昌龄的造访背疽发作而死,这一事件虽在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中有所记载,但较为简略,而且疑点较多。结合中医情志学及中医病理学相关知识,梳理孟浩然晚年诗作及其与张九龄、王昌龄诸人交游可知,孟浩然之所以身患背疽,乃是因为在张九龄幕中七情内伤而又膏粱厚味,从而火毒内蕴而致郁结。其后他辞归襄阳,经过一年多的静心调养,背疽有所好转。但因对自己病情误判,王昌龄遇赦北还时,孟浩然与之浪情欢谑,最终引起背疽发作而死。
孟浩然;火毒内蕴;王昌龄来访;食鲜疾动;背疽而卒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孟浩然(689—740)虽生逢开元盛世,却始终未能为世所用,是当时少有的以布衣终老的诗人。近年来学界对于孟浩然的家世交游、生平行事、思想活动、心理性格及诗歌艺术研究较多,但孟浩然的身体健康与情志疾病,尤其是他晚年患疽病并最终导致其死亡这方面,似乎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比如,晚年孟浩然何以身患背疽之病?他患病期间行事如何?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悟?当王昌龄造访之际,他竟然不顾背疽之疾尚未痊愈而犯忌食鲜,个中心理又是怎样?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本文拟从中医情志学及中医病理学角度对此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从背疽的发病原理看孟浩然晚年患背疽的原因
刘文刚先生所作《孟浩然年谱》,除了对“孟浩然的家世、里居、交游、生平行事、思想活动、创作道路、诗文系年,以至子嗣、坟墓等,作了细致的探索”[1]卞孝萱序3外,其对于孟浩然的身体状况及晚年所患疾病亦有较多的考证。从刘谱来看,孟浩然共生过四次较为严重的疾病,第一次是在开元八年(720)暮春,孟浩然卧疾襄阳,其时有诗赠好友张子容,刘文刚先生特下按语云:“浩然此次重病,当起于去年,至今年暮春,方见好转。浩然时值壮年(按,孟浩然时年32岁),便患此大病,说明身体颇不好。他颀长消瘦,本有些病态,加之不得志,故一生都为疾病缠绕。病也是浩然一生之大不幸!”[1]21第二次是开元十七年(729)寒食,孟浩然卧疾于洛阳李氏家中,有诗《李氏园卧疾》记之。[1]44-45第三次是开元二十年(732)初春,孟浩然卧疾于浙江乐城馆中,有诗《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作》记之。[1]59第四次是开元二十六年(738)夏,孟浩然因患背疽从张九龄幕中辞归,卧病襄阳。[1]94直到开元二十八年(740)春夏,因为诗友王昌龄的造访,背疽尚未痊愈的孟浩然与之浪情宴谑,最终引起背疽发作而死,结束了诗人落拓不遇的一生。
欲探究晚年孟浩然何以患背疽之病,首先需要我们搞清楚背疽的发病原理,然后结合孟浩然一生行事尤其是晚年情志及身体状况进行探究。所谓背疽,乃疽之发于背部者。何谓疽?其发病原理为何?按《灵枢经》卷十二《痈疽第八十一》曾专论痈疽之病,借黄帝与岐伯问对,对痈疽发病原理做了精到的分析:“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煎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藏,藏伤故死矣。”[2]198并区别痈疽云:“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于骨髓),骨髓不为燋枯,五藏不为伤,故命曰痈。……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骨肉,内连五藏,血气竭尽,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状)如牛领之皮。痈者,其皮上薄以泽。”[2]202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痈疽是发生于体表、四肢、内脏的急性化脓性疾患,是一种毒疮。痈与疽的区别在于:痈发于肌肉,红肿高大,多属于阳证;而疽发于骨上,平塌色暗,多属于阴证。而痈疽之生于脊背部位者,统称“发背”,属督脉及足太阳膀胱经,系火毒内蕴所致。痈疽分阴证和阳证两类,阳证又叫“发背痈”或叫“背痈”,阴证又叫“发背疽”。《新唐书·文艺传》说孟浩然“开元末,病疽背卒”[3] 卷二百三,5779,其中的“病疽背”,正是王士源在《孟浩然诗集序》中所说的“发背”[4]558。按“发背”之名,始见于《刘涓子鬼遗方》*《刘涓子鬼遗方》,晋末刘涓子撰,因托名“黄父鬼”所遗而得名,为古代汉医经典之一,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只存五卷。原书又称《痈疽方》,对痈疽的辨证论治阐释得尤其详尽,可称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该书卷第四有云:“凡发背,外皮薄为痈,皮坚为疽,如此者,多现先兆,宜急治之。皮坚甚大,多致祸矣。”[5]28隋太医博士巢元方所撰《诸病源候论》*《诸病源候论》,又称《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古代中医学名著,共五十卷,隋代巢元方等撰于隋大业六年(610),是中国最早论述以内科为主的各科病病因和证候的专著。卷三十三说:“疽发背者,多发于诸脏俞(按:指脏腑俞穴,皆在背脊部)也。五脏不调则发疽,五脏俞皆在背,其血气经络于身。……疽重于痈,发者多死。”[6]328由于脏腑俞穴皆在背脊部,发背者多因脏腑气血不调,或火毒内攻,或阴虚火盛凝滞,使气血蕴滞于背而发。依其所发部位之不同,而有上发背、中发背、下发背之分;或以上搭手、中搭手、下搭手而命名;或以其形态之不同,而有莲子发、蜂窝发等分别。由此看来,孟浩然晚年所患,正是因火毒内蕴而发于背部的疽病,较之痈更为严重。
如我们所知,孟浩然晚年曾在张九龄荆州幕中待过一年左右(737年夏至738年春夏):“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旧唐书·文苑传》)本来孟浩然可以在张九龄幕中一直做下去的,但他没有。学界推断,孟浩然之所以入幕一年便辞归襄阳,当是生病的缘故。如芳村弘道在《唐代的诗人研究》一书中,就曾如是推断:“在完成了这一唱和之诗(按,指《和张丞相春朝对雪》一诗)后不久,孟浩然便辞去了张九龄从事一职,返回了襄阳。此次归乡似乎是源于疾患缠身。”[7]36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前言》也说孟浩然“大约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又从(张)九龄幕府辞归,回襄阳养疾”[8]前言7。而刘文刚先生所作年谱,则明言孟浩然开元二十六年(738)夏乃因患背疽而卧于襄阳,并作按语云:“浩然患背疽时间,书均不载。考本年(按,即开元二十六年)春浩然尚在张九龄幕中,尔后活动突然中断,而从浩然诗和行动看,他并无马上离开荆州之意。其离开显然系因为背疽发作。”[1]94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可以推知孟浩然在张九龄幕中这一年左右时间,其健康状况应每况愈下,直至“疾患缠身”,才不得不辞归襄阳。孟浩然入幕后的诗作为我们略窥其健康状况及情志心理提供了最可信赖的材料。
张九龄开元二十四年(736)冬被李林甫排挤罢相,次年(737)夏四月被贬为荆州长史。到荆州任后,便将孟浩然“辟置于府”(《新唐书·文艺传》),“署为从事,与之唱和”(《旧唐书·文苑传》)。这一时期,他随张九龄外出行县、祠祭、游猎,时相唱和,几乎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从唱和诗来看,孟浩然在入幕之初,对于张九龄还是心存感激的,甚至于感到欢欣鼓舞:“觏止欣眉睫,沉沦拔草莱。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荆门上张丞相》)[4]183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骨子里那种放性不拘的性格使他越来越不满于这种“羞逐府寮趋”(《和宋大使北楼新亭》)[4]194的幕僚生活。《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迥(迪)张参军》一诗业已流露出诗人对幕僚生活的厌倦:“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岁暮登城望,偏令乡思悬。……世禄金张贵,官曹幕府连。顺时行杀气,飞刃争割鲜。……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4]79-80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冬,写他随张九龄巡行途中在纪南城打猎的情况。首四句说自己不喜好田猎,只登城遥望而触动了乡思之情。后六句写官员们飞骑联翩追随张九龄田猎的情景。最末两句“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用楚狂接舆之典,意即像我这样一个纵情狂歌之士,不承想居然也在张九龄田猎的队伍之中,做一些自己所不愿的“顺时行杀气,飞刃争割鲜”之类的事情。虽是戏赠之辞,但透露出孟浩然对于幕府生活的不满,而对张九龄亦不无微词,足见其性格中的狷傲。不仅如此,我们从这首诗中还可体味到他跟幕府生活的格格不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格格不入的不适感,他的身心情况才越来越糟糕。最要命的是,他还不能在张九龄面前发作,而只能勉强隐忍。有论者认为,孟浩然在一代贤相张九龄面前其实是“窘迫拘谨”的,而“这种拘谨是由于张九龄的高位和名望”[9]109,因此,孟浩然对于幕府生活的诸多不满,就只能通过戏赠他人的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纾解。孟浩然对于张九龄本人,还时常在诗中表达知己之感:“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愁。”[《陪张丞相登嵩(当)阳楼》][4]443亦多称颂其燮理之才:“迎气当春至,承恩喜雪来。……不睹丰年瑞,焉知燮理才。”(《和张丞相春朝对雪》,作于738年立春)[4]197-198而当张九龄流露出归隐之念时,孟浩然亦衷心希望他能效仿东晋的谢安拯救天下黎民:“谢公还欲卧,谁与济苍生。”[《陪张丞相祠紫盖山述(途)经玉泉寺》,作于738年2月][4]85尽管如此,孟浩然对于幕僚生活的不满与厌倦却与日俱增,这在《和宋大使北楼新亭》(约作于737年岁末或738年初)诗中表露无遗:“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谁谓山林近,半(坐)为符竹拘。……愿为江燕贺,羞逐府寮趋。欲识狂歌客,丘园一竖儒。”[4]194孟浩然在诗中明言“返耕意未遂”,此即情志不遂之征。从诗句来看,孟浩然或曾向张九龄委婉提出过辞归之意而未被允许,直到738年春夏身患疾病才被允辞归。联系前后几年孟浩然的身体状况及心理,我们似可做这样的推测:开元二十二年(734)再入长安求仕失败归来,孟浩然即已决绝仕进之念,故爽约韩朝宗,叱骂提醒者。但当张九龄被贬荆州而相邀入幕,他却又动心了。孟浩然求隐而有仕进之念,求仕而有慕隐之心,正是因为孟浩然对自己有诸多的误读,结果命运亦似乎总是开他的玩笑:欲求仕而不果,欲求隐而不得,结果摇摆不定,“仕隐两失”[10]111。既已身在幕中,却因为本性散淡纵情,加之不能忍受嵇康所谓“七不堪”*“七不堪”意即七种不堪忍受之事。《文选》卷四三载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论之甚详。孟浩然有诗《京还赠张淮》(约作于734年秋离开长安之前)曾提及“七不堪”之典,诗云:“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见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之类吏事俗务,以及自诩颇高,羞与府僚俗吏为伍,遂与府僚俗吏格格不入。但碍于张九龄的高位和名望,他又不能发作,只好强行隐忍,如此情志不遂,遂致内伤成疾。因而可以说,孟浩然身患背疽之病而辞归襄阳,正是由于他在张九龄幕中七情内伤而又膏粱厚味,从而火毒内蕴而致郁结。
二、从孟浩然病中诗看诗人患背疽期间的调养及行事
年已五十的孟浩然在张九龄幕中因情志内伤,以致身患疽病,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春夏辞归襄阳,在涧南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两年左右的时光。背疽卧疾的这段日子里,孟浩然是怎样度过的呢?诗人作于这一时期的几首病中诗可以为我们大致勾勒出其中的线索。
孟浩然之死既跟王昌龄的造访有关,而且在孟浩然集中亦颇多赠王昌龄的诗篇,因此,孟浩然与王昌龄之间的交游便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作为盛唐名家之一,王昌龄(690?—756?)素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被誉为“七绝圣手”。开元十五年(727)春,年近不惑的王昌龄应进士举一举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其后心有不甘,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再应博学宏词科,又一举登第,但仅被授予汜水尉,属正九品下,其品秩不升反降。开元二十六年(738),王昌龄由于“得罪由己招,本性易然诺”(王昌龄《见谴之伊水》)而被远贬荒僻的岭南,次年(739)方有幸遇赦北还,并量移江宁丞。不幸的是几年之后,又因所谓“不矜小节,谤议腾沸”[11]90而再遭斥逐,贬为龙标尉。安史乱起,竟被亳州太守闾丘晓所杀。王昌龄一生虽科场得意,但仕途却颇为失意,屡遭贬谪,“垂历遐荒,使知音者叹息”(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而在他第一次贬谪岭南期间,曾两次途经襄阳,拜访了正患背疽之疾的孟浩然。孟浩然与王昌龄的结识,当在开元二十二年(734),那一年王昌龄再应博学宏词科及第,孟浩然亦再上长安求仕而未果。是年秋,孟浩然愤然返归襄阳,出潼关时,有赠王昌龄诗:“向夕槐烟起,葱茏池馆曛。客中无偶坐,关外惜离群。烛至萤光灭,荷枯雨滴闻。永怀蓬阁友,寂寞滞扬云。”(《初出关怀王大校书》)[4]399表达了两位诗人之间深厚的情谊。其后开元二十四年(736)冬,王昌龄归故里,途经襄阳,孟浩然陪游,并设宴款待,有诗记之:“归来卧青山,尝(常)魂在清都。漆园有傲吏,惠县在招呼。书幌神仙箓,画屏山海图。酌霞后对此,苑(宛)似入蓬壶。”(《与王昌龄宴王十一》)[4]453-454诗表现了孟浩然游长安回故乡后的隐居生活,“酌霞后对此,苑(宛)似入蓬壶”二句,表明此时的孟浩然身体还比较健康,故可饮酒。临别之际又作诗相赠:“导漾自嶓冢,东流为汉川。维桑君有意,解缆我开筵。云雨从兹别,林端意渺然。尺书能不吝,时望鲤鱼传。”(《送王大校书》)[4]505离别感伤之情溢于言表。至开元二十六年(738)秋,王昌龄被贬谪岭南*关于王昌龄贬谪岭南的时间,谭优学《王昌龄行年考》、胡问涛《王昌龄年谱系诗》及蒋长栋《王昌龄评传》等均认为发生在开元二十六年(738),一年后,即开元二十七年(739),王昌龄遇赦北返。(见毕士奎《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刘文刚《孟浩然年谱》及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亦持此说。〔见刘文刚《孟浩然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页笺注一。〕,途经襄阳,又拜访了孟浩然,孟浩然作诗相赠,表达了对王昌龄此去岭南的担忧:“洞庭去远近,枫叶早经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查头。已抱沉痼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间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送昌龄王君之岭南》)[4]357-358“沉痼疾”意即历时较久而顽固难治之病,说的正是孟浩然所患的背疽,对此孟浩然难过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还有一点悲观。须注意的是,诗中提到襄阳特产查头鳊。按查头鳊在孟浩然诗中出现频率颇高,是孟浩然引以为自豪的家乡美味。但随后转出“已抱沉痼疾,更贻魑魅忧”二句,除了表达孟浩然对于被贬岭南的友人的担忧之外,似乎还表明,孟浩然因背疽病重而不能像往常那样酣醉痛饮,说明此时的孟浩然在卧病调养的过程中还比较理性。
到了第二年也即开元二十七年(739)夏,孟浩然仍旧卧疾家中,毕曜还曾前来探视并有馈赠,孟浩然作诗《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耀)见寻》,表达了自己病中的感受和内心的感激:“伏枕旧游旷,笙簧劳梦思。平生重交结,迨此令人疑。冰室无暖气,炎云空赫曦。……壮图哀未立,班(斑)白恨吾衰。……顾予衡茅下,兼致禀物资。脱分趋庭礼,殷勤伐木诗。脱君车前鞅,设我园中葵。斗酒须寒兴,明朝难重持。”[4]290-291细揆诗意,我们不难体会孟浩然此时的心理。诗人长期卧病在家,平时少有人来探望,竟因此感叹“伏枕旧游旷”,认为“平生重交结,迨此令人疑”。“冰室无暖气”句表明诗人久病的艰难。“壮图哀未立,班(斑)白恨吾衰”二句,慨叹老年已至而壮图未成,紧扣题中“家园卧疾”四字,表现了诗人身心俱病的状态。诗人对于前来探望的毕太祝心存感激,留客共饮,理由是“斗酒须寒兴,明朝难重持”,担心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开怀畅饮了。由此二句,可看出诗人的背疽之疾似有好转,同时流露出诗人及时行乐的潜意识。当年华老去,死期将临,诗人不想再克制自己,这就为第二年(740)因王昌龄的到访而浪情欢谑埋下了伏笔。
可能是心情欢欣的缘故,其后孟浩然病情稍有好转,还曾外出拜访家园附近龙泉精舍的友人,《疾愈过龙泉精舍呈易业二公》一诗详细抒写了此次为期半天的出游经历:“停午闻山钟,起行送愁疾。寻林采芝去,谷转松翠密。傍见精舍开,长廊饭僧毕。石渠流雪水,金子曜霜橘。竹房思旧游,过憩终永日。入洞窥石髓,傍崖采蜂蜜。日暮辞远公,虎溪相送出。”[4]100按龙泉寺在襄阳北十五里,从诗中所写可知,孟浩然已能够走很远的路,并可“入洞窥石髓”和“傍崖采蜂蜜”,其调养功夫可见一斑。尤需注意的是,诗中提到采灵芝、窥石髓及采蜂蜜,此三者皆有却病延年之功效(其中,灵芝对调整身体机能的平衡有很大作用;石髓即钟乳石,传说古代求仙的人服食石髓可以长生;野蜂蜜对人亦有强身健体之功效,而且还是许多丹药的药基),似可表明孟浩然对于自己背疽之病的调养具有某种自觉的意识。
三、孟浩然患背疽而卒的原因分析
开元二十八年(740)春夏,王昌龄遇赦北还,经过襄阳,又拜访了孟浩然,而此时孟浩然的背疽尚未痊愈。不幸的是,孟浩然与王昌龄相得甚欢,浪情宴谑,最后竟因为“食鲜疾动”而终于南园,享年五十二岁。
关于孟浩然晚年患背疽而卒这一事件,《旧唐书·文苑传》只说其“不达而卒”[12]卷一百九十下,5050,对于患背疽一事根本不提。《新唐书·文艺传》虽提及患背疽之事,但也非常简略:“开元末,病疽背卒。”[3]卷二百三5779唯王士源所撰《孟浩然诗集序》记载稍详:“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发背,且愈,得相欢饮。浩然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南园,年五十(有二)。”[4]558这段话成为我们研究孟浩然患背疽而卒的重要参考材料,但其中尚有很多疑点,需要我们深入分析。
从王序来看,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前来拜访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的背疽其实尚未痊愈。我们知道,王士源是在孟浩然去世五年之后即天宝四载(745)“始知浩然物故”[4]558的,很显然,王序说“浩然疾发背,且愈”(尚未痊愈),乃是从孟浩然最终因“食鲜疾动”而死这一点出发推出来的结论。那么,我们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来访时,孟浩然自己知不知道他的背疽尚未痊愈呢?我们仔细分析他作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秋的《疾愈过龙泉精舍呈易业二公》一诗,当不难看出其中的端倪。在这首诗里,孟浩然所用的诗题是“疾愈”,很显然,早在去年秋他就认为自己的背疽已经痊愈了,所以才要外出访友,尽享山林游玩之乐。而在开元二十七年夏,孟浩然作《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耀)见寻》,说明那时候的孟浩然并不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但尽管如此,他还是留客对饮,“脱君车前鞅,设我园中葵。斗酒须寒兴,明朝难重持”,说明他的背疽确实有所好转,已可留客小酌。由此我们似可推断,孟浩然晚年患背疽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从张九龄幕中辞归之后,他静心调养了一年多的时间,背疽已经有所好转,不过尚未彻底痊愈,但孟浩然自己认为已经痊愈了。由于卧病静养的时间较长,孟浩然感到特别乏味无聊,所以他感叹“平生重交结,迨此令人疑”,表现出诗人对长期卧病而无人探视的悲哀,于是好不容易有人前来探望,他就会兴奋不已。与此同时,诗人背疽稍有好转(其实尚未痊愈),就耐不住寂寞,自己动身前往附近的龙泉精舍寻访友人,而且还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遇赦北还前来拜访的时候,孟浩然背疽其实尚未痊愈,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孟浩然自己以为已经彻底痊愈了,这是孟浩然对于自己病情的误判。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孟浩然乃是出于对自己病情的误判而与王昌龄浪情宴谑,才导致他“食鲜疾动”而死,那么王士源为什么不这样记录呢?从王士源的序来看,他所记载的孟浩然交游事迹主要有四件:其一,孟浩然在秘书省联句,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一联使得四座称赏,“不复为缀”;其二,张九龄、王维等名流显宦“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其三,爽约山南采访使太守韩朝宗;其四,开元二十八年与王昌龄浪情宴谑,背疽发作而卒。而对孟浩然赴京应进士举不第、转喉触讳、漫游吴越及入幕张九龄等事不置一词。我们认为,这其实是王士源有意为之的举动,是王士源作为一个隐士的选择性心理的外化形式。“王士源的序文,记录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孟浩然,他只是选择性地写了孟浩然的一面。”[13]13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受众)往往只选择那些能加强自己信念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东西。……在受众的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即选择性心理)非常重要”[14]267。按,王士源作为一个好游山泽,又咨术通玄丈人,问道隐者,习隐诀的隐士,其“对孟浩然的认同,主要是对孟浩然隐士身份的认同。他选择性地注意、理解并接受了孟浩然身上近于隐的一面,因为这一面最符合他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符合他自己的文化倾向”[13]13。此即《周易·乾》所谓“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15]5。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王士源何以在记载爽约韩朝宗事件之后,给了孟浩然一个“好乐忘名”的评价。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王士源之所以如此记载孟浩然患背疽而卒的事情,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当孟浩然知道自己的背疽尚未痊愈,却还要与遇赦北还的王昌龄浪情宴谑,才能表现出孟浩然“好乐忘名”与放性纵情的高士形象,而这也正是王士源作为一个隐士想要达到的传播效果。
[1] 刘文刚.孟浩然年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 灵枢经(校勘本)[M].刘衡如,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 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宋刻本)[M].宋白杨,刘宇,孙冬莉,点校.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6]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宋刊本)[M].刘宇,孙冬莉,点校.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7] 芳村弘道.唐代的诗人研究[M].秦岚,帅松生,田建国,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
[8] 徐鹏.孟浩然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9] 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0] 叶嘉莹.叶嘉莹说初盛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 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2]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 李园.孟浩然及其诗歌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14]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
[15] 王弼.周易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张怀宇
On Meng Haoran’s Back Carbuncle and His Death
WEI Jia, YANG He-wei
(Chinese Department,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panshui 553001, China)
Meng Haoran suffered from back carbuncle disease in his later years and had to lie in bed. His friend Wang Changling came to visit him which caused the disease to attack and Meng passed away. Although this case was recorded in the preface ofMengHaoran’sPoetrybyWang Shiyuan, it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questionable. The overall point of this paper is concluded by carding Meng’s later poems and analyzing his interaction with his friends, Zhang Jiuling, Wang Changling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knowledge of Chinese Emotion Medicine and pa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ng Haoran suffered from back carbuncle because his seven emotions were stimulated when he assisted Zhang Jiuling. At the same time, he ate lots of delicious food causingthe intrinsic stagnation of burned toxin. Meng then resigned to Xiangyang, and his back carbuncle has improved with self-meditation and nursing in more than one year. But because of their misjudgment of the disease,Meng and his good friend Wang Changling who passed by Xiangyang indulged in drinking and eating, which eventually caused the carbuncle attack and the death.
Meng Haoran;the intrinsic stagnation of burned toxin;Wang Changling’s visit; eatingdelicious food and causing disease attack; death from back carbuncle attack
2016-05-21
六盘水师范学院校级课题“疾病体验下的孟浩然及其文学创作研究”(LPSSY201508)。
卫佳(1985—),女,安徽泾县人,文学硕士,六盘水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红楼梦》、古代文论; 杨和为(1973—),男,贵州江口人,六盘水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汉语、古代文学批评、修辞学。
I206.2
A
1671-9824(2016)06-00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