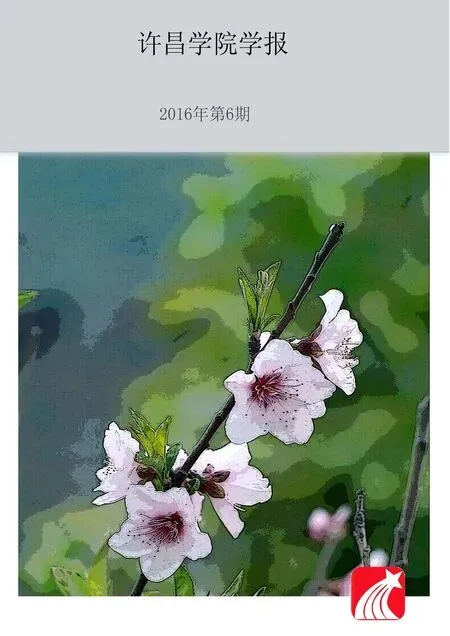赵树理传播接受中的误读与期许
张 舟 子
(商丘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赵树理传播接受中的误读与期许
张 舟 子
(商丘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人们在评价赵树理时,往往存在刻意的误读,从而形成了对解放区作家和赵树理本人的一种期许。作为党员作家,赵树理对这种期许可谓亦步亦趋,但是,由于其自身文学构成中的启蒙因素和现实主义因素,他的努力很难达到时代的要求。今天看来,恰恰是这些在那一个时代成为杂质的因素,使赵树理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
赵树理;误读;期许;问题小说
对赵树理评价的风云变幻,形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从无人问津到好评如潮并被确定为“方向”,被确定为“方向”之后,又受到“中间人物论”的批评和种种责难,责难之声未落,突然又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然后再度跌落神坛,可谓跌宕起伏、聚讼纷纭。个中原因,学者们已经从政治、历史、文学角度做出了种种解读,但很少有人关注过赵树理评价史上那些有意无意的误读,以及赵树理对这些误读的迎合与抗绝,也许,只有通过对这些误读、迎合与疏离的梳理与分析,才能更为接近赵树理作品的实际情况,才能解释清楚对赵树理评价的翻云覆雨,从而对赵树理的作品,得出更为合乎实际的评价。
一、误读与期许:赵树理方向的提出
赵树理与现代文学邂逅,并迅速受到高度关注,得到高度评价,很大程度上缘于一场有意识的误读。1943年5月,赵树理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但是迟迟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同年9月,因为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题词,才得以出版发行。始料不及的是,小说的出版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欢迎,过去,新华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以印刷两千册为极限,这本书在当年连续印刷了两万册仍然供不应求,不得不在翌年三月,“决定重新排版、再版两万册”[1]176。正是由于读者的热烈欢迎,完成于同年9月的《李有才板话》才得以在1943年11月顺利出版。耐人寻味的是,《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虽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却并没有给赵树理带来相应的重视,文艺界对赵树理的态度仍然是冷漠的,小说出版后,“在太行山区,仍然有些知识分子对他摇头,冷嘲热讽,认为那只不过是‘低级的通俗故事’而已”[1]176。可以说,赵树理这颗解放区的文学新星,并没有随着《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两部代表性作品的出版而引起文艺界足够的重视。
赵树理受到高度关注缘于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1946年8月2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这篇著名的文章,此时,距离《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出版已经将近三年。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周扬高度评价了赵树理小说的成就,认为“‘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2]53。正是这一论断,将赵树理的创作提高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的高度,引起了郭沫若、茅盾等人的热烈响应,最后,陈荒煤等人又沿着这一思路,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就是“最朴素、最具体的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因此便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3]63由此,陈荒煤在其文章中提出了“赵树理方向”,并将这一方向的内容概括为三点,分别为:“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赵树理同志的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3]61-62对赵树理的评价,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仔细审视赵树理创作的过程,深入阅读赵树理的作品,不难发现,不论是在赵树理创作与“讲话”的关系之间,还是在对赵树理作品的理解上,都存在明显的,甚至是刻意的误读,厘清这种误读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对于我们认识赵树理作品的丰富内涵,理解赵树理在历史评价中的风云变幻,包括认识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复杂现象,无疑都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重误读是关于对赵树理早期创作和“讲话”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表面看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毛泽东分别于5月2日和23日在会上做了后来被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言,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则分别创作于1943年5月和9月,受到讲话的影响、启发,并进而用创作实践讲话的精神,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事实上,赵树理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是他自己长期艺术探索的一个成果,赵树理的艺术探索虽然与“讲话”的精神有某些契合之处,但并没有受到“讲话”的实际影响。熟悉赵树理的人都知道,赵树理早年就深感“五四”新文学作品不能真正为普通群众所接受,因而立志做一个“文摊”作家。事实上,赵树理不仅密切关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而且进行了积极的艺术实践。1981年,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发现其发表于1981年第5期《汾水》上的《盘龙峪》最初发表于1935年,据董大中考证,《盘龙峪》应创作于1934年前后,在其中,赵树理最为人称道的农民口语已经运用得熟练自如,有学者将《盘龙峪》视为赵树理风格成熟的标志,并指出:“在三十年代上海进行大众化问题论争而没有产生出真正大众化作品的时候,在僻远的太行山山沟里,却有人实践了革命的主张,并取得可喜的成绩。这个人就是赵树理。”[4]5由此不难看出,赵树理的创作和毛泽东的讲话,是对同一问题长期关注得到的比较相近的认识,赵树理对此的探索和实践甚至早于毛泽东,因此,将其视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果,无疑是有意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拔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虽然在1942年5月已经做出了这个讲话,但内容直到1943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身在偏僻的太行山区的赵树理,不可能在此之前了解讲话的精神。前文提到的在《小二黑结婚》发表后遭到冷嘲热讽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这一结论。作为华北局宣传部长的周扬不可能不了解这一情况,那么,他为什么要刻意将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创作看作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果呢?如果说周扬有可能是一时失误的话,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出版的两套大型文艺丛书中,对其进行特殊对待,不仅收进展示解放区文学实绩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也收进1942年前就已有作品问世的作家的《新文学选集》,确实“反映了将之‘经典化’的迫切”[5]99。可见,对赵树理与“讲话”关系的强调,以及迫不及待地把赵树理的创作树立为一种方向,是由于时代的需要而有意的误读。
如果说将赵树理和“讲话”精神的邂逅解读为赵树理有意对“讲话”精神的实践是一次刻意的误读的话,对于赵树理作品思想内容方面政治意义的强调,同样是一次有意识的误读。如我们上文所引,对于赵树理方向的界定,放在首位的,也最为重要的是其作品被认为政治性很强,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和斗争。对照赵树理的作品,恰恰在这一点上,作品本身与评论者的总结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赵树理作品中矛盾的表现形态最主要的是“老字辈”与“小字辈”的矛盾,其次是“小字辈”与“坏干部”之间的矛盾。仔细审视这些矛盾,其本质并不是什么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是新与旧、科学文明与封建愚昧的矛盾。在《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和小芹的对立面主要有二诸葛、三仙姑和金旺、兴旺。其中,小二黑、小芹和二诸葛、三仙姑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年轻人和利用封建迷信干涉儿女婚姻自由的传统家长之间的矛盾,小说通过这组矛盾,对封建迷信和封建伦理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小二黑、小芹和金旺、兴旺之间的矛盾,则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年轻人和企图利用封建迷信干涉年轻人的恋爱自由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坏干部之间的矛盾。其中,留给读者更为深刻的印象、在小说中居于主要矛盾地位的,无疑是两个年轻人与两个愚昧的家长之间的矛盾,完全不是什么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即使是小二黑、小芹与金旺、兴旺之间的矛盾,也主要是年轻人追求幸福生活时与品德败坏的干部的矛盾而非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即使是作品思想政治方面的内容,批判的也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坏干部,而不是对地主阶级的批判。赵树理晚年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认为《李有才板话》“阶级阵营尚分明,正面主角尚有。不过在描写中不像被主角所讽刺的那些反面人物具体”,《李家庄的变迁》“虽然也写到党的领导,但写得不够努力,原因是对党的领导工作不太熟悉”。[6]344结合赵树理作品当时的接受情况,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对赵树理作品政治性的强调,是一次有意的误读。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树理之所以被确定为解放区方向性的作家,主要是因为其大众化的探索成果被误读了。需要说明的是,赵树理方向的提出,无论是提出这一说法的文艺界领导还是赵树理本人都明白,赵树理方向有对赵树理本人创作成果的总结和肯定,但更是对赵树理及广大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一个期许,给大家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二、问题小说:力不从心的追赶步伐
正如上文所说,赵树理方向的提出,有对赵树理大众化风格的肯定,更有对赵树理及其他解放区作家的期许。事实上,赵树理方向提出的当时,赵树理本人就感到不合适。据陈荒煤回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写完后请赵树理看过,赵树理一再提出,“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但是,陈荒煤后来仍然认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个口号,对当时晋冀鲁豫的文艺创作的确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7]242-243。应该说,这个口号对赵树理本人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他亦步亦趋地走在追随“方向”的道路上,但是,由于自身思想和文学传统的复杂,他的追随脚步始终显得力不从心。
赵树理在“讲话”发表之前在大众化方面所做的探索,和“讲话”中的许多论断高度接近,因此,在看到讲话的时候,赵树理异常兴奋,觉得自己的探索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支持,兴奋之余,也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积极性。但是,他的创作实践和“讲话”精神的契合只限于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方面,对于讲话提出的政治要求,他的创作还远没有达到,作为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他的内心对于讲话的政治要求是理解的,也是拥护的,为了真正能够达到讲话的要求,赵树理开始自觉加强作品的政治性,方法就是自觉地将小说写成他所说的“问题小说”。谈到自己的创作,赵树理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还没有例外。”[8]124-125这样的写作方式,正是为了配合具体的工作。“文革”期间,赵树理检点自己的创作,甚至能够一一说明哪篇作品是为了配合当时的什么工作,对于作品政治性的追求,可谓如影随形。始料不及的是,赵树理努力实践“讲话”精神的结果,不但没有使自己的创作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反而凸显出自己创作实践和“讲话”要求的分歧,招致评论界反复的批评。
赵树理对政治性的理解与“讲话”的要求,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文革”期间,他回顾自己创作时谈到成名之后到入京以前这一段创作的缺点时说:“(1)对主席的讲话接受得有片面性,忽略了‘以歌颂光明为主’的最重要一面;(2)过分强调了针对一时一地的问题,忽略了塑造正面人物。”[6]345应该说,这个说法虽然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做出的,但仍然是诚挚的和中肯的。这两个“缺点”实际上都是从“问题小说”中派生出来的,既然是“问题小说”,要反映工作中的问题,自然在歌颂光明方面会有所欠缺,为了把问题写得透彻,自然离不了社会环境、思想环境的深入刻画,这既会影响“光明”的程度,也难免使正面人物的高大程度打折。同时,由于赵树理自身的文学传统的复杂性,这样的“缺点”在他的创作中事实上是无法克服的。
说到赵树理的文学传统,许多人立即会想到民间艺术传统。的确,赵树理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的特色,但是,赵树理的文学传统远不是简单的民间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对赵树理的影响至少同样深刻,如果不是更为深刻的话。稍微熟悉赵树理的人都知道赵树理关于“文坛”和“文摊”的说法。1925年,赵树理进入山西省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并萌发了要成为一个作家的念头。但是,暑假回家,当他把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新文学作品带回家并推荐给父亲看时,父亲竟然对此不屑一顾,赵树理由此认识到,新文学和普通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赵树理确立了“文摊”作家的理想,努力学习民间文艺传统,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众化风格。但是,在强调民间文艺传统的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五四”新文学对赵树理的影响。其实,相比于民间文艺的影响,“五四”文学的影响虽然是潜在的,但也许是更为深刻的,这种影响不但表现在赵树理小说始终若隐若现的启蒙主题上,更表现在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上。我们不妨通过赵树理作品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后,赵树理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登记》、《三里湾》延续了《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变迁》的传统,而对于现实政治工作的配合则更为自觉。这两部作品无疑是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作品。值得深思的是,这两部作品在被改编成不同艺术形式广为传播时,作品的名字分别被改为《罗汉钱》和《花好月圆》,其主题则被改编为对传统包办婚姻的批判和新时代青年新的婚姻恋爱生活的描写。《登记》本意在于宣传新的婚姻法,但是,当小说塑造出小飞娥这样的人物形象时,小说的主题就远非宣传婚姻法那么简单了。那么,这两部作品的主题,究竟是歌颂工农兵、歌颂新生活的工农兵文学,还是“五四”新文学启蒙主题发展的新阶段呢?显然,赵树理在创作工农兵文学时,潜意识里受到了启蒙文学的暗示和干扰。这一点,在《孟祥英翻身》前面的小序里体现得更为清楚。小序很短,摘录如下:
因为要写生产度荒英雄孟祥英,就得去找孟祥英的人。后来人也找到了,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度荒,而是孟祥英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我想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也是大家愿意知道的,因此,写这本小书,书名就叫《孟祥英翻身》。
至于她本人生产度荒的英雄事迹,报上登载得很多,我就不详谈了。
在这个小序里,赵树理透露出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小说是和最初的构思存在差异的。很显然,赵树理最初想要写的,是一篇塑造新人物、反映新生活的符合“讲话”精神的作品。但是,在接触到孟祥英以后,他被孟祥英身上的另外一种东西,即孟祥英精神成长的过程吸引住了,从而使他偏离了最初的构想,写出了《孟祥英翻身》这篇作品。仔细阅读这篇作品,可以说,小说描写的正是孟祥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奴役创伤”的治愈,这样,小说的主题就具有了双重性:一方面,当然是对民主政权的歌颂;另一方面,小说舍弃孟祥英生产度荒的英雄事迹,更关注的是孟祥英自身精神世界的成长,这显然是一个“五四”文学启蒙的主题。这篇小说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赵树理创作心理的一个隐喻,在理性层面,赵树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政治上起作用”,因而自觉按照时代的要求去写作,去从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但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他身上“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又会不知不觉地使他偏离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增添一些新的因素,从而模糊了既有的主题,而显得犹豫不决,缺乏时代所要求的政治的鲜明性和坚定性。另一个影响赵树理作品政治主题鲜明性的原因是现实主义。赵树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最为深刻,现实主义精神要求他如实刻画农村的生活场景,并从对生活的深入了解中反映生活。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系列作品中塑造了革命队伍中一系列的蛀虫形象,正是基于他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崭新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延续了对这一类型人物的关注。《“锻炼锻炼”》中的杨小四等人物,显然是这一人物系列的新的发展。董大中在《赵树理与鲁迅》一文中,在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认为:“赵树理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这种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9]356无独有偶,美国学者西里尔·贝契不仅从赵树理文字的省约和精练方面联想到鲁迅,而且敏锐地意识到“虽然赵树理的小说全部写于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但是他大量的素材取自旧时代。他永恒的主题是谴责旧时代”[10]473,所谓对新政权的歌颂,只是小说结尾的一个光明的尾巴。遗憾的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深刻的洞察,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受到的批评和非议,大都可以从他的这种创作心理中找到原因。
最近,有学者通过对赵树理作品的语言研究,发现了赵树理语言中的一个有趣现象,认为赵树理的大众化语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翻译”,“叙事者用读者听得懂的语言翻译那些方言”,“将文学语言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翻译,对赵树理来说,是以一贯之的”。[11]实际上,赵树理作品本身也是一种翻译,将他内心有意义的文本“翻译”成一种符合时代需求、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可以发挥作用的文本。可惜,他内心的文学世界,仍有不符合时代规范的启蒙的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杂质,因此,无论他多么努力,也无法追随当时文学规范的步伐,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和指责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
三、 余论:刻板印象与重读赵树理
“刻板印象”是从社会心理学借用过来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对某个事物形成的一种固定、僵化的看法,反过来,接受这个事物的人,又按照这个已经固定、僵化的看法来认识这个事物,导致无法对该事物做出正确的认知。
事实上,在赵树理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个刻板印象。从赵树理进入人们的视野起,赵树理的作品就被看作是自觉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结果,是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思想内容方面强烈的政治性和表现形式方面的大众化是其鲜明的特点。不可否认,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在赵树理登上文坛之初,对于其作品的迅速传播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赵树理能够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与这个刻板印象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个刻板印象的形成,是赵树理传播过程中长期以来误读与期许,以及赵树理对这些期许自觉迎合的结果。问题是,刻板印象在便于事物迅速传播的同时,又往往会遮蔽事物本身的丰富性,妨碍人们对事物的个性有更为深刻的体认。我们在上文分析了赵树理作品与“讲话”的符合与差异,以及赵树理作品中的启蒙因素及现实主义传统,可以看出,赵树理作品实际上是有其丰富的个性的。遗憾的是,这些因素大都在赵树理作品的传播过程中被遮蔽了。这个刻板印象的直接后果,导致了赵树理作品被看作另一个时代的产品而难以进入今天的阐释语境。重新走近这位杰出的作家,充分认识其作品的丰富性,必须挖掘其作品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因素,尤其是其作品中的启蒙因素和现实主义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赵树理对于今天的意义和价值,才能释放其作品被刻板印象禁锢了的魅力。
[1] 戴光中.赵树理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2]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M]//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3]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M]//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4] 李国涛.赵树理艺术成熟的标志——读《盘龙峪》(第一章)札记[J].汾水,1981(11):61-66.
[5]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 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M]//赵树理文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陈荒煤.《赵树理小说人物论》序[M]//回忆赵树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8] 赵树理.也算经验[M]//赵树理文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董大中.赵树理与鲁迅[M]//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0] 西里尔·贝契.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M]//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 李松睿.地方色彩与解放区文学[J].文学评论,2016(1):52-53.
责任编辑:郑国瑞
2016-05-05
张舟子(1969—),男,河南灵宝人,博士,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6
A
1671-9824(2016)06-0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