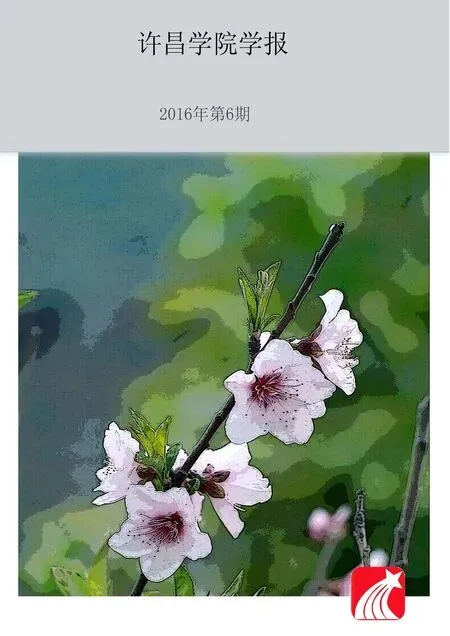论荷马史诗中英雄主角的终极追求
侯 朝 阳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论荷马史诗中英雄主角的终极追求
侯 朝 阳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在荷马史诗中,英雄们的人生抉择、生死体验及其应对各种关系时表现出来的生命智慧,都是其终极意识与终极追求的体现。对于这些英雄主角来说,战争承载着生命的终极价值。他们在战争中意识到个体生命的渺小与卑微,切身体验和感悟到生命的局限、死亡的必然和命运的神秘。无论是面对神灵还是面对自然世界,抑或是面对他者和自我,他们都能始终遵循适度原则。从英雄们的终极意识与终极追求中可以管窥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所能达到的高度。
荷马史诗;英雄;死亡;终极追求
对生命本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等终极问题的思考、追问和探求,历来为众多文学经典所关注,并因此构成了蔚为壮观的人类文化与精神之巅。荷马史诗便是其中很有分量的巨著。鉴于荷马史诗的主角是英雄,故而本文主要通过考察英雄们的人生抉择、对生死的感悟及其在应对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生命智慧,归结出其精神诉求中所蕴含的终极意义,并对之做出相应的分析与评价。
一、英雄们的人生抉择——为人之尊严而战
众所周知,根据《伊利亚特》的描述,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苦战。在血雨腥风、朝生夕死的险恶环境中,诸多无可回避的问题摆在了每一位英雄面前:参与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战争与个我有何关涉?这场战争能否承载自我有限生命之意义?……简言之,“我”为何要参加这场充满凶险的战争?就某种意义而言,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自我作答构成了英雄们在战争中所有行为的内在依据,也是其终极意识与终极追求显现的一个维度。因此,让我们撇开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既定成见,单单通过对文本中英雄们的行动或话语的考察来分析他们做出这一生死抉择的动因。
对于《伊利亚特》中的诸位英雄来说,特洛伊之战或多或少地承载着以下几种意义:
其一,超越平庸生活并赢取不朽声名。他们远离故土和亲人千里迢迢来参与这场战争,无非是不甘平凡,渴望建功立业而垂名青史。最典型的是阿基琉斯。战前,他早已从母亲口中预知了自己的命运:或是参加战斗,获取永垂不朽的名声,但必然早死;或是一直居于故邦安然生活,寿终正寝却一生平庸。在战场上,克珊托斯和赫克托尔又先后两次预言了他的死亡,但阿基琉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一种命运并坚持战斗到底。再如欧赫诺尔,他的父亲是预言者,曾告诫他:“将来或是患染重病殁于家中,或是去特洛亚死在阿开奥斯人的船边。”*参见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以下相关引文均出自该译本,仅在文中标明书名和页码。但他并未听从父亲的劝告,而是像阿基琉斯那样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此生湮没无闻。可以说,极强的荣誉观念已成为英雄们“特殊人格的决定因素”,他们“就是为这种特殊人格的无瑕的光辉、高贵和光荣而斗争”[1]239。
其二,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在大多将士看来,战场是最能衡量一个人有无胆识的场所:是否敢于参战、在战场上的表现是否英勇、战绩是否突出是其能否领受别人尊重的试金石。只有经历了战火考验的真英雄才配得上各种荣誉,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因此,他们才选择奔赴战场,挥洒一腔热血,并有不同凡响的战绩。如墨涅拉奥斯,作为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号召进行特洛伊之战主要是为了报夺妻之恨,洗雪加于己身的耻辱。从他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来看,他确实维护了个人的声誉,为自己挽回了尊严。而萨尔佩冬则用尊贵的身份来激励战友:“格劳科斯啊,为什么吕底亚人那样用荣誉席位、头等肉肴和满斟的美酒敬重我们?为什么人们视我们如神明?……我们现在理应站在吕底亚人的最前列,坚定地投身于激烈的战斗毫不畏惧,好让披甲的吕底亚人这样评论我们……”(《伊利亚特》,第278页)由此可见,获取他人的尊重是许多英雄英勇参战的一个重要缘由。
其三,可以将家世的荣耀发扬光大。荷马史诗产生于“英雄时代”,而这一时代“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他的家族和他的种族中的一个成员。……每一个人决不推卸他的祖先的行为和命运,而是心甘情愿地把它们看成是自己行为和命运”[1]239。所以,史诗中这些英雄出身高贵、家世显赫。他们要么是神的后嗣,要么是名门权贵之后,并均以英勇善战而享誉四方;在他们看来,出战和战绩不只关乎自我,而且与能否光耀家世密切相关。如格劳克斯曾面向对手狄奥墨得斯这样述说自己家世出身的荣耀:“希波洛科斯生了我,我来自他的血统,是他把我送到特洛亚,再三告诫我要永远成为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不可辱没祖先的种族。”(《伊利亚特》,第138页)这在《伊利亚特》中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即在剑拔弩张之时,英雄们常拿自己煊赫的家世炫耀并以此激励自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英雄们的参战是自觉地维护家族整体荣誉的行为。
与此相应,对于特洛伊及其同盟军而言,战争的首要目的和意义在于保家卫国或救助盟友;而对盟友的忠诚和保家卫国,亦代表着个人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的巨大荣誉。因此,赫克托尔这样鼓励将士:“让我们一起去进攻船只,如果你们有人被击中遭到不幸,被死亡赶上,那就死吧,为国捐躯并非辱事,他的妻儿将得平安,他的房产将得保全……”(《伊利亚特》,第353页)显然,就这场战争的性质而言,生存还是毁灭对于特洛伊一方的将士来说是更为直接也更为严峻的命题,他们不得不参与战争来保全自己,否则只能拱手沦为奴隶,失去作为人的荣誉和尊严。
总之,战争对史诗中的所有英雄来说都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不仅关涉每个人的生存和存在方式,也“为每个人提供了机会”(《伊利亚特》,第277页)。为此,英雄们才在浓雾弥漫般的战火硝烟中披挂整齐,奋勇出击。那么,该如何评价这种为了荣誉的献身呢?从表面看,英雄们在战场上生命的维系仅在于荣誉,甚或可以说视荣誉重于生命,荣誉似乎是他们人生的最终追求和至高意义所在。但细究之,无论是为家族扬威,还是为了个人的荣耀,其实质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的愿望和理想,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只有这样理解诸位英雄不惜牺牲生命来追求荣誉的心理动因,才能真正把握其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核心及其精神追求的实质。
当然,《伊利亚特》不是一曲自始至终都充满着英雄主义气概的慷慨激昂的赞歌,其间也始终渗透着悲苦者的不满、叹息和哭泣,甚至在多处出现了对战争的哀怨与控诉的“杂音”。 譬如,奥德修斯在规劝阿尔戈斯人时曾说他们“像柔弱的幼儿或者寡妇,满怀怨怒地相对哭泣,一心想回家;这里的辛苦叫人难忍也想把家还”(《伊利亚特》,第36页)。再如,当赫克托尔提出由帕里斯和墨涅拉奥斯两人决斗分出双方胜负并由此结束战斗时,“阿开奥斯人和特洛亚人很是喜欢,希望结束这艰苦的战争”(《伊利亚特》,第63页),因为双方都已厌倦了这场长期未决并导致双方都损失惨重的战争。总而言之,“这真是一场悲天悯人的战争,双方都是心里明白的;战争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可无法归罪于哪一个人”[2]43。这些都说明,战争对所有英雄而言不单有夺取荣耀桂冠的喜悦,同时也是一场煎熬和深重的苦难;尤其是当英雄们被死亡的噩耗攫住灵魂的时候,他们坚强而又脆弱的心灵莫不感受到了战争的残忍和难挨。此时,哀号就成了发泄心中的绝望、痛苦和恐惧等复杂情绪的唯一方式。这些“杂音”尽管与讴歌战争和牺牲的主调不同,但恰恰证明了英雄们并不是嗜血成性的好战者,而是具有生命感受力和自我意识的有血有肉的生灵。他们对战争的反思恰恰说明人的理性和情感并未因战争而窒息,人的生命本体意识并未被死亡泯灭。
在另一部史诗《奥德赛》中,还乡归家成为主人公奥德修斯的另外一种生死抉择。在奥德修斯眼中,“家乡是最可爱的地方,父母是最贴心的亲人,即便浪子置身遥远的地界,丰肥的疆域,远离双亲,栖居异国他乡”*参见荷马:《奥德赛》,陈中梅译,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以下相关引文均出自该译本,仅在文中标明书名和页码。。为此,他面临着两个征服对象,需要进行两场战争:首先要与自然抗争,解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锁链;其次,在回家之后要打败所有以求婚为口实的财产掠夺者,夺回属于自己的财产,恢复个人荣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指出:“实际上《奥德赛》所写的还是一种战争,因为希腊将领们在经过十年离乡背井之后回家时,发现他们的家乡领土已变了样子,要重新征服。”[3]126可以说,这两场战争都充满了艰险和死亡的气息,生存本身成为奥德修斯返乡途中和返乡之后最具意义的事件。最终,奥德修斯靠着他的勇敢和智慧,既实现了生之梦想,又重新获得了原有的尊荣。
二、英雄们的生死感悟——向死而生
外在困境的逼迫、内在心灵世界的挣扎往往更能促发人的自我反省和对生命现象的思考。在荷马史诗中,超乎寻常的战争经历、严酷的生存环境、死亡的威胁逼迫这些英雄们在审视自己人生抉择的同时,也对生命本身和死亡产生了诸多感悟,这构成了他们的终极意识和终极追求的第二个维度。
英雄们在战争的旋涡中首先认识到了个体生命的渺小与卑微,因此他们把战争中的荣誉和尊严作为人生的追求以避免自我的生命在群体和历史中悄无声息地滑落。诚如格劳克斯所言:“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伊利亚特》,第136页)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英雄们看来,人生在世有盛有衰,很快凋零,因此每一个体必须建功立业,成就盛名;另一方面,英雄们面对惨绝人寰的战争和各种危险又意识到人世的更替、自我的前途和命运并不以自我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如沧海一粟。故而奥德修斯指出:“大地哺育的生灵中,所有呼喘和行走在地面的族类里,人是最羸弱的聚种。”(《奥德赛》,第338页)他以此来提醒人们不能对自身的命运盲目乐观。而许多英雄则站在保全个体生命和尊严的立场上对战争本身发出了斥责和诅咒,其实,这也是一个个自视渺小的灵魂对悲苦命运的深沉叹息。
其次,英雄们也切身地体验和感悟到了人的局限性。譬如,波吕达马斯指出,尽管赫克托尔作战英勇,但人的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做到事事躬亲”,因为“神明让这个人精于战事,让另一个人精于舞蹈,让第三个人谙于竖琴和唱歌……”(《伊利亚特》,第310-311页)奥德修斯也有相同的认识:“神祇不会把珍贵的礼物统赐凡人,无论是体型、智慧,还是口才。”(《奥德赛》,第136页)这些英雄明确地意识到人不可能像神明那样无所不能,人囿于各种局限而不能盲目行事。
再次,由于身处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之中,英雄们对于生命有限性亦即死亡有着至深的体验。譬如史诗多次写到阿基琉斯早就预知自己葬身沙场的命运,也写到赫克托尔清醒地意识到他本人连同整个城邦最终将被毁灭。由于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死亡这一最终归宿本身对所有存在者来说或者显示出生命的伟大,或者是生命意义的消解,所以史诗中所有人,特别是这些英雄的命运都多少带上了悲剧色彩。对此,尼采曾经指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其真正的悲痛在于和生命本身的过早分离:“‘对于他们,最坏是立即要死,其次坏是迟早要死’。这种悲叹一旦响起,它就针对着短命的阿喀琉斯,针对着人类世代树叶般的更替变化,针对着英雄时代的衰落,一再重新发出……荷马式人物感觉到自己和生存是如此难解难分,以致悲叹本身化作了生存颂歌。”[4]12的确,荷马史诗是把死亡当作英雄们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为悲凄的事件来描写的,他们追求终极理想的精神之光总是伴随着死亡的阴影。
可以说,处于“临界境遇”的英雄们极为敏感地意识到了人的生命的卑微、受限和必死的命运。这种境遇极易触发英雄们转而思考究竟该如何去承受生命的重担,该怎样去面对和克服生命的凄凉。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人在临界状态里,也就是在面临苦难、死亡、内心矛盾和真理及信仰问题时,就感到有超越。”[5]67荷马笔下的英雄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并没有自轻自贱,更没有陷入绝望或虚无,而是对生命更加留恋和热望,更为热切地追求个人理想和人生意义,以此来超越有限的自我。如阿基琉斯的亡魂曾经表示:“我宁愿做个帮仆,耕作在别人的农野,没有自己的份地,只有刚够糊口的收入,也不愿当一位王者,统管所有的死人。”(《奥德赛》,第211页)这段话充分流露出他对于生之强烈渴望。与此同时,英雄们追求建功立业,成就声名,知其必死而毫不畏之,亦显示出向死而生的勇气,让有限之生命焕发出更耀眼的亮光。这正如汉密尔顿所言:“荷马史诗中的主人公死去的时候呼唤着更多的光亮,哪怕只是为在更多的光亮中死去。”[6]24唯其如此,诸位英雄的形象才显得崇高伟岸,他们的生命也赖此超越了凡俗而达至不朽。
三、英雄们的生命智慧——遵循适度原则
纵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英雄们既不满足于庸常的生活和命运,积极地实现生命的神圣意义,又遵循一定的限度,试图在各种关系中保持合宜的位置。这种对适度原则的遵循,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智慧,也体现着英雄们实现其终极追求的特点和方式。
首先,从人神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英雄们尽量以不触犯神灵的意志为行事原则。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神比人更有威权、更为纯洁、更为强大,神的心智不为凡人所能揣测,神的意志也不因人的意志而轻易改变,更重要的是,神能对人施加种种力量和影响,会对“任何破毁礼规的行为”进行责罚。这样,神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于人,人与神之间有着一条不能随意跨过的鸿沟。
既然承认了人神之间的差异和距离,那么人就要“臣服神祇”,从而使人神关系处于一种有主有从的合宜位置。因之,英雄们在战争过程中总是主动回避与神灵对抗。比如狄奥墨得斯曾说:“我可不愿意同天神作战……我不愿同永生永乐的神明斗争。”(《伊利亚特》,第136页)而墨涅拉奥斯在准备与赫克托尔对战时曾误把对手当作神明而打算弃战,因其认为如果他违背神意同神明宠爱的人作战,那么就可能会立即遭受巨大的不幸。英雄们也认识到,如若凡人过于自傲,敢于在神灵面前夸口或者胆敢与神争竞,那么他就会受到报复。比如色雷斯人塔米里斯,他由于夸口说自己的歌声胜过文艺女神,结果在她们的愤怒中被弄瞎了双眼;奥纽斯国王因没有把葡萄园的初次收获奉献给阿尔特弥斯,所以遭受了外敌入侵的惩罚。总之,他们认为所有悖逆神和挑战神的权威的行动都会遭致恶果,只有遵循适度原则、顺应命运才能使人神关系得到调和,从而使高高在上的神成为可理解的、可相处的。
当然,英雄们也认为当触犯了神灵导致人神之间关系破裂时,可以通过献祭、祈求等方式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变神的意志。所以福尼克斯说:“天上的神明也会变温和,他们有的是更高的美德、荣誉和力量。人们用献祭、可喜的许愿、奠酒、牺牲的香气向他们诚恳祈求,使他们息怒,人犯规犯罪就这样做。”(《伊利亚特》,第206页)阿迦门农正是由于侮辱了阿波罗的祭司而遭到报复——阿波罗使军中发生瘟疫,使将士死亡。此后,希腊将士又通过献祭平息了阿波罗的愤怒。在此,由于阿迦门农的高傲破坏了人神之间的和谐关系,致使人神之间出现了裂痕,而献祭实则代表着认错、纠错,意味着人向合宜的位置回归。这样,人神之间的裂隙方可得以修复。
其次,就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由于自然对于人的双重作用,英雄们既反抗恶劣的自然环境,又顺应自然,遵从自然对人的限制,使得不可预测的自然力不再是单纯、可怕的力量而显现出了美丽的色彩。在史诗中,大自然固然有其凶险的一面,对英雄们尤其是奥德修斯显示出恐怖的、异己的、毁灭性的力量;但它同时也是人活动的舞台,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它要求人的顺服。所以它不止露出狰狞的面目,也常常绽开笑脸来满足能够遵循适度原则的英雄们的部分愿望。比如奥德修斯,他在十年漂泊途中经历了来自自然的重重磨难,但由于他在面对危险时或者勇敢地与之进行搏斗和抗争,或者诚心祈愿其他神灵的帮助,所以总能化险为夷。再如阿基琉斯,他因急于想点着帕特罗克洛斯火葬的柴堆,就祈愿西北二风的降临,结果是天遂人愿。可以说,在两部史诗中,“一切自然的现象,黑暗的夜,玫瑰色的晨,地球和太阳,风,河流和海,水面和死亡——这一切都经过一番制造,变成了神怪的和有意识的人形了,可以为祈祷者所求得,可以为预言家所逆断,并可以为激动及控制人类的相等的情感与欲望所了解”[7]5。再加上作者使用了浪漫式的笔法来描绘自然,如将黎明来临称为“有玫瑰色手指的美丽的曙光女神”的出现或“年轻的黎明,吹着玫瑰红的手指,重现天际”等,使得自然甚至有时显得妩媚动人。如此,谢林认为“在荷马的诗歌中,没有超自然的力量,因为希腊的神是自然的一部分”[8]17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英雄们也遵循着适度原则。比如,在《伊利亚特》第三、四卷中,本来交战双方已发出盟誓,以墨涅拉奥斯和帕里斯两人进行决斗的方式结束战争,这对早已厌战的双方士兵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和解方式。但特洛伊一方首先违背了神圣的誓言,破坏了握手言和与友谊的桥梁,最终落了个城毁人亡的悲惨下场。由之可见,英雄们要求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遵循一定的准则和伦理规范,把所有与之悖逆的行为都看作是不适度的。此外,英雄们也认为在人与人交往中,即便是上下级关系也要尊重他人,保持适当的礼节,否则就是不适度的行为。比如阿迦门农最初对于将士高傲无礼,但在阿基琉斯愤怒拒战引起希腊联军重大伤亡之后,他对将士非常尊重,在一次巡夜时还嘱告墨涅拉奥斯要尊重所有的将士,勿存傲岸之心。另外,这种适度原则也体现在不宜过分热情,不能让客人享受“虐待式的优待”上。譬如,墨涅拉奥斯在接待奥得修斯之子时说过:“我不赞成待客的主人过分盛情,也讨厌有人对客人恨之入骨,漠不关心。凡事以适度为宜。……妥当的做法应是欢待留居的客人,送走愿行的宾朋。”(《奥德赛》,第274页)
最后,史诗中的英雄在处理个体与自我的关系时,力图在自我的理智与情感、自由与自我约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践行的也是适度原则。一方面,作品并不排斥英雄们激烈情感和情绪的流露。如《伊利亚特》浓墨重彩地渲染了阿基琉斯对阿迦门农的愤怒和对帕特罗克洛斯之死的悲伤、哭泣;《奥德赛》中,涅斯托尔之子裴西斯特拉托斯曾如此直言:“我决不会抱怨哭嚎,对任何死去的凡人……此乃我等唯一的愉慰,可怜的凡人,割下我们的头发,听任泪水涌注,沿着面颊流淌。”(《奥德赛》,第60页)正由于荷马史诗对英雄们的正当情感的宣泄表示许可,后人对这一点给出了高度评价:“阿喀琉斯和普赖姆两大敌人痛哭过去彼此所做的惨事,以及战胜者允许他的高贵的敌人的尸体满载荣誉运回,这种结束场面之精美,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这最末两卷连同第23卷里赫克托尔与安德洛玛刻离别的一段在内,显然把《伊利亚特》提高到单纯的征服和胜利故事的水平之上,而居于崇高的希腊悲剧的地位,它超越战争的光荣,显示了更为深广的人情的真理。”[2]14
但另一方面,史诗又指出某种情感的宣泄不可毫无限制,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被认为是不合宜的举动并将招致批评。比如阿基琉斯就曾因其坚决拒绝和解而遭到埃阿斯等人的谴责。但后来,又是阿基琉斯本人意识到情感需要理性樊篱的约束,对自己的过分愤怒产生了悔意:“愿不睦能从神界和人间永远消失,还有愤怒,它使聪明的人陷于暴戾……但不管心中如何痛苦,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必须控制心灵。”(《伊利亚特》,第425页)而阿迦门农也认识到了自己的愚蠢,认识到自己顺从了自我“恶劣的心理”,他与阿基琉斯之间的敌对是“无意的冲突和争吵”,继而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主动要求和解。
难能可贵的是,英雄们也能在享受自由与自我约束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们认识到人们是自己“逾越既定的规限,替自己招致悲伤”,苦难并非神灵所给;他们也认识到自由的底线是不为恶,对触犯了这一底线的埃吉索斯之流痛加斥责。唯其如此,门托尔控诉那些为了满足个人贪欲的求婚者“随心所欲,肆意横行”,“正用绳索勒紧自己的脖子”,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为此,英雄们将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等关系中不能逾越的界限和限度视之为命运,并且认为命运是不可违逆的,只能遵从。因而人在自我定位时既要有精神上的超越追求,有所
成就,又要认识到超越的限度,在遵循适度原则的基础上去努力实现人生的梦想,这或许就是荷马史诗中诸位英雄的终极意识与终极追求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荷马史诗中的诸位英雄的这种通达、乐观同时又富有智慧的终极意识与终极追求呢?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恐怕与希腊人的民族精神和思维习惯有关。正如汉密尔顿指出的那样,“在整个希腊历史中,生命的信念始终充盈着人们的心灵”[6]17,这样一种始终铭刻着生之快乐的民族精神使得古希腊人尽管“深切地、无比深切地知道生之无常和死之切近”,却没有表现出灵魂与肉体之间无穷的争斗或者跌入虚无主义的泥淖,而是更加看重此生此世的美好生活和人生理想与价值的实现;除此之外,古希腊人也具有“将所有事物都看作某个整体的一部分的思维习惯”[6]277,所以他们从来不单单突出自我,而是把人生的命运通过“无限的背景”展示出来。其结果,反倒使得自我在各种动态的关系中更易处于某种均衡、适度的位置上;古希腊人信仰中的阿波罗崇拜和狄俄尼索斯崇拜的完美结合就证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荷马史诗中诸位英雄的终极意识与终极追求既是古希腊人生命智慧的形象化展示,又是希腊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它留给后人的启示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1]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M].孙席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 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5] 让·华尔.存在哲学——基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马塞尔、萨特的基本思想导论[M].翁绍军,译.赵鑫珊,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6] 汉密尔顿.希腊精神[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7] 狄金森.希腊的生活观[M].彭基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 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责任编辑:郑国瑞
2016-03-09
信阳师范学院2014年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侯朝阳(1979—),男,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讲师,南开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圣经文学、基督教思想史。
I106.2
A
1671-9824(2016)06-00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