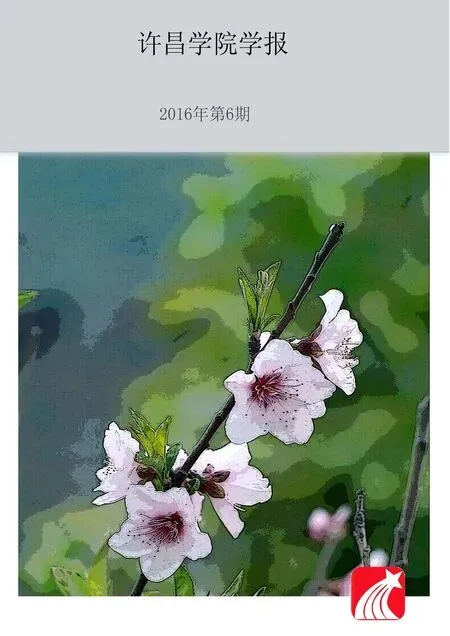成长视角下《简·爱》的女性意识研究
苏 仕 敏
(蚌埠学院 外语系,安徽 蚌埠 233030)
成长视角下《简·爱》的女性意识研究
苏 仕 敏
(蚌埠学院 外语系,安徽 蚌埠 233030)
《简·爱》是一部女性文学经典,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叙述了主人公在盖茨黑德、罗沃德、桑菲尔德、沼泽居和芬丁生活的五个不同阶段的成长经历。简·爱在盖茨黑德度过了孤独的童年,在罗沃德求学交友,在桑菲尔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爱情,在沼泽居收获了亲情,最后在芬丁与罗切斯特终成眷属。在坎坷的成长过程中,简·爱自尊自爱,坚定地追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爱情上的平等,勇敢地反抗当时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传统观念,展现出不屈不挠的女性意识。
简·爱;成长;疏离感;女性意识
《简·爱》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部经典的女性文学作品,自问世以来一直深受全世界众多读者的青睐。作者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对女主人公简·爱成长经历的描述表达了当时的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和平等地位的女性意识,简·爱也因此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经典的独立女性形象。她自尊自爱,坚持道德标准,积极地探索女性的未来出路,向歧视女性、没有给女性平等地位的社会传统发出了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依然信奉男权至上,大男子主义制约着女性,因此,主人公简·爱对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及其后来的幸福生活并非一蹴而就,也是经历了很多人生的坎坷才逐渐达到的。本文从成长的视角出发,根据主人公生活过的五个地方,即盖茨黑德、罗沃德、桑菲尔德、沼泽居和芬丁,将简·爱的成长经历分成五个阶段,并分别阐述在不同阶段简·爱的女性意识是如何慢慢地萌芽、觉醒、发展和成长的。最后结合作者的生活经历,浅析作品中展现出的女性意识的局限性。
一、成长的概念
“成长”一词来源于人类学,它指青少年首先要经历生活中的一系列磨砺与考验,然后逐渐变得成熟与强大,获得独立应对社会生活的才智、能力以及信心,最后与童年告别,进入人生的新阶段,即成年。[1]
“成长小说”一词源自德语Bildungsroman,原指德国文学中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它往往是以一个“白纸状态”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描述他毫不离奇的日常生活,他和别人交往的社会经历,以及他在社会熔炉中思想情感的磨砺、变化和发展,来展现他在心智上的成长以及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1]莫迪凯·马科斯把成长小说的定义分成两类:一类把成长描绘成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另一类把成长解释为对自我身份与价值的认识,以及调整自我、适应社会的过程。[2]成长小说通常展现了青少年在经历了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改变了原来的世界观或自己的性格,从而逐渐摆脱了童年的天真,最终进入真实复杂的成人世界。巴赫金指出,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3]
因此,成长小说就是以记叙青少年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它往往通过对青少年成长经历的叙述,展现他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感悟,反映出他的思想情感和心理智力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
二、成长视角下简·爱的女性意识发展
(一)盖茨黑德:童年时的疏离感及女性意识的萌芽
疏离感这个概念最早由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来,后来受到了社会科学的极大关注。巴克利在SeasonofYouth中指出,成长小说的基本要素包括成长和自我发现的过程、疏离感、与环境的格格不入、爱情的苦难经历等。[4]笛安认为疏离感标志着两个或者更多独立个体间的疏远或距离,包含着苦恼或者失落的意识。[5]我国学者杨东教授对于疏离感的解释是:疏离感是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以及自身等种种关系间,由于正常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支配控制,从而使个体产生的无意义感、压迫拘束感、社会孤立感等消极情感。[6]
小说中,主人公简·爱因为父母早逝不得不寄人篱下,住在盖茨黑德。盖茨黑德的主人里德太太虽然是简·爱的舅妈,但是毕竟毫无血缘关系,因此对简·爱的态度十分冷漠残忍,她竭力将简·爱与自己的孩子隔离开来。甚至连府里的佣人都直言不讳地说:“你连仆人都不如。你不干事,吃白食。”[7]9小说从“红房子”事件开始。因为无法忍受表兄约翰的蛮横无理,简·爱与之反抗,结果遭到里德太太的惩罚,被关到红房子里去。这个红房子自简·爱的舅舅里德先生去世之后就再也无人住过,年幼的简·爱一个人被关在漆黑的屋子里,不禁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坟墓死人之类的想象,因此惊吓过度,昏厥过去。这件事成了简·爱童年产生反叛意识的导火索:“她在通向我未来的道路上,播下了反感和无情的种子。”[7]33正是这种反叛的精神使得简·爱渴望摆脱盖茨黑德的生活,所以当药剂师劳埃德先生建议让简·爱出去读书时,她不禁产生了向往:“上学也是彻底变换环境,意味着一次远行,意味着同盖茨黑德完全决裂,意味着踏上新的生活旅程。”[7]23
童年的简·爱无疑是孤独的,她虽身居华府却被排斥在家庭生活之外,自幼就缺乏安全感,因而在情感上产生了疏离感。而正是这种疏离感使得简·爱幼小的心里萌发了离开的念头,使她渴望自己能早早独立,这种对独立生活的渴望也极大地影响了简·爱之后的人生。因此,后来当她完全适应了罗沃德的学校生活之后,她却渴望了解外面宽广的世界;当她发现罗切斯特先生的太太还活着时,尽管前途迷茫,她还是毅然选择离开桑菲尔德;而当她在沼泽居获得了亲情和财富时,她却又因为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前往芬丁庄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童年的疏离感正是简·爱早期女性意识萌芽的体现,她虽寄人篱下,但是心中所念的并非如何巴结讨好他人,而是向往自由,渴望尽早独立。
(二)罗沃德:自我能力的不断提升和女性意识的发展
在罗沃德的最初生活十分艰难,那里充斥着恶劣的饮食、刺骨的严寒和繁琐的规章,而对于刚刚到达的简·爱来说,最让她难以忍受的莫过于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对她的羞辱。布罗克赫斯特先生是学校的经营者,为人虚伪残酷,他一方面向学生们宣扬忍受贫困磨难的说教,另一方面却和家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他在众人面前指控简·爱是个说谎者,当众惩罚她。这使得天性自尊自爱的简·爱倍感羞辱,无法忍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简·爱遇到了海伦·彭斯和玛丽·坦布尔两位女性。作为她的良师益友,她们帮助简·爱度过了在罗沃德最黑暗难熬的日子,引导她以积极阳光的态度去面对今后的生活。
海伦·彭斯是个安静、有忍耐力又早熟的女孩,对于生活的荒谬和不公、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当被老师严厉惩罚时,她也能泰然处之。此外,她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诚。当简·爱为她受到老师的当众责罚而愤愤不平,以为她想离开罗沃德时,她回答:“送我到罗沃德来是接受教育的,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就走才没有意思呢。”[7]57她劝说简·爱要学会原谅宽容舅妈对她的不公和残忍:“暴力不是消除仇恨的最好办法。同样,报复也绝对医治不了伤害。”[7]59布罗克赫斯特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羞辱简·爱,称她是个说谎的孩子,要求全校师生都提防着她,这令简·爱羞愧不堪,感到自己永无翻身之日,但是海伦的安慰使她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海伦说:“即使整个世界恨你,并且相信你坏,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知道你是清白的,你就不会没有朋友。”[7]73在海伦的影响下,简·爱逐渐感悟到人的胸怀的博大深邃,能以更宽容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快,这对她后来勇敢面对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影响非常大。
玛丽·坦布尔小姐是罗沃德学校的校长,外貌优雅端庄,心地善良仁慈,做事公正利落,她的身上似乎总是笼罩着圣母玛利亚般的光环。简·爱遭受诽谤时,她让简·爱为自己辩护,并亲自写信揭发真相,最后为简·爱昭雪平反,在全校师生中恢复了简·爱的名誉。这对年幼的简·爱来说,意义非同小可,使她终于能卸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产生了积极的生活斗志。“我打算从头努力,决心排除万难披荆斩棘地前进。”[7]79正是在她的引导下,简·爱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同时又感受到了母爱和友谊。“我所取得的最好成绩归功于她的教诲……她一走,那种已经确立了的使罗沃德有几分像家的感情和联系,都随之消失。”[7]90玛丽·坦布尔小姐离开之后,简·爱意识到真正的世界无限广阔,她渴望了解、体验外面的精彩世界,开始了真正的对独立生活的追求。
如果说布罗克赫斯特代表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力量,这股力量目空一切、自以为是,那么海伦·彭斯和玛丽·坦布尔则是男权社会中优秀独立的女性代表。前者忍耐包容,后者睿智独立,正是受她们的影响,简·爱感到“比较和谐的思想,比较有节制的感情,已在我的头脑里生根”[7]90。除了海伦和坦布尔对于简·爱的积极影响,罗沃德学校的生活对于她的一生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她在那里获得了广博的知识,两年的教师工作让她熟悉教学,她能够“胜任良好的英国教育所含的普通课程,以及法文、绘画和音乐的教学”[7]93。这一切都为她后来的独立生存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此外,她拥有深刻的思想和渴望自由的心灵,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憧憬。因此,在罗沃德的生活,是简·爱女性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她渴望独立自由,敢于独身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这与当时社会对女性应安分守己的要求是相悖的,但也因此更凸显了她渴望独立的女性思想。
(三)桑菲尔德:爱情经历和女性意识的成熟
爱情经历是成长小说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巴克利指出,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对生活的直接体验至少包括两场恋爱或性的遭遇,一个粗俗沉沦,一个激越飞扬,当主人公能够堂皇地决定融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青春期,进入了成年。[4]
简·爱在桑菲尔德的生活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她遇到罗切斯特之前,桑菲尔德的生活平静安宁,对她来说如同一潭死水。由于刚刚离开了生活了八年的罗沃德,她渴望的是更富于变化、更具备挑战的环境。在桑菲尔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感到“对这种生活的稳定安逸的长处,我已难以欣赏”[7]119。很显然,此时简·爱在心中考虑的是自己的将来。在那个男性主权的世界里,她对自己身为女性的处境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思考:“一般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她们对严厉的束缚、绝对的停滞都跟男人一样感到痛苦。比她们更享有特权的同类们,只有心胸狭窄者才会说,女人们应当只做做布丁,织织长袜,弹弹钢琴,绣绣布包。要是她们希望超越世俗认定的女性所应守的规范,做更多的事情,学更多的东西,那么为此去谴责或讥笑她们未免是轻率的。”[7] 120这段话是简·爱女性意识最为清晰的表露。身为女性,她十分清楚要想在这个社会中成就一番事业绝非那么容易。她本身目前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人们要求女性的标准,她独立自主,有自己的思想,甚至开始为自己规划未来的事业:“我最大的愿望,是积攒下足够的钱,将来自己租一间小小的房子,办起学校来。”[7]222在桑菲尔德的家教工作,是她整个计划的起点。
作为一名独立的女性,简·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未来筹谋规划了,但是这些计划都因为遇到了罗切斯特而被搁浅。她和罗切斯特之间的爱情是整部小说的主线,也最能体现出简·爱反抗传统偏见的女性意识。
简·爱相貌平平,只是桑菲尔德的一名家庭教师。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其地位等同于一般的佣人,因此被认为比主人的地位低下。但是对于罗切斯特来说,简·爱与他过去接触的漂亮浅薄的女性不同,她单纯、庄重,可同时又独立、思想深邃,两人认识不久,她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长相并不帅气,尽管他身份高贵,收入可观。在简·爱看来,罗切斯特与众不同,在和他的相处中,她的人格得到了他的尊重,在精神上她感到与他平等:“你稳重、体贴、细心,生来就是听别人吐露隐秘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不易感染的头脑,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我不可能腐蚀你,而你却可以使我重新振作起来。”[7]161罗切斯特对简·爱的尊重和信赖,他们之间的交流谈心,不断地促使两人之间的感情升温。失火事件加深了两人彼此的信赖,尽管后来出现了英格拉姆小姐,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之火没有被减弱,相互反而更被对方吸引。简·爱勇敢地面对世俗的目光,冲破阶级的偏见,坦露了自己的心迹:“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遭人践踏,也没有弄得古板僵化,没有混迹于志向低下的人之中,也没有被排斥在同光明、健康、高尚的心灵交往的一切机会之外。”[7]284
对于简·爱来说,尽管她与罗切斯特在地位、金钱上有着差异,但是两人的精神、灵魂是平等的。也正是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使得她后来在发现伯莎·梅森的存在后,虽然痛苦万分,但还是选择了离开出走:“无论怎么说,已没有我的份和我的容身之地了,先生。”[7]341面对生活的沉重打击,简·爱虽然悲痛欲绝,但是没有哭闹哀怨,而是沉着冷静地思考着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罗切斯特恳求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并许诺给予她绝对的尊重,但是简·爱心中明白,尽管她可以打着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旗号留下来,但这既是对自己独立人格的践踏,也是对同样身为女性的伯莎·梅森的侮辱:“对那个不幸的女人来说,你实在冷酷无情。你一谈起她就恨恨地——势不两立。那很残酷——她发疯也是身不由己的。”[7]343她以自己的道德气节战胜了自己痛苦的感情,毅然离开了罗切斯特。
简·爱当初答应了罗切斯特的求婚是出于对他的爱情,而这种爱情是基于两人在精神思想上的平等。后来选择离开,正是其独立的女性意识发展成熟的表现,尽管前途一片迷茫,充满荆棘,但是她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道德标准,身为独立的女性,不做任何人的附属品,保持自尊自爱和对自己命运的掌握。
(四)沼泽居:收获亲情和思想上的升华
离开了桑菲尔德的简·爱在荒野中流浪了两天,被好心的圣·约翰兄妹收留。她与戴安娜和玛丽两姐妹志趣相投,她们互相学习,很快便成了好友。圣·约翰相对来说寡言少语,他致力于自己的宗教事业,并且希望简·爱也能同他一样,献身于此。在圣·约翰的帮助下,简·爱开始在村里的女子学校当教师,这也给了简·爱一个新的机会让她重新拾起自己的梦想,并对自己的处境开始了深刻并且清醒的反思。起初她对学生的无知、周围环境的贫穷和粗俗有些失望,但很快,她开始意识到这些情感是不对的,并且努力消除这些情感。随着对学生了解的深入和学生不断的进步,“我发现她们中间不少人天性就懂礼貌,自尊自爱、很有能力……这些人渴求知识,希望上进。我在她们家里度过了不少愉快的夜晚”[7]407。工作上带来的满足感让简·爱对生活心存感激,在回忆和反思过去的生活时,她感到“自己坚持原则和法规,蔑视和控制狂乱时刻缺乏理智的冲动是对的”[7]408。
沼泽居的生活在简·爱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使她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亲人,原来圣·约翰兄妹与她是表兄妹关系。这让她一直被排挤的孤独人生一下子充满了亲情。她和圣·约翰兄妹平分自己意外得来的财产,享受着充满亲情的家庭温暖。但圣·约翰的求婚让她震惊彷徨,而最终她还是没有接受,因为在心里她明白,虽然圣·约翰所从事的事业伟大光荣,他向她求婚的理由也冠冕堂皇,可是他的求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把她当作了传教的工具,认为她坚忍的性格适合做传教士的妻子。他对宗教事业的忠诚和奉献令人敬畏,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这差点使简·爱违背自己的内心感受而顺从他,但是最后对罗切斯特的深切思念,还是让她摆脱了圣·约翰的影响,远离了失去自由和迷失自我的威胁。
在简·爱的成长过程中,她遇到的每一个男性都对她的独立和尊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威胁。[8]布罗克赫斯特的虚伪冷酷、罗切斯特的一往情深和圣·约翰的奉献与专横,都是那个男性主权时代对女性的蔑视,简·爱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自身的尊严和独立无时无刻不受到威胁。在经历了种种情感的跌宕起伏和生活的严峻考验之后,简·爱在理智和情感的调和中,从冲动易怒的女孩成长为一名自尊、自爱、独立、成熟的优秀女性。
(五)芬丁:终成眷属和完美的结局
简·爱最终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尽管这时的桑菲尔德已经被烧毁,罗切斯特也在火灾中失去了健康的体魄,但是伯莎·梅森——阻碍他们婚姻的唯一缘由,已在火灾中丧生。有情人终成眷属,简·爱和罗切斯特最终苦尽甘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是小说的完美结局,体现了夏洛蒂·勃朗特对于理想爱情的坚定信念:爱情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两颗心的契合,婚姻是爱情的最高表现形式,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依照习俗缔结无爱婚姻的反驳。简·爱和罗切斯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同时,他们都保留着自己的尊严和个性。简·爱给予罗切斯特的帮助并不是怜悯和施舍,而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和真爱;罗切斯特虽然身体残疾,但是接受简·爱的帮助并不觉得痛苦或者屈辱,这也是由于平等的爱没有令他丧失尊严。[9]
在小说的结尾,所有人物的命运都做了交代。善良的人们最后都有了好的归宿:罗切斯特后来终于恢复了一只眼睛的视力,看得清自己孩子的长相;里弗斯姐妹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圣·约翰献身给自己追求的事业。小说的完美结局,表明了夏洛蒂·勃朗特对于女性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也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追求独立自由的信心。
三、 总结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依然以男性文化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女性的成长必须以社会的需要而非其身心发展或创造潜力的实现为出发点。[10]因此,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成长就意味着要具备从层层厚茧中突围而出的勇气。夏洛蒂·勃朗特作为女性作家从自身的生存体验出发,借助简·爱艰辛的成长之路,讲述了当时的女性希望独立生存的愿望,表达了她内心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她的笔下,童年的疏离感赋予简·爱反叛的精神和对独立自由的渴望;罗沃德学校的生活既教会了她后来赖以生存的技能,又养成了她忍耐坚韧的性格;桑菲尔德的家庭教师工作使她第一次真正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这让她对生活和人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清醒的思考,她和罗切斯特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更坚定了她要坚持独立、追求自由的决心;在沼泽居,她收获了亲情,同时乡村女子学校教师的工作使她有机会反思自己的过去,并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在经济上独立、精神上自尊自爱、不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的信念;最后她在芬丁庄园与罗切斯特终成眷属,这是她不顾世俗偏见、坚持追求真爱的结果。夏洛蒂·勃朗特以女性的独特视野展现了当时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她对女性独立存在价值的肯定。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夏洛蒂·勃朗特展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不够彻底。如她在小说中描写了简·爱在求学之路上的追求和对未来事业的打算,但也只是简单几笔带过。简·爱意外收到遗产之后,就没有继续做乡村学校的教师,在她最终嫁为人妻之后,作者没有进一步叙述她在事业上的追求,也没有提及她当初打算办一所学校的计划。她和罗切斯特最后的结合也是在她意外地获得了一大笔遗产之后才发生的。因此,小说结局的理想化削弱了小说中女性对社会习俗的抗争力量,体现了夏洛蒂·勃朗特对男性社会的妥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知识女性在争取更多女性权益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矛盾和迷茫。
[1]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 Marcus M.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0 (2):221-228.
[3] 巴赫金.小说理论[M]. 白春仁,晓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 Buckley J H.Season of youth:the bildungsroman from Dickens to Golding[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5] Dean D G. Alienation: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1(26):753-758.
[6] 杨东,吴晓蓉.疏离感研究的进展及理论贡献[J].心理科学发展,2002(1):71-77.
[7]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 黄源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
[8] 刘丹.论《简·爱》的成长主题[D]. 华中师范大学,2005.
[9] 赵艳梅.《简·爱》中罗切斯特爱情观解读[J].长江大学学报,2012(1):37-39.
[10] 毛竹生.简·爱的成长之路及其心理机制[J].邯郸师专学报,2001(6):30-33.
责任编辑:张怀宇
A Study of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inJaneEy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itiation Story
SU Shi-mi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China)
JaneEyreis a classic feministic work. The author Charlotte Bront narrates the heroine’s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Gateshead, Lowood, Thornfield, Moor House and Ferndean. Jane Eyre has an isolated childhood in Gateshead. She gets education and friendship in Lowood. In Thornfield she experiences ups and downs of her love, and then she goes to the Moor House where she obtains family love. Finally she marries Rochester in Ferdean. In spite of all the hardships, Jane Eyre’s self-respect and her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and equality reflect a strong feminism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Jane Eyre; initiation; alienation; female consciousness
2016-08-05
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转型期青少年成长研究”(2013SQRW071ZD)。
苏仕敏(1981—),女,安徽全椒人,讲师,硕士,2014年赴美国特洛伊大学进修,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4
A
1671-9824(2016)06-0063-05
——造梦城市中的精神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