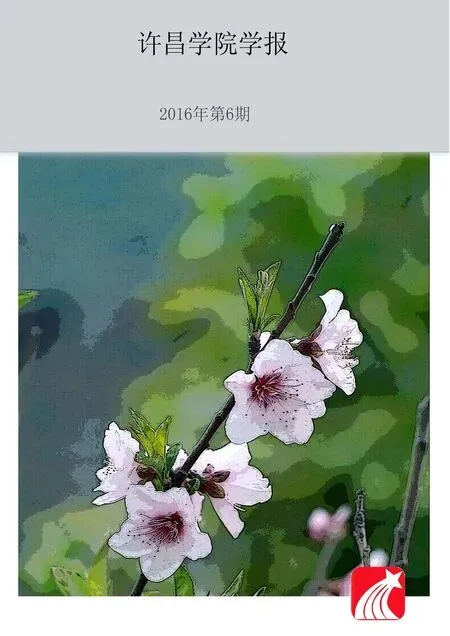“气”“治气”与“修人事”
——《尉缭子》思想研究
章 丽 琼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732)
“气”“治气”与“修人事”
——《尉缭子》思想研究
章 丽 琼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732)
先秦兵书相关记载中,“气”既指“士气”,也指战争过程中需要把握的“气机”,是治军作战的关键因素。有关“治气”之论,先秦兵书皆有所涉及,其中尤以《尉缭子》论述篇幅最为集中和系统。《尉缭子》在不同的篇章都提及“气”在战争中的作用,并对如何“治气”提出了多种相应的措施,其对“士气”“气机”的关注,是春秋战国时期重人事思想的体现。
《尉缭子》;士气;气机;治气;人事
庄公十年(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指挥时避敌锐气,抓住有利战机,取得战争胜利。鲁庄公问他指挥作战艺术时,则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1]183可见在战争中把握敌方的士气,并利用其规律来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先秦兵书中对战争中“气”的论述多处可见,其中《尉缭子》直接提出“战在于治气”[2]308。目前学者在研究《尉缭子》时大都倾向于版本学或者军制史方向的研究,有关《尉缭子》中“气”与“治气”所涉及的先秦军事思想研究的论述,尚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尉缭子》中关于“气”的内涵及“治气”手段的论述,结合先秦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趋势,分析先秦兵家思想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关怀。
一、《尉缭子》中“气”的内涵
“气”是先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指构成自然界的客观物质,也指人的身体血气。兵家在著书立说时重视“气”在治军作战中的重要性。如《司马法·严位》篇中有“凡战:以力久;以气胜”[3]102。《孙子兵法·军争》提及“三军可夺气”[4]113。《吴子·论将》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於一人,是谓气机。”[3]79上述文献皆强调“气”在先秦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前两则所论之气是指将士之“气”,后一则是指在战争过程中需要把握的“气机”,即通过对敌我双方士气的把握,而选择适当的作战时机。此外,《左传》也有对战争中“气”的论述,如庄公十年曹刿论道:“战,勇气也。”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楚战争过程中,当楚国军队要追赶晋军时,晋君撤退,当时的晋国军吏说:“以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1]458子犯之言即是说在出兵作战中,“师直”就是气壮,“师曲”就是气衰,军队的士气决定战争的结果,而不在于军队作战时间的长短。《左传》中对士气、气机的论述也与先秦时期的兵书意旨相合。由此看来,先秦兵书中的“气”,一方面是指治军作战中将士们的“士气”,可理解为士兵作战时英勇杀敌的斗志,又可解读为旺盛勇锐的士气[4]114,也可归结为军事战争中的“精神力量因素”[5]33,还可解读为战争中主客双方作战气势的“气机”,作战时需要将领去激励和把握,以便取得战争的优势。先秦时期的军事论著中无论是将士之“气”,还是战争的“气机”,都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
《尉缭子》一书中多次强调“气”作为一种独特的战斗力,对战争的结果会有决定性的影响。如“伤气败军,曲谋败国”,士气沮丧就会导致军队溃败[2]353。“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这是说讲求武备,分析敌情,设法使得敌人士气丧失而军队涣散,虽然军队完整但却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谋略取胜。所以“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即是指在战争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军队将士之“气”,掌握“气实则斗,气夺则走”的规律,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2]293。为充分说明士气的重要性,在《制谈》篇中,作者以一个亡命之徒作形象的比喻:“一贼杖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2]288这一亡命之徒在闹市中行凶,周围的众人都躲避他,并非因为他一个人勇敢,而是因为抱着拼死决心的气势远远胜于贪生怕死的怯弱。可见在《尉缭子》的军事思想中,战争中的士气与对战争气机的把握是战争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更好地把握运用战争中的“气”,《尉缭子》最终提出“战在于治气”。
二、“治气”: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气”在先秦兵书的论述中作为一种独特的战斗力,是决定战争结果的重要因素,如何提高“士气”,把握好作战的“气机”,是兵家治军作战理论的重要内容。《尉缭子·兵令》有云:“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奋也。”[2]360即是说,若是百万的军队不拼死战斗,还不如一万军队齐心协力杀敌,一万人的军队如果士气不振,还不如百人的军队凝聚成一股士气奋战。所以书中强调“战在于治气”,将“治气”的成功与否作为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孙子也提出“治气”一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军队刚投入战斗时士气饱满,过了一段时间士气就逐渐懈怠,到了最后士气就完全衰竭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先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到敌人士气懈怠时再去进攻它,这是掌握运用军队士气的作战方法[4]113-114。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解释为何在“齐人三鼓”之后再击鼓,是在于“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的军事谋略,即根据对敌我双方士气消长的规律的判断,对战争过程中“气机”的把握与运用。《孙膑兵法·延气》对“气”也有专门论述,并结合不同境况下的军气提出了“治气”的几种方略,如“利气”“延气”“激气”“励气”等[6]94。
从已有文献材料来看,“治气”是先秦兵书的一个重要议题。《孙膑兵法》有以“治气”为专题的《延气》篇,遗憾的是残简缺失内容较多,其他兵书也有零星论及,仅《尉缭子》中论述较为丰富,其“治气”主要表现为治军与作战两个层面:治军时需要提高军队中士卒的斗志,或者说保持士卒积极作战的精神面貌;战争过程中需把握主客双方的士气消长,以抓住最佳时机,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首先,制定严格完善的军事制度,保障军队的稳定和将领士卒心理情绪的稳定,是维持士气的一个关键因素。“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形乃明”。《尉缭子》把定军制作为治兵的首要内容,二十四篇中除《制谈》专论法令制度外,《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武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兵教》等篇都是对军制的详细描述与规定,涉及作战现场的军队法纪、部队的详细编组、部队编组内的不同标志、指挥信号,以及行军时保持的序列等等。只有有了完善系统的军事制度,将领、士卒方可依制行事,这样才能“士不乱”,保证军队将领、士卒心理情绪稳定,从而达到“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的状态[2]287。当然,这也是保持部队士气的一个重要方式。所谓“百人尽斗”“千人尽斗”“万人齐刃”的强大气势,能让人从中联想到在严格军制规定下,列队整齐的将士们在战场上勇敢杀敌的精神面貌。
既然军制是保障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那么,只有军制严明,才能保证士卒在战争中奋勇直前。“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若军制松散,则战争中军心涣散,士气也会受到消极影响。“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2]288。士气大乱则会导致内部崩溃,所以国家应实施严明的军事制度,加强对军队的治理,以便保证军队高昂的士气。“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才可以“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2]329。在实际治军过程中严格落实军事制度,通过“修吾号令,明吾刑赏”,最终达到“使天下非农而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2]289。在严明赏罚制度的激励下,天下广大民众争先恐后从事农耕,投入战斗,这种团结一致的求胜精神的发挥,是士气高涨的体现。
其次,要有专门的军队训练和明确的作战法令,并通过具体可行的方式来保证法令的实施,以保证战争过程中军队具有高昂的士气,最终克敌制胜。《勒卒令》载:“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即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皆有自己的用法:击鼓是命令军队前进,再次击鼓是命令军队发起进攻;鸣金是命令军队停止战斗,再次鸣金则是命令军队后退[2]339-340。将士根据各种指挥工具所发出的信号,来判断战斗中的进退,以此来保持军队阵势不乱,并适当借机激发士兵气势。再配合《经卒令》提到的布阵法:“以经令分之为三焉: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主张将左、中、右三军与青、黄、白三色相配,各行次依次配色,并配以金鼓等指挥法,保证军队士气的高涨[2]337。有了如此严整划一的指挥,配合派兵布阵的方法,就会形成“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三军”[2]340的作战气势,此阵势足以震慑敌人,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目的[4]36。
此外,严格遵从赏罚的原则,利用适当的赏罚形式,来激励将士作战的积极性。如“杀之贵大,赏之贵小”。杀戮,贵在敢于向大人物开刀;赏赐,贵在能够给小人物奖赏。即“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2]310。这样才能达到“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的战斗热情。
最后,注重发挥将领在激发士气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军事将领自身的素质培养。在军队建设方面,《尉缭子》把将领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心”与“肢”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权也”[2]300。将帅被视为军队的核心,是军队的灵魂,同时也是“治气”的主体,是保持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力量。国家的存亡安危就在于将领帅鼓槌头的指挥:“夫将提鼓挥枹,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端,奈何无重将也。”[2]310因此,要重视培养和运用军队中将领的指挥才能。《尉缭子》的《战威》篇进一步总结道,战争之本就是“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2]294。领兵作战的人,必须本着自身的表率作用来激励全体士卒,如果士卒的斗志没能激发出来,士卒就不会为国捐躯,全军就不能奋战。在《孙膑兵法》的论述中,对将士在激励士气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有类似的观点:“[上缺]以威三军之士,所以敫(激)气也,将军令[下缺]。”“[上缺]其令,所以利气也,将军乃[下缺]。”“短衣洁裘,以励士气,所以励气也。”[6]94从残缺简文中的“将军令”“其令”“短衣洁裘”等关键词,可见将帅的指挥乃是士气消长的重要因素。
据《尉缭子》中的记载,将领在激励全体士卒斗志时,都不乏有“励士之道”。《战威》篇提到:“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通过这种方式,制定出百姓满意的制度,实惠的田地俸禄,同乡同里相互劝勉,丧礼葬埋互相帮助,以此激励百姓的斗志,保证军队士气稳定,实现“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入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的“战之道”[2]294。
将领在军队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具有非常良好的修养。《尉缭子》提出:其一,将帅必须心胸豁达,要有“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的气质,同时也要克服“心狂、目盲、耳聋”三大弊端[2]285,保证在战争中法令的一致性,这对于提高军队的士气至关重要。“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2]293。其二,将领要爱护士卒。士卒在战斗中拼死奋战的斗志,奋勇向前的士气,都是需要自愿效力的基础,所以《尉缭子》强调将帅要处理好体贴关心士卒与树立威信两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古者率民,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2]294。即是说,善于领兵的将领,必须“爱在威先”。因为爱抚施行在下,士卒就会顺从;权威树立在上,将军就会得到士卒拥护。爱抚部下,士卒便忠心不贰;威震全军,士卒便秋毫无犯[2]300。将帅只有自身具有很高的德行,才能真正在军队中树立威信,让士卒信服,才能保证军令的实施,使全军保持“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的战争热情与高昂斗志[2]285。对此,《吴子》的《论将》篇也提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即军队士气的盛衰与战争中作战气机的把握,全扛在将领一人身上。
将领必须掌握运用士气变化的规律,把握主客双方士气的消长,抓住最佳时机。这要求将领在军事战争过程中,要有思想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尉缭子》指出:“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将领必须充分了解敌我双方的详细情况,反对冒昧出击[2]293。“兵起,非可以忿也”,不能逞一时之气而战,也就是“不起一日之师”、“不起一月之师”、“不起一岁之师”[2]285。《六韬·犬韬·练士》篇提到“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阵之士”[7]277,即将锐气之士聚为一卒,使其先去冲锋陷阵。曹刿论战中也特别强调“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由此可知,士气变化的一般规律是始时锐不可当,继而渐趋懈怠,最终完全衰竭,故“善用兵者,当其锐盛则坚守以避之,待其堕归则出兵以击之”[4]113。
《尉缭子》非常细致地注意到这些治军作战的精髓。在把握敌我双方情况后,要实施相应的策略,若策略不正确,就会大伤士气出现负面结果。比如在布置防守时,如果把英雄豪杰、精锐部队、优良武器全部集中在城内,同时收集城外地窖仓库粮食物资,拆毁城外民房,让民众全部退入城堡,这就是消极防守。此种做法会导致“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的负面结果[2]305。所以将领要懂得用兵之道,适可而止,能事先估计到不知适可而止所带来的失败后果。与此同时,也特别忌讳那些只知一味出击的军事行动。如《战权》篇就说:“凡夺者无气,恐者不可守;败者无人,兵无道也。”[2]327即轻易进兵而速求决战,敌人就会设计阻击,贸然中计前往,敌人便稳操胜券。
三、“治气”与“修人事”
《尉缭子》强调“士气”、利用“气机”在作战中的重要性,并且在如何“治气”方面着重从将领对军制的制定与执行、将领本身的基本素质以及将领与士兵的关系等方面来寻求答案,这是其军事思想中对将士与士兵,即对人的关注的体现,这与全书首篇《天官》中提到的“谓之天(时)(官),人事而已”的主旨相一致[2]282,也同先秦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大势相吻合。
自《尚书·西伯戡黎》中记载当周人大军压境之时,祖尹对纣王说:“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则责命于天?”[8]1047,1055即祖尹将天命不会眷顾殷商的原因归结为君主的统治无道与民众对君主执政失望。商周天命观的发展所涉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对人事的关注。罗新慧在《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一文中认为,周人所说之“德”还并非完全是道德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具体的统治方式,即怀柔民众的治术和上天所赐,周人的具体所得,并直接指出周人常常以人事来论天命[9]。可见虽周崇天命,但周人已经认识到人事对天命的影响。因此,“敬德保民”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至春秋时期,天命的思想逐渐被淡化,《左传》中所记与战争相关的卜筮之事,据学者统计达20次之多[10]26。此时虽有卜筮,但人们已非完全崇信卜筮。如僖公十九年关于卫人伐邢之卜,所卜结果虽是不吉,但宁庄子依旧伐邢,也并未因此而受到天的惩罚,反而在出师之日出现天降甘霖之吉兆;又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1]1392。司马子鱼请求改卜,对前卜持有怀疑态度。这些都是对“天命”决定战争胜负的怀疑,是对人的主动性与能力认识增强的体现。
先秦兵书中所论的“士气”指向的是人的精神、意志层面,其对人的关注,是对主观性的把握,这恰是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天命”观受到冲击,人本思想发展的体现[11]。疑天重民思想在先秦时期军事思想中非常普遍,如《左传》直接提出“无民,孰战”的观点[1]873,《尉缭子》也有“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的看法[2]293。因此,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是以民为重、“修人事”,否则就如《武议篇》武王伐纣事例,“武王不罢市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无祥异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2]293。军制、军令、将领的素质都是决定军队士气的重要方面,战争的胜利不是依赖于天官,而是依赖人事,所以有“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2]282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2]78之论。对“士气”的重视是用兵作战过程中“修人事”的体现,强调调动士气以把握有利的作战时机,即对战争之“气机”的运用与把握,亦是强调人对战争的规划与控制的体现,突破已有的对“天官”、“时日”的依赖,这是人自身得到重视的表现。
《尉缭子》强调“战在于治气”。其对“气”的重视,即是对人的重视以及对人精神力量的强调,这是先秦军事思想中人本精神的体现,是诸子时代丰富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变化趋势的表现。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黄朴民.黄朴民解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1.
[3] 黄朴民.黄朴民解读《吴子》·《司马法》[M].长沙:岳麓书社,2011.
[4] 黄朴民.黄朴民解读《孙子兵法》[M].长沙:岳麓书社,2011.
[5] 徐勇.《吴子》·《尉缭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6]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黄朴民.黄朴民解读《三略》·《六韬》[M].长沙:岳麓书社,2011.
[8] 顾颉刚,刘起玗.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 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J].历史研究,2012(5):4-18.
[10]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1] 黄朴民.先秦军事思想发展的概况及其特色[J].济南大学学报,2000(4):1-8.
[12]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罗 操
The Qi, Application of the Qi and the Human-orientated Thought——The Research on Thought ofWeiLiaoZi
ZHANG Li-qio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732, China)
Recorded in the pre-Qin books on strategies, the content of Qi refers to the soldiers’ mental outlook as well as the timing of grasping the troop’s spiritual power in the warring. Qi is the critical factor in governing the troops and directing their operations. On the Qi theory, all the pre-Qin military books are involved, especiallyWeiLiaoZi, which gives the most concentrated and systematic exposition. In different chapters,WeiLiaoZimentioned the role of Qi in the war and proposed a variety of appropriate measures on how to apply the Qi. Its focus and concern on the soldiers’ subjectivity and the way to improve it reflects the trend of pre-Qin ideas.
WeiLiaoZi; the soldiers’ mental outlook; the timing of grasping the troop’s spiritual power; the way to apply the Qi; humanistic thoughts
2016-05-16
章丽琼(1986—),女,安徽芜湖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
E892
A
1671-9824(2016)06-007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