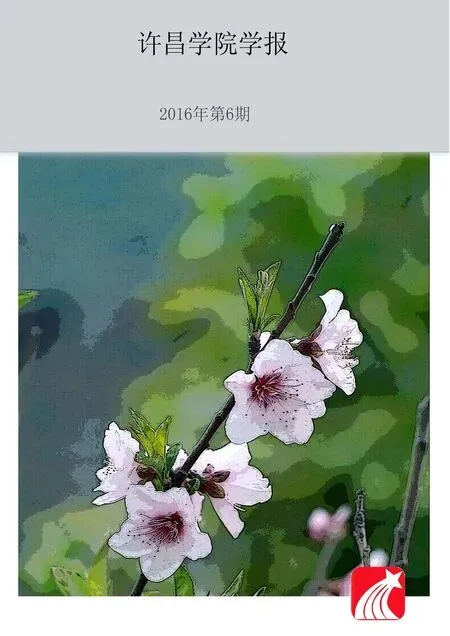政治晋升与表演:麻城建国社“放卫星”始末
宋 其 洪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政治晋升与表演:麻城建国社“放卫星”始末
宋 其 洪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1958年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放卫星成了当时政治表现先进与否的标志。那些具有强烈晋升意愿的省市领导积极响应这一政治号召,利用官僚制的组织渠道,将这一政治压力层层向下级递解。麻城作为革命老区,承担起放卫星的重任。建国社又是麻城的先进单位。社长王乾成在县委领导期许下,消除异议,利用掇秧并丘的办法,终于制造出天下第一高产量田。
放卫星;政治需求;政治表演
一、“全国学麻城,麻城怎么办?”
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农业生产“大跃进”。“大跃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湖北省委紧跟中央步伐,向全省发出号召,提出五到七年实现“四、五、八”的粮食增产计划。
5月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上出现了襄阳小麦亩产五千多斤、谷城油菜亩产一千多斤两颗高产卫星。这给与会的麻城领导造成很大压力。麻城过去一年的工作成绩,获得省委领导一致称赞。其中,亩产皮棉过百斤,成为全国棉花生产的先进典型。《人民日报》发表《向麻城人民学习,向麻城人民看齐》的专题社论。王任重曾撰文号召向麻城看齐,学习麻城。同时,麻城作为革命老区,若能在大跃进中拔得头筹,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可以获得出身麻城的中央干部的认可。作为省委领导眼中的先进县,县委副书记赵金良在本次会议上,却只“狠心上报小麦亩产五百斤(实际全县亩产不到二百七十斤)”。省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批评麻城“背着先进包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会议结束后,省委领导和黄冈地委书记姜一分别找赵金良:“全国学麻城,麻城怎么办?”他们要求县委领导回去考虑一下,“怎么样跟上目前大跃进的形势?”
省、地两级领导的点名批评、专门叮嘱,给麻城县领导层造成巨大的行政压力。与会县级领导迅速拍板成立“中共麻城县委高产办公室”。县委副书记赵金良传达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和省、地委对麻城工作的批评与指示,要求“在夏收的高产上……工作的着重点要放在水稻上,力争早稻第一颗高产卫星在麻城升起”[1]。同时,县委领导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改进领导方法,“加强集体领导,实行分地区、分战线负责,一包到底的责任制”。县委副书记赵金良“负责粮食生产”,“侯尚武、郭齐贤包白果”[2]。
为了保证早稻卫星第一个升起,县委领导要求工作人员“一是调查摸底早稻高产典型;二是破除迷信,用敢字当头的革命精神,提早二季稻插秧期,确保二级稻高产”[1]。尽管如此,在一两个月后,还是没有高产卫星的消息,背负巨大压力的县委领导,尤其是专门负责的县委副书记赵金良对下级提出严厉批评,斥责工作不负责任。7月中旬,闵集六大队妇女队长吴立荣在自己的试验田上,放出亩产可达六千多斤的卫星。县委领导积极组织验收,同时上报省委。《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出“第一颗早稻卫星上天”的消息。第一颗早稻卫星的升天,缓解了县委领导的巨大压力。然而邻省安徽枞阳县放出比闵集更大的卫星。这种来自省际的竞争,进一步加重县委领导的压力,“笑脸顿时消失,人人的额顶上又增添了几道皱纹”[1]。
二、天下第一田
为树立高产卫星的旗帜,麻城县委领导认为“能否完成新时期的各项艰巨任务,关键在于提高领导思想,改进领导方法”[2]。一方面紧抓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是统帅,思想是灵魂”,开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先进与落后、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斗争。其中,又以批判和克服各种形式的右倾保守思想为中心”,“从而使人们挣脱思想束缚,树立敢想、敢说、敢独创的共产主义风格,树立面向困难战胜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3]。为了彻底解放人们的思想,使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能长久延续,他们开展全方位的整风,运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实现整风经常化、制度化。另一方面“一切领导带头干,样样种好‘试验田’”,要求从县委到社队干部都亲自下田,带头深耕、密植。同时,掀起“全党、全民社会主义大竞赛,检查评比定高低”[3]。
6月中旬,县委在闵集乡召开水稻现场会议,学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研究如何鼓足干劲争取水稻大面积平衡丰产和创造高额丰产新纪录”。县委要求“到会的人能不能把稻谷搞成一年三季收?把原有的试验田提高一步,搞亩产3万斤的高产?”同时,他们给下级指点迷津,“把已经定值的早稻掇秧并丘,达到高度密植,腾出来的田,可以种一季晚稻,一季晚稻比二季稻产量又会高些”[4]。与会的建国一社主任王乾成面对县委高产卫星的要求,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先进工作者的身份所带来的政治压力。1957年冬季他以黄冈专区劳动模范的身份参加赴朝慰问团,并得到中央和省委领导发展生产的“嘱托”。回国后,王乾成被组织下放到建国社主持工作。在中共的组织培养制度中,先进模范和专员下放对干部的政治晋升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上级的重视,有重点培养之意,是政治晋升的前瞻步骤。县委领导对小麦高产卫星的褒奖,使王乾成彻底明白了上级的意志。县委掇秧并丘的点拨,解放了他的思想,让其体悟出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精神实质。
破除保守、解放思想的王乾成召开主任会议,商议放高产卫星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一听说要试验亩产一万斤、两万斤、三万斤,很多人惊呆了”,“干部办高产,第一次社主任会上,没有结果”。王乾成知道要想获得通过,就必须扩大与会人数,把潜在支持者纳入到会场中来,寻求更多人的支持,尤其是领导层和年轻人。不久,他召开管委扩大会议。到会的有三十七人。会上,王乾成详细分析形势,比较建国社的优势,“我们的社大,有十七八个垸子,一千多户,四千七百多人,男女劳力有两千多,土质好,油沙土,水源比较好”[5]。然而社委荣德宗坚持认为应该主要搞好大面积丰产,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面对众多异议,王乾成必须通过辩论,来消除不同意见。辩论,作为统一意见的主要方式,在“大跃进”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辩论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主导辩论的一方占据政治话语的制高点,控制着辩论的方向和结果。辩论的逻辑倾向于务虚和不辩自明的意义。因为辩论的重心在于:是否想要一种美好的目标。在政治话语里,政治目标具有先天的道德性和不可辩驳的真理性。若有人对政治目标提出质疑,则触犯了政治忌讳,极可能被定性为坏分子。更具影响力的是,头上悬着的右倾帽子对异议者有强大的震慑作用。为了辩驳反对者,他首先指出要不要高产卫星,继而陈述试验卫星的意义,“办高产是给大面积树立旗帜,为了更好的大面积平衡增产,让大面积的土地收更多的粮食”[5]。至于如何实现高产,他陈述小麦卫星的经验及县委领导的指导,“河南7千斤的高产小麦土地还有很大的空隙,水稻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翻五翻就是亩产三万多斤。插秧原来的试验田是1×4寸,1×5寸,一亩可以产5千多斤,掇秧不讲什么几几寸,尽田插满,8亩合在一起,不是就有4万斤了吗?”[4]这种叙说逻辑严重违背水稻种植经验和规律,却具有形式逻辑上的不可置疑性。经过一番“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反对者不得不保持沉默,接受他的意见。王乾成也得到副主任冯福炳、会计罗文存、社委王茂训、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等人的支持。一番表决之后,最终获得二十七人赞成,尤其青年积极分子最为积极响应。
试验高产的决定已经通过,接下来管委会选择试验田的位置。他们认为高产田必须:“(一)土质好,是油沙土;(二)劳力足,办高产也不影响大面积增产;(三)水源充足,干一百天也没有关系;(四)骨干强,青年人多。”[5]最终,委员会认为河北垸的一块1.016亩的田地符合条件。之前,这块田就有过三千斤的纪录。同时,他们决定由王乾成、冯福炳、王茂训、罗学江等人具体专职负责该试验田的生产和培育。
当试验高产田的决定传到河北垸的时候,社员们议论纷纷。他们内心深处更多的是顾虑和担心。他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不满,“亩产4万斤,把二、三十亩谷打在稻场里差不多”,“好事没见你们搞来,吃亏的事总是你们搞来”[4]。社员的非议打击了干部们的信心和热度,很多人中途退场。
面对这样的僵局,王乾成迅速召开青年人大会,让他们分头下去串联发动社员,要在社员间掀起一场高产卫星的辩论。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异议声音,重新动员干部,鼓励社员参与进来。首先,了解社员的顾虑。社员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劳力浪费、工分、肥料、减产赔偿等问题上。针对这些问题,社委宣布“社里论工分,达不到不赔产,增产得奖,如果劳动力不足,青年突击队四十人可以帮助”[5]。同时,社里指出干部试验田“一般都开小灶,比大面积的田块多用工多施肥”,并承诺只要“缺粮变余粮,红榜考头名,电灯、电话还先架河北垸”[4]。在社队干部控制下,辩论氛围对异议者产生强大的政治压力。无论是指陈右倾保守,还是批评观潮派,乃至支持者激情澎湃的言论,都迫使他们选择沉默与应声。对社员来说,他们尽管对高产卫星的真假心知肚明,但试验卫星可增加工分,会额外得到肥料,减产不会赔偿,增产反而奖励,至于高产带来高征购,及后来更严重的后果,他们当时无法预测。
在排除一切阻力后,建国一社在王乾成的领导下,以青年突击队为主力军,开始种植高产试验田的操作。整个试验田的劳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播种到第二次移栽前,也就是“在原来八亩田里培育秧苗,打下丰产的基础”,“基本措施是抓住育壮秧、深、肥、密”。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移栽到收割,集中八亩田培育的结果,让它在一亩田里充分地表现出来”[4]。为了深翻到1尺4寸、1尺5寸,他们不得不采用普遍套犁和锄头深翻。一天挖断了很多锄头,最后甚至徒手去挖、用人拉犁。每亩田在底层施了两千斤绿肥,中层是两千担塘泥,最表层散发了200担陈土。密植做到1寸×4寸。待到秧苗壮硕时,每亩又追肥50担。两个月后,开始将八亩秧苗移栽到试验田里。首先施足底肥。在这试验田里,共施底肥“陈土300担,绿肥3000斤,塘泥100担,水粪30担,石膏6斤,石灰30斤”[6]。为了尽快移栽,他们把梯子、门板当担架,挑箩、提水桶在八亩田里掇秧。移栽做到“挨挨寸”,每一寸土地都挤得满满的,腾出的田地,接着就插上一季晚稻。为了给密不透风的稻田灌水,他们“用细长的竹竿,慢慢地在田中掏小孔,在泥上开水渠,好让水流进去,使秧得到必要的水分”。面对伏旱天气,他们“用细长的竹竿把秧一兜兜的分过去又分过来,一天三次”,同时,“用喷雾器安上喷枪喷射井里的凉水,让禾叶吸收日光、空气和水分”[5]。
8月3日麻城县委在白果区召开早稻生产现场报喜表彰会。县委领导亲自表扬“梁家畈乡燎原四社亩产10237斤,当场颁发奖旗一面,奖金300元”。县委对卫星典型的大力褒扬,使王乾成下定放出更大卫星的决心,保住先进模范的身份,实现名利双收。为了进一步督促下级,县委书记处书记当场点名质问王乾成:“人家早稻亩产万斤,你还是区委下放的干部,能不能拿点硬东西?”县委书记处书记与王乾成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是王乾成的入党介绍人。书记的当场点名,显示出领导对王的重视与期许,也意味着将王逼到马下。王乾成只能夸下海口:“我们有硬东西,过几天再向领导汇报。”[7]
回社后,他更加细心管理试验田。历经狂风肆虐、暴雨吹打,他领导社队干部、社员,还是保住了试验田的稻谷。黄澄澄的稻谷进入收获季节,王乾成迫不及待地向县委领导汇报。县委书记处书记迅速来到建国一社考察,他喜形于色,让人滚一个鸡蛋到上面。面对密密匝匝的水稻,书记知道一旦卫星放出,会有大量人前来参观、学习。这需要王乾成介绍经验。为了不至于被问倒、质疑,他不断地演练现场会议上可能被问及的问题,如试验田的管理、种植诸问题,还特批抽调鼓风机给建国一社,以备检查、质询时用。
建国社即将放出早稻卫星的消息,逐级上报,地委、省委得到消息后,迅速成立由省委副秘书长史林峰领衔的验收组织,于9日前来验收。参加验收团的还有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黄冈地委验收团姜西影、麻城县委及白果区区委书记汪凤元。此外,为广泛报道与宣扬这颗卫星,省委下派武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负责现场摄影,新华社记者也前来现场报道。验收团首先丈量田亩,之后开始收割、打场,连夜过秤入库。其实,为了保证放出更大的卫星,验收前建国一社就召开了社员大会。社队干部讲“要千方百计把卫星放响”。为了说服社员,还“介绍外地已经放过的卫星,说我们的卫星一定要放过3万斤”。社员们尽管对试验田的产量心知肚明,但他们知道“领导需要的是高产典型,是想要我们放卫星”,“你不放卫星,人家就说你保守。那个时候谁敢背个保守名?社队干部不敢,社员更不敢”[6]。这一右倾保守的帽子,对社员构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为了达到卫星的要求,在干部的组织下,社员们想尽办法,趁着晚上从中作假。他们或者把其他田的稻谷挑来,或者将已经验收的稻谷,故意留些稻谷在竹筐里,或者干脆直接称了一遍又一遍。这样一夜的劳作,验收团宣布结果,在1.016亩试验田里“收获”干谷36956斤,要求验收人员签字。此时,有专家质疑:“那么密的秧苗怎么深耕?怎么施肥?怎么通风?时间长了不都烂了?”王乾成按照县委领导之前的对策,“下肥除深耕层层施肥外,追肥时将化肥兑成水,在稻田周围作高埂子往田里灌;通风先是用竹竿捅,后来用鼓风机往田里送风的”[8]。验收的领导当场严厉批评了那位年轻专家,之后对他进行了政治处分。如此一来,仍有异议的人心里已明一切。当晚,参加验收的省委副秘书长向省委书记王任重做出汇报。当三万六的卫星传遍社里时,原先异议的社员在社队干部的安排下,敲锣打鼓,欢庆早稻卫星。
三、“皇帝的新衣”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通栏红字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从此,麻城再一次名满天下,建国一社主任王乾成也一举成名。从县级、地级、省级到中央四级党报纷纷详细报道高产卫星生产、种植、管理、收获的过程。几位曾经参加过“三万六”卫星的社员,后来承认“除了三万六是假的,其余的倒是真的”[6]。
扬名天下的建国社,很快迎来了川流不息的人前来参观学习,“到十二日为止,到建国一社参观江西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高产田的人,已经超过十万”[9]。其中有朝鲜、苏联、东德、越南政府官员、专家慕名而来。人来人往的参观者是王乾成始料未及的。他内心深处既兴奋,又忐忑不安。于是,召开社员大会,会上“统一扯谎口径,谁敢乱说打谁的右派,吃不了兜着走”[7]。
8月15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专程前来参观、祝贺。他“亲手把一面‘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大锦旗,奖给了高产制造者”,并鼓励“一亩田今年能产三万斤,明年能不能高产五万斤,大面积单产一万斤呢?我想是有可能的”[10]。根据James Kung教授和Shuo Chen博士的研究,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主政的省份在粮食超额征收率、放农业卫星数量、公社大食堂的普及度、集体化进度四个指标中均超过其他由正式委员和非委员主政的省份,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当时中央委员的必要条件是苏区革命和长征的经历,而没有这些经历的官员,只有在大跃进中敢为人先,以此积累晋升的资本。作为候补委员的王任重,没有长征经历,若想获得高升,就必须紧跟毛的大跃进政策,放出更大卫星。在省委书记的鼓舞下,湖北很快陆续放出更大、更多的卫星。8月下旬麻城明山乡创造亩产四万三千斤的中稻纪录。28日建新六社后浪推前浪,放出五万多斤的卫星。9月17日易家大垸高潮三社放出亩产中稻十万斤的卫星。
三万六卫星的高高升起,给麻城县委和建国社社队干部带来了极大荣誉。王乾成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区长,后为白果公社党委书记,并以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身份出席在京召开的大会,受到中央官员的接见。县委副书记升任县委第一书记,县委第一书记升任地委副书记,地委第一书记升任副省长、省委副书记。
尽管麻城声名鹊起,但高产卫星终究是弄虚做假造出来的,县委为防止“纸里包不住火”,在大小会议上反复讲道:“在亩产‘三万六’问题上要统一口径不能乱讲,这不仅关系到麻城红旗,还关系到地委、省委威信。”[8]尽管如此,白果区区委书记汪凤元还是听说了卫星的真实情况。他试图出面查证,但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虽然不知道炮制亩产‘三万六’的真正后台是谁,但是已经预感到这其中来头不小,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吃不了兜着走”。随着卫星升起而来的是高征购。到10月份,原来风光无限的建国社此时出现了粮食危机,社队干部不得不到区里借粮。汪凤元怒从中来,对建国社的弄虚造假行为狠狠大批一顿。然而汪凤元的仗义直言“刺痛了麻城县委搞假红旗真浮夸的要害,实际上也刺痛了黄冈地委和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我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8]。1959年9月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运动展开,汪凤元作为麻城县的第一个右倾分子被揪出来批斗,最终被开除党籍,行政降级。
于此同时,三万六的谎言也不攻自破。“高产量”带来的高征购,最终使建国社的口粮出现严重短缺。王乾成作为三万六高产卫星的始作俑者,受到严厉批评,不得不自我检讨,受到降职处分。
四、结 语
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背景下,“放卫星”成为各级政府的政治需求,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政治晋升想法的省市领导。他们必须在大跃进的政治场域下,以“放卫星”作为最佳的政绩表现。为此,他们有重点、有选择地选中那些具有政治特殊性的下级。麻城作为革命老区,因为在上层有深厚的政治关系网,注定成为被领导格外重视的典型。麻城如若取得政治先机,就可以赢得出身麻城的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褒奖,自然就能在政治晋升中拔得头筹。因此,麻城被选定为制造和释放卫星的典型。
层层重压下的麻城领导也要将这一任务下派到公社干部身上。王乾成既与县委领导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又是先进代表,担负起这一重担具有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就这样,“放卫星”的政治压力从省级层层传递到基层干部身上。由此,各级形成了具有共同政治目标的攻守联盟。这个荣辱与共的政治同盟利用当时的政治惩罚机制,有效压制了任何异议,成功制造出亩产天下第一的卫星。然而卫星很快坠落,人们承担起高浮夸带来的严重后果。
[1] 缪镜洁.我在麻城“县委高产办公室”工作期间的见闻[J].麻城文史,1992(4):135-139.
[2] 麻城县关于改进领导方法的决定(1958年)[Z].麻城市档案馆,卷宗号:1-1-299.
[3] 关于领导方法的十条(1958年)[Z].麻城市档案馆,卷宗号:1-1-299.
[4] 乘东风破三万斤关——记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创造高产的经过(1958年)[Z].麻城市档案馆,卷宗号:134-1-3.
[5] 高举红旗争取更大面积的平衡增产——建国一社创早稻亩产36956斤的经过[N].麻城报,1958-08-15.
[6] 郑重建.天下第一田与亩产三万六[J].湖北文史资料,1998(3):35-38.
[7] 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J].炎黄春秋,1995(3):31-34.
[8] 汪凤元.一名基层干部求实的代价[J].炎黄春秋,2009(4):24-29.
[9] 建国一社创惊人奇迹各地已有十万人去参观[N].麻城报,1958-08-13.
[10] 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统治到建国一社祝贺[N].麻城报,1958-08-15.
责任编辑:罗 操
Political Promotion and Performance: “Satellite” Story from Macheng
SONG Qi-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In 1958 the great leap forward vigorously carries on. The “satellite” has become a sign of the political performance of the time. Thos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leaders with a strong desire to promote actively respond to this political task by forcing the political pressure to the lower levels of deportation through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al channels. Macheng County, as the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undertook the important task of “satellite”. Jianguo is an advanced unit in Macheng County. With county leadership expectations, Wang Qiancheng, president of Jianguo, finally created the world’s first high-yield field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dropping seedlings and mound.
satellite; political demand; political performance
2016-05-03
宋其洪(1985—),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史。
D651
A
1671-9824(2016)06-00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