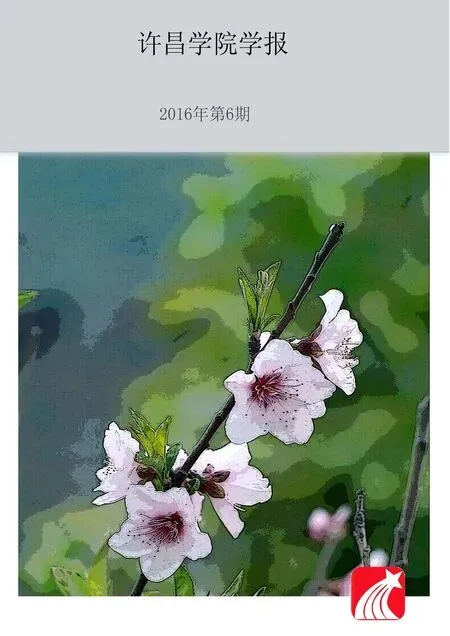论自然力与自然生产力
崔 永 和
(郑州工商学院 督导组, 河南 郑州 451400)
论自然力与自然生产力
崔 永 和
(郑州工商学院 督导组, 河南 郑州 451400)
自然力即非人为力,它在没有人的参与下可自行发生作用。在社会历史领域,按照是否有利于人的价值标准来评判,自然力包括积极自然力与消极自然力。经由人的自觉能动的参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或削弱消极自然力的作用,并利用积极自然力发展生产,创造社会财富。自然生产力是在人的作用下由自然力衍生的劳动生产力。当今生态环境的全面退变,销蚀了大量的自然生产力,降低了人的生活质量,严重威胁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标志着现代工业化过程遇到了严峻挑战。反思和矫正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诸多失误,有效发展自然生产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
自然力;自然生产力;生态文明建设
一、自然力及其两面性
自然力是源于自然物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力量和效能,诸如天然的风力、水力、火力、太阳能、气候变化、地质变迁、物种演化等等,这些自然力依据一定条件进入人类社会领域并发生作用,在人的参与下有可能转化为自然生产力。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尽管人们在认识、转化、利用自然力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有利于自身的文明成果,有效利用包括空气、水源、气候、土地、阳光、自然能源等在内的自然资源,但是,人类却从来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征服和驾驭自然力,甚至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因为受狭隘功利主义的驱使而招致难以预料的负面后果。
当今时代条件下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全球背景,是提出和诠释自然生产力的现实根据。在现实生活层面,自然生产力几乎成了难以绕开的重大理论课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主要是指与人的生活相关的自然要素,它是地球上一切生命体所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环境是指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自然环境和社会坏境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进化起着重要的影响、制约甚至决定作用,同时,人类活动又促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世代延续的人类在适应和改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自身。在这里,“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92。
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经由人的实际活动这一中介彼此联系、相互过渡、相互转化、相互生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生产力的生成与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素质和能力)的生成,在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两种结果,二者具有互为条件、相互交融的共生性。现代工业的历史,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生成和外化的过程,又是自然力向自然生产力的生成和转化的过程。在现实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向自然界延伸,引起自然界的种种变化;与此同时,自然选择也不断把自然的力量、自然的影响和自然的存在方式转化为社会存在形式。在这里,如果人类能够同时兼顾“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就将彼此和谐、彼此适应地持续演进;反之,如果人类在纵欲无度的追逐狭隘功利的价值观驱使下,一味贪图眼前的物质利益,完全弃“物的尺度”于不顾,那么,自然界就将转化成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障碍或异己力量,迟早要对人类进行“报复”。
生态环境的好坏,标志着自然力转化为自然生产力的程度和性质,它既是现实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又是人的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于自然生产力的生成和人的环境需要的满足,马克思曾经做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219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差异,人对自然的依赖和作用程度也就不同。早期的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界直接提供生活资料;在其后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它标志着人类文明有了一定的进化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因此人不能须臾离开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因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3]105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标志着人的本质力量及其生命的现实存在不断进化,从而把不同文明程度的人类历史划分为几个彼此区别的历史分期: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不论人类处于哪个文明阶段,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不能脱离自然界企图在自然之外生存,不能脱离自然条件去从事任何社会生活与实际活动;没有自然界,人类就根本不能生产,不能生活,不能创造自己、展示自己、实现自己,不能存活和持续发展,更谈不上享受什么幸福生活和审美愉悦了。自然力和自然资源从来就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或重要先决条件,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合作、相互生成,是人类生活与人类历史过程的基本内容。当人类自命不凡而把自然物踩在脚下肆意蹂躏的时候,就意味着人类丢掉了宝贵的自然力和自然资源,自己的活动结果不仅不能有利于,反而有害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切不尊重自然、危害自然的行为,都最终难逃自然法则的制裁。总之,自然界和一定的环境质量是人类生存与活动的基础,是判定人的价值选择和人的其他活动之是否合理、是否真正具有价值意义的重要尺度。
人的需要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结构和复合过程,它主要包括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需要和环境需要。其中,环境需要往往被一些人错误地忽略了,其实,人的环境需要的满足,要求具备诸多的自然条件,包括清新的空气、生态的土壤、清洁的水源、绿色环保的食品、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等等,所有这些条件的获得,都是需要通过人的自觉自为的、有目的的活动与自然物发生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人们借助于自然力创设这些条件的活动过程,就是自然生产力的生成过程,也就是环境生产过程。无论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自身的生产,还是环境的生产,都需要运用与之相应的现实生产力。所谓生产力,就是现实的人所拥有、支配,并在其现实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能力,它是现实人的主体素质结构的有机内容,是生成和实现人生价值意义的手段、条件和标志,是主体本质力量的生成与确证。人一旦拥有了一定的生产力,就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他实现了从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转化,标志着他的能力同盲目的动物本能具有了本质区别。
二、从自然力到自然生产力的转化
当自然力被人所认识、掌握、驾驭,并被运用于现实的劳动生产过程时,它就转化成为具体的、现实的生产力,即自然生产力。比如,当人们利用一定的科学技术把诸如风力、水力、太阳能、原子能等自然力转化为电能的时候,当被人驯养的牛马被用于劳动生产过程的时候,当大片的草原被用来做牧场的时候,当鱼产丰富的水被人用来做渔场的时候,当河水被用来灌溉、江河湖海被用来航行的时候……这些自然力就具有了现实生产力的意义。这种被人的活动转化来用于生产劳动过程的自然力,特别是在被用来创造优越的自然条件以满足人的环境需要的时候,这种自然力就是特殊的生产力形式——自然生产力。
当然,自然生产力的生成不是自发的、盲目的过程,而是需要经由人的自觉的活动中介,需要人发挥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创造出由自然力向自然生产力转化的现实中间环节,比如,当今时代的风力发电,就需要把风力转化为电能的机械设备。正如马克思所言:“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4]424
相对于自然生态大系统,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环境是一个子系统,自然生产力是该子系统的内生机制,它是人力和外在自然力的交融统一。这种复合力量发挥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如果有利于自然生态的有序生成,即是正向的自然生产力;反之,如果有损于自然生态的有序生成,则是负向的自然生产力,也可称之为反生产力。
由于自然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传统生产力概念暴露出诸多弊端,需要重新加以补充和矫正。长期以来,生产力被界定为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中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这种界定,虽然把生产力同人从自然压迫下争取解放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却用片面的物质生活需要掩盖了人的其他方面的需要,用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掩盖了人的其他方面的能力,因而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合理性;如果把物质生活需要的重要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它就会走向真理的对立面,转化为谬误。人类有史以来的解放活动,大致存在过以下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人从自然压迫下争取解放的阶段。这时期,基于人的能力素质的相对低下,生产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5]104,人在享受大自然的恩泽的同时,也几乎处处都在受自然界的摆布和奴役。第二个阶段,人从神的奴役下争取解放的阶段。自然界奴役人的结果,促使人从对自然的崇拜转至对天国的崇拜,在被上帝或神灵禁锢的人们看来,上帝是俗人的主宰,神性是人性的主宰,灵魂是肉体的主宰,来世是现世的主宰。这样对理想世界的悬设,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人以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人的现世苦难因此而有可能以虚幻的形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它终究不过是非现实的梦幻。肇始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从神性奴役下解放人性的先河,一时间,民主、科学、个性、人格、文学、艺术得到空前的张扬。第三个阶段,人从物的奴役下争取解放的阶段。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人们对自然界展开了日益全面的改造、征服、掠夺、利用,大量的生产力从地下被呼唤出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77然而,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人的幸福指数并未能够得到同步提升,反而导致了社会关系和价值关系的普遍扭曲,导致了人的普遍异化,即科学技术从充当人类改造自然的助手转化为被人用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工具,人对于财富的占有和享受转化为财富以及货币对人的奴役,人占有物转化为物控制人,人沦为如同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曾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的注意力仅限于追求物质享受,那么,对这个社会来说,就意味着是一个走向没落腐朽的‘病,态社会’、异化社会;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则意味着变成了畸形发展的、丧失了人性的人。”[6]346第四个阶段,人从生态环境的困扰中争取解放的阶段。如果人对于物的奴役能够进行冷静的反思,逐步从物的奴隶变成掌握物、利用物的主人,如果追逐利润的资本增殖法则能够被人理智地驾驭,并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那么,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有望得到缓解,人类就有可能摆脱生态环境灾难,在人与自然彼此和谐相处、互依共生的互动关系中,双方就有望得以互补和持续演进,这是生态文明的高级历史形态。由此观之,生产力并不限于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而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它更包括人们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帮助自然,用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精神生活资料、环境生活资料和审美生活资料的能力。即是说,人类不是在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生活,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生活。因此,广义的、全面的生产力概念应当同时包括人们认识和改变自然、认识和改变社会、认识和改变自身的能力,因此,它至少包含人的学习能力、运用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的能力、使用科学技术和其他生产工具的能力、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改善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能力,以及同自然协作和同他人协作的能力。
马克思曾经这样分析: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4]208-209。人在劳动过程中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人自身的自然,“劳动首先是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4]201-202。人在改变自然并同时改变自身的过程中,由于受不同条件的制约,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当人尊重自然,同自然和谐相处时,就会使自然万物协调发展,人自身的身体更强健,头脑更灵活,生活更幸福;反之,当人违背自然法则,同自然严重对峙时,就会导致自然退变,环境恶化,人自身的身体日益弱化,智力日益扭曲,生活质量日益下降。
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1]81-82。这时被人类认识和驾驭的有限的自然力,作为人们从异己的自然力那里获得解放的手段和能力,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期,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量事实表明,被用来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资源的所谓生产力,其实已经成了“反生产力”或“负生产力”,成了现代人异化的现实根源。
生产力虽然在本质上是人们拥有和支配的能力,但是,人的能力的现实生成却同时具有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共同基础,即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仅需要与他人彼此协作,而且需要立足于自然基础之上,得到自然力的帮助,或者说,人要善于同自然合作。马克思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7]56-57事实上,生产力作为人的能力,它的发展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合过程,“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53。工业文明以来,人们生活在技术化和物质化的世界里,感官的物欲满足遮蔽了人的本真的存在,片面的物质欲求掩盖了人生的全部意义,由此不免令人逐渐淡忘了自然力的意义,淡漠了广博大度的自然生态意识和生命意识。
自然界从来就是人类劳动的基础,离开自然界人们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8]298,当自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和确认,并进而转化为被人所认识和拥有的生产力的时候,这种生产力就是自然生产力。
自然生产力是用来生产满足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命体的环境需要对象的“生产能力”,它是人类的生产能力与自然的“生产能力”的耦合或合力。自然生产力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无私利性的“公共生产”,因为生成环境、改变环境的结果不能用经济学的精确眼光去计量,不能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也不能对该结果实施专利性的私人占有。诸如清新的空气、水源,为该环境中的所有生命体所共享;水质严重污染、雾霾笼罩的环境中,一切生命体都必将备受折磨。外在于人的自然力以及相关的自然资源,一旦得到人们的正确认知、适度开发与合理利用,从而参与人所从事的生产劳动过程,它们就成为积极的自然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不仅可以用来直接生产人和自然物的环境需要的对象,同时还可以为其他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
自然生产力一方面是源于自然环境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是生产环境需要对象的生产力。具体说来,它具有以下特征:其一,自然生产力是人类对于自然力的自觉发现、借用和转化,使之同人本身的自然力交融一体,并用于现实的生产劳动过程;其二,自然生产力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彼此和谐基础上的产物,它既是人类借助于自然力所获得的生产能力,又受人的能动驾驭和影响;其三,自然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它既是用来生产环境需要对象的生产力,又是参与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生产力;其四,自然生产力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生产力具有彼此不同的发展水平、发展程度和价值意义。在人类的早期,自然生产力大多是以自在的形式盲目地、有限地发挥作用;随着人类的个体独立性的发展,自然生产力遭到日益严重的人为破坏,由此导致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当人类对生态危机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时候,人类历史将趋向于生态文明的历史阶段,这时候,自然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凸显,从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生产力。
三、保护和发展自然生产力的根本出路
有害自然力的泛滥和自然生产力的空前丢失,缘于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日甚一日的污染与破坏,因此,发展自然生产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从根本上修复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说来,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化敬畏自然的意识
现代人类要从技术工具论和自然工具论的世界潮流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强化尊崇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自觉领悟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自然力的珍贵性和环境需要对象的匮乏性,懂得同自然友好相处、彼此合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深刻揭示了“异化劳动”条件下新陈代谢链条的断裂,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7]579-580资本主义的发展酿成了对于自然力和环境资源的灾难性后果,并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蔓延、扩散到世界各地,这就急需一种富有批判力的环境意识对人类普施生态启蒙,引导人们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反思和矫正人类的反生态的实践行为和生存方式。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得到执意坚守,它把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认为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任意掠夺和控制自然,随心所欲地改造和摆布自然。“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基者就高扬一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坚信‘知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自然在他眼里是一个‘被拷问’、‘被命令’的对象,只有‘服从’的权利。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正是这种对自然的不敬、对自然的否定态度,导致了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毁灭。斯坦芬也认为,人类今日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这种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的直接结果,是它的‘可怕的社会代价之一’”[9]。从后现代的第二次启蒙角度看问题,“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因此应该“予以摒弃”。人的这种“自命不凡”不仅是一种“错觉”,而且还是人类自我毁灭的祸根。第二次启蒙的理论取向的特点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崇文化互补意识;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差异之美;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9]。沿着这一文化走向,人类就有可能真正地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珍惜自然资源,明智而适度地寻求自然力的帮助,创造人力与自然力彼此合作的环境生产力,在实践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上均有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这原本是人类早就持有和向往的美好理想境界。
(二) 保护生态环境
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实行广泛的国际协作,把发展地区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把生态生产与生态生活有机统一起来;切实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那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施以有效的行政监督、技术检测、舆论谴责直至法律惩治;在城乡普遍建立生态环保社区,尊重和鼓励社会力量开展环境保护和环境自救;对于空气、水源和食品安全开展经常性的卫生指标检测,及时发现和处理威胁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环境污染事故;减少污染物排放,节约环境资源,继承、发展和推广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自然资源、传统生产工艺和传统民俗文化;逐步完善城乡生态对接工程,充分利用城市废物,把城市生活垃圾转换成农业有机肥料,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发展生态绿色农业,保证健康、安全的食品供应,同时提升环境质量和人的健康水平。
(三) 完善环境立法
工业文明以来,人们遵照资本增殖的经济运行法则,在“投入最小和收益最大”目标的诱惑下,不惜赌上沉重的环境代价而追逐眼前利润,无视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牺牲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对峙和频繁的生态灾难。严酷的现实说明,遏制狭隘功利主义、实现价值观的根本转变迫在眉睫。
早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土地资本化就酿成了“羊吃人”的历史:追求资本增殖,赶走土地上的居民,拆除地面上的原有建筑,成为无法阻挡的资本风暴。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7]880并且他进一步分析:“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7]878由于对自然物的私有权(占有权)的荒谬的泛滥,自然物便具有了某种“归属”,由此也就可以在貌似“合理”“合法”的名义下,对自然物进行“估价”或“定价”。当前,在我国随意破坏环境、污染水源、圈地强拆之风之所以难以有效遏制,就在于:资本法则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强力驱动,致使少数人非人道牟利,大多数人蒙受生态环境灾难;有的环境立法虽然已有明文规定,但执法过程中常有人用金钱打通关节,用关系讨价还价,表面守法,暗地污染;风来守法,风去污染;有的环保部门甚至常年靠吃“污染罚款”谋取私利,环境监督中的“猫腻”反映了环境立法和执法的诸多漏洞,为我们的环境立法执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四) 确立自然生态系统价值观
置身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在做出价值选择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摆正自己的身份定位,即不是以“征服者”的傲慢姿态,而是以谦卑的态度尊重自然,珍惜自然资源,帮助自然以培育环境资源的再生机制,杜绝“竭泽而渔”式的征服、开发和利用自然。在自然生态大系统中,人类只是一个价值因子或价值要素,自然界中的动植物都同样是自然生态大系统中的价值因子或价值要素,现实的人既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又要兼顾自然生态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价值,以及兼顾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价值,即是说,有理智、有超越精神的人类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要力争做到使自利性的内在价值、利他性的工具价值、互利性的系统价值这三重价值并行不悖、共融共生,避免用实现任何一方的片面价值而损害自然系统价值,更不能为实现眼前的暂时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譬如一条江河,如果由于人为原因而招致航运阻塞,生态破坏,气候异常,地质灾害频发,那么,这些有害自然力的接连不断地发生,就标志着人在改造江河的活动中违背了自然规律,犯下了令自然界难以承受的错误。美国学者G.哈丁早在1968年就提出了著名的“集群性悖论”(又称“公用地悲剧”),深刻反思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无限度地利用和对于生态环境破坏的逻辑悖论。他指出,为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但却不能围圈的开放性资源,如公共牧场的土地、公共渔场的海域等,由于每个放牧者或渔猎者都想最大限度地获利,天长日久,便造成牧场草地的退化或水产资源的枯竭。他痛心地指出:“这就是悲剧之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奔向的目的地,每个人都在一个信奉公用地自由享用的社会中追逐各自的最大利益,公用地的自由享用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10]176马克思曾经以独到犀利的视角剖析大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552这就清楚地揭示出,随着工业化而实现的粗放城市化过程,割断了集中居住在城里的人同土地的联系,使他们原本来源于土地的以衣食形式被消费掉的东西,在成了粪便和生活垃圾以后不能再返还到土地中用来肥田,以致使土地肥力递减,环境遭到生活垃圾的污染。
当今时代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好坏是评价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不是仅仅看它在一定时间周期内取得了多少经济效益,完成了多少具体经济指标,更具体一点说,不是看它圈了多少地,拆了多少房,盖了多少楼,赚到了多少钱,而是看它的空气是否清新,土地是否有机肥沃,水源是否卫生,生活消费品是否绿色、环保、安全,生态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人们生活得是否舒适幸福。如果一个地区为了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强有力的法制手段关闭了一批污染严重的企业,即使经济暂时呈现下滑趋势,少赚到一些钱,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为经济的可持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积淀了后劲,其实质便是经济好转的景象。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从生态系统价值观出发曾经做出这样的概括:“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1] 213这个准则对于当今时代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过程,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从自然生产力角度出发,一切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不论它暂时创造了多么巨大的经济价值,都是破坏生产力的错误行为;而一切尊崇自然、保护环境的行为,不论它在当下获得多么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效益,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行为。
对于当前的市场经济,既不能“跳越”,也不能盲目迷信。按照历史主义观点,市场经济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它同时也有“作恶”的一面,有论者分析指出:“就市场而言,第一,它一定导致投机。因为市场追逐利润,哪个利润更大,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它就会那样去做。这一定会导致投机,这一点通过市场本身没有办法消除。市场只能通过投机制造的后果来惩罚投机,而不能在投机的根本的源头上去解决。第二,市场对非利润的生产完全没有兴趣。因为市场是以利润为它的杠杆,所以,像法国这些国家,每年要拿出财政预算的7%完全去支持芭蕾舞,去支持歌剧,支持非盈利的文化事业。现在流行音乐铺天盖地的时候,歌剧还有谁去看。听任市场去解救歌剧,那歌剧早就解体了。第三,市场一定导致垄断。市场本身有它不可消解的缺陷。假如对这些缺陷缺乏深刻了解,引发像金融危机这样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若干年就会来一次。”[12]如果自然力任凭功利主义摆布,必将引发诸如环境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等等,后患无穷。大量事实已经并继续证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冲突,是引发自然退化、导致有害自然力和生态环境危机的制度性根源。逐步规范市场经济,确立自然生态系统价值观,是发展自然生产力的社会保障。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曹玉文.西方人看马克思主义[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7]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王治河.中国的后现代化与第二次启蒙[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2):51-60.
[10]转引自黄鼎成.人与自然关系导论[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11]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2] 黄万盛.人文关怀的历史反思[J].现代大学教育,2009(1):1-8.
责任编辑:师连枝
On Natural Force and Natural Productivity
CUI Yong-he
(Instructor Group, Zheng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Zhengzhou 451400, China)
Natural force is non-human force, which can play its own role without human participa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according to whether it is conducive to human beings, natural forces include positive natural forces and negative natural forces. Through the conscious participation, peopl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can reduce or weaken the role of negative natural forces and use positive natural forces to develop production and create social wealth. Natural productivity is the labor productivity derived from natural forces under the action of human beings. The comprehensive degene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eroded the natural productive forces, reduced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and threatened people’s health and life safety seriousl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rocess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has met a severe challenge. I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important cont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reflect and correct human errors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o effectively develop natural productive forces.
natural force; natural productiv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2016-08-12
崔永和(1942—),男,河南清丰人,硕士,河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工商学院督导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唯物史观与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
B031
A
1671-9824(2016)06-00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