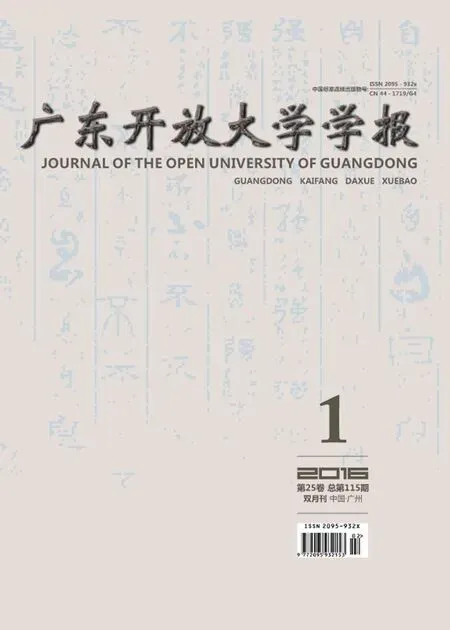论“元嘉体”诗歌的用韵特征
白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论“元嘉体”诗歌的用韵特征
白崇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东广州,510665)
【摘要】“元嘉体”诗歌以押平声韵为主,通韵规范基本定型,与唐诗声律运用大体吻合的现象非常明显。但在个别韵部的运用上,“元嘉体”用韵存在上古韵的遗留,通韵韵部的组合使用相对于唐律更为自由,整体上体现出新旧交融的状态。“元嘉体”的用韵是由古诗音韵向律诗过渡的中间环节,对诗歌韵律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元嘉体;用韵;古韵;唐律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三张二陆诸公之诗),元嘉体(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永明体(齐年号。齐诸公之诗),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南北朝体(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1]689。严羽从时间角度审视诗歌的发展,注意到特殊历史阶段的诗歌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这很有价值。但严羽并没有对“元嘉体”的概念进行说明。诚然,严羽认为“元嘉体”包括了颜延之、鲍照、谢灵运等作家的诗歌,在时间范围上,可以视为是刘宋时期的诗歌。而且严羽将“建安体”、“黄初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并列起来考察,说明他是按照诗歌发展的主线来立论的。从六朝诗歌体制发展来看,从建安到齐梁,四言诗已经走入末路,而七言诗则方兴未艾,因此诗歌发展的主要体式是五言诗。所以,本文认为“元嘉体”主要是针对五言诗而言。关于“元嘉体”,清代沈德潜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2]532“性情渐隐,声色大开”不难理解,魏晋诗歌内容充实,重视作家情感的抒发,但南朝诗歌整体上更为关注外在的东西,例如辞藻以及形式艺术,诗歌的主体抒情性淡化。魏晋诗歌形式较为古朴,但南朝诗歌的形式则在骈俪、声韵上有极大的进步。所以“诗运转关”的内涵显然不仅仅包含中古诗歌在内容与感情上的变迁,也同样是针对元嘉诗歌在诗歌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作用而言,视其为从古诗向近体诗演进的关键。实际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更多是形式的演进,而情感与题材则较为稳定。对于元嘉诗歌体制诸要素的研究,以往更受关注的是对仗艺术与声律平仄运用,而用韵的考察则略显薄弱。用韵体现了诗歌气势的收束,对诗歌意蕴表达影响极大,因此也是诗歌演进的重要因素。关于元嘉时期诗文中用韵的考察,王力先生《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最为详尽①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页。,单个作家用韵情况又有欧阳戎元《鲍照用韵考》一文②欧阳戎元:《鲍照用韵考》,《语言研究》,2002年特刊。,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王力先生的考察是诗文并重,欧阳戎元主要以鲍照为研究对象。因此,对元嘉五言诗整体用韵情况还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索。
一、“元嘉体”韵脚平仄与本韵考察
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的轻重节奏关系较为接近,音乐理论家王光祈先生说:“平声字中系包含一切‘重读’之字,其性质为向下沉坠的,富有收束力的,平稳如泰山。反之,仄声字中系包括一切‘轻读’之字,其性质为浮于空中的,未有收束力的,轻飘如有游丝。”[3]9又说:“中国之平声,则兼有‘重’‘长’两项特色,实为全诗之重心。故中国律诗绝诗,亦多以平声之字为结尾。”[3]3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体制成熟后,押平声韵的主要原因。古体诗的押韵并不固定,押仄声韵较为常见。在古体诗向律诗过渡中,“永明体”一贯被视为诗歌律化的先声。刘跃进先生在提及永明诗歌的用韵情况时,认为永明诗歌在用韵上有三个特征:多押宽韵,但也押窄韵;以押平声韵为主;押本韵甚严,押通韵多已接近唐人③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2-139页。。从元嘉诗歌用韵看,永明诗歌用韵的前两个特征也同样适合于元嘉诗歌。刘先生认为颜、谢的诗歌“连一首窄韵诗都没有……元嘉诗歌仄声韵居多”[4]132-133,主要是因为刘先生考察的是四句、八句、十句的五言诗,并没有将所有为《文选》、《玉台新咏》所收录的元嘉五言诗全部考虑在内④研究元嘉诗歌的用韵应考虑诗歌的完整性,目前为止《文选》与《玉台新咏》所收录的诗歌可以确定是完整的。。因此,有必要对元嘉诗歌的用韵,尤其是韵脚平仄、本韵的情况进行进一步梳理。
从整体上看,《文选》、《玉台新咏》共收元嘉五言诗116首,其中押平声韵的诗歌有63首,占全部的54.3%;而仄声韵有37首,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显然,元嘉诗歌主要押仄声韵的说法并不准确。押窄韵的诗在元嘉时期虽然很少,却也存在,通押微韵的如鲍照《苦热行》,主要押文韵的诗歌如颜延之的《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纷分云闻芬文(文)殷(欣)、《还至梁城作》:军群分云文坟君闻(文)勤殷(欣)。永明文学与元嘉文学是紧密联系的两个阶段,不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文学现象。
从作家用韵的情况看,押本韵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在《文选》与《玉台新咏》所收录的元嘉五言诗中,有21首押本韵,分别是:鲍照《代白头吟》通押蒸韵、《苦热行》通押微韵、《咏史诗》通押至韵、《咏双燕诗》通押支韵;鲍令晖《拟青青河畔草诗》通押东韵、《拟客从远方来诗》通押侵韵、《代葛沙门妻郭小玉作诗二首》(其二)通押寝韵;袁淑《效古诗》通押东韵;刘铄《拟明月何皎皎诗》通押月韵、《拟孟冬寒气至诗》通押鱼韵;孝武帝刘骏《丁都护歌二首》分别通押语、止韵;王僧达《答颜延年诗》通押侵韵;范晔《乐游应诏诗》通押侵韵;谢惠连《代古诗》通押蒸韵(另外,《西陵遇风献康乐》五章中前四章分别押月、侵、脂、尤韵);颜延之《五君咏•阮步兵》通押送韵、《五君咏•刘参军》通押霰韵;谢灵运《晚出西射堂诗》通押侵韵、《登池上楼诗》亦通押侵韵、《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陈琳》通押德韵;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通押东韵。需要指出的是,此处考察所依据的材料是代表中古音系的《唐韵》与《切韵》。这说明元嘉诗歌用韵已经与后来的律诗有了近似之处。
但是在很多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现象:通篇基本押某韵,但又有个别韵脚押其它韵部中的字。如上文所引颜延之《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以及《还至梁城作诗》,又如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晖归微霏依扉违(微)推(灰),又如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阳方强梁霜扬张良殇(阳)望(漾),又如《文选》所收鲍照《拟古诗》三首中的第二首:通宫风功戎弓终(东)锋(钟)。虽然东钟、文欣这些韵部的字在元嘉时期可以通押,但从作者主要用某一韵部字的情况看,他是希望韵部能够一致。对此,如果考虑上古音韵与中古音韵之间的联系,就不难发现,在元嘉诗歌中还保留有上古音韵的残留。如“推”在上古音系中也属于微韵。“殷”、“勤”在上古音系中属于文韵部,在中古时期才转移到欣韵部。而“漾”在上古属于阳韵部,而后来才转入望韵部。“锋”在上古音系中属东部而不属钟部等等,上面的几首诗歌实际也具有押本韵的特征。
从上面的梳理中可以看出,押本韵的诗歌在元嘉体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但也很有价值。非常明显的是,元嘉中后期作家如颜延之、鲍照等作家的作品中押本韵的现象出现频率较高。但早期作家如谢灵运的作品中,则偶尔出现。这说明,在刘宋时期,押本韵呈逐渐上升的态势,这与六朝诗歌声律化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刘宋时代正是诗歌声律化的第一个阶段,如钟嵘曾引南齐王融的话曰:“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5]5可见,刘宋时代已经有不少人探索过诗歌声律:谢灵运也有声律学著作,《高僧传》记:“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谘叡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6]260但可惜的是,这些作家的声律探索文献缺如。元嘉诗人对声律的关注,自然会引导他们注意诗歌平声韵与本韵的应用。
二、“元嘉体”通韵考察
通韵也是律诗中常见的现象,一般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部可以相通,或其中一部分相通。通韵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源远流长,《诗经》之中已经有通韵的存在。进入中古五言七言之后,韵部发生了变化,通韵依然普遍存在,然而五七言古诗通韵较宽,近体诗则受严格的限制。从宽松到严格的过程说明,通韵的规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也与中古诗歌律化的过程一致。王力先生将南北朝时期的韵部重新整理为54部⑤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61页。,本文据此考察元嘉诗人作品中的通韵情况。元嘉诗人用韵通押的很多习惯源自于魏晋诗歌,但随着语言的演进以及对诗歌声律的关注,元嘉诗人不同韵部通押的规范逐渐增强,有些通韵已经类似唐人,如下可见。
薛屑同用——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诗》:越发月歇阙别(薛)蔑(屑)。药铎同用——谢灵运《富春渚诗》:郭薄错壑托(铎)弱(药)诺落蠖(铎),《斋中读书诗》:壑寞雀作(铎)谑(药)阁乐托(铎),鲍照《采桑》:作阁箨幕萼(铎)烁(药)藿托诺薄洛涸(铎)酌(药)。支佳同用——谢灵运《游南亭诗》:驰规歧池移垂斯(支)崖(佳)知(支)。月没同用——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歇(月)没(没)发发月越阙(月)忽(没)伐(月);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诗》月阙发越发(月)没(没)歇(月);刘铄《七夕咏牛女诗》歇月阙发越(月)忽没(没)。仙先同用——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旋延川鲜传缘(仙)年(先)。钟东江同用——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楥诗》:同中风(东)江(江)墉(钟)窗(江)峰(钟)功(东)踪(钟)同(东);鲍照《代陈思王京雒篇》:窗(江)龙(钟)风(东)容(钟)中鸿蓬空(东)缝浓从(钟)。先仙山同用——谢灵运《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山(山)泉(仙)贤阡烟(先)筌传(仙)前(先)湲然(仙)。尤侯同用——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游州流舟浮斿(尤)讴(侯)洲畴丘柔(尤);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钩(侯)仇游丘州浮(尤)侯(侯)流求忧(尤),《上浔阳还都道中作诗》:洲留俦遒(尤)鸥(侯)流浮秋游忧(尤)。东钟同用——颜延之《直东宫答郑尚书道子诗》:工风(东)墉(钟)中宫穷衷(东)松(钟)充桐(东)。齐皆同用——颜延之《和谢监灵运诗》:迷栖闺睽(齐)霾乖(皆)蹊荑稽泥(齐)淮(皆)藜畦(齐)偕(皆)凄圭(齐)怀(皆)。真谆同用——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人神(真)沦驯(谆);鲍照《行药至城东桥》:晨闉津尘人亲身(真)春沦(谆)辛(真)。清庚同用——孝武帝《自君之出矣》:精(清)生(庚)。歌戈同用——王僧达《七夕月下诗》:波(戈)柯罗河(歌)。仙先同用——鲍照《赠故人马子乔诗六首》(二):鲜(仙)坚(先)缘(仙)年(先)。山先同用——鲍照《学刘公干体诗五首》(三):山(山)前年妍(先)。东江同用——鲍照《数名诗》:东宫(东)邦(江)鸿丰风(东)钟重容通(东)。脂微同用——鲍照《梦归乡诗》:逵(脂)畿(微)归机帏辉(微)蕤(脂)徽违飞巍(微)衰谁(脂)。另外王力先生还提到,德韵字偶尔与烛、屋韵同用,这种情况有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诗二首》(一):足(烛)得(德)。
还有一些诗歌表面上具有通韵特征,如谢瞻《经张子房庙诗》与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通押阳唐韵,谢瞻诗韵脚为:章亡殇(阳)光(唐)王昌枪(阳)皇(唐)乡疆(阳)荒(唐)阳尝忘(阳)行(唐)场方良(阳)康(唐);谢灵运诗韵脚为:方(阳)冈(唐)肠凉忘(阳)行(唐)芳伤妨将常扬章(阳)。这些韵脚中光、皇、荒、行、康、冈等上古音中皆阳韵。又如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魏太子》真臻同用:辰津民(真)臻(臻)仁新陈人茵尘珍(真),诗中韵脚臻在上古韵中,属于真韵。再如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徐干》栉质同用:瑟(栉)密毕栗质室一日匹失(质),诗中韵脚瑟上古韵中属于质韵,后中古时期属栉韵。很明显,如果将中古时期韵部的分化演进考虑在内,元嘉体中的一些通韵使用也有通韵的痕迹。这是非常特殊的,也说明通韵之所以后来成为律诗规范,本质是通韵对于诗歌的韵部和谐没有产生影响,甚至有类似押本韵的效果。
元嘉诗人还经常把一些韵用在一起,这应当是当时诗坛的一种独特的用韵习惯,如庚青清耕,谢灵运《初去郡诗》:荣生(庚)名(清)耕(耕)并(清)卿生荆平迎行明英(庚)停(青)情(清),《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刘桢》:平京英(庚)城情(清)生(庚)轻(清)鸣(庚)声并(清)冥(青);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溟(青)成(清)京(庚)营(清)灵(青)明(庚)坰(青)甍(耕)英(庚)情征(清)氓耕(耕),《拜陵庙作诗》:灵(青)茔(清)庭(青)情轻(清)形(青)并(清)迎(庚)城(清)垌青(青)生(庚)声旌(清)萌(耕)贞倾(清);鲍照《代升天行》:城情(清)平荣生(庚)灵经(青)行(庚)庭龄(青)声(清)腥(青),《赠故人马子乔诗六首》(六):鸣(庚)形(青)城(清)扃(青)明(庚)并(清),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明、并、停、情、冥、溟、灵、坰、庭、形、青、经、龄、腥、扃等属中古青部的韵脚,在上古音中则属于耕部,所以这些韵部也可以看做是庚清耕通押,这三个韵部合用在当时诗坛是一种习惯,到了唐代诗歌则演变为庚清通押。当然,后世的很多诗人在写五言古体的时候,也非常喜欢将庚清耕三部通押。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通韵情况在元嘉诗歌中普遍存在,他们的这种实践对于韵部之间通韵规则的形成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另外,从统计的角度而言,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元嘉早期作家,不同韵部共同使用更为频繁,说明这一时期作家受古诗押韵传统影响明显。而到后期鲍照等人那里,韵部间共用的规范程度已经明显提高。南北朝时期,是上古语音过渡到中古语音的关键阶段,韵部的分化导致诗歌韵脚较之唐代更为复杂。而且,古典诗歌从可以歌唱的《诗经》与汉代乐府,过渡到不可歌的五言徒诗,早期歌诗的声韵系统崩溃,但新的徒诗的声韵系统尚未建立,魏晋诗人开始意识到声韵的和谐对诗歌的重要价值,所以陆机提出“既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7]2013,但诗歌新的声韵系统不可能在短期建立,魏晋诗人并没有对诗歌韵律做出进一步探索。到刘宋时代,诗歌形式艺术得到快速发展,韵脚的使用虽然存在明显的古诗痕迹,却开始向规范化靠近。“元嘉体”诗歌中类似于唐人律诗的押通韵情况的出现,说明伴随着语言的演进,刘宋诗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韵部之间需要进行调整,他们对此进行探讨与总结。这些探索,虽然在当时并不是非常成熟,却恰恰给后来的永明诗人甚至是唐代诗人做出了先导。
三、总结
综上所述,元嘉诗人对诗歌用韵进行了探索,努力使韵部和谐。虽然“元嘉体”的用韵较之后来的“永明体”带有更明显的魏晋诗歌的特征,但整体上已经开始向律诗用韵的规范靠近。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形式探索的高峰时期是南朝,元嘉诗人对诗歌对仗以及声律的探索是中古诗歌发展的关键。不可否认,这一阶段的声律探索存在一定问题,如古韵的遗留、押韵较为自由等现象,说明元嘉诗歌依然受魏晋五言诗的影响。但元嘉诗人对押平声韵、押本韵的重视以及通韵基本规范的探索,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诗歌押韵的某些规范,因此,他们的这种探索必然启迪后世“永明体”诗人去做进一步总结。而且,“元嘉体”诗歌基本是十二句以上的长诗,诗歌用韵必然会变得复杂。“永明体”诗人对诗歌短化做出了积极探索,这有可能是长诗押韵复杂所导致。随着诗体长度的缩短,押韵的难度降低,其规范也因而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一工作在永明诗人那里得到了较好的实践。所以,可以这么说:“元嘉体”是古体诗到近体诗演进中的重要环节,它本身带有古体与律体糅合的特征,很多律体的规范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奠定。
【参考文献】
[1]严羽.沧浪诗话[A].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沈德潜.说诗晬语[A].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3]王光祁.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
[4]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6.
[5]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 楚和)
On the Phon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ry inYuanjia Style BAI Cho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65)
Abstract:Yuanjia style, basically using Yin rhyme and having the basic formations,apparently coincides with the phonology in Tang Dynasty in its application. But the application of some phonology in Yuanjia style still bear the pre-Tang phonology characteristics, butis freer in the common use of the similar phonology comparing withthe Tang Dynasty, integrating the old with the new. The phonology in Yuanjia style is, in fact, a connectionbetween the pre-Tang poetry and the metrical poetry,forming a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Key words:Yuanjia style; application of the phonology; pre-Tang phonology; phonology in Tang Dynasty
【作者简介】白崇(1977-),男,河南泌阳人,文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12-05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六朝文学演进中的正变问题研究”(GD12XZW02)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2x(2016)01-0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