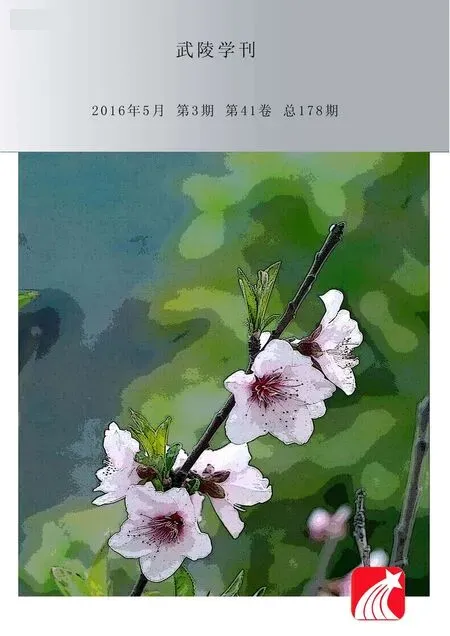论荀子之“法”的理论基础及伦理意蕴
金妍妍
(洛阳师范学院 马列理论教研部,河南 洛阳 471934)
□中华德文化研究□
论荀子之“法”的理论基础及伦理意蕴
金妍妍
(洛阳师范学院 马列理论教研部,河南 洛阳 471934)
荀子“法”思想独具特色,不仅强调个体的伦理德性养成,而且注重整体秩序和谐的价值导向。然而,长期以来,荀子之“法”的社会伦理思想的独特内涵与现代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学界所忽视。如果我们超越诸子各家的历史局限,公正、客观地审视荀子之法的伦理思想,不难发现其不仅继承了孔孟的伦理思想,而且丰富完善了先秦儒家的法律伦理,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内涵独特的价值体系。荀子“性恶论”的理论之基、“隆礼重法”的治理原则诠释了“法”的独特伦理内涵。荀子之“法”的社会伦理思想为建构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道德秩序提供重要启示与借鉴。
荀子;“法”;现代价值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因明确主张“人之性恶”,应“隆礼重法”而背上了非儒家正统的名声,只因一句“性恶”,则“大本已失”,其儒家之“法”的社会伦理思想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学术界所忽视。然而,如果我们超越诸子各家的历史局限,公正、客观地审视荀子之法的伦理思想,不难发现其不仅继承了孔孟的伦理思想,而且丰富完善了先秦儒家的法律伦理,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内涵独特的价值体系。
一、“性恶论”:荀子之“法”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路诸侯兼并杀伐,期望以“实力”相争而定鼎天下。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的战国时代取代了“有孝有德”的西周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和对人性的探索成为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时代问题,为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利人利己观点;道家从“无为”出发,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2],老子不赞成把社会人群分成不同的层级,希望社会安于混沌少欲的安宁状态;法家一面揭示人类“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的本性,一面又走向高扬法的极端,如商鞅所言:“故法者国之权衡也。”[3]“法令者,民之命也。”(《商君书锥指·定分》)韩非则更是主张“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4],其理论自身充满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总之,以上各种理论学说都无法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
儒家则另辟蹊径,从人的现实层面探究人性,力求摆脱“非道德主义”“专任刑罚”式研究路径的困扰,诠释人性的崭新内涵。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首开道德哲学研究的先河。张岱年认为:“第一个讲性的,是孔子。”[5]《论语》中记载孔子讨论人之性的文字有两处:一是“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二是子贡转述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两处文字表明,孔子认为,从生理角度论“性”,人的天生禀赋差别不大,所谓“性相近也”,如告子所言“生之谓性”。从道德价值角度来看,人们对道德状况的追求不同,积善成德的方式各有差异,因此人们会“习相远也”。在孔子论“性”的基础上,孟子将儒家的“人性论”推向了新境界,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认识在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得到确认,《三字经》一开篇就开宗明义点明主旨并成了其总纲。为此,“性善论”在中国民众中影响深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性善论在中国民众中的潜在影响既深且广;而它的倡说者,便是孟子。”[6]2孟子的“四端说”认为人性本善,并以此引出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论,以及以人为本、以仁治国的政治方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四端说”赋予人区别于禽兽的向善爱人的道德天性,“与道家的庄子相先后,从不同角度完成了对人的天赋尊严的论证”[6]2,是憧憬理想人性的呈现。荀子则立足现实主义视野,提出了“性恶论”。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校注·性恶》)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荀子只一句“性恶”,就“大本已失”,他就是仇视人类的无情之人。因为其他学派对“人性恶”也有相近的认识。墨家提出的“兼相爱”的思想主张,其思想来源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缺乏相互关爱、共同谋利的正确反映。天下最大的祸害是什么?墨子说:“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相篡,人之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7]100-101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诸侯相争,人与人相互残杀,父子之间缺少慈爱孝顺,兄弟不和睦等这些社会现象?其根源是什么?墨子认为,是因为人类的不相爱的缘故。而影响人类相爱的社会根源是个体私欲至上。因此,他认为,要实现天下人的“兼相爱”,必须“交相利”。在道家创始人老子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人自私自利的本性,统治者最好做到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这样才能使人民“不欲以静”(《老子·三十七章》)。只有人民不起贪欲而归于宁静,天下自然就安定太平,否则,“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老子也深刻认识到了人自私自利的“性恶”本性。庄子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庄子·天地》)的理想构思,正是对现实中人性恶与等级社会的批判。庄子“等万物,齐生死”的相对主义哲学立场,表达了其否定外在事物差别的良苦用心,希望以此缓和社会矛盾,呼唤人类从功名利禄和权势诱惑中觉醒。庄子认为,“只有把人性从权力、金钱、名誉、成见等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纯真素朴的生命本真,才能从‘有待’的现实世界进入‘无待’的逍遥境界”[8]。法家商鞅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锥指·算地》)他揭示了人的自私本性。针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明确提出了人之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荀子校注·性恶》)生活在战国末期的荀子,基于特定时期的道德生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性的弱点。值得一提的是,荀子的这种人性之恶论,同样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其一,因为人性“恶”,所以人要向“善”,必须要“伪”;其二,对人性之“恶”防患于未然。荀子的“人性恶论”是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人性向“善”的逻辑起点,也是其“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起点。概言之,是荀子社会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因此,不论是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老子的“无为”所达到的“不欲以静”的安定太平和庄子“至德之世”“等万物齐生死”的哲学原则,还是法家的“民之性,饥而求食”的“人性自为”的理论都是以满足个体的私心和个体利益为基础,都以不同方式承认了人的“性恶”本性,只是各派站在不同立场,对理想社会胸怀不同的憧憬,对理想人性采取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态度。儒家学派的代表荀子与墨、道等学派的区别,不仅在于荀子能够集诸子各家之长,正视人性恶的客观存在,而且还在于他预设了“化性起伪”即人性恶到性伪合的桥梁。无所谓“兼相爱”“无为”“人性自为”,关键在于荀子学派能够立于现实主义视角,建构“群居和一”的社会伦理思想体系。
因此,那种认为荀子提出“性恶”“大本已失”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面对战国之际的列国争雄、诸侯兼并、百家争鸣的局面,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各家的思想精华,重新构建先秦儒家“群居和一”的社会伦理思想体系。荀子的社会伦理思想不仅解决了“礼崩乐坏”时代的文化秩序重构问题,而且为秦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性恶论”是荀子社会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是荀子人性论的逻辑起点。荀子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好利焉”“疾恶焉”“好生色焉”的自然属性是恶的,道德个体只有通过修身塑德,才能达到弃恶向善的目的。可见,荀子站在儒家现实主义立场对特定时期的人性既进行了“现实人性的白描”[9],又基于社会管理的立场,在揭示“性恶”的同时,回答了建构理想的“群居和一”社会秩序的问题。
二、隆礼重法:荀子的国家治理原则及伦理意蕴
如前所述,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巨变、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社会秩序失范,正如《史记》所载:“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0]怎样拯救时弊,新兴制度,重拾人类道德生活的基本伦理准则和规范是诸子百家关注的重要课题。
老子认为“自然无为”是最高的人生境界,他向往鸡犬相闻,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他认为:“德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意思是说道生成万物,德养育万物,所以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珍视德的;人类的苦难,是由于背离道的结果。如果人类能够重新回到合乎万物生长的“大道”上来,就一定能够恢复生命的“本真”。墨子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兼爱”,在墨子的视域里,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相互矛盾的原因在于缺乏一种无差等的爱;如果全天下人都相爱的话,那么,强不制弱,众不掠寡,富不欺贫,贵不傲贱,“凡天祸篡怨恨”则不再发生。韩非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他对当时的社会道德现状作了这样的描写:“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祍,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11]因此,他认为要整肃混乱的社会道德秩序,必须树立“法”的绝对权威,主张通过赏罚、“法治”以确立崭新的社会道德秩序。孔子认为要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2]的大同世界其路径在于“教化”。荀子则高瞻远瞩,以崭新的视角睿智洞见提出“隆礼重法”并把它作为治国的根本礼法,以此实现“群居和一”的理想蓝图。人“恶”之性发展的结果就是使社会秩序最终“归于暴”,因此,要遵循“师法之化”,彰显仁爱谦让的道德意识;遵循“礼仪之道”,培养知法守法爱法的观念。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够达致太平、稳定与和谐。荀子“隆礼重法”的主张恰恰顺应了这一时代需求。
荀子所论“性恶”指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等自然情欲与自然本能,黑格尔讲的“性恶”则是人类精神层面的恶性,二者存在本质的不同。荀子与黑格尔的“性恶论”不同点在于:荀子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警示人们弃恶扬善,强调道德个体修身塑德,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强调以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秩序。墨子认为,尽管天下为父母的人很多,为学者很多,为君者众多,可是“仁者寡”,所以“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7]22。荀子不同于墨子,明确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校注·礼论》)墨子在君亲师“仁者寡”的前提下赋予天绝对的权威,因此,其主张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荀子在肯定天的自然内涵基础上,肯定了君亲师的重要历史作用,发掘人性的善端。荀子和道家不同,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最神秘的管理手段”;认为要自然就必须无为,不以主观的欲望来破坏天然,不用矫揉造作代替自己的天性,只有无为才能有自然[13]。荀子则是立于现实主义的视野,洞察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尊“师法之化”,行“礼仪之道”。荀子有别于法家。法家极力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以“法”的绝对性、权威性来确立社会的价值准则。荀子则不仅“重法”而且“隆礼”,主张治理国家必须“礼”“法”并重,使二者相辅相成。荀子与孔孟不同。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4]主张以“德”与“礼”治理社会;孟子以“仁政”治世。荀子则不仅“隆礼”而且“重法”,他提出性恶论,是基于人天生而有的种种物欲、情欲,认为贪欲是至“恶”的根源,所以,荀子的根本目标同孔孟一样,主张教化使人去恶向善,知耻守礼成为君子,提升人民道德境界,使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德性”威力,彻底改变人们的“性恶”本性。荀子认为,在“隆礼”的同时还要“重法”,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奸民”和“元恶”若不重用法律加以严惩,就难以保证社会安宁。因此,荀子的“隆礼重法”体现了道德柔性管理和法律硬性约束的内外结合,是刚柔相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荀子集百家之长,继承、改造、发展了法伦理思想,赋予儒家法伦理思想崭新的内涵。
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具有显著的特色。其一,高度重视“礼”的作用。重视以礼治国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何谓隆礼?在荀子社会伦理思想中,“礼”起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人的无限之情欲与有限之物资供给对立统一的产物。人类生存之物欲矛盾因有“礼”而得到化解;“礼”使道德个体“养人以欲,给人以求”,保持自我内在和谐统一,崇“礼”可以“实现心物平衡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性恶论的目的指向就是礼义的产生与遵循。”[15]77总之,在荀子看来,“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和基本纲领,是“国之命”,主要表现如下:首先,政治性之“礼”,“国无礼则不正”。荀子认为:“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校注·王霸》)“礼”好比量器、墨线、圆规用来衡量轻重,裁割曲直,划定方圆。礼的政治内涵体现在治国之中,“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校注·成相》),“礼”是治国的准绳和价值追求。其次,经济性之“礼”,“故礼者,养也”,“礼以治利”。因为荀子洞见人之性恶,在他看来,当社会物质财富难以满足人的无限贪欲时就会出现“争夺生辞让亡焉”的混乱社会局面,圣王“恶其乱也”,所以制定了“礼”。“礼”既能调养满足人的欲望追求,又能规范人之利益欲求。“礼者,别也”,主张按照人的不同等级来分配物质财富。再次,管理性之“礼”,“明分使群”。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校注·王制》)人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必须明分使群;而明分使群的关键在于“明分”,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校注·礼论》),以此规范社会中的等级名分,促进人人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复次,道德性之“礼”,“以义制利”,“人生不能无群”。在荀子看来,群体要和谐运转,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即“群”“分”“义”;只有“分”得好,才能使个体在各得其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秩序中防止争夺与混乱,“而‘分’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和原理,这就是‘义’。‘义’所体现的是群体的整体利益和价值,是天下之‘本利’所在,因而它是超越个体利益的,并且往往要对个体的欲望构成一定的约束和限制”[16]。“以义制利”体现“礼”的道德功能,它是维系群体和谐,拯救时弊的一剂良药。最后,社会性之“礼”,个体是否守礼表现在为人处事、德性修养、行为举止等方方面面。“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校注·修身)
其二,重视“法”的作用。首先,“《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校注·劝学》)荀子认为《礼经》确定了古代法律的总则,因此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必须以礼的伦理精神为依据,不得背离“礼”。其次,“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荀子校注·性恶》)“法”强调强制性的硬性约束,其社会功能重在治理;而“礼”的作用在于柔性管理,其手段是通过教育而“化”之。因此“教化”与“治理”相辅相成是治理国家的不二法门,是实现“群居和一”理想蓝图的途径。再次,“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校注·富国》)。只强调依靠道德规范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那些‘奸民’和屡教不改的‘元恶’,如不予以严惩,就无法保证国家的安宁。”[17]248刑罚的威慑力量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所必须的。复次,“君子者,法之原也。”这里强调的是,法不可能独自发挥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条例也要依靠人去执行。所以,荀子认为,道德高尚的执法者是可贵的,执法者的职业道德决定法律的社会效果。最后,“轻刑轻罪,重刑重罪”。荀子跟法家不同,“反对法家的‘轻刑重罚’,而是强调要‘轻刑轻罪,重刑重罪’,要求刑罚的‘轻重’应同罪行的‘轻重’相吻合,从而克服了儒、法两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性。”[17]249概而言之,荀子“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开创了我国政治思想史上“礼法并重”的先河,“只有礼法结合,双管齐下,才能使国家‘合于文理,归于治’。”[18]当然,任何思想都难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荀子的性恶论没有逻辑地导向法制观念的强化,这是荀子思想的一个历史遗憾。”[15]77
三、荀子之“法”的现代价值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法”思想独具特色,在强调个体伦理德性养成的同时注重整体秩序和谐的价值导向。荀子蕴含现实主义的“法”的理念,对秦代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发展等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特别是对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实现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价值。
第一,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个体道德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构建取决于个体道德修养的提升。个体道德修养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身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基础。荀子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恶的,何以避恶向善,只有“化性起伪”。“所谓‘化性起伪’,就是使道德个体的自然属性通过个体道德的社会实践转化为社会属性。‘化性起伪’的过程,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过程,即道德个体如何弃恶向善的过程。”[19]个体仁义谦让的道德意识,知法守法的法律观念,必须遵循师法之化才能够培养起来。“荀子希望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德性’威力,彻底改变人们的‘性恶’本性。荀子跟孔孟不同,孔子主张以‘德’与‘礼’治理社会;孟子以‘仁政’治世。荀子不仅重视‘礼’,而且也重视‘法’。他主张治理国家要‘礼’‘法’并重,相辅相成。荀子的根本目标还是引导人民提升道德境界,知耻守礼,成为君子。”[20]当然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刁民”和“元恶”不能姑息纵容,否则就无法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安宁。因此,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对我们加强官德建设有积极意义。“对道义的追求,就是儒家哲学理念中的目的正义。所以重要的是,儒家道义论蕴涵了追求道义的正义。官德境界和义务境界根本上就是来自于这种目的正义。目的正义是行动开始的标准,也是行动目标的旨归。它主导产生集体性意识的方向。基于这样的意识方向,儒家为官德提供了不可小视的集体性意识设计。”[21]这一点在荀子的思想中尤为明显:一方面,荀子希望政府官员能够道德自律,注重修身塑德,具备爱民情怀,具备管理国家、维持秩序和谐的能力。他憧憬建立“群道当”的和谐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管理者是“爱群”“善群”“合群”的人。另一方面,要加强他律,完善政府监督体系,把权力关在法律制度的笼子里,依法行政,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校注·成相》)在任何时候,德治和法治要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安宁,人民幸福,天下太平。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是治国的根本原则,在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荀子的法伦理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人们的观念中,儒家是主张人治的,而荀子之“法”汲取法家思想精华,纠正以往儒家和法家的“礼法”各执一端的片面性,赋予儒家思想以崭新的社会伦理内涵,开创了我国政治伦理思想“礼法并重”的先河。荀子的“重法”思想的现代转化,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同时,法治也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保证,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法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保障,法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22]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75.
[2]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8.
[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83.
[4]班固撰.汉书[M].李润英,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9:392.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83.
[6]赵昌平.孟子:人性的光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
[7]孙诒让,撰.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0-101.
[8]成云雷.庄子:逍遥的寓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
[9]朱贻庭.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30.
[10]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主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2542-2544.
[11]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656-657.
[12]礼记译解[M].王文锦,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287.
[13]戴建业,赵目珍.老子:民族的大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
[1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12.
[15]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的逆向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77.
[16]徐克谦.荀子:治世的理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0.
[17]罗国杰.罗国杰自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8]郭志坤.荀学论稿 [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1:130.
[19]金妍妍.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J].武陵学刊,2013 (6):11-15.
[20]金妍妍.“群居和一”:荀子社会伦理思想研究[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5:63-64.
[21]杨建祥.儒家官德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74-75.
[22]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04.
(责任编辑:张群喜)
金妍妍,女,河南潢川人,洛阳师范学院马列理论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及现代践行。
B222.6
A
1674-9014(2016)03-0012-05
2016-03-11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社会转型深化期德育新理念——以荀子‘群居和一’思想为例”(2015-QN-511);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社会转型深化时期道德教育新理念——以荀子‘和’思想为例”(2014A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