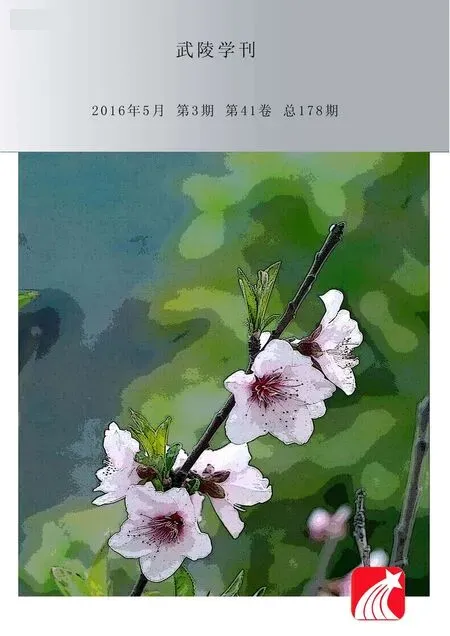“心外之物”与“物外之心”二元对立的终结
——胡塞尔对心灵本质问题之心物二元论的反思和批判
朱耀平,赵庆波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心外之物”与“物外之心”二元对立的终结
——胡塞尔对心灵本质问题之心物二元论的反思和批判
朱耀平,赵庆波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在胡塞尔看来,近代心理学对心灵本质的笛卡尔式的错误理解是它不断陷入“危机”之中的根本原因。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把心看成可以离开对物的显现作用独立存在的“物外之心”。它和把物看成离开心独立存在的“心外之物”的物理学主义犯了实质上相同的错误。实际上,正如意向性理论所表明的,心归根到底不过是对物的显现,它只有在对物的显现中才成其为心。但心与物的相互依赖决不意味着可以将心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混为一谈。
笛卡尔;胡塞尔;心物二元论;心灵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对心灵本质问题上的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反思和批判开始的。贯穿其发展始终的基本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心灵并不是可见的物质实体之外的另外一个不可见的实体。”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的话来说,心灵并不是类似于“机器中存在着某个不可见的幽灵”那样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赖尔(Gilbert Ryle)《心的概念》(1949年)一书的发表作为当代西方心灵哲学诞生的标志,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尽管哲学家们在心灵或意识的体验特别是把其中的感受质作为表象是否能够彻底还原为被表象物体的属性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在“心灵并非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实体”这一点上,则没有什么分歧。就此而言,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心之说”——它倾向于认为它的研究对象——心灵——作为实体是不存在的。
然而,实际上赖尔并不是第一个对心灵的实体地位提出质疑的人。早在19世纪末期,布伦塔诺就认为心理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作为实体存在的灵魂或心灵,而仅仅是心理现象,就像物理学的对象不是物质实体,而是物理现象一样。布伦塔诺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心灵实体的存在,但实际上已经把它打入“冷宫”。在他看来,他本人创立的描述心理学与在他之前的发生心理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堪称“无灵魂的心理学”。
作为布伦塔诺开创的描述心理学遗产的继承者,胡塞尔对近代心理学在心灵本质问题上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偏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力度丝毫不亚于后来的赖尔。换言之,对心灵的实体地位的质疑,对在心灵本质问题上的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的批判,决不是从赖尔的《心的概念》开始的,而是在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心理学中就已经开始了。弄清和记住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的理论实质及其必然被抛弃的历史命运,从而为获得对心灵的本质的正确认识奠定更加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一、近代心理学在心灵本质问题上的二元论偏见
(一)心物二元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心灵看成与物体相互并列的“物外之心”
对于胡塞尔来说,正确理解心灵的本质的关键,在于将它与物体严格区别开来,而不是将二者混为一谈。这不正是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所要求的吗?笛卡尔的那个理论之所以被称为“二元论”,不正是因为它强调心灵与物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吗?然而,在胡塞尔看来,笛卡尔凭借“思维”与“广延”对心与物所作的区分并不妨碍他把心灵看成物质实体之外的另外一个实体,也不妨碍受其影响的近代心理学用“物理学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心灵。虽然身体被看成一种特殊之物,但它仍然可以用精密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而心灵只不过是身体这种特殊物的附属物,“虽然它具有与物体不同的结构,不是有广延的东西,但仍然在与物体相同的意义上是实在的”[1]258。总之,对笛卡尔及受其影响的近代心理学来说,心灵与物体是两个彼此有别、相互并列的实在之物。但对胡塞尔来说,把心与物看成两个相互并列的实体本身就已经是荒谬的,是“违反在生活世界的经验中实际所给予的物体与心灵所固有的本质东西的”[1]259。同样荒谬的是把心理学看成与物理学平行的“精密科学”。实际上,“有关心灵的科学,根本不可能按自然科学行事,根本不可能在方法上求教于自然科学”[1]268。
吊诡的是,恰恰是笛卡尔主义者对心与物的区别和对立的强调导致他们将二者并列起来进而混为一谈。正如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在《心的概念》中所指出的:“相信在心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两极对立就是相信它们是属于同一逻辑类型的词项。”[2]18笛卡尔主义者没有看到的是,心与物具有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凭借“是否存在于空间中”不足以将二者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差异揭示出来。用赖尔的话说,“心”与“物”是两个不同类型的范畴,笛卡尔主义者却依然用关于物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心的存在,把心看成类似于“存在于机器中不可见的幽灵”之类的东西,这是一种典型的“范畴错误”[2]10。对赖尔来说,心与物的不同在于心灵具有完全不同于物体的存在方式,即它并不是像幽灵一样隐藏在身体的内部,而是作为身体的可见的行为或功能存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从空间的角度对心灵与物体加以区分的做法本身没有任何可取之处。物体之为物体,即使像声音这样的无形之物,也需要通过空间才得以存在;而心灵则不直接凭借空间存在。在胡塞尔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也正是它们二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给予”的原因。就“在空间中存在的物”而言,“在任何可能的知觉中,在任何可能的一般意识中,物都不可能绝对无条件普遍地或必然地作为真实内在的东西被给予”[3]117。一方面,空间物有不同的侧面,我不可能以一览无余的方式同时把握它的各个不同侧面,它总是从这个侧面或那个侧面以“侧显”的方式向我呈现。另一方面,对空间物起侧显作用的感知体验本身作为存在于心灵之中的“内在之物”则不再通过侧显被给予,即“侧显本身不再侧显”[3]124。实际上,任何意识体验都不再通过“侧显”被给予,“如果我看着它,我就具有某种绝对物,它不具有那些可以有时这样有时又那样来呈现的诸侧面”[3]123。也就是说,“在不存在空间物之处,从不同观点,沿不同的变化方向,因此按不同的呈现自身的侧面,按不同的视角、显现、侧显去谈论看,这是无意义的”[3]119。总之,对物体的“看”与对心灵或其中的意识体验的“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前者是超越的,后者是内在的。
在胡塞尔看来,认清心与物之间的上述这种区别,是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因此把心与物绝对对立起来,则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心与物是不可分离的,离开物,心就成为虚无,反之亦然。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对心与物的混淆,并不是由于它分不清哪个是心、哪个是物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它把心与物绝对对立起来造成的。它既不懂得心通过物才成其为心,也不懂得物通过心才成其为物。也就是说,它不懂得心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是通过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将二者外在地并列、对立起来的方式将二者混为一谈的。
(二)物理学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物看成“心外之物”
以上说的是心离不开物,心唯有通过物才成其为心。反过来,物也离不开心,物唯有通过心才成其为物。这也正是王阳明“心外无物说”所极力宣扬的观点。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通过先验还原的方法完成了先验唯心论转向的胡塞尔比王阳明走得还更远一些。对于“深山老林里自开自落尚未被任何人看见的花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王阳明的回答是:“你未看此花,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4]310当你没有看到花时,你心中没有任何关于花的念头,此时你的心就像木头一样沉寂着,相应地,山上的花,对于你那颗像木头一样沉寂着的心,既谈不上存在,也谈不上不存在,你的心既是沉寂的,那花也就是隐而不显的了。只有当你来到这棵岩中花树跟前看到它时,此花颜色方才“一时明白起来”[4]310。不过,这时我们仍然想问的是,那些人迹罕至的山谷里没有任何人看见的花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时你已经不能说你没有关于那些花的念头,说你的心是沉寂的了,因为你已经受到眼前这棵“岩中花树”的触动而开始“惦记”那些隐藏在幽深的山谷中或许终其一生也不为任何人所见的那些花来了。那些自开自落的花难道不是在人心之外的“自在之物”吗?胡塞尔“观念”中的下述这段话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一个自在的对象绝不是意识或意识自我与之无关的东西。物是周围世界的物,即使它是未被看见的物,即使它是实际可能的、未被经验的但可经验或也许可经验的物。”[3]131结合上面的例子,不难读出胡塞尔这段话的意思:为什么你会认为除了你看见的花之外,还有你所没有看见甚至不被任何人看见的花呢?那样的花的存在本身就包含着人的理性推论的因素,因此仍然不是离开心独立存在的。它们之独立存在,它们之自开自落,归根到底还是人心中的设想。
总之,对胡塞尔来说,物并非离开心独立存在的东西。物理学主义把物看成与心无关的东西,这既是对物的误解,同时也是对心的误解。把物看成客观的自在之物,无形中就抹杀了心对物的显示、解蔽作用。认为物是独立于心存在的自在之物,与把心看成与物相对立的“封闭的盒子”,只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只有彻底摆脱这种物理学主义的心物二元论的观点,对心灵的本质的认识才有可能进入新的更高境界。
二、意向性理论对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的超越
胡塞尔坚决反对把对世界起构造作用的先验主体或纯粹自我与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的心灵(经验主体)混为一谈,但他并不否认心灵的存在;也不否认以人的心灵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在于,什么是心灵?心灵的本质是什么?心理学对心灵的研究必定是在关于心灵的本质某种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尽管心理学家们对此并不一定有自觉的意识。而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则预先决定着心理学研究的成败。换言之,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不能保证其研究成果的真理性,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心灵的本质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
在胡塞尔看来不幸的是,在笛卡尔式心物二元论的影响下,以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为代表的近代心理学研究一直是在关于心灵的本质的一种完全错误的先入之见的支配下进行的。其直接后果是,“心理学预先就被加给了一种与自然科学并行的科学任务和这样一种观点:心灵——心理学的主题——是与物质自然——自然科学的主题——相同意义上的实在东西”[1]255。对心灵的本质的这种错误理解是心理学不断陷入“危机”之中的根本原因。“只要这种有数百年之久的先入之见的荒谬性没有被揭露出来,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心理学是有关真正心灵东西的科学,即有关那种最初从生活世界获得其意义的东西的科学。”[1]255胡塞尔后面这句话不仅揭示了心理学陷入危机的深层原因,而且指出了摆脱危机的根本出路——摆脱笛卡尔式心物二元论的先入之见,从生活世界本身的教导中达到对心灵的本质的正确理解。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心理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它所渴望的成就。
如果遵循维特根斯坦的思路,那么,像其它任何类似的哲学问题一样,心灵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心灵”这个词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和语言游戏中的用法问题。胡塞尔同样强调不应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心灵”这个词的意义,而应从它在生活世界中最初被给予我们的意义上去理解,这无非是说要根据“心灵”这个词在现实生活中的用法来确定它的意义[1]255。就此来看,虽然他们二人分别代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传统,但在强调“向生活世界回归”这一点上,这两位大哲学家可以说是不约而同、殊途同归。
在胡塞尔对近代心理学提出严厉批评之前,他的老师布伦塔诺已经看到了他那个时代心理学的局限性。他认为除了研究心理现象产生和消失的生理原因的“发生心理学”之外,还应当建立一门用经验描述的方法研究心理现象本身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心理学”。与前者是包含生理学杂质的生理—心理学不同的是,后者是“纯粹心理学”[5]3-4。
按照布伦塔诺的看法,他的描述心理学堪称“无灵魂的心理学”[5]11。因为它认为心理学的对象不是作为实体存在的灵魂或心灵,而仅仅是心理现象,就像物理学的对象不是物质实体,而只是物理现象一样。因此,心灵与物体的区别问题在布伦塔诺那里转变为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问题。但前后两个问题归根到底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罢了。这也正是布伦塔诺认为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已经预先对他本人第一次提出的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问题做出了某种回答的原因[5]85。当然,对布伦塔诺来说,尽管笛卡尔的看法得到了斯宾诺莎、康德等人的认同,但实际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据“是否具有空间大小和位置”并不能真正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区别开来,心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的根本特性在于它们的“意向性”——“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把某物作为对象包括于其自身之中。表象是关于某物的表象,判断是对某物的肯定或否定,爱是对被爱者的爱,恨是对被恨者的恨,渴望是对被渴望者的渴望,如此等等。”[5]88举更加具体的例子来说,看总是对某个有颜色的东西的看,而非对“看本身”的看;听总是对某个声音的听,而非对“听本身”的听,如此等等。总之,“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就是意识或心灵的意向性。
恐怕布伦塔诺本人也没有料到的是,他的意向性理论经过胡塞尔进一步的精雕细琢之后成为其现象学的理论大厦的主要基石,并对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心灵本质问题的视角来看,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的不同在于它不像后者那样把心与物简单对立起来,而是深刻地揭示了二者的内在关联。意向性理论对心与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这种界定的要害在于不再把心看成可以离开物独立存在的东西。“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味着心归根到底不过是对物的“显现”,即只有在对物的显现中才成其为心。也就是说,心只有超越它自身走向物才能成为它自身,否则它不过是“虚无”,萨特把布伦塔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心灵、意识或“此在”的这样一种认识和态度称为“从自我逃离”[6]。
但对于胡塞尔来说,心并非只有通过其意向性才能与物发生关系。事实上,虽然心灵本身并没有“空间上的广延和位置”,但它并不能与具有一定空间大小和位置的物体相分离,也就是说,心灵不可避免地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物体化”。胡塞尔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从本质上说,世界的一切对象都物体化了,正是因此,一切对象都‘参与’物体的空间时间;对象的非物体方面也‘间接地’参与物体的空间时间,这种情况适合于每一种精神对象,首先是心灵,但也适合于任何其它种类的精神对象(如艺术作品,技术构成物等等)。就赋予这些精神对象以精神性含义的东西方面来看,这些精神性对象是借助它们‘具有’物质性的那种方式被‘物体化’的。这些对象以非常本然的方式在这里那里存在着,并且与自己的物体一起扩展。它们同样也在物体的空间时间中间接地有其过去的存在与将来的存在。”[1]260
三、心与物的相互依赖决不意味着可以将心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混为一谈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王阳明、胡塞尔等人的上述这种“唯我论”所要表达的东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它不可说,而只能自己显示出来”[7]120。“唯我论”不可说的原因在于,物对于心(我)的依赖,并不是在同一个世界中两个现成存在着的事物之间的依赖与被依赖关系,而是向“我”呈现出来的整个世界及其中的物对不出现在这个被呈现的世界中的“我”的关系。由于与“我”作为主体并不出现在由“我”构造的那个客体世界中,因此,主体与客体不能被看成在同一世界中两个并列存在的实在之物。
维特根斯坦认为心与物之间的上述关系类似于我的眼睛与我的视野的关系。首先,我能看到我的视野中的一切东西,但却看不到我自己的眼睛,也就是说,我用于观察世界的眼睛并不出现在我通过它观察到的世界中;同理,“唯我论”把自我、心灵作为整个世界的“阿基米德点”,但自我、心灵并不出现在以其为支点的那个世界中,否则它就不再是那个世界的支点。其次,在我的视野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推出它是被我的眼睛所看到的[7]122。这就是说,我不但看不到我的眼睛,而且也“看不到”我的眼睛对我的视野所发生的决定作用;同样的道理,尽管向我呈现出来的世界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但世界在我看来并不是通过我才是其之所是,而是不论有没有我,它都是其之所是。这也正是造成下列这个事实的原因——尽管物离不开心,物只有通过心才能显现出来,但人们却倾向于认为物是在心之外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
“唯我论”把整个世界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而“纯粹实在论”则认为实在世界本身是自足的,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就此而言,“唯我论”与“实在论”是相互对立的。但就真正彻底的“唯我论”并不认为世界的物质部分依赖于它的被称为“自我”或“心灵”的精神部分而言,它与“实在论”又是一致的。由此不难理解,“严格贯彻的唯
我论与纯粹实在论相一致。唯我论的我缩为一个无广延的点,而与其一致的实在则保持不变”[7]122。反过来说,如果“唯我论”意味着把整个世界建立在其中某个被称为“自我”或“心灵”的实体上,那么,它就与人为世界里的精神现象依赖于其中的物质现象的“庸俗实在论”一样浅陋不堪了。这也正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文所告诫的:“如果唯心论意味着把一切存在者都引回到主体或意识,而主体与意识就它们的存在来说始终表现为无所规定的,或最多只被消极地标画为‘非物质的’,那么,这种唯心论在方法上就恰如最粗糙的实在论一样是幼稚的。”[8]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上述一正一反、一唱一和式的阐述所共同主张的就是不能把“自我”“心灵”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混为一谈,不能把前后二者之间的关系看成在同一个世界内并列存在的两个实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从存在论上来说,主体与客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心物对立”或“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范畴错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主体是孤立的还是开放的,而在于主体(此在)具有完全不同于客体的存在方式,以至于二者不能被看作是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中的两个东西。
[1]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王阳明.传习录:全鉴[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5]Brentano,F.Descriptive Psychology[M].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BenitoMüller I.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6]Jean-PaulSartre.L'être et le néant[M].EditionsGallimard,1943:60.
[7]Wittgenstein,L.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New York:Barnes &Noble Publishing,Inc,2003.
[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39.
(责任编辑:张群喜)
朱耀平,男,福建武平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
B516.52
A
1674-9014(2016)03-0032-04
2016-02-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胡塞尔遗稿中的心灵哲学研究”(13YJA720029);教育部第49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被动综合、身体、空间和他者问题研究”。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