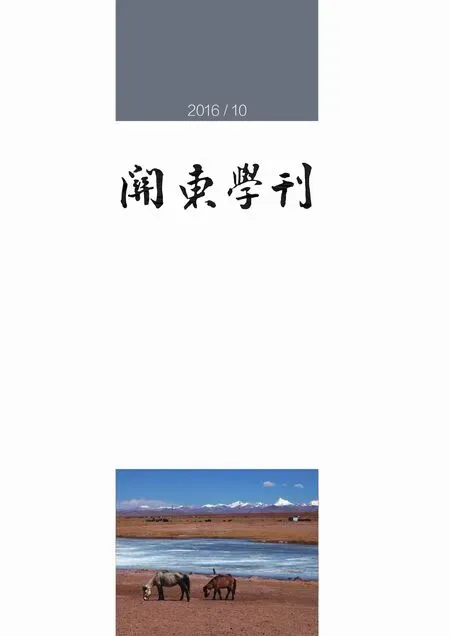江湖满地一渔翁:论杜甫《秋兴八首》
陈岸峰
江湖满地一渔翁:论杜甫《秋兴八首》
陈岸峰
历来有关杜甫《秋兴八首》的诠释可谓汗牛充栋,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前贤的基础上,尝试对此连章组诗的思想、结构以及其在七律发展上的突破及其地位作进一步的论述。
杜甫;悲秋传统;凋伤意识;结构;七律
一、前言
公元766年,亦即唐代宗(李豫,726-779)大历元年,距离“安史之乱”(755-762)结束已有十年之久,自唐玄宗(李隆基,685-762)蜀之后,亦已换了肃宗(李亨,711-762)与代宗(李豫,726-779)两朝天子。杜甫(子美,712-770)除了在至德二年(757)至乾元元年(758)间回京任左拾遗外,自乾元二年(759)即已远离长安,至今已有七年,而他确实至死也回不了长安。
心系故园、帝阙的杜甫,自代宗宝应元年(762)开始寄于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严武(季鹰,726-765)幕下,广德二年(764)甚至获其表荐为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在严武于翌年永泰元年(765)四月病故之前,杜甫为赴严武所表荐之“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陈尚君先生指出杜甫离蜀并非《旧唐书·文苑传》所说的因为严武逝世而无所依,而是因为严武的表荐而上京赴工部员外郎任职,可惜事与愿违:“杜甫自述因卧病伏枕而稽留峡中,以致未能北归朝廷,隔断了与尚书省及郎署的联系,失去了与皇帝面议的机会,并因此失去了官位,淹留成客,随舟漂流。”因此之故,陈尚君认为杜甫最后五年的思想及诗歌创作发生了变化:“忧国与恋职的作品交替出现,对皇帝和朝廷的态度从忠恋发展为怀疑不满。”见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5、286页。若按陈尚君在此文的考证及推论的结果,杜甫在《秋兴八首》中的“违伏枕”、恋职以至于对李唐王朝的怨怼与讥刺,亦也有了基本的依据。买舟携家从成都东下,由于卧病伏枕,*陈尚君详细指出杜甫患病的原因及其病症,乃“由于旅途劳顿,舟行受潮,多年旧疾肺病与消渴症同时发作,病情极其严重。”与此同时,蜀中自严武逝世之后,军阀混战,令杜甫失去退回成都草堂之路,可谓进退失据,经济也十分拮据。详见陈尚君:《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唐代文学丛考》,第293、301页。有关杜甫的因病而淹留,除了《秋兴八首》的第二与第五章之外,还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中的“卧疾淹为客”,其它作品可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客堂》《十二月一日三首》《峡中览物》以及《赠郑十八贲》等作品。而莫砺锋则指出杜甫在云安患了肺病、风痹、疟疾、消渴(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因双脚麻痹而滞留于当地养病。及至夔州,因水土、气候不适应,病益重,而致眼暗耳聋,牙齿半落,行路也需要倚杖甚至别人搀扶。见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9、171页。由此可见杜甫在《秋兴八首》中的“违伏枕”与卧病沧江,确是实在很严重的百病缠身,此时距其逝世只有四年,绝非无病呻吟。据萧涤非先生考证,杜甫之绝笔便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杜甫研究》(下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50-256页。又因“经济拮据、朝廷联系中断等原因,一再延宕改期”,*陈尚君:《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唐代文学丛考》,第295页。辗转流寓于夔州,已近两载。*杜甫淹留夔州的时间乃从大历元年着春至大历三年初春,近两年的时间。参同上注,第294页。
在某个秋天黄昏,五十六岁的杜甫登上白帝城,极目远眺。此际,去国怀乡的他目撃枫树凋零,波浪滔天,风云色变,悲从中来,抚今追昔,遂写下名垂千古的《秋兴八首》。此七律悲秋之组诗在中国诗歌史上,陈继儒(仲醇,1558-1639)评之为:“云霞满空,回翔万状,天风吹海,怒涛飞涌”;*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499页。郝敬(仲舆,1558-1639)则称誉为:“力扛九鼎,勇夺三军”、“虎视词坛,独步一世”。*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99页。此组诗实乃集悲秋传统之大成,*宇文所安指出:“在这些秋天世界及其意义的复杂感怀中,夔州诗的丰硕成果达到了高峰。”见宇文所安著:《盛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42页。创造性地为七律作出了突破,为中国诗歌的全面成熟发展作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贡献,*萧涤非指出:“杜甫的‘集大成’,也表现在对各种诗体的擅长方面。”见萧涤非:《写在“下卷”之前》,《杜甫研究》(下卷),第2页。故黄生(扶孟,1622-?)评曰:
杜公七律,当以《秋兴》为裘领,乃公一生心神结集之所。*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5页。
可谓的论。
然而,历来有关此诗的诠释可谓汗牛充栋,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前贤的基础上,尝试对此组诗的思想、结构以及其在七律发展上的突破及其地位作进一步的论述。
二、悲秋之诗学传承
(一)悲秋之诗学承传
其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其五: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汉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其六: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珠幕绣柱围黄鹤,锦缆牙樯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其七: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堕粉红。
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因秋起兴,杜甫即从天地在秋季的变化着墨。一开始即出手不凡:“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深秋则万物凋零,杜甫目击枫树凋伤,其身心与天地同感,悲从中来,从而创生了创作的冲动,即诗之六义的“兴”。吴渭曰:
诗有六义,兴居其一,凡阴阳寒暑、草木鸟兽、山川风景,得于适然之感而为诗者,皆兴也。……汉魏至唐,杰然如老杜《秋兴》八首,深诣杜甫阃奥,兴之入律者宗焉。*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98页。
吴渭推崇《秋兴八首》乃律诗中以“兴”而创作之典范。王嗣奭(右仲,1566-1648)则曰:
“秋士悲。”秋原易悲,而公之情事,有许多可悲者,而感秋景以生情。*杜甫著、王嗣奭校、曹树铭增校:《杜臆增校》,香港:艺文印书馆,1971年,第443页。
杜甫此时淹留夔州,返京无期,自然愁绪万端,即浦起龙(二田,1679-1762)《读杜心解》于《其一》诗末所云:
“秋”为寓“夔”所值,“兴”自望“京”发慨。*浦起龙:《读杜心解》(卷4),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51页。
然而,杜甫一下笔并非直抒胸臆,而是极为冷静地紧随悲秋之传统。《秋兴》第一章第一句“玉露凋伤枫树林”,便呈现出其清晰的诗学传承意识。《楚辞》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李攀龙编选、森大来评释、江侠庵译述:《唐诗选评释》,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第429页。钱谦益(受之,1582-1664)曰:“宋玉以枫树之茂盛伤心,此以枫树之凋伤起兴也。”*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台北:世界书局,1998年,第764页。杜甫亦曾有诗:“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五首(其二)》)。第一句的“玉露凋伤枫树林”更具体的影响应来自李密(法主,582-619)《感秋》中的“玉露凋晚林”。*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4页。而“枫树林”确为长江两岸之实物,阮籍(嗣宗,210-263)诗中便有“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且有“远望令人悲”之具体陈述。*阮籍:《咏怀诗(其十一)》,《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4页。杜甫目击枫树之凋零而伤年华将逝,亦即桓温(元子,312-373)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叹。此际,杜甫登高临江,身在巫山巫峡之寒气中,面迎波涛涌天的江水,感受到的寒气令他有如置身塞上。巫山位于四川省巫山县之东,两岸之断崖,沿江壁立,高数百丈,绵延四十公里。据《水经·江水注》记载:
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时分,不见曦月。*转引自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第170-171页。
此际,赶制寒衣之砧声的传来,则将外在环境之描写而归结于具体的感受,即所谓的:
催刀尺,制新衣。急暮砧,捣旧衣。曰催曰急,见御寒者有备,客子无衣,可胜凄绝。*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4页。沈德潜亦指出此乃“客子无衣之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香港:中华书局,1977年,第192页。
而“砧声”之选用,亦是杜甫紧随思乡的诗学传统,陈贻焮在引用了沈佺期(云卿,约656-约714或715)《古意》中的“九月寒砧催木叶”与李白(太白,701-762)《子夜吴歌(其三)》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后,得出如下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古人听来,捣衣声有着强烈季节性感伤意味。因此老杜闻之感发,写在诗里,自会增强悲秋的艺术效果……。*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23页。
金圣叹(若采,1608-1661)又指出:
唐人诗,每用秋字,必以暮对。秋乃岁之暮,暮乃日之秋也,都作伤心字用。*金圣叹:《金圣叹选批杜诗》。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由此可见,杜甫是在对“悲秋”的诗学传统极为清晰的创作意识之下而展开创作的。由目击枫树凋伤开始,心绪漫飞,其巧夺天工之处,在于紧扣主题,篇篇秋意。
(二)篇篇秋意
杨伦(西木,1747-1803)指出《秋兴八首》:“对结无痕,篇篇映带秋意。”*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4页。张谦宜(稚松,1646-1728)则认为:
《秋兴八首》,“秋兴”二字,或在首尾,或藏腰脊,钩连甚密。*张谦宜:《絸斋诗谈》。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44页。
方东树(植之,1772-1851)则认为第一章一开始即与以下七章之蕴藏各处有所不同:
他篇或末句结穴点“秋”字,或中间点“秋”字,此却易为起处,横空突入,又复错纵入妙。*方东树:《昭味詹言》。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6页。
杜甫乃因秋起兴,自然必以凛烈的秋寒及实际的山川变化以营造声势慑人的气势,而其描写可谓说确是大气磅礡,渲染出一片愁云惨雾的氛围。在第一章中,几乎全为描写秋天大自然景观之变化,以及秋天在杜甫个体之内化。前两联从“玉露”以至于“枫树林”,从“巫山巫峡”以至于山峡之萧森气象,江间波涛上接于天,令人深感彷佛置身塞上之风云变色,可谓极其夸张之能事。秋天气象之变幻莫测,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后二联则从外在之秋天而转化为杜甫内在之秋天,“丛菊”两见,“孤舟”滞留,寒衣处处,“暮砧”声急,益增客子秋寒而思故园之心。
杜甫在第一章中,极力渲染的是视觉上的萧森肃杀的秋色,此中包括枫树林、巫山巫峡以及江间波浪。而在第一章尾联开始己出现捣衣之砧声,及至第二章则将视觉之满眼摇落转为听觉之秋声:“听猿实下三声泪”。《水经·江水注》: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衷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转引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第171页。
此处,杜甫乃汲取民歌入诗。此际又已是北斗闪烁,遂又接下:“奉使虚随八月槎”。“八月”已然中秋,在此又点明了季节。接着的“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而以“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作结,其意何在?由黄昏至月影,石间藤萝上的月色,已映照洲前的芦荻花了。月亮越升越高,可见他伫立良久,已至深宵。此联之月色,与上联之山楼、悲笳,同为渲染出落寞凄清的悲秋感受。王嗣奭指出:
堞对山楼,悲笳隐动,皆写日落后情景。萝间之月,忽映洲花,不觉良宵又度矣。听猿、悲笳,俱言暮景。八月、芦荻,点还秋景。*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6页。
此言不虚,却未尽具体。月移固有王氏所说的“不觉良宵又度”,而实际上是芦叶可卷而吹之,谓之“笳箫”。*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7页。更进一步者,则杜甫满目皆摇落之悲,江涛翻涌,天色阴晦萧森,而风吹芦叶所引发之悲音,则又将悲秋与思归之情绪推至极致。
由第三章中首联的“静”字,可见杜甫的心情在剎那的极悲之后暂归平静,再次眺望江面。而困坐山城,孤舟一系,已过两载,颈联之“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又是外物之刺激而生感慨。信宿之渔人有家可归,清秋之燕子自由飞翔,而杜甫却日日困坐城楼,遂起下一联关于长安同学名成利就的感慨。同样,由江面之渔人与燕子之感兴,杜甫在下一章中以“鱼龙寂寞秋江冷”返回自身之处境,以蛰伏于此的“鱼龙”自喻。《水经注》曰:
鱼龙以秋日为夜。龙秋分而降,蛰寝于渊,故以秋为夜也。*见杜甫着、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90页。
故“鱼龙寂寞秋江冷”一句可见,杜甫既有未遇之感慨,更有自负与不平之气,正应对上一章的“匡衡抗疏”与“刘向传经”之经历与志向,也在此表示了其不屑“轻肥”的同学之所在。钱谦益认为:
抗疏之功名既薄,传经之心事又违,旋观同学少年,五陵衣马,亦渔人燕子之俦侣耳,故以自轻肥薄之。下一自字,与还泛泛,故飞飞,翻倒相应。杜陵有布衣老大心转拙,于长安卿相何有哉。*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66-767页。
由此可见,杜甫要传达的是:这是“鱼龙”的秋天,亦是他自身的秋天。秋风之冷凛,令他惊觉时间之飞逝,“岁晚”不止是指季节,而是自身年华之流逝。“惊”字可谓用得狠准,既突显了不可挽留的时光,亦再呼应了第二章之“虚随”。
这一点很关键,故此组诗并非单一的怀乡思君,更主要的是杜甫的自伤。
第五章主要描写宫阙壮丽与朝省尊严之回忆,然而尾联则又突转至尾联的“一卧沧江惊岁晚”,以“岁晚”点出秋意,再以“几回青琐点朝班”作结,已埋伏笔。故此,第六章首联即点明李唐王朝与秋天的关系:“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风烟”与“烽烟”同音,*高友工、梅祖麟著:《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页。因为万里的烽烟,昔日春游之繁华胜地也迎来了象征颓败与衰亡的“素秋”。*王夫之评曰:“‘接素秋’妙在‘素秋’二字,止此之外,不堪回首。”见《唐诗评选》,第181页。这正与上一章的“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互相呼应。故此,杜甫在中间两联极力渲染盛世长安曲江头之景况,而再以“入边愁”呼应“万里风烟接素秋”,下启讽刺与哀悼之“回首可怜歌舞池,秦中自古帝王州”。*萧涤非亦认为这两句有讽刺之意。见《杜甫研究》,第176页。无论如何的反复思量,江上的冷风,吹醒了他的耽溺于回忆。
在第七章中,描写秋天的景物更为细腻,以进一步突显秋天与李唐王朝之关系,森大来指出:
前数章写夔必带叙秋意,如云鱼龙寂寞秋江冷及一卧沧江惊岁晚等。此独不及于秋者,以在二联昆明之景物中点逗秋色,无复遗憾也。*李攀龙编选、森大来评释、江侠庵译述:《唐诗选评释》(上册),第456页。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再将池中秋天景物与李唐王朝的关系作了具体分析:
甚至连波中漂浮的菰米和红粉的微小世界,也充满了预兆——无助、分崩、结束、及秋天。*宇文所安著:《盛唐诗》,贾晋华译,第243页。
高、梅二先生则从颜色看出衰亡的象征:
运用“红”、“黑”这样色彩强烈的词进一步暗示即种趋于腐烂的过熟。……“沉”和“堕”都是明显表现衰落的词。*高友工、梅祖麟著:《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21-22页。
仇兆鳌(沧柱,1638-1717)认为此两句乃“想池景之苍凉”,并以为:
织女、鲸鱼亘古不移,而菰米、莲房逢秋零落,故以兴己之漂流衰谢。*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95页。
萧涤非先生据韩愈(退之,768-824)《曲江荷花行》中“问言何处芙蓉多,撑船昆明渡云锦”以证中唐时菰米、莲花还是很多,并认为:
足证此二句乃是追思繁盛,而不是感慨苍凉,仇说未确。*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第177页。
梁鉴江先生以为仇说:
牵强附会。其实四句皆写昆明池盛况;前二句重在景色,后二句重在物产。*梁鉴江:《杜甫诗选》,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第110页。
仇、萧及梁之见,虽观点对立,然均只见表象而不及要害。昆明池乃昔日汉武帝训练水师之地,这是关键,故景色与物产之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而仇氏之诠释为杜甫之自伤,则忽略了首联“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的意义。昔日军事重地,而却沦为游乐、产米、植莲之地,此为李唐王朝之秋天,讽刺之说,*葛晓音便指出杜甫之因救房管而被贬,实乃政治斗争,是肃宗有意向否定玄宗派永王璘出镇东南的决定而作的报复性的大规模罢免蜀郡旧臣,杜甫便是其中的牺牲品。因此,葛先生认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破除了杜甫对肃宗的崇信……杜甫的君臣观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详见葛晓音:《略论杜甫君臣观的转变》,《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05-412页。呼之欲出。
逝者不可追,命运无法改写,故而杜甫再度走进回忆,在第八章他又追忆盛世长安曲江头之春游:鹦鹉啄香稻,凤凰栖碧梧;佳人江头拾翠,才子泛舟吟唱。然而,尾联则又突转至当下此刻的“白头”以及“江湖满地”,以呼应第二章的“违伏枕”与第五章的卧病沧江,杜甫自觉地告诉读者,他已是白发苍苍,而目前的困境是万难突破,这亦是他自己的秋天。
故此,这组诗乃从悲秋传统入手,描写了季节之秋天,暗喻李唐王朝之秋天,感慨自己已迈进凋零的岁月。
三、“凋伤”意识
杜甫一开始已为组诗定下基调:“凋伤”。萧涤非先生认为《秋兴八首》的“真正价值乃在于“爱祖国胜于爱家园的精神”。*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第170页。此说恐怕过于简化此组诗的复杂性。陈贻焮先生则认为此组诗:“无顾影自怜之态,有伤时忧国之心。”*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第928页。然而又说:
其七忆长安昆明池,因想池景苍凉,而兴己漂流衰谢之叹、可叹我浪迹江湖,回不了家乡,就像个到处漂泊的渔翁。其八思长安近畿胜境,忆旧游而叹衰老。*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第927页。
其实“顾影自怜”与“伤时忧国”并没冲突。此组诗超越时空,抚今追昔,从当下自身之困境而触及李唐王朝百年兴衰,而最终仍是慨叹自身年华之流逝,实乃自我与家国相结合之凋伤。
(一)时间焦虑:一卧沧江惊岁晚
由第一章中的“催”与“急”,第二章写的“每依北斗”与月移,第三章之自喻为蛰伏秋江之鱼龙;第五章之“惊岁晚”以及第八章之“白头”,以上例子,处处可见杜甫的时间焦虑。故杨伦说:“岁晚本言年老,亦带指秋深。”*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下册),第646页。森大来亦认为:“岁晚虽本是暮年衰老之意,然亦映带秋意。”*李攀龙编选、森大来评释、江侠庵译述:《唐诗选评释》,第449页。可见杜甫之悲秋,亦是悲叹自己之年华流逝。正如方东树说:
每者,二年在此,常此悲思,而今不觉忽又值秋辰,玩末章末句可见。*方东树:《昭昧詹言》,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8页。
王嗣奭亦认为:
公在江楼,暮亦坐,朝亦坐。此章言朝,承上言光阴迅速,而日坐江楼,对翠微,良可叹也。*王嗣奭:《杜臆》,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8页。
杜甫在第一章中极力描绘秋天之萧杀以及山川、江间之风灵变色、波涛涌天。然而,颈联的“两开”与“一击”却招来不少的误解与批评。胡震亨(孝辕,1569-1645)批评此诗说:
“一系”对“两开”,一字甚无着落,为瑕不小。*胡震亨:《唐音癸签》,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4页。
而吴农祥(庆百,1632-1708)则认为:
“两开”、“一系”之无谓,岂不知工中有拙、拙中有工者。*吴农祥:《杜诗集评》,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5页。
实际上,“两开”指的是秋菊两度绽放,“两”字似无足轻重,而在时间上却已是二载;“一系”之“一”更似单薄,而却是系舟之后,淹留两年。故“两开”对“一系”,均隐含意想不到之感慨,即施鸿保(可斋,?-1871)所说的:
此言乘舟至夔,一系以来,已经二载不乘也,亦急于出峡之意。*施鸿保:《读杜诗说》,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6页。
既有“急”之意味,更多的是无奈。
杜甫闻砧声而思故园,故园不得归,已从心急转为心灰,方有“他日泪”*关于“他日泪”的解释基本上分为两派,一种解释为昔日之泪,如沈德潜解释“他日泪”为“犹往日”,不当。见《唐诗别裁集》,第192页;萧涤非则说:“他日泪,犹前日泪,见得不始于今秋,乃是流了多年的老泪。”见《杜甫研究》(下卷),第171页;梁鉴江亦认为:“因回忆往昔而落泪。他日,往昔。”见《杜甫诗选》,第100页;而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他日”应指来日,“他日”,今人作将来解,而唐人则兼解作过去,而合下一句“孤舟一系故园心”而言,则应指重归故园之日,定会因当下之淹留而下泪,即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义。故赵次公曰:“盖公于夔州见菊者二年矣,方丛菊之两开,皆是他日感伤之泪也。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39页。钱谦益亦指出:“丛菊两开,储别泪于他日。”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64页。之想象。随此低落的心情,第二章第一句承接的是“夔府孤城落日斜”,杜甫感到孤寂,故而夔府也成为孤城,而斜阳余晖更令心情黯淡,仿佛与世隔绝。故吴农祥说:“起语怅然。”*吴农祥:《杜诗集评》。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7页。杜甫之“怅然”,究其原因,在于“虚随八月槎”。关于这一句,历来众说纷纭。张谦宜指出:
时以京官留幕府,故称奉使。海边槎依时而至,而我拟还京,年年不果,故曰“虚随”。*张谦宜:《絸斋诗谈》,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7页。梁鉴江亦持相同观点。详参梁鉴江:《杜甫诗选》,第101-102页。
“虚随”二字颇见怨言,按张氏之见乃指杜甫入朝之希望像八月乘槎上天的神话一样虚幻。萧涤非先生更确切地指出“八月槎”实即“博望槎”,因张骞(子文,?-前141)封博望侯,杜甫是为了突显秋天并与“三声”作对而借用“八月”。*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第172页。高、梅二先生则认为,这一句乃指严武武功之远不如张骞。*高工友、梅祖麟著:《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18页。至于仇兆鳌则认为指“八月槎”乃用严君平在蜀事,而“奉使”又指参用张骞出使事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6-1487页。前者隐居,后者拓边,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在两种诠释中,前者为怨,后者为刺,按杜甫与严武并不太愉快的关系,*可参郭鼎堂(沬若):《杜甫与严武》,《李白与杜甫》,台北:帛书出版社,1985年,第240-243页。两说皆可成立。
接着“违伏枕”道出正在病中,这在第五章的卧病沧江再得到呼应,此为关键。此时此刻,杜甫正在病中,更道出了感觉秋寒的内在原因。此际,杜甫之心由凋伤之枫树林及在病中与感觉寒冷,而联想到自身或离“枫树之凋零”为期不远,由此而感慨平生。故而在第三章中,杜甫便触及“功名薄”“心事违”以及长安同学之名成利就。关于这一章,孙琴安批评说:
若单以字句论,此首不仅逊于前二首,即在八首之中,亦属下乘。*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9页。
此乃其不理解这一章在整组诗中的重要性。“还”与“故”给诗歌增添了一种淡淡的忧伤,*高工友、梅祖麟著:《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4页。传递出一切依然,突显枯坐之无聊。迭词“日日”在“泛泛”和“飞飞”的映衬下,显示了杜甫凝视江流的倦怠心情,*高工友、梅祖麟著:《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5页。甚至带点“恼乱”“触迕”的感觉。*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66-767页。许总亦指出“渔人泛泛”与“燕子飞飞”会在“自身对照中引发极度的不稳定感”,并构成“内心世界的躁动婆惶之反衬”。见许总:《杜甫律诗揽胜》,台北:圣环图书,1997年,第122页。正暗示了杜甫因惊觉岁月流逝而终日无聊空坐城楼之百无聊赖,因而思及壮志难酬,而同学却身居要位,享尽荣华,故而内心充满焦虑而又无可奈何。这是杜甫挥之不去的心结,在组诗中占关键位置,实即屈复所说的:“此伤马齿渐长,而功名不立于天壤也。”*屈复:《唐诗成法》。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29页。可谓一语中的。
(二)几回青琐点朝班
感觉时间之流逝而产生焦虑的意识,乃人之本能。杜甫忠君爱国,复有匡扶社稷之理想,多少年来均望能为朝廷出一分力。然而,从“安史之乱”至今,杜甫仍是沉郁下僚,甚至因上疏救宰相房管(次律,696-763)而遭贬出朝廷,故此对时间之流逝益加感慨。此时,杜甫困坐山城,年华已老而仍一事无成。
在第二章中,杜甫忆起昔日在京为官时经历过“画省香炉”的荣显。杜甫曾任左拾遗,属尚书省的郎官。*梁鉴江误以为当时杜甫乃“工部员外郎”而得以入侍。见梁鉴江:《杜甫诗选》,第102页。其实,杜甫的“检校工部员外郎”中的“检校”表明此乃严武表荐之虚衔,从没正式上任,则为虚衔。杜甫应在公元757-758年之间曾以左拾遗之职入侍,而得以见识“画省香炉”。萧涤非先生则更认为杜甫既曾以左拾遗入侍尚书省,而此刻又是“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望京华而想起这种生活”。见萧涤非:《杜甫研究》,第172页。关于“检校”是否虚衔或实授,可参陈尚君:《杜甫离蜀后之行止原因新考》,《唐代文学丛考》,第283-286页。古尚书省用胡粉涂壁,画古贤人画像。尚书郎入值,有侍女史二人捧香炉烧香从入,为当朝百官熏染官服。昔日荣耀,彷如梦幻,如今则因病而伏枕沧江,侧耳倾听孤城悲笳。杜甫的心结终于在第三章中完全表露了出来: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匡衡抗疏”指的是汉元帝(刘奭,前74-前33)时,任博士给事中的匡衡(稚圭,生卒年不详),曾上疏论得失而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刘向传经”指的是汉宣帝(刘询,次卿,前91-前49)时,刘向(子政,前77-前6)讲论五经于石渠阁,成帝即位后,又任命他领校内府五经秘书。杜甫像匡衡那样抗旨上书救宰相房管,反遭贬遘斥出京为华州司功参军,又因“家素业儒”而想效法刘向那样传经授业,又事与愿违,既不能兼善天下,复不能独善其身。*可参高友工、梅祖麟著:《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5页。
杜甫虽在第五章中对宫阙壮丽、朝省尊严作了精彩而生动的描写,然却以自己的悲伤结局而结束全诗。除了赵次公(彦材,生卒不详)认为:“几回青琐点朝班”,乃“想望省中诸公之朝”*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下册),第1142页。之外,很多注家都认为乃杜甫之悲叹立朝时日不多。沈德潜(确士,1673-1769)认为第五章乃:
追思长安全盛时,宫阙壮丽,朝省尊严,而末叹已之久违朝宁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第192页。
钱谦益亦认为:“几回青琐,追数其近侍奉引,时日无几也。”*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70页。陈贻焮在解读“几回青琐点朝班”时则很明确地指出是:“至德二载十月肃宗还宗后朝会事。”*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第926页。陈先生明确地指出,肃宗至德二载(757)五月至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为左拾遗。*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第926页。又说:
几经碰壁,逐渐对肃宗和朝政有了较清醒的认识,没想到他垂老岁暮竟如此深情地缅怀着这段其实并不那么快意的往事。*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第926页。
杨伦更具体地引吴瞻泰(东巌,1657-1735)之语说:“此处拾遗移官事”*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下册),第646页。指的是杜甫抗疏救房管而被“移官”之事,*可参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册),第322-323页。亦即钱谦益所说的“近侍奉引,时日无几”。而据陈尚君先生之见,应指杜甫在感慨“卧疾已迫岁晚,不知何日方得入朝供职”。*见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第296页。
由第三章之“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起,杜甫在第四章以对昔日朝见皇帝之辉煌,而如今却在寂寞之秋江,以“鱼龙”自况,既有怀才不遇之慨,亦由江边之“冷”而照应秋之主题。秋冷而寂寞且老病,投闲置散于山野,亦一再响应由第一章一开始所说的“凋伤”。
(三)彩笔昔曾干气象
由于时间的焦虑,杜甫既自负蛰伏之鱼龙,一时急着离夔回乡,一时又感叹年华流逝而才能未展,此时的情绪非常波动,于是乎,他回忆起他青壮年辉煌的住事:“彩笔昔曾干气象”。“彩笔昔曾干气象”所“干”之“气象”为何?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叶嘉莹先生肯定《翁批》,认为“气象”乃指山水之气象,“大抵谓昔游之彩笔与山水之气象正复相得相映耳。”*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5-436页。而高、梅二先生则除了指出“彩笔”暗指江淹梦中所得的神笔,认为杜甫“昔日的荣耀是附丽在更为遥远的旧日梦幻之上的”*高友工、梅祖麟著:《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29页。之外,并没有解决有关这一联由来已久的论争。方瑜先生据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之见而作引申说杜甫乃以彩笔干涉了《秋兴八首》中的气象,甚至:
干犯了造化、改变了现实世界的时间,在秋天中创造了春天。*方瑜:《困境与突围——以杜甫〈同谷七歌〉与〈秋兴八首〉中的春意象为例》,《台大文史哲学报》2008年第69期。另可参阅宇文所安:《盛唐诗》,第232页。
然而,杜甫指的是“昔曾”,而非当下,若以为杜甫能以彩笔干涉时间,则似乎推论过深。陈贻焮先生则解释为:“彩笔曾渲染过盛世的山川气象。”*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第928页。庶几接近。梁鉴江则解释为:“上凌星辰,诗才感动皇上。”*见梁鉴江选注:《杜甫诗选》,第111-112页。似乎较为合理。
森大来对“干气象”之诠释者的过度诠释作出了批评说:“迷妄之甚。其殆梦乘车而入鼠穴者欤。”*李攀龙编选、森大来评释、江侠庵译述:《唐诗选评释》(上册),第459页。他又指出:
少陵献三大礼赋时,曾与岑参兄弟泛舟渼陂赋诗相乐。当时逸兴,实有耿耿于怀而不能忘者及于此,良有以也。追彩笔于壮盛,感星象于至尊,其干明主而惊动当时,有如彼三大礼赋。*李攀龙编选、森大来评释、江侠庵译述:《唐诗选评释》(上册),第458页。
又说:
其诗有“忆献三赋蓬莱宫”及“往时文彩动人主”之语、云移二句,可想身以布衣而召试于帝前。当时之身恍有凌云之想、今则一卧沧江而惊岁晚。*李攀龙编选、森大来评释、江侠庵译述:《唐诗选评释》(上册),第449页。梁鉴江亦持与森大来相近的观点,见《杜甫诗选》,第111-112页。
“彩笔”的典故来自《南史·江淹传》:
江淹,字文通。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宇文所安指“彩笔”乃源自郭璞的故事,显然有误。见宇文所安著:《盛唐诗》,贾晋华译,第243页。
“干”应指“干谒”,其用法有如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所说的“不屈己,不干人”。*李白“不屈己,不干人”中的“干人”与“干谒”同一用法的例子,可参葛晓音:《论初唐文人的干谒方式》,《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关于干谒,葛晓音先生指出,其时士人向与“正常科举相关的向州县官和考功员外郎上书行卷”,是干谒的行为;*葛晓音:《论初唐文人的干谒方式》,《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219页。而“直接向皇帝上书投匦”,也要向“负表收封事的献纳使”进行干谒。*葛晓音:《论初唐文人的干谒方式》,《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220页。葛先生又再明确地指出杜甫向玄宗献《三大礼赋》《雕赋》以及《封西岳赋》即乃以“通过投延恩匦进献的”。*葛晓音:《论初唐文人的干谒方式》,《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220页。虽然杜甫也曾说过“独耻事干谒”(《赴奉先咏怀》),而事实上他却向达官投过不少诗作,而此次的对象乃唐玄宗,故此处“气象”应乃指作为皇帝玄宗。杜甫在天宝十年(751)献《三大礼赋》而得以“识圣颜”。*《演义》:“其时公未授官,所作之诗,皆以文采干动时贵,求见知也。”见《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410页;叶先生认为质疑“气象”何所指?若以指朝廷时贵之气象,亦颇牵强。见《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411页。《杜臆》指:“尔时国家全盛,天子好文,尝以彩笔干之,所云献赋蓬莱宫是也。”见《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413页。但叶先生又说“若但以蓬莱献赋释‘彩笔’一句,则似未免失之拘狭矣。”见《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413页。《钱注》:“公诗云‘气冲星象表,诗感帝王尊’,所谓‘彩笔昔曾干气象’也。公与岑参辈安游,在天宝献赋之后,穷老追思,故有白头吟望之叹焉。”见《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413-414页。钱谦益以“星象”对照“帝王”,以杜甫之《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还原“气象”之义,实在博学而高明,但叶先生仍说“仍嫌牵强”。《金解》:“‘彩笔昔曾干气象’,先生曾于蓬莱宫献《三赋》,干动龙颜,虽实有此事,然此处提出,非自夸张,不过借作转语,以反衬出‘白头吟望’七字来。”《会粹》则指“‘彩笔昔曾干气象’,即‘往时文彩动人主’,‘赋诗分气象’意。”《集说》,第417页。此外,《论文》《通解》《沈读》均持此见,然皆为叶先生所否定。气象与白头应作对照考虑,方能得确切之解释。“白头”乃就功名未就而慨叹,而“气象”则应指他曾以彩笔干谒天子而位列朝班。此即杜甫在《莫相疑行》所记他天宝十载(751)以彩笔在蓬莱宫中的超群绝伦的表演而达致的辉煌: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其自豪溢于言表自不在话下,而此中明确地用了“笔”字,正与“彩笔”相印合。从八首诗中念兹在兹的朝廷昔日的辉煌,可兹证明。
(四)江湖满地一渔翁
第七章最后一联由想象而拉回杜甫当下的困境:“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前一句描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后一句形象地自喻困于水中孤寂无助的渔翁,在此与第三章之“信宿渔人”的有家可归,形成强烈对比。此际,杜甫已绝望至极,似乎已绝无希望有任何突破之可能。这也与之前数章结尾的时间焦虑相呼感,即方东树所说的:
气激于中,横放于外,啧薄而出,却用倒煞,所谓文法高妙也。沉着悲壮,色色俱绝。此渔翁,公自谓,乃本篇结穴。*方东树:《昭昧詹言》,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9页。
方东树之指“渔翁”一辞为结穴,亦就是窥见杜甫功业未就之自嘲。然而,钱谦益却说:
满地一渔翁,即信宿泛泛之渔人耳。上下俛仰,亦在眼中,谓公自描一渔翁,则陋。*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73页。沈德潜亦犯了钱谦益的同样错误,认为“二句喻已之飘泊”。见《唐诗别裁集》,第192页。
钱氏认为“渔人燕子”乃杜甫之自伤自况*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66页。已错,再认为“渔人燕子”即“江湖满地一渔翁”中的“渔翁”则更荒谬,可见他对此组诗根本没有透彻的理解。故姚鼐(姬传,1731-1815)批评说:
蒙叟谓渔翁即“信宿”、“泛泛”之“渔人”,谓公自指则陋,此谬解也。公以垂纶自命,诗本数见,何陋之有?结句若非自指,何以收拾本篇?*姚鼐:《五七言今体诗抄》,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8页。
方东树亦指出:
此“渔翁”公自谓,乃本篇结穴。《笺》乃谓“信宿”之“渔人”,成何文理!*方东树:《昭昧詹言》。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9页。陈贻焮也认为“渔翁”乃杜甫自况。见陈贻焮:《杜甫评传》(下卷),第927页。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亦指出:“这世界没有别人,只有单独一个渔翁,这就是沉思的杜甫,梦想着、描绘着色彩缤纷的过去和堕红的杜甫。”见宇文所安著:《盛唐诗》,贾晋华译,第243页。
《笺》乃指钱谦益之笺注。杜甫正因为知道“同学年少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益而感慨自己飘零半生而一直郁郁不得志,故方才有“鱼龙寂寞秋江冷”(第五章)、“几回青琐照朝班”(第六章)、“江湖满地一渔翁”(第七章)、“白头吟望苦低垂”(第八章)之连续自伤自怜,何陋之有?钱谦益之谬解,不攻自破。而杨伦则更具体地进出:
极天满地,乃仰俯兴怀之意。言江满踵广,无地可归,徒若渔翁之飘泊,昆明盛事,何日而能再睹也哉。*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下册),第648页。
杜甫是否有再睹昆明盛事之期待,很值得商榷,因为组诗乃以悲观的情绪结束。确切而实在的是,他自己的“无地可归”而若“渔翁之飘泊”。这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乃此组诗中的中心,可谓自伤其一无所有,百无一用。
此乃杜甫绝望情绪从文字上流露与意象上之呈现,而更巧妙地深藏在组诗的结构之中。
四、章法结构
(一)不可分割
王嗣奭如此细腻地分析此组诗的结构:
《秋兴》八章,以第一起兴,而后章俱发隐衷,或起下、或承上、或互发、或遥应,总是一篇文字。又云:首章发兴四句,便影时事,见丧乱凋残景象。后四句,乃其悲秋心事。此一首便包括后七首。而故园心,乃画龙点睛处。至四章故国思,读者当另着眼,易家为国,其意甚远。后面四章,又包括于其中。如人主之荒淫,盛衰倚伏,景物之繁华,人情之佚豫,皆能召乱。平居思之,已非一日,今漂泊于此,止有头白低垂而已。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尽言,人当自得于言外也。*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5页。
最基本是,八首为一章;首章乃发端,一首包括后七首;承上启下等等不同的章法结构。王夫之(而农,1619-1692)《唐诗评选》评《秋兴八首(其一)》云:
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体尽失,遗诗者之贼不小。*王夫之著、王学太校点:《唐诗评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
纪昀(晓岚,1724-1805)亦认为:
八首取一,便减多少神彩。此等去取,可谓庸妄至极。*纪昀:《瀛奎律髓刊误》,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1页。
即是说八首乃血脉相连,环环相扣,不可分割。屈复则认为应八首当作一首来读:
若八首作一首读,其变幻纵横,沉郁顿挫,一气贯注,章法句法,妙不可言。*屈复:《唐诗成法》。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44页。
而邵长蘅(子湘,1637-1704)则认为八章有八章之结构,一章亦有一章之结构。*邵长蘅:《五色批本杜工部集》。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43页。由此可见,八章为一组,各有其功能在其中,不容妄作切割或作优劣之品评。萧涤非先生则有具体的见解:
秋兴八首的结构,从全诗来说,可分两部,而以第四首为过渡。大抵前三首详夔州而略长安,后五首详长安而略夔州;前三首由夔州而思及长安,后五首则由思长安而归结到夔州;前三首由现实走向回忆,后五首则由回忆回到现实。至各首之间,则亦首尾相衔,有一定次第,不能移易,八首只如一首。*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第170页。
此分析基本将其结构作出了明确地勾勒,有助我们的进一步分析。
(二)序曲
第一首乃组诗之序曲,即沈德潜所说的“八章发端”,*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第192页。通过对长江三峡之动人心魄的秋色秋声的描绘,抒发了杜甫流寓他乡、缅怀故里的伤感,为整组诗渲染了一种萧条落寞的氛围。第一章之所以为序曲,即八句之中已蕴含了以下七章所要展开的一切,故八首为一组诗,此乃提纲撷领之所在。第一章即是画龙点睛,绘声绘色地渲染了秋天的夔州,以及站在白帝城上极目眺望所见的黄昏景象,从枫树林、巫山巫峡、江河波浪,再内化至其心灵与节季及天地之交感互应。此乃从宏观的角度而言之。
从微观的角度思索,即首联与颈联有关秋天之描写在以下七章,环环相扣,或明或暗,均予以呼应,甚至细致到第二章之藤萝、芦荻花,第三章之清秋燕子,第四章之“鱼龙寂寞秋江冷”,第五章之“一卧沧江惊岁晚”,第六章之“万里风烟接素秋”以及第七章之“露冷莲房堕粉红”。其次,“故园心”*沈德潜解释“故园心”为“樊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第192页。沈氏之说失之坐实。而且樊川是杜牧宗族之聚居地,而非杜甫之故居。实际上,杜甫是襄阳人,生于河南巩县,只在长安生活了十二年,从其“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可推测大概居于曲江附近,否则如何能天天喝醉了仍回得了家?肯定就是家在曲江附近。而从《秋兴八首》中的文字可见,他是多么的眷恋曲江的一切。然而,“故园心”实应泛指长安,那里既是曾经的故园,更多的感情因素是因为那里是帝阙之所在。之复杂情绪实则乃回忆昔日辉煌,则又可见于第二章之“画省香炉”,第三章之“匡衡抗疏”,第五章之“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麟识圣颜”,第六章之“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第七章之“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以及第八章之“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其三,“他日泪”即起于当下之郁闷困境,则下启了第二章之“违伏枕”,第三章之“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第四章之“鱼龙寂寞秋江冷”,第五章之“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简而言之,即由第一章而幅射以下七章,一开始即布下操控之绳索。
(三)承上启下
屈复(见心,1668-1745)指出:“七昔游,结后四首,八今望,结前四首,章法并然”。*屈复:《唐诗成法》,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41页。屈氏从第七章与第八章着手,认为第七章此乃从大结构而言的承上启下。实际上,除了沈德潜之外,很多注家都认为第三章乃承上启下之关键,沈氏认为虽于第四章尾联的“故国平居有所思”中评曰:“结本章以起下四章”,*屈复:《唐诗成法》,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92页。但又说:
以上就夔府言,以下就长安言,此八诗分界处也。或谓末句五陵逗起长安,此又失之于纎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第192页。
森大来对沈氏之见提出质疑说:
此章末既从自己不遇想到五陵之同学,于是次章接手而写长安矣。沈归愚讥之为纤,大非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第445页。
王夫之亦认为:“末句连下四首,为作提纲,章法奇绝。”*见王夫之评选、王学太校点:《唐诗评选》,第180页。此即王嗣奭所说的由第四章起“易家为国”。*见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第1485页。其实,由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都是有关长安的追忆,此乃宏观而言的承上启下。
而在独立各章中,又有各自的承上启下。方东树在评第四章时指出:
三、四近,皆“闻道”事,承明上二句。五、六远,忽纵开,大波澜起,既振又换。结“秋”字陡入,悲壮勒转,收足五、六句意。而“思”字又起下四章,章法入妙无痕。……此诗浑灏流转,龙跳虎卧。*方东树:《昭昧詹言》,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1-132页。
同样,第一章颈联之“丛菊”上承前二联有关秋天的描写,而“故园心”下启尾联之“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第二章之“虚随八月槎”上承“每依北斗望京华”,下启“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以至于尾联之虚渡光阴;第三章之颔联之“还泛泛”与“故飞飞”所带来之无聊与恼乱,上承首联之“日日江楼坐翠微”,下启颈联之“功名薄”与“心事违”;第五章之“惊岁晚”以否定的方式颠覆了前三联的宫阙壮丽与朝省尊严,点出此乃李唐王朝之秋,下启自己立朝时日之无多;第六章以颔联之“入边愁”上承首联之“万里风烟接素秋”,下启尾联之慨叹“回首可怜歌舞地”。
(四)往复回环
孙琴安先生认为第六章有以下不足:
若单以字句论,第四句不仅与起二句不称,即与八篇之壮阔亦不称。*方东树:《昭昧詹言》,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6页。
大概指的是第四句的“入边愁”突兀,而实际上“入边愁”正呼应了第二句的“万里风烟”,“边愁”对“烽烟”,此时曲江头正游人陶醉于春天之美景与盛唐之升平气象,而“花萼夹城通御气”所指的皇家耽于嬉游,正是导致“边愁”之由来。而此诗之中间两联描写曲江嬉游与穷奢极侈,正好衬托其它篇章之悲壮之由来。此乃所谓浓淡得宜。同样地,钱谦益亦就第六章说:
今人论唐七言长句,推老杜“昆明池水”为冠。实不解此诗所以佳。*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72页。
然而,他还是解读为杜甫忆起昆明池之织女、石鲸、莲房及菰米,“而自伤其僻远而不得见也。”*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73页。此见与胡震亨之评此诗“颈联肥重,‘堕粉红’尤俗”*胡震亨:《唐音癸签》。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页137。一样,皆未懂杜甫用意。昆明池乃汉武帝凿以备战,旨在武功,而此刻却是一派颓败荒凉,“夜月”对“秋风”见其凄寂,“沉云黑”对“堕粉红”见其颓败,昔日校场,今日荒凉,由此以象征李唐王朝之衰亡。*许总指出:“诗由昆明池写出唐帝国之兴衰”。见许总:《杜甫律诗揽胜》,第129页。张谦宜不同意钱谦益指“织女”、“石鲸”乃指盛时之论,认为:
“织女”、“石鲸”四句,皆言昔盛今衰,带写秋来零落之象。*许总:《杜甫律诗揽胜》,第138页。
可谓的论。实际上,组诗从第四章至第八章主要描写长安,而却用了由衰与盛之间的往复回环笔法,即张诞所说的:“盛衰之相寻,所谓不胜其悲者。”*张诞:《杜工部诗通》(第2册卷14),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第430页。杨义则勾勒出诗中的对立观念与行为,称之为“双焦点时空结构”。见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762页。可以盛衰相倚之法视之。第四章写长安百年变化之巨,人面全非,而北有回纥之侵边,西有吐蕃之犯京,此谓衰;第五章写全盛之长安的“宫阙崇丽,朝省尊严”,*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70页。此谓盛;第六章虽暗提“边愁”,而主要仍是写全盛之穷奢极侈,可谓盛转衰之转变;第七章乃承上一章之“入边愁”而写昆明池之颓败荒凉,亦可想见长安在战火之后的乱象,此谓衰;第八章又回到全盛之长安曲江头,佳人拾翠,仙侣同舟,此谓盛。而最后又启“白头”之叹,遂又可往复回环至第一章之悲秋之起端。即如杨伦引陈廷敬(子端,1638年-1712年)所说的:
八诗章法绪脉相承,蛛丝马迹,分之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合之如常山之阵,首尾互应,其命意炼句之妙,自不必言。*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下册),第649页。
这四章之衰盛往复回环之描写,实与杜甫内心之反复咀嚼思量李唐王朝之兴衰紧紧相扣。盛衰有象,往复回环,感慨万千,一唱三叹,即如论者所说的“形成震撼心弦的多声部夜鸣曲式的结构形态。”*杨义:《李杜诗学》,第747页。
(五)刺破法
第五章尾联的“一卧沧江惊岁晚”,笔锋突转,评论颇多。杨伦云:
前六句直下,皆言昔之盛,第七句打转,笔力超劲。*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下册),第646页。
而方东树则评曰:
忽跳开出场,归宿自己,收拾全篇,苍凉凄断。……言外有余悲,所以为佳。*方东树:《昭昧詹言》。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4页。
孙琴安先生亦认为:“一结则如梦方醒。‘惊’字妙。第七句转折亦妙。”*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4页。其实“打转”之法亦就是第四章的描写故国之思后,突然返回自伤的“鱼龙寂寞秋江冷”,第七章描写昆明池之颓败荒凉后突写目前己身困境:“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天一渔翁”,第八章描写盛世长安曲江头的明媚风春光与太平物象后又返回自身的感慨:“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故说第七句“打转”可以,而说“笔力超劲”则不妥,虽有突转,实以哀怨低徊之笔围绕“凋伤”之主调,实不应以“超劲”形容之。
高、梅二先生注意到杜甫刺破幻想的举措,指出:
5-7首诗作为一个整体,传达了一种维持梦境的印象,这是一个重建昔日的兴盛而顽强努力的梦想,但是,这种梦想总是在最后一联,被杜甫清醒面对的严酷现实所破灭。*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第26页。
准此而言,八章血脉相连,正如沈德潜所说的各章“隐隐作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第192页。又有如太极之回环往复,气象万千,变化无穷,可谓布局精深,心思慎密。
又有论者在第七与第八章两诗,哪一首是高潮,以及第八章何以以春天作结束,有不同的见解。翁方网(忠叙,1733-1818)认为第七章之秋意最浓,乃以此“正收秋思矣”。*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91-92页。方瑜先生据此又再追问既然已收束诗题之“秋兴”,又“何必再写末章,再写,要如何落笔?为何会变秋为春?”*方瑜:《困境与突围——以杜甫〈同谷七歌〉与〈秋兴八首〉中的春意象为例》,《台大文史哲学报》2008年第69期。而他的推论是,在第七章深刻沉重的无常感后,杜甫企图在第八章之结尾“欲借高乌之飞翔跃升”,以作“突围”。虽然他也承认,在“关塞极天唯鸟道”的仰视之后,顿时又落入“江湖满地一渔翁”的困局。*方瑜:《困境与突围——以杜甫〈同谷七歌〉与〈秋兴八首〉中的春意象为例》,《台大文史哲学报》2008年第69期。然而,方瑜先生还是认为:
《秋兴》末章,用心营造的不只是单纯的景物,而是整体氛围,从字行间散溢的明丽欢悦气氛。与前章、甚至前七章,截然区隔,并非完全写实的长安之春,杜甫去除杂质,撷取记忆中与特殊空间连结的鲜明印象,以七律精严的格律,留下欢愉和美,成为永恒。*方瑜:《困境与突围——以杜甫〈同谷七歌〉与〈秋兴八首〉中的春意象为例》,《台大文史哲学报》2008年第69期。
最后一章的尾联乃以“白头吟望苦低垂”结束全诗,何来“欢愉和美”的“永恒”呢?此即高、梅二先生所指出的:
在第八首也就是最后一首诗中,那些用以掩饰现实的、精心构制的美梦终于在一连串幻灭的打击下被彻底放弃了。*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26页。
又说第八首诗所造成的“反高潮”(anti-climax)适于表现挫折与绝望的主题性情绪。*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30-31页。然而,他们却又认为指出高潮应在第七章而非第八章,理由如下:
这首诗的高潮应在第七首而不是第八首,这一点不太引人注意,但这里有令人信服的标志。在第七首诗中,不仅每联都强烈地表现了各自的主题,而且四联合在一起,包括了整个组诗的全部基本主题。汉、唐之间的逐点对比在第一联达到顶点;第二联则在宇宙与人生的纷扰中表现了绝望的主题;过去的繁荣和今天的衰落间的对比在第三联得到展示;而第四联所表现的是以联系代表分离的矛盾现象和那不幸的小舟意象。*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30页。
其实,从整体的结构而语,第八章最后一联则更为精彩、惊险,在“彩笔昔曾干气象”这一句中,已在“昔曾”二字上暗含伏笔,而终在最后一句“白头吟望苦低垂”,以理想的幻灭的悲凉作结。从“关塞极天惟鸟道”形容不可突破之困局,“江湖满地一渔翁”形容无可着陆之叹,杜甫乃以自己的秋天“白头”结束全篇,方瑜先生所说的“留下欢愉和美,成为永恒”,恐怕难以成立。同样,高、梅二先生所说的“第八首诗所造成的‘反高潮’”的“挫折与绝望”情绪,亦值得商榷,因为从第一章开始,杜甫早已百无聊赖的姿态呈现于读者面前:“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其一)、“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其二)、“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其三)第一章开始就是“泪”与“孤”,接着的仍是“孤”与“望”(怅望),而再下去的又是“日日”坐江楼,重复地看着渔人去而复来。由此可见,前三章已一再呈现杜甫的困境及寂寥心态,一开始已是败局,何来高潮可言?及至第四章之“闻道长安似弈棋”,而此中参与了如此纷纷扰扰的政局而又是得益者的便有杜甫的同学,即颈联所描述的王侯第宅的“新主”与异于昔日的“文武衣冠”,而这些人却又是导致颌联所描述的动乱之由。相比之下,杜甫常常依北而望,关心国事,却落得如今的困坐山楼,蛰伏秋江。有论者指出:
此第四首……承上章言我之生平既未得其志,而时事之可悲又有甚焉者。*佚名:《杜诗言志》,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31页。
“未得其志”可谓一语中的。钱谦益亦曾说过:
公抗疏不减匡衡,而近侍移官,一斥不复,故曰功名薄。若刘向虽数奏封事不用,而犹居近侍,典校五经。公则白头幕府,深媿平生,故曰心事违也。*钱谦益:《杜诗钱注》(下册),第766页。
在此既明知杜甫“白头幕府,深媿平生”,而何以不理解其因惭愧而自嘲为“江湖满地一渔翁”呢?杜甫在组诗中之时间焦虑与功业未就之恨在此来个总结:昔日荣耀已成过去,如今已是江郎才尽。这是最最绝望的宣言,本来一直的时间焦虑,仍显示希望有所突破,回归长安,再列朝班。而如今他已清晰地道出自己的“白头”的现实。这是对时间焦虑的一种清醒的回答。最终,杜甫则连自己的才华也一并否定,一切的挣扎、期待在此宣告崩溃,故此诗最终乃以绝望的自我否定作结束。这才是全诗的高潮所在。
由此而言,杜甫因秋起兴,而终以自己之“白头”宣告已步入生命的秋境,宣告一生失败的绝望之作,即陈廷敬所说的:
笔干气象,昔何其壮!头白低垂,今何其惫!诗至此,声泪俱尽,故遂终焉。*《唐宋诗醇》,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140页。
确是道出杜甫的心声。“白头”乃杜甫个人的秋天,紧扣第四章的“鱼龙寂寞秋江冷”、第五章的“一卧沧江惊岁晚”以及第七章的“江湖满地一渔翁”。由此可见,诗题是悲秋,诗意亦是悲秋,而从结构安排上,亦是以杜甫“江湖满地一渔翁”的悲观情绪以否定自己的一生告终。
然而,杜甫《秋兴八首》之所以在七律以至于诗歌发展史上,占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除了思想含蕴深刻、结构幻化无穷之外,更在于其以极为严谨规范的架式,展开了这以八章为一组的《秋兴》之创作,与此同时,他又对七律中间两联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为七律之迈向成熟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五、中间两联的创造性
关于七律中间两联,高、梅二先生指出:
律诗的中间两联都具有一种作用于词语的内在平行力场,如果其中的每联诗又含有同样的歧义结构,那么通过这种平行力场及其对句的相互呼应,诗的效果将会成倍地扩大。*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12页。
第一章颔联由“江间”而突接“塞上”,画面转变之迅速,非常突然,再又以“波浪兼天涌”衬托“风云接地阴”,将气势磅礡而又瞩目惊心的场面,更推至想象的极致,彷佛将整首诗的力度拉至极致,连读者的呼吸也一并扯上去。这便是语言与想象的力量。当然亦是这两句诗的“平行力场”。然而,就在读者还来不及反应之际,杜甫之妙笔又突转入内在之感受,由惊涛骇浪而转为内心因面对如此悲凉之氛围而思念乡园之温馨而不得归之愁苦,故而在下一联则化为丛菊之两度重见与孤舟之一系不发之苦闷。此为外悲凉、内苦闷之张力及其相互呼应,这是杜甫营造的秋天的整体氛围。
随之而来,第二与第三章均为内省,力度转为舒缓。第二章的中间两联的关键在于颔联之“奉使虚随八月槎”与颈联之“画省香炉违伏枕”,说的就是心在帝阙而不得归,故而才有听猿鸣而下泪,闻笳声而生悲。心在帝阙,往上呼应“每依北斗望京华”,下接尾联的惊觉时光流逝之飞快。第三章颔联写渔人之作息有序,燕子来去自如,及至颈联则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功业未就,自愧不如。因此百无聊赖,“日江楼坐翠微”,更因功业未就心事违而在尾联提及长安同学之轻肥。
然而,第四章的中间两联的张力又突然加强。第四章先写长安府第主人变更之翻天覆地,文武百官之轮流登场,而颈联则突写北方回纥与西边吐蕃之侵犯,两联之衔接看似突兀,实乃暗示了两者的相互呼应关系。而颈联之“金鼓震”与“羽书驰”正好将灯红酒绿、耽于逸乐的长安的升平梦幻刺破,“震”与“驰”皆是震撼与急迫的力量的表现。
再下及的第五、六、七章又分别写宫阙、曲江头以及昆明池,力度又稍后舒缓。关于第五章,沈德潜认为:
前对南山,西眺瑶池,东接函关,极言宫阙气象之盛,无讥刺意。*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第192页。萧涤非认为:“秋兴八首为杜甫惨淡经营之作,或即景含情,或借古为喻,或直冬无隐,或欲说还休。”见《杜甫研究》(下卷),第170页。许总则指出第五章首联与颔联联乃讽刺玄宗之耽于神仙之事而误国的鞭笞,而颈联之“徐缓节奏,实即一幅昏愦君王之画像。”见许总:《杜甫律诗揽胜》,第126页。
若无讥讽,何以杜甫会在中间两联之辉煌壮丽之后,突转为“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中间两联有如梦幻之富丽堂皇,就是为了衬托杜甫所经历的沧海桑田。第六章之颔联,先写帝王之耽于逸乐,以致有“入边愁”之危机,颈联则仍旧描写帝王之穷奢极侈,而非直接写帝国崩溃,意欲何为?就在于突出帝王之不省,仍旧游乐嬉戏,益见帝国之岌岌可危,亦为下一章作了铺垫。第七章两联乃集中写昔日汉武帝所挖凿以作训练水师的昆明池。昆明池之建立乃汉武帝之雄心壮志及武功之所在,故而首联已明白道出:“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此诗以“汉时功”与“武帝旌旗”作为历史背景而展开的,而接下的是极为反讽的画面,中间两联的重心是当下的昆明池的荒凉现状,原因在于“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诠释这两句为:
织女机丝既虚,则杼柚已空。石鲸麟甲方动,则强粱日炽。*引自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343页。
王尧衢(翼云,生卒不详)《古唐诗合解》亦云:
一云石鲸麟动,比强梁之人动而欲逞,织女机虚,比相臣失其经纶,犹织女停梭,虚此夜月,亦是深一层看法。*引自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350页。
从杜甫当时在夔的切身处境亦可见,中央已失去了正常的运作,没有给予他丝毫的支持或联系,更为实在的是当时内忧外患,蜀中军闳混战,而吐蕃与回纥亦相继入侵。故以“虚夜月”与“动秋风”映衬昔日汉武帝练武之地昆明池之沦为产米、植莲所造成的季节性颓败、沧凉,藉此以呈现李唐王朝之衰落。此即杨慎(用修,1488-1559)评说的:
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则荒草野烟之悲见于言外。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莲房不采而任其坠,具见兵戈乱离之状。以中二联,谓专写丧乱,即蒙禒山之祸的长安者。*李攀龙编选、森大来评释、江侠庵译述:《唐诗选评释》(上册),第455页。
中间两联的作用,亦即叶嘉莹先生所说的“现实的感情”的意象化,即“意象化之感情”,*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46页。这些意象不止是实物,而是通过带有强烈情感的意象传递了李唐王朝如呈现衰败的秋天。中间两联之颓败、荒芜的描写正好与首联构成强大的张力,从升平气象而跌入悲观绝望。高、梅二先生则更将这两联作了细致入微的镜头距离解读,而“关塞极天惟鸟道”所产生的压抑,彼等称之为医学上所说的“幽闭恐怖”。*高友工、梅祖麟:《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23-24页。高、梅二先生之独到诠释,亦正是杜甫在以七律为创作模式的组诗中苦心孤诣之所在。
及至第八章,颔联之鹦鹉啄食香稻,凤凰之栖息梧桐,一派祥和的气象,正如盛世长安之曲江头,佳人岸边拾翠,才子泛舟吟唱。“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在句法上之颠覆,呈现表象之升平与底下之危机,一如昔日拾翠之佳人化为尘土,泛舟之才子如今白头困卧沧江。此两联的升平气象之营造,却全为了在尾联最后一句中被“白头吟望苦低垂”所刺破,以造成今非昔比,时不再来之慨。
再者,杜甫在有限的篇幅中亦为不同的场景作了悉心的安排。例如,第一章颔联写的“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第四章“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乃磅礡的气势的描写;第二章两联“听猿实下二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第三章与第七章,分别写的是百无聊赖的苦闷与沧凉寂寞;第五、第六章以及第七章的中间两联则又对宫阙壮丽、朝省尊严、帝王之穷奢极侈以及盛世长安曲江头的春游,作了细腻的描述。此外,又有远近距离之设置,现实与想象之分别,复以民歌、神话以及历史之博采,揉合而入诗。
简而言之,杜甫《秋兴八首》中间两联之创造性开拓,乃其学问、才思以及语言魅力的综合呈现,正如叶嘉莹先生所推崇的杜甫之七律“乃全出于一己之拓与建立”、“以独力开辟出一种诗体的意境”,*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7页。有关杜甫七律章法的研究,可参阅简锦松、陈怡婷:《杜甫七律章法规格化之研究》,《东华汉学》2009年第9期。堪称其诗学之丰碑。
六、七律之冠
杜甫《秋兴八首》从悲秋之诗学传承、思想情感之沉郁顿挫、中间两联之突破性创造以至于结构之精密,那么这组诗在七律史上又占据什么地位?
在《唐诗选》中,明代复古诗派*前七子乃以李梦阳(献吉,1472-1530)与何景明(仲默,1483-1521)为首,此外尚有徐禛卿(昌谷,1479-1511)、边贡(廷实,1474-1532)、康海(德涵,1475-1540)、王九思(敬夫,1468-1551)、王廷相(子衡,1474-1544);后七子乃以李攀龙(于麟,1514-1570)与王世贞(元美,1526-1590)为主,此外尚有谢榛(茂秦,1495-1575)、宗臣(子相,1525-1560)、梁有誉(公实,1519-1555)、徐中行(子兴,1517-1578)与吴国伦(明卿,1524-1593)。因为彼等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文学观念,故此一般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对这一流派也以“复古诗派”视之。的李攀龙(于麟,1514-1570)将李颀(东川,生卒年不详)仅有的七首七律全收,他说:
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致其妙,即子美篇什虽众,愦然自放矣。*李攀龙撰、包敬弟标校:《沧溟先生集》(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7页。
“自放”即不守规矩,当然“颇致其妙”者亦可能流于墨守成规而难见突破性的创造。复古诗派的推崇者胡应麟(元瑞,1551-1602)亦言:
李律仅七首,惟“物在人亡”不佳。“流澌腊月”,极雄浑而不笨;“花宫仙梵”,至工密而不纤。“远公遁迹”之幽,“朝闻游子”之婉,皆可独步千载。*此处乃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24页。
但他又说:“七言律,唐以老杜为主,参之李颀之神,王维之秀,岑参之丽。”*见胡应麟:《诗薮》,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第83页。清初的王士祯(贻上,1634-1711)则认为:
唐人七言律,以李东川、王右丞为正宗,杜工部为大家,刘文房为接武。*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页。
由此可见,王氏之见与李攀龙在七律上的观点相当一致,均推崇李颀与王维(摩诘,?-761),但他并没有批评杜甫,仍以杜甫“大家”称之,这与胡应麟的“以老杜为主”之见,分歧甚为明显。冠军谁属,关键则在李颀与杜甫两人身上。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与李攀龙在《古今诗删》的选唐诗部分一样,将李颀七首七律尽取,他说:
东川七律,故难与少陵、右丞比肩,然自是“安和正声”。自明代嘉(靖)、隆(庆)诸子奉为圭臬,又不善学之,只存肤面,宜招毛秋晴太史之讥也。然讥诸子而痛扫东川,毋乃因噎废食乎?*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13),第185页。
这是指毛奇龄(大可,1623-1716)在其《唐七律选》中因不满后七子而连李颀在七律上的艺术成就也一并抹杀。毛氏这样说:
旧唐名家多以王(维)孟(浩然)、王(维)岑(参)并称,虽襄阳(刘长卿)、嘉州(岑参)与辋川(王维)并肩而不并,然尚可并题。至嘉、隆诸子以李颀当之,则颀诗肤俗,不啻东家矣。明诗只顾体面,总不生活,全是中是君恶习,不可不察也。*转引自孙琴安:《唐七律诗精评》,第24页。
沈氏既不认同后七子对李颀的过高推崇,然却又认为毛奇龄因对后七子的不满而对李颀也一并抹杀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其客观与理性的一面。沈氏虽将李颀七首尽录,但却认为杜甫与王维的成就实远较李颀为高。在卷十三中,他对杜甫的七律有如下的高度评价:
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学之博也;才之大也;气之盛也;格之变也。五色藻缋,八音和鸣,后人如何髣髴。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饶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瞠乎其后,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13),第188页。
这就已将杜甫与王维在七律的成就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微分。沈德潜对王维的七律其实已作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风格最高、复饶远韵,为唐代正宗”,*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13),第188页。其殊荣似已无可复加。然而,沈氏认为王维在七律仍不及杜甫之处,乃在“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应是指杜甫的七律在风格的变化(“不及者四”中的“格之变”)上远较王维优胜。这亦即否定了李攀龙上述所批评杜甫的“自放”之所在。沈氏这个观点可从其在杜甫五律的总评中再得进一步的肯定:
杜诗近体,气局阔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可及处,尤在错纵任意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斯是凌轹千古。*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10),第150页。胡云翼亦指出:“杜甫能够在十分板滞的律诗里面,随意打发他那歌哭惊喜的感情,毫无束缚,这是别的杜甫所不能的。”见胡云翼:《唐诗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0页。吕正惠先生指出,清人李因笃发现,杜甫七律一三五七末字上去入三声必隔而用之,如《秋兴八首(其一)》的不押韵的三、五、七末字,分别为:涌(上)、泪(去)、尺(入),便是上去入三声递用,全不重复。朱彝尊以默诵的方式考察了杜甫全部的七律(一百五十余首),如包括异文版本的话,几乎没有一首违反如此精细的规律。这就是杜甫对七律的创造性所在。详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3),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84页。有关杜甫七律之“诗律细”及其突破性成就,可参吕正惠:《杜甫与六朝杜甫》,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136-147页;陈文华:《杜律四声递用法试探》,见吕正惠:《唐诗论文选集》,台北:长安出版社,1985年,第271-284页。
在《秋兴八首(其八)》后又说:
怀乡恋阙吊古伤今,杜老生平具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14),第192页。
沈氏指的是杜甫的七律之典范《秋兴八首》,具体呈现了的才、学、气、格,在沈氏眼中,可谓旷古轹今,后人难以比拟。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杜甫在乱离之际仍不忘忠爱,故而得圣人“温柔敦厚”之诗旨。然而,杜甫之所以为被尊称为“诗圣”,其成就并不止于此,他还有阳开阴阖、雷动风飞的雄浑格调一面。沈氏乃结合杜诗中的这两方面,才推之为盛唐大家的。*相关论述可参陈岸峰:《沈德潜诗学研究》,山东:齐鲁书社,2011年,第110-111页。
七、总结
杜甫飘泊半生,落拓无依,白发江湖,见巫峡之枫树林而慷慨悲歌。杜甫淹留夔州,时间焦虑与疾病的危机意识令他感慨万千,在痛苦与喜悦的追忆中的内心撕扯,意识到此乃个人与李唐王朝之秋天,故而忠君爱国而有怨怼,穷愁潦倒难免绝望。在目击枫凋伤树的剎那,杜甫悲从中来,抚今追昔,议论纵横,窥意象而运斤,换羽移宫,结构幻化无穷,遂令此组诗成为集悲秋之大成,七律之冠军,堪称千古之绝调。
陈岸峰(1975-),男,文学博士,香港大学教授(香港 999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