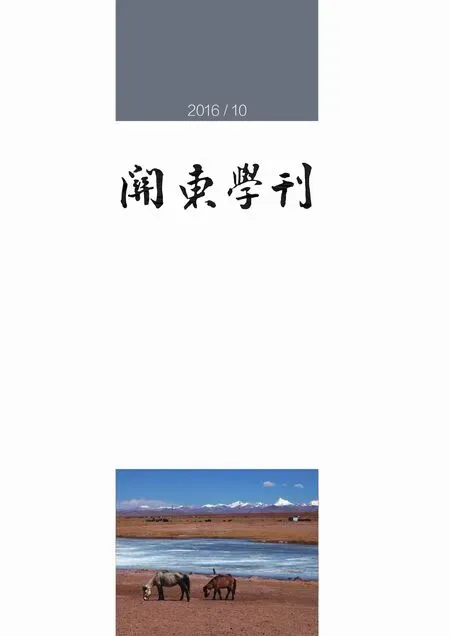文革时代的乡土中国
——李应该长篇小说《公字寨》的文革叙事
王学谦
文革时代的乡土中国
——李应该长篇小说《公字寨》的文革叙事
王学谦
即使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也总有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经历。就我们这代人——60后而言,永远也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是文革。它分明是远处的浓重的阴霾,却仿佛就在眼前,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即使是一个词语、一首歌、一个表情都能使它飞舞起来,而且,进入你的睡眠之中,让你惊醒,让你持久的恐惧。这是我读了李应该的长篇小说《公字寨》(2009)的第一感觉。
李应该是山东作家,按照现在流行的代际划分法来划分,他是50后作家,要比60后更充分地经历了“文革”。他本来更擅长戏剧创作,却又放不下小说,而放不下小说,就和他的文革经历相关。我想,那一段历史已经变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不能不感受它、体会它。据李应该回忆,在1982年的时候,就有了写《公字寨》的念头,因为忙于剧本创作不得不搁置起来。2003年的时候,终于动手,沉浸其中,2008年完成了第一部。
“文革”是当代文学一直书写的对象。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得过于狭窄的话,就很容易发现,当代文学一直在书写“文革”,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写法罢了。“地下文学”是那时的现场写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则属合理化的书写,合于清算文革的国家需要和社会大势,巴金的《随想录》是一种悲愤书写;知青文学的文革是一种悖论:知青要从文革废墟来树立起“人”的内在精神,告诉人们,我们在真诚的追求,然而,接受者却恐惧于历史经验,将这种追求看成是“后红卫兵”情结;先锋文学则掘进人性的幽暗深渊,比如余华的《一九八六年》。随后的文革叙事便以更灵活、多样的姿势呈现出来,虽然不是重心却又不时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刘醒龙的《弥天》等等,大体上是沿着余华的思路扩展开来,逼近人的内部去写文革,在外部状况与内部深渊的混合中,给人一种复杂体验,一种超越历史本质主义、启蒙本质主义的丰富感。
李应该的《公字寨》是另一种写法:从外部去写,从具体的文革人生经验去写,很质朴、很具体、很自由,也放得开,就那么缓缓地铺展着,流淌着,漫溢着,也颇有辽阔之感,像是生机勃勃的大片沼泽,到处弥漫着地方性的泥土气息。这种写法也许和他充沛的生活经验相关。他是写自己脚下的乡土,写自己熟悉的那些人和事,或者说也许是在写自己的家乡:“我铺开一张四尺红旗宣,郑重地写下了‘公字寨’三个大字贴在床头上,接着就坐下来起笔做人物梳理分析。《公字寨》的人我太熟悉了。他们就是我的叔叔大爷大哥哥大姐姐或者是我的弟弟妹妹或者是我的亲戚朋友。我和他们一同忍受饥寒交迫,一同忍受水深火热,一同过生活。得知我要写作《公字寨》,他们呼啦涌到我的面前。”*李应该:《公字寨·跋·走着的》,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是典型的乡土写实的路子,是文革中的乡土。小说分两部,第一部从“农业学大寨”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施行分田到户,第二部(2015)则写乡村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心态以及乡村风俗的变迁。李应该雄心勃勃,试图以一个村庄的生活和命运,反映大时代的状况。它属于那种散文化小说,没有精心组织的结构,也没有激烈、复杂的戏剧冲突,也不把笔墨集中在若干人物身上,只是像生活本身一样呈现乡村的生活状态,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进行下去。这种写法可能显得有点沉闷,却增强了写实色彩,有一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语言是乡土化的,是经过改造的地方语言,叙述语言和描写语言连同人物语言,全都沾着泥土,像刚刚拔出来的萝卜一样诱人。既不求精致,也不求简洁,只要一个自然,好像是山村里的井水,别有一种味道:
公社里散会时分,黄枯枯的太阳已经土埋半截了。老簸箕把行李往背上一拽搭,脚不沾地往家赶。等他从十里长的黑咕隆咚的大山沟里冒出汗津津的瘦头来,已经过了晚上饭时了……
黑水潭很怪,清清白白的山泉水只要流进去,立刻就会变成了黑水。从黑水潭里把黑水舀出来,立刻就会变成白水。黑水潭的水虽说黑如烟墨,但是,水波中闪动白白的银光,就像满天的星星。
当然,大量的“文革”语言更是不可忽视的。这种语言安放在乡土语言之中,形成一种骇人的张力。我相信,只要阅读《公字寨》都不会轻易放过那些密集的文革语言,那些被农民们随意表达出来的或者被作者叙述出来的文革语言,释放着陌生而熟悉的信息。可以想象,世世代代按照乡土习俗生活的人们,一直在说着家乡话的人们,却必须接受来自意识形态核心的官方权威语言,它是那样有力而蛮横,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就像一块巨大的陨石毫不含糊地砸入山村人的语言土地,然后,山村的人们就要学会它,膜拜它,从而使乡土语言改变了味道。许多人感慨说,我们的语言被污染了,其实,语言从来就不是封闭在逻辑真空里,而是敞开的,语言即是生活,语言就是世界。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正如每个时代人们都在生活一样。从语言中最能感受社会的脉动和人性状态。李应该似乎也格外注重这种文革语言的力量,以至于将它作为作品的小标题:“人换思想地换装”、“狠斗‘私’字一闪念”,“公……公的个‘公’”,这种文革官方权威语言像细胞一样遍布作品全身,格外醒目,从而给人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感: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
路线斗争天天讲,阶级斗争天天抓,高举红旗学大寨,村村建成新大寨,打破中游争上游。
不能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不能放松了抓阶级斗争这根弦。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阶级斗争一时一刻也不敢放松。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要想建成江南鱼米乡,一定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要以你为榜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挖出一个破坏共产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抓住纲,抓住线,大批判,促大干,三年建成大寨县。
还有一些名词:“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赤脚医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粮票”“布票”“革委会”“铁姑娘”等等,还有“王文革”“胡文革”等等人物的名字。当这些主流语言与乡土语言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让人感到恐惧,因为这意味着文革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每一处地方,人的每个汗毛孔。
“公字寨”的生活反映出“文革”时代的乡土生活的基本特征:农民生活是怎样在国家权威的感召、命令下进行史无前例的“革命”。“革命”的关键是改变生活,改变人,祛除“传统性”“地方性”习惯和“个人”私欲,让生活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统一在“革命”的旗帜之下,让所有人都如同一个“革命”机器的零件。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大战狼窝沟、不同派系之间的武斗、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批斗会等等,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那是个火爆而热烈的年代,尽管人们饥寒交迫,却精神振奋,充满着狂热的激情和自豪感,仿佛已经站在了共产主义的大门前。但是,我以为,最有意味的却是日常生活里的“革命”,这种“革命”更能让人感受到乡村社会的世态人心,也能够更切实地感到“文革”文化是怎样一点一滴地渗透在人心之中。
尽管“公字寨”的人们贫穷乃至饥寒交迫,但是“革命”依然无所不在。我们从一些细节上就能感受到乡村的极度贫困,比如,过春节的时候,乡村所能够获得的物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人们似乎觉得生活就应该如此或本来如此,这种氛围很容易让人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里的人们,而且丝毫不影响乡村的革命热情。乡村的春节,虽然经历人民公社化,却依然保留着一些乡土性传统习俗,“山上寨过年有个独特的传统,家家户户不贴对子,而是在门上挂辣椒子。一串一串的红辣椒,把个草门子挂得满满当当,一直过了正月十五才摘下来,也不知从哪一辈老爷爷行下的行仪。”今年过年却家家户户贴对子。村里的文化人卜立言以往背诵的对仗文字,诸如“祖德振千秋大业,宗功启百代文武”“天与三台并,儒开百代宗”等等,改换成“贫下中农千秋大业,文化革命百代文明”“闲寻野寺听语录歌,特酌山醪读红宝书”“斗私批修三台并,大公无私百代宗”等。杀年猪体现出革命性的仪式和等级秩序:杀猪前,“广大贫下中农们感激着毛主席的关怀,没有毛主席的关怀哪里会有这么肥的大花猪?大桂桂把胳膊一抡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一齐呼喊起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社员们分猪肉,“每人能分四两净肉,猪血每人又分了三两多。”“地富反坏右每人只给三两猪血。”骨头煮成汤分给每家每户。根原由于出身中农,性格孤僻内向,他喜欢笛子,躲在角落里吹笛子既是他苦闷情绪的排解,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对大时代的抗拒,然而,买笛子的愿望却使他遭受更大的折磨。为了能买到二角八分钱一只的笛子,他铤而走险去黑市儿倒卖布票,结果被发现,遭到毒打。村里成立“无人管理门市部”,被认为是“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辉”。这既是“无私”的标榜,它表明公字寨经过革命已经朝向共产主义迈开了步伐,也是压制人欲的巨大磐石,还是窥测、检测人欲的实验室。极度贫困中乡民们对于门市里少得可怜的商品——主要是盐,争相显示出自己的“大公无私”,经过一段时间的营业,盘点后居然涨了“三两盐”,于是,围绕着这“三两盐”展开讨论,县委宣传部长胡文革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说:“这是三两盐吗?不!它不是三两盐,它是颗颗珍珠。不!它比珍珠更可贵。三两盐,粒粒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然而,再过一段时间,却亏了“三两盐”,胡文革又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的疯狂进攻。农民大地瓜用女儿的彩礼钱购买了一台缝纫机,从此就遭受村人的白眼,被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被怀疑偷了门市里的盐,遭到审讯、软禁,由于害怕政治问题——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抽烟,就只好交代贪污的经济问题。他家的缝纫机作为退赔物资抬到了大队里。事实上,是根原偷了门市里的盐。大桂桂本来爱着根原,但是自从知道了根原偷盐以后,就从心底恨起了根原。在批判大会上,二桂桂用梧桐树叶给根原送水喝,大桂桂却将梧桐树叶打掉在地。根原与大桂桂、二桂桂之间的爱情关系是小说中处理得比较复杂的人物关系。大桂桂尽管爱着根原,但是她的爱并不会突破政治的底线,而二桂桂的爱却超越了政治的底线,这里折射出人心的丰富性,即使是最严苛的年代,人们的内心仍然有一点温暖、柔软的情感。如果小说的人物性格再饱满一些,对文革的叙述则会更加深刻一些。
总之,“文革”作为“文化”革命,它的各种方式和行为,不过是铲除“个人”的存在。它的目标是让人成为某种特别的人,既能服从一切“最高指示”,又能勤奋劳动。这种对“人”管制、规范和教育,尽管表面上有些新样式,但是,其最本质的地方就是消灭“个人”,和“存天理,灭人欲”是完全一致的,其背后是悠久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
在“文革”结束以后,老簸箕却仍然沉浸在“文革”中。他痛哭流涕地反对分田到户,“王文革以前多么王文革?如今也说分田到户好,在大会上公开号召分田到户。东山村是全公社第一个宣布共产主义的村庄,而今又是第一个带头实行分田到户。修正了,修正了,都修正了。革命革了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他娘的,什么社会。”当然,无论他如何反对,“文革”总是结束了,但是,这让我们不得不认为,历史的某些种子未必一定会死亡,它总是潜藏在时间的土壤里和人心的深处,寻找萌发的机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很难理解中国历史的循环重复。
王学谦(1962-),男,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