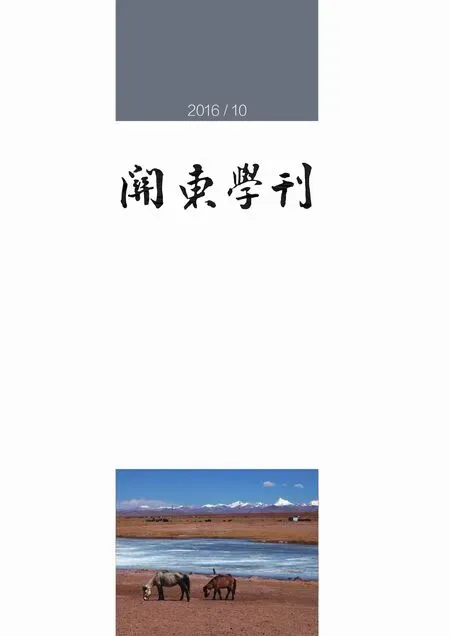看,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年代
——读李应该长篇小说《公字寨》
郭 帅
看,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年代
——读李应该长篇小说《公字寨》
郭 帅
李应该的长篇小说《公字寨》(第一部),十分生动地表现了乡村对革命的包容,因而是一部描写乡土中国风景的小说。《公字寨》表现的不是革命史,而是乡村生活史。它当然流露出了对革命历史的反思和批判,但也同样流露出了对革命历史的乡土中国的同情和理解。这种情感与价值向度,是这部小说与众多反思小说的不同之处。
《公字寨》;李应该;反思文学;乡土中国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文学借着“新时期文学”之名,开始了另一种叙述。“新时期”的“新”,本身包含着对于“旧”的排斥。但是,何谓“旧”?我们常常语焉不详或不敢详。显然,“新时期”文学是对照之前文学阶段而言的。对于1949年来的中国文学,“新时期”的文学史渐渐给出一个固定的名称: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表面上看,这是非常中性化的临时性命名,但是,在“新时期”这种热情的命名的衬托下,这种中性命名就在有形无形中,透出当代文学史家们的难言之隐。
或者可以说,这种“十七年文学”命名法,本身就是一个价值悬置的文学史操作。“新时期文学”的命名法,更是一种十分含混的文学史障眼法,无限的“新时期”与无限的“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凸显当代文学自我定位的尴尬。当我们把这两种命名所指涉的历史时段缝合起来,组成“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我们会非常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裂痕乃至裂口。可惜的是,我们却始终无法至少在文学史命名上,将我们对于文学史的态度舒展为自由的想象和清晰的指认。撇除众所周知的外因,缺乏具有穿透性的作品,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在这种“新时期”的文学史焦虑之下,“文革”以来的一切当代文学创作,大都逸不出“反思文学”的边界。不惟1980年代,无论对于“革命”的新历史主义表述,还是对文化的“寻根”,抑或不断翻新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乃至消费主义写作,都至少在可阐释层面共享着“反思”文学所具有的对抗性。也可以说,我们今天仍然处在“反思文学”的文学时代。
在这样一种略显诚实而保守的文学史估价下,来看《公字寨》式的文学创作,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苦心以及这部作品这几年所受到的冷遇。《公字寨》的诞生,当然是作者对个人经验的重演,但字里行间溢出来的某些深沉意味还是能使我们嗅到它的理性气息。因为,我们对这种气息实在太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已经熟悉到麻木的所谓呼唤人性、反思历史、暴露黑暗、批判极左的“反思文学”!似乎对当今任何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我们都能操起“反思文学”的评价话语和理性逻辑去接受和肯定。
这暴露了作为读者和批评者的我们,接近一部历史题材作品的能力和途径问题。在今天,是到了产生甚至早该产生《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式的作品的时候了。然而我们的文学史却依然在纠缠《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芙蓉镇》式的作品,纠缠那些作家用尽心思显摆出来的批判力度和反思深度。难道不可以说,我们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审美力和想象力,被元文学史非常隐蔽地规训了吗?所以当我们遇到《公字寨》式的作品时,甚至会为它感到惊讶,惊讶为什么如此一部作品,我们迟至今天才看到它,而且是在一个主攻戏剧的艺术家那里看到它。
从这个角度说,《公字寨》最大的不同,就是作者的动机与态度。作者李应该不是盯着当代文学史在写作,不是就着不可一世的批评家们荒诞的口味在推敲《公字寨》。尽管我们也难以定位《公字寨》的风格“是什么”,但是它明显的“不是什么”,却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这部作品的入口。
这部作品将不是文学史的宠儿。即便小说中常见批判的锐角,但是它的着力点,并不在对历史和政治的批判。相反,它对革命历史处处体现出十分矛盾的感情。这一点,仅从《公字寨》中的各类人物身上就可看的分明了。
小说中老簸箕和大桂桂两个人,是“革命”的化身。老簸箕是公字寨的领导人,理应为公字寨的发展高瞻远瞩。假如《公字寨》要挑出一个人来承担反思革命历史的笔墨,老簸箕绝对是第一人选,因而也完全可以将历史的愤怒向他倾泻。作者也确实把老簸箕置于了批判的位置,小说在写到整治涉嫌偷公字寨无人门市部半斤盐的村民梭猴子时,见了血:
“反复了几遍,就把老簸箕反复火了。老簸箕一挥手,两个民兵一个饿虎扑食就把梭猴子按倒在地,抡起枪托子就打,鲜血立刻就从梭猴子脸上流下来。梭猴子抱住头在地上翻滚着,撕心裂肺地嚎叫也就随着枪托子落下的节奏向公字寨的角角落落传播开去……梭猴子大叫了一阵子,渐渐地没有声音了,枪托子像是打在乱草垛上。没劲,真没劲。……老簸箕又一挥手,一条大肉缝里低沉而有力地崩出一句话:‘和党耍心眼子,绝无好下场!’话中飘舞着得胜的大红旗,而且还透着一股逼人的杀气。”*李应该:《公字寨》,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下引该文,仅随文标注页码。
这是小说为数不多地正面写到打与杀的段落,它塑造这种基层革命干部,与一般的反思小说没有太大的不同。小说写到中农青年根原为了从老簸箕手里得到一纸证明从而去城里打工,把家里珍藏的唯一一瓶兰陵大曲送给老簸箕,以求高抬贵手,谁知老簸箕“从锅台上摸过酒瓶,一扬手扔到大街上了,酒瓶子摔得粉碎”。根原心疼这瓶酒,更气愤老簸箕的无情:“老簸箕,你等着吧,别看你是个铁打的,我一口就能咬断你的胳膊!”然而,隔了一天,事情起了变化:
“第二天根原回到家,一步跨进门,姐姐喜盈盈地迎上来,手里拿着两张证明信举到根原面前。姐姐告诉根原,信是老簸箕亲自送过来的,老簸箕让我告诉你,有啥事办啥事,不要搞糖衣炮弹。他还嘱咐你,不要辜负了人民的期望,不要给公字寨丢了脸。”(第136页)
老簸箕摔碎了根原送的酒,却把根原需要的证明信亲自送了来,说明根原轻视了乃至根本不相信老簸箕的革命性,以致于反复追问“真是老簸箕亲自送来的?”然而,不能过度阐释这个情节,不能认为老簸箕也有浓郁的乡情和温暖的人性。老簸箕之所以拒绝了大曲酒的贿赂却又给根原开了证明,是出于革命理性的要求,与残忍地惩罚梭猴子一样,在革命道义之外没有剩余的情感。这一点,在《誓死了》一章最为明显,“文革”结束要分田到户,老簸箕无法接受:
“‘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可丢。’老簸箕一边说,一边把破褂子撕开,露出了铁锈般的黑肚皮。他从锅台上迅速摸过一把菜刀,照准铁锈般的黑肚皮呱唧砍了下去,一团灰呼呼的肠子哗啦滚了出来。老簸箕高举着菜刀,哭咧咧地大声喊着:‘我年丰年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不分田到户,绝不资本主义,誓死了!坚决誓死了!’”(第278页)
在一般人看来,作者的这个描写可能有点夸张,有些用力过猛。但在我看来,实在是非常贴的。老簸箕这种人,他的情感系统已经完全被革命填满,他所有的价值就是革命本身的价值,他当然可以笑可以哭可以爱也可以打杀,可以表现出类似乡情的温柔,流现出疑似人性的光斑,但这些乡情人情,都被包括进他的革命情感系统中,是革命情感系统的一部分,是被革命所允许的情感形式。所以,当革命结束时,老簸箕的情感系统当然要彻底崩溃乃至粉碎,如果不崩溃就不能说明老簸箕革命性的纯粹。老簸箕的挥刀剖腹,不啻为对“革命结束”的拒绝。作者安排他的求死壮举,更不啻为对这个人物的“完成”。可以看出,老簸箕在此时必然或死或疯,没有多余的选择了。作者安排这个情节,其实是在悯惜老簸箕,毕竟让他求死,比让他发疯要仁慈。
对于老簸箕这样一个人物,我并没有读出作者的批判。在同一序列的人物大桂桂身上,同样也找不到这种批判的态度,但显然,大桂桂要比老簸箕复杂一些。小说在写到大桂桂与根原的唯一的一次性爱时,小说提前进入了高潮:
“‘桂桂姐,你的……你的裤子……破了’
‘嗯,破了……’
烫人的热流烧灼着根原,大桂桂好像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肉里钻进了视死如归的怪家伙,她好像也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感觉心里很高兴。她摩挲着根原,就感觉摩挲着那支美妙的笛子。就像山泉流,就像石头滚,滴流滴流真好听。‘根原,你真好。’大桂桂说。
烫人的狂流狂滚了一阵子,随着莽莽的夜色流走了。根原像一个孩子,软软地蜷曲在大桂桂的怀里。
‘桂桂姐,我要好好向你学习。我的私心杂念为什么老是难除掉?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要狠斗私字一念闪,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时时斗。’
‘……我要向你狠斗私字一闪念,以后保证不闹情绪,不要私心杂念,再也不能偷盐了。’
‘什么?是你偷了门市部的盐?’大桂桂忽地从地上翻身爬起来。”(第178页)
读到这个情节,我想到了《1984》中,乔治·奥威尔安排温斯顿接到茱莉亚的纸条终于展开后发现上面写着“我爱你”的这个不朽的情节。《公字寨》描写中农子女根原与八代贫农团书记大桂桂的性爱体验,连续使用了小说中十分罕见的比喻句,性爱场景虽不是特别朦胧诱人,但已足以为下面的反转做铺垫。两个成分不同的男女在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性体验之后,还未从高潮体验中平息,就开始了狠斗私心杂念的探讨。根原因为太相信大桂桂而说出他偷了门市部半斤盐的事实,谁料,几分钟前的热烈情人马上变成了无情的专政者。作者将这个情节写的不动声色,十分巧妙:根原,包括读者们,原以为通过一场情不自禁的性爱使大桂桂至少暂时地消退了革命狂热,还原几分哪怕一分少女的羞涩,谁知,少女脸上的潮红还未退去便瞬时转为无私铁面,原来是根原和读者们自作多情低估了大桂桂的革命热情的烈度。这个情节,是《公字寨》的灵魂。
当“文革”结束,分田到户时,大桂桂并没有像老簸箕一样走向毁灭。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拿捏非常到位,大桂桂确实不应该毁灭,因为在革命理性之外,她还是别有心肠的,她至少与根原完成了一次野合,而老簸箕呢,当他逮住往裤裆里藏蔬菜的少妇大碾盘,当大碾盘把裤子褪下来跪下哀求老簸箕时,作者都没有安排老簸箕往大碾盘的裤裆里看一眼!
大桂桂与根原野合后,秘密地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被大桂桂扔在路上,却被她娘抱回家去,当做了她弟弟。换做别的作家,此处要挖空心思浓墨重彩地写,他们知道,批评家最喜欢分析和称赞这种桥段了。《公字寨》没有这么做,这个孩子也没有得到过多的笔墨,也没有写到大桂桂对这个孩子不一般的感情。小说为了让大桂桂与老簸箕稍稍拉开距离,特意为大桂桂配了一个彰显姐妹情的人物瘫巴花花。即使这样安排,我们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对于大桂桂这个人物,作者是顺着老簸箕往下写的:大桂桂不是比普通村民更有革命性,而是比老簸箕更多一点人情味。本质上,大桂桂也就和老簸箕没有区别了。
但是,在老簸箕和大桂桂这类人物身上,作者没有专意地诉诸批判的火力。写他们因为革命而展开冬天般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与写他们因为革命而别具春天般温暖的阶级关怀,是笔墨相当平分秋色的。而且,作者的笔锋,似乎过多地深入到这两个人的角色内涵中,以致于即使想对这二人实施批判,却难以形成有效的距离。
站在老簸箕大桂桂对面的,是根原。根原是富裕中农的孩子,而且,是公字寨唯一的中学生,是老簸箕大桂桂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公字寨》若是展开对革命年代的反思和批判,那么,小知识分子根原,应该是承担这种反思和批判责任最为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我们太熟悉了:秦书田、章永璘、钟亦成……一般的小说,先把这类知识分子角色定制为受难者,为他们匹配残忍的阶级斗争行刑者,然后笔墨集中于对知识分子从身体到心理的受难层次,中间当然可以以一个同情人物作为缓和,最终,革命结束,知识分子重获新生,行刑者忏悔,知识分子宽恕。总而言之,知识分子既是苦难的承受者,又是对苦难的宽恕者。然而,《公字寨》却十分不一样,小说开头便写到海归博士大右派孟瞎子的心理,似乎已经预示着《公字寨》对革命中小知识分子身份的颠覆:
“老簸箕一边骂,一边背过身解开腰带,伸手把裤裆里的小指头拽了出来。他抓起孟瞎子鲜血淋淋的手,一泡尿照准血口子就滋了过去。老簸箕系紧腰带,骂骂咧咧地嘟哝着:‘好了。尿能消毒,发不了。他娘的,废物!好好瞪起二饼来,别再砍了手。’
孟瞎子鼻孔里‘嗯’了一声答应着,低头看看被一泡臊尿浸润过的手,又把鼻子纵了纵。手上一阵温热,心头也一阵温热。老簸箕的声声斥骂就像一碗热乎乎的糊嘟汤,不但不伤人心,反倒使人心里暖烘烘的。孟瞎子好像忒喜欢听老簸箕骂人。”(第5页)
老簸箕一泡热乎乎的尿,撒在孟博士的伤口上,使他心里异常温暖。看到这样的情节,一些有洁癖的知识分子应该会受不了吧。可是孟瞎子偏偏感动,他又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感动,“他欣赏老簸箕,欣赏山上寨的每一个同类,可他不明白到底欣赏了什么”。若说孟瞎子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是给知识分子丢人的角色,是被阶级斗争洗脑的行尸走肉,也不合适:从小说写他对老簸箕一泡尿“鼻子纵了纵”“一阵温热”“热乎乎的糊嘟汤”“暖烘烘”的十分具体细致又亲切的感官反映上,我们知道,孟瞎子是相当清醒而敏感的,他当然可以厌恶这泡尿,但他确实被老簸箕的尿感动了。这种感情的发生,孟瞎子无疑是主动方。
根原的性格更加复杂,然而,他也不是一个受难知识分子形象,甚至不是一个可以获得同情的人物,更无法作为反思批判的意义承担者。根原身上既充斥着对革命论理的反抗,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对革命理性的认同。他被作者塑造为一个天然的受难者,也被赋予反抗的权力和机会,但是,作者为他的反抗设置了价值模糊的判断。
根原意欲摆脱他天生的中农出身——这绝不是一般人的想法。于是,根原一张大字报揭发了自己的爹在买盐时的一个小聪明,在他为了与家庭划清界限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传来了批斗他爹的吼声:
“‘谁贪图小便宜就叫他灭亡!’
随着一阵高过一阵的口号声,根原的体温在下降,心,也开始发凉。根原看见,吹吹把爹的胳膊越别越高,爹的脑袋越压越低,爹的脸上滴下大颗大颗的汗珠。根原不敢看那汗珠,那汗珠好像是自己心里的点点鲜血。先前还感觉爹是那么可恶,现在又感觉爹是那么可怜。爹的那点私心,为什么要给揭发出来?难道就为了证明自己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就为了自己进步入团?”(第82页)
根原以揭发自己亲爹为代价,意图摆脱自己家庭出身争取进步。这不是受难,而是心理的变态,是变相施暴。根原通过揭发父亲摆脱出身不成,便希望通过婚姻来实现:
“他时常想,能找个大桂桂这样的党员媳妇该多好啊!找个党员媳妇,能给自己黑五类家庭带来好运。”(第141页)
当他来到城里朋友的家里,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朋友的党员妈妈:“他感觉,良明亮的妈妈,就是自己的妈妈,他多么羡慕有这样的城里人妈妈,多么羡慕有这样的党员妈妈呀!”可见,在根原的头脑中,“血统”与“出身”成为他的精神大患。但是,根原喜欢党员大桂桂和党员妈妈,并不是向往革命和崇拜革命者,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目的。小说写到根原为了给父亲复仇,他偷了无人门市部的盐,而使梭猴子当了替罪羊被打个半死。当他爹严厉指责根原时,小说没有只言片语写到根原的表情,他毫不以梭猴子代他受难而有一丝愧疚,更不承认是他偷了盐。根原与大桂桂发生了肉体关系,以为和大桂桂已经身心交融的时候,他迅速地将话题转到询问大桂桂如何改造思想尽快入团上。也是在与团支书大桂桂鱼水之欢之后,他才第一次说出自己偷盐的秘密。根原的生命力和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资本,就这样被革命的话语所绑架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根原,他的追求进步与入团,并不是为了革命事业,也不是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尊,他的反抗是随时性的行为,是一种本能的自卫和复仇,有时带有本能的善,有时也不免本能的恶。《公字寨》所塑造的根原,全然不是一个常规革命叙事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让人爱不起来,更恨不起来,怜悯他吧常常觉得他是自作自受,批判他吧同时也会体察出他的痛苦挣扎。
《公字寨》充满了这种使人又爱又恨的人。或者说,共产主义公字寨里,没有一个“大好人”,也没有一个“大坏人”,都是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中不溜的人。
回到进入《公字寨》的入口,我们会发现,《公字寨》的确不属于文学史。它没有“反思文学”所擅长使用的隐喻手法,更没有那种常常流于煽动的抒情桥段,它是如此的热闹又如此的冷静,保持着一个老说书人般对故事的用意节制。《公字寨》里,没有对光辉人性的歌颂,没有对邪恶人性的鞭挞,没有抑制不住的对革命年代的反思,也没有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怀与倾诉。这种“没有”,决定了《公字寨》不是一部精心于虚构的作品,我想,小说的情节很可能来自作者李应该的亲身体验或者扎实的走访,因而具有实证般的准确。不过,作者对这些中不溜的公字寨人的情感也是较为矛盾的:我们能看出他的一闪一闪的嘲讽和批判,但这建立在作者的回忆和今天的时空中,是“痛定之后,徐徐食之”;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作者十分投入的进入了公字寨的当时,作为公字寨中的一员重新经过了那个时代和生活,因而,他的情感中又悄悄地透出几分留恋几分理解和几分不舍。作者有意使用鲁东南方言,来讲述公字寨的故事。这种方言非同一般,很有渲染力,适合公字寨人咋咋呼呼又带有天然幽默感的生活风格,当作者抛弃了普通白话而选择方言时,就把他自己裹进了他的故事中,“语言是存在之家”,公字寨的故事在这种方言的包装下,变得活灵活现,在语言的欢恣中,作者把他对公字寨的美好感情给露了出来。这种投入,让作者失去了评判的距离。
所以这不是我们常见的反思文学,这是一部描写乡土中国风景的小说,不是革命征服了乡村,而是乡村包容了革命:它既能包容革命,也能包容改革开放,能包容老簸箕,包容海归博士,也能包容根原,它能包容一切。可以说,《公字寨》表现的不是革命史,而是乡村生活史。如果我们说它流露出了对革命历史的反思和批判,那么,它同样流露出对革命历史的乡土中国的同情和理解。显然,这种价值向度,是不被今天的精英知识分子所欣赏的,他们希望《公字寨》能发出沉痛的反思和批判火力,能纯粹彻底。这种趣味,实在是不仅虚妄,而且滑稽的,作为一场发生在广阔中国时空中的革命,没有哪个人是纯粹的,受难者与行刑者,都不是单向度的人。而且,十年实在漫长,热烈的革命已经在日复一日中蜕化为日常生活。所以,在革命中走入无限迷狂的一端,与在革命后的想象中走向无限清醒的一端,同样可疑:没有彻底疯狂的人,也没有彻底清醒的人,没有天使,也没有无一不爽的圣人,都是公字寨中这般中不溜的人,和他们天天在琢磨的中不溜的事。
这就是《公字寨》的价值,它不是强行地诉诸反思和批判,不是有意结构自己的意义空间,反而以尽力摒除隐喻的语言把革命历史自然地呈现出来,读者啊,你愿意反思你就反思,你愿意批判你就批判,或者兼而有之或者你干脆怀念公字寨的火红岁月,你都能在小说中找到诉诸。从这一点上,我们能看到《公字寨》对诸多“反思文学”的超越:何必苦苦经营用意虚构?只要平心静气地把过往时空中的生活本身讲出来,就能让一切虚假战栗不安。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创新计划“新近解密档案在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中的应用”(2016002)。
郭帅(1988-),男,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