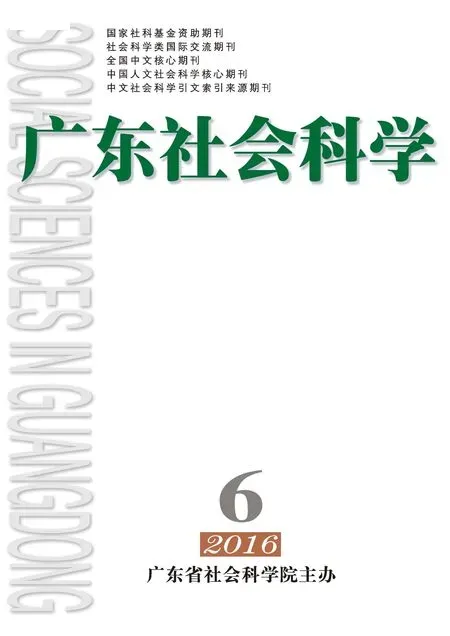“九一八”国难与东北抗战文学中的长篇小说
逄增玉
“九一八”国难与东北抗战文学中的长篇小说
逄增玉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性事件,此事件曾引起左翼文学的反响,但东北作家最先以具体感性的文学作品揭橥国难文学及抗战文学的大纛,显示出左翼反帝文学的实绩。长篇小说是东北作家写作的抗战文学中影响最大的部分,抗战中前期,其创作主要聚焦于国难中的人民悲愤与壮烈抗战,并各有共名主题下的叙事视角;抗战后期,则较普遍出现一种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反思、批判或褒扬的倾向,既从民族病疴角度探究屡遭国难的内因,也发掘弘扬东北人民抗战雄风的历史因子,还对战时大后方的社会世相予以批判性描绘,从历史与现实双重视角中思考战争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这是一批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东北 抗战文学 长篇小说
一
“九一八”事变肇始的中国抗战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重大意义,还没有成为普遍的共识——国内现代史一般都把1937年“七七事变”作为抗战的开始。甚至由于信息传播的有限性、大多数国民的知识和受教育程度的有限性、以及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的民族国家意识的相对薄弱,“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部分百姓对这场国难的认识还是有限的,鲁迅在此后为东北作家萧军小说写的序言里,就提到距东北最近的京津一带的部分民众,对来自东北的流亡百姓存在一定的拒斥,不愿意租房子给这些“亡省奴”。①
在这种情形下,最感到痛苦的,自然是陷于铁蹄之下的东北人民,以及作为人民思想情绪“感应的神经”的东北作家。此时的东北作家处于两种环境中:一种是在北满哈尔滨从事东北左翼文艺运动的北满作家群,即萧军、萧红、罗锋、白朗、舒群、金剑啸等人。面对故土沦陷的巨大灾难,冲天的悲愤和报国反抗之情自然勃发,萧军就一度打算到磐石一带去参加抗日义勇军。投笔从戎不成,他们就或者以自己的工作实际从事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如舒群等人实际是在职业掩护下为中共和共产国际进行地下斗争,或者开始以笔墨为武器,进行抗日反帝的文学创作,如萧军和萧红着手《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写作,同时从事左翼文学和戏剧运动。另一种是“九一八”事变时在上海、北平等地求学同时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东北青年学生,如身在上海与北平的李辉英、端木蕻良等人。最早以“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就是身在上海的李辉英。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三个多月后,就在1932年1月20日的左联刊物《北斗》上发表了小说《最后一课》,是年的3至5月间,又写作长篇小说《万宝山》,于1933年3月出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东北抗战文学、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最先出现的长篇小说,自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上海左翼文坛在“左联”决议中提倡“抓紧反对帝国主义的题材”的时代号召及其弥漫于整个左翼文坛的反帝思潮构成的语境,故土沦陷使自己成为最早的流亡者,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情与故乡情交织的情感旋律,是使得李辉英先于萧军等人最早写出东北抗日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
随着占领东北的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主义高压统治的日益严酷,在北满从事左翼文艺和抗日文学写作的哈尔滨左翼作家,于1934年前后被迫陆续流亡到关内青岛、上海和北平等地。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的中篇《生死场》等描写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人民苦难中崛起的小说,于1935年出版。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序言、小说内容的鲜活与独特,不仅在左翼文坛引起重大反响,也受到日益感受到民族国家危机的关内读者的欢迎。与此同时,舒群、罗锋等人也发表了《没有祖国的孩子》、《呼兰河边》、《第七个坑》等小说,马加出版了中篇小说《登基前后》,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成为左翼文坛瞩目的焦点。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东北作家近作集》,标志着集体性、流派性的东北作家得到文坛与社会的公认。
身在上海的东北作家反映东北抗日作品的饮誉文坛和鲁迅推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实质形成一种“召唤结构”和效应,对所有东北流亡青年和作家都发出了写作抗日文学作品的召唤:用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描绘的广袤的黑土地上的人民苦难和奋起抗争的新的题材与主题,丰富左翼文学的表现领域,满足广大人民由国难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引发的阅读期待和时代需求,鼓舞与振奋民族精神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此之际,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就参加北平左翼文艺运动的端木蕻良,作为东北流亡青年的一员,在故乡沦陷和北平左翼文艺运动受挫期间,以21岁的年龄开始着手宏大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写作。这部长篇小说辗转出版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但在此之前,受到上海东北作家在鲁迅推荐下取得成功的模式的影响,端木蕻良也给鲁迅写信,并开始写作《大地的海》等一批反映东北抗日军民生活的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类似的情形还有年轻的、来自东北中朝边境地区的青年作家骆宾基。在时代共振、共鸣和鲁迅与茅盾等左翼文学大师的推荐与引领下,骆宾基也创作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于是,一批东北作家写作的东北抗日反帝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文坛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抗战文学经典。截止1945年抗战胜利,东北作家在抗战前、抗战爆发后、抗战中后期,都陆续有长篇小说问世,在东北抗战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为中国的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做出了独特的、意义重大的贡献。
二
东北抗战文艺暨抗战长篇小说,应该包含两重含义:第一,不论是东北籍还是非东北籍作家写作的以东北抗战为背景和题材的长篇宏制;第二,东北作家写作的以东北或整个中国的抗战为背景和题材的小说。这其中,东北籍作家写作的作品,放到整个抗战文学的格局中来看,都属于佼佼者;而他们创作的以东北和中国抗战为题材和内容的长篇,在他们的全部抗战时期写作的小说中,又是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部分。这些小说虽然具体的描写对象不同,但都从各自的视角对东北沦陷后的现实社会,作了不同层次的剖视与叙事。它们整合起来,就构成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东北以及全国抗战宏图的立体的时代画卷。
如上所述,李辉英是最早发表聚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创痛的作家,其1933年出版的小说《万宝山》,是根据真实事件创作的半纪实、半虚构的“事件体”小说。万宝山事件是日本人在“九一八”事件前策划的一系列为侵略东北制造借口的事件之一,并借万宝山事件挑拨同属东亚被压迫民族的中朝之间的民族矛盾,把自己装扮成是被他们全面殖民的朝鲜民族的保护者、东亚民族矛盾的协调者和恩主。由于李辉英在1931年以前就入关读书、1934年才得以回乡探亲,此后又离开故乡,所以他只能根据各种新闻报道的资料,加上自己以前的故乡体验,来谋篇布局。因此长篇小说《万宝山》基本上属于纪实体小说,只是把群体性的农民个体化了,写出了具体的中国的农民为了保卫家园掀起的斗争,矛头并非朝鲜移民,而是背后的指使者和阴谋的策划者即蓄谋侵略中国的日本,并对汉奸型人物郝永德进行了从行为到心里的具体刻画。事件性、过程性、阴谋性和反日抗日的主题,是小说的最大特色,相比之下,中国农民个体与群体的形象和心理,情节与结构的安排,事件中寓含的政治与民族矛盾的深因,场面和气氛的营造,还显得简单,也显示出年轻的李辉英尚难以娴熟驾驭长篇小说。不过,相对于“九一八”事件后关内左翼作家艾芜等人写作的东北抗日题材小说《咆哮的许家屯》等,李辉英由于有故乡生活的经验,所以对于东北乡村环境与景物的描绘,人物乡土性语言和心理风俗的把握,还是比较真实和“入色”的,不像从未到过东北的艾芜那样把东北农民的名字叫作“幺娃子”——彼时东北乡村农民及其风俗不会有这样四川化的名字,也避免了把抗日主题塞进一个不真实描写的环境硬性“突出”概念化叙事的弊端。
李辉英的另一部写东北抗战的长篇小说《松花江上》,出版于1945年1月,距抗战胜利已经为期不远。此时故土沦陷已经14年,李辉英也从青年进入中年,但对家乡的思念、对沦陷中的同胞的生死挣扎与抗争的关注,从未止息,相反,在流亡的处境中,那份故乡情与民族情交融的流亡者的心理情感世界,更为丰富而浓烈。《松花江上》就是这种心理的投射和外露。这部长篇小说在极其浓郁的东北自然、土地和乡村构成的风情中,不再聚焦于“事件”及其对事件真相的揭露,也摆脱了《万宝山》的那种印象式、速写式的描写方法,而是真实地叙写了“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某乡村农民参加义勇军、组织抗日队伍的过程和过程的复杂性。在初期的东北抗战题材小说中,有把人民在民族苦难到来之际奋起反抗的心理与行为简单化、浪漫化的倾向,“苦难降临”必然地、迅速地引发人民的觉醒和起而抗争,把不同阶级、阶层、政治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程度和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的东北民众想象为同一性的“民族反抗共同体”,甚或带有民粹主义色彩。而《松花江上》难能可贵的,就在于看到和描写了生活于东北乡村的不同阶级与阶层的民众对于遭受民族敌人殖民的不同态度,对于是否奋起抗争的不尽一致的举措。小说在“父子冲突”、“阶级差异”的原型与模式中,既写了以王德仁老头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的顺民心理和对儿子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劝诱与千方百计的阻止,更着重描写了以地主乡绅和恶霸为代表的传统守旧势力对农民参加义勇军的阻挠和破坏,甚至以雇凶杀人的方式企图瓦解义勇军。而他们作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没有民族廉耻和大义,根本上还是利益的考量:担心日本人的报复,担心自己在乡村地位的动摇和瓦解,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义勇军的征粮行为已经实质上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使他们痛恨之后也“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对义勇军和民族抗日大业的破坏力量,他们做得比日本人还有过之而不及。小说对此的描写是真实、细致和充满乡土气息的,对义勇军领袖王中藩、老农民王德仁、参加义勇军的钱寡妇和傻大哥和乡村士绅人物的塑造,也是富有个性和充满立体感的,如一般文学作品那样,对老一代农民、有缺陷的农民和乡村守旧绅士人物的描写,甚至比对义勇军领袖和正面人物的描写更为个性化,对其形象、行为和心理的挖掘表现更为细腻和充满生活的质感。
更值得称道的是,李辉英在小说中固然遵循着他从30年代左翼文学继承的传统,以阶级的视角俯视和描写东北沦陷后抗日队伍崛起的复杂性与艰难性,在民族矛盾成为时代主旋律之际不忘阶级矛盾,把乡村绅士势力描写为破坏抗战和抗日队伍形成的主要“坏蛋”,一如抗战以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左翼作家的小说的叙事模式;但是在描写所谓正面形象时,李辉英继承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挥了作用,没有把抗日力量绝对化和神圣化,而是遵循真实性原则,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王德仁的儿子王中藩在回乡组织抗日义勇军时,对盼子爱子的老父亲显得薄情寡义,对乡绅和乡民的征粮行为显得蛮横和霸道,有点胡子砸窑绑票的味道,孔武有余而说服不足;钱寡妇是带着在乡村由于不守妇道遭受的歧视和屈辱、带着个人生理的与心理的欲望和不满参加义勇军的,傻大哥是带着反抗民族敌人压迫的民族道义感和在乡村出人头地的双重欲望携情妇走进抗日队伍的。小说这一方面的描写,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真实和原则,没有以流亡作家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情感把历史简单化和人民浪漫化。而这也是《松花江上》比《万宝山》更具有艺术力量的原因。
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不仅是受到鲁迅推荐后引起重大反响的东北抗战小说——30年代左翼文坛发生激烈论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派,都把这部小说作为证明自己主张具有政治正确性的标志;而且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主潮里,第一次描写中国军民在沦陷的土地上正面的、大规模的与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战斗的战争小说,从而把五四新文学的反帝主题和30年代左联停留于主张和口号的反帝要求,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具体化和形象化了;同时,也是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和旗帜,甚至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最早的果实。因此,该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这部小说在同样具有浓郁东北地域气息的环境里,以比较粗线条的方式,表现了“九一八”事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与侵略者的战争场面,写了义勇军领袖的粗犷与成长和整个队伍的成长,参加义勇军的知识分子的软弱仁慈和在血与火的战争中的转变,写了义勇军战士与与来自早已没有祖国的朝鲜女战士的战地恋情,写了中国农民在民族敌人的强暴下觉醒和抗争的艰难历程,写了日本兵的暴行和被俘后受到的优待。值得指出的是,这部被所有人都视为中国现代最早的抗日反帝小说,其实表现了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阶级斗争和不属于抗战而属于土地革命的内容:义勇军在民族抗战压倒一切、迫切需要结成统一战线共同面对民族首要敌人的历史时刻一度犯下的失误:打土豪分财产,甚至枪毙没有对义勇军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投敌当汉奸的乡下土地主夫妇。自然,过早离开东北的萧军,没有知晓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后来下达的关于团结一切阶级、阶层力量,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共同民族敌人的指示和满洲省委会议精神,因此把“九一八”事变后初期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既进行打击民族敌人、也继续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行为,都正面的予以描写和肯定。这种政治不正确的描写固然是失误,但也给我们呈现了东北抗战初期的真实的历史状貌。小说尽管艺术上还显得比较粗糙,多是粗线条的勾勒式、场面素描式的手法,人物个性特别是义勇军领导人的个性描写还很简单,远不如对于一度软弱的知识分子和动摇不定是否参加义勇军的农民的描写,但小说真实、质朴,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东北大野粗犷壮美的地域色彩。
端木蕻良直接描写抗战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和《大江》,在东北作家写作的抗战小说中,饶有自己的视角、思考与特色。端木蕻良出身于东北科尔沁旗松辽大地上一个大地主家庭,母亲是被豪族的父亲抢婚而来的农家女儿,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说自己一出生就带有忧郁性和内向性。南开和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参加北平左联的经历,对中外哲学与文学的深厚造诣,使同样成为家国蒙难时代流亡者的端木蕻良,在聚焦和描写家乡人民铁蹄下的生活与反抗时,不仅有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浓烈情感,还总是力图把现实的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行为,放到更宽广的历史文化视野里,带有历史哲学的形而上意味,带来他推崇的长篇小说的深度与宽度。《大地的海》就是这样的抗战小说,它把家乡人民在沦陷后遭受的各种苦难和在苦难中爆发的像大海狂啸般的激烈抗争,放到农民与土地、土地与国家、民族国家时代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中蕴含的民族生存空间争夺的历史与正义等宏大视域和背景下,予以描绘与呈现,同时还把人民反抗外来敌人的壮举与历史上的抗争和神话联系起来,从而把东北大地上的农民反对日寇铲除庄稼抢修公路的武装暴动的现实意义历史化和哲学化了。这也是端木蕻良一直强调和追求的小说应该挖掘和发现生活流之下的“意义流”和“潜流”的表征。由于有这种历史文化与哲学的铺垫和氛围的营造,造成小说的厚重感和哲思色彩,相比之下,没有亲身经历而更多是间接听闻、以流亡作家的激情和“文字的流”,讴歌故乡人民反抗斗争的“热血的流”②的强烈功利目的,驱使作家写出的人民抗战的故事和场面,则较为简单和单薄,小说中的艾老爹、儿子艾来头作为大地之子的农民形象,比他们作为抗日战士的形象,更为生动和鲜活。对汉奸和敌人的描写,则难免有点概念化。《大地的海》由于有历史文化哲学的“底色”和农民与大地血肉关系的透彻与出色的描写,所以展现的农民在悲凉中并非一蹴而就的缓慢的崛起过程,为保卫土地家园而最后进行的抗争,既真实且具有了宏大与壮烈的意义。而《大江》的背景更为宏阔,时间从“九一八”事件前到1938年武汉保卫战,地域则从东北的深山老林写到北平、山西直到武汉,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中,在这样的大背景里,小说倾全力打造了一个保家卫国的抗战英雄:铁岭。小说以浓烈的诗与绘画的手法,先追溯“九一八”事件前的东北深山老林,即萨满教的气息与鱼猎生涯构成的原始洪荒环境,铁岭就是一个打猎谋生的壮汉,粗野而质朴,混沌而勇迈。是突然到来的巨大民族灾难破坏了山林的寂静和狩猎生活,迫使铁岭逃出山林逃入关内,一如东北的大批难民。他参加了军阀军队成了大兵,在北平镇压过学生,学到了兵痞的一切恶习,善恶是非、民族大义都泯灭无存。抗战的爆发和所在军队被迫参加的抗战,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血与火、生与死的磨难与锤炼,促使他的人性和民族性一起觉醒,将一己的生死苦战、流血负伤与民族生存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最后一路征战来到华中,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铁岭站在象征中华民族的长江岸畔,如神话英雄安泰挺立大地一样,深情俯视着长江,涌起了强烈的民族爱国之情,感觉到曾经是一个猎户的自己成为担负民族国家道义的战士,个人的生死安危中有着祖国的影子和希望。如此,端木蕻良“写出一个民族战斗员的成长”的创作动机,在屹立长江边的铁岭身上得以实现。在小说里,民族的灾难和随后的民族解放战争,被“神圣化”和“宗教化”了,民族苦难固然是巨大的不幸,但它使无数铁岭一样混沌蒙昧的人民走出自我生活的圈子,民族抗战使他们不断地洗去满身物质的与精神的“灰尘与血污”,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悲壮熔炉里,焚毁个体的与民族的精神负累和渣滓,粹化和造就大批的民族战士和英雄,拯救和再造新的国家与民族——这也是当时“抗战救国”与“抗战建国”的时代性主潮。因此,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国遭遇的侵略,既是民族苦难,也是民族凤凰涅磐的烈火和熔炉,苦难不止具有苦难的意义,还有超出苦难的粹化民族、再造国家的巨大意义,而这是侵略者没有想到的,也是灾难到来之际的人民和民族没有想到的,我们的人民是在苦难和战争中感悟到并越来越自觉地在熔炉中锤炼和锻造着自己,从旧世界的奴隶变为新时代的战士;也锻造着民族和国家,使其从东亚病夫成为崛起的吼狮。端木蕻良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东北农民和猎户的逃难与战争的经历和传奇,表达和寄托了他所追求的“潜流”和“哲学”及“诗学”,通过一个从农民到民族战士的“战斗员”的成长史,表现和讴歌一个民族的成长史。而这样的成长小说,不止是写实的,更是诗意的和浪漫的,是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的战争英雄曲、英雄创世神话和民族浴火重生的史诗。
受到萧军成功模式的英雄和启迪,另一位年轻的东北作家骆宾基,也在从东北流浪到北平、上海之后,在不安定的生活和流亡者心曲的驱使下,写出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小说的笔法和艺术还是稚嫩的,但其内容则表现了东北抗战的另一方面。李辉英、萧军和端木蕻良都是30年代的左翼作家,所以他们写作的东北抗战文学中的武装力量,不论是义勇军还是游击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加历史真实,是这些小说如此描写的成因。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的抗日队伍的构成是多元的,既有中共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抗日义勇军和抗联,也有隶属于原东北国民政府和组织的抗日武装,还有来自大韩民国的参战队伍和北朝鲜的民众武装。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这些抗日武装多被遮蔽于历史深层,直到九十年代出现的反映东北抗日的小说如《雪殇》等,才予以展现和叙写。而30年代的骆宾基也是左倾的青年,但他能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在《边陲线上》表现了他的故乡——吉林省珲春中朝苏交界的县城与山乡的旧国民政府的党派和职员、教师和商人,在“九一八”之后,在民族大义感召下组成抗日队伍抗击敌人。民族灾难和侵略者的力量都是巨大的,在远离祖国内地、缺少明确政治目标和人民支持的边陲山乡,这样的抗日队伍的战斗是可歌可泣的,动摇和逃离也是不可避免的,坚持下去更是极其可贵和艰难的。骆宾基的小说写出了这一面的历史真实,因此尽管年轻的骆宾基尚难以驾驭这种重大的历史和战争题材,艺术水准也未见得有多高,却为人们提供了东北抗战历史的一隅,从边陲线上的小小抗战队伍的构成与活动,展现了东北抗战历史的全貌,弥补与缝合着历史的缺失。
此外,作为东北流亡作家之一的罗锋,也在流亡岁月中继续书写沦陷故乡人民的悲歌与壮歌,左翼批评家周立波在一篇评论中曾经评价罗锋的小说多写民族敌人的残暴,③而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则不止于写敌人的残暴,更力图写出东北人民反抗一切压迫的原始而强悍的精神与力量,像端木蕻良的小说把东北大地“直立”起来一样,罗锋的小说也是借文学的形象东北人民直立起来。还有进入关内参加抗战工作的马加,在东北读大学时代就是文学青年和校园文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对故乡的沦陷同样具有切肤之痛和冲天悲愤。但是他暂时把这份感情封存起来,在抗战胜利之际写出了《滹沱河流域 》,表现华北地域的抗战故事。而对故乡沦陷前后的记忆与故乡人民的苦难与抗争的历史,则在几十年后写成了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完成了一个遭遇故土沦陷的东北流亡作家的夙愿。
三
东北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反映现实抗战宏大内容的作品,最符合一般的抗战文学定义,也是一般人认为的最有特色的东北抗战文学。但是,如果放宽抗战文学的定义,把东北流亡作家和其他作家写作的并非直接描写抗战、表面无关抗战但与抗战的时代大背景密切相关的作品,也纳入东北抗战文学的范畴,那就不仅大大拓宽了东北抗战文学的边界,也会看到更为丰富的东北抗战文学的内容与主题,会看到东北流亡作家更为复杂丰富的、与流亡者处境和心绪融为一体的创作诉求。
即如端木蕻良,他在故乡沦陷、左翼文艺运动受挫之际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非《大地的海》、《大江》那样的直接聚焦和反映抗战烽火的作品,而是描写“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农村生活生活的《科尔沁旗草原》。这部篇幅浩大、笔力遒劲又细腻、被评论家成为把“科尔沁旗草原直立”起来的大作,既是容纳了端木蕻良家族、家庭若干事迹和影子的类“家族小说”,也是东北大地百年历史变迁的史诗性小说,是中国的《百年孤独》。时年20几岁的端木蕻良以巨大的热情和如椽大笔构制的这部鸿篇巨制,追述和描写了清末来自关内的流民丁家在动荡时代的发家史,而这样的发家史伴随着欺骗、暴力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一种原始野蛮性的东北大野的阶级的分化与斗争,写了父亲的抢婚与母亲的哀怨、阶级压迫与性暴力的野蛮组合,更着重描写了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型地主丁宁——聂黑留道夫式的忏悔贵族,力图缓和阶级矛盾而进行的改良及其失败,长工大山代表的农民的觉醒即反抗阶级压迫的力量的形成。这种描写既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也受到30年代左翼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影响,但是超越了30年代左翼文学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直白性与简单性,具有了更为博大的内容。小说的最后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以胡匪老北风代表的绿林队伍和部分农民参与的攻占县城的抗争义举。至此,这部内容浩繁的长篇史诗加传奇、写实加神话的长篇小说,其功利追求昭然若揭:在东北大草原百年的历史中寻找反抗阶级和一切压迫的力量与洪流,为作者要以自己“文字的流”讴歌故乡人民反抗异族压迫的抗暴之洪流,寻找和发掘历史的源头,以证明暂时沦陷的东北大野和人民绝不会屈服,因为在那片土地和人民中蕴含着巨大的反抗压迫寻求解放和幸福的“原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下笔很早却出版于抗战以后的小说,实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早的“寻根”小说之一。而这部小说的题材和内容是中国文学少有表现的东北大野和粗犷的人民,就更给小说带来了传奇与史诗的奇特性和浓郁的地域色彩。
具有这种“寻根”意识和倾向的,绝不止端木蕻良一人。另一位著名的东北作家萧军,在写作和出版了引起巨大反响和轰动的东北抗战小说《八月的乡村》之后,也开手写作长篇小说《第三代》。这是一部艺术上比《八月的乡村》更成熟的优秀之作,在抗战前发表的第一部,即引起批评界的好评,著名学者常风曾经赞誉它是雄浑的史诗。此后,不论是在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时代,还是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的旅途和最后的定居延安时代,不论个人的婚姻、家庭还是时代与政治的动荡变迁,萧军一直执着于这部长篇,并最终完成于延安。与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不约而同的是,萧军也力图在这部长篇中把他引以为自豪的故乡“三千万无教养”的人民的生活、形象与不屈服于压迫的原始“强力”,通过他们的乡村生活、啸聚山林的生涯、离开乡村进入都市的漂泊求生以及最后的返乡,在清末至民国的外乱与内乱交加的动荡时代,在东北乡村与城市广大的时空背景中,表现东北人民从参加义和团反抗外敌、到与官家和地主豪绅势力殊死搏斗的壮烈强悍的生活与性格,在呈现东北大地壮阔雄伟的自然风貌之时,着重诗意地挖掘和放大东北人民的原始洪荒般的生活意志与斗争意志,为此,这部小说用很多篇幅描写山林胡子的绿林生涯,像古典小说《水浒》一样,胡子不但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反而是积聚反抗能量、反抗官家和地主豪绅的“义匪”和“好汉”,是受到不公平压迫的农民的避难所,也是统治阶级的敌对冤家。更令人称奇的是,小说中写到的东北妇女也巾帼不让须眉,敢恨敢爱,极端者甚至敢于进山入“匪”等待报仇。这样的人民及其生活和性格,一旦遭遇民族压迫,同样会揭竿而起殊死战斗。这就是萧军写作这部长篇巨作的深因——他也是在故乡沦陷和随之而来的中国遭到野蛮侵略的时代,特别是在抗战进入中后期的艰难时世,以一个流亡者的心态和思绪,进入了具有时代普遍性的文化与历史的反思与寻根。这种反思与寻根,脱去了《八月的乡村》的一味壮烈和高歌,使《第三代》显得更为隽永绵厚。当然,与《科尔沁旗草原》一样,它们都是史诗和大河般的小说,而史诗与英雄和传奇是分不开的,传奇自然会有写实的“传”和浪漫的“奇”,大河的波涛汹涌之中也有芜杂和乱石,但根本上不影响大河的壮阔。
如上所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和艰难的苦战。当此之际,在作家和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被史家称文化反思与寻根的倾向。特别是在大后方,这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潮。中华民族为什么会遭此浩劫?帝国主义为开拓生存空间的殖民侵略固然是被侵略国家难以制止的,但近代以来国弱民弱的国情及其文化,也难辞其咎,落后挨打的思路是其中主线。由是,一批具有文化反思意味的文学作品陆续涌现,特别是在继承鲁迅启蒙主义传统的作家那里,表现尤为明显。曹禺的后期剧作《北京人》与《蜕变》,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小说和穆旦的诗,以及上述的萧军在延安的续写《第三代》,萧红在流亡中写作的《马伯乐》与《呼兰河传》,实质都是这种文化与文艺思潮的不约而同的自我实践。
东北籍作家的这种反思、寻根和写作,除了上述的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着重挖掘人民的原始强力的创作倾向之外,还有萧红长篇小说《马伯乐》代表的挖掘批判国民性病像的作品。在流亡生涯中,萧红仍然继承她写作《生死场》时的立场,以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的态度,对马伯乐代表的部分中国人的无民族国家观念、只在意吃喝活着和一己利益的愚弱性格与素质,予以辛辣的讽刺与批判,体现了萧红在1938年一次座谈会讲述的作家的使命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写作诉求,而这样的诉求无疑与鲁迅的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存在精神血缘。马伯乐这类国民其实是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愚民”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治绩”,萧红的描写针对性很强,惜乎对愚昧可笑的行为现象描写揭示过多,而深入的具有内在揭示性的东西挖掘与表现得尚不充分。
第三种是对国统区大后方现实的扫描与叙述。李辉英的《雾都》和端木蕻良的《新都花絮》,都是对战时陪都重庆的或纸醉金、或苟安无为的林林总总的人物与现实的批判性描写。在民族面临生存还是灭亡、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时代,偏安于大后方的各色人物,却似乎忘却国恨家愁,已无兵马的旧军阀将军表演似的总说要上前线却毫无行动,时髦男女依然在物质追求与虚飘爱情中萎靡享乐,全不顾广大的中国此时或沦陷或苦战的沉重。《新都花絮》里写的上流社会的男女,根本不像生活在国难沉重的时代,吃喝歌舞看电影“闹爱情”,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间或会有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富家小姐对孤儿院孤儿的一时同情,但这也是暂时的为排遣寂寞孤独的“赈灾”式的时髦,不会有对苦难人民和国难国家的真正关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古代诗人针砭时弊的痛语,鲁迅在为萧军小说写的序言里,对“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内地社会“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的现实,曾予以揭露和针砭。东北作家的这类不以沦陷的东北及其抗战为题材,还是描写大后方社会之怪现状的作品,看似不涉抗战,骨子里却是抗战爱国之情的忧思,是对忘却故乡、对不关心祖国蒙难和民族解放战争艰难的豪门权贵和上流社会的鞭挞,是流亡者难以忘怀的家国之情面对大后方沉痛现实的抒愤。可惜的是,东北作家的这类小说的思想深度、批判力度、讽刺强度,皆存在不足,艺术功力与水准也远不如他们写东北、写抗战的小说。
还有一位东北籍作家齐同,此时写作了反映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新生代》。齐同是亲身参加了这场学运的学生,而这场学运的目的是促使国民政府组织全民抗战不再退让,齐同作为故土遭难有家难归的流亡青年,与那个时期大多数身在北平的东北学生一样,强烈的乡情与民族情使他们感情冲动数倍,渴望打败外敌收复故土,一如端木蕻良短篇小说《乡愁》里写的那样,希望“王师”早日“北定中原”而不是“南望王师又一年”。齐同之参加学运和后来写作以此为背景和题材的小说,其内心的动机和诉求尽在于此。这部小说也属于广义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历史反思与寻根之作,对运动的过程和各种各样的学生的描写,战前北平社会的描写和历史场景的呈现,都有较好的表现和艺术功力。对于齐同小说的背景和内容,如果结合台湾东北籍作家赵淑敏的长篇小说《松花江的浪》、台湾东北籍学者齐邦媛的自传纪实《巨流河》,就会对从“九一八”到抗战以后,流亡北京与大后方的东北青年学生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流亡生涯和悲苦壮烈,有更深切的理解和感受。从这个意义上看,《新生代》是在比较平缓的叙述中蕴含沉痛、关乎抗战的忧愤寄托之作,有历史的风云和家国关怀的生命之流与时代寄托。
综上,当“九一八”事变这场巨大民族灾难降临之际,是东北作家以他们饱含血泪的笔墨,最先将“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④抗战军兴,他们在投入各种实际的抗战活动之余和之后,继续挥毫写作,为中国文坛贡献了一大批有特色的长篇小说,在现实描写与回溯历史之中,书写着爱国作家和流亡作家对于故乡、祖国、抗战、民族振兴、人民解放的思考与关怀,为中国的抗战文学贡献了具有历史与文学双重价值的重要作品,如果没有这批作品,中国的抗战文学的价值和面貌将大打折扣;有了这批作品,中国的抗战文学才如此丰富而令人难忘。同时,也为世界的反法西斯文学和战争文学,掀开了新的一页和篇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充满文学的自信,抛却西方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模式的影响,真正的将东北抗战文学,作为世界法西斯文学的开篇,将东北和中国的抗战文学,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林,并占有历史应该给予的地位。
①④ 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② 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③ 周立波:《丰饶的一年间——1936年的小说创作》,上海:《光明》,1936年第2卷2号。
[责任编辑 韩 冷]
I206.6
A
1000-114X(2016)06-0140-09
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24
广东社会科学 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