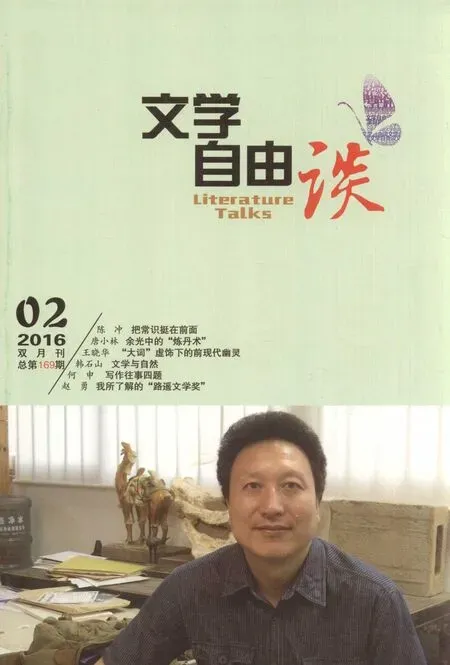何以承受鲁迅故里之“轻”?
孙仁歌
何以承受鲁迅故里之“轻”?
孙仁歌
无意中读到张承志的《鲁迅路口》一文,读后深感震憾!同为推崇并景仰鲁迅精神的拥趸,较之张承志先后两次专访鲁迅故里的虔诚与专注,笔者不禁顿生惭愧、汗颜之感。
近几年我给大四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鲁迅研究”,也曾多次向学生承诺拜访鲁迅故里是研究鲁迅不可或缺的一课,并已经提到个人的议事日程。是张承志的《鲁迅路口》,激发了我急切前往鲁迅故里补课的心愿。于是,2015年“十一”小长假,向来拒绝黄金周出游的我,义无反顾地直奔绍兴,拜访鲁迅故里。
即便已经坐在高铁上了,我还在默默地品味着几篇“挺鲁”美文在我灵魂层面产生的共鸣: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鲁迅为什么无与伦比》、《李泽厚论鲁迅》、张承志《鲁迅路口》、朱学勤《鲁迅、胡适与钱穆:逝去的铁三角与轻浮的当下》、李建军《话语刀客与“流氓批评学”的崛起》等等,每篇皆字字珠玑,妙语连连。李泽厚一直视鲁迅为自己的偶像,他认为“鲁迅由孤独的个体又积极回到争斗的人间,这才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彻悟了又回到人间,彷徨之后不是躲在院墙内谈龙说虎,饮茶避世,这才是真伟大。”李泽厚还认为,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聪明的作家太多,唯独鲁迅“不识时务”。
张承志的《鲁迅路口》中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这个站的站牌很有意思,好像整个绍兴的公共汽车都到这儿来了,每路车都在这个路口碰头,再各奔东西。一个站,密集的牌子上漆着的站名都是‘鲁迅路口’,这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象征,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拥挤在这儿。”
特别让我感到痛快的还是李建军在《话语刀客与“流氓批评学”的崛起》一文中所发出的声音:“一个产生不了巨人的时代,往往是一个对巨人充满敌意的恐惧之感的时代。因为巨人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尺度,他的存在固然可以成为引领人前行的积极力量,但也通过比照,彰显着一些人精神上的残缺和人格上的病态,带给他们的是横竖的不自在。”李建军正义凛然捍卫的巨人,正是鲁迅。当下之所以产生那些“亵鲁”之杂音,深层次的文化背景被李建军给一语戳穿了。
我是真诚怀着一份寻踪、续谱的心态前往鲁迅故里。哪承想,2015年10月2日那天,到了绍兴深入鲁迅故里之后,却被迎头棒喝:人山人海,群头攒动,万众一心都在这里奏响着“集结号”!哪里还能拜谒鲁迅故居,简直就是来看人的!
原计划,到了鲁迅故里,第一餐不在别处,一定要在咸亨酒店,感受一下当年孔乙己被奚落的情节。可是一走进所谓的咸亨酒店,却如同走进了一家购物超市,偌大的、涂满现代商业色彩的咸亨酒店居然也人挤人、桌挤桌,一派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大场面。唉唉,要在咸亨酒店吃一顿简餐,必先得“过五关斩六将”才如所愿。如此拥挤不堪人声鼎沸的咸亨酒店,哪里使人还有心绪去缅怀当年的孔乙己?慕名而点上桌的茴香豆,亦变作了乏味之豆。
挤出咸亨酒店,赶紧挤往鲁迅故居。鲁迅故居只是鲁迅故里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鲁迅祖居、三味书屋、百草园、鲁迅文物馆等等。也许是为安全起见,每个景点的入口都需反复绕行铁栅栏,以分隔人流进入。好不容易绕进入口,进入景点参观,又是人挤人。鲁迅故居的每一扇门窗,我都是走马观花,一眼带过,好像什么都看了,又好像什么都没看着。如此拥挤躁动之下,哪还能静下心来寻踪与续谱?本来庄严的一次拜谒之举,无端被喧嚣、嘈杂与浓浓的商业气息所包围。
鲁迅故里的几处景点,都在无奈的拥挤中一览而过,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三味书屋的清冷,与出口处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的喧哗——几乎每一个景点的出口,差不多都是如此。
鲁迅原本是我们民族沉重之所在,如今,却在浮躁的“世风”中被如此之“轻”!文化被商业化,精神也在被商业化。如此之化,何以了得!恕我直言,如今的鲁迅故居无论被打造得多么风光,被炫得多么富有人气,但其人文价值早已不及人为的商业价值了。
在鲁迅故里滞留的一天多时间里,想看的也都看了,百草园去了两次,每个书屋也都瞻仰了。当要离开鲁迅故里,要给这一次绍兴之行作点小结的时候,却蓦然感到整个世界都有些轻飘飘的了。这个世界似乎已经不需要任何人再活得那么沉重,即便鲁迅再生,也只能无奈地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飘来飘去地活着。我们当下这个世界似乎更喜欢经济,更喜欢金钱,更喜欢飘在空中做戏,沉重的高尚的人文精神已被挤到了角落。即便生活中仍有鲁迅精神的续谱者,面对今日人文异化了的世界,也难有回天之术,充其量也只能学学《孤独者》(《彷徨》)中的魏连殳,俨然一匹受伤的狼,面朝长空一阵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发展经济没有错,市场经济也并非洪水猛兽。但在一味发展经济中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和谐匹配,势必会因此积累不计其数的“欠单”。强势的经济主流话语有如无形的巨无霸,正在悄悄吞噬着人文社科的空间。知识被金钱熏染,道德在种种交易中渐被异化,被经济主流话语“炼”成的行尸走肉越来越多。是不思危,孰思危?
离开绍兴途中,再三感喟之余,也觉得自己很可笑。这世界已变得很轻飘,你一味庄重又有何用?但尚未泯灭的良知还是在不自觉地愤愤不平。唉,何时再能“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呢?
高铁到站了,悄然无声。从沉重的胡思乱想中又回到浮躁而飘然的现实,感到有几分熟悉,又有几分陌生。多年养就的一种习惯,承受“重负”时还比较适应,但一下转换为一种“轻”,就有些不自在、不适应了。“重”有时就是一种担当,而“轻”就是卸却应有的“担当”后的失重之感吧。
何以承受鲁迅故里之“轻”?轻与重有时是互相依赖的,也是互相转化的。与其说是承受鲁迅故里之“轻”,倒还不如说就是承受鲁迅故里之“重”,只是“轻”有时或许就是“重”到了一种极致吧?自然,万事“轻”不得,举重若轻又何妨?拥有一种担当“重”中之“重”的责任,应是立于商业化大潮之中的中流砥柱,而与那种真正随波逐流、避“重”就“轻”者流还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