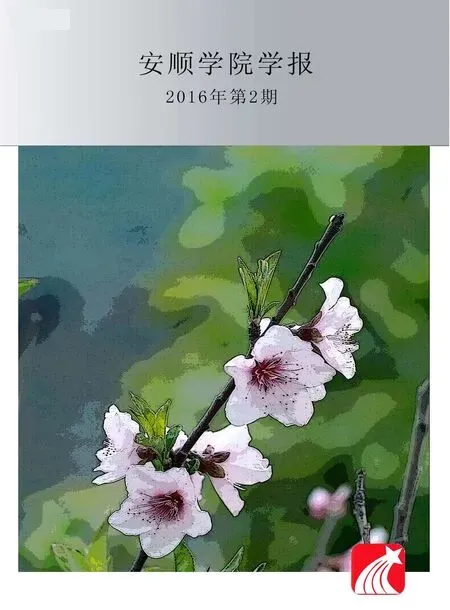曹禺与契诃夫戏剧语言艺术的比较
周海云
(蚌埠学院,安徽 蚌埠233030)
曹禺与契诃夫戏剧语言艺术的比较
周海云
(蚌埠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摘要:契诃夫是西方戏剧艺术发展史上代表人物之一,擅长用简洁凝练但又意味深长的生活化语言来表现人物角色的精神空间,从而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诗意化挖掘。这种诗化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中国戏剧作家,曹禺就是其中的一位。曹禺通过借鉴契诃夫戏剧艺术的创作思想,并将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表现手法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富于民族审美特性,独具特色的戏剧风格。
关键词:曹禺;契诃夫;戏剧语言
作为一名杰出的戏剧家,安东·契诃夫一生创作的剧本数目虽然不多,但都能称得上是精品之作,特别是《樱桃园》《三姊妹》《海鸥》等几部经典剧作在世界范围内频繁上映,反响强烈,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被公认为是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作品。[1]话剧并不是中国本土戏剧形式,作为一种外来戏剧,历经百年吸收、消化和创新,终于演变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种艺术戏剧形式,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典型文化现象,而曹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五四”前后,国内涌现出了大批剧作家,他们借鉴西方戏剧创作经验,探索符合国人文化价值观的本土话剧。在这些戏剧作家中曹禺不断耕耘,终结出丰硕果实,使中国话剧创作水平再上一台阶,达到历史新高度。
曹禺跟契诃夫一样,一生中发表的剧作虽数量不多,但多系佳作。1936年,曹禺处女作《雷雨》一经发表,就在国内文坛引起极大轰动。后续其创作或参与改编的《日出》、《原野》、《黑字十八》(与宋之的合作)、《蜕变》、《北京人》、《家》、《明朗的天》、《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和《王昭君》等一系列剧作也同样受到广泛好评。特别是《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即使现在也常被搬上银幕,上演率极高。纵观曹禺的多部作品,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创作深受欧美作家的影响,其中尤以俄国剧作家契诃夫的影响较大。曹禺多次坦言自己对契诃夫的诗化现实主义戏剧风格的欣赏与钦佩。如果将契诃夫与世界著名戏剧家相比,他的剧本“与莎士比亚以及易卜生的话剧都不同”[2],“它显得很深沉,感情不外露,看不出雕琢的痕迹”[3],“契诃夫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我发现,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4]。受此影响,《雷雨》的创作大获成功,但曹禺对此并不满意,之后开始不断反省,“技巧上,我用得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过后我每读一遍《雷雨》便有点要作呕的感觉。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地被他的戏感动着……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5]不难看出,曹禺对契诃夫的推崇,不仅如此,曹禺也将自己这段时间的思考付诸于剧作创作的实践中,陆续创作出《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这些作品的风格明显迥异于《雷雨》。本文试图以戏剧语言为视角,对曹禺与契诃夫两人的作品进行比较,揭示曹禺在借鉴契诃夫诗化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努力结合本土文化,创新实践,从而极大增强了自己的作品对现实生活的透视力和观察力,使得作品直指社会本质,引人思考,震撼人心,这也是外来艺术在中国本土民族化的一个缩影。
一、形式上的间断与意义上的连续
自古希腊开始,西方早期戏剧艺术家,如莎士比亚、易卜生,一味追求故事情节的矛盾冲突,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华丽典雅的语言,连绵不绝的悬念,组织严谨的戏剧架构,营造一种紧张的氛围,在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也让故事对现实刻画更具张力,从而令观众震撼。曹禺在创作《雷雨》时借鉴了这一艺术表现技巧,虽使自己一炮走红,但并没有让作者感到满意,他认为这样的戏剧设计太过于重视技巧的应用,从而显得“太像戏”,缺乏真实感。事实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本不是戏剧舞台上展现出来的一出出矛盾冲突,一幕幕悲欢离合,而更多的是一些平凡琐碎甚至无聊的画面组合,如果采用高度集中概括的形式不仅难以完整展现现代生活,而且更难以表现普通小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戏剧手段来揭示平淡生活中蕴含的悲剧,契诃夫的戏剧设计思想就是如此。
相比传统戏剧注重对故事情节与外部冲突的设计,契诃夫更注重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契诃夫曾说过:“在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每分钟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角逐情场……人们更为经常的是吃饭、喝酒、玩耍和说些蠢话。所以,应该把这些反映到戏剧舞台上去,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6],通过对诸如吃饭、聊天、喝酒、散步等日常生活题材的刻画去挖掘背后隐藏的戏剧性,因而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时一般都使用一种朴素简洁的戏剧语言。表面看来,似乎没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那般华丽典雅,酣畅淋漓,但仔细品味,你会发现契诃夫戏剧中每一句对白的背后都隐藏着故事人物的内心隐秘。观众只有在反复揣摩对白后,才能洞悉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与心理逻辑,才能把这种看似间断无关联的语言串联起来,从而明白其中真正的内涵。比如《樱桃园》中,加耶夫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整天想的都是“打台球”。对他而言,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即使是置身在人群中,对身边的人事也是充耳不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台球世界,有时冷不防地说出类似“红球进中兜”这样让人费解的话。同样孤独寂寞的夏洛蒂,在与好友久别重逢的时候,竟突然冒出与谈话主题毫不相关的“我的小狗还吃核桃呢”。如果依照传统戏剧创作理念,显然这些对白无助于故事情节的集中与矛盾冲突的强化,有点偏离剧情主题,但恰恰就是这样非常日常化的语言,让观众感到亲切的同时,更能深刻体会到剧中人物的内心孤寂,始终将自己尘封在内心世界中,与世隔绝。这种看似偏离主题的对白不仅符合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内心、语言、动作,同样也能让观众在细细品味台词后,在内心中构建相应的意象,引起共鸣。对于这种创作思路,曹禺非常欣赏,并将其付诸于自己的戏剧创作中。
在《北京人》第二幕里,曾霆和瑞贞本是夫妻俩,生活在一起多年,按理两人应该对彼此都很熟悉,心意相通才对。但在这个故事中,一个深夜,两夫妻在客厅相遇,但由于曾霆已经约好袁圆在此相见,所以希望瑞贞能尽快离开;而瑞贞此时已有身孕,尽管很想尽早结束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但仍希望将怀孕的事情告知曾霆。就是在这种故事背景设定下,曹禺借鉴契诃夫的戏剧语言风格,设计出既相互交叉,又互不相干的一场精彩对白。曾霆问瑞贞:“你坐在这里干什么?”瑞贞并不想让对方知道自己决定离开曾家,但犹豫是否应该告诉曾霆自己已经怀孕,所以回答:“没有什么。”曾霆感觉无趣,恰在此时,巷子里忽然传来声音,遂说道:“卖硬面饽饽的老头又来了。”这本是无话找话,却被瑞贞误认为曾霆饿了,于是关切问道:“饿了么?”此时此刻,身为曾霆妻子的瑞贞却没有看出丈夫的心思,两人间的隔阂顿显无疑。接着瑞贞哭了起来,曾霆只当瑞贞找自己是为了要钱,只是不好开口而已,便说道:“你要钱……你拿去吧。”可他哪里明白瑞贞哭泣的真正原因!哪怕到了最后,瑞贞一再暗示到,“我最近身体不大舒服”,“我常常想吐”。曾霆还是糊里糊涂,说“妈屋里有八卦丹,吃点就好”。至此,瑞贞能够得到的只能是失望。看到这,我们不由得感慨一句,夫妻本应比翼鸟,而今劳燕各西东。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如同打哑谜似的对白无疑暴漏出曾霆与瑞贞夫妻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即使两人相对而坐,却各有心思。从这些描述,我们看到曹禺是如何借鉴契诃夫的戏剧语言风格,让《北京人》这一作品中的对白更显生活化,更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因为这些语言是来自于生活中,真实反映出角色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人物心理活动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些语言让作品更具生活气息,而非曹禺所说的“太像戏”。
二、含蓄而诗意
纵观契诃夫的作品,其戏剧语言虽含蓄凝练,甚至看似简单,但却充满了一种散文诗般的风格,极富诗意。有些对白,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深刻透漏出剧中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有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也恰如其分抒发了人物的孤独忧郁。比如在《海鸥》中,剧中人物妮娜说道,“我是一只海鸥……啊,不是的。我是一个女演员。”看似简单的台词,却向读者暗示了妮娜悲惨的一生。妮娜好不容易摆脱专制家庭的束缚,但却在爱情上被作家特里国林所抛弃,自己的演艺事业也几近毁灭,如同特里国林在其写的一篇小说里的情节:一个过路人偶然走过,看见一只海鸥,只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便把它给毁了。由此,妮娜不由发出“我是一只海鸥”,哀叹自己命运的悲惨,但妮娜并没有被困难所击倒,她仍以极大的勇气怒喊“啊,不,不是的”,并在生活的磨砺下,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所以看似简单的台词却形象概括了妮娜奋斗成长的历程,一只差点被毁掉的海鸥最终成长壮大能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对于契诃夫这种朴实无华但却充满诗意的戏剧语言风格,颇受曹禺的欣赏与推崇,并用于自己的戏剧创作中,从而体现出一种诗意特征。以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或几句简单的对白,甚至几个常见的语气词,就能展现出故事任务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在某些情况下,更是用无声的语言来抒发委婉悠长的诗化意境。在《北京人》中,曾文清和愫方第一次见面时,只有三句简单的对白:
曾文清 (感愧的眼光满眼含着泪,低声)愫方,我,我——愫方低头不语
曾文清 (望望她也低下头,嗫嚅)陈奶妈来,来看我们了。
愫方 (忍着自己的哀痛)她,她在前院。
由于先前,曾思懿借愫方为文清烧了两碗菜的事,指桑骂槐地羞辱他们。想到愫方因为自己而蒙受羞辱,曾文清深感愧疚,特别在想到多年来都是愫方一直在关心自己、照顾自己,这种爱意让曾文清的内心情感一触即发,他本想说“对不起,愫方,我连累你了。我真地很感激你!”可愧疚之下,难以开口,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了句“愫方,我,我——”。一句并不完整的话,虽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但却准确显示出其欲说还休的复杂思绪。之后,曾文清改用“我们”,而不是“大家”或者“你”、“我”,其用意在于突出“愫方”和“自己”是一个整体,以显现二人的情投意合。而愫方回应道“她,她在前院”,看似偏离话题,是一种故意的回避,但却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愫方心中的难言之隐,让观众看到其内心的痛苦远较文清更深。三句平淡无奇的对白如同落入水中的石子,以一种含蓄的力量抒发了浓重的情意,在剧中激起一圈圈诗意的涟漪,剧中人物就是通过这些简洁但抒情的语言被生动地塑造出来,使这些人物身上披上浓厚的诗意。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说:“曹禺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诗人”的素质,促成曹禺将剧作的语言锤炼得极富抒情性。
结语
契诃夫作为西方戏剧艺术发展史上最著名的戏剧家之一,无疑,他的一些戏剧创作思想影响感染了一批中国作家,曹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需要指出的是,曹禺只是学习借鉴契诃夫戏剧语言的一些表现手法,因为这种诗化现实主义风格能够让作品更贴近生活,更具生活气息,从而打动观众内心,引发共鸣。在这一学习过程中,曹禺并非一味模仿,而是敏锐地发现了契诃夫戏剧语言所具有的凝练、含蓄、深沉的特点与中国古典文学审美趣味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从而将语言的凝练简约与本民族审美传统完美融合,通过诗一般的台词,营造出一种意境,使得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更加丰满,帮助观众在心中构建出相应的意象,可谓是情在诗中,境由意出,情景交融。
参考文献:
[1]石岩·契诃夫走上前台[N].南方周末,2004-10-09.
[2]曹禺·读剧一得[M].论戏剧.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64.
[3]曹禺·和作家们谈图书和写作[J].剧本,1982(2).
[4]张葆辛·曹禺同志谈创作[N].文艺报,1957(2).
[5]曹禺·日出·跋[C].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专辑(上).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1979:48.
[6]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95—420.
[7]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M].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Laurence Senelick.The Chekhov Theatre——A Century of the Plays in Performanc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责任编辑:颜建华)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ramatic Language Between Cao Yu and Chekhov
Zhou Haiyu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233030, Anhui, China)
Abstract:Chekhov, one of representative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drama literature, is expert in reflecting people's intricate inner world with concise and poetic language. In China, Chekhov’s writing style influence many playwrights, headed by Cao Yu. Based on profound experience of social reality, Cao Yu formed his unique drama style by making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national aesthetic images and poetic realism.
Key words:Cao Yu; Chekhov, Dramatic Language
收稿日期:2016-01-04
基金项目:蚌埠学院科研立项课题《文明的对话与次生文化的生成机理研究》(2015SK07)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周海云(1983-),女,安徽蚌埠人,蚌埠学院外语系教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07(2016)02-0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