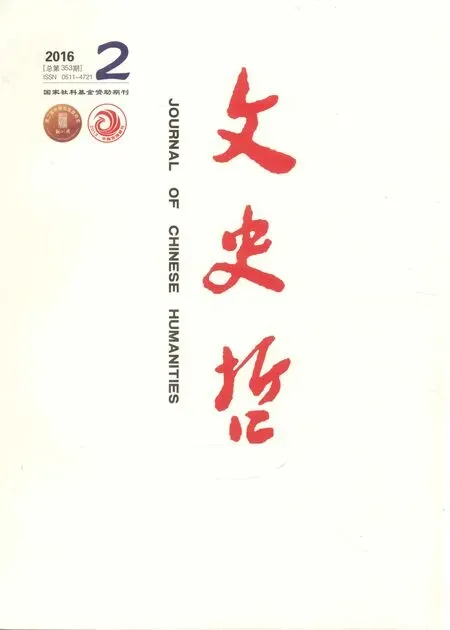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
孙之梅
从诗界革命到南社:新古体诗的蜕生
孙之梅
摘要:在白话文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古体诗仍然拥有为数不少的作者与读者,这种诗体或被称为“旧体诗”,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古体诗”。它是在文学转型过程中逐渐从古典诗歌中蜕生出来的既异于白话诗,也不同于古体诗的新诗体。诗界革命之“新学诗”、“新派诗”、“新体诗”分别从传统学术层面、表现事物与语言层面、审美层面对古典诗歌进行解构;而南社诗歌则是古体诗歌转型过程中的又一次调整,其表现为有选择地整合传统与西学,确立诗歌的现实针对性与功利性,使古体诗在古雅表象下实现气质上的平民化。民国以后随着新学制的确立与普及,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死文学”的恶谥,使古体诗处境维艰,但经过文人学者、政要、以及其他古体诗爱好者的坚持,古体诗蜕生为一种新诗体。
关键词:诗界革命;新学诗;南社;新古体诗
Fromthe Revolution in the Poetic World to the Southern Society:Transmutation of the New Ancient Poetry
Sun Zhimei
In modern times whenvernacular literature occupied a mainstream position, the poetry in ancient style still owned lots of writers and readers. Some people call this poetic style as “old-style”, and in this paper, it is called the “new ancient poetry”. It is a kind of new poetic style gradually emerging out of classical poems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both free verse in vernacular, and ancient poetry. The “new-learning poetry”, “new-school poetry”, and “new-style poetry” in poetic revolution separately deconstruct classical poetry from the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academics, the dimension of language and things to be represented, and the dimension of aesthetic; while the poetry of the Southern Society is another adjust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poetry, which expresses as selectively integrating the tradtional and Western learning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the realistic pertinence and utility of poetry, to make ancient poetry realize a nature of plebification beneath its quaint surfac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cient poetry entered a tough status al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new educational system, especially with the derogatory title of “dead literature” given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 Yet through the insistence of many scholars, politicians, and enthusiasts for it, ancient poetry transmuted into a kind of new poetic style.
白话文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代社会,诗坛上仍然活跃着古体诗*我国古代诗歌在形式上分古体、近体,此处“古体”着眼于时代之古今,概称古代的各体诗歌。,这种诗体往往被称为“旧体诗”。所谓“旧”,是相对于新诗而言。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歌革新派“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诗属于“旧学”的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与“旧”在表层意义之后潜藏着更加明确的褒贬,“新”代表进步、先锋、主流,“旧”代表落后、保守、陈旧。“古”是古典之谓,标志的是一种文学符号,如果把现代的类似写作称之为“古体”,则含有坚持古典传统的意味,因此用“旧体”称之,以表达某种程度的贬义。揣摩“旧体诗”称谓的渊源,其中实有微意。本文摒弃“旧”的称谓,命名为“新古体诗”,所谓“新”不含有新锐、先锋、先进的语义,而是指一种由古代“古体诗”蜕生出来的新型古体诗。其在形貌上与古体诗相同或相似,而精神气韵却大异其趣。之所以造成此种差异,除了社会生活、语言系统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古体诗的学术文化基础是经史之学,而新古体诗则是在经学解体、史学被裁割碎片化,西学被功利主义地吸纳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术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本文无意对新型古体诗进行全面梳理,只就其蜕生的早期步履进行探讨,分析其学理层面的历史逻辑。
一、诗界革命对古典诗歌的解构
甲午战争之后以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为首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出现了“新诗”(也叫“新学诗”)、“新派诗”、“新体诗”等除旧布新的尝试,古体诗的解构始于此。
中唐古代诗歌诸体大备,此后基本定型了的诗歌仍然能持续发展兴盛近千年之久,除了丰富其风格、技巧,以适应不断扩充的诗歌容量外,就是它与思想学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萧子显总结诗歌发展规律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其实整个诗歌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新变”和寻求“代雄”的过程。中唐以前,在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推动下,诗歌体式处于完备与定型时期,中唐以后则表现为文学吸纳特定时代的思想学术而寻求“代雄”的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诗歌根植于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两个层面。
清末,古代诗歌的“超稳定”形式面临新的危机:其一是社会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变局”,独立自主的经济结构被新型资本主义强行拉入世界格局,完整固有的版图被东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其二是传统的社会制度、文化学术在应对这些社会变局时表现得愚昧颟顸、迂腐封闭、张皇失措。甲午之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华民族进入全面危机的时代,因此“新变”首先是更张政治体制和文化学术。
1896年年底到1897年年初,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相聚于北京,尝试创作“新诗”。这次诗歌革新活动,虽然所取得的成绩有限,产生的影响有限,甚至梁启超本人也感到这是使诗失去诗的资格的失败的活动,但它对古代诗歌的冲击却直指根源。所谓“新诗”,也叫做“新学诗”。“新学”是相对于“旧学”而言。何为“旧学”?梁启超《三十自述》讲到自己的学术经历,说到二十一岁(1890)时师事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制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此所说“旧学”,是与康有为《大同书》、《公理通》相对的“训诂词章学”;所谓“新学”,即梁启超二十一岁入京会试,除了国学之书还购买了一些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融汇为东莞讲学时的公羊学、大同义理、世界公理*张伯桢《张篁溪日记》:“梁先生于光绪十九年癸巳冬到吾乡讲学,城内墩头街周氏宗祠内,时余才十七岁,从之游。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页。。显然这还不是“新学诗”之中“新学”的全部。
1894年到1896年间,梁启超居住在粉坊琉璃街的新会会馆,夏曾佑租住在贾家胡同,后来谭嗣同进京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他们“衡宇望尺咫”,“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回忆道:
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页。
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他受夏、谭二人的影响,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9页。。否定了垄断学界的汉学,并去打倒汉学的老祖宗,“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第5册,第22页。。清代的汉学以及周秦以后的学术传统全被推翻,便吸纳西学建立新的学术体系。他们企图建立的新学体系,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五经原典与周秦诸子。《亡友夏穗卿先生》云:“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其二是外国学问。“外国学问都好”,却不懂外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其三是“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第5册,第22页。。这三种元素混合,就构成了“新学诗”中不中不西的“新学”的主体。
这种“新学诗”首倡者是夏曾佑,他喜欢“把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常用诗写出来”*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第5册,第22页。,梁启超与谭嗣同与之唱和。《饮冰室诗话》回忆道:
当时吾辈方沉酣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如此“新诗”除了他们自己外无人能索解,梁启超后来概括为“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这样的表述,似乎“新学诗”只是触及一个语言层面的问题,但事实远非如此,新名词的背后却是乾坤大挪移,对古代诗歌赖以生存发展的学术文化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而移植进生吞活剥、“不西不中”的西学。从诗歌古今转型的角度考虑“新学诗”,可谓是一次古代诗歌与传统学术的剥离,脱离母体寻找一种异质的土壤。
“新学诗”稍后的1897年,黄遵宪把自己的《人境庐诗草》呈给曾广钧,请求其作序。曾广钧评价黄诗“善变”,为诗歌之“变体”*《新民丛报》第3年第4号载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有自序云:“重伯序余诗,谓古今以诗名家者,无不变体。而称余善变,故诗意及之。”。“善变”是说黄遵宪之诗善于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变体”则是说黄诗是一种新体。古代诗歌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古体到近体,从初盛唐到中晚唐、宋诗,每一次都是一种“变体”,都是寻求“代雄”而“新变”的结晶。曾广钧的这个评价很高,深得黄遵宪认同,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第二首云:
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新民丛报》与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善作”为“善变”。,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虬驷,出门惘惘更寻谁?
诗歌史的生生不息源于“善变”,在西学东渐,社会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也正是诗歌新变的机遇。显然,黄遵宪对时代与诗歌的转型比同时代人有更宏观、更自觉的认识,“新派诗”正是对“变体”的另一种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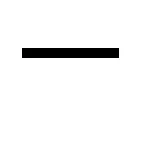
卷三共收诗十八题六十一首,其内容有三:一是与日本友人的唱和交往,二是描写日本的风土人情,三是针对日本某一历史事件抒发感慨评论。其中日本特色鲜明的如描写樱花的诗,《不忍池晚游诗》之五描写樱花盛开的景象:“百千万树樱花红,一十二时僧钟楼。”《樱花歌》描写日人赏爱樱花的情景:“坐者行者口吟哦,攀者折者手挼莎,来者去者肩相摩。……倾城看花奈花何,人人同唱樱花歌。”前者呈现鲜艳烂漫的樱花掩映着僧寺钟楼的别样风光,后者扣住日人对樱花的独特情感展开描写。再如描写日本民间风情的《都踊歌》,被梁启超称为诗人集中鲜见到“绮语”之作。《近世爱国志士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都是歌颂日本历史上的爱国人士,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也是黄遵宪诗集中保存最早的歌体。由于描写事物的改变,出使日本时期的诗歌开始“挦扯新名词”,如“欧罗巴”(《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其二“近年欧罗巴”)、“地球”(见《宫本鸭北索题晃山图即用卷中小鸭湖山诗韵》“地球浑浑周八极”)、“总统”(《罢美国留学生感赋》“总统格兰脱”)、“维新”(《琉球歌》“一旦维新时事异”)等。

光绪十六年(1891),黄遵宪结束了家居著书的岁月,跟随薛福成出使欧洲。自香港登舟,写下了《自香港登舟感怀》诗;经过越南,写下《过安南西贡有感》五首七言绝句;又过锡兰,写下长诗《锡兰岛卧佛》。到达欧洲后,与域外事物情景有关的诗有《温则宫朝会》、《重雾》、《伦敦大雾行》、《在伦敦写真志感》、《今别离》、《感事三首》、《登巴黎铁塔》、《苏彝士河》、《九月十一夜渡苏彝士河》、《泊舟波塞,是夕大雨,盖六月不雨矣》,本卷收诗二十题,域外题材占多数。这些域外诗最受人称道的是《今别离》组诗。此诗把传统的离别相思之情熔铸到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以及东西半球的新知识、新情景下书写,得到了新旧人物的赞赏。梁启超把此诗当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典范之作,陈三立称之为“千年绝作”。《锡兰岛卧佛》诗,回顾历史,叙述佛教,大量挦扯佛教典故。梁启超从长篇叙事诗的角度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有诗以来所未有也”,欲题为《印度近史》、《佛教小史》、《地球宗教论》、《宗教政治关系说》*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4页。。
卷七收诗八题。光绪十七年(1892)十月抵新加坡,第一题为《夜登近海楼》,此近海楼非顺天府之近海楼,而是黄遵宪初到新加坡的登楼诗*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本诗题解云:“近海楼,在顺天府境内。”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緒十七年辛卯”条云:“准此则先生离英当在八月之尾,九月之朔。……十月初,抵新嘉坡。十二月二十七日乞假百日回籍治父丧。光绪十八年壬辰四月假满回新嘉坡。”其间并无赴京的痕迹,此“近海楼”非顺天府之近海楼。再看其诗:“曾非吾土一登楼,四野风酣万里秋。烂烂斗星长北指,滔滔海水竟西流。昂头尚照秦时月,放眼犹疑禹画州。回首宣南苏禄墓,记闻诸国赋共球。”“曾非”句化用东汉末年王粲寓居荆州时所撰《登楼赋》之意,“四野”句说明是秋季登楼。黄遵宪到达新嘉坡正是秋末。登楼所观景色,为海边之景非内陆之景。“烂烂”两句之“北指”、“西流”表达思乡感情。“秦时月”、“禹画州”说自己在新加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恍惚之感。可见,此近海楼是新加坡之近海楼,这首诗作于新加坡的十月。。后为《续怀人诗》十五首,不同于第六卷《怀人诗》的是所怀之人多为海外人士,尤以日人为多。《新嘉坡杂诗十二首》写其地的“历史现状,民情风俗,土产风物”(钱仲联本诗题解语)。此卷受人关注的诗有《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与《番客篇》。前者梁启超评论道:“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32页。后者夏敬观称为“能直言眼前事直用眼前名物”*夏敬观:《吷庵臆说》,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462页。。这两首诗中用的新名词有“黄白黑种”、“支那”、“动物”、“植物”、“和兰”(荷兰)、“犹太”等。
曾广钧称《人境庐诗草》为“变体”,为“新派诗”,其原因在于黄遵宪的海外诗描写的是全新的事物、场景、知识以及作者的人生体验,为了表现这些新“意境”,诗的语言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黄遵宪的很多长篇诗是戊戌放归后所补写,受当时佛教热的影响,佛教语、声光电化语、西学名词络绎诗中,对古典诗歌语言系统的静止封闭状态冲击很大。如果说“新学诗”是对古典诗歌釜底抽薪的摧毁,而黄遵宪的“新派诗”则是为古典诗歌“换血”,它指示古典诗歌一种新的路向:域外是诗歌新的表现领域,新知识、“新语句”是古典诗歌的新血液。
如果要让诗歌承担“新民”的作用,则必须使其放低身份,实现由优美古雅向通俗化、大众化转变。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海外,依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发动了“诗界革命”,放归故里的黄遵宪致函梁启超云:
报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技辞。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黄遵宪:《黄遵宪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4页。
这段话有两点要特别注意:一是诗歌的通俗化不必考虑乐府体。乐府诗在古代诗歌中属于语言通俗、句法自由、长短不拘的诗体,黄遵宪认为新体诗要挣脱乐府诗的羁绊,斟酌于弹词与民歌之间,创作出一种比乐府诗更自由的诗体。二是诗歌题材疏离传统学术,重在关注新近事物。显然,黄遵宪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新目标,即用更加自由通俗的诗体以表现新近发生的事情。梁启超欣然同意,在《新小说》开辟“杂歌谣”栏目,陆续发表了一百余首“新体诗”与“新粤讴”。“新体诗”突出的特点是内容浅显,语言通俗自由,音节容易上口。因为它更适合宣传鼓动,得到了革命派的喜欢,秋瑾、高旭等人曾创作不少这样的诗。这种诗体应该如何评价,还有待斟酌,但其结果是使古体诗不仅与传统学术文化剥离,而且也消解了诗作为一种艺术应有的审美。
二、南社的拨返
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诗歌革新显然是有问题的,其“新”是建立在中国之外的,其情景是海外之景与海外之境,其学术根基是西学,其语言是泊来的新名词,其新意大致是身在海外的生活感受,然后再把诗歌形式变成歌体。我国古代诗歌是建立在汉字形、音、义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创作实践而形成的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汉语是国人的母语,只要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还在不断延续,古体诗就有存在的基础。引入西学来推进诗歌的转型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努力,但按照这一条路径走下去,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诗歌恐怕难以为继,这也正是诗界革命始终作者群有限,梁、黄等期待的一种新诗体很难推广开来的关键。
南社从一开始就有比较明确的诗歌变革主张,高旭1909年发表的《南社启》明确表示:“今者不揣鄙陋,与陈子巢南、柳子亚卢有南社之结,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民吁报》1909年10月17日。柳亚子《时流论诗多骛两宋,巢南独尊唐风,与余合……》云:“一代典型嗟已尽,百年坛坫为谁开?”南社诗歌变革的路径与诗界革命既有承续的一面,也有拨返的一面;既有推进的一面,也有退后的一面。承续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注重文学开发民智、激扬民气、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梁启超重视文学的宣传功能,但随着维新派改良政治思想的破产,并没有推行下去,真正把这一文学精神贯彻到底,并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则是南社。因此,柳亚子《新南社成立布告》不无自豪地说:“旧南社成立在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标帜了。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和同志们,在海外创设中国同盟会,以三民主义相号召……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高旭《无尽庵遗集序》也说:“当胡虏猖獗时,不佞与友人柳亚卢、陈去病于同盟会后,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之间也。”*郭长海整理:《高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12页。辛亥革命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在革命史中确立南社的地位,它几乎成了同盟会的一个宣传机构。
比较诗界革命的诗与南社的诗,它们的差别是明显的。诗界革命的诗属于“吟到中华海外天”的诗,表现出知识阶层对西学的大快朵颐,语言开放、新鲜、生涩、肤浅;而南社诗抒写的是甲午、庚子之后知识阶层与专制政体的决裂与追求新型社会体制的心路历程,诗的语言虽不乏类似挦扯新名词,但主流古典倾向更重,宗唐宗宋的诗学主张使南社诗也不无复古拟古的色彩。这说明南社诗歌不同于诗界革命的一味西化,对企图通过借径西学实现诗歌的转型有警戒的心理,而是从一开始就把文学革命的根扎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南社诗歌的传统主要集中于两点:其一是《诗经》以来的风雅传统。陈去病《与宋素、济扶两女士论文》云:“国学于今绝可哀,和文稗贩又东来。宁知蓬岛高华士,低首中原大雅才。”高旭《甲辰年之新感情》云:“鸦鸣蝉噪尽名家,鼓吹巫风兴未涯。小雅日微夷狄横,几人诗思了无邪。”柳亚子《怀人诗》其一云:“英雄沦落作词人,路索文章屈子魂。小雅式微夷狄横,宗邦多难党人尊。”他们不约而同地感慨“大雅”“小雅”诗歌传统的式微,自觉承担起《诗经》以来的古典诗歌传统延续光大的使命。其二是古典诗学传统的具体化,即明末清初以复社、几社为代表的反抗异族的诗歌传统与文化精神。高旭《钝根将回楚,索诗,成四章以应之》云:
谈兵把剑郁难开,飞雁关河暗自猜。种祸从来青史痛,真州岂竟陆沉哀。大都忧国新亭泪,如汝伤时小雅才。几社风微夕堂死,东南今日几骚坛。
钝根即湖南醴陵诗人傅尃。高旭哀痛“种祸”“陆沉”,期待着湖湘与东南连手,重振几社、王夫之消歇后的遗民文学,使其再兴于骚坛。此后,陈去病结神交社,其《小启》回顾明末东林、复社、几社之盛衰与国家兴亡的关系,明确表示“待续云间事,词林各骋才”*陈去病:《无畏、天梅、亚卢、疁公翩然萍集,喜成此什》,《神州日报》1908年1月7日。。柳亚子为《神交社雅集图》作记,阐发的仍然是几复风流之意蕴:“降及胜国末年,复社胜流,风靡全国,其意气不可一世。迨乎两京沦丧,闽、粤继覆,其执干戈以卫社稷者,皆坛坫之雄也。事虽不成,义问昭于天壤,孰谓悲歌慷慨之流,无裨于人家国也。板荡以来,文武道丧,社学悬禁,士气日熸,百六之运,相寻未已。岁寒松柏,微吾徒其谁与归?”*柳亚子:《神交社雅集图记》,见柳亚子主编:《南社丛刻》第1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20页。南社在湖湘的发起人宁调元《南社诗序》径把南社与复社相比拟:“吾友高子钝剑、柳子亚卢等既以诗词名海内,复创南社,以网罗当世骚人奇士之作,蔚为巨观。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昔启、祯之际,太仓二张,首倡应社……流派虽别,大都以诗古文词相砥砺,而统归于复社。山鸣谷应,风起水响,于斯为盛。春木之繁兮,援我手之鹑兮;去之三百,其人若存兮。有踵接而起者,固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柳亚子主编:《南社丛刻》第2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139页。宁调元把南社放在复社、几社的文化统绪中运思,通过南社与几复风流的呼应实现《诗经》“兴观群怨”诗学传统的回归。正是由于南社传统文化的选择,其诗歌呈现出与诗界革命迥异的风貌。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南社的诗歌相对于诗界革命是一种倒退,是对古典的回归。其实不然,南社在扎根传统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西学,南社的西学非诗界革命时期对新语句、新知识的吸纳,而是对西方学说的深入理解与自觉选择,并且力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学说解决中国的体制问题。南社的政治诉求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排满革命源于传统的夷夏之辨,而共和民主则是吸纳西学的制度性追求,而正是这两方面构成了南社诗歌的两大主题。汪精卫在《南社丛选序》中对南社文学进行了精当的概括:
革命文学之采色,必烂然有以异于其时代之前后。中国之革命文学亦然,核其内容与其形式,固不与庚子以前之时务论相类,亦与民国以后之政论,绝非同物。盖其内容,则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也。其形式之范式,则涵有二事:其一根柢于国学,以经义、史事、诸子文辞之菁华,为其枝干;其一根柢于西学,以法律、政治、经济之意蕴,为其条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抉,无前者,则亡国之痛,种沦之戚,习焉已忘,无由动其光复神州之念;无后者,则承学之士,犹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由得闻主权在民之理。且无前者,则大义虽著,而感情不笃,无以责其犯难而逃死;无后者,则含孕虽富,而论理未精,无以辨析疑义,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学,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树立。*胡朴庵选录,沈锡麟、毕素娟点校:《南社丛选》卷首,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页。

三、缙绅之诗转变为草泽之诗
诗界革命曾经尝试以粤讴、弹词、歌体推进诗歌的进化,这一点受到了当代评论者的高度肯定,笔者于此不敢苟同。弹词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能否拿来作为古体诗的替代,恐怕很难行通;粤讴作为区域性的民歌艺术,以之来取代古诗体,显然也行不通;只有歌体的自由、通俗、大众,与梁启超提出改良国民性的精神相契合。黄遵宪、梁启超创作的歌体诗都有明确的宣传目的。歌体诗继承了古体诗之乐府歌行等形式,适应近代宣传鼓动之功用,其在诗界革命后呈现两个走向:其一是逐渐与音乐靠近,成为真正的“歌诗”;其二是标语口号体或者叫做宣传体。这两个方向在南社都有不错的作者,前者如李叔同,是近代最著名的歌词作家*1905年李叔同编印《国学唱歌集》,1958年丰子恺编《李叔同歌曲集》,1990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弘一法师歌曲全集》。。后者如高旭。高旭早年在诗界革命影响下写过不少歌体诗,如《醉歌行》、《夷门行》、《新杂谣》、《侠士行》、《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近事新乐府三章》、《海上大风潮起作歌》、《光复歌》、《逐满歌》、《国史纪念歌十八章》、《登富士山歌》、《路亡国亡歌》等。但是这不能代表南社诗歌的主流趋向。南社诗歌学唐学宋,唐诗讲兴会,宋诗讲锻炼,都属于古典诗学的范围,与通俗化大众化无关。如果从诗体革新的角度看,南社较之诗界革命无疑是一种后退。
但后退不等于保守落后,从新古体诗的蜕生看,南社的后退无疑是古体诗向新古体诗迈进的一大步。古体诗基本上是一种士大夫的文学,明代有所谓台阁体,就是一种馆阁诗;与之相对的是山林诗,其实就是在野诗。进入清代,又有所谓儒者之诗、学人之诗、志士之诗、才人之诗、诗人之诗等分别,归根到底是缙绅文学。南社的诗歌革新没有选择体式,而是在诗的精神气质上做文章。柳亚子《寄胡寄尘诗序》批评清末诗坛:“就而视之,外吏则道府,京秩则部曹,多材多艺,炳炳麟麟,而韦布之士,独阒然无闻焉。呜呼!此与职官表、缙绅录何异?……余与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而尤重布衣之诗,以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肉食者所敢望。”*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7页。缙绅文学独尊诗坛,而“韦布之士”被排斥无闻。南社提倡“布衣之诗”,发起了对诗坛缙绅独尊地位的挑战。
“布衣之诗”包含有哪些特点?其一是重气节。南社的原型是几社复社,而几社复社的文化精神在明清之际就是由复兴古学演变为反清的民族气节。南社成立之初的《南社例十八条》第一条就是“品行文学两优者许其入社”。所谓“品行”,指的就是气节。傅尃总结南社在民国前后之表现,指出民国前“以激励国人为职帜”;民国后,“属大盗当国,欺世窃帝,威暴陵轹,士或以鬻;而吾社断躯瘐狱,逃命遁迹,不为威屈利疚者,盖顶趾相望,而刘歆、扬雄之伦不与焉,则数年来砥砺气节之效也。”*傅尃:《南社丛选序》,胡朴安选录,沈锡麟、毕素娟点校:《南社丛选》卷首,第3页。认为在袁世凯专政期间,南社人能“不为威屈利疚”,是由于数年来砥砺气节之功效。柳亚子《寄胡寄尘诗序》也强调南社民国后“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其二,布衣之诗的情感特点是慷慨激昂,奔放无羁。柳亚子《天湖阁集序》云:
昔人有言,诗穷而后工,余谓穷亦视其人何如耳。里巷小夫,所志不出藩溷之外,所谋不越温饱之微,求之不得,沾沾然忧之;叹老嗟卑,怨天尤人,毚焉若不可终日。自有识者视之,咥其笑矣,穷亦何必工哉。唯以嵚崎磊落之士,遘晦盲否塞之秋,国恨家仇,耿耿胸臆间,吐之不能,茹之不忍,于是发为文章,噌吰镗鞳,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斯其遇弥穷而其诣乃益工矣。*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第427页。
柳亚子把“穷而后工”的诗人分为“里巷小夫”,“叹老嗟卑,怨天尤人”的退官废吏和“嵚崎磊落”之士三种*柳亚子《斥朱鸳雏》反驳朱玺曰:“‘穷愁抑郁,苦语满纸’,正为仕宦未显;‘叹老嗟卑’,愈足见其无耻;‘忧国如焚,警惕一切’,彼亦第忧索虏之亡,而平生希望将绝耳。”见《磨剑室文录》,第473页。《胡寄尘诗序》云:“盖自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可见“叹老嗟卑,怨天尤人”指清朝的退官废吏。,前二者即使穷而其诗不能工,只有后者才能穷而后工。原因在于前二者说的是个人的情感,后者说的是国恨家愁。前二者其音苦,其调涩,后者则其音“噌吰镗鞳”。周实《无尽庵诗话》说南社诗“慨念国魂不振,奴性难除锄,思以淋漓慷慨之音,一洗柔软卑下之气”*周实:《无尽庵遗集》卷一,上海:国兴印刷所,1912年。。慷慨悲歌,激昂奔放是一种少年人的感情特征,所以曹聚仁曾在《南社·新南社》一文中说南社的诗文有少壮气,暗示着中华民族的更生。

南社顺应时代的要求,继承了诗界革命新民的路径,充分发挥了诗歌兴观群怨的政治功能;南社扎根传统文化,肩负推翻专制政体、实现民主共和的使命,对诗界革命“西化”的诗学进行了拨返;南社对西学的理解选择更深入理性,将之落实到社会制度层面的诉求,显示了对西学吸纳的推进;南社的诗体革新基本放弃了诗界革命用通俗化、大众化的粤语、弹词、歌体替代古体诗的方向,而是通过改造古体诗的内蕴气质,用“布衣之诗”的精神气韵来冲击古典诗歌的内在品质,实现诗歌从缙绅文学向草泽布衣文学的转变。
至此,古代诗歌的学术根基、语言系统、相对稳定的体式与审美趣味,以及精神气韵被诗界革命和南社的文学变革所冲击,已经蜕变出一种保留古典诗歌形式而今非昔比的体式。
古代诗歌走向现代的旅途中,并非单边运动,单线推进,最后结成新诗的“硕果”,而是多边运动多向前行。诗界革命与南社,从发生时间考量,南社无疑接受了前者的影响或者教训,把诗歌的现代转型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从与现代新诗关系的角度考量,又是两种路向、两副车驾。诗界革命与新诗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诗歌体式的解放与语言的浅白,直接导致了“五四”以后的新民歌运动;其二是借径于西方,用西方的思维、情感方式表达西化的生活体验。南社对新诗的影响甚微,胡适等人对南社尖刻的批评就能见一斑*胡适曾对南社进行过尖刻的批评,参看拙作《南社研究》第八章《南社解体原因新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南社在诗歌转型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在古体诗的肌体里注入草泽布衣文学精神,使之成为古体诗走向新古体诗的转折,促成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南社诗的基础上蜕生出一种新诗体——新古体诗。当然新古体诗并非由南社完成,它还要经受历史的洗礼,新学制的实行,现代学科观念与学术体系得以建立,彻底断绝了废除科举制度后读书人对传统学术的依赖,古体诗也完全失去了赖以生长存在的根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古体诗被冠之以“死文学”的恶谥,处境尴尬,举步维艰;但是运动风潮之后不论是旧派文人还是新派学者,甚至活跃于政界的革命家们,往往放不下传统诗歌体式,经过他们坚持不懈的创作,古体诗完成了蜕变,生成一种与新诗并行的另一种现代诗——新古体诗。
[责任编辑刘培]
作者简介:孙之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
——以广东社友的交游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