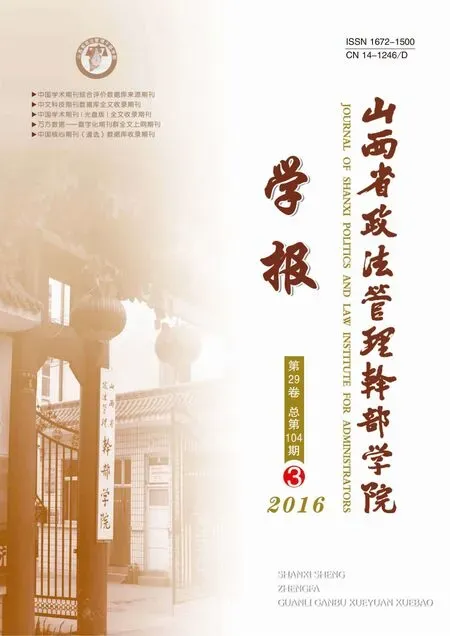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费用激励问题探究
赵子琪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民商法研讨】
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费用激励问题探究
赵子琪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构建诉讼成本激励机制能够最直接的解决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起诉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诉讼费用交纳上,对财产性案件,原告可先预交少量受理费,待案件审理完毕后再据判决补足;在费用补偿上,法院据申请判令公司对胜诉原告、善意败诉原告及带来实质利益的部分胜诉原告进行合理补偿较为适宜;在律师费用激励上,应扩大我国风险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促进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起诉。
股东代表诉讼;费用补偿;风险代理;成本激励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主要在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予以规定,当前,其存在的最引人关注的问题是激励难题。虽然该制度的运用能够较好的保护公司利益,但是在股东是否愿意提起诉讼这一基础问题上,却存在困境。这是因为,基于理性人的立场,股东在决定是否起诉时,除为公司考虑外,最关注的还是自身的利益状况。一方面,胜诉存在风险,诉讼目的能否实现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即使胜诉,股东从诉讼中获得的收益也远远低于其为此承担的成本。加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还可以转让股份,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公司,从而避免因公司利益受损而使自身利益间接受损情形。因此,如何促使股东自愿积极的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成为该制度运用的关键。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最显著的落脚点应当在如何平衡股东的诉讼收益与成本承担问题上。而构建诉讼成本上的激励机制可以最直接的影响股东提起诉讼时的利益考量,从而改善其处境,促使其提起诉讼。因此,本文主要从诉讼成本激励机制出发探讨如何破解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激励难题。需要说明的是,股东在提起诉讼过程中,其消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都属于诉讼成本,但是本文所指的诉讼成本仅限于诉讼中的金钱。
一、诉讼费用的交纳
股东代表诉讼涉及的费用主要包括三部分,即法院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及其他当事人费用,如差旅费、食宿费等。从法院诉讼费用方面看,当前该诉讼多涉及公司财产,根据2007年《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二十条规定,我国财产性案件的受理费是由原告、上诉人或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价额,按照比例分段累计预交。鉴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金额一般较大,尤其在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因此,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通常较多。而提起诉讼的多为公司中小股东,难以承受如此高额的费用,这就直接影响了其起诉的积极性。此外,实践中也出现原告股东为少支付案件受理费而减少诉讼请求金额的情况,“之所以降低索赔数额关键在于诉讼费用的不合理性。”[1]此时,即使原告胜诉,公司的损失实际上并未得到完全救济,如果其他股东就公司剩余损失再次起诉,法院可能会因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不予受理。因此,要求预交高额受理费实际上违背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目的。
对于此类案件,美国联邦法院通常不考虑诉讼标的,而是按件收费,其“民事诉讼的案件受理费一般在30到100美元之间,”[2]即人民币191到639元之间;日本在2006年《公司法》第八百四十七条第六款中规定“对诉讼标的价额进行计算时,应按照非基于财产权上的请求之诉来计算,”[3]也即按件收费,“案件受理费为定额,即现在一律为13,000日元,折合人民币大致为900元左右;”[4]“韩国‘民事诉讼等印花税法’也将该诉讼视为无法知道诉价的诉讼,不考虑请求金额,一律将诉价定为1000万韩元”,[5]并以此为基准计算固定案件受理费,按照我国现行财产案件收费比例计算约为人民币1180元。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对股东代表诉讼案件通通采取非财产性案件的收费标准,并且其收费额度大约在人民币1000元左右。
理论界多数学者因此主张,我国也应当统一改按非财产性案件标准减少收费金额,激励股东提起诉讼。而出于我国非财产性案件收费低,可能会引发滥诉现象的考虑,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在非财产性案件收费标准基础上,同时采用诉讼担保制度加以限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仍然按照财产性案件标准收费,但应设定数额上限,其理由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司法投入不足,“直接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作为非财产类案件来收取少量的诉讼费用尚不现实。”[6]
笔者认为,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大部分涉及财产性利益,如果一律将其按照非财产性案件收费,一方面不符合案件性质,另一方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十三条可知该类案件每件只需交纳50元至100元,这个标准对营利性公司的股东来说似乎又太低,易引发不当诉讼目的下的滥诉。因此,为了不对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施加过大的成本负担,同时又考虑到受理费太低不利于缓解法院司法压力、也易导致滥诉,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建议仍按照财产性案件标准收取诉讼费用。但是原告股东在起诉预交案件受理费时可以只交一个固定的数额,比如1000元,待案件在法院审理完毕后若原告败诉,再由其按照收费标准补足尚未交纳的受理费。这样不仅缓解了原告股东的成本压力,而且也有利于激励股东在充分搜集证据、有胜诉把握情形下提起诉讼,可以有效抑制恶意诉讼,进而保证诉讼质量。
二、相关费用的补偿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如果原告股东败诉,则需要负担除对方律师费及其合理费用外的全部诉讼相关费用;若胜诉,原告也需自行承担己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而胜诉时基于该诉讼的代位性,胜诉利益直接归公司,原告也只能按其持股比例从中受益。公司对原告股东为诉讼支出的相关费用不予补偿不合理,也易加剧原告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间的失衡状况,不利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激励。因此,有必要明确公司对原告的费用补偿机制。在对国内及国外相关规定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本文以比较法视角,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一)补偿原则
公司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对原告股东进行补偿?从最高院及各高院相关意见来看,均规定了胜诉股东可以获得公司补偿,而对败诉原告只有江苏省高院在《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八条中指明诉讼相关费用由其自担。国外对该问题的处理也分为两种模式,以日本《公司法》第八百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以及韩国《商法典》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为代表,确立了胜诉股东对公司的费用补偿请求权;而德国、美国《商事公司法》第7.46节规定以及英国《民事程序规则》第19.9第七款规定均表明不论原告最后胜诉或败诉,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原告都可要求补偿。这里的条件包括美国要求使公司获得实质性利益,英国要求原告提起诉讼是合理并诚信的,德国要求案件须经过法院诉讼许可进入正式审理阶段。
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目的在于维护公司利益,基于此,股东在提起诉讼时,与《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直接诉讼不同,其出发点并非为了自身利益,无论胜诉或败诉,都不会直接享有诉讼收益,从而使“股东代表诉讼本身具有‘公益性’。”[7]加之,股东的诉权来源于法律的直接授权,诉讼并非以传统公司人格独立理论为依托,根据《公司法》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般发生在公司怠于或无法行使诉权的情况下,有前置程序的要求。因此,在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的董事会、监事会怠于作为的情况下,股东代位公司提起诉讼,在诉讼中就具有公司董监事会的作用,类似于公司监督管理人地位。在此种法理基础上,笔者认为,对于尽到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的败诉股东也应当予以补偿,而对于恶意的败诉原告,由于其诉讼目的并非维护公司利益,非出于管理公司事务原因,公司对相关费用无须补偿。另一方面,从诉讼功能上看,股东代表诉讼除了能够使受到损害的公司获得赔偿,还具备威慑被告不再以错误行为危害公司利益的功能。原告败诉时,必然无法使公司获得赔偿,但通过诉讼程序的进行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阻遏、威慑作用,对公司未来利益起到保护作用。在此意义上,也有必要进行补偿。此外,从激励作用角度出发,对公司来说,补偿败诉股东费用相较于原告胜诉为公司挽回的损失来讲微乎其乎,但却能够鼓励原告不因败诉而放弃为公司利益起诉,这样也利于促进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
关于获得公司补偿应否附加条件限制问题,笔者认为,英国要求诉讼合理诚信实质上与我国学者主张的原告善意没有区别。美国要求诉讼使公司获得实质利益,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制度目的,也能够减少无益、恶意诉讼,利于形成倒逼机制,使原告股东真正站在公司角度充分准备诉讼,提高诉讼质量,应予以借鉴。由此,在赋予股东费用补偿请求权时要求其善意、并且通过诉讼为公司带来实质利益较为合理。
笔者认为,公司应尽量对原告股东相关费用予以补偿,以减少股东诉讼成本。当原告完全胜诉,胜诉利益直接归公司,根据谁受益谁分担的一般准则,公司应对诉讼相关费用予以补偿。在原告完全败诉时,原告代位公司提起诉讼类似于管理人地位,因此,对善意原告,公司应进行补偿;对恶意原告,无须补偿。在原告部分胜诉时,应以是否给公司带来实质利益为准决定补偿。这里的实质利益既包括金钱利益,也包括“如撤销被告与公司之间的股份转让合同、重大交易合同、要求被告归还公司印章等重要文件的非金钱利益”,即“只要使公司避免或减少损失,即视为公司获得实质性利益”。[9]以此使大多数原告股东在未完全胜诉时也可获得补偿,激励其起诉。
(二)补偿程度
公司对原告股东费用补偿的界限如何限定?国内大多限定为对胜诉股东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进行适当补偿,仅江苏高院在《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八条中明确了胜诉补偿费用的具体构成。美国《商事公司法》第7.46节、ALI《公司治理原则》第7.17条,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19.9条第七款,以及日本《公司法》第八百五十二条第一款,韩国《商法典》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等对原告费用补偿都有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国外对胜诉股东补偿范围也限定在除法院诉讼费用以外的律师费及其他必要费用内,对败诉股东“美、日、韩等国缺乏对此问题的相关规定,英国则对有合理理由起诉的败诉股东与胜诉股东获得费用补偿的范围作了相同的规定。”[10]同时在补偿程度上除要求是合理、必要、适当费用外,美国还有公司的补偿不得超出原告股东为公司赢得的救济(包括非金钱救济)价值的一个合理的比例的限制,日本、韩国也规定补偿金额应在因诉讼产生的实际费用数额范围内,英国则将补偿金额的具体决定权交予法院。
由此笔者建议在补偿费用的具体构成上,对胜诉原告,其法院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只需补偿律师费及其他当事人费用。对败诉善意股东,由于其提起诉讼出于维护公司利益目的,没有明显过错,并且实践中败诉多由于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其他配套制度不完善,如没有规定公司协助提供证据义务,导致关键证据难获取,举证不能而败诉,因此,其需承担的法院诉讼费用应当得到公司的补偿。为激励起诉,公司也可以承担一定比例的律师费及其他当事人费用。这里可以考虑败诉股东及其律师在诉讼中的具体表现、案件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在补偿的程度上,原告股东原则上仅限于就诉讼实际产生的合理、必要、适当费用,要求公司进行完全、足额的补偿。是否合理、适当、必要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发挥自由裁量权判定。这里可以借鉴日本东京高院相关裁决中法院对“相当金额”的认定标准,即“考虑到请求的金额、当事人数量、案件的难易度、律师工作的繁简程度(口头辩论的天数、提出的诉讼材料的内容、证据调查的内容、协商和解的过程、案件持续的时间等)、起诉前采取的措施、公司在诉讼结果中得到的利益等诸多事项,客观判断。”[11]不同案件在补偿程度上有不同幅度的变化,也有利于达到对原告实质补偿的目的。同时,公司对原告的补偿也应以原告为公司带来利益的范畴为限。公司通过诉讼获得财产性利益的,补偿不应超过该利益范围;获得非财产性利益的,也应根据案件的诉讼因素来确定合理的数额进行补偿。
(三)补偿决策
谁来决定公司对原告股东进行费用补偿?国内外基本规定了三种模式:一是由法院直接判令公司负担相关费用或公司对原告予以补偿,此种方式体现在江苏高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八条,上海高院民二庭《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第一部分第(五)项,以及美国《商事公司法》第7.46节规定中;二是规定股东对合理费用可以向公司主张承担,即明确赋予原告股东费用补偿请求权,主要在山东高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八条,江西高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六十三条,日本《公司法》第八百五十二条第一款以及韩国《商法典》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中有所体现;三是根据原告的请求或申请,由法院判令公司负担或补偿相关费用,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19.9条第七款以及我国最高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五条有规定。
笔者认为,通过法律仅赋予原告费用补偿请求权,而未规定公司拒绝补偿时原告的具体救济措施,即“原告股东是需要再向法院起诉来寻求救济,还是可以直接依据法院关于该股东代表诉讼的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实质上是将补偿与否的决定权交到公司决策机关手中。鉴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多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乃至控股股东等,其对公司的决定影响力较大且存在利益冲突,可能会使公司最终做出不予补偿决策,而原告无从救济,使其利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因此,费用补偿与否应当由法院决定。若由法院直接判令公司对原告补偿,不考虑当事人是否申请,违背了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由此,采用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及公司对原告股东的费用补偿相关事项进行判决的方式较为合理。如果公司拒绝履行其费用补偿义务,原告股东便可直接依据法院的生效裁判书申请强制执行,以此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基础上实现对其利益的有力救济。
三、律师费用的激励
律师费也是股东代表诉讼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国外为促进股东提起诉讼,在律师费用上设置了特别的制度规定,典型代表是美国的“胜诉酬金”制以及英国的有条件付费制。后者要求律师与原告签订协议,只在案件胜诉时律师可在一般成本中索要固定数额的“成功酬金”。此种做法虽然能够激励律师代理案件的积极性,但是基于报酬数额固定,律师胜诉后收益与其在案件中通过努力争取到的胜诉赔偿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又会反过来限制其最大程度的代表公司利益诉讼。相较而言,“胜诉酬金”制在激励作用上有其优越性。该制度下,在胜诉或和解为公司带来实质性收益时,律师获得的报酬是根据公司所获赔偿的一定比例计算的,将律师在诉讼中的所有努力与其收益直接挂钩,其在案件中争取到的赔偿越多,所获得的代理费就相应增加,无疑会有力的推动诉讼的进行。同时,败诉时律师费用自担,当事人的诉讼风险一定程度上移转给律师。这就使律师在决定是否建议当事人起诉时,能够适时运用专业知识对胜诉可能性等进行判断,减轻当事人败诉风险,激励其起诉。
事实上,我国早已存在类似美国“胜诉酬金”制的风险代理收费机制。国家发改委、司法部2006年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确认了风险代理收费的合法性。那么,可否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引入该机制?从第十二条规定看,当前仍需解决群体性诉讼案件不适用风险代理收费的问题。这是基于我国《公司法》一百五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提起该类诉讼没有持股比例及持股数量与时间的要求,即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属于单独股东权。而在股份有限公司中,由于提起诉讼的股东必须符合持股比例、数量及时间的限制,因此,中小股东通常联合起来起诉,导致该类诉讼多为群体性诉讼,在当前规定下其律师费无法适用风险代理收费机制。
国外的风险代理制度实际上并不排斥群体性诉讼的适用。美国仅将家庭关系案件及刑事辩护案件排除在外,而在集团诉讼中,风险代理制度已成为集团律师最普遍的收费方式。[12]日本风险代理制度适用范围甚至比美国更大。[13]而我国排斥群体性诉讼适用的理由,笔者认为,可能是担心出现律师煽动当事人起诉,为自身利益与被告串通和解,恶意诉讼、滥诉等现象。其实,这些可能由风险代理引发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相应制度的健全得到解决,比如加强法院对诉讼和解的审查等。此外,对群体性诉讼适用风险代理制度,也能够化解原告无力承担律师费用的困境,将律师利益与原告利益捆绑在一起,减轻诉讼风险、减少诉讼成本。因此,缩小到股东代表诉讼中,基于我国当前实践中60件股东代表诉讼案件只有1件针对股份有限公司提起的现状,有必要扩大风险代理的适用范围,通过该制度的运用从诉讼成本方面激励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小股东起诉。
[1]谢良兵,邰婷婷.“潘石屹案”:股东代表诉讼的标本案例[N].法制日报,2004-09-15.
[2]周剑龙.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司法运用[A].赵旭东.国际视野下公司法改革[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10][日]高桥均.股东代表诉讼的理论与制度改进[M].梁 爽,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4]王 丹.派生诉讼资金激励问题研究[J].比较法研究,2015(5).
[5]胡宜奎.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公司参加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
[6]王 丹.公司派生诉讼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7]耿利航.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成本承担和司法许可[J].法律科学,2013(1).
[8]何张凤.股东代表诉讼[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
[9]胡宜奎.论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费用补偿[J].政治与法律,2014(2).
[11]赵亚坤.群体诉讼中律师风险代理制度研究[D].保定:华北电力大学,2011.
[12]石 媛.律师风险代理制度探析[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
[13]黄 辉.中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实证研究及完善建议[J].人大法律评论,2014(1).
(责任编辑:李江贞)
Analysis of Cost Incentive Mechanism of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awsuit in China
ZHAO Zi-qi
(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cost incentive mechanism can most directly solve the problem that plaintiff lacks motivation to prosecute in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Plaintiff can pay a small fee in advance for property cases, and then make up cost according to judgment; it is appropriate that the corporation should compensate the winning plaintiff, the partial victory plaintiff with substantial benefits and the unsuccessful plaintiff with good intentions with reasonable expenses;for attorney fees,we should exp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n risk represent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in the joint-stock companies to file a claim.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awsuit;expenses compensation;risk representation; cost incentive
2016-06-01
赵子琪(1991-),女,山西人,西南政法大学2014级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DF411.911
A
1672-1500(2016)03-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