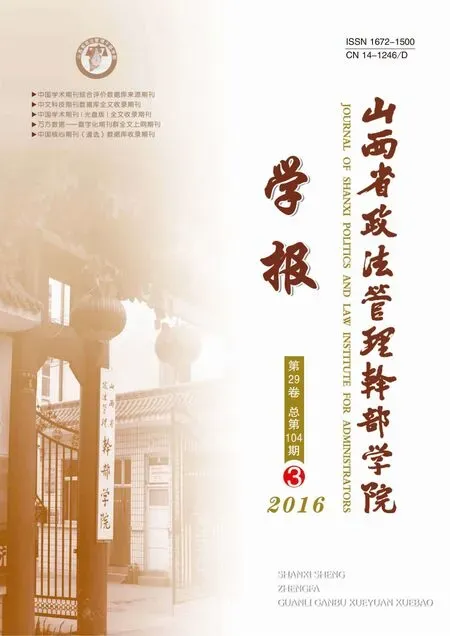国际投资仲裁中对人管辖权初探
马 敏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司法实务】
国际投资仲裁中对人管辖权初探
马 敏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对人管辖权不仅应当包括仲裁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还应当包括主体的主观同意。但近年来,ICSID为扩张其管辖权,不论是主体资格还是主观同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即附加便利机制和无默契仲裁。各缔约国在确定对人管辑权的认定因素时,能借由对人管辖权的扩张来放大CSID的管辖权,同时,应当注意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的“同意”方式。
国际投资仲裁;对人管辖权;主体资格
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对物管辖权和对人管辖权通常是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法院据此确认其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无施加约束的权限。对人管辖权相较于对物管辖权更为复杂,因为人具有流动性,法院有时就必须通过权力扩张获得对被告的管辖权,例如,美国的长臂管辖制度就是如此。而在国际投资领域当中,任何仲裁机构对争端进行管辖都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事实上同样存在对物管辖权和对人管辖权的问题。仲裁机构解决争端主要有仲裁和调解两种方式,而仲裁因其正式性、对抗性、裁决终局性等特点适用更为广泛。*就ICSID官方网站目前为止公布的数据而言,调解类型的案件仅有9例,而仲裁类型的案件有551例。就仲裁而言,所谓对物管辖权主要是围绕争端内容是否可以提交仲裁,而对人管辖权不仅从客观上要考虑投资者和东道国的主体资格,还需要双方主观上的“同意”。[1]
一、ICSID要求的主体资格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依据《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又称《华盛顿公约》或《ICSID公约》)得以建立。《ICSID公约》1965年被批准,1966年获得生效,截至目前,该公约已经有160个成员国。ICSID秘书处登记在案的有560个案件,已有351个审理完毕,剩余209个案件悬而未决。*参见ICSID官方网站,https://icsid.worldbank.org/apps/ICSIDWEB/cases/Pages/AdvancedSearch.aspx[EB/OL],2016-02-26.ICSID审理案件之前,管辖权是必须解决的程序性事项,只有仲裁庭确定其对争端拥有管辖权之后,才能对案件实体争议进行审理和裁决。
(一)《ICSDI公约》条文的限制
《ICSID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中心的管辖适用于缔约国(或缔约国向中心指定的该缔约国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因直接投资而产生并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的任何法律争端。该条将仲裁庭管辖适用的主体资格限于公约缔约国和另一缔约国的国民,也即东道国和投资者母国都必须是该公约的成员国。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缔约国”是指已经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国家,不论条约是否生效。所谓可以接受ICSID仲裁庭管辖的缔约国是指ICSID秘书长登记仲裁申请之时,该争端东道国已经满足成为公约缔约国的要求。而“缔约国指定的组成部分”包括国家的领土单位,如省、州和市,“缔约国指定的机构”是指可以代表该国行使公共职能的实体。[2]该条也对“另一缔约国国民”进行了解释,从自然人和法人的角度分别对“缔约国国籍”进行了阐述。多数情况下的投资者是法人身份,投资者国籍实际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投资者必须是《ICSID公约》成员国的国民,其次,投资者不能是东道国的国民,这两个条件是可以正反佐证的。若以双边投资条约作为仲裁的依据,则很明显,接受管辖的双方主体就是条约缔约一方和另一方的国民。而根据该公约规定对国籍进行判断不仅有时间上的结点,对国籍的界定本身也是技术上的问题,它客观上成为了决定仲裁庭对投资者有无管辖权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二)新的契机——附加便利机制
1978年,ICSID理事会创设了附加便利机制(Additional Facility),专门用于处理ICSID管辖范围之外的案件。相反层面而言,这是ICSID管辖权的扩张之举。长久以来,ICSID就拥有广泛的管辖权,在Lucchetti诉秘鲁案中,智利投资者Lucchetti依照双边投资条约对东道国秘鲁提起了仲裁,秘鲁反之依据双边投资条约对智利启动了国际司法程序,但最后仲裁庭拒绝中止仲裁程序,导致国际司法程序被迫停止。由此可见,ICSID的仲裁程序不会受到其他国际救济程序的干涉。《ICSID公约》本身管辖权的范围只通过公约文本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但ICSID仲裁庭在诸多案例中通过条约解释不断扩张其管辖权,该附加便利机制无疑是超出公约最基本范围的制度创新,严格来说,其不应当属于ICSID的职能。
从主体资格的角度来看,附加便利机制对ICSID管辖的突破主要在于其可以处理仅有一方当事人为《ICSID公约》成员国或成员国国民的案件。该机制对于没有批准加入《ICSID公约》的国家具有现实意义,其既不会因为案件本身受到《ICSID公约》的限制,又可以将争端置于ICSID中心严密的管辖程序之下。在该机制之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将不适用《ICSID公约》,而与国际民商事仲裁裁决一样,适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崛起,逐渐与发达国家形成对峙,两边各自主张的卡尔沃主义和赫尔规则对于财产征收的补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联大决议没有明确任何一种主张,但条约必须遵守和习惯国际法的地位却得到了确认。随着双边投资条约的签订,发展中国家不再可以仅仅凭借国内法规则对外国人的保护和外国财产征收采取措施。相比较传统的外交保护方法需要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而现代国际仲裁程序减少了投资者获得保护的难度。但是附加便利机制下的裁决和国际仲裁庭下的裁决还是存在明显差异,一般的国际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而附加便利机制下的裁决可能会被适格的国内法院审查乃至撤销。不论这种制度创新是否是ICSID的权力扩张,只要其有可以依托的公平的规则,不失为国际投资仲裁突破ICSID传统主体资格限制的方法。
二、争端双方的主观同意
国际投资仲裁究其本质还是仲裁,而仲裁的基础是仲裁协议,ICSID仲裁也不例外,同样需要仲裁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实定法学派就主张仲裁需要合意。不论是国际商事仲裁还是国际投资仲裁,都强调仲裁协议的书面性,甚至在同一书面文件中确立双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
(一)传统的书面同意
《ICSID公约》在起草阶段,世界银行总顾问阿伦·布洛切斯(Aron Broches)就声明ICSID中心管辖机制是自愿使用的,仅加入《ICSID公约》不等于愿意接受中心管辖,ICSID不会强制缔约国将争端提交给中心管辖,争端双方还必须另外表示同意ICSID的管辖。[3]《ICSID公约》第二十五条要求这种同意必须是“双方书面同意”,对同意的形式作出了限定。批准公约仅仅构成ICSID具备管辖权的前提,而争端双方的同意是限制条件。一旦双方对于仲裁管辖作出了同意,任意一方不得再单方面撤回这种同意,此时自愿管辖转为强制管辖。
书面同意一般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首先,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后直接通过缔结书面仲裁协议表示接受ICSID管辖。且这种仲裁协议可以是单独的,也可以体现在投资协议当中。这是比较常见的形式,在国际民商事仲裁中也尤为普遍。其次,接受ICSID管辖的同意可以体现在国内法的规定当中。法律具有普适性,这就可能导致表示同意的规定过于宽泛,发生争议后无法明确争议是否属于ICSID仲裁的范围。再次,以投资条约中的仲裁条款为同意的依据,这种形式已经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目前世界各国订立的绝大多数双边投资条约中都有仲裁条款。最后,书面同意还可以以多边投资条约的方式出现,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两种形式实际上不再将双方当事人局限于公约规定的东道国和投资者,而是延伸到了国家和国家之间。投资者母国的同意并不能代表投资者的同意,因此,这两种书面同意不足以满足公约对主观要件的要求。
一国对ICSID管辖权的接受通过同意表现出来,不论是以投资条约中仲裁条款的形式,还是以国内法律规定的形式,又或者上升到国家交往层面,以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以多边投资条约的方式。这种同意的直接目的通常是吸引外国投资者,用国际仲裁保护作为表明国内投资法律环境安全的保证。但需要注意的是,ICSID对争端的管辖权获得以投资者或者东道国将争端提交给中心为确定时间点,东道国可能会在争端发生以后、提交以前的时间内修改国内法律,导致提前撤销“同意”,阻止ICSID中心的管辖,这种情况会将投资者置于不利境地。
(二)无默契仲裁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以来,ICSID的管辖权范围明显扩大,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争议双方事先达成的仲裁合意不再成为仲裁的必要前提条件,无默契仲裁初现端倪。所谓无默契仲裁就是指外国投资者依据东道国事先在国内法律或者投资条约中单方面作出的同意将有关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的承诺,将东道国违反保护投资的义务向相关的仲裁机构提起仲裁。[4]无默契仲裁的出现和发展似乎突破了传统的仲裁基础也即仲裁的合意,将投资仲裁由自愿性转向了强制性。该种仲裁管辖权的理论基础就在于,除了在投资条约中预先加入仲裁条款或者在争端发生后另行签订仲裁协议外,缔约国可以通过概括性声明接受ICSID对外国投资者提起的有关投资争议的仲裁。实际上,早在公约起草的过程中,这种观点就已经出现,在《ICSID公约》第二十五条拟定之初就已经提出这种单方面申请进行仲裁的可能性,尽管公约最终并没有采纳,仍然坚持书面同意的要求。
在ICSID为扩展管辖权发生一系列举措之后,仲裁庭终于正式确立以这种单方的意思表示作为ICSID确立管辖权的基础。这种管辖依据的来源主要有东道国国内法律和投资条约两种。在著名的SPP诉埃及案中,埃及政府取缔了香港SPP公司在埃及投资的旅游项目,SPP公司根据埃及1974年的《外国投资法》第八条向ICSID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埃及政府进行赔偿。仲裁庭最终认为该《外国投资法》第八条构成了埃及对ICSID强制性管辖的同意,这种同意符合《ICSID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主观要件。该案就是以国内法律的规定为东道国同意接受ICSID管辖的依据。而以投资条约为依据确立ICSID强制管辖的实践始于1990年的AAPL诉斯里兰卡案。该案中的香港农产品公司投资的养殖场在斯里兰卡发生的军事行动中被占领破坏。该香港公司未与埃及签订过任何投资协议,也未在争议发生后签订仲裁协议,最后只得依据英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向ICSID申请仲裁。根据该双边条约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同意将另一缔约国国民在本缔约国境内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提交ICSID以协商或仲裁的方式解决。仲裁庭一致认为该条规定足以构成ICSID行使管辖权的基础。
实际上,无默契仲裁或者说单边仲裁并不是只有一方当事人同意仲裁,只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双方仲裁的意思表示存在时间和载体上的分离。东道国表示接受仲裁的意思早于投资争议发生的时间,甚至早于投资行为发生的时间。从载体或者形式上而言,双方同意仲裁的表示不在同一法律文件中,甚至没有以书面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对传统仲裁要求的背离。而且,无默契仲裁只为投资者提供了救济的可能性,东道国无法借此制度主张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无默契仲裁还是为国际投资保护呈现出新的契机,使得仲裁合意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面同意”形式。
三、“谢业深案”引发的思考
对人管辖权原先是民事诉讼法中的概念,以美国为例,法院对其领土所及范围内的所有事项(除联邦法院专属管辖事项外)有一般管辖权(general jurisdiction),[5]事物管辖权决定了案件纠纷归属于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管辖。美国法院不仅需要对某一事项有事物管辖权,还需要对被告有对人管辖权(personal jurisdiction),这决定了美国联邦或者州法院对案件纠纷有没有管辖权。对人管辖权的依据可以是被告本人,也可以是被告的财产,都是对被告本人发生作用。对人管辖权又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对人诉讼(in-personam)、对物诉讼(in-rem)和准对物诉讼(quasi-in-rem)。国际投资仲裁和民事诉讼中的对人管辖权问题只在对“人”方面具有同一性,实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中国而言,投资仲裁方面的对人管辖权问题也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谢业深案就是其中一例。2006年9月29日,香港居民谢业深向ICSID提出仲裁申请,因秘鲁税务局对谢业深在秘鲁境内设立并拥有90%股权的的TSG公司采取了税收征管措施,根据1994年中国与秘鲁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向秘鲁提出索赔。2009年,仲裁庭就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决,认定ICSID有管辖权,实际上外界都把该案作为ICSID扩张管辖权的例证。
(一)投资者是否“适格”
中国和秘鲁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中方投资者是指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这里就会产生疑问,香港居民是否是拥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仲裁庭就此案认定,谢业深可以依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仲裁,是适格的投资者。事实上,在该双边投资条约签署之时,香港尚未回归中国,因此该条约不应适用于香港。且根据中国和秘鲁之前的自由贸易协定,双方的领土范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包括领陆、领水、领空,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主权权力和管辖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香港不应涵盖在该范围内。仲裁庭仅仅依据双边投资条约就认定谢业深为适格的投资者,实际有不妥之处。香港居民和中国国民不是必然相同的,部分香港居民有中国国籍,在国际法意义上是中国国民,满足中外投资条约当中的“中国国民”定义,但是也有部分香港居民不具有中国国籍。且从时间上来看,香港回归之前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也不能适用于有中国国籍的香港居民。因此,谢业深不能依据中秘双边投资条约就取得“投资者”身份。由此看出,我国港澳台地区在对外投资关系中存在交往的漏洞,将仲裁庭对条约的解释一味地适用于这些特殊行政区域有失妥当,首先就条约本身而言,其并不一定能适用中国某些地区,其次,在条约不能适用的情况下,对条约的解释也自然不能用于该地区的居民。
(二)是否达成双方“同意”
根据《中秘双边投资条约》第八条的规定,投资争端首先应当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再通过东道国国内司法途径解决。第八条只明确中国和秘鲁双方同意将“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提交ICSID仲裁,除“涉及征收补偿款额”外的其他争议必须“经双方同意”才可提交ICSID仲裁庭。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和三十二条规定来解释“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认为“涉及”的通常含义应当是“包括”而不是“限于”,也即“征收补偿款额”仅仅是列举的一项内容,所有有关征收的争议都可以提交仲裁,都是经由双边投资条约中双方同意的。
条约解释应当遵循“善意解释”的原则,也即首先要按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结合条约上下文的语句,并就约文的通常意义进行解释。[6]这些解释原则有应用的先后,也必须都有所顾及。在该案当中,仲裁庭对争端提交仲裁的“同意”进行解释的时候,没有严格遵守“善意解释”的原则,存在着扩大解释的倾向。而扩大当事方同意的形式和范围可以通过限制用尽当地救济和运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等多种途径。[7]在国际实践中,用尽当地原则,是将投资争端递交到ICSID仲裁庭的前提条件。但在公约第二十六条的情形下,该原则发生了适用方式上的变化,即只有在明确要求的情形下,缔约国才能将用尽当地救济原则适用于投资争端,若没有明确的要求,则视为对该权利的放弃。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倾向于优先选择国际法规则,而不是优先适用国内法律,这些规则也逐渐形成保护外国人的国际最低标准。至于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问题通常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可以援用双边投资条约的当事人是否可以依据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享受投资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缔约的条约之下更加优惠的待遇;第二,其他条约之下的当事人是否可以依据其他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双边投资条约下更加优惠的条件,包括争端解决。[8]最惠国待遇条款实际上为ICSID仲裁庭创设了管辖权。甚至有学者认为,即使双边投资条约中没有同意ICSID管辖的规定,投资者也可以基于最惠国待遇条款,援引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规定来申请ICSID仲裁程序。
[1]张正怡.晚近ICSID仲裁庭管辖权裁决的实证考察——兼谈我国首次被申诉案件的管辖权抗辩[J].时代法学,2011(6).
[2]Rudolf Dolzer,Christoph Schreuer.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3]Christoph 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4]杨彩霞,秦 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无默契仲裁初探[J].比较法研究,2011(3).
[5]王泽鉴.英美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Rudolf Dolzer.Indirect Expropriations:New Developments[J].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2003(11).
[7]黄月明.ICSID仲裁庭扩大管辖权的途径及其应对——从“谢业深案”切入[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5).
[8]徐崇利.从实体到程序:最惠国适用范围之争[J].法商研究,2007(2).
(责任编辑:张建萍)
2016-05-05
马 敏(1992-),女,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2014级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私法学。
DF974
A
1672-1500(2016)03-00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