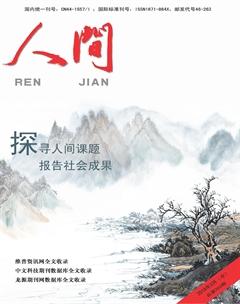爱情小说中的书生情缘
摘要:自古以来,文学便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为人类的感情世界提供一个宣泄口,小说自神话发轫,经过历朝历代的洗练,至唐代已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尤以唐传奇中元稹的《莺莺传》最为突出,张生是一位典型的“恐婚”书生,因外界的原因放弃了与莺莺的爱情,惧怕婚姻给自身带来的不良反应。而《连城》中的乔生则是与张生截然不同的形象,为爱而生生死死,执着于知己之爱。从爱情到结合是一条相互磨合的阶段,或终成眷属,或抱憾终生,磨合中的各个方面都有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而张生与乔生所处环境和自身爱情观的迥异是其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张生;乔生;性格;社会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1-02
开天辟地之时,文学便流传于世间,古人把自身的情感和对神明的敬畏用浅显简略的形式表现出来。自仓颉造字,人类的感情传递便不止于口头的交流,而是诉诸于笔下,各种文体呼朋唤友而来,中国的文学样式层出不穷,而最源远流长的便是诗歌和小说。
无论是唐传奇或是清文言小说,爱情题材永远是稳居榜首。典型人物的创作,任何时候都是小说创作的中心问题,都是摆在小说家面前头等大事。”在众多人物研究中,女性往往是人们争论的重点,男性往往处于一个附属地位或是一个构成故事的符号,其实不然,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封建社会,男权主义盛行的时期,男子的性格、思想是主导爱情的轨迹线。在爱情小说中,男主人公大多以书生为主,所以书生情缘是作品的常客,小说故事常常涉及到爱情与婚姻问题,就关乎一个“过渡”话题。开出爱情的花,却不能品尝甜蜜的果,这是唐传奇故事中普遍的一个规律,这里就有“恐婚”的因素在其中,所谓“恐婚”顾名思义恐惧婚姻,它并不等同于现代名词中的恐婚,其本质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婚姻,所有的男女都有可能相爱,但很有可能不能由爱进行到婚姻。而在清文言小说中,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小说中得到了解决,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较注重心灵上的交流,不仅仅是局限于郎才女貌的追逐上,多了一份知己之爱,他们的感情更加坚韧和有生命力,书生形象也摆脱了轻狂好色的本质,性格上的坚强和对爱情的忠贞让他们成功地脱离了“恐婚”的藩篱,进入到“适婚”的角色里。
唐代宗至宣宗是传奇的发展鼎盛期,佳作屡见不鲜,“然传奇诸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两人:其一,所做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莺莺传》堪称传奇中的状元,具有点醒人心的功用。张生与莺莺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是贯穿其故事的主线,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是小说的结局,多谓张生为薄情郎。其实张生也只是封建制度下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利益权衡下的懦弱者,是唐代特有的“恐婚”书生的典型。张生“性貌温美,非礼不动”,其容貌华美,文采斐然,在这种情况竟然“年二十三未常近女色”,在那个狎妓之风盛行的时代,张生可谓是洁身自好,有着自己处事原则和对未来伴侣的忠贞之情,坚持着自己的爱情哲学。人人都道张生无情,实则不然,他设法通过红娘传《春词》和《会真诗》;莺莺婚嫁后,过其门仍鼓起勇气以外兄的身份要求见莺莺,都可看他对莺莺有着真挚深切的感情,只是社会在抛弃了莺莺的同时也抛弃了他。他对莺莺的爱恋从未停止,只是在强大的封建制度和莺莺忽热忽冷的态度下妥协和变形了,莺莺出身名门,即使是家门没落的世家小姐,也是饱读诗书,才气逼人,在莺莺面前,张生虽苦苦追求,赢得了莺莺的心,但却仍感觉有一层隔膜横在两人中间,莺莺太过冷静理性,即使面对最后的抛弃也理智地面对,似乎是早已料到,这样的莺莺让张生无所适从,这是促使张生“恐婚”的一个契机,莺莺美则美矣,但作为结婚的对象,他犹豫了。张生遂止于京,大社会的影响使他再一次确定了要与莺莺分手的决心,他用了最无力的方式来解脱自己:女人祸水论。细想,“女人祸水论”并不成立,如果张生对莺莺毫无感情了,他不会苦苦追求,更不会过其门而求其见,可见,张生离开莺莺是得了社会风靡的“恐婚”征。在京城那样繁华的地方,受到诱惑是很正常的事,进士擢第、娶王世女和不老成仙是每个书生所梦寐以求的,张生也不例外,一旦娶世家女,便可在仕途上一举成名,所以张生在现实和爱情之间痛苦抉择,最后自身的利益和大众的主流风还是占了上风,同许多书生一样成为了“恐婚”一族。
相较于张生,乔生是忠于爱情,忠于信仰的书生典范。“一书二体”的《聊斋志异》虽是书斋之作,但其中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尤以《连城》最为经典。乔生和连城的爱情通过生生死死的考验,无坚不摧,视彼此为知己,终成眷属。乔生是古代“适婚”的典型,所谓“适婚”书生并不是以适合结婚的男人为定义,指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书生在外界给予的压力面前不畏向前,勇于追求自己爱情而最终与爱人结合的书生群体。乔生不是拥有奇特方术的异人,也不是鬼魅狐妖,是一个生活在现实当中的读书人,他有着科举的热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渴望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他见到连城征婿的《倦绣图》时,读出了连城的心声,随即附和,两个人在诗作往来中暗生火花,由此无法自拔的爱上对方,这是一种知己之爱,彼此惺惺相惜。连城在病入膏肓时,乔生“自出白刃,揆肉授僧”,没有丝毫的犹豫。而后连城病卒,乔生追随连城到黄泉时,连城劝其不要争“泉下物”时,乔生再次坦露心迹:“士为知己死,不以色也”,这是爱情的一次升华,乔生并不在乎外在的虚华,只看重内心的结合,不再是以往以貌而爱的书生。“不谐何害”的新潮观点更让我们对乔生的爱情观欣赏之至,只要两情相悦,任何因素都不能成为障碍。正是这种无功利性的爱情观,才使其“一痛而绝”,厌生乐死,为爱而生,为爱而死。乔生的爱超越生死、超越礼教甚至超越爱情,乔生追求的是灵魂的对话和知己之情,注重的是感情的交付和心灵的结合。
纵观两位书生大有不同,他们不同的心理轨迹和性格成为其爱情故事不同结局的本质原因。首先,从性格上说,张生没有乔生坚强的毅力和为爱受苦的决心,张生在科举仕途的诱惑面前,有过挣扎,有过痛苦,但终究是理性战胜感性,他经过爱情的甜蜜之后,不敢去想象婚姻之后的生活,张生没有从一而终很大是因为毅力和思想不够成熟,带有那个时代的通病:畏于现实而放弃爱情的“恐婚”征。而乔生在面对史孝廉的“千金”时,毅然忠诚于自己的爱情,没有被金钱所污染,即使封建等级制度在阻挠他与连城的爱情,他依然矢志不渝,史孝廉的另择他婿并没有让乔生放弃,而是更加坚定了知己之心,乔生是勇于挑战现实而坚守爱情的“适婚”书生。其次,以科举的魅力来讲,张生更热衷于仕途,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爱情恰好是仕途路上的绊脚石,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张生在艰难的衡量下,受环境的熏染下,选择了仕途,这是他的悲哀。而相较于张生,乔生没有过多地想科举仕途之路,他的心里只有对连城的深情厚意,不受大环境影响,忠于自己的心,对于乔生而言,外界的阻力并不足道,爱情至上的他更适合于从爱情走向婚姻。再次,从等级制度上言,张生更在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与莺莺身份的天差地别也是造成其心理落差的重要原因。古代讲究门当户对,而为考中进士的张生在心理上就与世家小姐莺莺不匹配,他更在乎他人的眼光。而乔生虽遭连城父亲史孝廉的不赞同,然乔生“梦魂中犹佩戴之”,而后的契机更说明他对连城的款款深情。最后,女主人公对书生的态度也是爱情结局的决定性因素,莺莺“端服严容”,对待张生忽近忽远,态度冷淡且对待爱情理性平静,往往有一种神秘感,使张生有莫大的距离感,从而为张生抛弃莺莺埋下祸根,也是造成张生“恐婚”的重要原因。但连城对乔生则是百般依赖和信任,连城理解乔生,视乔生为知己,他们之间是有感情共鸣的,视彼此为知己,他们的爱情攻无不克,克服生死,战胜等级,走向婚姻。
唐至清代,作家愈来愈注重“至情”,情为基底,爱情至上的观点深入人心。男女平等思想也突出重围,成为文学的标榜,束缚千万男女的程朱理学在顾炎武等人的批判下显得暗淡无色,人们大胆追求自由爱情,捍卫自己的权利,从而使小说中书生的爱情观也不尽相同,张生的“恐婚”和乔生的“适婚”应运而生。
欧阳修说的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如果张生能够再勇敢一些,对莺莺的爱坚定一点,唐代社会能够再公平一些,也许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张生和《莺莺传》,也就会有不一样的书生情缘。而乔生让我们相信执着于自己,爱情一定眷顾我们。书生们的情缘止于小说,而不止于社会。
参考文献:
[1]元稹,莺莺传[M].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2]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
作者简介:
李佩玉,女(1990-),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