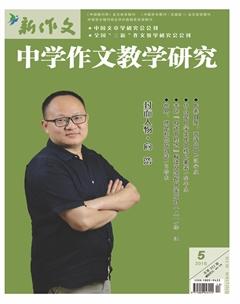陶养自我,言语立命
汲安庆
一
将很主观的写作,与很客观的效度扯到一块儿,似乎有些不伦不类。
仅就高考作文等级评分标准中“内容”一项来说,第一等级的要求是“切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感情真挚”。可是,切合、突出、充实、真挚这些标准,真的可以用科学、精确的刻度明码标出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还经常出现一些争议作文,不同教师给出的分数,差距竟能多达30分?如果可以,是否意味着朱自清的《背影》和鲁迅的《风筝》也会有一个可以量化的区分度?如果可以,“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又该如何看待?
诸如此类的质疑不无道理。与数理学科的答题相比,中学生写作的效度的确无法很精准地加以量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学生写作就无效度可言。在标准恒定的情况下,对一篇作文的评价尽管在小范围内会有所差别,但放置在更大的范围中看,其准确性和有用性则毋庸置疑。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假,但那一定是哈姆雷特,而不是林黛玉或焦大。只要依据标准认真比较,经典之作间的区分度依然可以划出。
如果换种思维,想想中学生写作中的低效、无效甚至反效现象,对写作效度的思考更应理直气壮。
二
低效、无效、反效的现象集中表现在:伪人格、滥抒情、糙叙事、弱说明和空议论。
毫不客气地说,由于怕袒露心曲会触及雷区或被人攻击,捏造已经成了不少中学生的写作“美谈”。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谈自强不息,编出自己残废、父母离世的故事,他们是一点儿都不会脸红的。抒情、议论,满篇的华丽辞藻,名人名言,却难见自我一星半点的真情和真思。在他们的作文中,你看不到花的颜色,听不到鸟的声音,人物内心的隐秘悸动更是难觅踪影。至于说议论类文体中的阐释、界定、分析、分类、反驳,几乎绝迹,唯一得心应手的似乎就是例证或引证。与论点有点儿关系的证据,拿来就扣,对错与否,恰当与否,统统不管。加上一些教师急功近利的诱导,如让学生精心熬制四五篇作品,千方百计地套作,致使学生制造文字垃圾的现象泛滥成灾。明知这种异化写作会令人恶心,却不加扭转,想培养健康、蓬勃、真诚、灵动、富有创造力的言语表现人格,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
据说,作家叶兆言以“禁止鸣笛”的交通标志为题,让学生看图作文,他们竟然也能写出备受推崇的“文化历史大散文”来。比如,从秦始皇的“禁止鸣笛”一直说到岳飞的“吹笛”,驾轻就熟,大放厥词。南京特级教师吴非讥之为“滥抒情,口吐白沫;假叹息,无病呻吟;沾文化,满地打滚;伪斯文,道貌岸然”。试想,这样的矫揉造作还能谈得上写作的效度吗?没有自我在场的梦呓式写作,即使嫁接组合,生搬硬套的功夫再好,都是无效的。没有比培植功利、虚伪、投机的言语表现人格更可怕的事了!梁启超指斥当年的写作教育“奖励剿说,奖励空疏及剽滑,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及不负责任,奖励偏见,奖励虚伪”(梁启超《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现在何尝不是 如此?
没有真诚人格打底的文字,表现技巧越娴熟越糟糕,仅从方法上动心思,想迎合阅卷教师,永远都是歪门邪道。
三
除了人格的决定因素,中学生写作效度的低下,还与知、情、意素养的薄弱,有着紧密的 关联。
说到知的素养薄弱,肯定会有人不以为然。当下的中学生,所学的科目多而深,一个初中生的知识总和便能超过孔子,怎能说薄弱?但一个明摆的事实是:这些学生在写作中呈现的知识充其量只是可怜巴巴的一点儿应用知识,而且还极其简陋,甚至是错误的,学术知识、精神知识,或闲谈和消遣知识表现,几乎谈不上。譬如写一个水杯,你对它的材质、工艺、造型、历史、审美创意一无所知,又能写出怎样高知识含量的文章来呢?即使是文学类写作,知识素养依然举足轻重。《红楼梦》中对服饰、器皿、饮食的细致描写,让人身临其境,可以轻松地加以还原,不正是得力于作者曹雪芹渊深、广博的知识素养,才有了超越时空的定格力和表现力么?
可是,谈到这方面的写作,很多中学生都会望而却步。何故?一味地忙于海量做题,机械背诵,感官早已不知不觉地瘫痪,审美的天眼也随之闭合,生活中的很多知识、情趣都被冷漠地过滤掉了。即使是应用知识的引入,也极其有限。我在初、高中生中不止一次地做过调查:举出你阅读经历中遇到过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描写,无一人能够脱口而出。即使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回忆,依然无人能答。这对很多老师津津乐道的经典片段赏析、写作秘籍传授,不啻一个巨大的反讽。连这种所谓最实效的知识,他们都毫无感觉,更别说化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形象地比喻、说理了,那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挟泰山以超北海。没有知识的化入,写作效度的低下,可想而知。
情的素养薄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照理,现代写作已经彻底摆脱了“代圣贤立言”的束缚,完全可以直抒胸臆了。文章以真情动人,只有感动自我了,感动他人才会成为可能。写作本质上就是一种传递真诚情思的艺术。可是,中学生写作中的真情表现依然不容乐观。集中表现在:①空抒情—— 离开具体的事实、场景,凌空蹈虚,为文造情;②伪抒情—— 一副忧国忧民的模样,成人腔十足,套话、大话连篇;③弱抒情—— 因不懂抒情技巧,也不敢追踪心灵的律动,致使所抒之情单调、乏味,千人一面,毫无韵味可言,因此弱抒情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糙抒情。
我曾指导过一位闽南女生的作文。作者回忆了父亲向母亲赔小心、安慰考试失利的“我”、闲时学习普通话、飞机上变魔术、带“我”逛书店、嘱“我”周末打电话这几件事,即使在白描式的勾勒中也能见出人物的些许神采,且忠于自己的感受,但依然让我觉得有雷同化的嫌疑。我问她,如果选一个独特的意象代表父亲,该选什么,她立刻想到了“蓝蓝的海”,并以之为题(《父爱是片蓝蓝的海》,见《东方少年》2011年第6期),重新对全文雕琢,一下子提升了文章的境界。
这说明,在情的素养培育方面,用真诚的言语表现人格,注重抒情技巧的触类旁通,还有追求独特表达、唯美表达的执着,一个都不能少。唯其如此,才能真实抒情,饱满抒情,自由抒情。
意的素养匮乏最为严重。这在议论类文体的写作中尤为突出,因为“凡是有所主张的文章,就是意的文”〔夏丏尊、叶绍钧.国文百八课.[M].北京:三联书店,2008.(647).〕。在夏丏尊、叶圣陶看来,写作“意的文”,关键是“以有没有敌论者为条件”,强调的是在和假想敌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主张。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中学生写作议论类文章,为了防止因思想另类而跑题,几乎清一色地选择遵命作文——在命题者所命之意的诱引下,在“引——议——联——结”模式的规范下,搜肠刮肚地找些平时就积累好的素材,绞尽脑汁地拼凑、组装,典型的机械作文、奴性作文。如此一来,还有什么效度可言呢?人们指责高考阅卷草菅人命,一秒钟就能给出分数,能看出什么来?避开高分和低分,一个劲儿地围绕平均分上下略作波动,公平性何在?可阅卷教师也叫屈,结构基本雷同,立意大同小异,连“炒冷饭”都几乎一致,想慢一些,想区分度鲜明一些,可是得给我理由啊!
其实,比“敌论者意识”缺席更为严重的还有很多。比如,观念层面强调写作贴近生活而非贴近心灵,强调文从字顺而忽略彰显自我,强调以读带写却忽略以写促读;文体方面,只注重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种教学文体的训练,却忽视了小说、散文、随笔、论文、调查报告等真实文体的训练,指责学生的文体四不像,殊不知任何文体都可以含有叙述、描写、说明、议论的成分,只是比重有所不同罢了。当下写作,最热门的是议论类文体的写作,可是在写作方法上重论证轻分析的现象特别严重,连很多的满分作文、优秀作文都不能幸免。试问,在论述“热爱诞下创造的婴孩”(《热爱诞下创造的婴孩》为2011年福建省唯一的高考满分作文)的命题时,可曾想过:仅凭热爱,是不一定能创造的,而不热爱,一样可以创造的事例也并不鲜见。围绕论点,只找有利于己的材料来谈,难怪要被一些学者视为不讲理了。
当然,关于知、情、意素养的修炼和积淀是个长期的工程,系统的工程。倘若只注重单方面的培养,肯定是无法培育写作素养,提升写作效度的。实际写作中尤其如此,情、意不经知识的统领,便会渺无头绪;知识不经情、意的濡染,永远都是冰冷、异己的存在。
四
对写作效度起根本性影响的还有写作信仰的有无和高下。
必须承认,这种本体性的思考,在很多中学生的心中是极其荒芜的。即使有,也多是停留在为迎合老师,为拿高分,为考名校,为满足虚荣心的层面上——如一度热火的“新概念写作”,很多师生就是冲着获奖可以免试读重点大学去的,比较少考虑到写作是为了记录自我成长的心灵轨迹,与他人实现幸福的沟通与分享,寻找或确证优秀的自我,更谈不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
让写作信仰停留在功利的、实用的层面,动力注定有限。目的一旦达成,动力则会随之消失。但如果进入确证自我言语生命、精神生命的崇高境界,写作则会化被动为主动,化暂时为永恒,化附庸为独立,成为立足生活又超越生活,充盈自我又能实现自我的坚韧而诗意的存在方式,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可以归入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一切。”〔许金声、程朝翔译.[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3.〕
简言之,通过写作,不断地与优秀的自我相遇。秉持这样的信仰,何愁没有写作的效 度?
(福建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3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