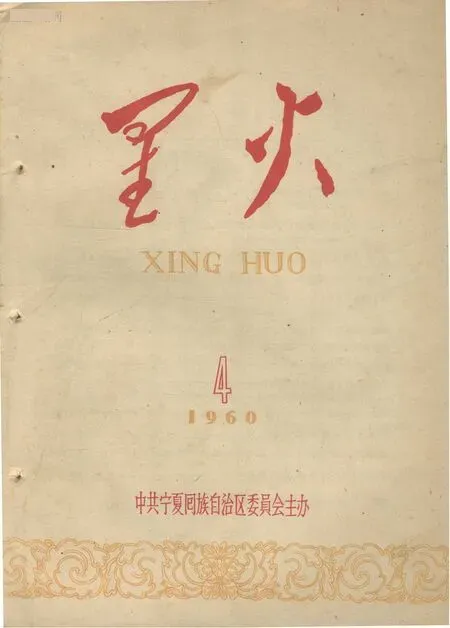每一个人都走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创作谈)
○鲍 贝
每一个人都走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创作谈)
○鲍 贝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天堂到底在哪儿,它长什么模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想象中的天堂。仿佛天堂就在身边、在眼前、在生命中的每一个转角处,它触手即至,却又遥不可及。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座图书馆的模样。而对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姆来说,遇见青枝,便是遇见了天堂。哈姆从小在寺庙里长大,他的身份是喇嘛,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一位圣徒。青枝生活在杭州,这是一座被人称之为人间天堂的城市,但它毕竟不是天堂,只是一座居住着高度密集的人群的城市。它在凡间,带着尘世的味道。
既然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过天堂,它只是靠我们用自身的想象和感受来完成,或者抵达,那么,它亦有可能存在于尘世间的某个地方,或在某个人的身上。
哈姆和青枝,一个来自佛世间,一个来自尘世间,本无交集的可能,但他们却阴差阳错地相爱了,把人世间最无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刻骨铭心、爱得诚惶诚恐、爱得天崩地裂,爱到背叛宗教连信仰都变了,最后连命也不要了……谁又能说得清楚,这种自我毁灭式的爱情,到底是把他们推向地狱,还是把他们带到了天堂?
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到过天堂的人,也一定看见过天堂的模样。爱情即天堂。真正的爱情所挥发出来的魔力和能量,如同佛光普照。
好吧,我并不想借这个故事来讨论爱情本身。爱情没什么好说的。爱情只是一场致幻,一场梦境,没有人看清过它的本来面目,就如同没有人能够把天堂描述清楚一样。为了爱情,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姆成了宗教的背叛者,一个现世的罪人。当然,在这里,我也无意于谈论宗教。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里充满荒凉和苍茫,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总是被神秘而不可知的色泽所笼罩着,又仿佛被看不见的魔掌所控,当我们陷于迷茫或者需要自我救赎的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宗教,宗教是我们最后的退路。然而,宗教真能拯救得了一个迷途中的人吗?
我不是佛教徒,但我从来都保持着一份对天与地与神灵的敬畏心。我相信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宗教具有开启、引导和唤醒的意义,它让我想起佛性、人心、静、寂、定、空,还有那终极虚无。而空与虚无,对于一个俗世中的人来说,却是一份沉重的负担。
哈姆原本是一个圣徒,一个虔诚的修行者,深居寺庙的他通过修行变成了一枝缺少想象的单纯的芦苇。是青枝的出现,重新赋予了他想象、欲望、爱情和另一种生命的意义。哈姆变成了另一枝芦苇。从一枝芦苇变成另一枝芦苇的过程中,毫无疑问,青枝对他起到了开启和唤醒的意义,让他如梦初醒,又如获至宝,也从此变成了一个罪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它是我在几年前行走不丹的旅途中,听一位藏族朋友说的。我只是隐去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从不丹回来之后,我曾心血来潮飞到某市去见哈姆。现实生活中的他,早已被爱情和女人抛弃。听说爱过他的那个女人已回到另一座城市,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他终于一个人在这红尘滚滚的人世间顽强地活了下来,活得风平浪静,活成了现世安稳。是我在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的时候,最后安排他们都去死了,去了另一个天堂。
为了书写方便,我把女主人公的地址搬到了杭州,这是我居住的城市,写起来比较顺手。最初写成的是一部长篇小说《观我生》。现在我把它写成一个中篇,《带我去天堂》,这是我在动笔之前便跃入脑海里来的标题,犹如灵光一闪,只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标题了。
小说中提到的绝大多数地址,都是真实的。每一条路甚至每一家餐馆的名字也都真实可寻,因此导致了好几个看完小说的读者朋友,根据我提供的地址,专程去找青枝开在西湖边的那家“梅茶馆”,他们根据我提供的文字依据,绕来绕去,却怎么也找不到。
这就是写小说的好玩之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2016年2月16日写于吻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