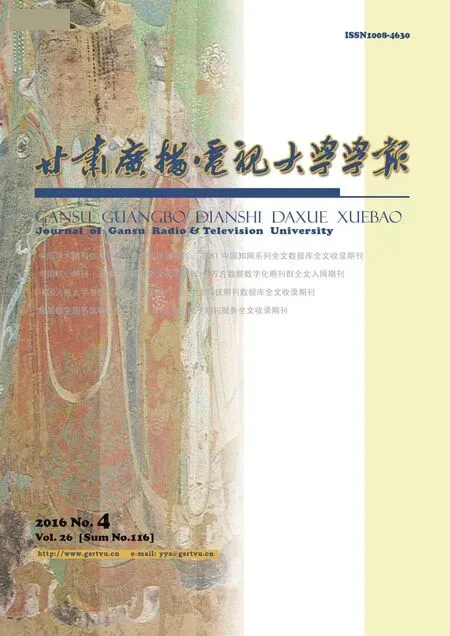《山海经》神祗珥蛇现象的文化解析
李晴晴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山海经》神祗珥蛇现象的文化解析
李晴晴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佩戴蛇耳饰是《山海经》中比较普遍的现象,人面鸟身之海神、王权享有者夏后启、炎帝之裔夸父通过珥蛇行为获得了能够急行或飞举的推动力等特殊能力。珥蛇文化与信仰基础、思维基础、功能基础以及自身属性息息相关,对先民生死观念的转变、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以及佩戴耳饰的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山海经》;耳饰;珥蛇文化
一、《山海经》珥蛇神祗分类
以蛇类形象作为耳部装饰物在《山海经》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四海之神以珥两蛇、践两蛇的形态呈现于世人面前,其双耳和双足所佩戴之蛇正好构成上下、左右以及色彩的完美对称,呈现出和谐圆融之美。总计来看,《山海经》中珥蛇之神共有9位。珥两青蛇者共5位,其中包括夏后启和奢比尸,以及西、南、北3位海神。珥两黄蛇者共2位,分别是夸父和东海海神。

第二,在《大荒西经》中可以看到,居于黄帝帝都昆仑山的凤凰虽是古代的神鸟,但胸前也佩戴着蛇,由此推测蛇类能够增加神鸟的神性,而珥蛇之举为其飞举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在启开创夏王朝的时代,天地可以互相沟通,人神能够自由往来,夏启借助珥蛇的力量腾飞。夏后启珥蛇也暗示了他是一位王权的享有者。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男性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时龙图腾兴盛壮大,隐含了龙代表的是男性本身,也代表了男性所拥有的至高权力。夏后启是夏王朝的君主,本身拥有至高的权力,龙蛇本为一体,龙的崛起相当于蛇的起飞。珥蛇之举强调了其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同时使得这种权力具有了合法性。“开上三嫔于天”道出夏后启曾经被天帝多次招请上天作客,这也足以说明启地位的独特性和神圣性,这与珥蛇的强调性作用不无关系。
第三,夸父是炎帝之裔,也是身材高大壮硕的巨人。夸父行走速度很快,一方面是其本身力大无穷兼有神力,另一方面是珥蛇所带来的推动力。夸父珥蛇还体现了商部族事神的手段。商代盛行太阳崇拜,如“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1]129。太阳代表光明和真理,为了能使太阳常留人间,人们便举行巫术般的拜日仪式,如中美洲的印第安阿兹特克人把太阳比喻为羽蛇神。“我是有羽毛的蛇。我爬行,我飞翔;我从空中来,我在地下去。”[1]50羽蛇神即为普通蛇类的变形,而蛇身人面的伏羲也曾被认为是日神之形象,由此看来,蛇与太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商部族对于太阳的崇拜即相当于对蛇的崇敬,夸父珥蛇也即祭祀神明的方式。
二、《山海经》神祗珥蛇原因分析
《山海经》神祗珥蛇具有诸多原因,笔者试从信仰基础、思维基础、功能基础,以及自身属性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自然不仅是宗教最初的原始对象,而且还是宗教的不变基础、宗教的潜伏而永久的背景。”[2]表现最为显著的是动物崇拜。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动物,因而有奉之为神加以崇拜的可能性,“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天使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由此产生了动物崇拜……圣神的东西最初产生于动物界。”[3]在我国古代,蛇是危害人类生命的隐形杀手。为了能够找出与蛇(神)相抗衡的力量,必须塑造出能够操纵蛇类的神明,“只有凭藉动物,人才能超升到动物之上……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4]拥有海洋管辖权的四海之神把蛇形象作为耳部装饰品,夏王朝君主夏后启也以珥蛇为升天的驱动力,更强大的力量操纵着相对处于弱势的力量,形成“强强联合”之势。蛇类作为动物崇拜的对象,有了强于它们的神明来压制其狂暴的力量,人们既能够祈求它们不要伤害人类,还能使这种力量化为神明所用,为人类谋取更大的福祉。
第二,珥蛇神话具有一定的思维基础,原始先民通过投射幻化等方式观察自身所处的客观世界,真实的客观世界在人们眼中具有了感情色彩,充满了人性化意味。
《山海经》珥蛇神话渗透着现实和理想的因子,是理想与现实重叠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人们借助自然的力量从自然中获取所需之物,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面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人们自身的软弱暴露无遗。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类不得不祈求自然对自己施舍恩惠、降临福祉。由此,人类常把自然拟人化,认为有神灵的存在。神产生于人格化的自然力,自然所具有的灵性成为神灵具有神性的必要因素。祈福于自然和神灵主要出于实用主义观念,食物的来源和后代的繁衍,以及如何避免自然灾害的侵害等关乎自身和氏族发展的重大问题,都需要神灵的指引。从本质上讲,人们产生于自然、置身于自然之中,自然和神灵受到人类的尊崇和敬畏是人类感激其为己提供必备需要的体现,有了需要便有了想要满足需要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具体表现为实用性。
第三,《山海经》诡异怪诞的神祗意象是原始先民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映像加以改造并神秘化之后的产物。先民以独特的观物方式打破了自身的想象空间与思维局限,赋予神祗独特的形象和意义。

第四,神祗珥蛇与耳的特殊性和神秘性有着莫大关联。耳处于人体头部两侧,具有通天通神的特性。
《山海经》神祗大耳的形态与珥蛇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爱弥儿·涂尔干指出:“人自身具有某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虽然分布在整个有机体中,但有些特殊的部位则格外明显,有的器官和组织特别突出,尤其是血和头发。”[7]从涂尔干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体特殊部位具有格外明显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在血和头发中体现最为明显。头发作为人体向外突出的部分,与同样向外突出并处于头部的耳息息相关。《海外东经》奢比尸国人皆“兽身、人面、大耳”。清人厉荃所编写的《事物异名录》中曾提到“耳为天柱”之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金箍棒能够直伸到天宫,金箍棒就可视为“通天柱”,耳的“通天”功能和金箍棒的作用相类似。而在希腊神话中,耳与通神之间形成直接关系,蛇作为启发人特异能力的钥匙,也具有了“神”的意味。耳饰是耳部的延伸,令耳部特征更为明显,这不仅使耳通天通神的特性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在与神交流时增添庄严性、肃穆性,耳通神的特性也会得到直观的显现。
三、珥蛇神话发展意义
神话是情感的寄托和信仰的支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生发出的纯粹的“幻像”。作为一种感情的表达形式,人们对自己塑造出的神充满了复杂的心理,而种种神人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在“风雨飘摇”的原始社会,人类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后代的繁衍也极为艰难,基于人丁兴旺、氏族壮大的美好愿望,人们对具有蜕皮重生功能的蛇产生了尊崇的好感,这种好感逐渐具有了神话化的性质。《山海经》中以蛇为图腾的氏族共有8个。复生神话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卡西尔教诲人们,“死亡绝不意味着人的生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生命形式的一种变化,即由一种生存方式向另一种生存方式的简单转换。在生与死之间,没有任何鲜明的确定界限”[8]。人们自然顺应着生老病死,对于死亡逐渐失去畏惧,死亡只是生命的再一次轮回,是新生命的起点,生死的转化蕴涵了人类对延续生命的渴望。以此看来,死亡观念其实就是“不死”观念,再生或复生体现了人类对于生命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
第二,一提起蛇,就会联想到龙,龙与蛇的渊源极为深厚,最初龙的本体即为蛇。《山海经》神祗珥蛇有时会与乘龙的情况杂糅,如北海海神禺强的形象一是被描述为“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另一说则为“乘两龙”,蛇与龙的混杂,正反映了龙蛇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发展。开天辟地的盘古呈龙相,黄帝为黄龙体,夏禹为虬龙,伏羲女娲皆为人首蛇身,这些神话英雄人物形成了华夏儿女是“龙的传人”的人文依据,龙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龙在形成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加神奇的能力,它能够呼风唤雨、上天入地,具有超越自然力的本领。在自然面前,人们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完全不存在的创造物身上,使恐惧心理有所依托。盘古死而化身为天地万物,为人类开创美好家园;女娲补天治水繁衍后代。这些以“龙”为依托的神祗本身拥有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华夏民族不怕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品质奠定了良好基础,对后世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树立了榜样。

在《山海经》中,神祗与蛇类的结合使得神灵与神灵的力量融为一体,如人面鸟身之海神、王权享有者夏后启、炎帝之裔夸父,而神祗珥蛇深厚的文化渊源也为珥蛇行为奠定了基础。此外,珥蛇神话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在当今社会,耳饰的“饰美”功能与《山海经》神祗所佩戴耳饰的意义具有一脉相承性。
[1]高福进. 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 王太庆,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
[3]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1
[4]潜明兹.神话与原始宗教关系之演变[J].云南社会科学,1983(1):92-99.
[5]苏宝荣.说文解字今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274.
[6]马昌仪. 古本山海经图说[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77.
[8]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 范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59.
[责任编辑张亚君]
2016-03-22
李晴晴 (1989- ),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I206.3
A
1008-4630(2016)04-00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