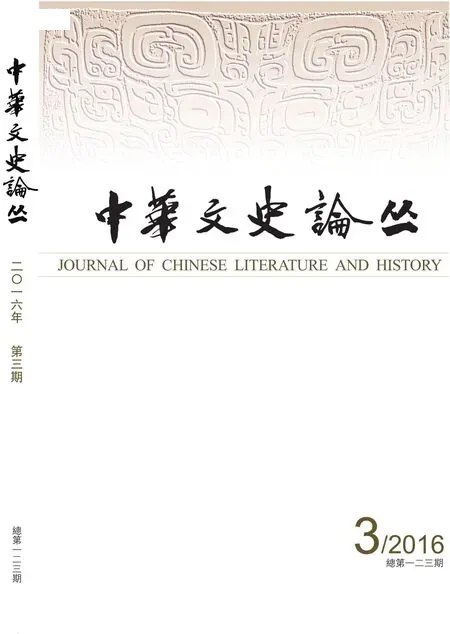不可盡信的《通鑑胡注表微》
楊 訥
不可盡信的《通鑑胡注表微》
楊訥
《通鑑胡注表微》是陳垣先生的名著,是他自稱的“學識的記里碑”,涉事廣泛,體例獨特,問世七十年來一直受人推崇。但如認真檢閲,不難發現書中錯誤不少,有的“表微”實爲虚構,故作此文辨之。
關鍵詞: 陳垣胡身之乃馬真后表微
一 來自夏承燾的評論
1947年9月30日,詞學家夏承燾先生收到陳垣送給他的《通鑑胡注表微》(下或簡稱《表微》)一部,當晚在日記中寫道:
陳樂素送來其尊人援庵先生《通鑑胡注表微》二册,燈下閲數頁,甚精深博贍。
次日,夏氏續讀《表微》,在日記中又記曰:
閲《通鑑胡注表微》,似亦有失之貪多處。如上册一二九頁以魏高貴鄉公作潛龍詩見忌於司馬昭,爲身之有感於皇子竑被廢於史彌遠之事,此等殊近附會,可以節省。*《夏承燾集》(6),《天風閣學詞日記》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23。
兩篇日記相隔一天,夏氏對《表微》的評説已在“甚精深博贍”之餘追加了“似亦有失之貪多處”,“殊近附會,可以節省”等字,可見夏氏看出的問題當不止皇子竑一處。
我不知道夏氏當初有否將他日記上的評語公之於衆。但即使有所傳出,僅憑這三言兩語,恐怕也引不起多少人的注意。1980年史學界紀念陳垣百年誕辰,受到特别推薦的還是這部《通鑑胡注表微》。1997年夏氏日記出版,至今已近二十年,其中對《表微》的批評仍未引起重視,《表微》仍是一部分史學工作者的經典,就像夏氏的批評從來不存在一樣。然而夏氏的批評不爲無據,只要認真檢閲該書,就會找出“表微”的不少錯誤、附會,甚至是虚構。我的這篇文章,就是檢閲《表微》的結果。受本人知識面的限制,我在這裏只講兩個元人的事,一個是元太宗皇后乃馬真氏,一個是《胡注》作者胡三省(身之)。希望透過這兩人的事揭示《表微》存在的一些問題。
二 關於乃馬真后
乃馬真后是元太宗窩闊台的六皇后,名脱列哥那,乃馬真是她的姓。1241年冬,太宗卒,她稱制攝政四年餘。1246年七月,扶長子貴由即汗位,是爲定宗。胡身之注《通鑑》,一次都没有提到乃馬真后,她出現於《通鑑胡注表微》,是陳垣闡釋《胡注》的結果,是陳垣改寫《胡注》的“牝雞”條造成的。這裏就從《胡注》中的“牝雞”説起。
(一) “牝雞”謂誰
“牝雞”,見於《表微·倫紀篇》“漢安帝建光元年(121)”條的《胡注》。《通鑑》此條主要講本年三月去世的東漢和帝皇后鄧綏(和熹后、太后),她自元興元年(105)和帝去世後臨朝十六年,其治績《通鑑》有褒有貶。陳垣僅引《通鑑》的一段褒詞,謂:“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内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其下引《胡注》評和熹之政,僅十七字:“和熹臨朝之政,可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矣。”接着便是陳垣的“表微”:
《鑑》文於后無貶詞,而《注》云云者,爲元太宗、定宗后言之也。宋理宗淳祐間,元太宗窩闊台殂,皇后乃馬真氏稱制,越五年而始立長子貴由,是爲定宗。定宗殂,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復稱制,又三年而拖雷子蒙哥立,是爲憲宗。憲宗之未立也,定后所屬意者,太宗之孫失烈門,憲宗立而定后賜死,失烈門遠竄,太宗后及諸王皆徙極邊,骨肉參夷,至此而極。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者,殆指此。*《通鑑胡注表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245。
很奇怪,《胡注》講“牝雞之晨”明明是指“和熹臨朝之政”,怎麽一經陳垣闡釋,就成了元太宗后和定宗后之政了?陳垣有甚麽理由嗎?從《表微》的文字看,惟一的理由就是“《鑑》文於后無貶詞”。陳垣的意思是,“牝雞”是貶詞,只能用於《通鑑》已加予貶詞的女主,而《鑑》文於和熹后“無貶詞”,故而“牝雞”不會是指和熹后,依陳垣看來,是指乃馬真后與斡兀立海迷失后,只是胡身之不便明指,所以用漢和熹后來頂替。照陳垣的意思,這纔是胡身之的本意。

初,鄧太后臨朝,(杜)根爲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1609。
太后從弟越騎校尉(鄧)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絶屬籍。*《資治通鑑》,頁1607—1608。
對和熹后來説,上引杜根、鄧康的上書是褒語還是貶詞,是一目瞭然的,故而她閲後“大怒”,必欲置根等於死地。《鑑》文據事直書,不爲后隱,將鄧氏之攬權暴露於史册,怎麽能説“《鑑》文於后無貶詞”呢?明明《鑑》文於和熹后有貶詞,是陳垣有意避開不引罷了。而且我還要提醒一句: 在《鑑》文所據的《後漢書·杜根傳》中,還講了“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後漢書》卷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839。可見從《後漢書》到《通鑑》,在指責鄧氏把持漢朝政柄上是一致的,實際上均視和熹后爲“牝雞”。身之稱和熹后爲“牝雞”,既承繼了前代史書的看法,也是他本人的判斷。陳垣無視《通鑑》對和熹后的貶詞,强行以乃馬真后替換和熹后,反道《胡注》講“牝雞”是“爲元太宗、定宗后言之也”,未免隨意曲解過甚。
(二) 晚年與歸宿
“牝雞”問題已如上述,但陳垣對乃馬真后的議論到此並未結束。與《倫紀篇》相隔一篇,在《邊事篇》“後梁均王貞明三年(917)”條中,我們又看到了陳垣對乃馬真后的議論。這次陳垣引的《鑑》文,是講契丹主耶律阿保機的述律后(879—953)勸阻阿保機攻打幽州的事。其下《胡注》評論述律后之言曰:“婦人智識若此,丈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機因其能勝室韋,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使能爾,曷爲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内虚其國,又不能爲根本之計,而終有木葉山之囚乎?”身之這段話不算很短,但仍未提及乃馬真后,在這一條裏提出乃馬真后的,還是陳垣。《表微》説:
身之不滿於述律后,爲元太宗后乃馬真氏言之也。述律后佐阿保機得國,《歐史四夷附録》稱其“多智而忍”,後爲其孫兀欲囚於木葉山。乃馬真后稱制四年,《元史·耶律楚材傳》稱其“崇信姦回”,後爲太祖孫蒙哥徙於極邊。二后晚年所遇相同。並見《倫紀篇》。*《通鑑胡注表微》,頁304。
乃馬真后比述律后晚三百多年,兩人的事迹實在没有多少可比的。至於“晚年所遇相同”,更是子虚烏有。從史籍看,蒙哥確曾徙太宗后於極邊,但被徙的太宗后並非乃馬真氏。請看《元史·憲宗紀》憲宗二年(1252)這段記載:
夏,駐蹕和林。分遷諸王於各所: 合丹於别石八里地,蔑里於葉兒的石河,海都於海押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於擴端所居之西。仍以太宗諸后妃家貲分賜親王。*《元史》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45。

三 隱士胡身之,備見天下事——兩個胡身之
本章的標題可能讓讀者感到費解,但其意不出於我,而出於陳垣,我只是會其意而用之。
胡身之入元後隱居不仕,被陳垣稱爲“有迹無名之隱士”。陳垣説:“身之宋亡後謝絶人事”,“山中注書”,“杜門不出”,“不輕與人往來”,“隱居二十餘年而後卒”,“殆可謂真隱”。*《通鑑胡注表微》,頁60,66,69。這是陳垣介紹給讀者的第一個胡身之,隱士胡身之。
然而,還是陳垣,又向讀者介紹了另一個胡身之,即一個“能備見成宗初政”的胡身之。*《通鑑胡注表微》,頁209。身之在成宗統治時期生活了八年,自元貞元年(1295)至大德六年(1302),説他經歷了成宗初期,當然没有問題,但説他“備見成宗初政”,那就大成問題了。因爲“備見”兩字凸顯了他對時政的關心和了解,這與一個“謝絶人事”的隱士是格格不入的,兩者不能兼容於一身。這中間的距離,是習慣於應用邏輯思維的學者一望便知的。可是,陳垣顯然不這樣看,他既堅信胡身之是“真隱”之士,又確信自己能够證明胡身之“能備見成宗初政”,我們可以從陳垣的《表微》中看到不少他持以爲證的事例。
事證一,見《表微·治術篇》“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條。此條引《通鑑》述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 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鑑》文下《胡注》曰:“康澄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於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知警省,非篤論也。”《注》下陳垣“表微”曰:
康澄史無傳,疏見《舊史·明宗紀》。古者君主尊嚴無上,惟天變足以儆之。若以是爲不足懼,則更無可以致人主修省之術矣。《元史·成宗紀》: 大德三年正月,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説耳,豈可一一聽從耶!”身之所云,蓋有感乎此。*《通鑑胡注表微》,頁220。
陳垣是説,《胡注》所言乃有感於朝中君臣的議論而發。然而區區一個邊遠地區的山中注書人胡身之,是怎樣得悉朝廷議事内容的?陳垣於此,理應交代他的史料根據。如無根據,只憑一句“身之所云,蓋有感乎此”,即作猜想與虚構,如何取信於人?
事證二,見《治術篇》“梁武帝天監十一年(512)”條。《鑑》文引武帝詔:“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其下《胡注》曰:“所謂寬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亂也。”《注》下陳垣“表微”曰:
元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大都路總管沙的,坐贜當罷,帝以故臣子,特減其罪,俾仍舊職。明胡粹中評之曰:“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以故臣子,特減其罪,則廢法矣,法廢而欲治天下得乎?其後江浙平章教化、的里不花、南臺中丞張閭,互相告劾,兩釋不問。元之政綱,淩遲墮廢,不待至正之末而後見也。”語見《元史續編》五。教化與的里不花、張閭,互劾贜污事,見《成宗紀》大德三年三月條,皆身之所親聞者也。*《通鑑胡注表微》,頁203—204。
沙的之事見《元史》卷一九《成宗紀二》。陳垣是説,沙的貪贜罪及教化等互劾事皆獲朝廷寬宥,爲身之所“親聞”,故身之以梁武帝之政譏成宗。與“事證一”一樣,陳垣在此也應交代自己的史料根據,因爲沙的、教化等人被寬宥的事亦非山中隱士能够聞知的。而最讓我不解的是“親聞”一語。怎樣算是“親聞”呢?是朝廷議決寬宥時身之在場嗎?顯然没有這種可能性。這個問題,令人愈想愈不明白。
事證三,見《出處篇》“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條。《鑑》文述隋故官張玄素出仕竇建德事。其下《胡注》僅十二字:“史言隋之故官,漸就仕於他姓。”此《注》言簡意明,本已無微可表,用夏承燾的話講是“可以節省”的,想不到陳垣還能表出這樣一段文字:
張玄素先辭後起,以江都之敗否爲衡,所謂投機耳。崖山既覆,宋遺民亦漸有出爲告糴之謀者,如月泉吟社中之仇遠、白珽、梁相皆是也。……仇、白、戴(表元)、牟(應龍)之就微禄,則身之所親睹也。……故身之唏嘘言之。*《通鑑胡注表微》,頁279—280。
這裏我先對陳垣講的仇、白、戴、牟四人作點介紹。
1. 仇遠(1247—?),錢塘人,字仁近。元初不仕。大德二年(1298)後出爲鎮江路學正,以杭州路知事致仕,有《金淵集》傳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頁1428下。參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頁24。
2. 白珽(1248—1328),錢塘人,字廷玉,號湛淵。以薦授太平路學正。大德四年(1300)轉常州路教授,後以蘭溪州判官致仕。有《湛淵集》傳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頁1429上。參《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一),頁263。
3. 戴表元(1244—1310),奉化人,字帥初。宋咸淳進士,建康府教授。入元後長期未仕。大德六年(1302,身之去世之年)始被薦,授信州路學教授。有《剡源集》傳世。*《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頁1424中。參《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四),頁2063。
4. 牟應龍(1247—1324),吴興人,字伯成。宋咸淳進士。元初不仕,後爲溧陽州教授,晚年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元史·儒學傳二·牟應龍》,頁4337—4338。參《元人傳記資料索引》(一),頁334。今《全元文》收其文五篇。
從仇、白、戴、牟四人的簡歷看,他們的確是在成宗前期仕元的。但是,僅此一點就能斷定胡身之“親睹”了這四人的仕元並爲之“唏嘘”了?須知我們完全不知道身之與這四人有甚麽關係。身之的書中没有提到他們,他們的文章也没有提起身之。如果這樣就能斷定身之“親睹”了他們仕元,那麽再找十個類似例子也不難,但是這樣做能算是史學研究麽?
事證四,《邊事篇》“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條。本條《鑑》文謂:“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唐顏師古曾注《漢書》“得職”爲“皆得拜職也”,身之不予認可。《胡注》曰:“余謂顏説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注》下陳垣“表微”曰:
宋南渡之初,使臣聘金者,每被抑留,强使拜職。如司馬朴、朱弁、王倫、宇文虚中之徒是也。朴、弁在元遺山《中州集》南冠五人中,倫、虚中則《宋、金史》皆有傳。身之以顏説爲非者,蓋有感於此。德祐之末,參政家鉉翁亦以奉使被留二十年,强授以官不拜,元人高之,元貞元年乃放還,此身之所親見也,故益不以顏説爲然。*《通鑑胡注表微》,頁287。
陳垣這段約近二百字的“表微”,舉出了五個宋人,都是使金被拘留過的,下面是他們的經歷:
1. 司馬朴,陝州夏縣人,字文季。以外祖范純仁遺恩入仕,累遷兵部侍郎。靖康初,隨徽欽二宗被金人虜往北方。徽宗死,爲之服喪,朝夕號哭。後卒於真定。*《宋史》卷二九八《司馬朴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907—9908。
2. 朱弁(?—1144),徽州婺源人,字少章。朱熹族叔祖。建炎初,以通問副使赴金,言和戰利害,爲金拘留。紹興初,金人迫仕僞齊,誓死不屈,被留十七年始得歸。著有《曲洧舊聞》、《南歸詩文》等。*《宋史》卷三七三《朱弁傳》,頁11551—11553。
3. 王倫(1084—1144),大名莘縣人。建炎元年(1127),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使金,被拘留。紹興二年(1132),放歸。七年,又充迎奉梓宫使赴金。九年,充迎梓宫、奉還兩宫、交割地界使,被金拘於中山府,終以不屈被殺。*《宋史》卷三七一《王倫傳》,頁11522—11526。
4. 宇文虚中(1079—1146),成都華陽人。大觀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曾上疏諫阻引金攻遼。金兵南下,爲軍前宣諭使,數使金營議和。建炎二年(1128),使金被留。歷官金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號國師,曾多次諫阻金兵南下。後被誣謀反,全家被焚死。*《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虚中傳》,頁11526—11529。

以上所述五人,前四人司馬朴、朱弁、王倫、宇文虚中均南宋初人(司馬朴生卒年無考,但其主要事迹在徽、欽二朝,可視爲當時之人)。朱、王、宇文三人均卒於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或十六年,沒有史料能證實身之一定知道四人之事。至於家鉉翁,生卒年亦失載,但成宗時尚在世,可算與身之同時代人。只是上文已言及他對元朝的態度前後是有變化的,云其“得職”已稍勉强,説身之“親見”其事,更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
上面我們讀了陳垣爲證實身之“備見成宗初政”提供的四條事證,其證全靠陳垣不斷宣告身之“有感於”、“親聞”、“親睹”、“親見”來支撑。至於陳垣是從何得知身之“親睹”、“親聞”的,陳垣没有舉出一條史料,也就是説,史籍根本没有記載。所以説,這些“親睹”、“親聞”,不過是陳垣的虚構,是不可信的。
真相難知,虚構易爲,陳垣從而出現了夏承燾所説的“貪多”現象,以致連通常的資料考訂工作也省而不做,把成宗身後之事當作身之“備見”的“初政”來看了。此事見《治術篇》“唐太宗貞觀六年(632)”條。《鑑》文記太宗與魏徵論爲官擇人。《胡注》僅十六字:“觀此,則天下已定之後,可不爲官擇人乎!”其下的“表微”卻説出這樣一大段話:
“天下已定”,爲元初吏治言之也。今《元史》本紀,悉本於官修實録,事多隱飾。然貪賄之事,猶史不絶書,如《成宗紀》大德七年條,言“所罷贜污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時身之卒後一年也,則成宗初年之吏治可知矣。《元史》一七六《王壽傳》,載:“壽大德中爲侍御史,論事剴切,嘗言:‘世祖初置中書省,安童等爲丞相,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左右之,當時稱治。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八都馬辛是一人,非兩人,陳垣誤。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摇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如此。臣今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懲其既往,知所進退’”云。所謂近者,即指成宗初政。然其實世祖時吏治已壞,廉希憲、許衡之徒,混一後不久即逝。所相與圖治者,如盧世榮、桑哥等,皆蠹國病民之尤,而用之於天下既定之後,故身之爲之喟然。*《通鑑胡注表微》,頁210—211。
《胡注》十六字本來是泛泛之言,卻引來陳垣近二百字的議論。陳垣釋王壽説的“近者”爲“成宗初政”,其用意無非是説胡身之有感於王壽所言。可是陳垣錯了,身之聽不到王壽的話,這不僅因爲身之遠離朝廷,更因爲王壽説這些話時身之已離人世數年。這裏的鐵證是王壽講的“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摇神器”。這是發生在大德十一年(1307)春季成宗去世以後,以成宗皇后卜魯罕、安西王阿難答、左丞相阿忽台爲一方,以懷寧王海山(武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仁宗)、右丞相哈剌哈孫爲另一方的帝位之爭,以前一方的失敗告終。阿難答、阿忽台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八都馬辛等被殺。此事研究元史的人大多熟悉,本文没有必要多費筆墨。既然王壽講了這次帝位之爭,他上奏的時間只能是在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以後。因此,當我看到陳垣釋王壽説的“近者”爲“成宗初政”時,一度懷疑此條“表微”恐非出於熟諳《元史》的陳垣之手。當然,《元史》編纂者對這個錯誤的造成也負有一部分責任,是《元史·王壽傳》先把王壽的話錯置於大德九年之前,然後纔有陳垣未能甄别之錯。
現在可以斷言,陳垣爲把胡身之塑造成“能備見成宗初政”之士的努力完全失敗了。認真想想,這是必然的,否則胡身之還成其爲“真隱”嗎?
結 語
以上是我對《通鑑胡注表微》部分“表微”文字的批評,發表出來,供讀者評議。
《通鑑胡注表微》的重心應該在《胡注》。“表微”成績如何,首先看它對《胡注》之“微”的闡釋是否精確到位。即使“表微”作者欲借“表微”之酒杯澆自身之塊壘,也須與《胡注》原意相應不悖並證以真人實事,不得曲解,不可虚構。可是,在陳垣的“表微”中,“殊近附會”者有之,張冠李戴者有之,時間顛倒者有之,自相矛盾者有之,隨意虚構者亦有之。在此情形下,縱有“精深博贍”之篇章與之並存,還可奉爲“經典”嗎?
2016年5月於温哥華
(本文作者係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