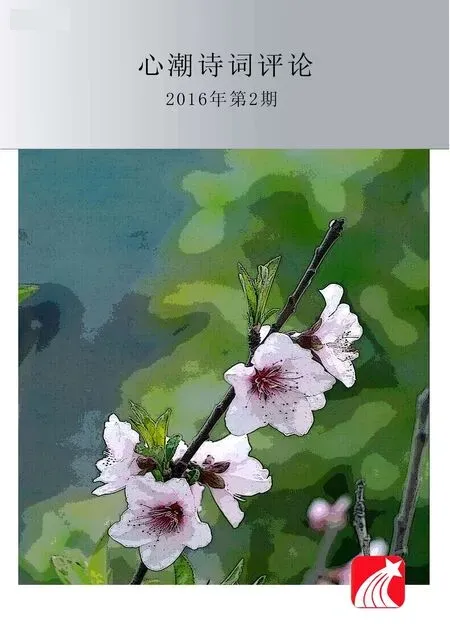读《抗战十章》并略谈刘亚洲诗艺术特色
范诗银
诗论纵横
读《抗战十章》并略谈刘亚洲诗艺术特色
范诗银
刘亚洲将军的五言绝句,读来如万马奔腾啸呼卷席,如秋树临风霜寒黏叶,如春红初绽晴岚摇风,如锥沙锋画力透纸背,如芰荷豆雨奇响天成。浸润于斯,其思也沉着,其情也激昂,其乐也无穷。前段时间,《国防大学学报》和《中华军旅诗词》第六卷,都登载了刘亚洲将军的《抗战十章》五言绝句。读这组诗,胸中就如翻滚着岩浆,裂变着,奔涌着,酝酿着那一刻轰然的喷发。但是,灼热的火焰并未直冲九霄,依旧在读者的胸中激荡回旋,渐变为疾速的脉动,悲痛的思绪,郁勃的情怀,慢慢地渗过似乎在滴血的伤口,沉淀为一声又一声沉重而警醒的呼唤。
举重若轻的历史感。1931年9月18日、1937年7月7日、1937年12月13日、1945年9月3日,一组承载着中华民族悲惨、屈辱、抗争、复生的数字,一幅用呐喊、血肉、生命、魂魄凝成的画卷,一把插在中国人民心上、远远没有拔掉的、整整70年的东洋刀。这个在昆仑山下繁衍生息的民族,曾经强大到独步世界的中华帝国,三番五次遭受北方铁骑的滋扰。虽然历尽劫难,却在抗争中,搏得了汉武唐宗的绝代功绩。然而,不幸发生了,由北而南并由水上樯橹带给这个民族几近灭族灭种的灾难,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着、重复着。
南海接东瀛,昆仑衔北溟。
江河承一脉,几度叹零丁。
(《抗战十章·序》)
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的己卯二月,文天祥这个大诗人,被同是诗人的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押于船上,在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极其残忍地令其亲眼目睹了南宋政权的最后覆灭。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六月,南明唐王逃亡入海,十二月清军破广州,残喘一隅12年后,南明彻底灭亡。零丁洋又一次见证了灭国于北来铁蹄与南来征帆的合围。中华民族有可能灭绝的又一次横祸,则是发生在1938年10月下旬。侵华日军海陆配合,攻陷广州,不久,又克武汉,打通粤汉铁路。零丁洋再一次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涕泪横流。酸眼羞风,明帆宋舵,“几度叹零丁”,极富感情的诗句,概括了近千年来中华民族被外族侵略蹂躏的凄惨与悲痛。把压得人们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历史,轻轻举起又轻轻放下,形象而又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读这十首绝句,就是在读我们中华民族的抗争史。对每组数字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作者都用诗化的语言,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物象,放在中华民族史的大画卷中,予以形象化的演绎。就如在读一幅幅黑白画面,并透过画面,仿佛听到跳动的心声和流动的血液。这种举重若轻的历史感,在将军咏史诗中表现的更为直接。如《读史八章·揖别》:“青枝方揖别,枯木已生烟。飞石穿狐耳,陶鱼煮旧年。”诗人选取我们先人直立、钻木取火、以石器猎杀小动物、捕鱼等典型画面,通过简洁的二十个字,把一部人类由猿到人的进化史,形象鲜活、情感轻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善于通过浓缩的历史,增加诗的厚度,同时也显示了诗人饱满的学养和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我们深知,适应诗这种特殊体裁的需要,举重若轻,以灵动深情的笔墨写活历史,是一个难题。读这组绝句,应能从中得到启发。
深入骨髓的家国感。读《抗战十章》,能真切地感受到宋人文彦博“家国哀千古,男儿慨四方”那样的诗境。诗中所写离我们是那样的近,使我们的感觉别有一番深刻和沉痛,几欲深入到骨髓中,沉淀在灵魂里。《序》中以昆仑衔海关照南海东瀛,重在写家国之脉;《“九一八”》中通过揖盗之悲、抗敌之艰,写家国之难;《“七七”》中先写举国抗战,接写肝胆相付,寸心相报,以牺牲诠释家国情怀的终极境界;《“九三”》中用对比手法,写胜利的代价,写胜利后的隐忧,诗人心中的家国,总是笼罩在沉郁的氛围里,给人以重之又重的感知;《“一二一三”》中以悲情为线,吊魂招魂,通过悲悯之情直抒家国情怀的最基本特征;《跋》中把庆云篇与开春桨相连接,赋予家国情怀以历史纵深,并为这组悲郁之诗,涂了一笔明丽的色彩,可看作这组诗中家国感的总结性表述。
一番生死劫,万古庆云篇。
启梦开春桨,东风送旧年。
(《抗战十章·跋》)
初服黍离,江山百姓。对国家的忠贞不渝,对人民的怜惜悲悯,是诗人家国情怀的基调。从屈原始,杜甫、辛弃疾、文天祥、林则徐,汗青留下一串长长的爱国诗人的名字。他们通过自己的诗句,把这种情怀演绎成了诗人特出之高标。这十首绝句,字里行间渗透着这种情怀。度过一番生死劫后,天下太平的尧舜盛世之景展现在眼前。驶向复兴之梦的航船,划过屈辱的历史,驶向充满希望的未来。《抗战十章·跋》中描绘的这一景象,以暖色笔调,将诗人对家国的一往情深,沉重的记忆,痛惋的过去,充满希望的未来,一并展现给了读者。无哀怨之词藻,却有沉着的力量。正如诗人《招魂九歌·其九》:“星穹殇雨滴,山海祭云沉。魂兮归来兮,哀哉共梦心”一样,哀而不伤,给读者以力量,给未来以希望。美化过的哀苦悲壮,易于让读者直视而有所感悟;诗化后的哀苦悲壮,则比直接的论说更富有穿透力。这一诗中的极高境界,在本组诗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
开合有度的时空感。刘亚洲将军是著名的战略思想家。读他的理论著作,给人以上天入地、熔古烁今的思想纵深和开阔感。这种大开大阖的大场景、大气魄,表现在诗里,无疑有着很强的感情穿透力和震撼力。但是,诗毕竟是诗。诗人在诗的创作中,把政论思维上的大开大阖,恰如其分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将思维和感情安置在适当的“空域”里,保持了诗的思想深度,诗的充沛感情,从而保持了诗的蕴藉,赋予诗作以鲜明的画面感和足够的含蓄美。
其一
喋血千千万,拼争年复年。
白旗归贼寇,半壁剩焦烟。
其二
勒我青铜鼎,还伊黄菊刀。
应怜衣带水,休戚共滔滔。
(《抗战十章之“九三”》)
这两首诗,其一的前两句展开历史的纵深,后两句展开横幅画面。千千万万的生命,年年岁岁的拼争,近说从1931年“九一八”至抗日战争胜利的十五年,远说从甲午海战到抗战胜利的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拼争与牺牲,就浓缩在这两句诗里。在后两句的横幅画面里,扛着白旗滚回去的日本贼寇,千疮百孔的半壁中国江山,对比鲜明,富有冲击力。其二则不同,前两句画面是横向的。后两句则是在一幅画面里展开思维的纵深。鼎是中华民族传统中的国之重器,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大事记,当然应铭刻于鼎。菊是日本皇室的徽记,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标志。一个“还”字,既道出了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遣返大批日军战俘的史实,也暗含了中国人的宽宏大度和仁本精神。后两句的纵深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怜取“衣带水”的邻里历史,二个是对“休戚”与共的希冀。所谓前不忘古人,后不负来者,真个是道不尽的诗人情怀。诗人的时空感自非常人之时空感,关键在“诗心”。诗人之心就像一面镜子,历史之象,未来之象,世间万象,或直射,或反射,或曲射,无不显现出本色的影子。诗人之心又像浩淼的大海,前波未平,后波又起,一浪逐一浪,一直追逐到遥远的天际。这样的时空感,又赋予鲜活的画面,可以说是这组诗的一个突出特色。
雄浑阔雅的清俊感。“将军本色是诗人”,柳亚子称许陈毅元帅的这句诗,也是解读刘亚洲将军诗之特色的一把钥匙。大凡有成就的诗人,其诗必有自己的特色。其诗特色,又必是其人本色的反映。比如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豪迈沉郁”,苏轼的“清旷雄奇”,辛弃疾的“雄健悲凉”等等。如若也找四个字来概括刘亚洲将军诗的特色,似乎“雄阔清雅”可道着大概。
其一
松花辞碧树,衢里间扶桑。
揖盗割华夏,泥胎作道场。
其二
白山连黑水,褴褛冻刀挥。
果腹轩辕子,游魂雪上飞。
(《抗战十章之“九一八”》)
刘亚洲将军的诗,就整体而论,气象雄浑廓大是其突出特色。但是,这种雄浑廓大的整体气象,却是以清新雅致的个体形象来组成并支撑的。如《登秦岭》:“相顾昆仑小,弹襟太白峰。苍茫界南北,万古一轮红。”确实有思接千古,一览天下的雄阔。莽莽昆仑,以其小反衬出太白之高;红日一轮,恰见证了诗人登高一望;而太白峰上一“弹襟”,更透出几分清新与儒雅。深刻的思维,精确的描写,明晰的画面,使雄浑阔大的场景如在眼前,触手可及。在《抗战十章之“九一八”》两首诗中,其一对“九一八”发生之前东北形势的描写,前两句以清丽之笔,选取清新形象,东北的松树,代指日本的扶桑,一个“辞”字,一个“间”字,描画出了退与进的势态,写出了日本强盗的渗透。后两句又不乏讽刺地以“揖盗”、“泥胎”,刻画“不抵抗”、“做傀儡”的当时那个社会的现实,揭示了东北被占领的深层次原因。其二笔法也大体如此。这种思维形式与笔法结构,运用到现实题材描写上也颇见功力。比如,诗人在参加会议期间,创作了两首《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席》,其一:“风清华幕卷,晓度几声钟。秋宇晴光好,横天一道虹。”其二:“荡海采骊珠,剪云开画图。回眸听石语,天问涉江初。”这两首诗,每一句都借助一个清新的事物形象,给读者描绘出一个清新的画面,然后构成廓大的场景,以其内在的张力和意蕴,达到雄厚浑阔、清新雅致的艺术境界。
一往情深的真诚感。诗三百,思无邪。无邪,就是诚。诗人的真诚,一是对自己,心有所感,情有所动,发而为诗,皆是真情实感,对得住自己那颗诗人之心。二是对读者,则以真的景致,真的情感,真的思虑,奉献给读者,全无哗众取宠之意,也无掐尖取巧之谋,对得住读者的那份期待。
刘亚洲将军的诗,居高临远之真情思尽在平常文字中,指画江山之真谋虑皆于斑斓万象画面里,使诗人之真诚又多了许多的亲切感。
其一
可惜长江月,曾悲血水流。
冤魂沉碧海,还梦故乡否。
其二
钟山一炷香,白下祭歌长。
多少元元泪,锥心哀国殇。
(《抗战十章之一二·一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的那一天。这个日子,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仍在滴血而不敢轻易触碰的日子。其一中,以月还复来,水流不归的永恒,写出冤沉海底的千载不复之痛,还有有乡难梦之悲。其二中,以黎元之泪,锥心之殇,举国之祭,写出对亲人的诚挚追思与深切怀念,给读者情浓得化不开的感觉。两首诗,以悲伤基调承载沉重历史,以感伤画面表现悲壮心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诗句就像闸门,使浓烈的感情集中于诗句框定的范围里,奔涌翻卷,回环激荡。特别是其二中“钟山”、“白下”两个地名的使用,无意中,使祭奠有了摹状质感,也有了传统的色彩。这正合了传统诗词韵味调和、形象圆润的审美要求。在这些方面,刘亚洲将军诗中还可举出不少。如《望南海》:“天山遗雪莲,南海碧螺盘。曾母可安好,茫茫一望间。”“天山”、“雪莲”、“碧螺”、“曾母”等词语的运用,既写出碧螺是天山余脉,雪莲献于曾母的书面感觉,更巧用“曾母”之音之象带给读者的感觉和想象,赋予了曾母暗沙以具体的形象,也就有着落地承载了诗人的情感,而这情感通过诗句,形象而又具体地传导给了读者。
(作者系国防大学中华军旅诗词研究创作院副院长、《中华军旅诗词》执行总编)
责任编辑: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