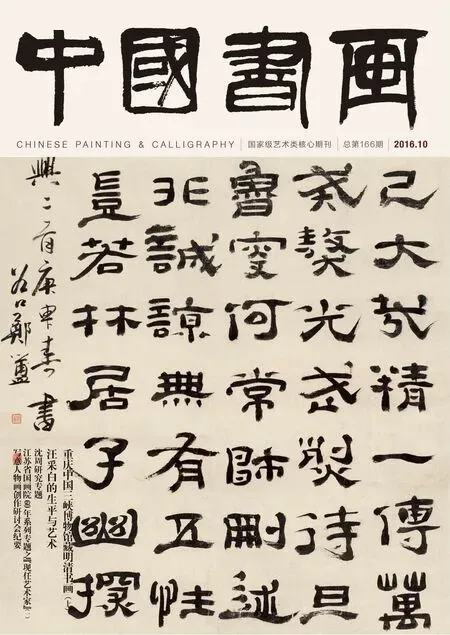沈周宜兴之游与纪游画作
◇吴刚毅
沈周宜兴之游与纪游画作
◇吴刚毅
在中国绘画史上,纪游图滥觞于宗炳,宗炳的“卧游”思想可说是纪游图的最终目标,宗炳当时的“卧游”仅以其自身为目的,然而这种卧游思想却启发了后世各种形式的纪游图,尤其到明代吴门画派始发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画目,不只针对作者本身可以观图卧游,甚至包括受赠者及观画者都能借纪游图而感到身历其境。沈周在纪游图题材上也多有建树,本文介绍沈周宜兴之游的相关画作。
一、沈周一生至少游历宜兴四次
沈周一生很少离开家乡,但他倒是多次游览宜兴山水,沈周首次及第二次宜兴之游的时间不详,据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五〈跋沈石田游张公洞诗后〉云:
石田尝两至宜兴,与克温翰林谋游张公洞,辄为雨阻,叹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岁乃始与大本隐君游,而愿始遂,因作图而系诗于后,更为序引……他日传至都下,予获读之,盖虽未及游,而兹洞已在吾目中矣。

[明]沈周 游張公洞图并诗引卷(局部)
由吴宽跋语可知,沈周前两次宜兴之游是与克温翰林吴俨〔1〕同游,并且当时即规划赴张公洞一游,然而因雨而未能成行。再根据吴宽跋中所言:“去岁乃始与大本隐君游,而愿始遂。……”因此第三次宜兴之游是与吴纶(大本,1440—1522)〔2〕同游,并且首次得以一偿宿愿而游览张公洞。
在《石田诗选》卷二及《石田先生诗钞八卷、文钞一卷、附事略一卷》卷四均收录有沈周〈游张公洞并引〉云:
弘治己未之三月余来宜兴,客吴君大本所二十一日,大本倡曰:“张洞,果老修真处,古福地之列,吾邦之仙域也,必启君一游。”余笑曰:“业已订之矣。”于是理舟载酒,从洑溪而南,历罨画溪,迤逦四十余里,始舍舟陆行,望西南诸山,高下层叠丛然,莫知所谓洞处,诘之樵人,指盂山曰:“此中是已。”余于宜兴二过,洞尚相昧,今于一识,迨老始获之。……大本请记,而系以诗,诗曰:……
因此,沈周“三游宜兴”的时间为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三月,沈周是年73岁。沈周此次张公洞之游不仅有上述诗引之作,再根据前引吴宽《跋沈石田游张公洞诗后》“因作图而系诗于后,更为序引”,可知沈周亦绘有游张公洞图。吴宽作跋的时间是沈周游张公洞的次年,也就是弘治十三年(1500),当时吴宽仍在北京,据吴宽跋言“他日传至都下,予获读之”一句推测,吴宽应该只有听闻沈周绘有《游张公洞图》而并未亲眼目睹,吴宽所读到的恐怕只有沈周的诗引文字而已(我认为吴宽所读到的沈周诗引并非是附于《游张公洞图》后的诗引书迹,而是指辗转传钞的沈周诗引文字内容)。因此,吴宽的《跋沈石田游张公洞诗后》只是单纯的一篇“诗跋”,而非书于沈周作品之后的“题跋”。
沈周游张公洞图及诗引有流传下来,翁万戈先生旧藏有一卷沈周《游张公洞图并诗引》卷,此卷有图有诗引。另外,上海博物馆亦藏有《行书张公洞诗引》卷,只有诗引而无图。此外,沈周赴张公洞途中经过罨画溪,现存一卷沈周《罨画溪诗画》卷传世。上述作品有真有赝,本文将一并研究上述作品之真伪及内涵。
沈周三游宜兴的时间已知在弘治十二年(1499)三月,并且是接受吴纶的招待而住了二十一天。现存一件沈周《吴中奇境图》卷却说明了沈周于弘治十三年(1500)九月二十六日又再度作了宜兴之游,此次宜兴之游是沈周四游宜兴,该次宜兴之游亦接受吴纶的接待,而《吴中奇境图》卷就是沈周绘赠吴纶之作品。
沈周五游宜兴的时间“疑似”在正德四年(1509)春,沈周是年83岁,沈周于该年八月二日卒。关于这段记载见于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十二《沈石田游善权洞诗稿》,其序云:
史永龄跋云:正德己巳春,阳羡吴大本邀先生游善权。归,永龄往问起居,出《小水洞图》示之。别后先生即卧病,及秋而卒。永龄奔送棺敛毕,见斯画委弃床下,因拾以归。明年又检得当时记游诗一通,后十二年辛巳装成轴。
笔者对于沈周是否在正德四年(1509)五游宜兴表示怀疑,因为目前尚无其他更有说服力的史料证明此事。不过,沈周在三游或四游宜兴的其中一次,倒是曾经计划游览善权洞,当时规划此游的人亦是吴纶,只可惜当时未能成行。考《石田先生诗钞》卷四,列于《游张公洞并引》之后有沈周《酬吴大本邀游善权不果》一诗,该诗无纪年,《石田先生诗钞》将此诗编年于弘治九年(1496)至正德元年(1506)之间。在这段时间中,沈周曾于弘治十二年(1499)与弘治十三年(1500)分别应吴纶之邀请与招待两次游览宜兴,故沈周《酬吴大本邀游善权不果》一诗必定是在这两次宜兴之游时所作。
二、纪游画作
1.《吴中奇境图》
《石田先生诗钞》卷四有三首诗连缀排列,依次为《自甲浦道太湖四十里,见吴、香诸山,喜而有作》《汎罨画溪》《游张公洞并引》。沈周《自甲浦道太湖四十里,见吴、香诸山,喜而有作》的诗文即是弘治十三年(1500)九月二十六日沈周四游宜兴时所作之《吴中奇境图》卷之卷后题诗。沈周此诗与诗题详尽地描写出其乘船赴宜兴的路径与太湖一带列嶂群山秀烂远近之情状,想必这些列嶂绵延、群山环列的景致在沈周心目中必定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明]沈周 为珍庵作山水图轴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博物馆藏
沈周《吴中奇境图》卷,纸本,水墨,纵35.5厘米、横317.8厘米,现藏处不详。画卷本幅无款识,仅于卷首下方钤有朱文“启南”及朱文“有竹庄主”人两印。卷后另纸沈周题识曰:
庚申九月廿六日,自苕溪往宜兴道太湖,见西岸异香诸山,紫翠重沓,随舟北行,历四十余里,实吴中奇境。喜而赋此:清苔达宜兴,道湖已成算,仆夫却告难,风浪卒莫玩,劝我陟山麓,虽劳免忧患,彼此有得失,我臆殊未断,譬山行望湖,昏昏只浩瀚,何如湖中行,坐挹山秀烂,仆尚请筮决,得需利在彖,毅然促飞栌,猛进不复懦,探穴有虎子,履险获奇观,出浦即会胜,列嶂在一岸,遐思榄吴香(传云:吴王于此山栽香),妄意觅仙幔,群耸势若监,巨浸东罔畔,天恐湖太淫,设此似按摊,云涛日撞摏,石趾力排扞,输赢各无能,两垒对楚汉,我经锋镝间,便以老命判,山疑作慰籍,逐逐笑供玩,始有舟楫处,尽被山破散,山亦有情状,要我绮语赞,气聚势则附,形散脉复贯,远近相衍迤,中自存博换,虽静寓动机,万态纷变乱,虹龙徐蜿蜒,狮倪悍奔窜,夷突各不一,小大略相半,正展芙蓉屏,横亘苍玉案,晓縠绉日光,暮熨锦绣段,金庭与玉柱,远弄波影璨,历历四十程,续续青不断,平生但传闻,洵美岂谩谰,芜篇聊梗概,归忆庶可按。长洲沈周。
下钤朱文“启南”、白文“布衣之士”、白文“石田”。
沈周题识后另接纸有吴纶、赵士桢、冯超然、吴郁生、吴湖帆题跋。引首为赵士桢题“吴中奇境”篆书四大字。此画历经赵士桢、南子兴、吴大澂、吴湖帆、丁惠康收藏,卷上有上述诸人鉴藏印记多方。
由沈周题识:“庚申九月廿六日,自苕溪往宜兴道太湖……”可知,此图是描绘弘治庚申(十三年,1500)九月廿六日沈周宜兴之游于途中所见之情景。笔者于前文考证出沈周此次是四游宜兴,并且也是受吴纶邀请。又此次宜兴之游根据沈周于该卷卷后题识的纪游文字可知是乘船沿太湖沿岸吴山及香山一带以水路经四十余里而达宜兴。沈周去年(弘治十二年,1499)三游宜兴亦是乘船以水路前往宜兴,想必路径应该相同。至于前二次接受吴俨邀请的宜兴之游是否走水路,由于欠缺资料而难以稽考。就目前所掌握之资料而言,沈周在过去几次宜兴之游时并未针对太湖沿岸的景色创作出纪游图之作品。目前所知沈周真迹中,能够协助吾人了解《吴中奇境图》卷的纪游内涵者,大概只有沈周于弘治十年(丁巳,1497)所作的《洞庭两山赋图》卷。因此,笔者必须先讨论沈周《洞庭两山赋图》之后,再回头讨论沈周四游宜兴所作的《吴中奇境图》卷。
沈周《洞庭两山赋图》卷,纸本,水墨,纵35.5厘米、横317.8厘米,原为黄君璧收藏。沈周于卷末题识云:
弘治丁巳三月,友人持济之太史洞庭两山赋见示,语意深奥,词旨变幻,政如七十二峰,风雨晴晦,出没万状,不可端倪。余披襟读之,不觉神思快爽,遂援笔为图。但用笔滞涩,草草不成景象,安得与济之之文并传不朽。图成书以志愧,沈周。
下钤朱文“启南”、白文“石田”。
由题识可知,沈周创作此图的动机并非直接对洞庭两山写生,而是由于读了王鏊《洞庭两山赋》的文章而灵感泉涌之作,又沈周此图是应友人之请,并且是专为匹配王鏊赋文所作之合卷绘画。王鏊的《洞庭两山赋》书法长卷亦裱褙在沈周图画之后,王鏊在赋中对洞庭东山及西山山群极尽写状之能事,是一篇既深奥又优美的赋记。
将沈周此画对照王鏊长赋,可以感到沈周此画的描绘比王鏊赋记的描写更为平实,在王鏊赋记中对于洞庭两山奇伟诡谲的描写似乎在沈周图中都未描绘出来,这代表着沈周此图并非是针对王鏊长赋所绘制的“图引”。相反的,沈周所表现的仿佛就是一幅对洞庭两山一带总体印象的山水长卷,但我们不能称其为“纪游图”,因为沈周创作此图的动机非在纪游。
沈周《洞庭两山赋图》卷的皴法是沈周晚年由吴镇、刘玨披麻皴及董、巨麻皮皴等风格演变而来的粗笔皴法,是沈周晚年典型的粗笔皴法风格。由于皴法粗犷而生动,配合画中树木翁郁、帆船熙攘,营造出一幅热闹繁荣的景象。然而如果吾人将沈周《吴中奇境图》卷与《洞庭两山赋图》卷比较,则会发现《吴中奇境图》卷初看下似乎是未完成的作品,其皴法基本上与《洞庭两山赋图》卷相同,然而整体皴法结构繁复单调,整幅作品亦未有明显的高潮。这可能是由于沈周《洞庭两山赋图》所诠释的是洞庭两山一带的太湖景致,而《吴中奇境图》所描写的是横山(吴山)与香山沿岸的太湖景致,两者描绘的地点不同,故实际景色有所差异。然而在表现风格上,这两幅作品的差异其实远超过实际景色所可能存在的不同。其原因为何?颇耐人寻味。沈周《吴中奇境图》卷有沈周纪游诗及题识,如果我们配合沈周此图的纪游文字来赏析此图,则会发现沈周纪游长诗中绝大部分皆是描述著太湖沿岸吴、香诸山山势蜿蜒衍迤的文字,例如:“列嶂在一岸,遐思榄吴香……群耸势若监,巨浸东罔畔……历历四十程,续续青不断。”然而沈周在《吴中奇境图》卷的构图上似乎受到更多的限制,沈周将重复出现的繁复山脉画在手卷的上半部,而下半部全是湖面,湖上有梭船两艘,另有一舸由船伕两人荡桨,舸中篷内一文士倚靠船缘作观看状,此人应即沈周自况。沈周将山脉构图在上半部正符合其纪游诗中“列嶂在一岸”之语,沈周这种构图的原因及目的也被吴郁生道出,吴郁生在卷后题跋云:“此在舟中看岸上群山连属、紫翠千重之象,布局似奇,写景则真也。……”因此,《吴中奇境图》卷是沈周在船中看到吴山及香山一带沿岸山峦起伏绵延叠嶂而写状,故一侧全是山脉,另一侧则为湖面。沈周这幅皴法繁复而构图单调的《吴中奇境图》卷就是将这段文字以及沈周对这部分沿岸山势的感受形诸于笔墨,如此一来,沈周《吴中奇境图》卷便十足成为一幅“配合游记且描绘总体印象之纪游图”了。
2.《罨画溪图》
沈周在游览张公洞之前曾经途经罨画溪,考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及陈夔麟《宝迂阁书画录》卷一着录有沈周《罨画溪图》卷,卷上沈周题诗及跋曰:
长溪碧衍玉光净,树夹两岸俱倒映,群峰树杪舀螺出,一一随行似相媵,小舟贴水天上坐,了见须眉落秋镜,溪当比我情尚澄,地固不凡游亦胜,舷歌偶尔及沧浪,野鸟忽飞鱼忽泳,中流手洗白磁觥,一勺分清空百病,喜闻秋潦转澄莹,健在能寻不妙更。弘治己未三月,泛罨画溪,作此图系诗,沈周。
此题诗即前述《石田先生诗钞》卷四所收录之《汎罨画溪》。而现存一卷沈周《罨画溪诗画》卷,纸本,设色,纵31.5厘米、横361厘米,藏处不详。画上无沈周款识,只于绘画部分的卷首与卷尾下方重复钤盖朱文“启南”及白文“石田”各两方。又画后另纸以大字行书书写《汎罨画溪》七言诗与跋:“长溪碧衍玉光净,树夹两岸俱倒映,……弘治己未三月,泛罨画溪,作此图系诗,沈周。”(即前引《吴越所见书画录》着录之诗与跋),并且于款字后方钤盖“沈氏启南”朱文印及“白石翁”白文印。根据画幅尺寸及画上收藏印等资料可以断定此卷即是陆时化及陈夔麟所着录者。又据《吴越所见书画录》可知此卷引首原有董其昌书“山水间”三字,而《宝迂阁书画录》着录时该董其昌引首已轶,而现存此卷亦无董其昌引首。

[明]沈周 洞庭两山赋图卷(局部) 35.5cm×317.8cm 纸本水墨
此卷的大字行书虽然有十分明显的黄山谷风格,然而其每一个“撇”画皆朝向同一个角度,并且所有“撇”及“捺”之用笔皆未送到,试比较沈周大字行书真迹《化须疏》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即可判断品质高下。另外,绘画部分之皴法虽接近沈周后期所变化出来的粗笔皴法,然而与沈周这段时期的绘画真蹟,例如:弘治十年(1497)的《洞庭两山赋》卷(原黄君璧收藏),弘治十年的《草庵图》卷(上海博物馆),弘治十年的《泛舟访友图》卷(上海博物馆),弘治十二年(1499)的《铜官秋色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弘治十二年的《游张公洞图并诗引》卷(原翁万戈收藏),弘治十三年(1500)的《吴中奇境图》卷(私人收藏)相比较,则可看出《罨画溪诗画》卷的风格与沈周同时期作品仍有些相异,笔者认为此卷之书法与绘画均为存疑。
3.游张公洞图
沈周现存两本与张公洞纪游有关之作品,其中一本是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行书张公洞诗引》卷,纸本,纵35.7厘米、横337.5厘米,只有诗引书法而无绘画。另一件是翁万戈先生旧藏之《游张公洞图并诗引》卷,此卷有绘画亦有诗引书法,全卷皆为纸本,而图画部分为浅设色,纵44.1厘米、横282.3厘米,至于诗引书法部分尺寸失记。

[明]沈周 罨画溪图卷(局部) 31.5cm×361cm 纸本设色
比较上述两件作品的诗引书法部分,可以判断出上海博物馆本的品质较差,其书法的结体全部朝向同一方向倾斜,运笔亦刻意伸手挂足,带有很重的匠气。而翁万戈本的品质较佳,不仅每个字的结体有变化,运笔亦自然而有力。至于翁万戈本是否为沈周亲笔,可以比较沈周这段时期的几件书法真迹,例如:作于同一年的《铜官秋色图》卷之题识,书于弘治十一年(1498)的沈周题《刘玨天池图》卷(天津博物馆),沈周作于弘治十三年(1500)的《吴中奇境图》卷之卷后长题,以及约弘治十二年(1499)(或以前)的沈周等人《群英遗墨》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等。将这些书迹互鉴之后,推定上海博物馆本为伪作,而翁万戈本为真迹。
翁万戈所藏《游张公洞图并诗引》卷之卷后诗引书法“游张公洞并引”即本文前引《石田诗选》与《石田先生诗钞》收录之《游张公洞并引》,将两者互校之后,除了诗集中“大本倡曰:张洞,果老修真处,古福地之列,吾邦之仙域也,必启君一游”一句,在翁万戈藏本上书为“大本倡曰:张洞,古福地之列……”而省略“果老修真处”有差异之外,其余几处个别文字的差异皆不足以影响文意。兹将翁万戈旧藏之《游张公洞图并诗引》卷后诗引墨迹“游张公洞并引”全文附于注释,读者可参阅〔3〕。
笔者将沈周《游张公洞并引》所记载的纪游文字之内容与路径整理耙梳,略述于下:沈周从洑溪而南,乘舟船经罨画溪,迤逦四十余里。才舍舟陆行。沈周舍舟陆行之后,看到西南山势层叠而找不到张公洞的所在位置,经樵夫指点得知洞口在盂山之中,在前往盂山张公洞的路程中经过了三里多的田地,然后折向北方行走一段路便看到张公洞之天窗,再转及山椒(山陵)则看到洞口,洞口朝向西北方,且洞口上有石冲,好似门楣。(即诗引中“始舍舟陆行,望西南诸山。……路次临一穴,甚深晦,其唇有杂树蔽亏,人谓此洞之天窗也。转及山椒,则洞口在焉,呀然向西北且隘,有石冲亘于上,如门楣然”这段文字)。诗引中又说明上述游历由于天色已暗,故仅入洞浏览便下山。次日沈周与吴纶再游张公洞,这时天色尚明,沈周入洞后由洞下平台仰视天窗,沈周也在诗引中描述了天窗四壁及钟乳石惊奇满布的情景(即诗引中“台踞洞北,趾崇丈余,南面而立,则三面环见皆石壁,壁拔地渐高而偃,如鹏翼骞空焘下。其中豁豁壁之理,上下皆庚。而横理中乳溜万株,色如染靛,巨者、么者、长者、缩者、锐者、截然而平者、菡萏者、螺旋者、参差不侔,一一皆倒县。俨乎怒猊掀吻,廉牙利齿,欲噍而未合,殊令人悚悚,乳末余膏溜地,积为石椔数长躯,离立兀兀,色糅青绿可爱”这段文字)。继之,沈周又花了一段文字说明张公洞内诸小洞之通达幽深之情形,并感叹造物者的伟大,同时抒发自己因此而领悟到的人生道理。
在掌握沈周张公洞之纪游文字之后,再来检视沈周的《游张公洞图并诗引》卷的图画部分,则由画卷左方可以看到由两排树木及屋舍围成的河道,河岸停泊小船数艘,象征着“舍舟陆行”之意。河岸左侧有一位点景人物柱杖而立,此人应与沈周无关。由河岸右侧至卷首均无人物,沈周似乎有意将自己与吴纶等人的形象省略,这与沈周其他纪游图有较大的差异(例如《吴中奇境图》便将沈周自己的形象绘于图中)。由河岸向右延伸,有一段田地的表现,这是描绘沈周诗引中的“冉冉曲经田塍间三里许”。在田地后方及右方有许多山头,这是诗引中所谓的“望西南诸山,高下层叠丛然”及“盂山”。由沈周绘画对照诗引中“西南诸山”的方位,可以知道沈周将卷尾代表东方,而卷首代表西方。在田地与山头交接的地方,沈周画出一段栏杆,这段栏杆与稍早的小桥暗示了田边小路的存在与路线,而此栏杆后半部被山麓挡住,并于山头右方山凹处绘出一条小径弯转至画卷下方,这就是诗引中的“由林麓左行折而北”的写照。笔者前文论述沈周将画卷尾端定为东方,而卷首定为西方,因此这条蜿蜒向画卷下方延伸的小径便符合“折而北”的路线动势。这条小径又在布满钟乳石的“张公洞天窗”左下方出现,并且在天窗右方曲掩蜿蜒向上,在小径向上蜿蜒的途中,沈周画了洞口,并且还以小字在洞口中标注“洞口”二字,这就是诗引中“路次临一穴,甚深晦,其唇有杂树蔽亏,人谓此洞之天窗也,转及山椒,则洞口在焉”。另外,我们注意到洞口的位置面向观画者而开,并且洞口方正,这符合诗引文字中“(洞口)呀然向西北且隘,有石冲亘于上,如门楣然,入必俯首,上摩小方,有刻”的叙述。更重要的是,洞口朝向“西北的方位”与此图将洞口所营造的方向也是符合的。(这点十分重要,因为沈周在此图将卷尾朝向东方、卷首朝向西方的构图考量就是为了迁就洞口的正面表现而定的。反观若将卷首定为东方、卷尾为西方,则面朝西北的张公洞洞口便无法正面展示在画面中,而必须藏在山背后方了。)再则“天窗”上的钟乳石密布,状似张口獠牙满布,这是描绘沈周诗引文字中的“而横理中乳溜万株,色如染靛,巨者、么者、长者、缩者、锐者、截然而平者,菡萏者、螺旋者、参差不侔,一一皆倒县。俨乎怒猊掀吻,廉牙利齿,欲噍而未合,殊令人悚悚”。归纳而言,沈周在构图时将卷尾定为东方、卷首定为西方,由卷尾至卷首所有景点的位置与路线的安排与方位都与沈周诗引文字叙述符合。
在传统的手卷绘画中,由于观赏开合的方式是以左手徐徐展开、右手徐徐收合而逐段由右至左开展,故手卷绘画的构图与手卷书法的次序皆是以右方为首左方为尾,凡绘画构图与书法文字皆是由右至左布局安排,观赏者亦是由右至左逐段观赏。然而沈周《游张公洞图并诗引》卷的绘画构图却违反过去手卷的构图惯例,其布景是由左至右,因此观画者若依循传统的手卷开合习惯,则先看到此次张公洞纪游图的结尾,最后才看到沈周所谓“始舍舟陆行”之游历起始,如此则与沈周诗引纪游文字的铺陈叙述刚好相反。那么沈周为何要违反过去构图的习惯而将开始放在卷尾?其中关键原因正是因为张公洞“洞口”的安排,沈周为了明白地表现出洞口的地理位置,故必须将洞口面向观众正面绘出,注意沈周还以小楷“洞口”二字“注明”洞口的所在。如果洞口必须面向观众且在沈周纪游诗引中已经说明出洞口是朝向西北方,则以洞口的方位推定,画卷下方为北方,卷首为西方,而卷尾为东方,故沈周舍舟陆行并朝西南诸山行走的安排只好由卷尾向卷首构图。这代表着沈周在构思此纪游图的功能上是想“再现”当时游历的路线与行进方向,沈周希望借此纪游图忠实地呈现游历的历程与景点的位置,并让观画者能依据画面所暗示的路线对照纪游文字的叙述感受到他在实际寻访张公洞过程中所经历之景致,并且沈周将洞口标注出来以使观画者体会到他发现洞口的喜悦。因此,沈周《游张公洞图并诗引》卷是一件“配合游记的纪游图”,是沈周这一类型纪游图的代表作品,也是一件“企图以再现手段写实描绘游历历程的纪游图”。
(作者为台湾独立艺术史学者)
注释:
〔1〕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丁未进士,选庶吉士,除编修,历官侍讲学士,逆瑾中伤,罢归,瑾诛,召用,终南京礼部尚书,道文肃,性方严清慎,文章庄重,诗词清丽可讽。”
〔2〕王鏊《王文恪公集》卷二十六有《封奉直大夫礼部员外郎吴府君墓表》:“宜兴有逸人焉,氏吴、纶讳、大本字,风神散朗,操履修洁……创别墅二于溪山间,南曰樵隐,西曰渔乐,逍遥乎其间。自号心远居士,意以靖节自拟也。……至苏必过沈石田,流连浃旬乃去,余无所诣。子仕登甲戌进士,官户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进礼部员外郎,又以诏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
〔3〕“弘治己未之三月余来宜兴,客吴君大本所二十一日。大本倡曰:张洞,古福地之列,吾邦之仙域也,必启君一游。余笑曰:业已订之矣。于是理舟载酒,从洑溪而南,历罨画溪,迤逦四十余里。始舍舟陆行,望西南诸山,高下层叠丛然,莫知所谓洞处。诘之樵人,指盂山曰:此中是已。其山于群山最下,而小计其高,不过二十仞,心甚易之,岂灵区异壤能有乎是哉。冉冉曲经田塍间三里许乃抵,已暮。亟由林麓左行折而北二百步,路次临一穴,甚深晦,其唇有杂树蔽亏,人谓此洞之天窗也。转及山椒,则洞口在焉,呀然向西北且隘,有石冲亘于上,如门楣然。入必俯首,上摩小方,有刻,未暇读。门侧置片石,楸纹纵横,云为仙枰,疑好事者设之。自兹从石级下度,再上再下,崎岖甚疲于老足,故小憩旁石,瞰下冥冥。时岚气滃渤如水涵于中,不可儗步,隐隐惟见石台耳。瞑色渐翳,迨无所睹,乃下山,议宿道士张碧溪林馆,规以明日补其未足之游。夜二鼓,雨作,檐声浪浪,怅然谓必败迺事矣。黎明,天就霁,即蹶起,厌浥行湿莽中。喜剧,兴热却掖猛进,冉冉焉足若虚蹑,洫洫焉身若渊墬,愈下而境愈奇。乃及台,而昨俯见天窗者,今则仰观之。日光下映,四顾了然,下多乱石倾亚,有崩跌势。洞传孙氏赤乌间霹雳所开,天窗可想其迹也。台踞洞北,趾崇丈余,南面而立,则三面环见皆石壁,壁拔地渐高而偃,如鹏翼骞空焘下。其中豁豁壁之理,上下皆庚。而横理中乳溜万株,色如染靛,巨者、么者、长者、缩者、锐者、截然而平者、菡萏者、螺旋者、参差不侔,一一皆倒县。俨乎怒猊掀吻,廉牙利齿,欲噍而未合,殊令人悚悚,乳末余膏溜地,积为石椔数长躯,离立兀兀,色糅青绿可爱。西壁下作大裂,斜而衍,幽而窅,内多流石错互。初随行小童误由洞口岐而入,忽见蹒跚出于罅处。众讶曰:何小子之佻达也。东壁下一小洞,厕门内有石洼,滴水满中。又一洞正南壁下,中极黟黑,云通半里许。余闯之,寒气淰淰袭人,不可久伫。大本则挟僮奴二三辈,执炬踉跪而入,觉其挺诣之无难也,非但不能,抑不敢以老身试其不测,惟盘桓台下,恣得俯仰之观。嗟乎!设者不自知其巧,而使游者知之。知也,有不能尽其知。游也,亦有不易者焉。余于宜兴二过,洞尚相昧,今于一识,迨老始获之。可信境于人间不多设,游于人生不能几遭。因饮酒独酌,心与境融,乐与迹超,洋洋乎欲参造物者游,谓可遗世而长存,不知果翁之得!果何如哉!时大本自别洞出,仍来候余,历言其中石床石灶丹田之异,旁之列洞,不可殚记。余曰:毋多谣我。我亦有神偕子往矣。大本请记,而系以诗。诗曰:仙山不在高,灵区设中冓,包蒙自太古,霹雳始与牖,暗然不耀地,白日已通画,遂亵世游人,我及千载后,登顿入地中,足与石角斗,飞崖临紫云,既掀势还覆,仰面欲成压,山鬼自司救,元气不蒸雨,五色变乳溜,支本万不齐,纂纂簪笋瘦,又如人披覆,呈此琅玕秀,旁扉表云房,曲密通寲窦,跬步必容炬,老胆怯且逗,神仙未易求,冥探亦何遘,矫手采瑶华,和饮千日酬,聊度三千年,儗与石同寿。长洲沈周。”下钤“启南”朱文、“白石翁”白文印。

[明]沈周 吴中奇境图卷(局部) 35.5cm×317.8cm 纸本水墨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