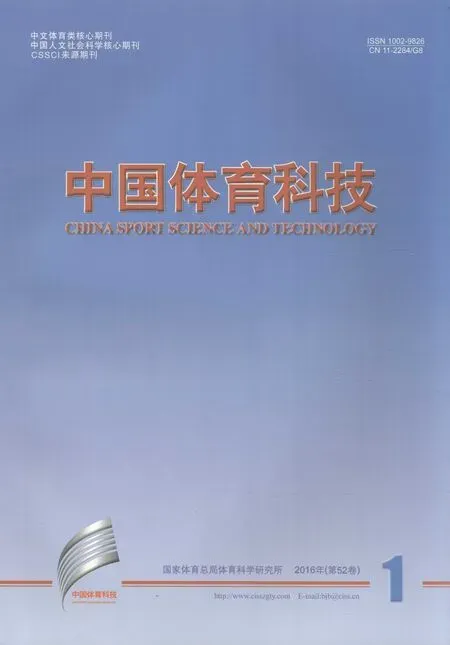民国时期学校武术考论
吕思泓
民国时期学校武术考论
吕思泓
通过梳理文献史料,对民国时期学校武术(文中也称“国术”)开展的历史背景、介入其中的社会角色及其作为、学校武术教育状况进行深入考证,从不同视角对民国学校武术做出评价和反思。研究认为:精英基于强种、卫国与保存国粹的目的对武术的提倡,是学校武术发展并成为重要传播途径的主要动力;学校武术在精英的努力下持续推进,基本实现了武术在学校课程中的主流化;除进行形式多样的武术教学之外,学校武术的推行,还依赖地区武术运动的社会基础、当地国术团体的积极作为、当地政府的配合3个重要条件;武术师资呈三元结构且此消彼长,师资培训堪忧,中、小学武术课时有限,教材编制标准不一。整体观之,民国学校武术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时代需求,但其历史功绩差强人意。学生个人兴趣需求被国家、民族观念和对抗西方体育的观念所宰制,其竞技化努力成效不明显,在西方体育教育框架下发展而遭遇诸多弊端。
武术;民国;学校;教育
前言:近代学校体育思潮
晚清时期,中国屡遭重大变革,一连串的军事失利使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加上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传以及西学的影响,中国人开始寻求变革图强。此时,在保种、强国思潮及晚清以来提倡武备教育的影响下,军国民主义体育教育逐渐形成。此时,国人普遍关心保种与强国议题,借以争取个人与国家的生存权。蒋百里认为,“学校者,国民之制造所也,国风之渊源也,而国民职业之豫(预)备校也” ,因此,要组织全体军人,就要先从学校开始,他主张“一学校即一军队也,一国家即一军队也”[18]。可见,清末民初的体育教育目的,主要着眼于尚武的层面,体育为军事服务,也形成了一般学校教育为军事教育铺路的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思潮引进,加之战时各国死伤惨重的影响,使中国的体育教育从之前的军事化、国家化,转向教育化、个人化发展。此时的军国民体育也被时人所抨击,进而影响学校兵操训练存废议题的产生。如体育学者徐一冰在一战前曾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整顿全国学校体育应废除兵操[44]。陈独秀也表示,“军国民教育的时代过去了,什么兵式的杀人思想,少输入点到青年底脑筋里罢”[8]。甚至连先前极力声援军国民教育的贾丰臻也认为,自己之前视军国民教育乃20世纪教育之唯一主义是一个错误,他也为此错误而忏悔[16]。此时,国内对体育教育提出更多见解,重新诠释体育的价值与意义并将体育视为教育的一环,认为体育是培育身心健全的个人,应重视体育课中的自然活动,顾及学生兴趣与身心发展之需求以及改良体育教学法等[41,45]。此时期,新教育思潮对中国体育确实有深刻影响,一方面,它将学校体育视为教育的一环,改变原先体育为军事服务的片面化作用,充实了体育的内容;另一方面,它让时人意识到当时国内体育事业的缺陷并予以改善,尤其是留意学生个人身心状况与兴趣等需求,近代中国体育思潮因之丕变。西学东渐也包括西方体育东渐的过程,武术既受武备思潮影响,也随社会变迁趋向个人化,同时更是作为一种与西方体育拮抗的“土体育”形式而备受推崇者重视。
1 精英对“固有武术”的提倡
自晚清以来,国人就一直有提倡固有武术的声音。如梁启超曾呼吁,国人应该崇尚中国旧有武术,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得以获胜,注重武术训练以培养士兵胆量体魄是一大原因。因此,梁氏主张,中国不应只重视西方体操,更应该好好研究中国武术,并成立一门普通学科,一旦使国人精此技术,配合新式的战争技术,则足以捍卫国土[25]。体育学者徐一冰于1914年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整顿全国学校体育的意见,他表示,本国技击是中国最古最良的体操,“能稳步伐,能固筋骨,手足之灵敏,全身之坚强”,因此主张高等学校、中学师范应添授此项目,借以“修养勇健之体格,保存国技之菁华,强种强国,亦教育之急务也”[44]。孙中山也曾呼吁提倡中国武术,他在民国8年为精武体育会的纪念特刊《精武本纪》[34]作序,序中提到:
概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曩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失大计也!
以上3人基于强种、卫国与保存国粹而提倡中国武术,梁启超和徐一冰等更是有远见卓识地提出了武术学科化和教育化发展的主张。对武术锻炼国民体魄价值深信并力倡,不仅是本土精英的群体意识,国外学者也不乏倡言者。1922年,麦克乐(C. H. McCloy)应申报创报50周年之邀,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麦克乐曾勾勒出近50年来中国武术的发展状况,也告诉世人,在面对时代变迁之下,中国武术何以再度获得国人的重视[29]。在中国人摸索与追求体育的同时,传统武术也加入了改造国民体魄的行列。一方面,虽然战争形态改变了,但武术本身仍具有若干军事价值;另一方面,习武本身也是一项身体活动,有些武术也具备养生、健身的功效(如太极拳)。更重要的是,传统武术是中国固有的本土体育项目,可以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体操[54]。
在学界、政界等中、外人士的提倡之下,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进入了教育化发展的轨道。中央国术馆成为国民政府时期声援国术成为学校课程,乃至成为全民必学技能最主要的发声单位,在民间武术家、武术社团、各级国术馆及体育专门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武术被作为重要的“土体育”项目引入各级学校,在教育领域广泛传播。
2 从边缘到主流的努力
从1915年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程起,武术在校园中很大程度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即武术大多作为选修课而非“正课”存在。之后的很长时间,武术教育提倡者都在为校园武术的主流化而努力。如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提出《请令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该案建议1年之内中央与各省区或设武术专门学校,或于各大学内增设武术系,各大学暑假学校中特开武术班,最近3年内,除前期小学外,均得自由增设武术科,3年后,武术教师将会基本够用,即由大学院修正令各级学校将武术正式订入课程[12]。但此议案仅被大会议决作为参考,未见下文。1931年6月,第六届国民会议中,张之江等人提出《请审定国术为国操推行全国学校暨陆海空军省警民团实行普及以图精神建设期达强种救国案》,以及同年7月张之江呈请国府的《呈请定国术为国操挽颓风兴国民党案》,同是这类议案[48,49]。经过不懈努力,国术逐渐被推向学校体育的中心。1932年通过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规定各校在体育设备上应设国术场,在研究体育机构方面,包含国术馆;把国术原理、派别、教学及比赛方法等内容列入体育研究事项中;学校体育课程与教材都应包含国术[30]。此外,当年教育部也随之成立体育委员会,18位委员中包括褚民谊、张之江、马良、许霱厚、陈泮岭等推行国术甚力的人士[51]。
20世纪30年代中期,教育部以行政命令规定了国术的必修课性质,各级学校体育课程对国术做出了相应的规划,而且拳种和器械套路不断增加,武术教学趋于系统化。小学教育方面,1936年教育部公布《小学体育教授细目》,针对小学高年级安排了太极操。中学方面,1931年《初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与《高级中学体育课程标准》都包含有国术与角力,以上两项课程标准都在1936年修正,其中规定初中的国术应注重刀、枪、剑、棍等简单器械的应用,高中部分除此之外,还要加入石担、石锁以及攻守法等内容[24]。师范学校方面,1934年公布《师范学校体育课程标准》,其中包含国术[39]。大专院校方面,1936年教育部公布《暂行大学体育课程标准》,其中规定国术课程内容包含少林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刀术、棍术、枪术等[39]。国术提倡者在努力争取实现了国术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必修”身份后,不断细化,增添技术内容,其推行武术教育心情之迫切也可见一斑。
3 学校国术的推行
如前所述,学校国术倡导者基于国术的种种优势,竭力在学校扩大武术的传播空间。从历史经验看,学校武术发展一方面需要外部力量的推行,另一方面,其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地区的综合条件,内外两方之力均不可或缺。
3.1 北京体育研究社的调查
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曾针对北京、河北、辽宁、湖南、陕西、四川与广东等地40所中等以上学校,进行体育课实行情况的调查,其中有“校中教授体操其中种类为何?已否加授国技并是否列入正课?如已加授国技,学生对其兴味如何?”的项目,结果显示,40所学校中,加授国技的学校有29所,其中把国技列入体育课(包含正课与选课)的有25所,仅在课外活动中举行的有4所,足见比例很高。而这些加授国技的学校均表示,学生对国技课颇感兴趣[1]。就整个中国而言,40所学校的取样或许太少,但从中已能大略了解当时学校推行武术课程的概貌。而北京体育研究社的这份调查也提供了一个范例,国术在学校单位的推广,可以列入正课或选课,也可以通过学生参与课外活动的方式来进行。
从推行者的角度看,29所学校加授国术,似乎还难以满足其对学校武术发展的期待,但从作为正课的武术课程比例来看,前景似乎更为乐观。无论如何,这份调查至少启示当时的学校武术推行者,多元化的教学形式是武术在学校生存的重要一步,从无到有,从多元(有正课与选课之分)到一元(全部列为正课的理想状态),是武术在学校推行的必然路径。
3.2 求助行政力量
武术作为一项传统体育形式进入学校平台发展,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其从民间到官方的身份转变。因此,借助官方力量推行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
以北平市为例,北平市国术馆曾于1931年调查本市中等以下学校国术课程推行状况,发现有国术训练的学校实属少数,因此,于该年12月呈请北平市政府通令全市中等以下学校将国术纳入课程中。北平市政府遂于隔年1月令教育局遵照办理[32]。1934年7月4日,教育部体委会第12次常会中指定了国术课程标准实验区,包括北平、济南、青岛、南宁、桂林等地,并由各处教育行政机关指定学校实验区[20]。但北平市国术馆发现,当地如市立师范及市立中等学校竟然停止教授国术。因此,希望市政府能令行社会局转令全市中等学校一律添授国术,此呈案后来也获得市政府认可[3]。此外,1934年6月,为推行国术教育,北平市国术馆与北平市社会局合作,举办为期6个月的小学教员国术讲习班,共有50余名小学教员参加[2]。该馆截至抗日战争前,至少举办过3期此讲习班,并于1937年11月应北平市社会局所托,举办北平市中、小学教员国术讲习会[29]。
可见,学校武术的推行涉及市政府、教育局、社会局等诸多官方部门,在推行遭遇种种困难后,没有官方行政力量的介入很难达到预期成效。
3.3 地方国术馆的努力
由于当时的国术馆上至中央下至县区、村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武术组织系统,成为武术传播的主要组织,自然也对学校武术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武术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如山东地区本身有尚武风气,青岛市学校武术运行良好。1927年,青岛国技学社负责人杨明斋就曾被北京路小学聘为武术教师。1931年,沈鸿烈任青岛市长兼任青岛国术馆馆长,通令全市各中、小学添增武术课程,并选派第一期教授班毕业学员赴各中、小学担任教员[38]。同时,鉴于该市国术教员程度参差不齐,青岛市国术馆曾于1931年10月与1933年12月,举办两届国术教员检定(第一届82人、第二届约百余人合格),内容包含受检人资料调查(姓名、年龄、籍贯、受业师父之姓名及籍贯、所习国术种类、负责介绍人、受检人现在职业及地址)、表演与笔试。同时规定,凡是身有残疾、有不良嗜好、性情暴躁、品行不端、曾受刑事处分、未满20岁者,均无受检资格。通过之后,取得合格证书(3年为限)始得于该市任教[31]。
一些县级国术馆同样对学校武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1930年,四川省江北县国术馆副馆长曾在县立高级小学、县立女校任教,教练员吴洪楠也是当时江北县立模范小学教师[50]。由于江北县学校缺乏国术师资,县政府于1934年8月1日,举办了为期1个月的小学国术教师讲习班;1935年1月,举办了各区、乡、镇教育委员的国术讲习班,为期10日;同年8月,举办全县各公、私立中、小学国术教师讲习班,为期1个月[50]。该馆也曾选派学员支援缺乏国术教师的学校,如该馆专科班学生黄天觉于1936年被派赴石船镇仁里乡村师范学校担任国术教师,兼任第一区立小学国术教师[50]。
综上可见,学校国术教育事业的推行,一方面依赖教学形式多样化,这有利于逐步实现武术在学校体育教学从辅到主、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转换;另一方面,行政推行始终为倡导者所重视。除此之外,还须依赖当地武术运动的社会基础、当地国术团体的积极作为和当地政府的配合。
4 学校国术教育状况
在了解民国时期学校武术的推行状况后,再从师资来源、培训、课时、教材等微观方面聚焦考察,以利于对民国学校武术发展做出恰当的评价和反思。
4.1 师资来源的三元结构
民国以来,学校国术师资来源大致分3类:1)民间武术家;2)来自民间的武术社团;3)各级国术馆及体育专门学校或学系所培养的学生[13]。可见,当时国内尚未针对学校国术师资设计一个通盘的培育与甄选方式。
1. 民间武术家。如浙江的金鼎回忆,民国初期的吴兴县创办了一些新学校,这些学校都设有国技课(后改称国术课),当时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便聘请杭州的李宝瑚担任国技老师,他也在金鼎当时就读的高级小学堂兼课,后来金鼎拜李为师并学有所成,李宝瑚便派他到一些学校教武术[23]。1926年,陈泮岭担任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时,曾聘请少林拳师郭少芳(许昌人)担任该校武术教师。陈泮岭在担任该校校长前,也曾在当时开封北仓女中担任过武术教师[11]。其他如刘殿琛、斳金亭、李存义等武术名家都曾被若干学校聘为武术教师。
2.民间的武术社团。如上海精武体育会曾于民初支援师资到上海、江苏等地部分学校教授武术,包括上海中国体操学校、上海复旦公学、中华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东亚体育学校、江苏省松江第三中学、上海澄衷中学、爱国女学、上海培德学校、崇德女校、吴淞水产学校、南洋女子师范学校等[9]。佛山精武会于1922—1926年,支援当地道济、公理、元甲学校等共17所学校国操教学[10]。上海中华武术会于1920年起,向厚德小学、圣保罗学校、启明小学、沪北公学麦伦书院派任会中教师或会员到校担任教授或表演[40]。有时,民间国术社团的表现会影响当地学校是否加授国术。如1931年,西北军骑一师到宿迁驻防,由于师长张华棠本身热爱武术,同年举办了宿迁、睢宁、邳县及沐阳四县运动会,宿迁县国术研究会在此次运动会表演出色,声名大噪,使得当地学校间形成国术热,中学因此专设了国术课[27]。
3. 各级国术馆及体育专门学校或学系所培养的学生。自晚清以来,中国陆续成立培育体育师资的学校,这些学校中多有教授武术课程。光绪33年(1907年),徐一冰在上海成立中国体操学校,其术科中除了各式体操与兵式操外也包含武术[52]。1917年,北京体育研究社附设体育讲习所成立,1920年改制为北京体育学校,教授术科中以各类徒手与器械国技为主,兼含兵式操、普通体操、球类、田径、童子军与日本柔道[46]。
大体而言,民国初期学校直接从民间聘请武术教师的情况较多,民国中后期仍有此现象。之后,由于学校需要武术与体育运动兼重的师资,师范院校体育科系或以武术为重点的专门院校(如中央国体专校)应运而生,来自这类体系的师资渐渐变多[13]。而在国民政府时期,各地国术馆在培训当地学校国术师资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另外,中央国术馆身为最高国术机关,一直有学生被选派到各单位服务,截至1935年,中央国术馆几乎每年都选派人员到学校任教[14]。
4.2 国术师资培训质量堪忧
一般学校国术师资的培育,的确必须依赖各地国术馆或社团。虽然1932年《国民体育实施方案》通过后,明确规定国术师资“应在国立体育学院或体育专科学校训练,在体育专科学校未有国术毕业生以前,由国术馆负责训练之”[37],但就实际层面来看,当时一般师范院校体育科系的国术课程所占时数不多,每周总教学时数33小时中,国术只占1小时(男生多加4小时军训)[22]。如1918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体育专修科,在每周课程总时数37小时中,拳术与摔角课程共占8小时,因为都是必修课,其时数比例算是高的[21]。但该校在1923年改制成北京师范大学后,其体育专修科也于1929年改成体育系。此时各年级学生体育术科必须任选竞赛运动、体操、技巧运动、舞蹈、武术等科目至规定的学分:一、二年级为8学分,三、四年级为10学分,其中武术占2学分,但其他如竞赛运动与技巧运动等都占4学分;而三、四年级8学分的必选学科中,国术研究只有2学分,其比重下降由此可见[28]。
从1934年12月教育部颁布的《体育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科目》[17]来看,其实也可见国术在体育师范学校的地位,表1为男生术科部分。
表 1 《体育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科目》男生术科部分一览表
Table 1 “Graduation Examination Subjects of Sports Nnormal School Students” Boys Technical Part

具体项目 合格标准田径类100m及格:15s;优等:14s;最优等:13s1500m及格:6min30s;优等:5min30s;最优等:5min急行跳高及格:1.25m;优等:1.35m;最优等:1.45m急行跳远及格:3.50m;优等:4.50m;最优等:5.50m掷标枪及格:15m;优等:30m;最优等:35m掷铁饼及格:20m;优等25m;最优等:30m16磅铁球及格:6m;优等:7m;最优等:8m临时发问包括规则及教学方法之问答器械类单杠引体向上3次,继以向后回环上,侧腾越下双杠摆动向前振身上,继以肩倒立,向前滚翻摆动俯腾越下木马横木马高1m,向前跑去行分腿腾越球类 足球停球、传球、运球、踢射4项基本动作篮球传递、投篮两项基本动作排球发球、托球、压球、传递4项基本动作柔软操柔软操(一)自编教材一套并说明动作的功能;(二)自编仿效操一套并说明动作的功能
由表1可见,教育部此时未将国术列入会考科目中,因此,当时的北平市国术馆便分别致函中央国术馆与华北国术促进会,希望能向教育部反映此事[4]。于是,教育部于隔年1月增加国术合格标准,男、女生都是器械1套及徒手1套。但就此会考科目标准来看,无论是田径、球类、器械还是柔软体操,都有详细的及格标准与内容,唯有国术只规定“徒手一套,器械一套”,未免过于空泛。然而,国术一项是由国术团体出面反映后才增订,且张之江此时是教育部体委会委员,因此,此项国术会考合格标准如此空泛,确实是相关提倡者的缺失。同时,也反映出国术与其他田径、球类运动相比,确实难以量化测量。
严格说来,体育师资人才不足也包括除国术外的其他领域。因此,当时的教育部为训练体育人才,1933年7月10日~8月20日于南京举办暑期体育补习班,对象是现任中小学体育教员、现任公共体育场职员、现任国术馆教职员、现任教育行政机关办理体育行政人员,以及对体育确有相当研究及特别兴趣并有当地教育行政机关证明者。在为期1个月的训练时间内,针对国术一科也做了规划[5]。这种做法很像现在的教师研修班,但可惜的是,隔年由全国体育协进会承办第二届暑期体育补习班,却没有将国术列入其中。更因地处偏僻,加上各指导人员多未出席授课,造成许多学员中途退出[6]。此外,这类讲习班的训练时间很短,加上参与的教师可能只任教体育,未必都曾学过国术。所以这类讲习班的训练成果如何,确实令人怀疑。
4.3 中、小学国术课程时数极为有限
由于国术被纳入体育课,在每周有限的时数中,每所学校能否在体育正课内安排国术确实令人怀疑。至于大专院校的体育课程,在1931年以前没有相关规定,1932年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才规定:“大学体育课标准,在未经颁订前,应由各校自定细目试行,每星期2小时;不及格者,不得升学或毕业”[30]。1936年的《暂行大学体育课程标准》中才明订每周2小时的课程与体育课相关范围,但严格来说,体育课程还是各校的自主内容。一般中、小学校体育,本就不为培养专业运动员,且由于时数有限,还必须与其他体育项目分享,因此,这些国术课可能只能浅尝辄止。以1936年小学到高中体育课程分配时数为例,展示学校体育相关学科每周分配时数与体育教学总时数(表2)。
表 2 各级学校体育相关学科每周分配时数与每周教学总时数[22]一览表
Table 2 All Levels of School Sports Related Disciplines Distribution Arrangements and Teaching Hours Per Week

小学高年级初中 高 中每周体育、童军、军训课时数3h体育与童军共4h体育2h、军训3h体育教学总时数23h31h30h(三年级下学期为29h)
注:小学仅有高年级纳入太极操课程,故只列高年级时数。
4.4 国术教材标准长期不一
1919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呈请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学校武术课程教材,该呈附上数种拳术、器械教材供该部参考。包括内家拳、少林十二式、岳氏连拳、唐拳、潭腿、八卦拳、岳氏散手、剑术(神禹剑、纯阳剑、昆吾剑)、刀术(八卦刀、太极刀、六合刀)、枪术(杨家梨花二十四式枪、太极枪)、棍术(少林棍法阐宗)、戟术(方天戟)等。此案获得北洋政府教育部通过,并分行各省转饬各校办理。此外,中央国术馆也曾在1934年受教育部请托,预备编定初中与高中课程,当时已拟定第一期的教材,初中为五行拳、弹腿、劈挂刀、三才剑4种;高中为八极拳、八卦掌、梅花刀、昆吾剑4种。小学方面,则把太极操纳入高年级体育课程当中。
1934年11月1日,华北国术促进会正式成立[26],计划统一国术教材并每年举行华北国术竞武大会。在1935年间,华北国术促进会拟定一套《大中小学校国术教材标准》[7],此案获得教育部体委会通过,并经教育部获准采纳施行,通令各省、市作为国术教材暂行标准(表3)。国民政府时期,青岛市国术馆鉴于该市中、小学国术课程一向没有规定,召集各校国术教员讨论国术课程标准,于1933年12月制定了该市课程标准[31](表4)。
表 3 《大中小学校国术教材标准》[7]一览表
Table 3 Martial Arts Teaching Material Standards of Universities,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教学目标年级教学内容 备 注小学1)灵活肢体,敏捷官能,发育人类固有的机能,并增进其智慧;2)矫正身体不良姿势,使复正常状态;3)教以国术的技能,俾能精深研习各种较深的国术;4)养成练习国术的习惯,借以训练良好的武德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1)太极操;2)少林十二式;3)拳术基本(如蹓腿穿掌等)1)太极操;2)拳术基本;3)简单拳术一种1)岳氏连拳(八路);2)太极操;3)拳术基本附注:太极操、少林十二式、拳术基本、岳氏连拳等均已编有讲义,印刷成书。

续表 3
表 4 青岛市中、小学国术课程标准一览表
Table 4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Martial Arts Curriculum Standard of Qingdao

年级必 修选 修小学初小四年级弹腿踢毽、刀棍、摔角高小一年级拳式、连贯高小二年级单拳、大刀中学初中一年级单拳、棍摔角、射箭、单器械、对器械初中二年级摔角式、对拳初中三年级大刀、拳、剑式高中一年级拳、摔角对摔摔角、射箭、单器械、对器械、石墩子、打镖、测力高中二年级拳、对散手、单棍、对棍高中三年级拳、单剑、刺枪小学(女子)高级踢腿、拳式踢毽中学(女子)初中一年级单拳、对拳踢毽、射箭初中二年级单拳、单刀初中三年级单拳、舞剑高中一年级单拳、对剑测力、弹弓高中二年级单拳、单刀高中三年级单拳、双刀
国术教材编制标准长期不一,一方面是由于没有一个具备足够统摄力的机构专门负责教材编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即便有官方推行的教材编制标准,但未形成上行下效的局面,这一点从青岛市国术课程标准与华北国术促进会编制的教材标准相差诸多可见一斑。但应该认可的是,此时已经认识到国术标准化问题的重要性并尽力实行。另外,从上述教材标准的复杂性也可看出国术界对国术体育化、教育化的重视,也可看作是“土体育”遭遇西方体育之初与之角力的写照。
5 民国武术教育的反思与评价
基于对民国时期学校武术不同层面和构成要素的历史考察,本文从以下4个方面对其作出评价,反思彼时学校武术发展的抵牾,以期为当今学校武术发展提供借鉴。
5.1 学校运动会的观察
时人对学校武术的看法,从其对学校运动会中武术表演的意见可窥知一二。如1914年11月,首次江苏省立各学校联合运动会中,就有拳术、武器、薙刀术等武术表演[15]。1915年5月,蒋昂(时任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教员)参观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与常熟联合运动会后,提到常熟联合运动会中县立三校有柔术表演,认为“尤为提倡国技,大足以为各校取法”。因此,蒋昂也认为第二女子师范不妨也在课余时加练柔术[17]。同年10月31日,江苏省立各学校第二次联合运动会中,国技项目就占了1/6,被评为“最有价值”。有参观者亦认为,此次大会中的拳术、柔术、武器、击刺等都逐渐进步,“大有可观,使旧时武道借以流传”[47]。1916年11月,江苏省第三次联合运动会,省二农校表演的拳术,被观众评为“颇见工夫”[42]。总之,在那个尚武的时代,又基于保存国粹、唤醒民族精神的需要,对学生学习武术大多是赞成的。
5.2 武术进入学校体育框架的困境
1921年,体育学者徐一冰总结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推行体育的状况,认为,中国这20年来的体育成绩,“一言以蔽之曰:‘无成绩’”[43]。五四运动以后自由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思潮,一方面确实导正了先前国人过度偏重军国民教育的风气;另一方面,也带来不良后果,因当时国内体育师资良莠不齐,导致有些学校出现体育课任由学生爱打球就打球,爱跑就跑的“放羊式”教学[53]。学校国术课程方面,虽然若干学校对此不重视,但不少地区的学校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屡屡向各地国术团体与国术馆聘任教师。地方习武风气以及地方政府的配合程度,是影响国术课程推行成果的重要关键。不过,由于国术是被纳入体育课程之中,而各级学校体育课时数本就有限,相应地缩限了国术正课的份量。至于体育科或体育专校,本身担负培训体育教师的责任,但国术无论在学科、术科乃至于毕业会考中,比例也较为偏低。因此,最终各地国术馆以及中央国术体专成为培训国术教师的主要机构。
5.3 武术发展与个人兴趣的抵悟
一战过后,在新文化运动批判旧传统的风气之下,此时的教育风气是注意学生个体之发展需求,讲求健全之身心。因此,学校中的武术课程,便更加讲究适合学生。陶行知在1919年担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时,曾于该校校务会议上提出,除体育专修科外,其他各科应把拳术改为随意科(选修)。陶行知认为,鉴于个人体质与兴趣,不应强迫人人学武术,且改为随意科后,教师能活用方法,学生也应其所好,效果较好[36]。1926年第11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通过了《学校体育应特别注重国技案》,要求各学校加授国技,但也要求以不妨碍儿童身体发展为原则,并要求设有体育专科的学校要加授国技学科,以储备师资[12]。此外“不妨碍儿童身体发展为原则”的要求,足见当时的自由主义、平民教育思潮之影响。作为一种个人兴趣,国术绝非适合所有学生,这就与精英联合国家进行大范围的学校武术教育推行形成了矛盾。无论其立意如何,是培育尚武精神还是弘扬国粹,国粹的弘扬终究不是所有人的事,这一点,在极力推行学校武术的现今,仍值得深思。
5.4 武术竞技成效不彰
从武术竞技比赛成绩来看,学校武术推行收效甚微。唐豪本人批判民国时期的第六届全运会国术项目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所调查的14个单位共240位国术选手,仅有16位出于学校,有165位出于国术馆与国术团体。这意味着推广国术最有成效的是国术馆与国术团体,教育当局与体育界提倡学校国术的效果不佳[35]。由于一般学校的国术课程时数少,而国术馆系统又培养出一批国术专门精英,其训练的质与量自然非一般学校学生所能相比。因此,除非一般学校愿意组织国术校队,否则很难让一般学生与这些国术馆精英竞争。由此可见,一些重大的国术比赛也趋向精英化,先前国术界力求国术普及的呼声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口号,甚至也步了若干西洋体育竞赛选手制的后尘,这恐怕也是国术界始料未及的。
[1]北京体育研究社.调查京内外中等以上学校体育情形一览表[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9[C].北京:中国书店,2008:311-322.
[2]北平市国术馆.本馆设立小学国术讲习班[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15[C].北京:中国书店,2008:389.
[3]北平市国术馆.呈北平市政府请令行社会局通令各中等学校教授国术以重体育由[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15[C].北京:中国书店,2008:415-416.
[4]北平市国术馆.函中央国术馆;致华北国术促进会函[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15[C].北京:中国书店,2008:136-139.
[5]北平市国术馆.教育部暑期体育补习班规程;教育部暑期体育补习班入学规则[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15[C].北京:中国书店,2008:316-317.
[6]参观青岛体育讨论会之情形[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16[C].北京:中国书店,2008:396.
[7]重远.有办法了——国术[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27[C].北京:中国书店,2008:184-186.
[8]陈独秀.青年体育问题[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82.
[9]陈铁生.派往各团体教授技击职员表[A].精武体育会.精武本纪[C].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175-176.
[10]佛山各校之国操概况[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5[C].北京:中国书店,2008:277-279。
[11]高韦伯.解放前的开封高中;胡绍芬.忆开封北仓女中[A].全国政协文史数据委员会.中华文史数据文库:文化教育篇(第17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202-211.
[12]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议决案选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17.
[13]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48.
[14]国术周刊.中央国术馆历年派出之学生及姓名服务机关一览表[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25[C].北京:中国书店,2008:194-197.
[15]幻龙.参观江苏省立学校联合运动会记事[J].教育杂志,1914,6(1):35-39.
[16]贾丰臻.忏悔篇[J].教育杂志,1919,11(4):27.
[17]蒋昂.参观江苏第二女师范及常熟联合运动会纪[J].教育杂志,1915,7(7):45-47.
[18]蒋百里.军国民之教育[N].新民丛报,光绪28年第22号:33-52.
[19]教育部公报室.教育部公报(第六卷,第49、50合期)[Z].1934-12-16:25-26.
[20]教育部体委常会决定参加世运会,指定平济等地为国术课程标准实验区[N].大公报,1934-7-6(6).
[21]教育公报.北京高等学师范学校周年概况报告书[A].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310-311.
[22]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1019.
[23]金鼎.李宝瑚与湖州武术[A].政协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州文史(五)·教育医卫史料专辑[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35-137.
[24]金兆钧.体育行政[M].上海:勤奋书局,1931:173-190.
[25]梁启超.论今日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17-19.
[26]刘建民.华北国术促进会成立情况[A].河北体育文史编委会.河北体育史料(13)[C].石家庄:河北体育文史编委会,1989:51.
[27]罗韫辉.宿迁县国术研究会[A].政协宿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宿迁文史资料(八)[C].江苏省:宿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74-76.
[28]吕古青.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现状[A].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312-321.
[29]麦克乐.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文选[C].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109-112.
[30]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编委会.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47[Z].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23082-23088.
[31]青岛市国术馆之推行工作[A].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编委会.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50[C].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24845-24846.
[32]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15[M].北京:中国书店,2008:311-322.
[33]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17[M].北京:中国书店,2008:257-258,411.
[34]孙中山.精武本纪 [M].上海:精武体育会,1919:1.
[35]唐豪.对于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国术”部门的再检讨[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20[C].北京:中国书店,2008:225-240,261-262,287-289,319,336.
[36]陶行知.改拳术为随意科[A].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389.
[37]体育周报.国民体育实施方案[A].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编委会.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47[C].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23082-23088.
[38]王第荣.青岛武术史话[A].青岛市市北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市北文史资料(一)[C].青岛:青岛市市北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3:140-141.
[39]吴文忠.中国近百年体育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169-201.
[40]吴志青.本会一年之历史[A].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编委会.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50[C].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341。
[41]湘青.体育究竟是什么[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C].中国近代体育文选.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125.
[42]心宏.江苏省各校第三次联合运动会记[J].教育杂志,1916,8(12):185.
[43]徐一冰.二十年来体操谈[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C].中国近代体育文选.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77-80.
[44]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C].中国近代体育文选.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23-24.
[45]杨贤江.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A].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C].中国近代体育文选.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119-123.
[46]伊见思.北京体育学校之组织[A].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9[C].北京:中国书店,2008:392-398.
[47]张世鎏.参观江苏省立各学校第二次联合运动会记[J].教育杂志,1915,7(12):87-96.
[48]张之江.呈请定国术为国操挽颓风兴党国,1930-7-2[Z].国史馆藏.国民会议案(六)[C].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110-0015,入藏登录号:001000000079A.
[49]张之江.请审定国术为国操推行全国学校暨陆海空军省警民团实行普及以图精神建设期达强种救国案,1931-6[Z].国史馆藏.国民会议案(六)[C].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110-0015,入藏登录号:001000000079A.
[50]赵子虬,陈尚洁.民国时期的江北县国术馆[A].政协江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北县文史资料(三)[C].重庆:江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1.
[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文化(二)[M].上海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914.
[52]中国体操学校.中国体操学校章程[A].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297-299.
[53]曾瑞成.新文化运动时期之体育思想:民国八年-民国十六年[D].台北:台湾师范大学,1991:102-103.
[54]MORRIS A D.Marrow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185.
Textual Research on School MartialAr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V Si-hong
Through combing historical document,this paper detailed studi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its origins,the social rol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chool martial arts education condition,and makes a reflection and evalu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school martial arts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elites' promotion of the martial arts,which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people's bodies,defending country and saving the quintessence,was the main power of school martial arts' development,and it makes school martial arts become an important route of transmission. In elites' efforts,martial arts advanced continuously and became the mainstream basically in the school curriculum;In addition to various forms of martial arts teaching,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 martial arts education career,at least depended on three important conditions:regional social foundation of martial arts,local martial arts groups positive achievements,coordin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Martial arts teachers showed a three-element structure,teachers training was worrying,martial arts class time was limited,the standard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was no consistent. Generally speaking,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school martial arts of republic of China is just passable. The school martial arts of republic of China had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to some extent,but it had ignored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interest demand,the competitive efforts was ineffective,and it suffered many dis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martialarts;therepublicofChina;school;education
1002-9826(2016)01-0016-08
10.16470/j.csst.201601003
2015-04-30;
2015-08-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5YJC890016);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14CTYJ23)。
吕思泓(1969-),女,山东青岛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竞技体育政策研究,E-mail:lvsihong@qlu.edu.cn。
齐鲁工业大学 体育与文化产业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3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nan 250353,China.
G812
A
——以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汇刊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