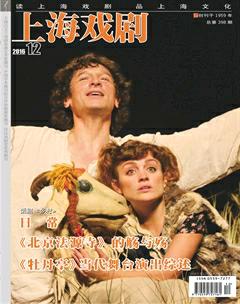《北京法源寺》的觞与殇

深秋时节,在上海能看到《北京法源寺》这样一部讲述历史话题和带有艺术家个体强烈印记的作品是一种幸运,它既激发了你我已被上海数以百计的低俗化与模式化的舞台剧弄得麻木不堪的艺术知觉,也让我们再次思考戏剧的形式和戏剧人所承担的责任等诸多问题。
在剧终的掌声之后,很多人也在探讨这部作品。有人说这将是一部“新世纪的话剧经典”,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一场语言密集、情绪激昂的剧本朗读”。有圈内人似乎客观地认为“前半部有些平淡,后面较为精彩”,也有激进的青年戏剧评论者说“这是田氏话剧的末路”。一部作品能激发出那么多的想法,往往意味着这部作品在创作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艺术家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及其运用有时会同时产生正负两极的效果。
觞,名词为盛酒容器,动词为“欢进,饮酒”。
这部作品的信息量和台词量之大是近年来罕有的。同时以即时的观剧体验而言,对大多数的观众都是一次可谓“醇真”的话剧。
戏觞与情觞。
不可否认,田沁鑫是当下中国兼有传统戏剧精神、当代意识、文学修为的导演,再加上她对佛学与历史的喜爱,都在这一部《北京法源寺》里得以施展。使得这部作品呈现出先锋与戏曲的糅合,诗意与禅意的蕴存。别人的戏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这次是将无数的时空、众多的人物都压进这法源寺的庙宇之内,让国家命运与生死抉择以及相伴的观念与道德都在这里展现。好不酣畅淋漓,让人目与耳都难以暇接。幸好,舞台还是以往的空灵,音乐也比较恬淡。
作为国家话剧院的导演并受到资本、媒体、观众的多重青睐,田沁鑫在这次的创作中可以说握着满手的好牌。此外,从《狂飙》开始,她还显示了作为导演调动与激发演员戏剧能量的擅长。应该说在这出戏里,不管是老戏骨还是年轻的演员,都被导演释放出了其需要的情绪,时而是平静的表述,时而是澎湃的激情。我尤其喜欢周杰对光绪的人物处理,他的激情蕴藏在平缓的语调与慈光中。他和戊戌君子间跨越阶级的友情是新鲜的、感人的,身处禁地,他的胸怀又是宽广的。
在光绪这里的停顿近乎是全剧中仅有的,更多用了密集叠加来将这种舞台表现做到极致。这样的手法无疑打动了很多在场的观众,甚至给人产生了一种营养汲取过剩后的满足感。当走出剧场时,我觉得有些口渴,这才想起入场时被剧院服务员扣下的矿泉水。我感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作为观众是需要冷静与平淡的。田导的《四世同堂》曾让我在观剧时热泪盈眶,那是因为我的父辈和祖辈就是那样的故都子民,在那国破的岁月隐忍地维护着家庭的生计与尊严。而这部作品反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离我祖辈曾经是咫尺之遥,但想来当时担任禁卫军的他们又是遥远的,而这之后改变的中国乃至世界的轨迹又是那样的始料不及。
殇,一个与死亡与悲伤相关的多义词。一解为“为国而战死者”,另一说法则是“未成年而亡”。
国殇与戏殇。
《北京法源寺》通篇讲的是政治与历史,最后聚焦的还是生死。谭嗣同和他的朋友是为国而死。可视为“国殇”。
在这部容纳了艺术家颇多文学、历史、哲学、戏剧想法的作品内,有太多东西来不及体现与发展。这值得惋惜,也是当下戏剧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甚至让我们看不到今后的自愈与发展。可谓“戏殇”。
历史是一面镜子。
回看历史往往有些惊诧与不堪。除去遥远的大秦、西汉和盛唐,大清是具有帝国之相的。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清朝的GDP已是世界第一达百余年,白银的贸易顺差更是惊人。在将北方的大量领土拱手相让给沙皇俄国前,更是版图的世界第一。可怎么五十年就到了光绪年间的分崩离析,六十年后朝廷坍塌,九十年后差点被东夷所灭?为何当年的变法出不了京师,百姓毫无知觉?难道变法的失败真的仅是因为袁世凯的出卖?历史上的袁世凯是以在朝鲜以少胜多的抗日英雄形象亮相的,就像在剧中编剧给予他的自我评价一般“好名声在这一天毁了”。我们期待历史剧,固然希望再现那些惊心动魄的情节与场景,更希望艺术家给出自己的见解与答案。
抛开那些帝王戏和清宫戏,我个人认为《曹操与杨修》之后真正的历史剧不多,杰作更少。从这一点来看,《北京法源寺》无疑是当下较好的历史剧呈现之一。据说田沁鑫为了写这个剧本看了四十多套历史书。我无从知道这些书都是哪些,但我知道当下的历史写作与戏剧一样佳作匮乏,更多的是史料或演义。其实还是应该回首比较李敖的原著,我觉得本剧在形式、人物和主题方面还是未达到相应的位置。
虽然也有人认为李敖原著有些像游记,比较松散,但是他从唐代悯忠寺的来源一直讲述到1927年中国再次面临的剧变与生死抉择,其中有国的兴衰与朝代的轮回,也有着人物境遇的变化和多重角度的审视。有的浓墨重彩,有的抓到一两个细节则让人唏嘘不已。比如老家人将谭嗣同的身首缝合后拉往法源寺,忽然发现他所活动的浏阳会馆和行刑之地如此之近,并且是必经之路。
李敖笔下的人物往往几笔就跃然纸上,却与历史书中有些不同。这些不同不仅是小说与现实的差距,更是深剖和浅析的距离。
在原著中康有为是最丰富的人物,但在舞台呈现中却被戏谑化了。剧中康有为的形象塑造,不像李敖小说中那样是一个心中有导向有乾坤的人,他的变法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舞台剧中加入了网络语言、方言等不符合人物性格的东西,例如康有为和光绪帝会面的时候说自己“颜值不高”,在和袁世凯对峙的时候说对方“就是一块钱。”这样的设计固然在剧场里会引发一定的效果,让年轻观众乐于接受,但也使康有成了一个没有辛酸的丑角。在那个时代,陈旧的官僚群体因他立足高远而试图绞杀,后来的革命派也曾嫌他保皇落伍而弃之如敝履。
对谭嗣同的处理,舞台剧《北京法源寺》中主创将他对生死的超脱、世事的洞察与赴死的豪迈,一同展现了出来。而在小说中则多了很多作者的思辨,谭嗣同之所以毅然赴死,一是为了向改良派同仁和世人展示以血来变法的决心,二是引发革命派对高层改良之路不通的认识,并且形成从底层激发革命的可能。历史上的进程,从辛亥革命到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也验证了这一点。
田沁鑫曾经这样回答记者:“想要还原历史真相是不可能的。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要从容。”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我觉得还是有些做大布局的意思,田沁鑫也给予了作品她自己的风格,犀利而不失幽默,但如那一见面就被人喷了一脸白粉的袁世凯一般,并未渗入肌肤。
尤其是光绪与康有为会面之后,作品的焦点与指向是凌乱的。在接近剧中时,主创将六君子的生死之别一一展开,虽有映衬也感人,但总觉得就像那次变法一样,仅是历史的小浪花。若真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屡屡回顾、细细考量?再反观原作,既有着人生的禅意超然,也有着政治的疾风逼人。坊间曾有传言李敖曾因这部作品被提名“诺贝尔奖”,过去曾认为是空穴来风,今日配着舞台剧再品味一番,觉得作者在狱中开始构思的小说的确值得深读。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戏剧美学汇入当代舞台,又如何将西方的戏剧观念融入传统,这是导演们一直在努力尝试却又成功者寥寥的。田沁鑫一直是这支队伍的领跑者,从《生死场》到《狂飙》,成绩斐然。这次尝试,不能说很失败,但也不能说很成功。那些成功的作品大多给了舞台很多留白,这次《北京法源寺》一开始留白很多,但导演不时地填充进很多东西。虽然那酣畅淋漓的台词、冷静和激情交替的表演让观众目不暇接,但也阻碍了观众对这个作品的审度和思考。
在戏剧观与样式方面,《北京法源寺》将戏曲假定性与西方一些重要的戏剧观念糅合在了一起。细细品来,既有来自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戏剧家皮斯卡托政治剧的影响,也有俄罗斯导演梅耶荷德创造性戏剧假定性的反哺。甚至在两边台口的立式话筒的运用上有着当代德国邵宾纳剧院著名导演奥斯特玛雅的用“麦”介入到舞台与演出的效果。此外由于史料与舞台呈现的新颖性,也给观众带来了相当的“陌生化”效果。但我觉得恰恰缺少了布莱希特式的间离和思考。这部作品当中,在导演的引领下,所有的演员都表现出了献祭般的问道精神,却缺少了李敖作品中的导向性与切割。舞台上高浓度、高信息量地展现历史的过程与结局,原著被审视、被撕开、被重构,却少了一些被诘问。
创作需要源点,也需要终极目标。
几乎所有展现戊戌变法的小说与戏剧都是讴歌或惋惜这些“国殇”者的。但为何我们要关注李敖的这一部小说和田沁鑫的这一版舞台呈现?
李敖的小说,构思精妙,从盛唐败军朝鲜后在北京建的悯忠寺到见证戊戌变法并替谭嗣同等人收尸超度的法源寺,叙事而不依附,展现的是“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的际遇”。你会追问:“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残忍?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李敖在书中感叹道:“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借此,我们可以感到冷锋割开的痛。而在舞台剧的呈现上,导演依托于庙堂完成了她的述说,让人感到死亡与复生之间的超然,铺垫着的《清平调》显得如此贴切。
应该说,田沁鑫比现在的一些导演更长于戏剧时空的打破、交错、跳跃的技巧,并娴熟于心。她能把传统戏剧舞台团块式的布局打碎,然后犹如蝉翼一般地展开……然而这次的作品还缺少发酵剂。可能是导演有意的隐忍,也可能是导演高耸庙堂的游戏精神使然。如果是这样,某种意义上,这倒是一条相对中庸的道路。最近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戴锦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代中国最大的困难是失去了坐标。”但,这也给了我们重构坐标的机遇。
有如歌德与席勒,又如曾写《关汉卿》的田汉,如果我们要谱写的是我们民族的史诗,需要的是洗礼、是炼狱和涅槃。如果我们要的是如布莱希特或迪伦马特般的反思和自省,那就舍弃激情与忘我,保留悠然与理性。
我很喜欢王恺在《戏剧文学》2016年第三期中发表的本剧剧评的标题——“在一个即将崩溃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是承担者”。我更愿意说,在一个期待建立新伟业的时代里,艺术家应该是一个先行的承担者。
就如同当年这些为国而殇的历史人物一样,不奢望不惧失,则必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