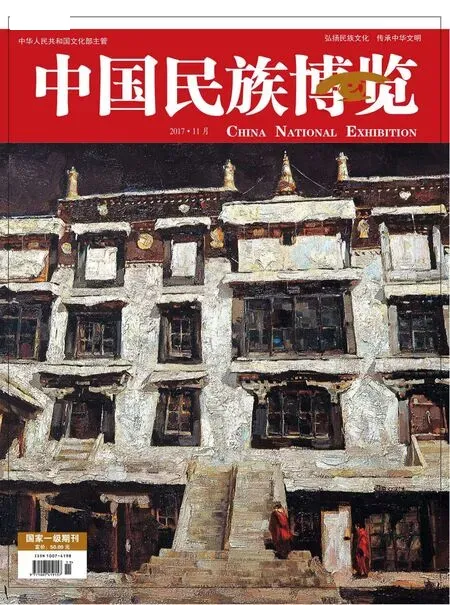浅析吉林陈汉军旗萨满的文化认同
佟国强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浅析吉林陈汉军旗萨满的文化认同
佟国强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在东北社会长期历史发展中,陈汉军萨满文化以其传承中诸多特性绵延不息。作为文化传承者的陈汉军萨满,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承载着神人使者的文化身份,并因之对文化和社会起到关键性的沟通作用。
陈汉军;萨满;文化身份
一、文化下的萨满
作为有别于佛、道、满洲萨满教与民间信仰的陈汉军萨满文化,自其始祖辽阳道士杨子修于康熙23年创立以来①,始终以其兼容并包的文化血统、广接民众的文化根基、凝聚宗族的社会效用为东北地区民众所信服。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陈汉军萨满以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被建构与塑造,在历史进程中逐渐稳固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人神使者,并因之对文化与社会起到了关键性的沟通作用。
二、“通神”的萨满
陈汉军萨满具有“神性”。在漫长的历史环境中,陈汉军萨满在民众的认识中,具备一些神的特性。这种神性色彩弥漫于萨满选拔、认证到祭祀的各个过程,是他们得以为人所信服的根本依据。
从选拔上看,陈汉军萨满分为师传、家传和神传②,而最主要的继承方式还是家传和神传。家传是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而家族内部遴选萨满时,选出的往往是体弱多病者,这是受当时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发展程度所限。一则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生活条件艰苦,生病的人很难得到有效的治疗;二则当时民间有着发达的鬼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抚慰群众的精神需求,因而病者在医者处得不到希望,便将希望寄托于神灵,希望借神祇的“神力”使自己痊愈,所谓“因病许愿”。一旦病愈,他们对神灵会更加虔诚地供奉,所谓“病愈还愿”③。而在族人看来,他们得到了神灵庇佑,沾染神性,因而是萨满继承人的不二之选。
当他们作为继承人被选中后,还要经历漫长的技艺方面的学习和训练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萨满。他们被要求完成常人所不能完成之事,譬如“打五路”——表演天神为人间“开辟了东、南、西、北、中五条光明大道”④,每一次开辟光明大道时用右手中的铡刀向放于左臂的铡刀连击三下,而手臂安然无恙;“放太位”——所谓“太位”即野猪神,为了更逼真地扮演带獠牙的公野猪神的形象,用两根三毫米粗的银簪分别穿过两腮,表演完而两腮完好、滴血未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通过完成这样常人无法做到的事,萨满在族人眼中更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同时,在表演过程中萨满会进入一种迷狂状态,即“痴迷”,这种状态绝非药物的作用,在旁人眼中便是神灵附体,而萨满则距离“神”更近一步,更加令人敬仰、敬畏。
在经过数年的学习、打磨之后,便要举行“台神”仪式,以宣示继承人个体正式成为萨满。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声和香烟缭绕的神秘氛围中,被台神者如果昏迷过去就被认为是为神所接受。举行了台神仪式,便是对神灵、祖先和族人做出了承诺,从而得到了神的授意,萨满就得以正名,其身份也最终得以神化。这种神化不仅为族人所信服,萨满本人也对其深信不疑。
究其根源,这种萨满即“神”的身份的建立是出于整个家族甚至陈汉军这个族群的现实需要。在陈汉军萨满形成之时,民间对神灵的崇拜和信仰是高于一切的,当人们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他们自然要祈求神灵的庇护,“鬼神”便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依托。对于陈汉军旗人来说,萨满就是他们的信仰核心,在他们看来,将族中选出的萨满塑造成一个具有神性的“通神之人”,就是了却神灵的愿望,可以让渺远的神灵与人相通,族众便在这样的过程中认为自己得到神灵庇佑从而产生了莫大的心理慰藉;而由萨满主持的隆重的萨满祭祀仪式,实际上起到巩固信仰、明确族人道德准绳和共同价值的作用,让族人可以在萨满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抵御艰苦的生存环境。
三、“人间”萨满
身份的神圣性使得陈汉军萨满保持一定的威望,而在平日生活中,他们仍是作为人而存在。在族中,他们是“智慧者”、协调者;在当地社会,他们是教导者、表演者。他们的日常权威大部分来自神性,表现出来则是规范乡里习俗,处理的是俗世人事,当然也存在问神或者采取神秘手段的行为,但陈汉军萨满更多利用道德规制乡邻,或者以德重者的身份名望充当协调者,体现的恰恰是经过神性沐浴的人性。
而即便是在神性最为丰沛的烧香祭祀仪式中,陈汉军萨满也表现出浓郁的人间色彩。萨满在履行祭祀职责时,不会完全进入神迷状态,始终能保持人性的清醒,亦是世俗的要求。在保持一定的神秘感的基础上,扎根于乡村社会的陈汉军萨满负有娱神娱人的责任,追随的自是贴近现实的人性一面。如王成名先生所言,“祭祀中的萨满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乡里人,他们十分熟悉当地群众的心理要求,群众信什么,他们就即兴创作唱词唱什么。”⑤陈汉军萨满将自身看作神和人沟通的中介,但在祭祀中,萨满代表人和神进行沟通,即使在一些模拟神的祭祀环节,萨满也保留人性,与传统萨满“降神”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在进行“放太位”时,萨满要扮演野猪神,双颊植入银簪表示獠牙,模仿野猪神的动作和神态,考验的是萨满的“技艺”,不排除其具有通过仪式入神的氛围,但实质上更倾向于一种表演活动,注重的是表演特定神的形态。⑥“汉军萨满文化,是由人和神的中介——察玛(萨满)说了算,一切就掌握在察玛手中,包括坛场的设计、坛场里活动,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而满洲的萨满信仰中,人完全听任神灵的摆布。”⑦从文化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应审慎辨析,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确切无疑:区别于原生型的萨满文化,陈汉军萨满更强调人性的主体地位,一方面是基于陈汉军萨满文化形成的较为独特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世俗的要求。
陈汉军萨满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的历史密不可分,汉军旗人借鉴满洲的萨满文化,既包含一种“入乡随俗”的文化心理,也可视作异乡人抚慰心灵的一种文化手段。而在实施时却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简言之“水土不服”。具体表现为首先汉军萨满文化起源时间晚,从文献记录来看,不早于康熙年间;其次,这种萨满文化很独特,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它是少有的通过后天学习形成的祭祀文化,并且当时汉军不完全具备萨满文化形成的基础,学习的成果很大部分是仪式和一些萨满技术。因此陈汉军萨满文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祭祀文化,它的源头就不是单纯的神灵崇拜,这就为人性存在于神的领域创造了可能。进一步来说,文化的传承也采取了通融的做法——通过类似教学徒式的“开乌云”和组建坛班,慢慢形成了兼具信仰活动和表演形式的萨满文化代代传承,浓厚的萨满人性色彩亦始终不褪。
神性影响了萨满的人性身份,或者说萨满的人性浸染着神性,是一种神性影响力向下延伸的表现。神性演变而来的世俗化权力,在各种文化信仰习俗中并不少见。而陈汉军萨满文化形成的历史因素使其萨满神性并未达到神权或类似的世俗权力的程度,相应的,陈汉军萨满文化从起源之初到后来的发展,人性的成分占据重要的地位,即人性反过来影响本属于神性的领域,形成陈汉军萨满人神交汇的特性,这种交汇集中在其祭祀活动中体现,也渗透到萨满的培育、传承上,最终对萨满自身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何陈汉军萨满也被称为“神匠”的原因。
四、总结
要之,作为信仰者的陈汉军萨满由普通的人因病许愿于神灵并治愈得以沾染神性,从此坚定萨满信仰;同时家族和社会的构建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了萨满本身的神性;在成为萨满的过程中,他们学习的一系列演唱、表演、组织等素质使其不断区别于常人,而在表演过程中神灵附体、迷狂状态以及模仿动物神的行为向普通民众表现出其神性。在具有神灵的的替代者身份的同时,他们又始终保持着作为人的清醒。
在一系列的文化过程中,人与神的成分不断绞缠并融汇。而正因其神人无隙的身份,陈汉军萨满既能作为神灵的代言人,有一定的权力来规范社会、娱神娱人,另一方面借助人的属性使得传承队伍不断发展。神人身份确认的同时,陈汉军萨满对文化与社会起到了关键的沟通作用。
注释:
①吉林省艺术研究所等编《汉军旗香坛续与神本》,长春,1985。
②出自2017.1.15笔者对张氏已故察玛张宗华先生访谈录.。
③出自2017.7.6笔者对张氏家族文史专家、吉林市政协文史委张荣波先生访谈录。
④吉林省艺术研究所等编《汉军旗香坛续与神本》,长春,1985。
⑤王成名,《陈汉军旗萨满祭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⑥刘红彬,《陈汉军张氏萨满探析》,《满族研究》2009年1期。
⑦出自2017.7.6笔者对张荣波先生访谈录。
C95
A
——以吉林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