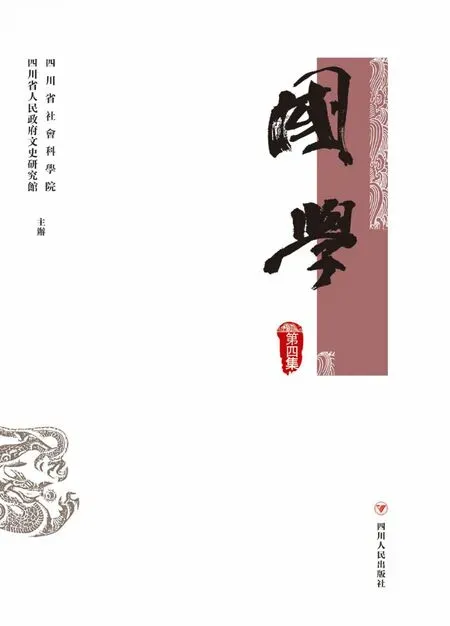宋學簡論
宋學的起始
宋學是中國經學史上的一支突起異軍,是變古派。因爲無論是注重微言大義的西漢今文學派,還是注重訓詁考證的東漢古文學派,都很講究學術源流和師承,有所謂“師法”“家法”之説,唐代雖也有少數經學家不因注迷經、因疏迷注,然而經學的主流爲義疏之學,它仍是古文學派的支流。及至宋代,經學則一反漢學的師承和訓詁傳統,大膽懷疑,拋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求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由於宋儒治經多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爲主,故又稱“理學”。又因它以繼承孔孟道統自居,亦稱“道學”。一般就經學而論,稱“宋學”,自哲學而言,稱“理學”。儒家首先談性命關係的是子思,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對子思的學説加以闡發,因此儒學中有思孟一派。宋學從思想淵源來説,它繼承了儒學思孟學派的學説,但它又受有佛家與道家的影響,尤其是佛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給予了不小的刺激,因此宋學的建立,實是以儒學倫理思想爲核心,而又糅合了佛、道二家思想的結果。
宋學的興起,有以下幾點原因。從政治上看,自唐代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長期處於割據、分裂和混戰的局面,倫理關係尤其是君臣一倫完全被破壞,宋王朝要想鞏固自己的政權,需要建立嚴格的儒家的綱常倫理和一套社會哲學理論來維繫和强化封建統治,因而極其尊崇經學。趙匡胤不但下令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親自爲孔子、顏淵撰寫贊詞,詔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而且自己還喜歡讀儒家經典,手不釋卷,他的宰相趙普還是個“論語通”。因此宋學雖然高談心、性、理、氣,但重點還是在倫常方面。從宗教文化方面看,魏晉以來,佛教盛行,文人士大夫頗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雖然佛教思想有麻醉性,統治者也需要它;但是講出家,背君棄父,又同儒家的倫理綱常發生矛盾,因此統治階級和文人士大夫在借助經學來重整綱常倫理時,也必然和必須要對佛教思想的有用成分加以吸收和改造,宋學高談的心、性,其中就有很大的佛教禁欲主義成分。道學思想當然也給宋學的興起助了一臂之力。雖然張載、程頤、朱熹都曾批評過莊子,但是莊子的有關思想和提法都曾被他們利用和改造,莊子在《大宗師》中描述真人的神通,要求人們摒除物欲回歸自然,從而達到“無己”的“絶對自由”境界時説的“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就被利用改造爲“明天理,滅人性”的思想而大得程頤的稱贊。從經學本身看,漢學從西漢末年的今文、古文之爭到西晉時的鄭學、王學之辯,到南北朝時的南學北學之分,已逐漸由思想的闡發流入於語言文字的訓詁,及至隋唐,義疏派實乃古文派之支流,其研究領域已愈趨窄隘,無可發展,而進入末路,士大夫中的才識之士自不得不别求途徑,以與佛道結合的方式重新激起思想的火花。宋學的起始,其遠源除了啖助、趙匡、陸淳等的《春秋》學外還有韓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其弟子李翱的《復性書》以及韓、李的《論語筆解》,其近緒則是劉敞的《七經小傳》、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歐陽修的《毛詩本義》和《易童子問》,而“宋初三先生”之説則是其椎輪和雛形了。
啖助、趙匡、陸淳等的《春秋》學研究開啟了宋學捨傳求經、大膽懷疑、探求本源的風氣,韓愈、李翱等則主要是通過“道”與“性”的研究,提倡倫理綱常。韓愈的《原道》主要提出、論述與佛教、道教的“道”相對立的“道”以及與佛教祖統相抗衡的道統。認爲儒教的仁義即道德,指斥釋、老之“道”“去仁與義”,“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毁滅倫理綱常。提倡“有爲”,强調《大學》中儒家的修齊治平思想,批駁釋、老的“虚無”,並且構造了堯、舜、禹、湯、武、周公、孔子至孟子的所謂“道統”。《原性》則提出“性情三品説”,認爲“性”與“情”各有上中下三品,對“性”,贊揚上品而引導中品;對“情”,主張“求合其中者”,以符合封建倫理的基本原理,爲封建倫理和等級制度提供理論依據。李翱的《復性書》,認爲“性”和“情”(情欲)是對立的,“性”善而“情”惡。主張用“齋戒其心”的辦法去滅“情”。他所説“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此齋戒其生者也,猶未離於静焉”“方静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静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這裏很明顯是儒道佛相結合,雖然要求達到的是儒家“至誠”的最高境界,是以《中庸》爲根據的,但它受到莊子“心齋”“坐忘”體“道”途徑的影響與佛家“寂滅”思想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韓愈、李翱都不是經學家,但有時也講點經學。但他們同注的《論語筆解》,牽强附會之處很多,學術價值不高,如釋“宰予晝寢”,將“晝寢”説成是“畫寢”之誤,釋“六十而耳順”,認爲“‘耳’當爲‘爾’,猶言如此,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這些都是很難講得通的。但它對宋學疑經、改經之風,卻有先導作用,而且個别的解釋也頗有見地,如釋《論語·先進》篇“浴乎沂”之“浴”字爲“沿”字之誤,就得到俞樾的肯定。
劉敞,字原父,世稱公是先生。北宋慶曆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其學識淵博,篤志經術,猶長於《春秋》學,著有《七經小傳》《春秋權衡》等。劉敞治經,與漢唐經學家依據古注對經典進行闡釋大不相同,好以己意釋經,開宋儒擺脱傳注束縛,評議漢儒的先聲。《七經小傳》(“七經”指《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是劉敞的代表作,也是宋學的發端作之一,其優點和特色是重義理輕注疏,發義新奇、不拘古訓。如對於《論語·里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二句釋爲:“君子在上位者也,言君子懷於爲德,導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如君子懷於用刑,導之以政,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己者以歸之矣,所謂免而無恥也。此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導之而已。”這裏明顯在於義理之發揮,與向之注疏迥異,就文理看,也有增字解經之嫌。劉氏於闡發義理外,有時亦兼及考證,如《論語·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釋爲“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舊説婦人即父母,予謂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按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父母猶存乎?以義推之,此亂臣蓋邑姜必非文母也;武王使九人者治外而邑姜始也,故得以同之亂臣。”這是好的方面。但劉氏治經,好穿鑿臆斷,甚至不惜改經。這類例子頗多,如將《尚書·無逸》“此厥不聽”作“此厥不德”,改“聽”字爲“德”字,將《詩經·小雅·常棣》“烝也無戎”作“烝也無戍”,改‘戎’字爲‘戍’字,都是明顯錯誤的例子。後世學者每致譏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便批評爲:“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
王安石曾著《三經新義》,對《書》《詩》《周禮》作了新的解説,擺脱繁瑣的訓詁,用來作爲變法的理論根據。熙寧變法,考試用經義論策,規定無須用《新義》之説。原書已失,清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收入《經苑》。今人邱漢生又輯校《詩義鉤沉》一册,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從上述二書中看,王氏藉經義以重事功、正法度的思想是十分明顯的。他在《周官新義》中説:“天地四時之官,各以象類名之,其義甚衆,非言之所能盡,觀乎天地四時,則知名官之意矣。蓋治所不能及,然後教;教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所不能勝,則有事焉;刑之而能勝,則無事矣,事終則有始,不可窮也,故以邦事終焉。”於《詩》,則認爲:“或曰:‘《國風》之次,學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猶以爲惑。今子獨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聖人之於《詩》,既取其合於禮義之言以爲經;又以序天子諸侯之善惡,而垂萬世之法。其禮天子諸侯,位雖有殊,語其善惡,則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詳,而十有五國之序,不無微意也。’嗚呼!惟其序善惡,以示萬世,不以尊卑小大之爲後先,而取禮之言以爲經,此所以亂臣賊子知懼,而天下勸焉。”(《臨川先生文集·臨川集補遺》)另外,《周官新義》還附會《周禮》經義,提出理財、整軍等改革。其訓詁亦時有割裂經義、牽强附會之處。
劉敞的《七經小傳》和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對宋學疑經之風的真正形成影響較大,王應麟在《困學紀聞·經説》中説:“《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事實上宋儒第一個突破舊唐注疏束縛,大膽辨僞糾謬,發抒己見,從而開創了宋學疑古惑經,闡發義理的時代風氣的是歐陽修,他的《毛詩本義》問世於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其子在《先公事略》中説:“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情性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未有説者其於《詩》《易》多所發明。”歐陽修主張,《詩經》研究應以探求《詩》之本義爲宗旨,要從蕪雜的漢唐注疏中解脱出來,直接從《詩》之原文出發,還詩人作詩、“聖人”定詩的本來面目。他辨詰毛、鄭,對毛《傳》、鄭《箋》脱離《詩經》原文的“臆説”“衍説”“妄説”“曲説”,予以批評。他指出應該“必因其信,據其義以爲説”,否則便是“臆説”(《詩本義》卷八《何人斯論》),而毛、鄭之失就在於“以衍説害義”(《詩本義》卷一三《一義解》),“妄意詩人而委屈爲説,故失《詩》之義愈遠”(《詩本義》卷一二《有駜論》)如《詩·風·静女》,他認爲是“情詩”,“據文求義是言静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彷徨爾,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貞静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捨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説耳”。這是很有見地的。尤爲難得的是,他還反對改字釋經,這在宋學中可稱絶無僅有。另外,歐陽修的易學著作除了著名的《易童子問》外,還有《易或問》《明用》《張令注周易序》《傳易圖序》《送王陶序》(一作《剛説》)、《繫辭説》多種。概括而言,其中表現了主張義理的易學傾向,而反對卜筮,反對河圖洛書,也反對以心性説《易》,認爲《繫辭》《文言》以下都非孔子所作,强調《易》主於明人事,與天道無關。歐陽修在易學疑古之風方面也有開啟之功,但他反對河圖洛書卻並不正確。[注]關於“河圖洛書”的重新評價,可參看《易學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千古〈河圖〉與八卦關係的解釋》,載《光明日報》1996年11月20日。
“宋初三先生”指胡瑗、孫復、石介三人。胡瑗,字翼之,因世居陝西路的安定堡,學者稱安定先生。他和孫復、石介“以仁義禮樂爲學”,曾於蘇、湖二州主教二十餘年,從學者甚衆,程頤亦出其門下。講“明體達用之學”,“體”是封建道德的準則,“用”爲準則的應用,注重封建道德的體用結合。對性與命亦有所闡述,認爲:“命者禀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在天者順之。”(《論語説》)開宋儒性命之學的先聲。孫復,字明復。曾舉進士不第,退隱泰山,聚徒講學,世稱泰山先生。以講《春秋》著稱,提出“尊王”爲本,著《春秋尊王發微》,認爲孔子著《春秋》之目的在於“尊王”,對擅專的諸侯“正以王法”。又著《睢陽子集》,推尊儒家道統人物,謂自漢至唐,唯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乃“始終仁義,不叛不雜”,使“聖道晦而復明”。反對佛、老“虚無報應之事”和“去君臣之禮”。石介,字守道。因隱居徂徠,世稱“徂徠先生”。官至太子中允。長期從事教育,門人衆多。著有《石守道先生集》《徂徠集》。從儒家立場出發反對佛、老,標榜王權,爲宋初加强中央集權提供論據。所作《辨惑論》,指斥佛、老,謂“天地間必然無有者三:無神仙、無黄金術、無佛”,並對宋初的浮華文風進行了抨擊。三人之中,胡瑗、孫復之影響尤大,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叙録》中對他們的學術個性作了評價與説明:“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二先生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而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又説:“泰山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
宋學的主幹
宋學的主幹是“濂”(周敦頤)、“洛”(程顥、程頤)、“關”(張載)、“閩”(朱熹)四派。而閩派朱熹是宋學(即“理學”)的集大成者。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曾官郴州郴縣令、大理寺丞、知洪州、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等。因其築室於廬山蓮花峰下十溪旁,以營道故居之濂溪名其堂,故學者又稱“濂溪先生”。後追謚元公。周敦頤的主要著作是《太極圖説》和《通書》。《太極圖説》中“説”的部分,雖只有二百五十餘字,但卻很重要,它言簡意賅援道入儒,依據陰陽之學的原理,提出與闡發了一個與佛教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論,使之成爲宋學(即“理學”)的經典文獻,周氏也就成爲了宋學的開山人物。其文甚短,全引如下: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度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度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静(無欲故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兇。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説。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説”可分爲三個層次,第一層言“太極”,第二層論“人極”,最後一層引《周易·説卦》之文,以“大哉《易》也”作結,説明《太極圖説》的思想是完全以《周易》爲依據的。周“説”的理論意義和價值有以下幾點:一是它與佛教的勢力自南北朝迅速擴大,以其特有的精微的思辨哲學和心性論向道學、儒學挑戰有關。如唐代華嚴宗大師宗密在《原人論》中就指斥儒、道二教以元氣爲本原的思想實爲淺薄,比不上佛教以本覺真心爲本原的思想,應用佛教來取代二教,説什麽“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原,則佛教方爲决了”,“寄語道流,欲成佛者,必須洞察粗細本末,方能棄末歸本,返照心原”。二是在這以前儒家研討《周易》,有的言天而不及人(如劉牧),有的言人而不及天(如李覯、歐陽修);有的雖言及天人但是從儒家的人文主義而論(如司馬光),有的言天人則自道家的自然主義而言,只有到了周氏,纔以儒爲本,吸收道家學説,特别是《老子·二十八章》“復歸於無極”的提法,又根據宋初道士陳摶之《無極圖》,提出“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以“有生於無”的精微玄妙的思想,爲儒家建構了天人結合的宇宙論和性命論的框架結構,以與佛教抗衡。其三,我們從周氏的有關詩文著作中更可以瞭解他的以儒爲本而又吸收佛、老的事實。其《讀英真君丹訣》:“始信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處更知微。”“希夷”乃陳摶的賜號,這説明周氏易學與道教有深厚的淵源。其題《大顛壁》:“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説明他不贊成韓愈之排佛,而主張對佛教應有所瞭解。他的《養心亭説》一文,更公然批評孟子關於“養心莫善於寡欲”的説法,而認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這無疑是吸收了佛教心性修養中的“無欲”主張。他還常與高僧道人爲友,流連於山巔水涯間(見其內兄蒲宗孟《周敦頤墓碣銘》)。再聯繫周氏所説“一部《法華經》,只有一個‘艮’卦可了”(《二程外書》卷一〇),可以充分説明周敦頤的以儒爲本,廣泛吸收佛、老的本色,也充分説明宋學本身實是以儒家思想爲核心而又糅合了佛、道二家思想的這一客觀的宏觀事實。
《通書》原名《易通》,一稱《周子通書》。全書共四十章,雖論述了多方面的問題,但主旨在於闡發其《太極圖説》的中心論點,論述由太極以立人極的思路,使其天道性命之學成爲完整的體系。首二章《誠上》《誠下》爲全書的總綱,而其基本思路與手法則是以《中庸》爲體,《周易》爲用,以《易》證《庸》。《中庸》曾把“誠”提高到天人關係的哲理高度來進行闡述,指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但是,這種闡述過於簡單,未作具體論證,使人不明天道何由具有倫理的性質而又以誠爲本的問題。而《通書》則對之作了簡明扼要的闡述與論證,首章以“誠”爲至人之本,純粹至善,而又引《易》以明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乃“誠”之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是“誠”之所由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就由天道而言及人性,並以“元亨”爲“誠”之通,“利貞”爲“誠”之復,最後結以“大哉《易》也,性命之原乎”,説明“誠”爲“乾”,“乾”爲天道,“誠”亦爲天道。這裏主要言天,由天而及人。第二章則説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又説“誠則無事矣”。主要言人。這就溝通了天道與性命之間的關係,通過對“誠”的闡述與演繹,爲儒家的道德本體論確立了天道自然的哲理基礎,對封建的綱常名教進行了哲學論證。自此之後,理學家言性命必上溯天道,而言天道則必下及於生命,這一理論基礎實自周敦頤始。另外,周氏還把《周易·乾卦·彖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物咸寧”的“太和”這一天人關係最高層次的和諧加以具體闡釋,他在《樂上》中認爲:“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這是説的社會人際關係的和諧。在《樂中》內又説:“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這裏又就宇宙自然的和諧而言。這種以天人整體價值觀念以言“太和”的思想與提法,對以後的理學家和一些思想家都有很大的影響,張載、朱熹乃至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都曾用以表達思想,闡述問題,雖具體所指不盡相同,但基本意思並無二致。張載著《正蒙》更以《太和》開篇,並進一步認爲“太和”即是“太極”,這無疑是受了周氏的啟示,周敦頤實爲理學的開山祖師。
程顥、程頤是兄弟,世稱“大程子”“小程子”,學於周敦頤,合稱“二程先生”。程氏世居中山,後徙河南,故二程爲河南人。因二程兄弟長期居洛陽講學,故稱其學爲“洛學”,二程同爲理學奠基人。
程顥(1032~1085),字伯淳,童年誦詩書,强記過人。曾任鄠縣、上元縣主簿、晉城令,有治績,重教化。宋神宗時,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每召見,務以誠意感動神宗。王安石雖與之議論不合,亦嘗愧服。後出知扶溝縣,又被貶至汝州爲酒監。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僅五十四歲,文彦博采衆議,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追謚純公。程頤(1033~1107),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遊太學時已爲胡安定所特契。哲宗時,官至崇政殿説書,頗多匡正,而議論褒貶無所避忌。反對王安石新政,被列爲奸黨,屢被劾,削籍貶至四川涪州,年七十五卒於洛陽。卒後追謚正公,學者稱“伊川先生”。二程兄弟著述、書信、奏章、語録等,經弟子後學整理,後人編《二程全書》,其中包括《明道文集》四卷、《伊川文集》八卷、《伊川易傳》四卷及《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經説》八卷、《粹言》二卷。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二程集》。
二程在學術和政治上相同的地方很多,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各有自己的特色。其相同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提出了“天理”這一宇宙本體和價值本體的理學最高範疇。程顥曾説:“吾雖學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外書》卷一二)“天理”二字始見於《莊子》內篇之《養生主》,“依平天理”,是指庖丁解牛的訣竅在於順著牛的自然紋理和結構去用刀,“理”,唐成玄英釋爲“腠理”。二程據此又加以改造與深化,於是成爲理學的最高範疇。其二,都反對王安石變法。其三,都反對道、佛。明道批評“老子之言,竊弄闔辟者也”(《二程遺書》卷一一),伊川批評莊子,“蓋上下、本來、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别是一處,豈有此理。”伊川批評佛云:“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學此,是被他恐動也。至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故只管説不休。”(《二程遺書》卷一)明道則云:“釋氏説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二程遺書》卷一三)其四,都爲唯心主義,其思想內也含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而伊川較爲明顯。明道認爲,“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减。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如此耳。”(《程氏遺書》卷一一)指出人們要體認這種没有單獨而必然有對待的現象存在。伊川不但也有類似的話,而且還認爲,“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程氏易傳·恒卦》),“消長相因,天之理也”(《程氏易傳·復卦》),指出並肯定了事物運動的普遍性與永恒性。同時也指出了事物有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的一面,承認事物的矛盾是事物變化的根源,“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程氏易傳·賁卦》)。但在論述社會等級關係時,則認爲,“上下之分,尊卑之分,理之當也”(《程氏易傳·復卦》),“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遺書》卷五),認爲矛盾雙方是不能轉化的。其辯證法思想最終陷於形而上學,爲封建名教綱常辯護。他還進一步認爲寡婦再嫁是大逆不道,甚至説,“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遺書》卷二二)。
二程之不同點,主要在兩個方面:大程明道著有《識仁篇》與《定性書》,前者在哲學本體上,提出“以仁爲本”,“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他認爲,天地萬物皆與“我”渾然一體,融客觀於主觀。還提出“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遺書》卷一五)的命題,强調人心與外物不可分,不應“以內外爲二本”(《定性書》)。在認識論上,强調自我修養內省,以誠爲主,宣導傳心,與天地相合,“學在誠知、誠養”,“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並其明,非在外也”(《遺書》卷一一)。後爲陸九淵所繼承發展。小程伊川則强調格物致知,窮理寡欲,“致知在格物”,“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固已近道矣”,“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遺書》卷一五)。後對朱熹的影響很大,可以説陸學近大程,朱學近小程。
二程不但學説有異,氣象亦頗不相同,《宋元學案》之《二程傳》中均有記載。大程待人接物渾是一團和氣,小程則嚴肅有加。大程與門人議論,有不合處則曰:“更有商量”,小程則直曰:“不然”。大程明道嘗曰:“異日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張載(1020~1077),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等。不久,退居南山下,教授諸生。因是關中人,故稱其學派爲“關學”。其著作元明時有散佚,現存有《正蒙》《經學理窟》《易説》《二銘》《張子語録》《文集》等。1978年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張載集》,其中《正蒙》有明清之際王夫之《張子正蒙注》。
張子橫渠一生艱苦自學,用心默會,研究天人之學。《宋史·張載傳》記述了他因其弟張戩之累辭官西歸後講學著書的情形:
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
這裏將橫渠先生爲學的宗旨、要求以及學習與生活上艱苦卓絶的情况,叙述得簡練明白,令人肅然起敬。而張氏本人更是把自己爲學一生的宗旨概括成四句名言: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這流傳極廣的名言,是據《宋元學案》所載,而《張載集》中之《張子語録》與之小異,作“爲天地立志,爲民生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第一句“爲天地立心”是講宇宙觀,也涉及人生觀;第二句“爲生民立命”是講人生觀,合起來就是講天道性命之學,也就是理學家所强調的內聖性命之學;第三句“爲往聖繼絶學”是講文化觀,要繼承往聖的心性之學;第四句“爲萬世開太平”是講政治觀,由內聖的心性之學開拓出外王的經世之學。概言之,張氏的這四句話,把儒家的“內聖外王”之學具體化了,這是他的爲學宗旨,也是他傾注一生心血研究的四項重大課題。“內聖外王”一詞,原出於《莊子·天下》:“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宋林希逸《莊子口義校注》:“內聖,體也;外王,用也。”梁任公《莊子·天下篇釋義》:“‘內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部,其旨歸在於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
第一句“爲天地立心”是説要有空納天地的廣闊心境,天心人心融爲一心。只有這樣,纔能不被逆境、困難和煩惱所困擾,而在克服艱難困苦的探索中領悟中華文化之精華。它既是宇宙觀,更是人生觀,是天人合一的。《正蒙·太和》中有一段話很重要: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王夫之注曰:“名者,言道者分析而名;言之各有所指,故一理而多爲之名,其實一也。太虚即氣,絪縕之本體,陰陽合於太和,雖其實氣也,而未可名之爲氣;其昇降飛揚,莫之爲而爲萬物資始者,於此言之則謂之天。陰陽具於太虚絪縕之中相與摩蕩,乘其位而著其功能,五行萬物之融結流止,飛潜動植,則自成其條理而不妄,則物有物之道於此言之則謂之道。此二句兼人物言之;下言心性,則專言人矣乘太虚和氣健順相涵之實,凝於形氣,而五常百行之理無不可知,於此言之則謂之性。人之有性,函之以心而感物以通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故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於聚而有間之中,統一於心,由此言之謂之心。順而言之,則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發知道;逆而推之,則以心盡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而盡心知性,則存順没寧,死而全歸於太虚之本體,不以客感雜滯遺造化以疵纇,聖學所以天人合一,而非異端之所溷也。”這裏,橫渠先生把何謂“天”“道”“性”“心”論述得言簡意賅,極爲清晰,而船山先生則根據自己的理解把“天”“道”“性”“心”是如何産生的,闡釋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由此亦可明瞭“太虚”與“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初無須討論兩者究竟是“一”還是“二”。再者,張氏還肯定了“氣”是充塞宇宙的實體,“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正蒙·乾稱篇下》)。無形的太虚也是氣,“太虚無形,氣之本體”,“知虚空即氣”(《正蒙·太和篇》),進而指出虚空乃氣分散而未聚的狀態,由“氣”聚散的運動變化而形成種種事物,認定物質的“氣”是永恒的,不生不滅的,即“形聚爲物,形潰返原”(《正蒙·乾稱篇下》)。從而批判了佛、道兩家所謂“空”“無”的觀點。還指出“一物兩體”,在太和之氣的統一體內部,存在著對立面的矛盾,是爲物質世界運動的根本原因,“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正蒙·太和篇》)。明顯有唯物辯證法的思想因素。在認識論上承認人的知覺産生於與外物的接觸,“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人本無心,因物爲心”(《張子語録》),也有一定的唯物論因素。
第二句“爲民生立命”是講人生觀,從天人合一的角度看,上面所説的天道性命之學當然是人生觀的重要部分,但從人生觀本身來看,除內聖性命之學外,還有“誠”與“禮”以及“民胞物與”之説。張氏認爲“誠”則必須遵“禮”。《中庸》重視“誠”,但未説到“誠”與“禮”的關係,唐李翱雖有所論及,但遠不如張氏説得透徹。他在《經學理窟·氣質》中説: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有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理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這裏,他把“誠”與“禮”的關係緊密結合在一起,並且指出只有兼修二者,纔能使學者“成就其身”。他還强調了“民胞物與”的思想,見於《西銘》,此篇原爲張氏書於西牗示學者之文,題爲“訂頑”,小程伊川以啟爭爲疑,改曰西銘。王夫之《張子正蒙注》:“而張子門人原合於《正蒙》,作《乾稱篇上》,今仍附之篇中,以明張子學之全體。”今節録於下:
乾稱父,坤稱母,予滋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其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鳏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可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没,吾寧也。
張氏這種“民胞物與”的精神境界,本於孔孟之道“仁者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但又將它與天道性命之學結合,“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别也”(《正蒙·誠明篇》),“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其視天下,無一物非物,心則知性知無以此”(《正蒙·大心篇》),從而達到天人合一,把自己看成宇宙的一部分,把宇宙萬物看作爲與個人脈息相通的整體,這種道德修養,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句“爲往聖繼絶學”,第四句“爲萬世開太平”,表達的是文化觀和政治觀。張氏認爲,繼承首先要有具體對象,於是他在先秦《中庸》《孟子》和唐韓愈所述的道統基礎上又提出與建立了一個新的道統,這在《張子語録》與《正蒙·作者篇》中都有論述,語録中則闡發得更爲明確: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黄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黄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舜以功,故别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這裏明確指出,作者必須是在物質生産和禮樂制度方面的創建者,而“人臣”是不能稱爲作者的,這就把道統與人類歷史的發展與文明程度的演進緊密聯繫了起來,頗有新意。其次,他提出了培養立志於聖學道統學者的重要性,“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經學理窟·義理》),也是很有見地的。
在政治觀方面,他有改革的思想,這是鑒於當時國力既殫、邊兵日弛及西夏侵擾、邊民日困的情况。但是,他與王安石的改革頗有不同,最主要在於,王安石主張“頓改”,而張氏主張“漸化”,認爲這樣可以在無形之中通其變革,人民可以在“漸化”中慢慢適應,所謂“神而化之,使民不知其所以然,運之無形以通其變,不頓革之,欲民宜之也”(《橫渠易説·繫辭下》。但是,他的具體主張卻並不怎樣高明。他主張以“井田”來利民,來解决土地不均帶來的貧富不均的問題,“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正是均平”《經學理窟·周禮》)。事實上這種“均平”是相對的,没有“采地”的農民與有“采地”的卿大夫在納貢、服役方面的負擔是大不相同的,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當然”,根本無法實現。與他的“井田”説頗有關係的,是其“封建”論,“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經學理窟·周禮》。)張氏所主張的恢復封建與唐柳宗元的《封建論》大不相同,前者批評“封建”,肯定“郡縣”制,而張氏則主張在中央集權的專制下實行分封制,他在《經學理窟》之《周禮》《宗法》二文中,極力論説宣揚以血緣關係爲基礎的宗法制的好處,但實際上説明,國家就是家庭的擴大,君臣關係就是宗子與衆子的關係,君就是“宗主”,大臣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家相。表面上似乎温情脈脈,事實上仍然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而且賦予了皇帝以更高更大的權威與更加方便的統治方法及力度。這也並無什麽值得肯定之處。另外,張氏鑒於當時死刑太濫,竟主張恢復“肉刑”。所謂“肉刑”,是指墨、劓、剕、宫等切斷人的肢體或割裂人的肌膚的酷刑,相傳始於夏代。後來隨着歷史的發展,社會文明的進步,已逐漸被廢止。西漢文帝廢除墨、劓、剕三刑,隋文帝又廢除宫刑。而張氏竟認爲,“肉刑”“此亦仁術”(《經學理窟·周禮》),這當然也是不符合歷史發展的需要,與社會文明程度背道而馳的。
由上所論,可以看出張氏的“關學”對於宋學的影響很大,他的天人合一的天道性命之學爲程朱學派所繼承發展,其“氣”論則爲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所衍申發揮,他實爲宋學的主要奠基者。就是他的不太高明的社會政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後來陳亮、朱熹也曾主張“井田”,另外朱熹在探討研究集權與分權的關係時,也曾吸取張氏關於“封建”的一些主張,也主張恢復“肉刑”。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别號考亭、紫陽。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居建陽(今屬福建),因稱其學爲“閩學”。青年時師事李侗,爲二程四傳弟子。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知南康軍、樞密院編修、秘書省秘書郎等職。朱子平生不喜仕宦,常屢召不起,以各種理由辭免。平生大多時間主要在福建崇安、建陽一帶講學著書。生活清貧窮窘,學生遠近來從學,自負糧米,常無肉菜,然不以爲意。
朱氏一生以繼承伊洛傳統爲己任,以二程思想爲基礎,又充分吸取北宋其他理學家的思想養料,從而建立了完整的、龐大的理學體系,是宋學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文化史、中國經學史上繼孔子、董仲舒以後的第三個重要人物。朱氏博極群書,自經史著作而外,凡諸子、佛學、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他在經學方面著述很多,除了在《春秋》方面没有著作外,《易》《書》《詩》《禮》《孝經》諸經和《四書》皆有著述(有的已佚,《書》類著作全佚),最重要的則是《四書集注》《詩集傳》《周易本義》和《朱子語類》。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朱子全書》,收朱氏著作二十四種,合編二十七册,一萬三千五百萬字,爲大型個人全集,網羅宏富,搜輯完備,體例嚴謹,校勘精良。朱子與他人合著的亦收入,並附有歷代文獻家對朱氏著作的著録、序跋、考訂等,頗便查閲。
朱熹在哲理指歸和經學思想方面的成就與特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在本體論中,堅持理本體,强調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源。他説:“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朱子語類》卷一)並認爲“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但是,他又從張載那裏接受了“氣”的論題,並且有接近唯物論的解釋,認爲“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朱子語類》卷一)他還説:“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類之生,必禀此理,然後有性;必禀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文集》卷一五)由此可見,朱子論“理”,極爲肯定,説“氣”也比較清楚明白。另外,再聯繫朱氏在《朱子語類》卷一中所説:“(理與氣)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説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理亦無挂搭處。氣即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朱子應該基本上屬於理氣二元論。
在宇宙形成論中,朱子無疑也有一些唯物主義的因素。他説:“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説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虚空偪塞,無非此理。”(《朱子語類》卷一)這裏説的很好,但他在回答龍行雨之説時,則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朱子語類》卷一)雨是陰陽氣蒸鬱而成,有一定唯物因素,但他又把雨分爲尋常雨與龍之行雨兩種,肯定了龍的存在,則又錯了。”“龍”是根本不存在的,“龍”的原始真實形象應是來源於星象之狀。[注]見《龍的傳人之“龍”指星象》一文,載《瞭望新聞週刊》2016年18期。他在回答動物有知、植物無知時,則有非凡的超前意識,他説:“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故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朱子語類》卷一)現代科學研究證明,植物不但有“知覺”,甚至還會“説話”,它在缺水時,就會發“牢騷”,但它比人類説悄悄話的聲音還低一萬倍,人們不戴特製耳機是絶聽不到的。[注]見《植物也會説話》一文,載《工人日報》2014年1月17日,《文摘報》2014年2月8日曾轉載。
在認識論上,朱氏强調格物致知,强調一分爲二,這些都含有合理的成分與進步的因素。他在《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中説:“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這裏,他説明認識的主體、認識的程式與認識的方法,都有唯物論的因素。他在回答《周易·繫辭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時,説:“此只是一分爲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朱子語類》卷六七)朱氏的“一分爲二”説,顯然出自《莊子·天下》中記載的惠施“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思想資料,後來邵雍和張載都提出過“一分爲二”的理念,但是,“一分爲二”的思想命題講得最簡潔明確的是朱熹,他這種世界萬物都是一分爲二的,而這個一分爲二的過程又是無窮無盡的,也是互相依存的,不是辯證法又是什麽呢?
足以説明與表現朱熹經學與文學的結合與矛盾的,是他的名著《詩集傳》。朱氏不僅攻擊毛《傳》鄭《箋》,認爲《詩序》實不可信,而且指出《詩經》中有男女淫佚之詩二十四篇,《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陳風》皆有,而《衛風》最多,占了十五篇。他批評《鄭風》説:“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但是,指斥《詩經》中有淫佚之詩,則等於承認其中有戀歌、情詩,已自脱於經學的陳説與牢囿,這實際已使經學與文學交融,承認《詩經》的文學性質與價值;然而畢竟是指斥爲淫詩,而未肯定爲戀歌、情詩,這固然出於宋代重整綱常倫理以維繫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也與朱氏本人的衛道者立場有關。這也正是宋學本身懷疑與信仰的矛盾所在,即雖然大膽疑古惑經,而最終卻走上維護封建統治的道路,並逐漸發展成爲封建專制主義新的理論支柱,趨向於反面。
最能説明朱氏經學思想與哲理指歸的,是其代表作《四書章句集注》。所謂“四書”,就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部書。《論語》爲孔子弟子及後學所記的孔子和其著名弟子的言行;《孟子》爲孟子及其弟子所記他們自己的言行;《中庸》據傳爲孔子孫子子思所作,雖是《禮記》中的一篇,但早在漢時已有單行本,後南朝梁武帝又作《中庸講疏》;唯有《大學》雖也出於《禮記》,然而不知作者姓名,兩宋以前,也没有單行本。直到朱熹,纔將《大學》和《論語》《孟子》《中庸》並列,而成爲“四書”。
朱熹成立“四書”,完全是出於當時哲理鬥爭的需要。因爲自魏、晉、南北朝、唐、宋以來,作爲印度文化主流的佛學,逐步由輸入而日益發展,它已由僧侣的尊信,漸漸深入到士大夫官僚中,引起他們探究的興味,並且逐漸動揺了當時社會的儒學的理論基礎。朱氏本人對佛學原有相當的研究,他深感僅僅靠“五經”已不能維持儒學的尊嚴,因爲“五經”裏所説到的本體論和方法論都遠不及佛學經典博大精微。要想維持儒學的主流與支配地位,非要有針對性地另尋新材料,另加新解説不可。終於,朱氏在《禮記》中找到兩篇極重要而爲前人所忽視的文章,它就是《中庸》和《大學》。朱氏認爲,《中庸》所提倡的《中》,是儒學本體論的核心,而《大學》裏所論述的“致知在格物”,是儒學方法論的主體。從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內聖外王”的一套方法論;從喜怒哀樂未發的“中”,做到發而皆中節的“和”,再達到“天地位”“萬物育”的境界,這又是儒學“內聖外王”的另一套本體論。總之,用儒學“內聖外王”的統治哲學與現世哲學去打倒佛學的“超凡入聖”的反統治哲學與出世哲學,《大學》和《中庸》是相當厲害的理論武器。於是,朱熹就説《大學》一篇有經有傳,經是孔子的話語而被曾子所轉述,傳是曾子的意見而被曾子的弟子所記録。這樣,朱熹就徹底完成了建立儒學道統的工作,即由孔子的《論語》,傳到曾子的《大學》,再傳到子思的《中庸》,再傳到孟子的《孟子》,儒學不是如此有序而真實地傳下去嗎?這也正是朱熹在後世一直被封建統治者尊崇和利用的原因。[注]詳可參看周予同先生《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中《〈大學〉和〈禮運〉》一文。
應予指出的是,朱熹的經學在國外也有很大的影響。13世紀後,朱熹經學逐漸東傳朝鮮、日本。19世紀初,朱熹經學在日本得到提倡,翻譯出版了朱氏的著作。明清之際,進入東方的傳教士,開始接觸朱子之學。19世紀中葉,《朱子全書》中的有關章節被譯成英文。朱子學對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也有相當的影響。朱子後裔在韓國竟有十四萬人之多。東渡高麗的朱氏先祖朱潜,是朱熹次子朱鉅之孫。朱潛在宋王朝即將覆亡之際,痛心疾首,攜子女及門人東渡高麗,在金羅南道錦城定居。朱潛待人接物寬厚仁慈,有朱子之遺風,朱氏後裔尊奉他爲在韓國的開基之祖,人們譽稱其居地爲“仁夫里”或“君子里”。[注]見《在韓國的孔朱後裔》一文,載《團結報》1999年3月20日。
朱陸之爭以及程朱學派、陸王學派、浙東學派
當時學者與朱熹對立者,主要爲象山學派,象山爲陸九淵之别號。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静,自號存齋,撫州金溪(今屬江西)人。於江西貴溪象山建精舍講學,學者稱象山先生。青年時主張抗金,爲“心學”創始人,與兄九韶、九齡並稱“三陸子先生”。著作經後人編爲《象山先生全集》,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陸九淵集》。
朱、陸二人既是朋友,又是論敵。在哲學的本體論、人性論及方法論上,朱陸均大不相同。就本體論而言,朱氏爲理氣二元論者,爲客觀唯心主義;陸氏則以“心”爲構成宇宙萬物的根源,斷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先生全集·雜説》),認爲一切現象都由“心”生,離開“心”則一切現象無存在的可能,爲主觀唯心主義。就人性論説,朱亦爲二元論者,將人性分爲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陸則爲一元論者,認爲性、情、才,不過爲一物的異名。就方法論説,朱主歸納,主潜修,主自外而內,主自物而心,主自誠而明;陸主演繹,主頓悟,主自內而外,主自心而物,主自明而誠。一般稱朱學爲“道問學”,陸學爲“尊德性”。實際上這又來自於《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這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朱陸各執一端,後人因以稱之。
朱陸兩大家主要有兩次爭論。第一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朱熹好友吕祖謙邀請陸九齡、陸九淵來信州鵝湖寺相會。據《象山年譜》記載,這是方法論之爭。當時論及教人,朱意欲令人博覽泛觀而後歸之於約,陸氏兄弟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九淵和九齡詩中有“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之句,朱見之不悅。次日又相致辯,討論了三天,終以意見不合而散。三年後,朱熹又和了二陸一首詩,內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之句。
第二次是在1188年,是圍繞“無極”與“太極”的爭論,乃本體論之爭。此番爭論,源於對周敦頤《太極圖説》中“無極而太極”一語的理解。朱既講太極,又講無極。陸認爲在“太極”之上加“無極”,非儒學,而是受老氏之影響(《陸九淵集》卷一五)。朱則肯定“無極而太極”乃周敦頤之本意,“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朱文公文集》卷三六)爭來爭去,也無結果。陸不談“無極”,是反對把“理”解釋爲客觀精神,因爲他的觀點是“心即理”,“心”這個主觀精神,纔是宇宙萬物的本體。
關於朱陸之異與爭,有幾點必須明確,一是朱陸兩位學術大師的關係,還是比較好的,彼此互相尊重,也常有書信來往,切磋一些學術問題。朱氏在知南康軍時,於廬山重建白鹿洞書院,曾請陸氏主講《論語》,並贊揚陸的講授內容。二是朱陸在晚年都有自悔之意,自悔所學有所偏頗(《宋元學案·象山學案》)。三是宋元之際,學術思想界有一股和會朱陸的思潮,甚至由陸入朱的學者還不少。其中鄭玉的分析較爲公允、客觀,文長節引如下:“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明;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因其質之所近而爲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耳。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玄説妙,至於魯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萎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耳。”(《師山文集》卷三《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録序》)在朱學門户中,和會朱陸的代表人物是吴澄,與鄭玉類似,他也對朱陸兩家在學術思想的宗派觀念很反感,他也把三綱五常等看作爲朱陸和會的基礎,只是把重點放在禮學上而已(《宋元學案·草廬學案》)。
宋學學派中有程朱學派、陸王學派和浙東學派之説。程朱學派是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和南宋朱熹兩學派的合稱。後人亦稱程朱理學。因兩派思想基本一致,朱熹又是二程的四傳弟子,因有程朱學派之稱。陸王學派,是南宋陸九淵和明王守仁(世稱陽明先生)兩學派的合稱。後人亦稱陸王心學。兩派之思想一脈相承,與程朱學派相對立。陸主“心即理也”之説,爲學以“發明本心”爲主;王則更爲大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説。明代以來影響很大。
浙東學派,是南宋以浙東地區爲活動中心的學派,主要又可分爲以陳傅良、葉適爲代表的永嘉學派和以陳亮爲代表的永康學派。這兩派也是朱學的批評派和反對派。反對空談心性命理,他們從文史入手,重視《尚書》《周禮》等典籍,以史學爲基本功,以文學爲表達的工具,主張政治經濟爲中心,强調事功之學。其中葉適最爲突出,他不但對子思、孟子和佛、老都進行了批判,動揺了程朱理學的基礎,而且提出了體用兼備的功利主義思想。他的理論是人性天賦論、理欲統一論、義利統一論等;而他的改革主張,則是功利主義的實際運用。他認爲,只有改革來達到去害興利,變弱爲强,才能最後實現抗金復仇的大義。他説:“夫復仇,天下之大義也”(《水心别集》卷九)。他認爲,“利惟謀新,害不改舊”(《水心别集》卷一〇)。他還建言孝宗皇帝“究古今之變,盡其利害之情,而得難易之實”(《水心别集》卷一五),主張改革除弊,以使國家富强起來。
葉適的愛國主義與事功之學,不但有思想,而且還付諸行動。開禧北伐失敗後,水心受命出鎮建康,在北兵壓江、國家危急之際,毅然採取渡江劫營的戰術,打敗了金兵,後又建立了堡塢,安頓流民,經營兩淮,建立防禦體系,以圖進取中原。然而當政者急於求和,不但不賞葉適,反而將葉削職罷歸。對於浙東學派,特别是葉適、陳亮等的思想值得深入探究。
宋學的特色、缺點及其矛盾
宋學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能融合、吸取道家和佛學的文化,特别是能吸收佛學尤其是禪宗這一外來文化,從而形成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本民族的新文化。宋學中二程、張載、朱熹這些大家都批評過、罵過釋、老和莊子,但他們也都吸納了不少佛學和莊學的文化因素,有的甚至連其中的語彙都照搬不誤,如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説:“氣坱然太虚,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朱熹則不但在好多處直接化用莊子“通天下一氣耳”的命題,而且在論“心”時的所謂心體“湛然自明”“心量廣大”、心體“萬理俱足”等説法,俱與《六祖壇經》所論相似。《六祖壇經·般若品第二》:“世界虚空,能含萬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心量廣大,遍周法界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亦可見,朱熹的這些説法與《壇經》的淵源關係。二是具有懷疑精神,有自己的哲學思想,能夠提出自己的看法,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其功績應予肯定。
宋學也有它明顯的缺點。首先,它是爲封建王朝專制主義制度服務的,宋學歸根結底是講倫常,宋學的著作從總體上説,都是明性之作,明道之作,更是明教之作。其二,有主觀臆説的成分在內,不夠重視資料,調查研究不夠。其三,小學的基本功不夠,缺乏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知識。如王安石的《字説》(已佚),講形聲字卻用會意來解釋,説什麽“波”是水之皮,實在不高明。又如朱熹的《楚辭集注》用叶韻,稱古人有叶音,而不明瞭古今音的變化,以爲古人改變字的讀音,也是錯誤的。明陳第撰《毛詩古音考》,破除古人所謂“叶韻”之説,直言古音與今音不同。又列《詩經》的韻字四百餘條,以《詩經》爲本證,以其他古代韻語爲旁證,以歷史觀點研究古音,開清代古音學研究之先河。
宋學重在懷疑,大膽提出新解,自是具有進步的因素與革新的精神,但由於它僅懷疑傳,懷疑注疏,並不懷疑經典本身,這就造成懷疑與信仰的矛盾,懷疑使其學説帶有哲理的、思辨的色彩,信仰則使其走上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的道路。朱熹雖然也曾指斥《詩經》中有男女淫佚之詩二十四篇,似乎觸及到經典本身,但那也是出於宋代重整綱常倫理的需要,而且朱熹還著有立正統、扶綱常,以修政事爲着眼點,表現其政治思想的《資治通鑑綱目》和以振綱紀爲核心,表現其倫理思想的《禮經經傳通釋》等著作。另外,宋學與先秦諸子不同,後者其時真正是百家爭鳴的時代,無所依傍(有的也有所假託),可以縱情議論,任意捭闔,提出自己的見解,發揮個人的哲學觀點。而宋學雖然懷疑傳、注疏,卻擺脱不了經的牢囿,它是藉經言以言哲學,再加上唐末五代大亂,倫常敗壞,這些時代關係的因素,和統治者的需要與提倡,遂使得宋學逐步發展成爲自己的對立面,形成新的宗教教條,成爲封建專制主義新的理論支柱,而爲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服務了。